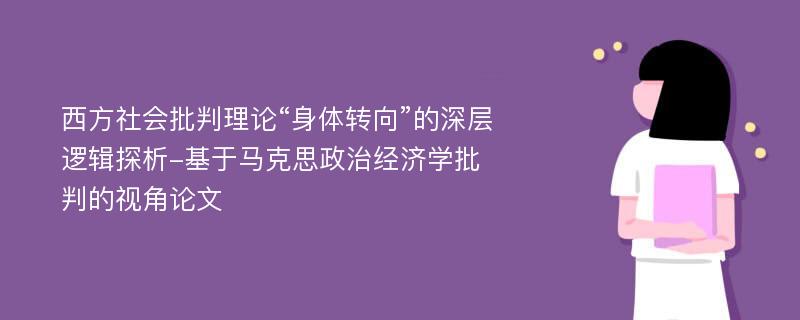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当代研究·
西方社会批判理论“身体转向”的深层逻辑探析
—— 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
王玉珏
( 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厦门361021)
摘 要: 20世纪西方社会批判理论“身体转向”的深层逻辑及其理论效应,应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加以审视,并在理论上揭示当代西方思潮中的身体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逻辑关联。从日常生活与文化观念的视域来看,身体是主体与世界的媒介,是多重力量交互建构的政治过程。身体及其社会建构性的实质,必须放到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中进行探究,并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关系再生产需要何种意义的劳动主体这个问题。从可变资本循环的生产性消费、 交换和个人消费等环节来探究身体对资本循环的重要意义,不仅可以彰显主体生产的微观视域;而且可以基于生产方式总体运动过程,深入阐发身体或主体的生产和再生产问题。
关键词: 身体;政治经济学;社会关系再生产;主体;资本积累
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身体无疑是主体理论的焦点问题。事实上,身体的塑形及其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问题,内嵌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视域之中。20世纪西方社会批判理论围绕“主体”议题呈现的各种“转向”,尤其文化与身体转向,与其说是指认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理论“空场”,不如说是将身体这一原本内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与批判这一宏大叙事中的“微观向度”,在新的时空论域中彰显了出来。以身体为焦点展开的从现当代思潮向马克思理论的回溯,并不是为了论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全面性与前瞻性,也不是仅仅为了指证历史唯物主义穿透时代的真理性,而是以身体为议题深入彰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逻辑、总体性视域及其在当代社会理论论域中的再现路径;同时,基于社会关系再生产逻辑中的“身体”这一微观视域,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主体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一、 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身体转向”与身体的社会建构性
在20世纪西方社会理论的视域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总是被限于生产劳动过程之中进行理解,而这也构成了西方社会理论家们基于时代变迁与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来指责马克思不足的逻辑支点之一。在工业革命卷席欧洲的时代,马克思更多地将精力放在对生产过程中工人所受到的剥削进行解释与批判上;而在资本主义进入“丰裕社会”的20世纪及当下,人们则将批判视角从生产劳动车间转向了大众的日常生活。随着福特制的全面推广,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过程越发呈现为一种自组织的自发结构,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带来的财富增长,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福利主义的推行,使人们越来越容易满足于当下,在消费浪潮的席卷下,沦为马尔库塞笔下的“单向度的人”。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越来越通过科学技术,将人们整合到社会生活进程中,从而顺利地编织着自身合法性的神话,实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深度(个体心理结构)和广度(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上的全面扩展。受此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远离经济和政治斗争的理论视域,转向思考大众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从而弱化了阶级问题的理论牵引力。在这过程中,阶级这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议题,也逐渐散裂为文化、性别、意识形态等议题,而身体就逐渐成了其理论的逻辑支点。
1.利端:(1)无枯竭危险,能源质量高;(2)安全可靠,无噪声,无污染排放外,绝对干净(无公害);(3)不受资源分布地域的限制,可利用建筑楼顶的优势;(4)建设周期短,获取能源花费的时间短;(5)减少楼顶受曝晒程度,对楼顶起到一定保护作用,一定程度上减缓楼顶防水层的老化。
理论视角的转移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马克思曾把一切社会形式中都存在着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特定生产方式理解为“普照的光”与“特殊的以太”,并指证了资本的扩张与再生产机制终究会越出生产领域,像普照之光那样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页。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在逻辑上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复杂机制呈现了出来。在现代社会,随着政治权力多元化的发展,资本的力量以越来越微观的方式渗透到复杂的社会结构之中,以更加隐秘的方式不断地实现自身的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中,除了生产出社会财富,还生产出不断更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绝不只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而且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更是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多次强调,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而言,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最为重要的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顺利再生产远比物质产品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更为重要。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0-451页。 因此,对任何一个社会形态而言,既要确保生产力的再生产,同时更要确保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在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领域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经济生产过程,扩展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马克思思想的后继者需要解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今天资本主义还没有遇到它的界限,反而在全球化的过程之中不断得到发展。就此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种转向,不管是身体转向、空间转向,还是语言转向,不仅是对笛卡尔的身心、主客、时空二元问题的挑战,也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问题的回应。身体转向之所以成为热点问题,其原因不仅在于身体构成了主体与世界的“媒介”,而且在于身体作为意义的承载,同时意味着一种政治性,体现了社会多重力量交互建构的过程。
1)首先根据王家会站1992—2016年最大流量,计算频率并绘制频率曲线,取频率p为10%所对应的流量10.0 m3/s为高水流量。
身体具有政治性,体现了社会多重力量建构的过程。20世纪围绕身体的理论叙事指证了一个问题,即身体具有可塑性或可变性,因此它成为权力关系的对象与政治斗争的场所。当代女性主义思想家在身体、性别、性征等问题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她们的研究对经典社会理论中的身体观提出了诸多挑战,深化了我们对身体的思考。她们不仅质疑经典社会理论中关于自然与文化的习惯性区分,而且进一步批判男性女性分别作为文化性与自然性的对峙和比较观。③ 布莱恩·特纳:《身体问题:社会理论的新近发展》,汪民安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18页。 巴特勒在其身体政治学研究中指认了身体的物质化过程及其规范的生产机制:个体在其中获取性别身份并确认自己为一定形式的主体。为了阐明这一点,巴特勒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文化的可理解性”,即性别与主体都是在文化中存在的,必须借由文化才得以存在并被人理解。以性别界划为例,“可理解的”性别是“那些建立和维系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性实践与欲望之间的一致与连续关系的性别”。④ 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23页。 除此之外,其他的性别并不具有文化的可理解性。通过巴特勒的研讨,可以看出女性主义之所以对身体理论而言是根本性的,是因为女性主义将生物、性别、性征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化了⑤ 布莱恩·特纳:《身体问题:社会理论的新近发展》,第18页。 ,也正是通过女性主义的理论建构,人们才越来越意识到,身体是被社会性地建构和生产的。
二、 劳动生产过程中的身体与主体的生产
哈维认为,只要性别、种族特征和种族划分全部被理解为是社会建构的,而不是自然形成的,那么当它们进入资本循环中时,必然会被资本主义生产所塑造、重建。⑤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第102页。 这种身体重建,必然与个体所处的阶级地位、个体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位置相关。布尔迪厄在《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中提出,身体是一种界限,更是一种区分方式,身体所显示出来的趣味与文化资本之间的关系,使身体象征成为文化资本的一个重要特征;身体成为权力的刻画空间,不同的身体趣味对应不同的阶层文化,即便是体育活动,也对应着不同的阶级。布尔迪厄所说的身体是一种阶级趣味的载体,这些趣味不仅仅是文化偏好,还是不同阶级的生活世界或习性的独特表现,彼此之间的差异成为一种社会区隔的标志。⑥ 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95-323页。 在布尔迪厄那里,身体是作为个体文化资本的一部分,身体成为社会阶级力量对比的展示空间,因而也成了权力的符号。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是一种囊括了历史、文化、自然、观念等多重意涵的总体性过程,既包括了物质与价值形态的再生产,也包含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其中最核心的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正如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所揭示的那样,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焦点问题在于生产出其所需要的“主体”,即高度契合并认同主导性社会关系的生产当事人。阿尔都塞的这一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中社会关系再生产思想的继承。马克思在理论前提上蕴含了这样的基本假设:劳动力的生产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确立、维系和扩大的重要一环,“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这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工人把他本身作为劳动能力生产出来,也生产出同他相对立的资本,同样另一方面,资本家把他本身作为资本生产出来,也生产出同他相对立的活劳动能力。每一方都由于再生产对方,再生产自己的否定而再生产自己本身。资本家生产的劳动是他人的劳动;劳动生产的产品是他人的产品。资本家生产工人,而工人生产资本家”。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50-451页。
身体是我们与世界产生关联的首要媒介,正如人类学家毛斯(Marcel Mauss)说的那样,“人首要的与最自然的技术对象与技术手段就是他的身体”。③ 毛斯:《社会学与人类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306页。 身体不仅仅是一种肉体的、生理性的存在;更是意义的载体,是人与自己周围世界和文化进行交流的重要媒介。在梅洛·庞蒂看来,身体是“我们能拥有世界的总的媒介”,不仅彰显于保存生命的必要行动或“生物学的世界”预设之中,也体现在“阐明这些重要行动并从其表层意义突进到其比喻的意义的过程”中,兼具自然意义或习惯性运动意义的身体与围绕身体这一中心的“文化世界”设计过程这两种意涵。④ 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4页。 哈维甚至将“身体”视为与“全球化”并称的两个重要概念,认为身体已然成为理解事物发展的中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事物越来越呈现出非中心化的趋势,而“身体成为一切事物的中心,恰恰是对其他所有事物非中心化的一个回应,非中心化正是由作为人类活动和思考场所的球体形象(而非二维的地图)所提出的”。①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在今天,我们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如何与自己的身体相处、如何思考和谈论自己的身体,成为我们所居住的人际世界和物质世界的核心所在。② 约翰·罗布、奥利弗·J·T·哈里斯编:《历史上的身体:从旧石器时代到未来的欧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译者序,第22页。 我们对身体理解方式的变化,不仅仅是因为生理学研究的推动,还伴随着对社会历史发展理解方式的变化。当我们叙述身体的历史时,实际上是在再现每个社会对人类身体的理解方式,是理解身体如何按照特定的社会框架演化成“正常”的身体。特定的社会理解框架与身体再现方式,意味着知识与权力的身体塑形与主体生产过程。这正是福柯探思主体生成机制的重要视角。
对工人来说,作为个人的劳动者可以是多样的,但作为经济职能与角色出现的劳动者只能是单一的,即工人只能作为适应资本主义生产要求的“合格的”劳动力而存在。哈维认为,马克思在劳动者(作为个人、身体、意愿)与劳动力(从作为商品的劳动者的身体中榨取出来)之间所做的区别,为激进批判理论提供了一个大好机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之中,劳动者必然是异化的,因为他们的创造力被资本家当作劳动力商品而占有。②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第98-99页。 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作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当事人,绝非是先天给定的存在,而是剩余价值生产的产物。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要求,催生了作为劳动力的劳动者,“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产生,是资本价值增值过程的主要产物……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对象化的劳动同时又表现为工人的非对象性,表现为与工人对立的一个主体的对象性,表现为工人之外的异己意志的财产,所以资本就必然地同时是资本家……资本的概念中包含着资本家”。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08页。
那么,对劳动力的榨取与身体的逻辑关联应如何理解?身体作为一种界限的存在,不是纯天然的存在,而是被社会环境所建构的。工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是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塑造的主体,即是一种身体主体(bodily subject)④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第98页。 。工人的身体在资本循环的过程中被生产方式所塑造,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动化的发展而得到解放,反而成为服从体系的躯体。马克思指出,人与动物之不同,就在于人有意志、能创造,能通过客体——作品的呈现证实人作为主体存活于世。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促成了文明的进步和主体的产生。然而,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及其得以展开的社会形式中,作为身体主体的工人是被资本积累的力量塑造出来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充分揭示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过程,是劳动者的身体与活力越来越依附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过程,因而也是一种身体的“献祭”史。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工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都是无关紧要的,只需要手的重复运动,就能完成工作量,就像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刻画的形象一样,机器的节律甚至内化为一种肌肉记忆。在这个过程中,工人的身体是一种被动的实体,失去了自己的创造力。马克思批评道,人的主体与对象客体两方面都不应只是作为片面的主体和“纯粹有用性”的自然对象而存在,而是必须成为人的社会的存在。马克思举例说,“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可是,“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5-126页。 马克思在这里所指出的问题是,作为个体的人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变成一个合乎生产要求的主体的问题。
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启发,福柯将这个问题转化成权力的规训力量与人的身体塑造的关系问题。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揭露了身体被权力规训的微观机制,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过程的异化问题研讨相呼应。福柯指出,规训权力对身体的活动进行了精细的规划,不仅体现在时间上的严格管控,以及对人的每一个动作和行为过程都设定了严格的时间限定;同时对人体的姿态进行反复的操练,让身体变成一个工具。“这是一个操练的肉体,而不是理论物理学的肉体,是一种被权威操纵的肉体,而不是洋溢着动物精神的肉体,是一种受到有益训练的肉体,而不是理性机器的肉体。”① 福柯:《规训与惩罚》,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175页。 以身体姿态为对象的精密设计和精确操控,让人的肉体变得顺从而有用,且可被顺利地驾驭,其本质就是将特定的个体变成符合权力关系所需的主体:“为了控制和使用人,经过古典时代,对细节的仔细观察和对小事的政治敏感同时出现了,与之伴随的是一整套技术,一整套方法、知识、描述、方案和数据。而且,毫无疑问,正是从这些细枝末节中产生了现代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人。”② 福柯:《规训与惩罚》,第160页。
自由主义向每个人承诺分得更大的蛋糕,从而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有信仰者与无神论者、土著与移民、欧洲人与亚洲人和解。如果存在一个不断增长的蛋糕,上述的和解是可能达到的。而且这个蛋糕很可能还会继续增长。然而,经济增长可能无法解决目前因颠覆性技术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因为这种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更具颠覆性的技术的发明。
无独有偶,巴特勒在对性别不平等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进行研究时也提出,性别化的身体生产就包含在社会大生产的生产方式之中。性别化的身体再生产——即对符合规范的“男人”和“女人”的再生产——依赖于资本主义社会对家庭的管制,也依赖于异性恋家庭的再生产;“异性恋家庭作为再生产异性恋的场所,生产出适合作为一种社会形式进入家庭的人……规范性的性别再生产是异性恋家庭的再生产的核心。”③ 朱迪斯·巴特勒:《纯粹的文化维度》,凯文·奥尔森等:《伤害+侮辱——争论中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页。 巴特勒指认了再生产领域是如何受制于性规则,强调了性别化的身体对经济运转的重要性:“如果这些生产对于政治经济的性秩序运行十分重要,那么把这些生产理解为‘单纯的文化领域’就是错误的,即对其运行构成了根本威胁。与再生产相联系的经济必然与异性恋的再生产相联系。”④ 朱迪斯·巴特勒:《纯粹的文化维度》,凯文·奥尔森等:《伤害+侮辱——争论中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第52页。
然而,作为身体主体的工人,真的仅仅只能是被动的主体而没有改变的可能吗?在阐明身体形塑的政治学时,福柯与巴特勒都难以避免其逻辑困境,即从作为积累策略的身体领域转换到作为政治行动者的劳动者概念,中间需要一些什么样的环节?对此,他们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回答。因此,哈维提出,我们应该扩大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的传统定义,将其置于资本的循环和积累中进行考察,从可变资本的循环过程去理解劳动力及其再生产的总体过程,在其中寻找激活身体所蕴含的变革作用的可能。与此对应的逻辑是,哈维将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劳动并将工人看作劳动力商品这一问题,转变成“可变资本(劳动力和剩余价值的榨取)的循环对它借以周转的那些人的身体(个体和主体)有什么影响”这个问题。⑤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第98、99页。 也就是说,不能局限于生产劳动过程或观念与文化层次探讨劳动者身体的塑形与再生产机制问题,而应基于可变资本在资本循环的社会总体性过程,从更大的视域去思考劳动力的身体形塑机制与主体性的再生产机制问题。
三、 作为可变资本的身体与资本积累的总体过程
还可以用梨和百合、银耳炖个甜品,如果没有糖尿病,可以加点冰糖,每次15克百合、三四朵银耳、一个梨,一起炖煮,这是一天的量,连续吃上几天,嗓子、鼻子的干热也能缓解。
1.生产性消费环节
不管是在马克思,还是在福柯、巴特勒的研究中,我们都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劳动者身体的彻底改变。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充分揭示了资本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不断地突破工人身体的界限——“道德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和夜的界限”。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20页。 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本增殖,资本主义大工业突破了传统的道德规范与约束,破坏了传统的家庭结构,将妇女与儿童作为廉价劳动力,“资本认为,在煤矿和其他矿井使用裸体的妇女和少女,而且往往让她们同男子混在一起的做法,是完全符合它的道德规范的,尤其是它的总账的,所以直到禁止使用妇女和儿童以后,资本才采用机器”。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452页。 马克思认为,身体不是一种本质主义的预先设定或自然存在,而是被特定的生产方式所塑造出来的,一个劳动者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都被其身体所承载的种族、年龄和性别划分等符号标示出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身体标示的标准是随着资本增殖的需要而动态变化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福柯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思路。福柯揭示出权力、知识与身体之间的关联,认为身体是被知识生产的。福柯拒绝以一种本质主义的方式来看待性的历史,在《性经验史》中,他研究了19世纪的性话语,借助系谱学的研究方法,认为“这些事物都没有本质,或者说,它们的本质都是一点点地从外在于己身的形式中制作出来的”,而“在事物的历史开端所发现的并不是其不可改变的源始同一性;而是对其他事物的分解”。③ 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学术思想评论》第四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82页。 正如特纳所说的,福柯的性史研究证明了19世纪性话语的出现是如何将性这一个主题进行理论化的,以及性是如何成为以理性知识的名义展开政治斗争的对象。④ 布莱恩·特纳:《身体问题:社会理论的新近发展》,第26页。
我们知道,马克思运用劳动二重性理论,以资本不同构成部分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不同作用为根据,把资本区分为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资本和以劳动力形式存在的资本,即不可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就身体(主体)的问题而言,需要研究的是,在可变资本的循环即劳动力再生产的不同环节中,资本家采用了何种方式来确保劳动力的再生产。这就需要深入资本积累的总体过程,从可变资本循环的生产性消费、交换和个人消费等不同环节探究身体对资本循环的意义。
2.可变资本的交换环节
如果说身体政治学揭示了身体的社会建构性、文化的可理解性及其社会过程本质;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则在于:我们该如何审视这种身体观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关系。这一问题须聚焦和转化为如下问题:身体的社会可塑性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意味着什么?很显然,答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关系再生产过程内在地需要并不断催生出符合其要求的劳动者身体。
总之,身体总是基于特定的历史、地理、文化和传统中,被特定的生产方式所建构。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者的创造力、爱好、情绪不是资本循环所关心的,劳动者不是作为丰富的个人存在,而是作为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存在。“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所以,成为生产工人不是一种幸福,而是一种不幸。”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5-556页。 在这种生产体系中,工人只有在作为能生产剩余价值的、可交换的劳动力商品时才有价值,而作为人所期待拥有的生活却是无关紧要的,这是异化的主体,是资本主义生产中价值循环必然的产物。一旦劳动者的身体出现了疾病、虚弱,甚至不合规训的性征,使其不能在可变资本的循环中完成剩余价值的生产,那就会变成失去了“文化的可理解性”的身体,这在福柯关于疯狂的研究中已经有所体现。
无意中,晏殊等人犯了宋代君主之大忌。宋朝自建国伊始,就吸取前朝教训,重在制定各种措施以“防弊”。宋代统治者“防弊”措施之一就是以台谏监督宰相等大臣,为有效起到监督作用,对台谏内部也订立了职事回避制度。“台谏系统内部的职事回避”之二,即“台官与谏臣不能私相往来”,“台官与谏臣禁止私下交往的原则,与台谏内部避亲避籍的用意是一致的,都是旨在预防台谏系统成为一个独立封闭的官僚圈而结党营私”。另外台谏官还有“谒禁”规定,“谒禁的根本目的是唯恐台谏官趁着出谒、受谒其他官僚之际而植党结派”[4]71、73。
如果从社会建构的角度去理解身体,我们就会看到,当劳动者的身体进入资本循环时,其作为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就与其所处的特定生产方式、传统、文化相关了。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对于身体的承受力、劳动时间的界定不是固定的,不仅依赖自然条件,也依赖文明社会中对什么可以忍受和什么不可以忍受这些道德观念的规定。“劳动力的身体界限”既包括纯粹的“身体界限”,也包括“社会界限”,后者表现为弹性的“道德界限”以及决定工人精神需要与社会需要范围与数量的“一般的文化状况”。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9页。 这种“社会界限”使劳动者身体的交换价值变得不稳定,全球化的发展更是加剧了这种不稳定性。
由于劳动者身体是被资本循环所重建的,因此工人所处的时空环境决定了可变资本的价值,又因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劳动者身体被卷入了空间上的竞争之中。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加剧了这种竞争,影响了可变资本的交换价值,资本的不平衡地理发展变成了身体的不平衡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作为人的存在以及劳动者身体的承受力和健康程度进一步被忽视,只能作为劳动力的价值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参与竞争。正如哈维所言:“通过资本循环建立特定的时空关系同样会在我们穿在身上的名牌衬衫、我们运动时所穿的耐克鞋、我们行走于上面的东方地毯,与中美洲、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只列举这些商品的一些生产点)好几万受剥削的妇女儿童的劳动之间建立一种联系。”③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第104页。
3.劳动者的消费环节
工人作为劳动者,不仅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是资本主义生产有效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工人消费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完成工人本身作为劳动力的再生产,而且消费还可以成为资本积累的有效途径。因此,工人的消费状况是资本家关注的焦点之一,甚至能影响资本家的生产安排。在当代西方社会,随着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和工人的工资增多,工人虽然拥有一定的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是相当有限的,因为工人的消费属于资本力量借以壮大的一环。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86页。
综上所述,肺消炎饮联合头孢呋辛钠治疗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疗效确切,能够有效增强患儿免疫功能,改善机体炎症状态,是一种安全可靠的治疗方案。
资本不断地制造出新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并没有变得更加自由。20世纪中期开始,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消费对资本再生产的力量渐渐显示出来。富兰克林所说的“时间就是金钱”中的时间,原本只是工作时间,现在还包括了工作外的休息时间或休闲时间。最初的资本主义生产只利用劳动时间,因此要尽可能地延长劳动时间。现在即便缩短了劳动时间,资本家仍然有利可图,因为他们可以用对娱乐业等消费产业的投资,使工人的消费成为生产的延续。消费的产品一旦离开了工厂,就变成了一种工具,其任务就是制造出人们对产品的需求,以及为扩大产品使用所必要的生活方式。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一书中对资本主义从生产转向消费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她认为普遍的享乐主义导致了普遍的不幸,劳动者没能在消费的浪潮中获得平等。① 阿伦特:《人的境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1-104页。 劳动者被各种景观符号裹挟,形成了“强迫同意”,自由主义理念强调个人可以为自己负责,人们自己所选择的生活方式是自己的“个人”选择。但实际上,正如达尼·罗伯特所说的,强迫同意使“我”将自己放置在这种应用于“我”整个人的管理话语之中。管理话语让消费者觉得,如果想要开发自己各个方面的潜能,就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尽量开发自己的资源,让这个看上去自由的“我”做出自认为是自由的选择。② 达尼·罗伯特·迪富尔,《西方的妄想:后资本时代的工作、休闲与爱情》,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174-175页。 这种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资本家为了创造出更大的利润,通过一种合理性的管理,引导劳动者进行符合资本积累要求的“理性消费”。
在列斐伏尔和鲍德里亚等人看来,这种“理性消费”背后隐藏的是,资本通过制造消费中的虚假需求来塑造主体的故事。在他们看来,消费社会的核心策略在于以隐秘的方式操控、制造并再生产人们的“需要”,使生产出来的主体高度契合消费社会的需求体系,产生出自由与自主选择的“主体性”幻觉。在这个过程中,消费是一个自足、自我再生产的体系,而主体则沦为它的产品和属性。在此意义上,身体不自觉地陷入资本设定的斗争场所,进而也是权力斗争的场域。女性主义因此提出,“身体是姿态以及美好年代以来不断涌现的知识性言论所鼓吹的价值观的承载者,也是权力的场所,尤其女性的身体更是‘管理与集体控制的重地’”③ 让·雅克·库尔第纳:《身体的历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5页。 。巴特勒用其著名的“性别述行”理论,区分了身体的物质性和身体的物质化之间的区别;女性主义则一再证明,性别作为一种社会建构,是通过服装、行为以及走路方式、吃饭方式、就座方式、站立方式等一系列日常生活中的实践而生产出来。④ 约翰·罗布、奥利弗·J·T·哈里斯编:《历史上的身体:从旧石器时代到未来的欧洲》,第364页。
总之,从可变资本循环的总体过程来看,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运动过程来看,劳动者并不真正具有对自身身体的主宰权,而是呈现为一种不稳定性,并被资本积累的逻辑所支配。劳动者身体的形成,绝不仅仅是生理的、肉体的,更是历史的、社会的,必须居于一定的政治空间中才能被理解。在资本循环的过程中,资本以各种手段按照自己的积累需求塑造劳动者的身体,并且努力使这种需求内化于劳动者的认知框架之中,铭刻在劳动者的身体之上。然而,不管是在生产中,还是在交换、消费的过程中,用以标示和区分劳动者身体的文化趣味、体力、智力、姿势等都是不稳定的,这也是为什么从泰勒制、福特制,到丰田管理体制等所谓的科学管理方法会层出不穷。正如哈维所言,身体的不稳定性永远不会消失,从而为劳动者提供了颠覆和反抗的机会。⑤ 哈维:《希望的空间》,第100-101页。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日,身体必须被视为一个诸种力量交汇的战场与矛盾过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依旧构成了我们今天理解身体的历史形成、文化再现、矛盾运动、抗争潜力及其政治意涵的基础视域与方法论原则。如此才能深入理解身体在劳动生产与日常生活总体过程中被隐性权力形塑与建构的复杂过程,从而找到改变世界的实践路径。
作为意指实践的文化: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及其评价 ………………………………… 张 谡(2.8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6CZX011); 福建省高校杰出青年科研人才计划资助项目( JYJQ201701)
(责任编辑 王浩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