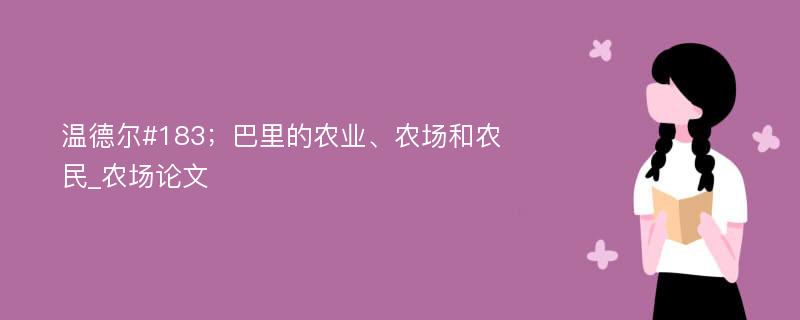
温德尔#183;贝瑞笔下的农耕、农场和农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耕论文,笔下论文,农场论文,德尔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温德尔·贝瑞(Wendell Berry,1934-)是美国当代文坛著名诗人、小说家和社会批评家;同时他也是一个小农场主。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出版小说、诗集和散文集40多部,曾获美国国家艺术和文学院奖和T.S.艾略特奖。国外对他的研究主要涉及他的农业文化思想、宗教思想以及环境保护意识。美国当代文学评论家伦纳德·西格杰把贝瑞和安蒙斯(A.R.Ammons)、默温(W.S.Merwin)以及史耐德(Gary Snyder)一起称为当代美国诗坛最具代表性的四位生态诗人。①作为当代美国文坛一位独树一帜的诗人,贝瑞把农耕、农场和农民作为他创作的重要主题。对贝瑞来说,农耕是连接他与土地的精神纽带,是他的宗教思想与文化精神理念的体现;农场是他回归自然、批判工业社会的场所,是他与自然和社会结合的特殊形式;农民是他作品中始终关注的对象。贝瑞的诗歌蕴涵着他回归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表达了他对美国农业企业(agri-business)的批评,具有深厚的农业文化意识。本文以贝瑞的诗集《农耕手册》(Farming:A HandBook,1970)和《开垦农田》(Clearing,1977)为主要文本,结合他的其他作品,探讨其农事诗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农耕:贝瑞的宗教思想与文化精神理念的体现
自然一直是诗人创作的一个重要话题,诗人对于创作田园诗歌也很感兴趣。自古以来既长期从事农耕活动又不断创作农事诗的著名诗人相对较少,贝瑞不仅长期亲自在地里劳动,还写了许多关于农耕的诗歌。这些农耕诗除了描写平时的农场劳动以外,还揭示了农耕活动的精神和文化内涵。在贝瑞的农耕诗歌中,泥土是他关注的重点。他在多首诗歌中描写了泥土所蕴涵的宗教意义,并从基督教的角度看待泥土与生命的关系。在《流动》(“The Current”)一诗中,诗人写道:“将双手扎入泥土,/在那里撒播种子,希望的种子让他的生命经久不衰,/与土地结合,如同婚姻/如果他离开土地,肉体的疼痛会让他回归。/放开手中鸟儿,/像根一样扎入黑暗,/土地在永恒中苏醒,迅速而又漫长。”②贝瑞把他和土地的关系看作“如同婚姻”,通过播种和耕犁,诗人接触泥土,泥土在他眼里成了物质世界的象征和价值观的依据。“作为一个亲历耕作的农民,贝瑞坚定地认为农耕生活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体现了一种生命的价值。”③现代社会的工业化使得人灵肉分离,要消除这一现象,关键是要恢复个体与社会、人类与土地间的结合,而最能实现这种结合的活动就是农耕。回归泥土的意义不仅仅是拥有农田或农场,而是一种可以使灵魂和身体保持一致的生活方式。在《身体与土地》(“The Body and the Earth”)一文中贝瑞写道:“我们来自泥土,也返回泥土;因此,我们生活在农耕中就像我们生活在肉体中。”④
在诗集《农耕手册》的开篇之作《生来务农的人》(“The Man Born to Farming”)一诗中,贝瑞直截了当地说他“生来就是一个农民,/他的手触碰着土地,使其生根发芽,/泥土是一种神圣的药。/每年他走入死亡,然后快乐地复活。/他看到闪亮的光照射在一堆粪便里,又在谷物中浮现。/他的思想像田鼠一样穿越田埂,/他吞下了多么神奇的种子/口中洋溢着无数的充满爱意的话语。”⑤诗人让读者感到每一寸土地都是神圣的,“是一种神圣的药”,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在基督教文化中,“闪亮的光”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耶稣诞生时东方出现的亮光,具有神秘的宗教色彩。贝瑞或许表明农田里的肥料其实暗藏着“神启”或“天机”,因为有生命就有消化和排泄,没有粪便这样的自然养料,农田就会贫瘠,就不可能在田里长出“神奇的种子”。因此,农肥暗示了一条朴素的生态真理。农民把手插入泥土不仅是为了爱抚土地,而且是为了让土地给他带来新的生命。“走入死亡,然后快乐地复活”揭示了诗人的生态宗教死亡观:死亡意味着复活和新生,死亡是一种快乐,没有死亡的世界是一个可怕的世界。反过来说,正是因为有死亡,才有大地的荣枯交替和万物的“生根发芽”,生命的美才会永存。贝瑞在《动荡不安的美国》一书中写道:“没有死亡和腐朽就没有新的生命,死亡催生了新生命的诞生。”⑥他试图在农耕活动中通过颠覆永恒来肯定死亡,并且把以土地为支撑的生命和死亡的规律看成是美的原动力,二者共同促动自然之轮的滚动,任何一方的缺席都会使之停止运转。
贝瑞认为,农耕的本质是一种文化,一种能够把个体和社会、历史和传统联结起来的文化精神。因此,贝瑞笔下的农耕诗歌不仅具有宗教意义,而且体现了人类生存的精神力量和沉重的文化历史感。在《夜晚的山》(“On the Hill Late at Night”)中,贝瑞写道:“非常愿意置身于/闪亮寂静的繁星和倾泻满地的绿草之间/对我来说,山像一只脚。/我寸步难行,/直到我抓起这把泥土。”⑦虽然大山使他行走艰难,但泥土给了他向前的精神力量。正如泰戈尔所说:“土地不仅能够支持人的身体,还能给他的心带来快乐,因为它的接触不仅是表面感受到的,它是一种生机的表现。”⑧在《灾年之歌》(“Song in a Year of Catastrophe”)中诗人表达了同样的声音:“一个声音告诉我,把双手插入泥土,/与土地结合。/我走过去,把双手插入泥土中,/它们生根发芽/获得丰收。/透过厚厚的树叶,/听到了我出生前消逝的声音。/我懂得了黑暗。/像一个绝望的游泳者一样沉入泥土,/最后却找到了安逸和快乐,/找回了我所有失去的东西。”⑨贝瑞认为,“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在生物和生态角度上讲是一种必然,所以接受死亡成为一种精神上的职责,这是唯一一种使生活完整的方式。”⑩在《播种》(“Sowing”)这首诗中,诗人把自己置于这片土地的历史以及这个世界的命运之中:“在这个宁静的地方,有条河流,/这里建了房子,蓄水池和谷仓,/这里长着野花野草,石头围墙微微倾斜,/……/后来大火吞噬了这里的一切,/我拿着沉甸甸的种子来到这里,/在光秃秃的山上播撒着绿色生命的源头。/我播撒下三叶草和牧草的种子。/历史上死亡阴影曾笼罩着这片土地,/树木将获得重生,/我提出要求并且付诸行动,/和这个世界的命运融为一体。”(11)贝瑞重视这片土地的历史是因为传统农耕思想在他心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他认为,传统的一个作用是“传达人的本质的永恒性以及作为生命之根本的一些必要的价值概念”。(12)传统不仅存在于过去的历史中,它更存在于现实的生活中。尽管现代传统农耕生活有种种局限和缺点,但贝瑞把传统农耕看做一种文化。在文集《人们追求什么?》中,贝瑞强调了农耕过程中泥土的生态文化意义。他认为泥土的循环过程与人类文化生活有着微妙的相似:“万物生长、死亡、埋葬和腐烂这个缓慢的过程已经在地球上形成了数英尺厚的腐殖质。我在森林中的山顶上也看见过同样的过程……万物消亡与泥土融为一体,却又依靠泥土生存。”(13)在贝瑞看来,农耕和生态是两个平行的概念,生态学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耕作这一行为:“农业并不只是意味着生产,还包含着农作物腐烂后埋入土地中这一生态现象。”(14)农耕活动并不只是一种经济现象,它还是一种生态行为,这一行为使每个人都能感知到自己与自然的关系。看到农场一棵大树上挂着的一只旧铁桶,贝瑞联想到了泥土、文化传承以及创作三者之间的关系:
它是一个标记,我通过它来了解我的国家,了解我自己。在我看来,这个旧铁桶有着不可抗拒的暗示性,它收集随着时间流逝而飘落的树叶以及树林里的其他飘落物。它还收集那些随着时间流逝而留下来的故事。它的隐喻性无法抗拒。它正用一种消极的方法做着人类必须积极主动并深思熟虑来做的事情。人类社会也需要收集树叶和故事,并把它们表述出来。人类社会同样必须培育土壤,依靠泥土,并在传说、故事、歌曲里建立属于自己的记忆。这将成为人类的文化。(15)
农场:贝瑞回归自然、批判工业社会的场所
1964年,贝瑞毅然抛弃都市生活,回到故乡肯塔基州的农场。《回乡》(“Returning”)一诗就表达了诗人回到农场的心情:“在草丛和树叶之中,/我听到轻轻的歌声/……那里是我的家,/它耸立在这片土地上/小河流过这片土地。/无限的光辉洒在草地上,/仿佛春天已来到。”(16)重归故土,又见祖居,贝瑞以愉快的心情根扎家乡。《开垦农田》不仅描写了诗人对农场的感情,而且还描写了农场上的动植物等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小鸟,蝴蝶和鲜花,/从我的身躯里的各个季节穿过。”(17)贝瑞笔下的农场生机勃勃,是一个健康、稳定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里的每个生命——小鸟、鲜花、蝴蝶以及人类都展示了自然生态的内在价值。大卫·依格纳托指出:“贝瑞对农场的感情如此深厚,以至人们可以从他的诗歌中感觉到爱和被爱的奇妙和谐感觉。”(18)这种恰似美好婚姻的结合关系存在于他和土地之间,也体现在他和农场的一草一木之间:“与天地同在,/光和雨结合,溶解,/然后再次结合,/成为大地的形式和行为。”(19)在贝瑞的眼里,“和天地同在,/与光和雨结合”表达了生命的和谐形式;农场上的一草一木都有自己的循环过程和生命规则。即使“坟墓出现在眼前的农场上/灵魂最后的轨迹/不知走向何处”,(20)诗人仍然认为死亡意味着回归泥土,回归大自然。
在《梧桐树》(“The Sycamore”)一诗中贝瑞明确表达了他与农场这片土地的关系:“在其中我意识到一种原则,一种栖居意识/与大树相比,/大树更伟大,/我将以其为生活依据。/它耸立在那里,/汲取泥土的养料,/被滋养着,一个创造者。”(21)梧桐树的树根与泥土紧密相连,梧桐树与土壤有共生关系,它们彼此支撑。通过描写梧桐树与当地环境相结合,贝瑞揭示了他放弃都市生活来到乡间农场的感受,表达了他的“地缘感”。劳伦斯·布依尔认为:“地缘感体现了人们对所在地的地理性、社会性与地缘性的体验,表达了个体对环境的主观感受,反映了人们热爱家乡、希望诗意地生活在某个地方的环境意识。”(22)贝瑞曾说:“如果我们不了解一个地方,不热爱一个地方,我们最终会糊里糊涂地毁了这个地方。”(23)在辞去纽约大学教授之职回到故乡后,他如此谈及自己的感受:
在与这块土地的关系上我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前,说这块土地是我的只是由于偶然或碰巧;现在是由于选择它才成为我的土地。一开始我做出回家的选择是犹豫不决和试探性的,后来就变得一心一意和完全有把握了。我来这里是要留在这块土地上的。我希望在这里度过我的余生。这一思想确定下来后,我开始用一种新的定义、新的理解、新的真诚来看这块土地……我发现了它的富饶、它的历史以及它潜在的无限价值。(24)
对贝瑞来说,人在本质上是一个创造者和一个道德人,人只有在与周围的地理空间(土地)和社区的联系中才能完善其人性。有人将这种观念称之为“关于人的本质的生态观念”。(25)可以说,对土地的热爱加深了贝瑞对农场这个“家”的归属感。他的个体身份与文化认同与这种根系于一地的场所归属意识密不可分。贝瑞对自己生活的“地缘”负有责任,这样的态度也体现在他与农场互为关怀的关系上。贝瑞最后描写了梧桐树的枯萎和死亡,旨在表明农场在被无情的使用中丧失了人的关怀,农场的土地与人互为异化,而这正是现代社会人把世界和自然对象化从而使自己更加孤立的症结所在。
贝瑞对农场的情有独钟与美国当今工业社会对农业文化的破坏有关。1934年贝瑞出生时,全美共有大约680万个家庭农场,而到了1975年,这种家庭农场只剩200多万个,(26)商业农场的面积却与日俱增。这一变化既有工业发展大势所趋的客观因素,也有美国政府刻意制订计划的主观原因。贝瑞在小说《回忆》中通过主人公安迪的经历明确指出,工业化农场的单一作物、单一的机械化耕作方式、单一家庭和单一的思维,导致了社区和自然的消失以及工业化农场主们精神健康问题的出现,因为对支付巨额贷款的忧虑让他们患上了各种精神疾病。在贝瑞看来,这种农耕方式与杰斐逊主张的保持自由、独立的农耕方式相违背。在《动荡不安的美国》一书中,贝瑞分析了“作为性格危机的生态危机”、“作为农业危机的生态危机”和“作为文化危机的农业危机”。他指出:“由于人们越来越不知节俭、惜福……现在的农业侵蚀着表土、水资源、石化燃料以及人力资源等,且毫无悔意。”(27)他强调:“不论日常生活多么都市化,我们的躯体仍必须仰赖农业维生;我们来自大地,最终也将回归大地,因此,我们的存在基于农业之中,无异于我们存在于自己的血肉之中。”(28)工业化不仅使贝瑞小农场主的农耕理想破灭,而且也使自然美和人类的生存环境遭到了破坏,诗人心目中那种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生活方式一去不复返了。1992年,美国一家广播公司的主持人问贝瑞,为什么他的农场只有马而没有拖拉机,贝瑞明确回答:马不会污染空气,它们的粪便可以作为土壤的肥料,它们通人性并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快乐。(29)他在《马》(“Horses”)一诗中这么写道:“……拖拉机开来了。/马站在田里,像一件赠品/变老,死去,/或者像狗肉一样被卖掉。/我们的头脑接受了发动机的革命/我们的思想麻木地忍受着金属。……机器发出长长的音节,震耳欲聋/我们的耳边/不再响起人间的歌声。”(30)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梭罗式的生态环境思想。事实上,贝瑞并不是完全拒绝接受所有的新科技,他希望我们扪心自问:每一次科技革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不利影响?贝瑞认为,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自由”并非是指不受限制的个人自主,而是指应该遵循哪些选择,应该承担哪些社会责任。贝瑞回归农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类似梭罗回到瓦尔登湖的举动。当社会的所谓“发展”造成人与自然分离时,贝瑞试图借助农场来寻求一种文化上的解决手段,最终目的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
农民:贝瑞作品中始终关注的对象
农民一直是贝瑞作品关注的对象。他的许多诗作不仅描写了农民朴素的田园生活,而且还向读者展示了他心目中的理想农民;同时,他还通过“疯狂农民”(The Mad Farmer)这个形象揭示了农民对当今社会的不满情绪。
在《致西伯利亚樵夫》(“To a Siberian Woodsman”)一诗中,诗人首先描写了樵夫晚上回家后与儿女在一起的幸福生活:“晚饭后的家是那么温馨,/女儿演奏的风琴是那么动听。/你的微笑/显示出一个男人的信心,/在森林中你劳动一天,/头脑中出现锯木头的声音,还有那回家休息的憧憬。/餐桌旁你和儿子一起……”;然后,诗人比较了他和这个西伯利亚樵夫的不同生活,认为樵夫和大自然有着更加密切的关系;不过,诗人又强调:“我是这片土地的化身,/我之言语正是土地之言语,正如鹪鹩之歌就是大地之歌”,(31)流露出对大地的真挚情感。在《渴望和平》(“The Want of Peace”)这首诗里,诗人向人们展现了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美好愿望:“一切回归泥土,/我不追求过度的傲慢和权力,/只要求知足常乐:渔夫的沉默得到了河流的幽雅,/园丁在一排排的树木中聆听音乐/渴望那朴素的宁静。”(32)《野外的宁静》(“The Peace of Wild Things”)则展现出一幅充满希望的图画,人们忘记哀伤,尽情享受野外的宁谧:“我躺在树林中,林中的鸭子躺在水上,/野鹭在寻食。/我享受野外的宁静……等待着夜晚星星的出现。”(33)贝瑞所处的时代是人和自然脱离的时代,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如环境受到破坏、贫富差距的悬殊、人际关系的冷漠、对物欲的过度追求等,人们因此渴望找到一个宁静的家园或精神寄托。《站立》(“Standing Ground”)描写了农民坚定地站立在农田里,在平静的土地上证明自己的价值:“完全在黑暗中/静静地寻找着自己的出路。”(34)《春雨中冥思》(“Meditation in the Spring Rain”)以深沉的笔调叙述了一个“疯狂的农妇”,她秉持“一个上帝、一种信仰、一块玉米面包”的信念,“她亲眼见证了/在此矗立的原始森林”。看到这样一个农妇,诗人感觉到“他的思想在山体中涌动”,希望自己的“语言有分量,/变得优雅,/如山川般高耸,/厚重,/由此生命得以提升”。(35)在《农耕手册》的结尾,贝瑞表达了农民与诗歌创作的关系:“他所有的语言都为艺术服务,/敞开一个女人的身体或开垦一块地使他被接受。/他的话语将化作叶子,/以无声却迅速的反应回应太阳。”(36)
在诗集《车轮》中,诗人把一系列诗作献给了他的农耕指导者欧文·弗鲁德。弗鲁德是贝瑞心目中的理想农民形象。他很普通,但却很真实。诗人在《升起》(“Rising”)中这样描写他:“这些日子/这个男子因他佝偻在地里的后背/而众所周知,/他带领着我,虽然带着许多悲伤,/在我面前他像一名舞者一样移动着,/他是那么的兴高采烈,那么能干,/他心中充满着让土地成长的渴望。”(37)弗鲁德告诉贝瑞如何把劳动的“痛苦”转变成带有物质和精神意义的“享受”。作为诗人心中的完美人物,弗鲁德“靠种子穿越几个世纪”,他的生活或许是一种在田间小路来回往来的旅行,一年一年循环往复。以弗鲁德为代表的农民在精神上是乐观的,他们在传统的农耕中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和价值。面对现代社会的侵扰,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无助,他们是快乐生活的提倡者;他们并不孤单,因为他们与土地和自然建立了亲密关系。
贝瑞在《农耕手册》和《开垦农田》等作品中描写的另一个农民形象是“疯狂农民”。他是作者笔下一个热爱土地,熟悉农耕,敢于和工业资本家作斗争的现代农民。贝瑞借这个形象表达对美国农业企业的不满。在以“疯狂农民”为标题的几十首诗歌中,《宣言:疯狂农民解放阵线》(“Manifesto:The Mad Farmer Liberation Front”)揭示了工业社会中农民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当他们需要你消费时/他们会来找你。/当你为了他们的利益死掉时/他们会来找你。”(38)在《疯狂农民解放阵线宣言:第一修正案》(“The Mad Farmer Manifesto:The First Amendment”)中,诗人首先引用杰斐逊在1785年写的一封信中的话作为诗歌的“序”:“……我们应该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小规模的农场。小农场主是国家最宝贵的部分。”然后,他用批判的笔调描写了小农场主们的命运:“来自权力与金钱的联盟,/来自权力与秘密的联盟,/来自政府与科技的联盟,/来自科技与金钱的联盟,/来自野心与无知的联盟,……/迫使疯狂农民悄悄地离开了土地。”(39)从美国历史发展角度来看,贝瑞的思想透露了一种传统的美国社会政治理想,即杰斐逊曾倡导的美国式的农业民主。杰斐逊认为:“土地的耕作者是最有价值的公民。他们最有活力,最具独立精神,最守道德,他们与这个国家休戚相关,与这个国家的自由和利益永结连理。”(40)那些较小土地的拥有者是这个国家最珍贵的部分,是他们使这个国家免于腐败,人民身心健康。贝瑞在很多地方进一步阐述了杰斐逊的这个观点。同时,贝瑞始终关注农民是因为“一个好的农民是一种文化产品;他是经培训而成就的,他身上体现了时代人的要求,也是几代人的经历造就了他”。(41)在高度工业化的美国,贝瑞描写农民的诗歌带给我们另一种声音,这些诗引导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生存的方式和生存的价值。
贝瑞在他的一生中扮演过许多角色:他是长年倡导永续农耕的智者、道德与传统的拥护者、拒绝使用拖拉机的著名农人、反对用电脑写作的作家。但就他自己来说,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农民,是一个诗人。何谓诗人?乔纳森·贝特在《大地之歌》中回应说:“他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虽然他们经常试着去解释这个世界和人类在其中的位置。他们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家,至少从19世纪以来,他们主要的关注点不是用说教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如何生存。但是,在他们明确表达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存在与栖居的关系时,他们的作品通常具有独特的明晰性或启发性。”(42)20世纪70年代以来,贝瑞越来越关注生态环境问题。正如他在《远景》(“Vision”)一诗中所描述的那样,他创作的关于农耕、农场和农民的诗歌表达了当代人们渴望诗意地栖居在这个世界上的愿望:“……推开窗看见肥沃的田地和花园,/河里流淌着清澈的水,鸟鸣声像华盖一样笼罩在河流的上方。/山坡上/芳草如茵,午后的树荫下停歇着拴上铃铛的牲口。/……每家每户都将在土地上歌唱。/……这片土地的丰硕,人们和鸟儿的歌声,/将会成为健康、智慧和内心的光亮。”(43)
注释:
①参见Leonard M.Scigaj,Sustainable Poetry:Four American Ecopoets(Lexington: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99)129-174。
②Wendell Berry,Farming:A Handbook(New York:Harcourt,1970)43.
③金衡山:《回忆与愈合:当代美国作家贝瑞及其小说〈回忆〉》,载《北京大学学报》(外国语言文学专刊)1999年S1期,第121页。
④Wendell Berry,The Unsettling of America:Culture and Agriculture(San Francisco:Sierra Club Books,1986)97-98.
⑤Wendell Berry,Farming:A Handbook,127.
⑥Wendell Berry,The Unsettling of America:Culture and Agriculture,193.
⑦Wendell Berry,The Collected Poems,1957-1982(San Francisco:North Point,1985)113.
⑧泰戈尔:《正确地认识人生》,刘竞良译,见《泰戈尔全集》第19卷,刘安武、倪培耕、白开元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6页。
⑨Wendell Berry,Farming:A Handbook,161.
⑩Wendell Berry,Recollected Essays:1965-1980(San Francisco:North Point,1981)199.
(11)Wendell Berry,The Collected Poems,1957-1982,104-105.
(12)Wendell Berry,Standing by Words(San Francisco:North Point,1983)14.
(13)Wendell Berry,What are People For?(New York:North Point,1990)153.
(14)Wendell Berry,A Continuous Harmony(New York:Harcourt,1972)104.
(15)Wendell Berry,What are People For?,153-154.
(16)Wendell Berry,Clearing(New York:Harcourt,1977)4.
(17)Wendell Berry,Clearing,5.
(18)David Ignatow,"Review of Wendell Berry's Clearing," in Partisan Review 44.2(1977)317.
(19)Wendell Berry,Clearing,42.
(20)Wendell Berry,Clearing,43.
(21)Wendell Berry,Openings(New York:Harcourt,1968)65.
(22)Laurence Buell,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Cambridg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64.
(23)Wendell Berry,A Continuous Harmony,104.
(24)Wendell Berry,The Long-Legged House(New York:Harcourt,1969)177.
(25)James Campbell,"Personhood and the Land," in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1(1990)39.
(26)http://www.grist.org/comments/soapbox/2004/10/20/berry/?source=daily.
(27)Wendell Berry,The Unsettling of America:Culture and Agriculture,12.
(28)Wendell Berry,The Unsettling of America:Culture and Agriculture,127.
(29)Leonard M.Scigaj,Sustainable Poetry:Four American Ecopoets,129.
(30)Wendell Berry,The Selected Poems of Wendell Berry(Washington D.C:Counter Point,1998)121-122.
(31)Wendell Berry,The Selected Poems of Wendell Berry,61.
(32)Wendell Berry,The Selected Poems of Wendell Berry,29.
(33)Wendell Berry,The Selected Poems of Wendell Berry,30.
(34)Wendell Berry,The Selected Poems of Wendell Berry,116.
(35)Wendell Berry,The Selected Poems of Wendell Berry,77.
(36)Wendell Berry,Farming:A Handbook,179.
(37)Wendell Berry,The Collected Poems,1957-1982,241.
(38)Wendell Berry,The Collected Poems,1957-1982,151.
(39)Wendell Berry,The Selected Poems of Wendell Berry,89.
(40)转引自Wendell Berry,The Unsettling of America:Culture and Agriculture,143。
(41)Wendell Berry,The Unsettling of America:Culture and Agriculture,51.
(42)Jonathan Bate,Song of the Earth(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251-252.
(43)Wendell Berry,The Selected Poems of Wendell Berry,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