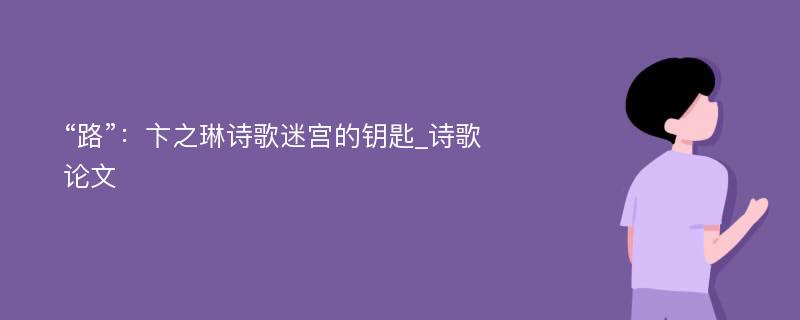
“路”:开启卞之琳诗歌迷宫的一枚钥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枚论文,迷宫论文,诗歌论文,钥匙论文,卞之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上承“新月”、下启“九叶”的现代派诗人卞之琳,其苦心结撰的诗歌的确像一座迷 宫。正如有的论者说的那样,卞之琳的诗歌“是个充满诱惑而又难缠的话题”,从没有哪个 诗人如此“让人评说起来倍感艰难,歧见迭出”。这也就说明了卞之琳的诗歌文本具有一种 内在的丰富性和艺术魅力,让人们可以作多种解读。当我们从“意象”的通道进入卞之琳的 诗歌世界时,似乎有一种柳暗花明、豁然贯通的感觉。卞之琳的诗笔下固然出现了许多意象 ,有的论者曾将他的诗歌意象分为古典型、日常型和现代自然科学型三大类这是一种比较系 统的归类分析。那么这个意象系统中有没有中心意象呢?当我们在卞之琳诗歌的意象建构中 搜 寻时,我们惊喜地发现诗人醉心于这样一个充满古典气息而又具有现代意味、缠绕人的外部 生活而又直指人的的心灵深处的意象——路!横亘而出,绵延而来,“路”以及它的同一形 象“街”、“桥”,以及大量的衍生意象如足迹、身影、车站、家园等便拼贴出“人”的生 存境遇和生命体验。“路”与“人”构成的人生道路、心灵归宿问题成为了卞之琳诗歌的最 重 要的主题表达,这是他区别于他同时代诗人的独特之处。
一
在卞之琳的诗歌中,“路”的意象主要包含以下三种涵义。
第一,人生苦闷的“路”。孤独、寂寞、空虚、迷惘,如影随形,在人生的路途上堆积、 蔓延,使人感到压抑甚至窒息。这种种内心情绪的体味和铺排,既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对 人生道路的限定,又是生命本源中的哀感伤痛在人生旅程上的涌动。
这样一种情绪基调,就决定了人生脚下的“路”是黯淡、凄清和荒凉的,而且环绕周围的 也往往是寒风冷雨、黄昏夕照。于是我们看到诗人在“冷清清的街衢”撑着伞“走向东,走 向西”(《一城雨》),在“夜雨”中“灵魂踯躅在街头”眼含着热泪(《夜雨》);我们听到 诗人无限伤心的叹息:“伸向黄昏的道路像一段灰心”(《归》),“秋风已经在道上走厌” (《落》)。而有时候是在“戏剧化的情境”中客观展示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人生:有秋风里“ 冷静的街头”胡琴的哀愁伴着的“行人”(《胡琴》),有“在街路旁边,深一脚,浅一脚” 消磨着时光的“闲人”(《一个闲人》),有“在荒街上沉思”的年轻人(《几个人》),有“ 在夜心里的街心”彷徨的梦游者(《夜心里的街心》)。这样,既写出了诗人的独自沉吟和彷 徨,又刻画了芸芸众生的普遍的生存图景;既有对自己心灵和前景的凝视,又有对底层社会 小人物的关注。
不仅如此,深刻的痛苦还来自于对“生命旅程”的打量。诗人常常把诗歌情境安设在“秋 天”和“黄昏”,在徘徊中由眼前的“路”想到生命的渺茫、虚弱和负重,因而生出无限的 哀怜和痛楚。在《长途》一诗中诗人写道:“一条白热的长途/伸向旷野的边上,/像一条重 的扁担/压上挑夫的肩膀。”这条“路”浓缩了生活的全部艰辛和生命的所有负荷,与漫无 边际的生命历程纠结在一起。在《长的是》、《西长安街》等诗歌中诗人一再感叹这“道儿 ”“觉得是长的”,于是不得不从内心深处迸发出“好累啊!”(《距离的组织》)的哀叹。 这一声叹息有如落叶既是对“冷清的秋”的回应,也是对“灰色的路”的抚摸,因而人生苦 闷中融进了社会的和生命自身的深刻内涵。
第二,心灵追寻的“路”。诗人不是在“好累啊”的感叹中倒下,而是“倚着一丛芦苇”( 《 落》)坚持,怀抱着“远方”,怀抱着“家”赶路、疾行。如地下涌泉,似山间潜流,诗人 心中始终流淌着“梦”的乳汁。“不用管能不能梦见绿洲”,诗人仍在辛苦地“远行”(《 远行》)。《夜雨》中写道:“他还驮着梦这娇娃,/走一步掉下来一点泪,/还不曾找着老 家呢,/雨啊,他已经太累了,/但怎好在路上歇下呢?”这个“远方”,这个“家”是什么 呢?诗人没有也无法明言,只是在某些诗篇中将其描绘得更形象生动。“就是此刻我也得像 一只迷羊,/带着一身灰沙,幸亏还有蔚蓝,/还有仿佛的云峰浮在缥渺间,/倒可以抬头望 望 这一个仙乡。”(《望》)这一片“蔚蓝”,这一个“仙乡”,与其说是世俗生活的幸福住所 ,不如说是心灵世界的美好家园。正是这种现代人对精神家园的寻找,才使得诗人在“夜雨 ”中“驮着梦”跋涉。这样,“回家”、“还乡”在卞之琳诗歌中就赋予了特别的含义。
正因为这样,诗人在抵达家园的道路上就渴望留下“足迹”。短诗《足迹》由蜜蜂想到自 己的足迹,为没有在人生的道路上留下深深的印迹而责问自己。而在《路》中,诗人这样表 白道:“路啊,足印的延长,/如音调成于音符,/无声有声我重弄,/像细数一串念珠。” 通向“家园”的“路”是美好的,也是艰辛的。诗人不仅渴盼在“路”上一步一步留下足印 ,而且深知要到达远方就必须具备足够的耐心和韧性。这也就不难理解,在卞诗中一再出现 “骆驼”的形象。《夜心里的街心》借“街心”对彷徨的人倾吐:“我最爱/耐苦的骆驼/一 抚/便留下大花儿几朵。”《远行》中写“乘一线驼骆的波纹/涌上了沉睡的大漠”。“骆驼 ”成为诗人走出“沙漠”接近“家园”的理想形象。
有了这样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换一种思路来看待卞之琳的某些诗歌。比如被视作经典的袖 珍 诗歌《断章》,一般人都认为表现的是一种相对意识,但笔者认为它传达的是人生旅途上的 “家园意识”。“桥”——“路”的另一种更雅致的形态;“风景”,可以解作卞诗中出现 过的“仙乡”亦即美好的精神家园;“明月”和“梦”以其明媚轻柔的光辉照亮了人的心灵 世界。于是一切都变得这样美好,这样诗情画意。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显得温馨浪漫 ,呈现出一派大的和谐。人们已经步入了人类历史长河中这样一个美丽的“断章”,这样一 个 诗意的“瞬间”!
那种认为卞之琳的诗歌“呈现为生活的无意义、灵魂的无归宿”的观点应该说没有很好地 把握卞诗内心的节律和脉搏的跳动。卞之琳虽然写了人生道路上的彷徨、迷惘和苦闷,但是 传达出的并不是混乱无序和消极颓废,诗人的手指直指苍穹的“蔚蓝”,诗人的眼睛凝望远 方的“仙乡”,有“明月”装饰心灵的窗子,有“绿洲”出现在梦中。诗人久久地等待、苦 苦地跋涉和寻找,就是因为生活以其光亮穿透了黯淡,心灵的追寻以其朦胧的诗意映照着“ 灰色的路”,诗人确信在这个风雨世界的背后有一个云蒸霞蔚的天空!
第三,慧心深蕴的“路”。正如许多论者指出的的那样,卞之琳是一位“主智”的诗人。 抒 情成分的消失在卞诗中意味着智性成分的增加。在卞之琳诗歌中,“路”不仅成为了诗人 思索人生道路、心灵归宿的载体,而且也成为了诗人视通万里、思接千载的智慧的“桥梁” 。从时间中浮现,在空间上伸展,与人的生存、归依和走向息息相关,“路”因此由实在而 虚化,由此刻的足音传导出历史的“音尘”,由梦的铺设和延展组接出生命和灵魂的斑斓与 沧桑。
从“路”引出对生命的思考。生命在尘世的出现和行走,是一种偶然,是一段过程。《投 》把初始的生命——“小孩儿”安设在“山坡”上,而“山坡”又意味着人生道路的坎坷和 回旋,“小孩儿”的出现或者说生命的诞生,就像“小孩儿”或者冥冥之中谁的手捡起的一 块“小石头”“向山谷一投”、“向尘世一投”,偶然之中带来必然,空幻之中产生神秘。
从“路”引出对命运的思考。《古镇的梦》其实是写人生的梦,写人的命运的神秘莫测。 命运是在“时间”的流转中展开的,于是诗人把命运和时间化为两种形象,一个是敲着算命 锣“在街上走”的瞎子,一个是敲着梆子“在街上走的”的更夫,白天与黑夜交替,命运在 时 间的手掌里演绎和轮回,一种先天的命定感、梦一样的神秘感和深刻的悲剧感在人生的“路 ”上伴着锣声与梆声弥漫。
从“路”引出对理想生活的思考。诗人在《圆宝盒》中幻想捞到一只圆宝盒,“你看我的 圆宝盒/跟了我的船顺流/而行了,虽然舱里人/永远在蓝天的怀里”。圆宝盒是一种完满、 理想生活的象征,在人生的“航程”上,依傍着诗意的心灵。“是桥——是桥!可是桥/也搭 在我的圆宝盒里”,通向水银一般的“晶莹”、灯火一般的“金黄”、雨点一般的“新鲜” 的美好生活,要依靠人生道路和桥梁上的艰难行走。
从路引出对爱情的思考。卞之琳是一个很少写爱情诗的诗人,但他的5首《无题》诗应看作 是对爱情的隐秘歌唱。有的论者指出:“《无题》写的是一粒种子的突然萌发,以至含苞, 预感到最终会落空的这样一段情事。”这一段爱情和“路”息息相关:《无题一》借“水路 ”写爱情如春潮奔涌,《无题二》写等待的心盼望听到爱情的“脚步声”,《无题三》写纯 洁的爱情不能沾上“路上的尘土”,《无题四》写欲在对“交通史”的研究中从四面八方向 爱情辐射,《无题五》写在“散步”中恍然觉悟世界包括爱情都是空的,这一条爱情的路串 起了遇合、等待、喜悦和哀愁,其间又渗透着佛门的空幻感,正如诗人后来自称的是“故寻 禅悟”。
二
这条“路”不是单色的,不是一览无余的,而是交织着夜雨和晨光、现实和梦境、远行和 还乡,千头万绪,峰回路转。“路”已穿过暮鼓昏鸦,穿过人的身影和足迹到达精神的腹地 和心灵的后方,进而传导出人的种种矛盾心理和错综复杂的内心体验。
“路”——倾听自己的足音和疏隔外面的世界带来的精神孤独。卞之琳没有像闻一多那样 站出来宣判当时的现实“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没有像蒋光慈那样满腔义愤高唱“哀中国” ,更没有像殷夫那样刻绘人生路上因为抗争用鲜血书写人的庄严。他与他生活的时代保持着 距 离,或者如他所说的是“小处敏感,大处茫然”。于是他用诗歌给自己建造了一座避风挡雨 的心灵围城,他当然听不到他那个时代的呐喊和怒吼。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他把人生的图景 和心灵的寓所往往置放在“荒街”上,这是些找不到出路的“荒街”,包裹它的是“古城” 、“古镇”,徘徊的心嗅到的是感伤、古旧的历史气息。不能与现实接通的心当然是孤独的 !这种孤独是不能面对现实而又不愿消泯自我的孤独,是投映着现实的影子而又上升为生命 层面的孤独。因此在一种更深层的意义上讲,卞之琳通过描写人生道路上的寂寞、苦闷和荒 凉,实际上传达出了20世纪初人类共有的精神的“荒原感”和“孤独感”。
“路”——无所作为和有所期待带来的生存焦虑。在封闭的世界里,诗人为自己的碌碌无 为而烦躁、痛心。《记录》一诗记录的是自己在“街上”无所事事,从白天到晚上空耗着时 光;《夜心里的街心》借梦写自己在“街心”乱迈着脚步,一声叹息惊破了梦境。更多的时 候是描写周围人事的空虚、无聊。有人“把所有的日子/就过在做做梦,看看墙,/墙头草长 了又黄了”(《墙头草》);有人在“街路”上手里拿着两颗小核桃“轧轧的轧轧的磨着/唉! 磨掉了多少时光”(《一个闲人》)。这种客观的描摹如同主观的内心记录一样,都寄寓着对 人生的无所作为的不满、厌弃,渴望着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于是在人生的路途上出现了“ 车站”;“古人在江边叹潮来潮去;/我却像广告纸贴在车站旁”,“我何尝愿意做梦的车 站”(《车站》),“车站”的意象传达出了诗人满怀着期待,渴盼着远行。而在《睡车》中 诗人写自己清醒地睁着双眼,表明他不愿昏睡而有所期待。于是我们也就在诗歌中不难看到 那些赶路、疾行的身影,虽然要到达的目的地也许是一个模糊、抽象的“远方”或“家园” 。
“路”——生命的突围和归宿的茫然带来的灵魂的诘问。鲁迅笔下的“铁屋子”同样出现 在卞之琳的笔下:“闷人的房间/渐渐,又渐渐/小了,又小,/缩得像一所/半空的坟墓”, “炉火饿死了,/昏暗把持了/一屋冷气,/我四顾苍茫,/像在荒野上/不辨东西”(《黄昏》 )。人生的出路在哪里呢?在《奈何》一诗中,通过一个人与黄昏对话:“‘你该知道吧,我 先是在街路边,/不知怎的。回到了更清冷的庭院,/又到了屋子里,又挨近了墙跟前,你替 我想想看,我哪儿去好呢?’/‘真的,你哪儿去好呢?’”如同一个梦游者,在“屋子”和 “道路”之间徘徊。心灵的一再发问,其实是内心矛盾和痛苦的表现。而《道旁》一诗,表 现了30年代“倦行人”深层的的精神状态。这种灵魂的诘问,本身就是一种自审自察,一种 大 彻大悟,一种源自心灵而回响在天空的纯净的声音。应该说这既是对个人出路的发问和寻找 ,也是对生活在“闷房子”里的芸芸众生的归宿的发问和探求。虽然还有些茫然,但毕竟有 了面对生活的勇气,做好了毅然前行的心理准备。这样也就不难理解30年代后期卞之琳的诗 歌在内容上开始发生的变化。
三
“路”这一意象出现在卞之琳的笔下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现实原因。“坟墓”一样的 现实环境,迫使诗人在压抑和忧郁之中俯视脚下的“道路”,寻求人生的“出路”。而“总 怕出头露面,安于在人群里默默无闻”的卞之琳,就敏感并执着地表现脚下的也是心中的“ 路”,因为这条路可以让诗人在苦闷中进进出出,进退自如,成为一种调节心灵、排遣忧烦 、追求梦境的生之通道、心之隧道。况且这条“路”又从历史深处蜿蜒而来,它连接着过去 的“废园”和“旧痕”,这正契合了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处境和心境。其次是文学方面的原 因。中国传统诗歌中“路”的意象成为了诗人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一个重要载体。屈原的 “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也好,还是李白的“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也好,对人生道路的思索,更不用说记游诗、田园诗、送别诗和边塞诗等多关联到“路” 这一意象,表现了丰富的内含。可以说“路”的意象串起了古往今来文人士子心灵的感叹和 追求。古典诗词修养深厚的卞之琳在现实窘迫、前途渺茫的处境下有意无意地接过了这一情 思包孕的意象,抒发作为一个现代人的思想感情。文学方面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卞之琳接 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潮的影响。卞之琳曾说自己“一见如故”的还是“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 义’文学”。他的那些表现自我精神苦闷的作品,就“明显渗入了西方现代派文学表现现代 人生命困境的笔调”。他笔下的“荒街”以及那些在荒街上走动的小人物、灰色人物,无疑 借鉴了波特莱尔的“审美”眼光;把自己的感慨和思考借助意象表达出来,又活用了艾略特 寻找“客观对应物”的创作方法,他的《归》中的“伸向黄昏的路像一段灰心”就化自艾略 特的“街连着街,像一场冗长的辩论/带着阴险的意图/要把你引向一个重大的问题”(《普 鲁费洛克的情歌》);他还接受了魏尔仑以及后期象征主义诗人叶芝、里尔克、瓦雷里等人 的影响。尽管卞之琳的诗歌渗透了现代主义诗潮的因子,但由于他对“路”以及相关意象的 选择并由此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和体验,就决定了他的诗歌在内在精神上还是现实主义的。
从诗歌中盘旋而出的这条“路”,既带着文学的诗性,又带着现实人生的硬度和厚度。“ 路”作为意象是存在于文学艺术之中的一个意味深长的符号,也是对人的经验世界和理性世 界的一种抽象和概括,它关涉时事风云、历史沧桑,但更直指人的生活道路、心灵历程和命 运归宿。从这方面理解,诗歌对“路”的关注和咏叹就具有了一种超越时代更迭、人事兴废 的普遍意义。“路”可以看作是人生、历史和宇宙的“根”,它敏感于岁月的步履和世事的 变迁,关联到社会的神经和心灵的变幻,而且常常伴随着生与死、灵与肉、起与伏、有限与 无限、时间与空间等这样一些哲学命题。这样说来,诗人虽然着墨于具体物象但又超越了其 表层意义,进入到对事物和世界根由和本质的谛听与触摸。中国新诗自发端以来存在两个极 端 ,一个是排拒“小我”而专注于社会群体的抒情,一个是远离大众退回到个人内心的呓语, 前者具有时代标本的意义但有时不免失之浮浅,后者显得很艺术化但往往又神秘莫测。那么 可以说,卞之琳因执着于人生“道路”的描写和表达,把个人生活的城堡以及生命的突围、 把内心的苦闷和时代的阴影、把个人对美景仙乡的凝眸和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联系起来,表 达了既是个人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的一种处境和心境。这就在诗歌艺术传达上对“小我 ”与“大我”的关系实施了一次很好的融合。
今天,现实生活中的人在忙着功名和利禄,人文精神、心灵关怀、家园意识普遍缺乏。几 十年前卞之琳的“我要上哪儿去”的诘问,仍似一线悲怆的箫声引发我们不尽的思绪。文学 的“路”,生活的“路”,该怎样走才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