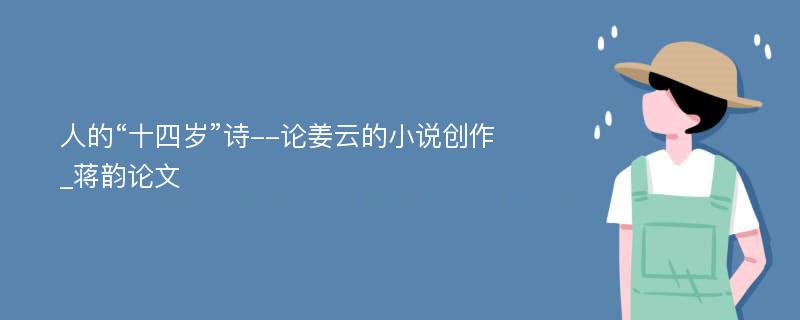
人类的“十四岁”诗吟——论蒋韵的小说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四岁论文,人类论文,小说论文,诗吟论文,论蒋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中,蒋韵作为一个作家,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女性作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
蒋韵创作实绩的丰厚与评论界对她研究的单薄是一件怪怪的事儿,这或许是因为蒋韵的创作从始至今始终因其独特性而与一波接一波的文学主潮有着一定的疏离,或许是因为我们不能把她的创作对号入座顺理成章地归入我们既定的文学研究格局之中,也或许是因为她用“肚子写作”而我们用“头脑思考”,还或许是因为一些其它什么我说不上来的缘故,但这或许更说明着我们在今天强调评论、研究蒋韵的“应该”。
蒋韵的小说创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多的对蒋韵小说创作的评论也有着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大致说来,有这么三个阶段:最初是评论家李国涛、段崇轩,他们指出蒋韵在七、八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大抵是塑造五十年代初出生的那一茬人的形象。1989年之后,蒋韵的小说创作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实在而趋于空灵,评论家毛时安曾比较准确地抓取了蒋韵这一时期创作的意义,他主要将其归之为“她对于死亡独具的生存意义的近乎执着的关注和顽强的表现”,“用隔世的眼光”使“此生此世”产生“令人无法捉摸的内在丰厚”(《美丽的忧伤》)。1996年蒋韵发表了其代表性长篇《栎树的囚徒》,作家李锐、成一将其归结为是中国文化破碎、解体的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飘流的故事”,是“悲剧里的悲剧”,“是宏大的历史进程中的生命感受”(参见《生命与历史:诗意的消解》)。这一解读典型地体现了李锐的思路,在李锐《旧址》以后的创作中,这一思路得到了更充分的展开。蒋韵本人似乎也比较认可这种解读,我甚至在她的《栎树的囚徒》对家庭的历史的设置、对朴园的设置、对贺莲东这一人物的设置中,看到了《旧址》那种宏大历史设置,那个白园、那个紫痕设置对她的潜在影响。应该说,李锐的这一思路是十分深刻、精辟的。但是,问题在于,这种解读的影响正有将蒋韵归入“类”从而覆没、遮盖蒋韵创作独特性的可能。这样,当我试图写这篇文章谈谈我对蒋韵创作的理解时,我知道我在做着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同时对毛时安先生所说“解读蒋韵是件令人振奋有冒险性的活儿”深有同感。
读蒋韵的作品,给你留下极为深刻印象的是她常常写到死亡,特别是女性的死亡,写到西边的落日,寂寞的河水,一棵孤单单的树,写到沿河水去作远方寻找的孤独者,写“十四岁的时候”,这些意象频繁、生动、形象地多次出现在她的作品之中,她为什么总是作这种描写?作这种描写的内在因由是什么?她的艺术地把握世界的方式是什么?读蒋韵的作品,还会给你留下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就是她的作品能指单独地看,并不复杂,但能指链条却缺乏外在的关联。在一部作品中,她往往设置几个表面看来完全无关的故事片断,如此一来,并不复杂的能指所体现的所指往往让你感到比较玄虚,缺乏外在关联的能指链也让你对作品整体所指的把握感到十分困难。用作家成一的话说,蒋韵是只写“冰山的尖端”,冰山则隐没在水里。蒋韵自己也承认自己所写的是“只露一个尖”,但读她的小说又确实给你一种很美好、很忧伤的感动,虽然当你试图用流行的话语进行言说时,你会有一种找不到话语形式的苦恼,但这或许正说明着蒋韵的小说对我们今天话语形式的突破性与挑战性,不是准确运用而是借用一下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说法,倒是可以说明一下解读蒋韵作品的特征,弗氏无意识学说认为,人的精神结构恰似一座冰山,起决定性支配作用的八分之七的无意识没于水下,作为表现形式的八分之一的意识部分则成为悬浮于水面上的冰山的尖端,无意识部分是一个永远无法穷尽的“黑洞”,我们只能通过冰山的尖端去猜测它、把握它。解读蒋韵的作品,我们遇到的情况与此很类似。自然,我说的是解读状态的类似,决不是指从意识、无意识关系的角度去对蒋韵作品作出解读。这样,我就再一次体会到解读蒋韵作品的困难,体会到解读蒋韵作品确实“是件令人振奋有冒险性的活儿”。
我觉得,很多人都忽视了蒋韵创作的初始动力源,对评论界李国涛、段崇轩最初对蒋韵所作的评论及这之后毛时安、李锐、成一对蒋韵所作的深入的评论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未给予应有的关注,深知蒋韵且对创作极具经验的李锐似乎也有这样一个错觉,他说:“蒋韵的创作,1989年以前还是跟着新时期一点一点地往前走……1989年以后,她找到了自己的主调”。而在我看来,蒋韵的创作始终未脱离她的初始动力源,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她创作的独特性。
蒋韵的作品,在最初,诚如李国涛、段崇轩所说,是写五十年代初出生的作者的那一茬人,而在这之后的作品中,又对“十四岁的时候”情有独钟。这个“十四岁”有时是实指,如《栎树的囚徒》中的天菊,《绿灯笼》中的苏锦,《裸燕麦》中的“我”,有时候则虚化、泛化为一种人生状态,这一点,我在后面再作展开,蒋韵这一茬人,在十年浩劫初期,正是十四岁左右,既是人真正脱离母体初具独立意识的时候,又不能如其时十七、八岁的红卫兵们接受某种既定思想风云于一时,自己没有相对成形的思想,却又开始对人也有了敏锐的初始的感受,面对的却又是一个破碎的世界,一个无人顾及无人关注他们的社会。他们用一双天真、好奇、纯净的眼睛观看世界,世界的破碎、扭曲又像烙印一样烙在他们尚未被社会格局所局囿的鲜嫩的心中,这注定了他们是敏感、飘流、无根、充满渴求、寻找的一茬人,注定了他们成为对美的消失充满忧伤的一茬人,也使他们成为最能体现人初始面对与人对立的世界的种种感觉的一茬人。每个作家,都有构成自己创作独特性的生命记忆、情感记忆之根,它会长得花繁叶茂,硕果累累,但却都源于、生长于这一根之上。构成蒋韵创作独特性的生命记忆、情感记忆之根正在这里。如果我的剖析仅止于这里,那么,这仍然还只是将蒋韵作为给有独特历史的一茬人及他们对世界、人生的情感审视立碑的一位作家,这部分内容虽自有其意义、价值所在,但蒋韵的深刻性、独特性不仅仅在这里,这些也构不成蒋韵创作的一半份量。蒋韵的深刻性、独特性在于她将这样的一种人生形态、情感形态提升到了一种形而上的程度,成为人、人类在自身成长史中的一种存在形态,成为人、人类初始的面对与自己对抗的无法完全认知、把握的外部世界及由此带来的对自身命运的关注的存在形态及相应的情感形态、审美追求。虽然人征服外部世界、认识自身的能力在不断增强,但由于欲望、追求的永无止境,人与外部世界的对抗,人对自身认识的困惑及由此而来的“美丽的忧伤”也在不断增强,人在螺旋形上升的轨迹中,在不同层面永远处在前述所说的“初始”状态。这样的一种初始状态与蒋韵这一茬人“十四岁”的状态是有着一种异质同构的同态对应关系的,这就是我前面所指出的蒋韵作品中的“十四岁”的虚化、泛化现象,蒋韵正是从具体的“十四岁”的生命记忆、情感记忆出发,通过审美提升,走向了一种超越特定时代内容超越特定时代的人的艺术永恒。
如此一来,蒋韵的作品中所写的重点就不在那些特定时空之内的社会内容上。譬如《落日情节》中“文革”阴影对人的历史覆盖,或者《绿灯笼》中抗战时代战争对人的损伤,或者《相忘江湖》中下乡插队生活对人生的潜在制约,她的代表性长篇《栎树的囚徒》的重点也就主要不在一种家族故事的历史叙事,而在于表述如上所述的人初始的对充满缺陷的人生、世界的丰富、细腻、深刻的感知、体悟、情绪,外在的社会、物理形态是为这种表达服务的。这样,蒋韵的小说,就与诗有了同一性,诗,成为她的作品之魂。
由于蒋韵是用作者的而不仅仅是主人公或人物的“十四岁的时候”的眼光来审视有缺陷的世界,所以,她的视阈往往集中在美好的生命在进入社会后的磨难、消损、毁灭上。中国的传统社会,男性处于社会的中心,因之,与社会相互缠绕、渗透为一体,女性则处于社会的边缘,更少地受到社会的污染,更多地保有人的生命的本真性,因此,蒋韵要想表现美好的生命在进入社会后的迷失、尴尬、磨难、困窘、毁灭,女性的种种悲剧就成为她赖以描写的最好的选择对象,事实上,她对此的描写也最为成功,譬如,她写了陈桂花、小红(《栎树的囚徒》)、谢萤(《旧盟》)刚烈的死,写了段金钗、关莨玉(《栎树的囚徒》)、宋翠微(《绿灯笼》)悲凉的死,即使活着的人,也往往活得那样尴尬、无奈,如《失传的游戏》中的鱼,《现场逃逸》中的马丹;或者在现实生活中被彻底地扭曲,如饱受折磨的苏柳,从监狱出来后,却每天自觉地、主动地写“小报告”,充当告密者。死去的人,虽然死得刚烈、悲凉,但当她们为之而死的男性其实却并不值得她们为之而死时,她们的死也就失去了意义,而活着的人,又活得那样无奈,那样尴尬,于是,无论是死是活,就都显出了人在一个外在于自己的客观世界里生存的无意义。但这种无意义,又以对人的生命的鲜活、美好的丧失的感伤为底色,因之,既充满了人性的温馨,又充斥了坚硬的力度与质感,构成了一种美丽的深刻的悲凉、感伤。蒋韵对此其实是有着十分自觉、清醒的把握与追求的。在《大雪满弓刀》开篇,作者夫子自道曰:一个黯淡的北方故事,却跳跃着几点南方明丽的颜色,这就是我喜欢的叙事风格。她还说:我的想象总是在不出十米的地方碰壁,碰出几滴血,溅在迎面的粉墙上,略事点染,倒成了几枝梅花。大雪地里的点点寒香,就是我想象的边缘。如果我们把北方、粉墙、大雪地比喻成社会、人的生存形态,而把南方,把梅花、寒香比喻成生命的美好,我以为,这比喻是大抵不错的。
我觉得,正是由于蒋韵笔下出色的女性描写,所以,往往使研究者容易用女性主义文学的视角来研究蒋韵的小说;也正是由于蒋韵的笔下生命的鲜活、美好的社会、历史挤压下的宿命般的消损、毁灭、无意义,所以,往往使研究者容易用“历史叙事”、“家族故事”的视角来研究蒋韵的小说,但又都只能从某一个角度来解释蒋韵作品的一部分,而无法把蒋韵作品划入女性主义文学或“历史叙事”的版图。我还觉得,正是初对社会,面对着生命美好、鲜活被无意义的消损、毁灭,又不能用成人成熟的理性,用历史的法则去给以解释、解脱从而来安妥自己的心灵,抚平心灵的创伤,所以,蒋韵的作品才会充满着一种迷茫、流浪、孤寂的情调。因之,在她的作品中,才会常常反复地写到落日,用落日隐喻美好的不可避免的失去,才会常常反复地要写到“一棵孤单单的树”,才会常常反复地要写到一条河经年累月地不知从哪里流来又要流向何处,而一个孤寂的旅人就沿着这样一条河流去展开着自己的生命,为流浪、漂泊所苦。蒋韵的作品还因此常常写到寻觅,总想生活在“别处”,“别处”却总是不存在,所以,这种寻觅就总是以没有结局而告终。天菊总想奔向西南草海的表姐,但最终西南草海的表姐却成为疯子死去而将五岁的男孩送了回来,于是,草海之梦终于归之于破灭(《栎树的囚徒》)。马丹去了广州,但在胡石的解构下,马丹去广州就成了一种不真实的存在(《现场逃逸》)。林琦确实去了国外,却最终因为听到一句“你们家在哪里?你们怎么不回自己的家?”而真正走上漂泊之路(《裸燕麦》)。陈忆珠即使只是在虚幻中带着刘钢作一种出逃,最后却也付出了死亡的代价(《完美的旅行》)。而当廖志平想要去寻回旧日的许诺时,则被人视为失踪。问题还在于,旧日的许诺在哪里,许诺相约的人早已去了无家可归的国外,这样的对许诺的寻找也就成为一种无意义的悲壮(《相忘江湖》)。如此一来,为解脱流浪、漂泊而产生的寻觅反而使流浪、漂泊更加深化,更加成为无可解脱的一种存在了。
蒋韵小说文字的优美每每令人称道。在我看来,这与她小说的诗化写法是相吻合的。蒋韵小说语言最大的特点在于她能用简洁、优美、富于质感的抒情语言,把特定时空实写的人物行动的片断一下子宕开去,拓展成一个涵盖广阔的时空、人生内容的比较空灵的意境,使作品一下子从实而虚,从而使作品在行文中时时地超出实在的具体人、事的描写而被赋予了更丰富更富于意味的内容。这种写法是蒋韵十分擅长的,在作品中可谓比比皆是。我们不妨随手拈来两例。譬如在《栎树的囚徒》中,当作者叙述范福生为阻挡大儿子虎子与怜儿相爱将虎子与怜儿囚禁在葵菽山房时,作者写道:“父亲不许大哥迈出它(指葵菽山房)一步,要他闭门思过。朴园的秋天使人伤情,梧桐树落了叶,桃李树落了叶,柳树杨树落了叶,满园落叶,满园秋雨。雨打着落叶的长夜大哥他难以成眠……他重温与她同行的三天,他在想象中一步一步踏上重返山林的路。奔向山林的路程是极乐的路程,就像圣徒奔向圣地。他们是朝觐的圣徒。朝觐的欢乐是欢乐的顶巅,世俗的欢乐哪里能够比拟。落叶在雨水中慢慢腐烂,第一场雪降临朴园。第一场雨雪总给人某种久违的清新的惊喜。雪花的飘舞纷乱而轻柔,像女人的消息。卓文君的素手在古琴上刮起狂风,十个指尖滴下点点鲜血,大雪红梅的鲜艳令人胆寒”。这样的文字早已远远超出了对事件的叙述,作者用自然景色烘托出的,正是虎子对大自然对人的本真生活的向往及这种向往不能实现的那种鲜活美丽的凄凉。再如作者写范福生兵败逃亡:“父亲星夜逃亡,唐朝的明月照着父亲的逃亡咯,蓼红苇白的大好秋色闪电般从父亲眼前一掠而过,如雪的苇花染白了马的四蹄。父亲从月升跑到日出,从日出跑到日落,黄河上的日落月升是多么苍茫的风景。汩汩的流水噬咬着他的心”。这样的文字一下子给读者一种历史沧桑感,并让读者在历史的沧桑中辨认范福生的地位,思索范福生命运的意义。可以说,蒋韵小说能指的单纯与所指的丰富,蒋韵小说的本体构成,正是依靠着这种实与虚的关系,依靠着这种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依靠着这样的语言形式来完成的。可以说,蒋韵的小说,在小说构成上,提供了一种新的构成元件,构成方式,对此是很值得展开深入研究的。
当然,在小说结构上,蒋韵还是很注意情节安排的。但她对情节的安排,同样不在于外部客观世界的关联性而在于自己对外部世界感觉的内在关联性。这与诗仍是相通的。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蒋韵小说往往是由从外部看来毫无关联的几个情节、几个故事片断来构成的。譬如在《冥灯》中,作者讲了三个毫不相关的关于死亡的故事;在《大雪满弓刀》中,作者也是讲了三个毫不关联的故事,大侠孙二与黑衣人、陈家瑞与赵芝庭及邱经理与苏虹;在《旧盟》中,作者讲的也是几个毫不关联的故事:隋小安、陈醒村的故事,留小老汉一家的故事,义军王七的故事。这种情节设置的方法,在《栎树的囚徒》、《失传的游戏》、《相忘江湖》、《古典情节》、《裸麦燕》等等作品中,几乎均是如此,习惯于阅读以客观事物之间的逻辑关联来设置情节的小说的读者,在面对蒋韵小说时,往往感到不得其解,其实,蒋韵正是要通过这样的互不关联的故事片断,在相互的烘托、比照、互补、映衬之中,来表达自己对世界、人生某种复杂的整体感受。作品中客观世界的片断之间是没有关联性的,但所有这些故事片断的选择、组合又都内在地统一于作者对世界、人生的某种复杂的整体感受。在这种思考、感受作者又不在小说中明言或没有能力明言。这与“十四岁的时候”面对能感知的世界却又无法用社会理性解析、言说的状态是十分一致的。
中国诗歌讲究意境,意境最根本最本质的属性乃一个“空”字,“是佛一空,何境界之有?”所以,中国诗讲究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旨、言外之意等等,但均不脱一个“空”字,蒋韵的小说在这一点上是十分凸出的。她的小说,通过语言描写、情节设置,往往再现具体时空但又不屑于此,而是由此超越具体时空从而指向了“空”,如此,令解释者不论从哪种角度谈,往往“一说就破”,这也就如同本文开头所说,蒋韵是只写冰山的“顶部”,而冰山的下部则是既定的话语无法穷晓、言说不尽的“黑洞”。
但正如诗之意境尽管是一个“空”字,但仍给读者一个把握、解释的范围一样,蒋韵的小说尽管也时时指向空,但也仍然给我们以把握、解释的范畴,那就是如上所说,将个人、特定时代的“十四岁”的生命形态通过审美提升,使其成为人类的一种生命形态。“五四”时代张扬“人的文学”,其后虽几次向度转换,但时至新时期,“人的文学”终于又成为一个十分响亮的口号,新时期的文学对人的揭示,或张扬个性,或为人性正名,或设置与社会相对隔绝的时空来对人、对人性作孤立的抒写,或者用物欲、情欲、性欲的恣肆来颠覆原有社会结构,消解其神圣,但蒋韵的作品明显地卓而不群。蒋韵的作品喜欢写水、写河,犹如水从山体孕育而出而又冲破山的怀抱流向远方,犹如水从土地渗出汇聚成河而奔流至海,蒋韵作品中那种对人与社会、时代的揭示也如水与山、土地的关系一样。水从山、土地中孕育而出又自成形态,蒋韵作品中的人也从社会中孕育而出而又自成形态,只是这样的一种形态我们是不能仅仅将之实在地归溯于、对应于一定的社会结构、历史形态,但它又不是脱离社会、历史而孤立存在无所依傍的,蒋韵对二者关系的处置、把握是令人称道的。
今年,蒋韵发表了两部长篇少年小说:《闪烁在你的枝头》、《谁在屋檐下歌唱》,应该说《枝头》比《歌唱》更为出色,原因何在呢?
我觉得,《枝头》所写“十四岁”的状态与蒋韵在其所有作品中所写的实指的、泛化的“十四岁”状态是相一致的,这里面依旧有漂泊、流浪(唐小芬离开母亲),有寻觅、出逃及寻觅、出逃的失败(唐小芬姨姥姥家的悲剧),有爱的虚无破碎(谢平凡、幼容),有美好的失落(幼容的死)等等,这样一来,这部小说就如同蒋韵的其它小说一样使“十四岁”成为人类的一种特定的生命形态、存在形态。而《歌唱》呢?妈妈的“十四岁”与蒋韵所有作品中的“十四岁”是一致的,而儿子的“十四岁”则只具备了一个实在的时空里的“十四岁”的内容,这就使妈妈的故事与儿子的故事失去了重量上的平衡,不是说,要把儿子的“十四岁”写得和妈妈一样,而是说,要把儿子的“十四岁”也提升到一种形上的层面,使其不仅是一种“象”、一种“景”,还要使它也如妈妈的“十四岁”一样,具备“景”外的“景”、“象”外的“象”,这或许会给蒋韵的创作构成一种新的挑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