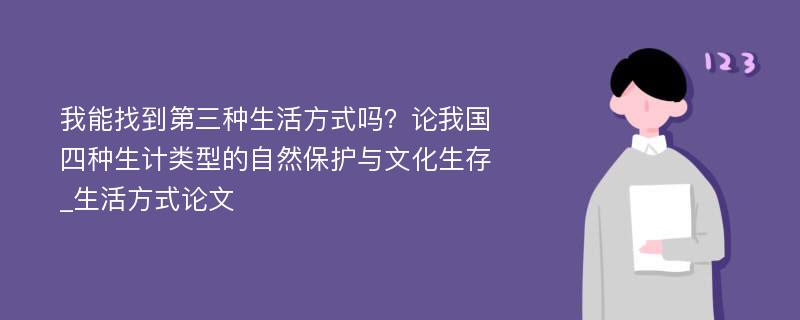
可以找到第三种生活方式吗?——关于中国四种生计类型的自然保护与文化生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活方式论文,自然保护论文,四种论文,生计论文,可以找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4;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6)07—0035—07
一
在有人参与的生态系统中,人类学关注包括区域人类诸族群和动植物种群在内的生物—文化多样性整合性存在的研究,或对其失序状态的改善研究。对于前者,涉及人类学家擅长的、对相对静止的经济文化类型的描述,特别是对20世纪那些较少受大规模现代“开发”和市场经济冲击的区域社会而言;后者则是对那些因不当干预而造成的文化生态系统紊乱的地方提供理论解释,以及有益的应用性建议。
关于中国生计类型的划分,最流行的是20世纪50年代由前苏联民族学人类学家切博克萨罗夫和中国人类学家林耀华共同研究的分类成果,他们按“经济文化类型”划分了中国和东亚地区的多种类别①。由于各民族的经济发展方向和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各民族的物质文化特点,这就使具有相近生产力水平和相类似地理环境的不同民族可能具有相近的经济生活和物质文化特征,从而构成相同的经济文化类型。除了他们划分的狩猎采集业、农业、牧业等大类以外,还有分区的亚类别。例如中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森林苔原驯鹿型、游猎型,北部和西北草原游牧型,西南部存在的山地游耕型以及南北汉人社会的稻作和麦作类型等。这一经济文化类型划分就其生物多样性的表达来说,虽受学科限制而略嫌单薄,但已经关注生态环境及其文化形态的有机联系,其分类背后的“历史民俗区”旨在说明区域生态—生计系统中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之间在历史上的有机联系,因此这一分类系统对地方发展至今有借鉴作用。
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生态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共同创造了新的研究成果,对在不同生存环境中不同族群的生计方式及其相关的思维与行为方式的关联有了新的认识,其中生物—文化的多样性整合的规则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成了对日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成功或陷入困境的重要评估标尺。如果把切—林分类范式中抽出那些如今已有新的理论发展的生计类型看,游猎、游耕、游牧和农作四类最为引人注意,这四种生计类型占了中国版图面积、人口和民族的大多数。而且这四种类型的人类居住地都被不恰当地干预过。这就属于人类学对上面提及的生物—文化多样性系统失序的改善研究。
20世纪50年代,斯图尔德(J.H.Steward)的文化生态学研究通过三个步骤考察有人参与的生态系统,“分析生计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分析具体生计技术与行为模式之间的关系;分析行为模式影响文化其他因素的程度”。② 而后来的研究对斯氏将生计行为置于首要地位的观点提出质疑。
20世纪中后期,人类学家继续热衷于对采集狩猎、牧民和当代农民社会的研究,但已经注意到“清晰地理解简单文化中的人类生态学后,生态人类学就能够更深入研究人类对于环境衰退、城市污染和其他的当代环境压力的反应”。③
人类学家在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过程中,从早期对环境的关注,对生计方式的解读,对人们如何感知世界的研究,以及对人(文化)与自然对立或非对立性的跨文化理念加以比较,使我们通过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从基本的生计方式过程出发,观察各个地理区域族群文化的历史与认知方式特点,以及他们相似的或不同的哲学基础,以便中肯地理解一个族群的文化的内涵,或运用这一理解完成其涉及该地区发展的应用性建议。
近年来,日益深入的国际环保工作与相关项目经常出现在生态环境遭到侵害、人民的生活方式处于困境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生计活动失去活力,文化体系也岌岌可危,已难以提出一般的所谓良性发展问题,而是表现为对那里人民的文化生存窘境的关爱与卓有成效的合作改善行动。为此,这就一定需要考虑依靠本地人,因为“在保护的尝试中,本土人是有力的同盟者。他们给保护带来大量知识、经验、道德及情感承诺;他们了解这些土地和生态系统,常常具有几代人利用土地的、与本地情况相适应的实践;他们也愿意密切关注这些土地将变成为什么样,将有什么生物在其中生活。我们应为他们与其家园保有情感和精神的关联,尊重地方族群生命的中心价值观,因为我们看到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认同已经危如累卵”。④
二
在我们所理解的切—林氏的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中,森林苔原驯鹿型被认为是最具传奇性的生活方式之一。例如,历史上中国东北部的鄂温克族长期住在针阔混生林带,林地密布着苔藓植物,是驯鹿群啃食的天然“饲料”。他们游猎和放养鹿群,一年一个移动周期,其大家族组织正是适应了这种灵活的游徙生活方式。鄂温克人熟知驯鹿的辎重、转移和奶制品等的实际价值,好的生活经验与群体意识无形中规定了苔原承载驯鹿数量的习惯标准。在居住地,驯鹿不仅作为彩礼交换互惠,还是人与神之间神灵的重要媒介。⑤ 鄂温克族的游徙人群与驯鹿种群和谐地相依为命,创造了自身的积极的生命价值。可以说鄂温克族的小生境系统整合了动植物种群、地方族群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的整体。这样的森林生态环境,在最近几十年间却因森林大面积被砍伐而消失,而附着地表的苔藓植物减少殆尽,随之,驯鹿业也难以为继。社会的发展颓势造成少数族群心理及社会病症,酗酒和非正常死亡比例增加很快。⑥ 狩猎游徙的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一样,还遇到了从民国时期的“弃猎归农”政策:解放后和大跃进时期,以及直至今天,地方政府仍积极贯彻定居政策。但事实是定居的思维与行动在游猎驯鹿民族生活中造成文化中断,出现“弃农归猎”或因不熟悉务农而使生活无着,甚至酿成高酗酒和高自杀率的严重后果。
总之,在中国东北部主要为满—通古斯语族的森林狩猎和苔原驯鹿类的民族共同遇到了社会发展与文化生存的困境。主要表现还在于:(1)从清代、民国以及解放后,政府数次推动上述少数民族下山定居的失败的努力,均源于定居优于传统林中游徙生活方式的“进化论”影响,以及外来价值观的强力跨文化实践。(2)在游徙与定居之间若即若离的生活状态,使得小民族陷入了社会文化生存的窘迫状而不能自拔,文化中断状态不能弥合,心理与社会问题丛生。(3)即使是小民族同意或接受的社会发展试验(如新的定居试验),也需要讨论文化中断—文化适应的“过渡期”选择问题。比如,笔者就曾参与由政府官员、学者、驻京国际组织以及当地居民参与的多头对案讨论会,讨论鄂温克人的定居方案,评估政府对少数民族新的定居计划与行动。
三
对中国西南部众多山地民族的游耕业(有称刀耕火种)的理解一直存在问题。一般的报道多认为二者相联系,误解了来自新石器时代就发明的最简便、经济和对林木植被更新最具适应性的耕作方法。人类除自身繁衍外,还需要将与自然植被和动物相关的物质文化及精神文化累世传递下去。因此,拉帕珀特⑦ (Roy.A.Rappaport)在新几内业的游耕研究更注意了文化信仰、人类行为和生态系统之间具有复杂关联网络的理论。⑧ 生态人类学必须注意生物性因素和文化性因素内在关系的研究。笔者在1980—1983年在云南省的5次田野考察, 也证明有序的游耕业是那里最简单、最经济和最具适应性的农作形式。⑨
笔者发现那里存在两种游耕方式:频繁迁徙的前进游耕型和螺旋游耕型。前者是在人口稀少、地域广袤的环境下,人们顺山脊从北到南寻找新的处女林实施砍烧农业,获取一两年的最佳作物产量,不等地力耗竭,随即迁移,所弃山林不久即林木复生。20世纪50年代的苦聪人(拉祜西)即是这种类型的代表。螺旋游耕型为多数交叉居住的山地民族,他们已经难觅到广袤无主的林地,而是在一个个被限定的族群居地中由集体智慧创造出有序的循环烧荒法,常常成螺旋状或相似的、逐一排定的砍烧顺序作业。这种方法保证了不会毁林,林木亦可轮流复生。例如笔者考察的西双版纳山地基诺族曼雅寨的游耕周期为13年,龙帕寨为7年, 并由习惯法与族群规范认同,⑩ 他们万物有灵的信仰保证了基诺族居地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信仰原则相互整合起来,构成那里人民传承已久的生活方式。(11) 而毁林烧荒(媒体几乎一致认为等同于刀耕火种)则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不与少数民族协商的前提下硬性划分国有林范围,虽保护了部分林木,却切断了山地民族的螺旋游耕序列,结果林木难以复生。后又因人口递增、口粮不足,导致无奈的地方人民开始无序地毁林烧荒,终酿生活之苦果。
似乎一些新型的生计替代办法,包括定居、开荒务农、引种中草药等,均因不能预估生计活动变动引起的周边生物环境的改变、忽视逐渐累积的水土流失灾难,以及出现生活不适应和文化中断而引发心理障碍与挫折。这些替代办法都属于不理解山地民族有序游耕的智慧所在,以外力将中原汉族社会贯彻多年的“以粮为纲”的重农主义政策强行切入古老有序的游耕生态系统。人们瓦解了游耕系统的传统运作,却有没有恰当的良性系统替代,既没有地方族群“迅速”适应的生计方式,也没有文化制度的有机衔接,结果有破无立,致使游耕者的生活无所适从。在这里,我们对所得到的新的知识阐释如下:
1.有序的游耕方式是人类集体智慧在生态适应性上的良好选择,硬性而无根据地打乱原有人类生态运转系统是错误和不足取的。
2.在已经打乱了原生的人类生态系统的情况下,如何重新安排国家政策(须考虑国有林的林地权和地方族群的主体性与选择权)?在不当政策贯彻多年从而导致生活方式不可逆的情形下如何重整生物—文化整合构架?这是一个许多地方面临的问题,其实质是在两个硬性接续的文化不适应状态下,哪些是可持续的(如神山崇拜、游耕小循环设计等),又有哪些是需要重新适应或应对的(如新生计方式与民俗文化、文化心理适应性准备,以及市场经济规则大量进入等)?
3.对于仍保留刀耕火种的少数村寨,在尊重其民族传统生计方式的同时,建议地方政府充分估计当地游耕族群不得不趋向定居的未来,务必在帮助其发展新生计的同时,让他们在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上有一个缓冲的空间。如果不给文化变迁适应一个相当的试验期,就会造成了长期文化生存的窘迫状态,因此如何规划新的生态社区也是人类学和多学科合作项目的基本出发点。
四
牧业民族要保护草原过人类与畜群和谐共生的游牧生活,而农业民族却要除草耕作过定居生活。这样,从古到今,人类社会形成了农牧两大区域:不同的动植物种群分布和不同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方式。然而,中国历史上两个相对分开的巨大的牧业和农业区划(以蒙、汉两族为主)在20世纪共同卷入了越发频繁的交流与互动。
游牧民族的习惯法和成文法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保护草原、水源、牲畜以及伴生的游牧社会文化风习。叶子奇的《草木子》中说“元世祖思创业艰难,移沙漠沙草于丹樨,示子孙勿忘草地,谓之誓俭草。”20世纪初开始的“移民实边”和开垦内蒙边地,使那里失去了大片牧场,从西部到东部,多起保草抗垦的民间运动可以说是族群之间不同文化价值观思维与行动的直接对峙。
蒙古族文化价值观体现在他们认同由游牧人群—牲畜—水草连接的游牧社会生态系统。草场的出草量大于畜群的啃食量时,牧民就不需要倒场轮牧,出草量小于牲畜啃食量则需要轮牧。畜群越多,草场的载畜率越低,所需草场面积就越大。由于人口压力日趋大增,耕地扩大而牧场减少,再加上农作改观后腐殖土层薄,地力不高产量低,造成三年就丢荒,丢荒后地表又快速风蚀,致使草原沙化严重。如今内蒙古2/3的旗县和60%的垦殖农田受到沙漠化威胁。(12) 其他的影响性因素包括内蒙农牧民的薪柴过度采伐(主要是沙蒿、沙柳、乌柳、柠条等植物)。一个五口之家每年需要采集挖掘40亩地,即10万户就要毁掉400万亩野生小灌木植被。内蒙阿拉善盟原来1700万亩的梭梭林现在只剩不到700万亩。牧场植被减少的原因还有开矿和修路等的巨大占地。在内蒙农业垦殖的一个世纪,还出现了蒙古族语言使用减少、蒙汉通婚引发习俗和婚姻家庭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等。生态环境过渡与文化交错导致在蒙汉交汇地带双向文化中断现象,远没有达到文化相互适应的状态。
在长江源头的高原牧场,那里的藏族普遍具有动物与人类同生同长的理念,加之藏传佛教的影响,牧民们世代“惜杀惜售”,不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却要保持心灵的祥和平静。(13) 但上个世纪根据国家的安排,扩大畜群规模,致使藏族深植内心的草场—牲畜—牧民的和谐生态共同体的链条被击垮。音调不定的政策变化使牧民无所措手足,“上面总是说,牧民要多养牛羊,牛羊多了,说破坏草山;牛羊少了,又责备牧民不好好放牧。最后我们自己也不知怎么做了。”人与自然之间,不仅是依存和攫取等功用性关系,还存在着通过时间建立的文化联系。生活在特定环境的人们,以自身千百年绵延的文化理念及行为同当地环境达成协调一致。当这种文化关联被外来文化冲击直至断裂时,生态环境恶化和本土文化的存在危机都将是难以避免的。显然,生态恶化背后包含着族群与环境之间的文化断裂。因此,我们可以反思国家发展的导向过程,即忽略地方人民的主体性地位将招致人类与自然关系失序,并因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直接牺牲牧业受益人。
笔者的理解是:(1)农耕哲学用在内蒙古草原, 百年农业垦殖换来那里的沙漠面积不断扩大,沙漠化前锋直逼北京,这是跨文化价值观实施之恶果的物化表现。(2)上述蒙汉族际交往过程,削弱了语言认同和族群认同,家族制度(包括赡养制度和继承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一般认为,走退耕还林、还草、还牧的道路才能根本改变内蒙古人口与环境恶性循环的被动局面,但实际上逆向的回转补救行为常常难以实施。这意味着游牧哲学将无可挽回地和牧草一样会被压挤,而被该游牧哲学限定了的草场生计观与信仰方式,在农耕社会毫无用武之地。(3)对藏族游牧生计和信仰整合呈现的良性人文生态系统的任何触动,都需要和那里的人民平等商量。如何把外在针对大自然二元对立的“开发”的思想与行动放缓,寻求藏族自身认同的安居乐业模式,是国家制定西部发展战略与政策实施需要优先注意的问题。
五
人们最少提及的是汉人社会的农耕系统问题,以为相比上述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要好些。实际上,汉人社会广大农村和城市都在20世纪后半叶遭受了所有制巨大变更与大型基本建设的影响。“以粮为纲”政策的大面积实施极大抑制了多种经营,粮食单产提高的代价是农作物品种单一、自然灾害(气候和病虫害并存)频生。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农人一样,汉人社会也在走如同美国超级市场的垄断性的品种减少/集中的过程,生物—食品品种多样性的商业限定已经在中国的超级市场里呈现。在人类受益和受害于化肥和农药的同时,水泥沟渠的普及摧毁了古老田埂栖息的无数动植物,由此消失了无数传说、崇拜(如水神崇拜)和人类生活陶冶的天然对象。上个世纪华北的农民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动员中“向大自然开战”,又学习科学控制的各种方法,在使农作品种减少和产量受益的同时,也无形中铲除了许多节气和民俗。科学和信仰实际上难以互为替代,二者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认知理念。所以今日汉人社会再次“复兴”了民间信仰。新的信仰和旧的神明是在提醒区域文化存在的文化整体性,因为现代物质社会的功利需求不是唯一的,而心理与精神需求将在急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经过整合而重新显现。例如,在华北农村和北京城里与“四合院”和“大杂院”构成的街道—胡同—院落邻里系统伴生的小型哺乳动物黄鼠狼、刺猬和飞蛾等多种昆虫等,随着楼群丛生与树木减少而消失,也随后丢失了北京城乡农民和市民共有的、和古老庭院共生的花草鱼虫情趣,丢失了多种自然传奇故事与信仰崇拜(如“小脚娘”——黄鼠狼信仰)。这是农村所有制变动与单一作物政策长期实施、城市建筑与家庭邻里系统配置剧变引起的生态区位失序的结果之一。
汉人社会文化的濡化受到现代社会建设的空前的挑战,城市被动性搬迁和楼群人际的疏离感加剧,动摇了家族伦理与道德传统,农村家族制度和村落之间的关系因所有制长期变动不已而尚未找到良好的协调运作机制。现在西北的物质精神文化在中国的进程从20世纪初的浮在表层到今日西化城市系统搬用而引发的两种文化的激烈角力之时,尚未看到本国良好的调动了自身文化精粹的深思熟虑的设计与规划。这种文化中断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民众所栖息的传统城乡生态系统被打乱,本土文化退缩而人类学意义上的生态文化适应尚未呈现。这说明,中国城乡社会文化的整合的确任重而道远。
六
在人类不同宇宙观、政治运动、科学与市场经济行为等外力干预下,林—切氏经济文化类型的原生和理想型系统状态都已经面目全非。所剩一些地理区域硕果仅存的原生文化生态系统的研究,如中国各地的神山系统研究,这对当地信仰者来说是理所应当的族群宇宙观与行为方式的统一,而对外在者——那些终于理解了生态惩罚的严重性的俗世人们而言,神山系统对植物和动物种群的慈悲关爱仅仅是一种意外的结果与侥幸。因此,今日关于神山系统的多种研究的意义,在于警示那些总是轻率地开发大自然的无知世人。
今日的世界性与国别性的生态与环保机构及其众多项目为扭转全球生态系统颓势贡献了力量。然而由于各个机构宗旨与人员专业组成的差异,造成一些区域性的生态与环保项目偏重于自然科学和动植物生态学的视角,而对由不同族群文化、社会问题引发的症结之观察不够深入,尤其是一些项目缺少对当地人的主动咨询,忽视了当地人的主体性与智慧。因此,这样的项目常常是项目基金停止的时刻就是生态环境治理结束的标志,所谓治标不治本。也就是说,基金没有用到实处,当然项目也就没有持续性之可能。
实际上,上述生态系统失调地区的问题还包括文化生存的问题,也就是说,那些植被破坏、动物种群濒临灭绝等情形,总是和那里人民的生计衰微,心理病症,文化认同迷失,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相伴随。所谓文化生存是一个弱小族群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因其生计与文化前程受到损害,故必须想方设法保持其文化传统的权益。经常的情况是,在外部环境的干预下,人们起来维护自己的文化特征和文化认同,从而保持作为一种文化的独立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比“文化保护”更为主动,是文化主体内在的主动性推动的挽回生计与社会文化颓势,是主体性的生存和发展。(14)
当上述四种传统生计方式被外力干预后出现不可逆情形的时候,一种情况是一个族群古老的生计与生活方式消失了,另一种情况是人们设计和推行的生计与生活方式难以成功。那么,人们可以找到第三种生计与生活方式吗?
笔者曾在西南部中国的山地社会进行调研,那些曾经游耕的山地族群已经渐渐处在半游耕乃至完全定居的状态,但文化适应并未成功,目前他们已能合理运用沼气和太阳能,大概是那里气候炎热和日照充足地区转换新生计和新生态系统的最有希望的办法。那里的经验是,一种新技术的合理选择极其巧妙地纳入传统游耕与农耕社区的新的生态系统中,其成功的标志之一就是该系统的新的良性循环以及同地方文化的合理整合。根据笔者在华北和新疆的调查,20世纪80年代的华北农村太阳能系统试验,有时拆掉了农民世代喜爱的热炕系统,因此整个系统试验受到以老年人为代表的部分抵制;在同一年代,新疆地区的一种“节柴炉”忽略了维族人民祖辈习惯的烤馕功能,也遭遇了实实在在的技术推广的“文化挫折”。现在,中国广西的山地社会的沼气系统推广成功,不仅没有遇到阻碍,而且获得了新生计系统中容纳的新文化的要素。这是一个对有破损的族群文化生态系统做“填充”式的、成功的技术系统支持设计。(15) 但不要忘记,其设计的思路已经考虑到当地人民的民俗生活特点,所节约的单位时间又为新的生计、新的文化赢得了机会。一般说来,现代人类环保的努力常常和商业市场的原则相抵牾,但沼气技术—文化系统的成功建立则获得了一个新的文化的良性整合。同样,在昔日游猎、游耕和游牧地区也会发现新的文化—生态系统的新的适应方式,而任何新的系统规划也必定以地方人民的文化主体性与文化适应性为前提和结果。在帮助其发展新生计的同时,有必要让他们在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上有一个缓冲的转换时空,这是一个必要的适应时期。其间,地方人民始终不是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进去。
显然,重构一种变化了的新生计生态系统就不得不开展改善旧有系统失序状态的研究。从文化中断到文化适应,恰当的技术支持和促进文化的整合是缺一不可的。其中,地方族群的主体性地位之保持是最重要的前提,而寻找生计方式与文化心理上的转换时空是文化适应的必要过渡期。这包括可能的成功的第三种生活方式之巩固,以及可能的失败的结局的重新认识与反省。
收稿日期:2006—04—20
注释:
① 经济文化类型和历史民族区的概念由托尔斯托夫、列文和切博克萨罗夫提出,后来切博克萨罗夫来中国,和林耀华教授共同以此概念对中国版图进行经济文化类型划分。参见列文、切博克萨罗夫《经济文化类型和历史民族区》,《民族问题译丛》,1959年《民族学专辑》;林耀华、切博克萨罗夫《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载林耀华《民族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 J.H.Steward,Theory of Culture Change: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55,pp.40—41.
③ Emilio F.Moran,Human Adaptability:An Introduction to Ecological Anthropology.Boulder:Westview Press,1982,p.57.
④ Stan Stevens(ed.),Conservation Through Cultural Survival:Indigenous Peoples and Protected Areas,Washington DC:Island Press,1997,p.3.
⑤ 参见任国英《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物质文化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187页。
⑥ 参见任国英《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物质文化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264页。
⑦ 参见唐纳德.L.哈迪斯蒂《生态人类学》,郭凡、邹和译,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Rappaport,R.A.,“Nature,Culture and Ecological Anthropology”,in H.L.Shapiro(ed.),Man,Culture and Socie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⑧ Roy.A.Rappaport,Pigs for the Ancestor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Rappaport,R.A.,“Nature,Culture and Ecological Anthropology”.in H.L.Shapiro(ed.),Man,Culture and Socie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⑨ 参见庄孔韶《中国西南山地民族人类生态学研究》,载《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庄孔韶:《民族生态学的基本问题》,《民族资料摘编》1987年第2期;庄孔韶、张小军《留民营——中国北方一个汉族村落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1984年;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⑩ 庄孔韶:《基诺族“大房子”诸类型剖析》,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11) 庄孔韶:《中国西南山地民族人类生态学研究》,载《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12) 参见吉尔格勒《游牧文明史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174页。
(13) 刘源:《文化生存与生态保护——以长江源头唐乡为例》,中央民族大学打印本。
(14) Stan Stevens(ed.),Conservation Through Cultural Survival:Indigenous Peoples and Protected Areas,Washington DC:Island Press,1997; Reyhner,“Cultural Survival Vs.Forced Assimilation:the renewed war on diversity”,Cultural Survival Quarterly,Jon.2001 25.2.
(15) 庄孔韶:《重建族群生态系统:技术支持与文化自救——广西、云南的两个应用人类学个案》,2004年“中日生态移民:实践与经验会议”。
收稿日期:2006—0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