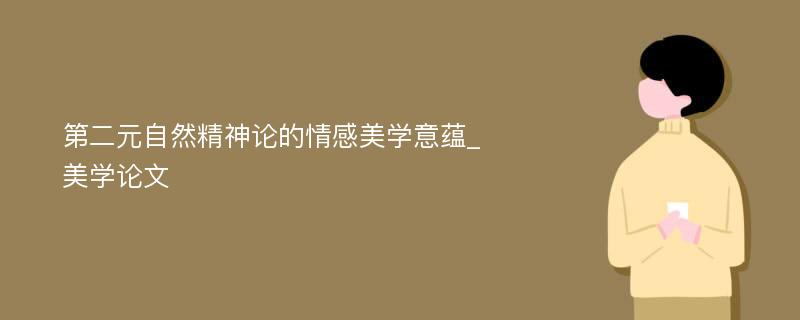
二袁性灵论的情感美学蕴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灵论文,蕴涵论文,美学论文,情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明袁宏道(1568—1610)和清季袁枚(1716—1798)隔代相继提出和张扬性灵论,这一理论作为明清时期主情美学思潮中的一个独特形态自有其理论特色,不仅在当时的文学批评和文论嬗变中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上,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与以往关于二袁性灵论的个案研究和诗学视角不同,本文着重从综合研究和情感美学视角进行专题探讨,深入分析二袁性灵论的基本内涵和性质特征,两者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其对情理、情形关系的新识,以及它在明清情感美学思想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和独特贡献。
一、性灵论的基本内涵和性质特征
明清时期是中国社会历史大转折时期,也是由古典文化精神向近代文化精神艰难蜕变的时期。这一时期,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经济伦理思想的涌动,在社会方面形成了不可阻挡的市民思潮,它以追求个性解放和高扬个体感性欲求为精神特色。与此相应,在文艺方面则出现了主情美学思潮,它以倡导个性自由和情感解放为思想特征。市民思潮和主情美学思潮都以自然人性论和趋新趋俗为共同特征。当时王学左派由开掘心主体的感性内容而引申出对个体感性存在的认识,南宗禅自性论由激扬色空无碍思维方式和狂禅行为方式而导引出对个体感性欲求的认可,由此生发和提升为与孔孟的道德理性和程朱的本体理性相对立的自然人性论和个性自由的观念〔1〕。 产生于这一特定社会经济基础和文化契机的明清主情美学思潮,以诗学系统的诗歌抒情论和曲学系统的戏曲写情论以及小说学系统的怨愤著书论为三大流脉,以徐渭的情真论、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唯情论、张琦的情痴说、王骥德的咏情论、袁宏道的“性灵”论、冯梦龙的“情教”说、洪昇的“情至”说、袁枚的“性灵”论以及李贽的不愤不作论、金圣叹的怨毒著书说、蒲松龄的寄托孤愤说为主要表现形态〔2〕。 这一主情美学思潮是以情本体论和泛情观为根本标志和思维高度,把情感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把缘情作为文艺的思维方式和本质特征而加以空前高扬。
在明清的情感理论系统中,袁宏道和袁枚相继以性灵论为标帜,反对从明代七子派到清代沈德潜的格调说。从性灵概念的性质特征来看,性灵主要指称个体主观情感,具有情感的属性和功能。“性灵者,即性情也”〔3〕。在袁宏道那里,性灵具有“性情”、“情实”、 “情至”的涵义。在袁枚那里,性灵具有“性情”、“情至”、“情致”的涵义。性灵概念早在六朝时期就与“情性”、“情灵”同义,偏重于指称摆脱伦理理性束缚的个体主观情感和审美情趣。刘勰《文心雕龙》之《原道》、《宗经》诸篇称“性灵所钟”、“性灵熔匠”,钟嵘《诗品》称“陶性灵,发幽思”。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谓“发引性灵”、“陶冶性灵”。庾信《赵国公集序》谓“含吐性灵”。《南史·文学传叙》称“申舒性灵”。当时随着尚情理论和畅情文学的空前发展,人们是从情感创造和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理解和运用性灵概念的。据袁宏道引用宋代杨万里关于性灵之语来看(下文有引述),杨万里是把性灵作为诗论的审美价值标准。明清时期王世懋、屠隆等人则把性灵概念作为诗歌的本质属性〔4〕。 袁宏道远祧《梁书·文学传论》“文者妙发性灵,独抒怀抱”的意旨,把性灵概念特别提升为性灵理论,作为一个诗论派别的理论标格和情感美学的独特形态。二袁的性灵论,具有独立自足的审美品格和个性自由的时代色彩,但也同中有异。袁宏道性灵论要义在于:“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5〕“要以出自性灵者为真诗尔。夫性灵窍于心,寓于境”, “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6 〕其性灵论的基本内涵指创作主体的本真情感、感性欲求和艺术灵感。这种个体情感具有自发性、本然性和宣泄性特点。袁枚性灵论的要义在于:“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7〕;“今人浮慕诗名而强为之,既离性情,又乏灵机, 转不若野氓之击辕相杵,犹应风雅焉。”〔8 〕其性灵基本内涵主要指创作主体的本然情感、率真天性和创作灵机。这种个体情感有着先天性自发性特点。二袁的性灵理论是以自然人性论为思想基础,以个性自由为美学标向,重主观抒情,重感性欲望,重天赋才情,既不同于六朝时期那种以情为美和重于审美特征的“情性”概念,也迥异于明清时期以情理中和论(以理制情)为底蕴的“性情”概念。〔9〕
二袁的性灵论受王学心本论和南宗禅自性论的潜在影响,其先验性虚灵性色彩较浓烈。性灵论把主观内在情感当作诗歌创作的源泉,所谓“师心不师道”〔10〕,“情以心出”〔11〕,“性情者源也”〔12〕,都强调创作的源泉在心灵。性灵论在性质特征上突出先天主观情感,认为诗美本质上是主体情感的表现;在主客体关系上重视创作主体而忽视对象客体,对创作主体只重视性灵而漠视思想;在题材内容上主张着重表现个体自我的闲情逸致,缺乏深厚社会内容。性灵论淡化了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退缩内心面向自我,“心灵无涯,搜之愈出”〔13〕,错认心灵为诗歌创作的源头,在性质特征上有着先验论的认识论色彩。
二、二袁性灵论的共同性
二袁的性灵论,在情感内容、情感表现、情感创造方面具有共同性。
首先,是强调情感内容的真实性。性灵论以情为本唯情是尚。袁宏道强调情感本真为贵,反对情感的虚伪性。“率性而行”的“真人”,“任性而发”以抒发“真情”,才能成为“可传”于后世的“真诗”,从真实性价值标准来看,“极意声伎”以求感官之乐也好,“究心仙佛”以祈长生之愿也好,这种“贪生畏死之心”,作为自然人性是真情的流露。诗艺就是要充分表现“人之喜怒怨哀乐嗜好情欲”这种真实情感。〔14〕。袁枚赞同“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15〕,为文学确立了传情而“传真”的审美价值尺度。他强调“情欲信”、“情果真”,要求诗人“葆真”和不失其赤子之心。诗歌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在于抒情的真实性。“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16〕。这就坚持了情感论与真实论的统一。在明清主情美学思潮中,情感论与真实论为言情派所共同提倡,而性灵论别有“传真不传伪”的理论自觉性和认识深邃性,侧重于情感本体的本真性和创作主体的真诚性的统一,显示出对文学抒情审美本质的深刻把握和对艺术情感的自足性超越性美学特征的深刻理解。
其次,是注重情感表现的独特性。性灵论在强调情感内容真实性的基础上又注重情感表现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主要包含情感本体的个体性和创作主体的独创性。袁宏道声称“大丈夫当独来独往,自舒其逸”〔17〕。他特别强调“独抒性灵”,“本色独造”〔18〕,“独抒己见”〔19〕,重在突出情感表现的独特性。“各出己见,决不肯从人脚跟转”〔20〕,高度申扬了诗家的独创性品格。独特性既与真实性相关,“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21〕;同时也与新异性相联,“流自性灵者,不期新而新”〔22〕。自出手眼,戛戛独造,“只要发人所不能发”是“真新奇”〔23〕,这是艺术创造的基本原则。袁宏道自觉地运用这一美学原则去反对明七子派的形式复古主义。
袁枚也注重创作主体的个性特征和独创精神。其所谓“创解”、“著我”、“吐故吸新”就是要求创出己意。作家皆独往独来,自树一帜,“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24〕。他认为诗写“各人之性情”〔25〕,作诗不可以“无我”而必须“有我”,“我”又须有“独知”。“我”即指诗人的创作个性,“独知”即指诗人独特的审美感知力。“天真还是一家言”〔26〕,“能各自成家而光景常新”〔27〕,这是要求诗家的独特个性与其特殊的才气和天赋融为一体而自得其得创意出新。袁枚还认为,既不能重复别人,学韩(愈)、杜(甫)而能变韩、杜,同时也不可重复自己,“使韩、杜生于今日,亦必别有一番境界,而断不肯为从前韩、杜之诗”〔28〕。袁枚自觉意识到不重复自己,把艺术独创性提升到一个新维度,实属难能可贵。明清言情派理论家大都认识到情感表现的独特性,“意辞要当独创”;“情以独至为真”〔29〕,较好地把握住个性化规律这一艺术创造的根本规律。而性灵论则从情感的个体性出发,由内在逻辑关系必然推导出情感表现的独特性,这是其同中相异之处。
再次,是重视情感创造的风趣性。由性灵的“天性”、“天真”又自然引出风趣。袁宏道力倡“求趣”、“唯趣”,“夫诗以趣为主”〔30〕。要求艺术情感创造“各极其变,各穷其趣”〔31〕。趣可分为童趣、清趣、俚趣。儿童具赤子之心,天真烂漫而富生趣,这是真率的童趣。山林狂士无拘无缚率性自适,自在而成趣,这是自然的清趣。市井平民率心而行己所欲,其对自然人性的真率表露也是一趣,是世俗的俚趣。这种童趣、清趣、俚趣表现出本真性特色,统称为“真趣”。与此相反,那种人为造作的所谓清远之趣,是非自然非本色的伪趣,只不过是“慕趣之名,求趣之似”。袁宏道还指出,趣与理不相兼容,“入理愈深”,而“去趣愈远”〔32〕,而趣多也会导致“理诎”〔33〕。“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34〕,这虽然把趣致描绘得神秘而难以捉摸,但也揭示了趣致的体悟性审美特征。
袁枚也非常重视风趣,强调“风趣专写性灵”,把风趣视为性灵所派生的内在特征。风趣既为性灵所派生,即与格调相扞格。格调只求“形似”,风趣则通于“灵机”。“诗有格无趣是土牛也”。〔35〕袁枚引用宋代杨万里之语:“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36〕这里指出风趣与“天分”、“天才”相联而与理知、“学力”相屏,突出了风趣的天赋性妙悟性色彩。“味欲其鲜,趣欲其真”〔37〕,无论是天趣、生趣、巧趣、机趣皆以真实为底色,指明了风趣的本真性并把风趣视为诗艺创意的一个成功要素。
二袁所讲的风趣,内源自性灵自我的张力,外现为清虚淡远的风致。当时诗论家普遍讲求真趣和妙趣。二袁则除了要求趣以致其真和趣以臻其妙之外,主要强调了风趣与“天分”、“才情”、“神悟”的关系及其自然性、虚灵性、体悟性特征。
二袁性灵论的共同点在于情感内容的真实性、情感表现的独创性和情感创造的风趣性,它们是三位一体、互动共生的。
三、二袁性灵论的差异性
二袁性灵论的不同点主要表现在表情方法的直寄性与工巧性之分和审美追求的平淡和灵动之别。
关于表情方法的直寄性与工巧性之分。
袁宏道前期偏重于表情方法的直寄直抒,“任性而发”,“直写性情”,“信腕直寄”〔38〕。直寄方法虽然突出情感的自发性宣泄性,但难免有浅露率直之病。袁宏道物为这种“太露”之病辩解:“曾不知情随境迁,字遂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并肯定屈原《离骚》怨情的直抒性特点,“忿怼之极”,“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穷愁之时,痛哭流涕,不暇择音怨矣,宁有不伤者?”〔39〕这里充分肯定了屈原发愤抒情的直致性特点,用“不暇择音”来概括怨情直致的内在必然性,突出了情感抒发的力度(爆发力和冲击力)和强度(高势能情感)。袁宏道是以直寄性表情法来反对儒家传统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主文谲谏的法式、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原则,亦即情理中和论(以理制情)、情感节制论。从屈原的发愤抒情论到后来的怨愤著书论都有不暇择音、直赋直陈的特点。袁宏道正是从反传统的角度高度赞扬屈原赋“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的美学风格〔40〕。但如果从艺术节制论和艺术内在规律来看〔41〕,直寄法只备一格,不能以直寄法代替比兴法。
与袁宏道偏重于直抒直寄的表情法相异,袁枚侧重于贵巧贵曲的表情法。袁枚把“传真”与“传巧”统一起来,要求诗艺“传巧不传拙”〔42〕,以《礼记·表记》所载孔子之语“情欲信,词欲巧”为经典根据而力倡“言之工妙”〔43〕。他从修辞尚巧推及作诗尚巧,确立以巧为美的审美原则。“凡作人贵直,而作诗文贵曲”〔44〕。表情方法宜曲不宜直,宜巧不宜拙,着意于含蓄蕴藉而不满于“率直”、“刻露”。所谓巧曲工妙,就是善用比兴婉曲致意,幽深迷人而余味无穷。袁枚批评那种不巧而拙、不华而朴的浅层次境界,意在提倡巧而后朴、浓而后淡的高层次境界。他的尚巧思想与其艺术风格多样化、审美追求灵动化的主张相契应。
二袁的表情方法虽然各有偏重,但并不是极端化绝对化。合二袁的表情方法,直寄与婉曲兼赅,赋与比兴互补,构成表情方法的多样化圆融化。二袁都反对情理中和论、情感节制论,但袁宏道所偏重的直寄方式,“情无不写,未免冲口而发”〔45〕,在情感宣泄上重快感而轻美感,忽视艺术节制论和艺术内在规律。袁中道后来对这种直摅胸臆而发泄太尽的弊端进行了自赎性反省。
关于审美追求的平淡与灵动之别。
袁宏道在后期审美追求中由狂禅的激越而转向平淡,以平淡为美,把平淡视为性灵论的本体特征和圆融境界。他把情感比之于水体,水至流至活,情感如水之无停流,恣肆而有“露”的特点;水至清至淡,情感“如水之极于淡”,澄清而有“淡”的特征。直露成为情感的表现方式,平淡则成为抒情的审美特征。“惟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灵也”;“惟淡也无不可造,无不可造,是文之真变态也。”〔46〕这就以艺术辩证眼光看到了平淡美的本真自然与妙造自然的整合性。平淡美的本质特征在于自然,它不累于理性认识,不累于学养学力,不累于刻意造作,因而平淡之中见真淳,平淡之中含清虚。袁宏道尚平淡而以平淡为美,是他由南禅主悟转向净土主修,由“放纵”转向“自律”之淡修自守所带来的审美追求的转变〔47〕。他晚年弃狂禅而走向淡修,也是对“往时大披露,少蕴藉”的一种反拨救正〔48〕,其佛学思想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文学审美追求的变化。
袁枚把“性情”和“灵机”作为其性灵论的两大理论支柱。他崇尚灵机,灵机在内在构成上表现为灵性、灵感,在审美特征上表现为灵动、活脱。在袁枚看来,作为创造力要素的灵性灵感来自“人之天殊”〔49〕,是一种天赋禀性和先天才能。“诗文之道,全关天分”,“用笔构思,全凭天分”〔50〕。天分即指代灵性灵感和特殊才气。袁枚《遣兴》诗谓:“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常见的对象客体一经艺术灵性的点化,就会成为自然灵妙富于情趣的美的作品。袁枚虽然强调了灵性灵感对于艺术创造的激活和点化作用,但却给其蒙上了先验的神秘色彩。从审美追求上看,袁枚崇尚那种灵动活脱的美感形态和艺术境界。灵动活脱要求充满生机活力,漾溢着“生气”、“生意”和“生趣”。“人可以木,诗不可以木”〔51〕;“宁可如野马,不可如疲驴”〔52〕,这里着重于灵动的神韵。“诗无生气,如木马泥龙,徒增人厌”〔53〕;刚出水的鱼虾,活泼泼地色味俱鲜;“死蛟龙,不若活老鼠”〔54〕。这里着重于鲜活的品味。灵动鲜活之标能擅美而为诗艺增添无限的活力和魅力。
性灵性所崇尚的平淡和灵动的审美特征,虽然标示出二袁不同的美学风神和审美情趣,但也从不同维度折射出性灵论的清虚的性质特征。性灵论着重于个体主体的自我情感,作为主观情感源自心灵而虚化,作为一己情感闲适自得而淡化。它离异主客体关系,向心内求返观默照,向往一种虚灵澄淡的精神境界,因而也衍生出平淡和灵动的审美追求。
四、性灵论对于情理、情形关系的认识
中国情感美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在内容方面包括情与性(情感与人性)、情与理(情感与理性)、情与欲(情感与情欲)、情与形(情感与形式)、情与景(情感与景物,涉及物感说和移情论)、情与美(情感与美感)的关系。这六种关系从不同维面标示了对情感本体的整体性和认识历程。中国情感美学思想发展到明清时代,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主情思潮,它以个性解放为精神特色而带有新的时代色彩,它在上述六种关系中均有突破性的新进展。就性灵论而言,它在情与理、情与形关系方面则有新识,应予重视和总结。当然,这种理论新识是以二袁反对崇古拟古、求变求新的精神为思想基础的。袁宏道反对明七子派的形式复古主义,袁枚批评沈德潜的格调说,坚持了文学发展通变观,高扬了反对传统的批判精神和革新精神。袁宏道提倡“穷新极变”和“宁今宁俗”,袁枚反对“舍己从人”,主张“有我”、“著我”,都认识到古今差异的历史必然性和文与时俱变的发展趋势,把握到文学的内容决定形式的基本规律,因而坚持批评从明七子派到沈德潜的形式拟古倾向和形式至上思想。二袁的性灵论关于情与理、情与形关系的新认识就是以此为前提的。
其一,对于情感与理性关系的认识
情感与理性的关系是中国情感美学理论中必然要正视的基本矛盾关系。儒家传统的理性美学观主张以理制情以理囿情而崇尚情理中和论(包括政治教化说,温柔敦厚论,发乎情止乎礼说,以道制欲论,乐通伦理说,乐以象德论等多种表现形态)。与此相颉颃的是情感美学观,力倡以情格理以情融理而标举情感本体论(包括缘情绮靡说和怨愤著书论两个系统)。前者言志求善,后者缘情求美,两者互抑互渗而前者居于统制地位。到了明清时期,主情美学思潮空前高涨,对情感与理性关系的认识表现出新的思想特色。这一时期,情理之辨具体表现于是以情抗理还是以理节情,整个趋势是从情感至上论逐渐转向对传统理性的文化复归。性灵论作为特异形态的情感论,受到自然人性和李贽童心说的直接影响,偏执于个体主体的自我情感,以心灵为创作之源,割裂主客体关系,因而坚执地以个体情感排拒道德理性(仁义礼智信)、本体理性(伦理化的理本体)和认识理性(指学识学力)。袁宏道肯定“嗜好情欲”为人性自然,反对理学禁欲主义。他曾坦然自白:“屈指平生别苦,唯少时别一江上女郎”〔55〕;肯定通俗民歌《劈破玉》、《打枣竿》之类“真声”的可喜可乐;认同怨情直致的美学风格而漠视温柔敦厚的诗教。他不仅以个体情感拒斥道德理性,而且认为自然趣韵与认知理性(“闻见知识”)不相兼容,要求“去理”而不要为“学问”、“识见”所缚,入理愈深而去趣愈远,“理必入微”而不可得韵〔56〕。袁宏道还批评宋诗之弊“流而为理学,流而为歌诀,流而为偈诵”〔57〕,指出理学诗禅理诗都堕入理窟而有理障。
袁枚对于沈德潜提倡诗“必关系人伦日用”和教化中心说以及崇尚温柔敦厚的诗教这种理性美学观持批判态度,以情感之真排斥道学之伪,认为“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情之所先,莫如男女。”〔58〕他指明男女之情为世俗性自然性情感,是人类情感中最本质的情感,歌颂男女爱情是诗歌的永恒主题和不朽魅力。他公然自称“袁子好味好色”〔59〕,竭力为人的自然本性张目,并且认定艳情诗自是诗家一格。袁枚不仅以“天性多情”排斥“义理之学”,以“天分”屏蔽“学力”,而且批评以学问为诗以考据入诗的时风。这种学理诗以诗明理是一种变相的理性美学观。“考据之学,离诗最远”〔60〕。以考据入诗实质上是炫耀学力而缺乏灵气才情,也是一种“理障”。“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61〕。诗艺不关考据也“不专砌填”(用典)。“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62〕。钟嵘《诗品序》批评了玄理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理障,提出了吟咏情性不贵用事的箴规。
二袁性灵论是绝对尚情的,作为彻底的情感美学观,它在情理之辨上是执情以遗理,坚决反对传统的理性美学观。它与汤显祖的“情有者理必无”〔63〕的以情括理论相呼应,与冯梦龙的“情为理之维”〔64〕的以情系理论为同调,与叶燮“情必依乎理”的“情理交至论”〔65〕相异趣。从明清情感美学理论新维度来看,“古之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今之所谓发乎情必戾于理”〔66〕,已认识到尚理论与尚情论的嬗递趋势和情胜于理的时代潮流;“理范于同,而情生于独,独之所生固未可强同”〔67〕,已把握到理与情的特殊矛盾特点和情感创造的个性化规律。其所标举的以情格理论和所揭示的艺术个性化规律是一种理论突破,性灵论关于执情遗理和崇尚“独造”的主张与这两个理论新识正是同声相应,表现出创造性的理论品格。
其二,对于情感与形式关系的认识
情感与形式的关系也是中国情感美学理论所必须正视的基本矛盾关系。汉代《淮南子》的情文相称论;汉魏诗赋理论关于情感与丽美(形式美)关系的论述〔68〕;六朝时刘勰的“情采”说,当时缘情理论涉及到情感与文辞、声律、对偶的关系和抒情与“造形”、“赋形”的关系;唐代皎然和司空图的情感超形论〔69〕,都从不同维度认识到情感与形式(包括内形式与外形式)的关系。二袁的性灵论与七子派和沈德潜的格调论之争,实质上是情感(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之争。从明七子派讲求格调到沈德潜标举的格调说,专从体制、法式、格律、声调外部因素着眼,专以依傍模仿为能事,拘宗汉唐成法不知通变,形式“求似”而不出新,是一种形式拟古主义。格调说作为一种以情为用的形式论,其根本失误在于,拘泥于古人格调模式而不知形式创变(格调又局限于一种模式范型);以形式代替内容而违背内容决定形式的普遍规律。袁宏道提出文体日变,法不相沿,“文章新奇,无定格式”〔70〕,强调形式的历时性因革,反对偏执于古人形式范型而不推陈出新。他批评明七子派只见格调不见性情,“其高者为格套所缚,如杀翮之鸟,欲飞不得;而其卑者,剽窃影响,若老妪之傅粉”〔71〕。他在“心”(性灵)与“体”(体格)、“情”(情感)与“法”(法式)的关系上是以前者挈领后者。袁枚主张以时代递变论格调,批评只讲诗格不讲性情、好谈格调不解风趣、只求调式不讲神悟的偏向,造成有格无情、有格无趣、有格无悟的弊端。“至于性情遭遇,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袭之”〔72〕。即反对形式拟古,也批评“征典求书”,依傍考据。认为形式风格可以多种多样,情感表现不可强求一律。
性灵派认识到内容决定形式的根本规律,它从纠偏角度出发批评格调派只重形式技巧不重情感内容的极化倾向,但又矫枉过正有失偏激。袁宏道要求“于情无所不畅”与“于法无所不有”的一致〔73〕,袁枚提出“情文双至”的标准〔74〕。虽然他们在思想上意识到情感与形式必须统一,但在实际操作上是唯情感内容是重而忽视形式美规律。袁宏道所谓“信腕信口,皆成律度”〔75〕;袁枚所谓有“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之外”〔76〕。“多一分格调,必损一分性情”〔77〕,这是从情中形外理论走向情形对立的偏向。从情动于中而形于外理论这一意义来说,格律在情感之中,这里注意到两者的一致性,但由此而滑向以情感屏蔽形式一端,虽然旨在反对形式主义,但也有否定形式自身规律之嫌。这样,从格调派到性灵派是从单纯追求形式美转向单纯追求情感美。格调派重形式不重情感,性灵派重情感不重形式,两种相异偏向,同一思维特征,即情感与形式的离析。而徐祯卿从艺术辩证思维角度,针对格调派之弊而提出“因情立格”的新美学的原则〔78〕,性情与格调融合为和谐之美,坚持以情定格以格畅情,情形互动互补的整合观。袁中道曾以情形递嬗的发展眼光指出,格调派形式主义倾向极化而性灵派起而“以性情救法律之穷”〔79〕。性灵派以情感救正格调派之弊,对于克服形式拟古倾向和形式至上理念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扭转时尚不良诗风的重要作用。性灵派与格调派的这种情形之辩,是和戏曲界临川派与吴江派关于表情与声律关系之争相映成趣的,在戏曲表情论的基础上,汤显祖力倡以情役律论,要求表情不受曲律约束,使曲律屈从表情,有忽视形式规律之嫌。沈璟则力主以情适律论,坚持表情要“谐律”,宁可协律而不惮屈情,陷入形式主义偏向。前者以情感表现来打破形式规范,后者以形式规范来束缚情感表现,各有偏颇之处。性灵派和临川派关于情形之辩的趋同性,说明他们毕竟把握了内容决定形式的根本规律,虽然反对形式倾向而有忽视形式自身规律之嫌,但却坚持了情感意蕴这一更为根本的方面。性灵派对创作主体的情感动力的热切呼唤和情感创造个性化规律的激切高扬,代表着时代的美学主潮和显示出时代的精神脉动,由此而昭示出性灵论在明清情感美学思想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和独特贡献。
注释:
〔1〕参阅拙文《试论中国理性观念的整体流变》, 载《江海学刊》1997年第2期,《试论中国理性观念演变中的共轭关系》, 载《西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
〔2〕关于“愤书论”, 参详拙文:《发愤著书:一种古典情感美学观》,载《福建论坛》1990年第3期; 关于汤显祖和洪昇的情感理论,参阅拙文:《论汤显祖的情感美学观》,载《江海学刊》1990年2期;《洪昇〈长生殿〉的情感美学思想》, 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1年第2期。
〔3〕钱泳:《履园谭诗》。
〔4〕见屠隆:《鸿苞节录·文章》; 王世懋:《李唯寅贝叶斋诗集序》。
〔5〕袁宏道:《叙小修诗》。
〔6〕江盈科:《敝箧集序》转引袁宏道之语。
〔7〕袁枚:《随园诗话》卷五。
〔8〕袁枚:《钱玙沙先生诗序》。
〔9〕明清时期, 言志派和言情派都使用“性情”概念而赋予不同涵义,言志派的性情概念指称伦理化的雅正之情;言情派的性情概念指称不受伦理理性制约的个体情感。
〔10〕袁宏道:《叙竹林集》。
〔11〕袁枚:《随园诗话》卷六。
〔12〕袁枚:《陶怡云诗序》。
〔13〕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
〔14〕袁宏道:《叙小修诗》。
〔15〕袁枚:《钱玙沙先生诗序》。
〔16〕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十。
〔17〕袁中道:《中郎先生行状》。
〔18〕袁宏道:《叙小修诗》。
〔19〕袁宏道:《叙梅子马王程稿》。
〔20〕袁宏道:《与冯琢庵师》。
〔21〕袁宏道:《与丘长孺》。
〔22〕江盈科:《敝箧集序》。
〔23〕袁宏道:《答李元善》。
〔24〕袁枚:《随园诗话》卷七。
〔25〕袁枚:《答施兰宅论诗书》。
〔26〕袁枚:《随园诗话》卷七。
〔27〕袁枚:《随园诗话》卷一。
〔28〕袁枚:《与稚存论诗书》。
〔29〕陈子龙:《佩月堂诗稿序》。
〔30〕袁宏道:《西京稿序》。
〔31〕袁宏道:《序小修诗》。
〔32〕袁宏道:《叙陈正甫会心集》。
〔33〕袁宏道:《西京稿序》。
〔34〕袁宏道:《叙陈正甫会心集》。
〔35〕袁枚:《随园诗话》卷七。
〔36〕袁枚:《随园诗话》卷一。
〔37〕袁枚:《随园诗话》卷一。
〔38〕袁宏道:《叙曾太史集》。
〔39〕袁宏道:《叙小修诗》。
〔40〕袁宏道:《叙小修诗》。
〔41〕参阅拙文:《艺术节制论》,载《中州学刊》1990年第4 期。
〔42〕袁枚:《钱玙先生诗序》。
〔43〕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一。
〔44〕袁枚:《随园诗话》卷四。
〔45〕袁中道:《阮集诗序》。
〔46〕袁宏道:《叙呙氏家绳集》。
〔47〕袁中道:《中郎先生行状》。
〔48〕袁中道:《告中郎兄文》。
〔49〕袁枚:《何南园诗序》。
〔50〕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五。
〔51〕袁枚:《随园诗话》卷五。
〔52〕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十。
〔53〕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三。
〔54〕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一。
〔55〕袁宏道:《与王子声》。
〔56〕袁宏道:《寿存斋张公七子书》。
〔57〕袁宏道:《雪涛阁集序》。
〔58〕袁枚:《答戢园论诗书》。
〔59〕袁枚:《再与沈大宗伯书》。
〔60〕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二。
〔61〕袁枚:《随园诗话》卷五。
〔62〕袁枚:《随园诗话》卷五。
〔63〕汤显祖:《寄达观》。
〔64〕冯梦龙:《情史·情贞类》。
〔65〕叶燮:《原诗·内篇》。
〔66 〕俞为民:《古代曲论中的写情论》, 载《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67〕王珻:《王石和文·文情》。
〔68〕参阅拙文:《“丽”:对艺术形式美规律的自觉探索》,《文艺研究》1993年第1期。
〔69〕皎然在《诗式》卷2和卷1中分别提出“情在言外”和“但见情性,不睹文字”;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提出“离形得似”,“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在实质上是情感超形论,强调了语言符号的审美遗忘和艺术情感的审美超越。
〔70〕袁宏道:《答李元善书》。
〔71〕袁宏道:《叙梅子马王程稿》。
〔72〕袁枚:《答沈太宗伯论诗书》。
〔73〕袁宏道:《雪涛阁集序》。
〔74〕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七。
〔75〕袁宏道:《雪涛阁集序》。
〔76〕袁枚:《随园诗话》卷一。
〔77〕袁枚:《赵云松瓯北集序》。
〔78〕徐祯卿:《谈艺录》。
〔79〕袁中道:《花云赋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