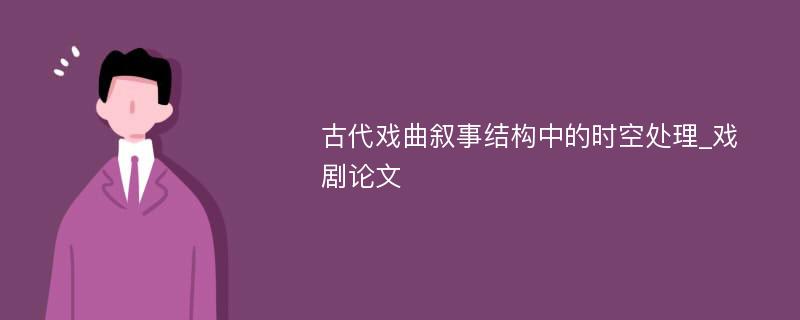
古代戏曲叙事结构中的时空处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曲论文,古代论文,时空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根据苏联戏剧理论家霍洛道夫的观点,戏剧结构是指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对戏剧行动的组织。(注:李明琨、高士产译,《戏剧结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页。)对时间和空间处理的不同,形成了中西方不同的戏剧风格。西方戏剧不强调时间的连续性,以情节发展的必然关系推演剧情,表现为板块状的时空结构。中国戏曲则强调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和连贯性,表现为线型的时空结构。我们首先分析一下戏曲的时间处理。
第一,顺时序叙事的线型推进及叙事内容时间上的无限性。
综观古代戏曲创作,在时间上都采用顺时序叙述故事始终。一般说来,这种处理方法势必导致故事的上限时间起于第一个演员上场时所表演的情节的发生时间,下限时间结束于最后一个演员下场前演出的情节的发生时间。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戏剧故事的时间长度要受到表演时间的限制。但从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中我们则发现在每一个剧本中都包容一个有头有尾、非常完整的故事,有时故事叙述时间能持续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中国戏曲顺时序的线型发展、有限的体制容量,何以能够容纳如此之长的时间长度?原因何在?
首先,作者可以通过剧中人的叙述,把故事内容的上限时间向前推移,延伸至第一个人物上场之前。如《赵氏孤儿》一开场,便通过屠岸贾之口叙述了自己与晋国忠臣赵盾不合的故事。无形中把搜孤救孤的故事上限向前逆溯了很长时间,把故事发生的背景都全盘告诉了观众。这一道白的叙事作用,历来被后世曲家推重,《赵氏孤儿》等白,直欲与太史公《史记》列传同工矣。盖曲体似诗似词,而此则可与小说演义同观”,(注:隗芾,吴毓华著,《古典戏曲美学资料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237页。)即发挥了宾白叙事的功能, 以叙述体简单介绍剧情,无形中扩大了戏曲时间容量。传奇作品在开场后进行“出角色”的活动,通过家宴,交游等情节分别叙述主人公的有关情况。其主要作用也是交待故事源起,介绍角色的身世以及个人品质等内容,这在西方戏剧中是受到反对的,西方戏剧以“动作”为“中心”,强调行动,反对离开情节逻辑而靠作者加标记(如自报家门)的形式介绍人物性格。在西方戏剧理论看来,“中国戏曲则力图表现一个故事的全过程,其开头离结尾相当远,……这就造成了结构松散,冗长的毛病”(杜书瀛《论李渔的戏剧美学》)。而这正是中国戏曲时间处理上的一个特点,符合我们审美接受的需要。周信芳指出:“这种铺叙,在戏里是不能忽略的,有些戏由于前面没有交代清楚,后面费了许多力气,观众还是无动于衷”;(《周信芳戏曲论文集》)因而这种上限时间的逆溯,把故事的原因交代清楚,是很符合其俗文学形式接受群体的需要的。如果置观众于不顾,直接展开戏剧冲突,必然会使观众如坠云里雾中,分不出来龙去脉。在对“故事背景”的叙述中,剧中人一方面作为剧中角色出现。另一方面,又作为剧作者的代言人出现,叙述相关的背景内容。这种角色的交叉与杂揉,与诸宫调等说唱文学形式有关,因为说唱艺人经常用第三人称对故事主要的背景和人物的经历进行简单的叙述说明,这都对戏曲有了直接影响。
其次,通过剧中人的叙述实现时间的跳跃。戏曲在时间处理上不追求逼真的再现,而讲究时间处理的灵活性。西方戏剧以再现为其美学原则,要求演出要毕肖生活,排斥将戏剧情节作一些暗场处理予以压缩,主张把“过去时”的戏剧事件进行“现在时”的如实表演,必须依据生活事件的长度和节奏进行演出。卡斯特尔屈维罗认为戏剧“表演的时间和所表演事件的时间,必须严格地相一致,”“它是在一个极其有限的时间内发生的,这个时间就是表演这个事件的演员所占用的表演时间……不可在别的时间内发生。”(注:伍蠡甫编,《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而我国戏曲在时间上则非常灵活,可以将时间跨度非常大的情节连接在一起。这种情况有时用楔子交代,有时靠语言或唱词说明。如《赵氏孤儿》中,程婴经过许多磨难,最终救下孤儿。第五折程婴上场即说“可早十八年过去了。”时间一下跳跃了十八年!象这样“×年过去了”一些字样,在戏曲中屡见不鲜,充分说明了时间处理的灵活性原则。有时,则以人物唱词叙述景物变化,暗示时间的推移。如《荆钗记》中《闺中思夫》一出,以丈夫去时“三月桃花浪暖”,今日“秋来风雨飘飘落,”点出时间的推移。为将时间线连接而做的这些方法,一般都叙述比较简单,“辞达而已”,不会用具体的表演叙述,也不会因此而占用明场情节的演出时间。这种处理方式应当说与小说创作中“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叙述方法有关,戏剧中加以借鉴,与中心故事关系密切的情节用明场大段敷演,关系较松散地则用叙述浅浅代过,这种处理方法也有助于突出戏剧的中心内容,在演出时间中更多地表现富有戏剧性的情节。
再次,戏曲创作中,不强调情节的戛然而止,而更多地强调“余韵”技巧,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戏曲的故事时间。中国戏曲特别强调结尾的处理,不但要收束全局,还应有袅袅余音。黄图珌《看山阁集闲笔·文学部》曰:“情不断者,尾声之别名也,又曰余音,余文,有广大清明之气象,出其渊衷静旨,欲吞而又吐者,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也。(注:《中国古代戏曲论著集成》第七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43页。)《桃花扇》则与写《余韵》一出, 并自题曰:“水外有水,山外看山,《桃花扇》曲尽矣,《桃花扇》意不尽也。”他们往往在故事情节完成之后,再加上一个抒情气氛很强的场次,将叙述故事的时间向后延展。《桃花扇》在生旦入道后,更用《余韵》一出写结束后的余波,重在抒情,但也在客观上扩展了故事的时间。梁廷楠《曲话》云:“《桃花扇》余韵作结,江山青峰,留有余不尽之意于烟波缥渺间,脱尽团圆俗套。”(注:《中国古代戏曲论著集成》第八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71页。 )杂剧中《梧桐雨》的结尾没有在马践杨妃一节停止,而是在御苑秋雨中,唐明皇面对孤寂的梧桐庭院的泣诉中结束的。充分体现了李渔对结尾的要求——“作临去秋波那一转也。终篇之际,当以媚语摄魂,使之执卷留连,若难遽别。”(注:《中国古代戏曲论著集成》第七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69页。)由于戏剧理论家对于“余韵”式结尾的激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剧作家的创作。这种激赏的原因虽出自以诗学审美来评论戏剧,但这种异于西方时间处理的技巧而扩大了戏曲的时间容量。
第二,时间的疏密处理。即根据作家创作意图,对故事情节的时间进行处理,或浓墨重彩加以渲染,或淡淡叙述“用意钩连”。我们知道,戏曲的时间广度之长、之大,是西方戏剧无法企及的,如果每个情节都严格按照故事在现实生活中持续的时间去再现生活,那么某些戏曲就根本无法搬演。而戏曲则按照作者的意图将某些情节用暗场处理,然后用剧中人以叙述的方式说出,或者用一些短场,如楔子或者过场表演,同时,又将某些情节大肆敷衍,使人物作淋漓尽致的发挥,延长其演出时间,甚至用大段的抒情场次表现生活中一个停止的“时间点”,用“间不容发,疏可走马”来形容戏曲疏密结合的时间处理特点,是十分恰当的。
如《窦娥冤》杂剧,就非常能够体现这一点。故事一共写了十六年的时间长度,楔子是对故事原委的一个交代:穷书生窦天章欠了蔡婆婆银子,为了抵债,把女儿窦娥质与蔡婆婆做童养媳。这一情节的时间较短,表演时没有做叙述化处理,也没有着力抒情。第一折时间发生在楔子故事情节后十三年,而这十三年的生活故事,蔡婆则用几句话交代过去,第一折情节较多,蔡婆婆外出讨债,几被赛卢医勒死,被张驴儿父子救下,又被张驴儿父子逼迫成亲,窦娥坚决反对,并有一套唱词,在时间的处理上,各个情节都比较紧凑、简单。第二折,时间紧接第一折,情节主要是张驴儿向赛医讨毒药,蔡婆婆要喝羊肚汤,被张驴儿投入毒药,不料被张驴儿父亲喝下中毒死去,张驴儿要挟窦娥成婚不果,告上公堂,桃杌太守草菅人命,窦娥体惜年迈的婆婆屈打成招。第三折故事情节则十分集中,就是监斩窦娥。窦娥指天骂地,控诉社会黑暗窳败,临刑前发下三桩誓愿。是一个以抒情为主的场次。第四折,距第三折事件三年。主要是窦娥鬼魂向父亲哭诉冤情,窦天章判决张驴儿。宾白极多,极密,魂旦的唱词多是对宾白内容的发挥,抒情性较第三折为差。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第三折在时间处理上最为浓重,将一折的演出时间来演述窦娥行刑前的情况。而其他则多个情节出现在一折的演出时间里,有的甚至将时间直接跳跃三年或十三年。这种疏密映衬的方法使得重点场次突出,中心情境更加真实、丰满。
那么,作者又是依据什么标准对时间进行处理的呢?
对某些能够集中反映剧中人物性格的场次,加以浓墨渲染。窦娥在前两折中性格比较单薄,缺乏个性特点。行刑前的这一场景,则是刻画窦娥性格中反抗性、斗争性一面的良好时机。于是作者用了大量的唱词,抨击世道的黑白颠倒,善恶不分。三桩誓愿,更是反映了窦娥至死不屈的抗争精神。对窦娥斗争心态、抗争精神的集中刻画,都体现了作者有意地在戏剧冲突激烈、心理行动复杂的场次中延缓时间流动,运用歌舞道白等综合手段予以表现”充分体现了戏曲作家们“重著精神,着力发挥使透”(王骥德《曲律》)的艺术追求。时间的延长是为表现人物而设的,是符合戏剧本体特征的创作手段。
时间处理的“密点”是剧中人物情感的高潮,也是创作者创作情感的高潮。作者要在此处表现自己的某种看法,并且要得到观众最富于感情的回应和共鸣。剧作者强烈的主观意图要在剧中突现,也必须在某些情节的时间中进行笔酣墨饱的刻画。韦尔特认为“高潮是给观众造成最大印象的时刻,是感情最强烈的时刻”。(注:韦特尔《独幕剧编剧技巧》,引自《编剧理论与技巧》,顾仲彝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版。)关汉卿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对于官府的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地痞无赖横行霸道的揭露是他一贯的创作原则。在《窦娥冤》中,控诉不合理的黑暗的社会现象,宣扬劳动人民至死不屈的抗争精神,既是窦娥个人故事中所要叙述的内容,也是关汉卿对人民、对社会体认和颂扬。这种观念要在窦娥死前的瞬间,作者就把强烈的个人观念附着在窦娥身上,以窦娥之口,以窦娥之歌向观众宣传。细节之处都是作者想要唤起观众共鸣的地方。由于戏剧是代言体文学,作者不能直接向台下进行宣传,而要在合适的戏剧情境中大笔勾画,借剧中人之口抒发个人情绪,否则就会破坏剧情,梁廷楠《曲话》中评《金钱记》时即说:“韩飞卿占卦白中,连篇累牍,接下来《红绣鞋》一曲,并无照应一句。”即说明了注意客观的戏剧情境,过分强调主观意图,势必会破坏戏剧效果。
由于戏剧情节时间处理不同,在演员表演时有的情节时间延续较长,有的简单表演,有的则跳跃而过,这些跳跃过去的情节时间,如果不交待清楚,则会使情节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不连贯的感觉。那么中国戏曲中又是通过什么方法使这些跳跃而过的,断了的时间线连起来的?作家们大都是通过人物叙述的方法,把暗场处理的情节,在人物下一次出场时交待清楚,如前文提到的《赵氏孤儿》。戏曲充分借鉴了其他叙事文学的特点,以精练的人物语言连接故事情节,话虽不多,却起着“用意勾连”的重要作用。所以李渔强调“欲观者悉其颠末,洞其幽微,单靠宾白一着”。(注:《中国古代戏曲论著集成》第七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55页。)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人物语言在串连情节,密结针线的作用。
第三,空间的连续流动性和空间展现的无限性。这一特点是相对于西方戏剧在“三一律”的严格要求下表现出的高度集中,高度浓缩的空间而言的。西方剧论家认为“戏剧作品是一种摹拟……与原形越相像,它便越完美。”(注:伍蠡甫编,《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65页。 )故而以固定的布景和舞台道具的真实存在做为剧中人活动的空间场所。如要表现空间的交换,就必须将布景和舞台道具也进行更换,而舞台上演出的戏剧情节也会因为布景的更换而中断,所以剧论家们指出“在同一幕中绝不要变换事件的地点,只是在不同的幕中才加以变换。”(注:伍蠡甫编,《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67页。)基于此, 西方戏剧的舞台空间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中国古典戏曲则不然,大多数戏曲作品中,往往是登山涉水,走马行船,上楼入室,空间表现上几乎穷尽了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长生殿》、《柳毅传书》、《张生煮海》等剧本中则更是显现了瑰丽神奇的天上宫阙,玲珑富丽的水中龙宫,使戏剧空间表现出一种无所不包的、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同时,我国古代戏曲在表演上又是以身带景,空间随着人物的变化而变化,演员也可以通过个人的唱念做打等综合技艺在不下场的情况下不断变换空间,使戏曲空间不断改变,如水一样流动不居。空间的连续流动和空间展现的无限性是密切联系的。一方面,空间连续流动导致了戏剧空间的变化,从总体上看表现为空间展示的无限性;另一方面,要使戏曲在空间上呈现出无穷无尽的生活情境,又必须以空间的变动不居,不断流动为基础。那么,中国戏曲空间的流动、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首先,戏曲以上下场的形式自由转换空间。通过人物上场下场前后所处的地点不同,表现空间的转移。如《救风尘》杂剧中,周舍上场,“我今做买卖归来,今日特到他家(宋引章家)去。”再次上场云:“自家周舍,来此正是他家门首,”就把两个空间很自然的连接起来。
其次,以曲词叙述空间的转换。人物不下场,通过曲词表现不同的特点,暗示空间的转换。如《西厢记》中第一折张生唱:“随喜了上方佛殿,又来到下方僧院,厨房近西,法堂北,钟楼前面。游洞房,登宝塔,将回郎绕遍。”随张生唱词,一句一地的出现了八个空间。有时,在某些抒情气氛很浓的唱词中,亦能表现地点的流动。《千忠戮》中建文帝的曲词,“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叠叠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这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飘一笠到襄阳。”主要是抒写建文帝对壮丽江山的无限留恋和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慨叹,但其情景交融的抒情方式,也让人感受到了他的一路行止。这种以语言或曲词表现行踪的叙述式方法,显然是受到了说唱文学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叙述手法的影响。
再次,用程式化的动作表现空间的流动。今天仍经常在舞台上演出的《打渔杀家》中女主角也以动作表现人在船上,船行而空间变化的情况:一会儿人物的身段动作变得不稳,手摇橹也有些吃力紧张,说明船在水流湍急的河面上前进,一会儿划桨的动作柔曼而舒缓,身体也比较平稳,就说明船已经驶入了水流平缓的水面。这些以动作表现空间移动的技法吸收了舞蹈等造型艺术的之长,用抽象的舞蹈的线条,来叙述空间和场景的变化。
最后,用圆场等程式并辅以人物叙述说明地点变动,在戏曲演出中,经常看见一个或几个角色在场上走一圈或半圈。并且以语言叙述自己行踪的变化,如《窦娥冤》中蔡婆婆到赛卢医处去讨债。即是这样处理的:蔡婆(云):我和媳妇说知,我往赛卢医家索钱去也,(做行科,云)蓦过隅头,转过屋角,早来到他家门首。地点的变化是通过蔡婆的行动,以及自述行踪共同完成的。
应该说,空间的连续流动性和空间展现的无限性是以戏曲空间的虚拟性为基础的。从上面对造成空间流动的种种原因的分析中我们发现,无论是以剧中人的唱词,道白展现空间,还是以演员程式化的动作表演空间,都没有实际存在的景物,而是以演员的表演、叙述和观众的想象共同完成的。走个圆场可以虚拟为路途三千,即使舞台上有桌椅等实际存在的道具,也仍然不能固定戏曲的空间。老旦上场,是老旦所演角色的厅堂,小姐上场,则又成了小姐的绣房,官员上场,则又变成了衙门官署。这正是中国戏曲空间的独到之处。
在空间流动性的处理原则之下,也不排斥空间的跳跃、交错的流动方法。如《琵琶记》中蔡伯喈所处的相府和赵五娘所在的陈留为二个固定空间,交替出现,一边是蔡伯喈杏园春宴,一边是赵五娘临妆感叹,一边是洞房花烛,一边是被劫跳井,一边是饮酒消夏,一边是吞咽糟糠,一边是中秋赏月,一边是麻裙包土。在空间的交替跳跃中展开对比鲜明的场景,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效果,表现了早期戏剧作家对演出场景艺术气氛的深刻认识和娴熟技巧。吕天成《曲品》称之为“串插甚合局段,苦乐相错,具见体裁。”(注:《中国古代戏曲论著集成》第六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24页。 )《长生殿》(上部)在宫庭和朝中两个空间里展开跳动,以缠绵平缓的文场,交替冲突激烈的武场,一方面调节了演出的气氛,易于观众接受;另一方面,也把安史之乱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逐渐积累,逐步强化,给观众一个逐渐加浓加重的印象,让观众体会到在歌舞升平中瞬息即发的火药味,为接下来出现的“渔阳颦鼓动起来”的急转层层蓄势。这与今天电影中所用的“积累蒙太奇”的效果是相同的,同样也是我国古代戏剧家的艺术创造。
第四,空间的全景式展现与特写式展现。在具体的空间场景的处理上,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有全景式的展现,也有特写式的局部展现,有登台演出的明场表现,也有借助人物语言和观众想象联合完成的叙述表现。
在对空间场景的全景式展现上,有一种常见的处理是,对于广阔的纷繁复杂的战争处理不直接用演员表演,而是让某一人物做为战争的见证人或目击者,向另一剧中人物叙述。如关汉卿的《尉迟恭单鞭夺槊》中对于尉迟恭和单雄信的战争情况没有让二人在舞台上进行打斗表演,而是在第四折中,让正末扮演探子向徐茂公叙述。两军交战的双方情况,对战斗场景进行全面的叙述。接下来又具体描述了双方主将交战的情况,甚至把单雄信射箭,由于紧张迸断弓弦的细节也不放过。实际上,探子只是以一个说唱演员的代言人身份出现在剧中,虽用了代言体的形式,却蕴含了叙述体的内容。
在舞上的明场演出中,我们也能发现全景式的表演和某些特写式的表演。《清忠谱·毁祠》一出,则是全景与特写显示的完美结合,以众多人物的奔走呼号和后台人物的应答奔上展示其群众性的全景,又以(净、丑作奔急撞跌介,扭打介,相骂介)展示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中的细节场面。对此,我们应当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这些空间的展示,是以谁的视点进行观察的呢?这实际上不仅与创作者冲破了代言体的限知视角有关,也与中国传统的移动焦点观察和散点观察习惯有关。一幅长卷《清明上河图》,我们感觉到画家如在汴京上空行走,视点在移动;一幅水墨山上,横云断山,山外有山,让我们不知画家置身何处进行观察。戏曲中这种空间处理方式正适应了传统的审美习惯。
第五,时空和空间关系的特殊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方式。二者不可分割,一个戏剧情节的确定,也离不开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实际上在我国戏剧情节的处理中,也多是一个情节只对应一个固定的空间和时间,即同时出现在一场中的人物和事件,其时间、空间是相同的。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有时两个情节交替出现,其空间不同,时间却是相同或相近的。有时两个人物同时出现在舞台上,其时间相同,空间却毫不相同。
同时异地的时空交错出现。《琵琶记》中赵五娘在陈留的场景和蔡伯喈在京城的场景交替出现,空间不同,但每一组对比性情节的时间是相同或相近的。表现这对原本相亲相爱的夫妻在“三不准”的封建伦理的逼迫下,一个享尽荣华富贵,一个却孤苦无依,“糠和米,本是两倚依,谁人簸扬你做两处飞?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共夫婿,终无见期”。除了传统上的冷热排场之外,我们能否感觉到一些象征性的意念:夫妻两人共用一个时间,似喻二人紧密相依的关系,两个空间,又表现了不同的遭遇与命运。在震撼人心的感观效果之外,让我们体会到了悲剧的来源在于何处,这种悲剧在历史的长卷中广度又有多少?这种同时异地的处理方式,有点类似小说中“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述方法,又有一定的进步性,小说中是以一条线为主,在叙述完插出的事件后,再返回原叙事线,是诉诸读者的阅读及阅读后的想象来完成情节的对比或映衬关系的。而戏剧则诉诸观众视觉和听觉,让观众直接感知,去了解、体会由对比而产生的艺术效果。
同时异地的时空同时出现在舞台上。元杂剧《桃花女》中就有这样的场景。舞台上一边是石婆婆按桃花女传授的方法在家中连续呼唤出外经商的儿子石留住的名字,一边是石留住在睡梦中听见有人呼叫自己而走出破土窑,摆脱了破窑崩塌,埋于三尺黄土之下的噩运。一个舞台上同时出现两个空间,这是中国舞台时空虚拟性和写意性的一种集中体现,充分体现两个情节、两个人物的有机联系。而这种情节在西方是不太可能发生的。西方叙事学家兹维坦·托多罗夫认为:“叙事的时间是一种线性时间,而故事的发生则是产生于立体的空间中,因为故事发生的实际生活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而话语只能把他们一件一件叙述出来。”(注:张寅德编,《叙事学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第294页。)中国戏曲则不囿于这种局限, 以空间的虚拟性和写意性去表现生活中这些联系紧密的故事情节。不刻意追求生活的“再现”,却“合逻辑性”地表现生活,体现生活中的有机联系,正是戏曲的诱人之处。《桃花扇·逢舟》一出更是这一方法创造的艺术精品。一个空间在李贞的船中,李、苏二人交谈,一个空间在侯方域船中,侯方域听出声音耳熟,倾而细听下,便扬声呼叫苏昆生,于是三人相认,侯方域登上李贞丽的小船,两个空间又变为一个空间。这个艺术处理是相当生动的。其实这种被人忽略的空间处理方法,又何尝不是中国戏曲的传奇之处呢?法国剧作家狄德罗曾对西方舞台上只能表现一个场面感到不满,认为“现实生活中,多个场面几乎总是同时进行的,如果同时把它们表现出来,经过互相加强,就会对我们产生惊人的印象。”(注:陆达成,徐继曾译,《文艺理论译丛》第二期,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他们这种设想却在中国戏曲的舞台上出现了。在这种处理方式之下,一方面减小了叙事的繁琐,减少了头绪。另一方面又能增加场上生动的舞台效果。
在中国古代戏曲中,还有一种同地异时的时空处理方法。如《梧桐雨》中第一折和第四折中情节的发生地相同,而人物情绪已大异。用“当初妃子舞翠盘时,在此树下;寡人与妃子盟誓时,亦对此树;今日梦境相寻,又被他惊觉了。”地点相同,时间不同,空间的景物依旧,而人事已几度沧桑,使人引发“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感慨。《桃花扇》中《访翠》、《眠香》、《题画》三出空间都在香君妆楼,但两时景物已异。《题画》眉批评道,“物是人非,情事不堪,此曲一唱三叹,无限低徊。”这种时空处理方法,在艺术上能够起到感动人心的效果,同时也能够体现出传奇“密针线”的结构要求,“不止一出接一出,一人顶一人,务使承上接下,血脉相连。”(注:《中国古代戏曲论著集成》第七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6页。)而且以情节内在逻辑联系和情感联系组织情节,更能体现剧作家对于情节、结构的深刻认知和把握,在明清剧论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关于情节结构的真知灼见:“每编一折,必须前顾数折,后顾数折,顾前者欲其照映,顾后者便于埋伏。”(注:《中国古代戏曲论著集成》第七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6页。)用空间的相似来纽结不同情感的故事情节,也能很好地体现上面的创作原则。
如果说同地异时的时空处理多以表达剧中人情感为主,并结合戏剧情节的相互照应和有机联系的话,那么用同地异时的时空来纽结剧中主要人物命运和经历的处理方法,则更显示出作者创作的匠心独具。如吴炳的《情邮记》即以“邮亭”这一空间纽结男女主人公爱情的悲欢离合:刘乾初题诗于黄河驿壁,通判王仁携家赴任时经过黄河驿,其女见驿壁题诗而和之,诗成其半。后紫箫进京时亦经过黄河驿,将诗补足。刘乾初访友归来又过此驿,见二女所和之诗。后三人终成眷属。三人行止何其太巧,都经过小小的黄河驿,足以显见作者构局之匠心。吴梅跋曰:“余谓此剧用意,实似剥蕉抽茧,愈转愈隽,文心之细,往往入扣。”也指明以“邮亭”建架合剧结构,是个人艺术所得。尽管故事情节婉转曲折,但由于有了“邮亭”作为贯穿故事的线索,并不显得头绪混乱。
以上,我们从多个方面探讨了中国戏曲在时空处理上不同于西方戏剧的地方以及各种时空处理方法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这里面有与西方戏剧相近的地方,显示了东西方艺术的共通之处,便更多的是与西方戏剧的相异之处,即能够体现中国戏剧独特的东方韵味的地方。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我国古代戏曲在时空处理中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时空处理的技巧,对于当代的戏曲、戏剧创作也应当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标签:戏剧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窦娥冤论文; 文化论文; 桃花扇论文; 赵氏孤儿论文; 窦娥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智利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