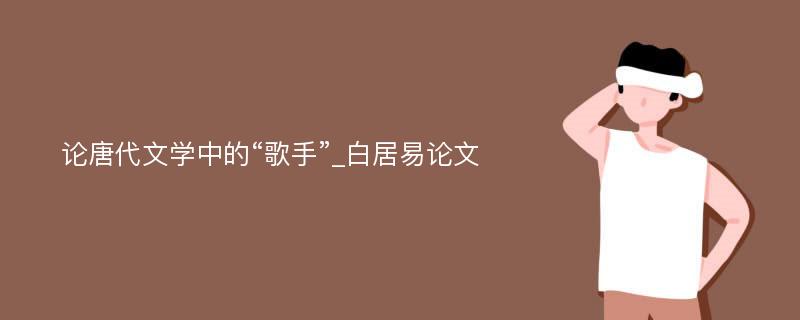
论唐代文学中的“歌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代论文,文学中论文,歌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1)03-0149-06
以“歌者”指称音乐表演者的身份,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是指从事歌唱的表演者,广义是指从事音乐的表演者,本文所讨论的“歌者”取其广义。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成员之一,“歌者”很早就为人们所关注并出现在典籍中,如《尚书·舜典》中的夔、《春秋左传》中的钟仪、《列子》中的韩娥、秦青、伯牙、钟子期等。总体而言,唐以前人们对“歌者”的关注主要是为了记述历史或阐发思想,很少将之作为纯粹的审美对象,描述时也仅仅限于他们的技艺与容貌等外部特点,如《诗经·国风·王风·君子阳阳》中的舞者、李延年所歌咏的“倾国倾城”的李夫人等。到了唐代,情况有了新变化:首先,“歌者”作为审美对象,大量地出现在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中。据笔者初步统计,以“歌者”作为审美主体的诗歌高达176首,小说虽然数量不多,约27篇(以李时人《全唐五代小说》为参照)①,但为后世所誉的唐传奇之杰作不少就是以“歌者”为描写主体的,如《柳氏传》、《李娃传》、《莺莺传》②、《霍小玉传》等。不仅如此,在唐人散文中也有不少关于“歌者”的描写。笔者对《全唐文》、《全唐文补遗》、《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进行梳理,发现以“歌者”为描述主体的篇目约有12篇之多①,其中柳宗元与刘禹锡的文章所记述的还是同一位“歌者”。其次,唐代文学对“歌者”的描写,已经由传统的外貌与技艺等外部表演拓宽到生活状况及内心世界。通过阅读这些作品,我们可以对唐代“歌者”的生活状况有更为详细的了解。如李龟年,杜甫《江南逢李龟年》描写其原来在京城生活,安史之乱以后却来到了江南;而李端《赠李龟年》则写他年迈时又从江南返回到了京城,并且仍然能够跟上当时音乐的潮流。这两首诗大致将李龟年的人生轨迹勾勒出来。如白居易《琵琶引并序》的序文与诗篇叙述了琵琶女的主要人生经历:年幼时曾入教坊学习,受到教坊名乐人的指点;青年时活跃于京城青楼,年老色衰后嫁给了商人,从此漂泊江湖。如刘禹锡《泰娘引并序》中的泰娘,一生足迹更广:苏州人,先是成为韦夏卿的家伎,随韦夏卿仕宦而在京城及洛阳等地生活,韦夏卿去世后,流落到民间;后又成为蕲州刺史张悉的家伎,张愻谪居时,她随之来到武陵郡,此后便一直滞留于此。如杜牧《杜秋娘》中的杜秋娘,原为金陵人,十五岁成为李锜的妾,李锜叛乱平定后入籍宫中,成为漳王的傅姆,年迈时因郑注用事诬陷漳王而被重新放归故乡。如杜牧《张好好诗》中的张好好,十三岁进入沈传师的江西幕府做营妓,十四岁随沈传师入籍于宣城府,十五岁成了沈传师弟弟沈述师的小妾,后来又离开沈述师,到洛阳做青楼饮妓。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歌者”的人生状况,还触及到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如元稹《莺莺传》通过莺莺与张生的感情纠结,写出了莺莺对张生的深情以及堆积内心的浓郁愁苦。如白行简《李娃传》通过李娃对落拓的荥阳公子的倾力拯救,赞颂了李娃作为歌妓所具有的不凡品格,“节行瑰奇,有足称者”、“倡荡之姬,节行如是,虽先古烈女,不能逾也”。如蒋防《霍小玉传》通过霍小玉与李益的情感发展及最终殉情,写出了她的多情,“风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除了传奇以外,诗歌如白居易《燕子楼三首》、元稹《崔徽歌》、张祜《孟才子叹》等也写出了歌妓的痴情。其他的如元稹《琵琶歌寄管儿,兼诲铁山》写出了李管儿的爱好自由:“段师弟子数十人,李家管儿称上足。管儿不作供奉儿,抛在东都双鬓丝”;梁补阙《赠米都知》写出了米都知的高洁,“贪将乐府歌明代,不把清吟换好官”等。可见,唐人对于“歌者”的观照,不再像前人那样,简单地将之与职业特点相联系,而是更多地将之作为有独特审美价值的人去观照。
当然,纵观唐人这些描写“歌者”的文学作品,我们发现其发展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分水岭: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以前,唐代文学对“歌者”的描写数量并不多。以诗歌为例,约26首,仅占整个唐代“歌者”诗歌的0.15%。不仅如此,描写内容也非常传统,除了李颀《听安万善吹觱篥歌》触及到乐人的内心以外,其他的仍以“歌者”的容貌与技艺为主,当然盛唐时期在“歌者”技艺描写上较之前人有了提升。但安史之乱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作品数量骤增,描写内容深入到他们的生活及精神世界,上文所论及的篇目基本上都产生于安史之乱以后。除了这两点变化以外,还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即这些“歌者”几乎都被塑造成悲剧形象,其不幸具体表现为生活漂泊不定、行动没有自由、精神缺少知音,情感无所归依等。上文所提及的“歌者”,生活漂泊者如李龟年、琵琶女、杜秋娘、张好好等,情感无所归依者如莺莺、霍小玉等。行动缺乏自由者,如柳宗元《筝郭师墓志》中的郭师,父母双亡后先后被吴王宙、薛道州伯高、张诫等强行滞留,逼迫表演,年迈疾病缠身才得以自由,但不久就病死异乡。精神上缺少知音者,如刘禹锡《泰娘引并序》中的泰娘流落民间后,“地荒且远,无有能知其容与艺者”;如顾况《听刘安唱歌》擅唱法曲的刘安,“即今法曲无人唱,已逐霓裳飞上天”;如元稹《琵琶歌》中的李管儿,“逢人便请送杯盏,著尽工夫人不知”、“曲名无限知者鲜”等。因此安史之乱以后,文学作品中的“歌者”往往与“断肠”、“愁”、“泪水”等表达悲伤的词语结合得非常密切,如白居易《夜闻歌者》:“邻船有歌者,发调堪愁绝。歌罢继以泣,泣声通复咽”、白居易《题周家歌者》:“一声肠一断,能有几多肠”、司空曙《观妓》:“银烛摇摇尘暗下,却愁红粉泪痕生”、高骈《赠歌者二首》:“酒满金船花满枝,佳人立唱惨愁眉”等。唐以后文学作品所成功塑造的“歌者”形象几乎都没有越出唐人藩篱,均为悲剧形象,众所周知的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如《桃花扇》中的李香君等。可见唐人在中国古代“歌者”形象史上所处的枢纽地位。正因为如此,揭示安史之乱以后,唐代文学对“歌者”描写在数量、内容及形象等方面发生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无疑极富意义。
笔者以为,其原因大致有三。首先,音乐发展的新格局及歌辞需求的增加,导致文人与“歌者”关系密切。安史之乱之前,宫廷音乐极为繁荣,它不但设有太常、教坊与梨园等多个音乐机构,使得宫廷音乐表演职责分工明确,而且还拥有众多的乐工,如李峤《上中宗书》“又太常乐户已多,复求访散乐,独持鼓者已二万员”等④。但由于朝廷对宫廷乐人的管理相当严格,除非皇帝与朝廷允许,否则禁止到宫外活动,即便出宫,也只是在一些权贵的宴会及朝廷组织的大酺上表演。关于初盛唐对宫廷乐人的严格管理,仅从记载盛唐教坊盛况的唐·崔令钦《教坊记》⑤就可以看出:如教坊女乐人模仿“突厥法”实行共夫制,而外人对此毫不知情,“同党未达,殊为怪异”(注:同党,指宫僚);如内人只有在特定的日子里才能与家中女性成员相见,“每月二十六日,内人母得以女对。无母则秭、妹若姑一人对。十家就本落,余内人并坐内教坊。内人生日是,则许其母、姑、秭、妹毕来对,其对所如式”;如崔令钦特别强调,这些史料都来源于曾在教坊呆过的武官们的讲述,“开元中,余为左金吾仓曹,武官十二三是坊中人,每请禄俸,每加访问,尽为予说之”等。因此初盛唐时期尽管宫廷音乐繁荣、宫廷乐人的数量众多,但人们对这些乐人并不熟悉。与此同时,初盛唐的民间音乐由于朝廷的严格限制而处于长期沉寂状态⑥,故民间的乐人数量极少。安史之乱前的这种音乐发展格局,导致人们对乐人的生活相对陌生。文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故当时的文学作品不但对“歌者”关注得少,而且描写时也没有突破传统,仍然在“歌者”的容貌与技艺方面下工夫。虽然此时也产生过几篇为人传颂的“歌者”作品,如李颀《听安万善吹觱篥歌》、《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等,但所作的突破,仅表现为描写这些乐人音乐表演技艺的技法方面。安史之乱以后,音乐发展出现了新局面。首先,宫廷音乐由封闭走向了开放。导致这种现状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战乱使宫廷机构受到破坏,宫廷乐人被迫流向民间。大的战乱主要包括安史之乱、德宗登基之初藩镇的联合叛乱及唐末的黄巢起义等。二、朝廷为了示宠而将宫廷乐人赏赐给朝臣,供其宴乐。这在德宗朝尤为突出,许多把持军权的朝臣曾受过这种恩赐。三、宫廷乐人受朝臣雇佣到宫外进行表演。其次,民间音乐水平也得以迅速提升,军营、家庭、市井及青楼音乐变得极为活跃。这既与宫廷音乐向民间开放从而使得宫廷的乐人、乐曲及音乐表演技术等迅速流向民间有关,又与自玄宗执政后期开始,朝廷对朝臣及百姓宴乐之风的积极倡导有关⑦。这种音乐发展的新局面不但造成了乐人数量的骤增,而且也使得乐人更加深入到唐人的日常生活,因此他们便为时人所熟悉。而就文人而言,他们与乐人的关系较一般人还更加密切,这与音乐的新发展带来了歌词需求的骤增相关。据元稹《乐府古题序》可知,唐人歌词产生的方式大致两种,一种是依声填词,一种是选诗入乐。其中文人歌诗是选诗入乐的重要来源。宋·王灼《碧鸡漫声》卷一曰:“以此知李唐伶伎,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常俗也。”如白居易《醉戏诸妓》:“席上争飞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诗”、熊孺登《甘子堂陪宴上韦大夫》:“楚乐怪来声竞起,新歌尽是大夫词”,《云溪友议·艳阳词》中的刘采春擅唱的《望夫歌》,“所唱一百二十首,皆当代才子所作”。当时著名乐人选谁的歌诗演唱,已经关乎文人的社会声誉,如唐·范摅《云溪友议·温裴黜》载当时周德华因擅唱《杨柳曲》而闻名全国,但她到京师后却没有选取当时极受时人欢迎的温庭筠与裴诚的歌诗,结果“二君皆有惭色”;甚至还关乎文人的前途,如元稹在宪宗时长期被贬,但穆宗登基不久就被重用,就与他的歌诗在宫中被乐人广为传唱有关,《旧唐书·元稹》:“穆宗皇帝在东宫,有妃嫔左右尝诵稹歌诗以为乐曲者,知稹所为,尝称其善,宫中呼为元才子”、《新唐书·元稹》:“长庆初,潭骏方亲幸,以稹歌词数十百篇奏御,帝大悦,问:‘稹今安在?’曰:‘为南宫散郎。’即擢祠部郎中,知制诰。”不仅如此,著名文人作诗给谁唱,也关乎乐人的身价及社会认可程度。如白居易《与元九书》曰:“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等。正因为如此,一些文人深受乐人们的追捧。如李贺与李益,《旧唐书·李益》“李益,肃宗朝宰相揆之族子。登进士第,长为歌诗。贞元末,与宗人李贺齐名。每作一篇,为教坊乐人以赂求取。唱为供奉歌词”、《新唐书·文艺下》:“李贺字长吉……乐府数十篇,云韶诸工皆合之弦管”;如郑员外,韩拥《送郑员外》“孺子亦知名下士,乐人争唱卷中诗”;如元稹,白居易《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暗被歌姬乞,潜闻思妇传”;如杨巨源,《酬杨司业巨源见寄》“渤海归人将集去,梨园弟子请词来”等等。故安史之乱以后,文人与乐人的联系非常密切。以元白为例,笔者曾对他们与乐人交往作过考证,其中可确证与元稹交往过的约24位,与白居易交往的约45位,并且还有5位与他们俩均有过交往⑧。交往的密切,使得乐人与文人有了更深层次的精神与情感交流,故不少成为文人的朋友、知音或恋人等。基于对“歌者”的生活状况及内心世界的熟悉、同情与感动等,文人在作品中对他们进行深入的描写,再自然不过了。
至于安史之乱以后,唐代文学中“歌者”往往被塑造成悲剧形象,其原因又大致有二。首先,新的音乐审美风尚,使乐人更多地从事悲伤乐曲的表演,并因力求声情并茂而呈现出悲伤的情态。在初唐及盛唐前期,唐人的审美风尚总体上以雅正为主。这主要与帝王及朝廷整体上对雅乐的重视有关。如唐太宗登基不久,便先后让祖孝孙、张文收主持雅乐建制,从而奠定了唐代雅乐的规模。如唐玄宗登基后让张说进行雅乐歌词改造,而自己则对雅乐乐曲进行改造等(参见《旧唐书·音乐二》)。正因为如此,此时雅乐与俗乐、华乐与夷乐之间的界限是泾渭分明的。人们对俗乐与胡乐的盛行一直持高度警惕的态度。关于这点,可以从李纲针对高祖授胡舞人以爵位、孙伏伽针对太常寺进行散乐活动以及吕元泰、韩朝宗和张说等对当时民间盛行的泼寒胡戏等所持反对意见的奏章看出来⑨。受其影响,宫廷所演的燕乐在风格上甚至也接近雅乐。《新唐书·礼乐十二》:“盖唐自太宗、高宗作三大舞,杂用于燕乐,其他诸曲出于一时之作,虽非绝雅,尚不至于淫放。”但到了玄宗执政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玄宗不但喜爱音乐,而且还精通音乐。所以其在执政之余也积极参与宫廷音乐活动。除了建制雅乐之外,他对俗乐也非常热衷。如其任太子时就参加女乐的挑选工作⑩;如唐·崔令钦《教坊记·序》载其在蕃邸蓄散乐一部,登基不久还组织这些散乐乐工和太常寺乐人进行“热戏”,并且为了安置这些散乐乐人还下诏成立专门的俗乐表演机构——教坊。同时还从太常寺坐部伎中挑选三百名乐工,教授他们法曲,这些乐工被称为“梨园弟子”,后来一些宫女也加入其中(11)。他对俗乐中的胡乐也非常喜欢,如《羯鼓录》载他极爱羯鼓,此乐器为胡乐,“出外夷,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当时龟兹部、高昌部、疏勒部、天竺部皆用之,玄宗“常云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比”,他不但精于羯鼓表演,而且还为之作曲达92首之多。玄宗对俗乐特别是胡乐热衷的态度,造成两者地位的迅速提升,如负责表演俗乐的教坊成为盛唐宫廷最重要的音乐机构;如胡乐不再像以前那样仅仅作为九部伎或十部伎的组成部分在有限场合作仪式性的表演,而是正常参与到宫廷的音乐活动,《新唐书,礼乐十二》:“开元二十四年,升胡部于堂上。而天宝乐曲,皆以边地名,若《凉州》、《伊州》、《甘州》之类。后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故从盛唐后期开始,俗乐与胡乐无论在朝廷还是在民间,其地位逐渐凸现,《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肃宗至德元载”:“初上皇每酺宴,先设太常雅乐、坐部、立部,继以鼓吹、胡乐、教坊、府·县散乐、杂戏”,唐·杜佑《通典·乐六·四方乐》“又有新声自河西至者,号胡音声,与龟兹乐、散乐俱为时重,诸乐咸为之少寝”,《通典·乐六·清乐》:“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等。
盛唐后期出现的这种雅俗乐发展不平衡的局面,除了因“安史之乱”暂时有所中断外,一直持续到唐末。《旧唐书·穆宗》载丁公著曰:“国家自天宝已后,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如白居易在《立部伎——刺雅乐之替也》题后注曰:“太常选坐部伎,无性识者退入立部伎,又选立部伎,绝无性识者退入雅乐部,则雅乐可知矣”;如白居易《废琴》:“古声淡无味,不称今人情”、《邓鲂、张彻落第》:“古琴无俗韵,奏罢无人听”等。雅乐与俗乐在审美风格上存在着巨大差异,雅乐节奏相对整齐舒缓,故使听众情绪趋向平和,而俗乐的节奏则相对丰富多变,能够激起听众情绪的波动。如白居易《听弹古渌水》“闻君古渌水,使我心和平”,如杜佑在《通典·乐六·清乐》称南方俗乐“哇淫”、“既怨且思”等。从盛唐后期开始,随着俗乐的兴盛,那些激发起悲伤情绪的乐曲逐渐成为音乐的主体,深受时人欢迎。这些乐曲既有前代流存的,又有时人新创的。如《鹧鸪》曲,许浑《听鹧鸪辞并序》序文曰“词调清怨,往往在耳”;如《梁州》,李频《闻金吾妓唱梁州》“闻君一曲古梁州,惊起黄云塞上愁”;如《伊州》,高骈《赠歌者二首》“便从席上风沙起,直到阳关水尽头”;如《竹枝曲》,顾况《竹枝曲》“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等。当时乐器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新兴的,多趋向演奏感伤的旋律为主,而乐人口中所传唱的亦以此种风格为主。仅以白居易《听歌六绝句》为例,其所提及的6首乐曲中至少有4首可以断定为悲伤的旋律。如《乐世》(亦称《六么》)诗曰“诚知乐世声声乐,老病人听未免愁”;如《水调》诗曰“不会当时翻曲意,此声肠断为何人”;如《何满子》诗曰“一曲四调歌八叠,从头便是断肠声”;如《离别难》诗曰“不觉别时红泪尽,归来无泪可沾巾。”而《相夫怜》,据宋·郭茂倩《乐府诗集·近代曲辞二》载,其原为《相府莲》,从郭茂倩所引诗歌来看,亦为悲伤的旋律,“夜闻邻妇泣,切切有余哀”、“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这样一来,6首中5首为悲伤的乐曲,可以当时悲伤乐曲所占的绝对比例。不仅如此,那些为人所称誉的乐工擅长创作的亦是悲伤的旋律。如李可及,《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八》“懿宗咸通十一年”:“乐工李可及作《叹百年曲》,其声凄惋,《叹百年曲》,历叙人自少而壮,自壮而老,少时娟好,壮时追欢极乐,老时衰飒之状,其声凄切,感动人心。”由此可见,安史之乱以后,悲伤的乐曲在俗乐中所占的绝对地位。同时安史之乱以后,随着音乐全面发展及人们音乐欣赏水平的提升,那些在表演时能够融情入乐的“歌者”深受时人赞誉。如卢纶《宴席赋得姚美人拍筝歌》“有时轻弄和郎歌,慢处声迟情更多”;如元稹《何满子歌》“犯羽含商移调态,留情度意抛弦管”,白居易《杨柳枝二十韵并序》“曲罢那能别,情多不自持”,《琵琶引》“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问杨琼》中对擅“唱情”的杨琼的赞誉等。故乐人们在表演时便因力求声情并茂而呈现出悲伤的神态。如羊士谔《彭州萧使君出妓夜宴见送》“自是当歌敛眉黛,不因惆怅为行人”,元稹《琵琶歌寄管儿,兼诲铁山》“管儿为我双泪垂,自弹此曲长自悲”等。
其次,安史之乱以后,乐人的人生遭遇为文人所了解,文人因此而联想到国家兴衰与自身命运,故滋生出伤感的情怀。一些乐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发展密切相连,如前文提及的李龟年,原为盛唐著名的市井乐人(12),出入于宫廷与权贵之家,受尽时人的追捧,安史之乱以后,却随流亡大军来到了江南。当时的江南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都非常落后,关于这点可以从白居易《江南逢天宝乐叟》、《琵琶引并序》等对中唐江南的描写看出来。故其境遇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李龟年以外,杜甫还曾关注过盛唐宫廷乐人公孙大娘及其弟子,描写了她与其弟子表演状况的强烈落差。(详见其《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无论是李龟年还是公孙大娘及其弟子,杜甫观照他们,目的在于激发起对国家兴衰的感叹情怀,因为这些人的命运转变与国家的兴衰密切相连。可以说,以乐人写国家兴亡之叹,起始于杜甫。此后顾况《听刘安唱法曲》、白居易《江南逢天宝乐叟》、元稹《连昌宫词》、王建《老人歌》、《旧宫人》等均是对杜甫这种情感表达方式的忠实追随。不仅如此,由于中晚唐乐人实行聘用制,人们可以自由雇佣他们,所以乐人易主现象极为常见,这造成了乐人的行踪不定,故他们的人生充满漂泊感。同时虽然乐人此时已经成为社会的活跃人群,可以出入于各种场合甚至宫廷,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却并没有随之得到相应的提升,仍然隶属于贱户,所以他们在诸多方面会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特别是婚姻方面,他们不得与良户、官户通婚,故在情感上往往很难如意。这样一来,那些有着卓越才情的乐人所经历的人生遭遇,引起了文人对自身命运的关注与悲叹。吴融在《赠李长史歌并序》中指出,罗隐赠诗给乐工李长史,是因为“半是悲君半自悲”。罗隐不仅赠诗给李长史,而且还赠诗给薛阳陶,后者曾做过李德裕的家乐,刘禹锡、白居易、元稹、张祜等都曾写诗赞誉过他的技艺,但李德裕被贬后,却沦落江湖,最终进入军营以谋生。(参见刘禹锡《和浙西李大夫霜夜对月,听小童吹觱篥歌,依本韵》、白居易《小童薛阳陶吹觱栗歌》、罗隐《薛阳陶觱篥歌》及五代·严子休《桂苑丛谈·赏心亭》等)罗隐在诗中通过对乐人人生遭遇的悲叹,实际上寄托的是对自身命运的悲叹。不仅罗隐有此寄托,吴融亦有,如其诗句有“咨嗟长史出人艺,如何值此艰难际。可中长似承平基,肯将此为闲人吹?”中晚唐文人由观照乐人而引发对自身命运的关注,极为常见。如柳宗元写《筝郭师墓志》后,刘禹锡读之,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与柳子厚书》曰:“倘佯伊郁,久而不能平”、“予之伊郁也,岂独为郭师发耶?”其他的如元稹之于李管儿(《琵琶歌寄管儿,兼诲铁山》、李绅之于善才等(《悲善才》),均是如此。一些女乐人的命运更易激起起文人这种感伤情怀,如刘禹锡之于泰娘(《泰娘引并序》)、白居易之于琵琶女等(《琵琶引并序》)。这可能与中国古代诗歌从屈原开始就有以女性自喻文人、以女性与男子关系比喻文人与君王之关系的传统有关。杜牧在此方面着笔尤多,其代表作有《宫人冢》、《张好好诗并序》、《杜秋娘诗并序》等。当然,上述只是文人通过观照有巨大人生变故的乐人以寄托对自身命运感叹的通常方式。除此以外,乐人单纯的身份也会引发文人的悲叹。如刘禹锡《与歌者米嘉荣》、《与歌者何戡》及《听旧宫中乐人穆氏唱歌》等作品,这些宫廷乐人都是诗人意气风发时所结识的,在被贬二十年后回到京城,与这些乐人相逢时,诗人由此发出了对自身不幸的深沉悲叹。当然,宫廷乐人所受到的恩宠也会引发文人对自己没落的感伤,如孟郊《教坊歌儿》、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五弦弹》等。
综上所述,安史之乱以后,唐代文学对“歌者”的描写数量骤增、内容大大拓宽,与音乐的新发展及歌词需求的增加导致文人与乐人联系密切,因而对他们有全面深入的了解有关。而这些“歌者”往往被塑造成不幸的悲剧形象,既与当时音乐审美风尚的变化导致乐人参与悲伤乐曲的表演,并因力求声情并茂而呈现悲伤的神态有关,又与文人观照乐人时会引发起对国家及自身命运的关注,从而融入感伤的情怀有关。
收稿日期:2010-09-19
注释:
①李时人:《唐五代笔记小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②关于莺莺的歌妓身份,参见柏红秀:《莺莺的歌妓身份与〈莺莺传〉的悲剧精神》,《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③相关篇目有:李讷《纪崔侍御遗事》、柳宗元《筝郭师墓志》、沈亚之《歌者叶记》、阙名《前长安县尉杨筹女母王氏墓志》、源匡秀《有唐吴兴沈氏(子柔)墓志铭并序》、萧蕃《唐清河张氏(德之)墓志铭并序》、《大唐华原县丞王公故美人李氏(二娘)墓志铭并序》、崔悼《郝氏女(闰)墓志铭并序》、《唐故陇西董夫人墓志》、《大唐故王夫人墓志铭》及《故美人李二娘墓志铭》等。
④董诰等:《全唐文》卷24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103页。
⑤崔令钦:《教坊记》,《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
⑥关于初盛唐对民间音乐的限制,可以从中宗对朝臣蓄家乐所颁布的诏书、玄宗登基之初禁止民间广场散乐及女乐表演,以及禁止民间表演泼寒胡戏表演等看出。文献依次详见王溥:《唐会要·杂录》卷34,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628-629页;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81,《禁断女乐敕》,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421页;陆心源:《唐文拾遗》卷9,《禁散乐巡村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1页;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109,《禁断腊月乞寒敕》,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517页。
⑦关于安史之乱以后民间音乐的活跃,详见柏红秀:《论唐代的家乐》,《艺术百家》,2010年第3期;《略论唐代的军营音乐》,《艺术百家》,2007年第1期;《宴乐之风与中晚唐宫廷音乐的发展》,《乐府学》,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
⑧参见拙作《白居易与乐人交往考》,《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6期;《乐人与元白诗歌的传播》,《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6期。
⑨董诰:《全唐文》卷133,李纲《谏以舞人安叱奴为散骑常侍疏》,第588页;刘昫:《旧唐书》卷75,《孙伏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634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18,《吕元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276页;董诰:《全唐文》卷301,韩朝宗《谏作乞寒胡戏表》,第1351页;刘昫:《旧唐书》卷97,《张说传》,第3052页。
⑩刘昫:《旧唐书》卷190中,《文苑中·贾曾》,第5028页。
(11)刘昫《旧唐书》卷28:“玄宗又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号为皇帝弟子,又云梨园弟子,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园。”第1051页。郑处诲《明皇杂录》:“天宝中,上命宫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北院。”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51页。
(12)关于李龟年市井乐人身分,参见柏红秀:《李龟年非梨园弟子辩——作为盛唐后期宫廷音乐向民间开放的一个视角》,《乐府学》20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