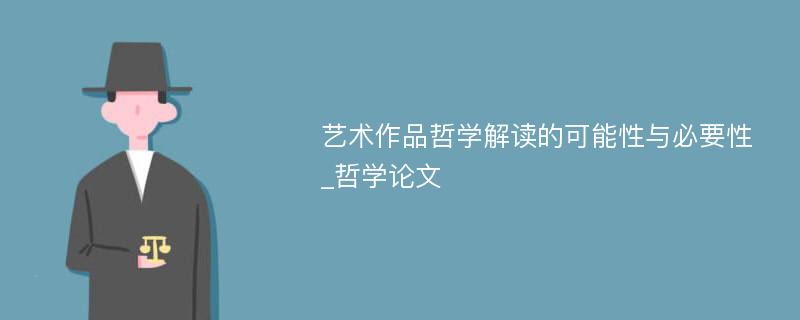
艺术作品哲学解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必要性论文,艺术作品论文,可能性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227(2003)04-0020-06
艺术作品的哲学解读到底有没有可能和必要?这个问题除了涉及到拙文《艺术作品的哲学解读是一种享受》(见本刊2003年第一期)中提到的哲学的审美维度外,还可以从艺术哲学研究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得到一些启发。所以本文拟先谈谈艺术哲学研究的重心问题,然后才进入艺术作品哲学解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具体探讨。
一、艺术哲学的研究重心问题
这个问题首先涉及到艺术哲学的定义,其次涉及到艺术哲学研究的历史转向及其所启示的艺术哲学研究的实在性和普遍有效性。
(一)什么是艺术哲学
艺术哲学,顾名思义,就是关于艺术的哲学。但这种解释等于没有解释。所以有人又进一步解释为:艺术哲学就是对艺术进行哲学的思考,亦即对艺术中最根本的东西的思考。然而,什么是艺术的最根本的东西呢?或者换句话说,是什么东西在根本上决定着艺术之为艺术呢?是艺术表现的对象以及被认为与艺术对象有密切关系的实有的生活世界或虚拟的理念世界,还是创造艺术的主体的主观因素,抑或是艺术作品本身?或者是这几方面因素的综合?对这个问题,理解不同,思考的重心不一样,就会有不同的艺术哲学。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艺术哲学,大概就跟对艺术的根本东西有不同的理解有关。
有一种观点认为,哲学是思考具体学科所不能思考的东西,艺术理论不能思考自身,因此,艺术哲学就是对艺术理论的思考。这种观点,如果从哲学思考是一种最高的、最后的思考的角度看,似乎也可成立,而历史上也确曾有过这样的艺术哲学;但如果从哲学思考是一种对最根本的东西的思考这个角度看,那就有把艺术理论看成是决定艺术之为艺术的根本东西之嫌,因此,认为“艺术哲学就是对艺术理论的思考”,似乎又还值得商榷。更何况,说艺术理论不能思考自身,这也是一种非理论的观点。理论之所以称得上理论,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它具有反思性。真正的艺术理论,应该是既能思考艺术问题又能对自身进行反思的理论。
关于艺术哲学是什么的问题,的确是一个富于思辨性的问题。看来,这个问题一下子也说不清。因此,如果转换一下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角度,看一看历史上艺术哲学研究的趋向,也许对我们进一步理解什么是艺术哲学,艺术哲学研究的重心到底应该放在哪里,会更有意义。
(二)历史上艺术哲学研究的几种倾向
历史上的艺术哲学研究往往随着时代和科学的发展而表现出不同的倾向:
1、把艺术和美上升到哲学的高度,重点从艺术和美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对艺术和美的根源、本质、规律、类型、结构、功能、典型等进行哲学的思考。重要代表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丹纳。值得指出的是,过去有一种误解,认为丹纳对艺术和美的研究是一种彻底转向艺术的外部规律的研究。其实,在丹纳看来,决定艺术之为艺术的本质因素,除了时代的、种族的和环境的因素外,艺术家按照自己的感觉、情感和思想创造性地表现对象的主要特征,也是决定艺术之为艺术的一个重要因素。[1](P503-504)我国解放以来倡导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艺术问题时,虽然对艺术的内部规律也多有触及,但重点还是放在外部规律上,相对地说还是不够重视对艺术作品的本体论研究。不过,对艺术的外部规律的研究,已达到一种新的历史高度,那就是揭示了经济基础对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的根本性影响。
2、从精神现象学的角度,研究艺术发展史与精神发展史的关系,用以解决艺术和美的根源、本质和规律等基本问题,并按照精神发展的阶段对艺术和美进行思辨,探寻不同艺术在物质结构和功能质上的区别,探讨艺术典型的特征及其与人类精神追求的关系。代表人物是黑格尔。值得指出的是,黑格尔这种艺术哲学虽然和他的绝对理念、绝对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比起谢林把“艺术哲学”等同于“宇宙哲学”,宣称“在艺术哲学中丝毫不谈经验的艺术,而只谈处于绝对之中的根源”,只强调通过“对艺术的高级反思”来推演出宇宙和上帝,用以了解艺术所包含的无限和绝对的东西,具有了更多的历史主义和辩证的因素。[1](P359)
3、对已有的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的历史进行梳理,对已有的理论体系、理论范畴进行哲学的反思,以求在更高层次上把握艺术的根源、本质和规律。代表人物是布洛克。[2]
4、19世纪开始,西方出现了一股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思潮,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以英国的弗雷泽、芬兰的希尔恩、瑞士的沃尔夫林为代表,主要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艺术的起源和艺术的本质、结构和功能等。[3]
5、20世纪以来的西方,艺术哲学研究又出现了新的转向:
一是转向从艺术与审美创造主体的主观层面寻找对艺术现象与其他审美现象的一种人本主义的内在理解,在这一点上,克罗齐和科林伍德的表现主义美学,狄尔泰、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美学,布洛、屈佩尔、瓦伦丁、立普斯、浮龙·李、康拉德·朗格的早期心理学美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美学,阿恩海姆的格式塔心理学美学,都有共同的倾向。[4]
二是转向从文本本体论的角度,对艺术现象和其他审美现象进行形式主义的、现象学的、存在主义的、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的、逻辑实证的、语义学的分析和阐述。例如以什克洛夫斯基和雅各布森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美学,以克莱夫·贝尔和罗杰·弗莱为代表的英国形式主义美学,以艾略特、兰色姆、布鲁克斯、韦勒克等为代表的英美新批评派美学,英伽登、杜夫海纳、梅洛·庞蒂的现象学美学,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萨特、加缪的存在主义美学,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美学和雅克·德里达、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的解构主义美学以及拉康、福柯的后结构主义美学,以苏珊·朗格为代表的符号学美学,摩尔和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美学,瑞恰兹的语义学美学,共同关注的就是艺术和其他审美实践如何表述主体所知道的世界本质。[5]
三是从文本本身转向重点研究接受,注重艺术意蕴的无限可能性,例如迦达默尔的解释学美学和姚斯、伊瑟尔的接受美学以及曼弗雷德·瑙曼的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6]
6、中国传统的艺术哲学,并未形成一门完整的科学。但由于艺术家和理论家们都深受儒佛道三家关于以“道”为核心而“道”又是无形无限的思想影响,认为艺术的意蕴只能品味、意会而不能言说,所以都倾向于心物感应,以接受主体的感悟来阐发艺术与其他审美现象的意蕴,重点放在从儒家的或道家的或佛家的精神境界或三家精神相融汇的境界上去解读艺术作品或其他审美现象。
(三)艺术哲学研究的重心应放在对艺术作品和其他审美现象上,使之具有实在性和普遍有效性
历史上艺术哲学研究的不同倾向说明:
第一,对于艺术的哲学思考是多元化的,因为决定艺术之为艺术的因素并不是单一的。就此而言,不管哪一种艺术哲学,都自有其对艺术真理的独特的发现和发明,都自有其学术价值。
第二,20世纪以来艺术哲学研究重心由外向内的转移,其潮头之大,趋势之猛,不仅是科学发展和分工的必然,更是人们逐渐明确内在地把握决定艺术之为艺术的本质因素的重要性和有效性的结果。
第三,艺术哲学研究重心向内转,或重点研究艺术和审美的创造主体,或重点研究艺术文本和审美现象本体,或重点研究艺术和审美的接受,在形而下的具体阐释中,由于有意无意地忽略艺术和审美创造主体与时代和现实的关系,或有意无意地割裂文本和审美现象本体跟作者、时代、现实的联系,或过分夸大艺术和审美接受主体的能动性,往往又导致艺术解读的有效性缺乏普遍意义,以至在反形而上学研究中不自觉地又陷进了形而上学的泥潭之中。
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批判地借鉴历史上艺术研究的不同倾向的经验与教训,在顺应艺术研究重心向内转的趋势时,高度重视艺术哲学研究的实在性和普遍有效性。
所谓实在性,指的是艺术作品和其他具体的审美现象才是艺术活动和其他审美活动的实在对象,以它们为核心辐射出去,我们才能顺藤摸瓜,才能看到决定或影响到艺术作品之成为艺术、审美现象之所以美的艺术家、生活世界、理想世界和读者及其他审美主体。换言之,以艺术作品和其他的审美现象作为艺术哲学研究的重心,以此辐射到艺术家、生活世界、理想世界和读者以及其他审美主体的接受,艺术哲学研究才真正具有实在性。
所谓普遍有效性,指的是在艺术和其他审美现象的具体研究中,努力避免主观唯心的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换言之,就是在对艺术作品和其他实在的审美现象进行本体论的哲学思考时,不要把艺术作品和其他审美现象看成孤立的本体,而要看到它们与艺术家、生活世界、理想世界和读者以及其他审美主体的复杂联系,要明确艺术和审美的文本的性质、特征、结构、功能等并不是自发自生的,而是艺术家或其他审美创造主体的艺术思想、美学理想和艺术行为、审美行为的历史、具体的表现,其中隐含着艺术和美跟历史的、现实的人和事的某种同构关系,隐含着人类(包含现实的读者和其他审美主体)的期待与需求,折射着处在复杂社会关系之中,具有“主体间性”的审美创造主体和审美接受主体的复杂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体现着对某种人生境界和精神境界的追求。因此,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吸取能与之融通的其他哲学方法论的合理成分,对艺术作品和其他审美现象进行历史具体的解读,艺术哲学的研究才会有普遍有效性。很显然,这种以艺术作品和其他审美现象为重心的艺术哲学研究,跟唯作品文本是“本体”的孤立、静止、片面的艺术哲学研究的有效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才把艺术作品的哲学解读作为艺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心问题来看待。
二、从艺术作品与哲学的对应关系看艺术作品哲学解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艺术作品与哲学在功能性质上具有诸多对应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艺术作品的哲学解读具有实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一)艺术文本实质上是一种诗化了的哲学文本,艺术与哲学在对人和人的生活世界的根本思考上具有一种异构同质、异曲同工的关系。
诺瓦里斯说:“哲学是真正思乡的。”艺术何尝不如此。艺术所表现的人跟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再复杂也离不开艺术家对人的生与死、爱与恨、痛苦与快乐的思考,离不开艺术家对人与生活世界本体论的“存在”和未来学意义的“存在”的思考,离不开对历史和现实的人的存活状态、人生境界、精神境界以及理想的人的存活状态和人生境界、精神境界的思考,这与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强调的经典哲学对人类的生存、发展、享受三大基本需要的思考,以及现代哲学的“思乡性”是一致的。前面我们提到的历史上西方的哲学家、美学家,他们哲学思维的路向和重点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同,但他们无不竭尽全力去探寻生活世界和人的本体论和未来学的意义;他们在运用自己的哲学研究艺术时,尽管有重在外部规律和重在内部规律或重在艺术接受的区别,但他们的终极指向又都涉及到艺术对世界(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和人的本质的表现问题;尤其是现代西方的哲学家、美学家,他们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艺术是怎样成为人的“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并且都各有建树,就因为艺术和哲学在对人和人的生活世界的根本思考上具有一种异构同质、异曲同工的关系。饶有兴味的是,中国传统的哲学,无论是儒、道、佛,它们的哲学思维有个共通点,那就是如何最终达到天人关系的和谐,使人达到自由的境界。当然,它们对天人关系中的矛盾的主要方面,理解有所不同:儒家相对偏重于现实层面,更重视人伦关系的和谐。比如孔子就大谈特谈“仁”,而对于天道和天性则尽量回避,对此,子贡就说过:“夫子之言性与道,不可得而闻。”(《论语·公冶长第五》)而事实上,从《论语》看,孔子谈到天神、天帝、天理、天道的次数也只有17次,而谈论“仁”则多达109次。但孔子在强调君子要“求仁”的同时,又强调要通过漫长岁月的修养而达到“知天命”,最终达到“从心所欲,不逾距”的自由境界。在他看来,艺术也跟哲学一样具有可以使人达于“仁”,最终达到天人和谐、使人获得自由的功能。这些我们可以从他关于“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第十七》)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第八》)的言论得到证明。而他在齐国听了《韶》乐以后,“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第七》)也正是他从艺术里得到哲学的启示,达到天人和谐、身心自由的结果。道家侧重于超脱现实,他们竭力宣扬“道”之“玄而又玄”,认为“道”是一切事物的本体,主张“致虚极静”、“自然无为”,以达到“道”的境界,也是为了追求天人合一,追求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自由。在他们看来,艺术的结构虽然不同,但对于“道”的思考却具有类似的功能性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庄子对寓言的运用中得到证明。佛家在天人和谐、人的自由这个问题上,则侧重于强调对“缘”和“涅槃”的感悟,以达到心灵的自由。在他们看来,艺术要表现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王维以及其他受佛学影响的艺术家的创作实践中得到证明。总而言之,中国传统的哲学和艺术,无论是儒、道、佛,它们的思维方式和侧重点虽然不同,但其终极指向却是一致的,那就是都对人和人的生活世界进行本体论的思考,都喜欢探寻理想的人生境界和精神境界。
历史事实表明,艺术与哲学在对人、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和理想的生活境界的根本思考上,二者是异构同质、异曲同工的,用哲学的方法解读艺术作品,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可以从中悟到艺术与哲学那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妙谛。艺术因哲学的思考而敞开它的人生境界、精神境界,哲学也由于回到意象的思考而获得新生。
(二)对艺术作品进行哲学解读是有内在依据的。因为艺术所表现的人的情欲与现实的伦理、道德、政治规范及其他理性要求之间的矛盾纠葛,从主观层面看,实质上是艺术家对人的自然生命、社会生命、精神生命是否可以达到内在同一性的一种艺术思考,这种思考跟传统哲学特别是现代的生命哲学对人的自然性、社会性、精神性关系的哲学思考是一致的。
(三)艺术作为心灵(情感和理念)的感性化形式,涉及到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只有用哲学的方法,才能从根本上读懂它。
(四)艺术的魅力和社会效应的变异性,关系于艺术文本本身诸多“自我”因素与“他者”因素的复杂纠葛,涉及到文本、文本作者、文本隐含的读者与历史、现实、未来以及现实读者之间的对话与沟通,这更需要运用现代哲学的方法来加以研究。
(五)对艺术作品的解读,可以有不同层次的解读。如果说,哲学的思考是关于最根本东西的思考,是关于最高的、最后的、本质的东西的思考[2],那么,对艺术作品的哲学解读,也就是对艺术作品的最根本的、最高的、最后的、本质的东西的思考。艺术作品最根本的、最高的、最后的、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呢?表面看来,艺术作品是物质构成与艺术功能的统一,但这种统一靠的是什么?是艺术家的精神劳动。而这种精神劳动又体现着艺术家的精神价值取向,体现着艺术家对特定的人生境界和精神境界的追求。因此,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哲学解读,具体了解艺术作品所表现的人生境界、精神境界,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不过,也有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例如,现代艺术的一些艺术家,他们就往往对用哲学的观点解读他们的艺术作品非常反感,认为要解读出艺术的意义是徒劳的,艺术的意义就是语言、声音、色彩、结构本身。但是,即使像号称野兽派代表的艺术家马蒂斯,他虽然反感于用哲学的眼光看待艺术作品,但他又坦率地承认,他是要用色彩炸开世界,用色彩来表现世界。这种独特的艺术观本身就包含有哲学的意味,因为在他看来,色彩就是世界的最高的、最后的、本质的东西。既然如此,就还是需要用哲学的方法去解读他的作品。在这个问题上,今道友信有一段论述十分精彩。他说:具有现代艺术特色的作品往往是一些非对象的、富于色彩的、从形态上说好像是还没有完成的抽象的作品。这些作品都具有马塞大学甘特纳尔所说的非限定性。还有就是东方亚洲以单一色彩描绘出来的、只画出对象的一部分、画幅上留出大部分空白的古典绘画,也具有非限定性。而非限定形式是对人的内在动力性的重视和尊重,它会促使人们关心和注意甘氏所说的形象化。可见,要正确理解这种绘画的美,理解艺术家的形象化概念,是由绘画的特性促成的。因此,对现代艺术作品进行哲学的解读,就成了现代艺术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对它们表现的理念以及对鉴赏它们的方法进行解释,也就成了欧洲以至全世界的艺术哲学的一个指导性的课题。而对于东方古典绘画那种单一的色彩和部分主义精神,也不能不从哲学上寻求其背景。[7](P303-305)
再如,极力推崇绝对音乐的人,认为绝对音乐是纯粹以美音的组合而引人入胜的,用不着哲学的思考。但是,被称为纯正音乐的绝对音乐,它虽然是想把形式美发挥到极致,并不想去跟客观生活事象和某种特定的情感相对应,但创作绝对音乐的人又几乎没有不认为绝对音乐是“最高超的想象的真善美”。[8]因此,不对它进行哲学的解读,就很难挖掘到它的宝藏。诚然,音乐的欣赏可以是知觉的欣赏,也可以是情感的欣赏,还可以是理智的欣赏,这是一般的常识。知觉的欣赏,只求悦耳,引起一种知觉的快感。例如轻快或强劲的节奏可以使人不知不觉地手舞足蹈起来,生动或婉转的旋律,华丽或雄伟的和声,也可以给人带来种种乐趣。美声,通俗如说话的气声,蒋大为、李双江高亢激越嘹亮而圆厚的民族唱法;关牧村浑圆厚实的女中音,它那即使欢快或庄严也略带淡淡的哀婉,即使雄壮也略带温和甘美,音色极像西洋的巴松管和云南的巴乌管的歌唱;西洋乐器中的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倍大提琴,圆号、小号、长号,单簧管、双簧管、萨克斯风、长笛、风笛、陶笛、排箫,钢琴、竖琴、手风琴,等等;中国民族乐器中的二胡、高胡、京胡、板胡、马骨胡、马头琴,琵琶、古筝、古琴、扬琴,笙、笛子、洞箫、锁呐、埙,三弦、阮、月琴、柳琴、东布拉,还有新疆手鼓、京戏中的班鼓、朝鲜族的长鼓,等等等等,无不以其特殊的音色给人以听觉的愉悦,令人难忘。情感的欣赏,则要求体验音乐所表现的情感,唤起听者自己的喜怒哀乐。例如从乐曲的调性体会乐曲的情感基调,比方大调表示愉快雄健,小调表示轻松或悲哀忧郁;从节奏的快慢、声音的高低强弱以及和声和音色的变化感受乐曲情感的发展变化,比方节奏紧张而短促表示奋发激怒,节奏和缓而悠长则表示婉约柔和,声音高且强时表示热烈,低而弱则表示沉着安宁,和声中的不协和音多表示冲突抗争,协和音则表示和谐,用小喇叭的音色表示战争,用单簧管的音色表示田野等等。理智的欣赏则要求懂得一定的乐理和乐器的常识,竭力探求乐曲的结构、主题的变化以及作者技巧的运用,了解各种重要曲调的形式,乐曲的流派风格、个人风格等等。尽管音乐欣赏一般可以分成上述三个层面,但单靠知觉的欣赏,很难得到音乐的真谛;即使音乐激动了你的情感,也不算了解音乐;只有上升到理智的高度,探求乐曲的奥妙,然后再进一步结合上述三种欣赏,利用相关的背景信息(时代的、个人的),在充分的想象中进行哲学式的体验,领悟乐曲所追求的精神境界,才能真正成为知音。
上述两个极端的例子及其推演,说明艺术作品的解读是拒绝不了哲学的。更饶有兴味的是,在第十届国际美学会议上,讨论的中心议题是“艺术对哲学的改造”,但讨论的结果多数人却认为“在任何意义上,哲学观总是革命性地决定着艺术观的产生”。[9]众所周知,特定的艺术观是决定艺术作品的具体特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既然“哲学观总是革命性地决定着艺术观”,那么,用哲学的方式解读艺术作品,不也就成了一种具有革命性的事情了吗?
不过,还是有人对此有存疑。他们认为,艺术活动是一种非意识的心灵自由活动,而对艺术作品进行哲学解读就意味着对“诗”和“诗化批评”的一种亵渎,意味着对艺术作品的肢解,最终使艺术的解读成为一种不伦不类的东西。他们这样看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是维柯在《新科学》中关于诗和哲学的区别的一段话。其实,这是一种只见对立不见联系、转化和统一的片面见解。不错,维柯是说过:“哲学把心灵从感官那儿拖开来,而诗的功能却把全副心灵沉浸在感官里”。但对维柯这一段话的理解,我们决不能停留在对哲学与诗的功能正好相反的理解上,而应进一步理解哲学的功能和诗的功能的特殊性到底在哪里,它能派上什么用场。应该说,把心灵感性化,让心灵成为可以直接观照的东西,这是诗也就是艺术的特长,但,诗、艺术却不能思考和说明自己把怎样的心灵和怎样把心灵感性化;而艺术理论,特别是长于对艺术的最根本的东西进行思考的艺术哲学,却有可能做到。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尝试用历史的、唯物的和辩证的哲学思维方式把诗、艺术中沉浸在感官里的心灵“拖出来”,以便了解个透彻呢?我以为,这就是维柯的话所蕴含的哲学和诗既对立又统一的道理给我们的启示。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让我们再来看看孔子的说法和做法以及日本研究孔子的专家今道友信的评论。
前面曾经提到过,孔子曾经对他的弟子门生说:小子们,为什么不学诗?诗可以兴,……。对此事,陈亢有怀疑。于是特地向孔子的儿子伯鱼打探孔子对他是否有私授。可是伯鱼却说“未也”,只是有两次单独的问话,一次问他学诗了吗,一次问他学礼了吗,然后简单地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第十六》)“不学诗无以言”是什么意思呢?从字面上看,是说不学诗就无法发表见解;深层的意思却是说学诗可以使人超越平庸的思维,洞明事理。而要做到这一点,学诗的人不用哲学的方式去解读诗的内容、结构和功能等等是很难的,充其量至多也只能停留在感奋和宣泄上。大概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孔子认为,懂得事物的内在联系,懂得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人生境界和精神境界,才可以读诗论诗。《论语·学而第一》中有一段记述:“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欤。’子曰:‘赐也,始可与论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讲的就是论诗的前提是要有哲学的头脑。以孔子自身为例,他之所以能指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就由于他能从人生境界和精神境界的哲学高度来解读《诗经》。“思无邪”,实质上是一种超越性的人生境界和精神境界。当然,对“思无邪”也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比如今道友信就把它看成是“思索的垂直上升”。[10]这大概算是一种语义学的理解(即先把“邪”与“斜”通假,然后从意向性上把“思无邪”理解为“思索的垂直上升”),不过这种理解已上升到语义哲学的高度。事实上,今道友信也是非常重视对诗的哲学解读的。他明确地指出:“研究诗的艺术,是要超越概念的领域,是要向那种存在进行精神上的飞跃……一首诗是一个独立世界,是一个小的宇宙,……对诗的内在的基本的了解是了解世界的缩影”。”[10]这一看法,明显的是受到了孔子的艺术哲学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引述了上面提到的《论语·学而第一》中孔子和子贡那段对话后发表的评论看出。他说:“孔子见子贡能把诗向自己不知道的根据上还原(按:指子贡已具有‘告诸往而知来者’的悟性),所以赞扬了他。对孔子来说,诗艺术的研究就是把人的精神引向并还原于根据,也就是解释。从向根据还原看这种解释是意义的发现,练习这种解释可以学会象征性语言的艺术,可以使人的思索自行上升并影响别人(按:这是他对‘思无邪’的理解)。”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对诗作品进行解释,并不是改写般的水平的解释,也不是剖解意义的水平的联想,更不是再说一遍。从意义上说,是从形象的象征的语言向被象征的诗的精神上的垂直上升(按:这又回到了他对‘思无邪’的理解),换句话说,就是精神向更高的阶段还原。诗的艺术可以使人的精神觉醒、兴腾,‘子曰:兴于诗……’的意思是什么,综上可知,是‘人的精神因诗的艺术垂直地兴腾起来,突破定义的上限’(按:这里又一次勾联了‘思无邪’)。对诗的艺术进行研究可以学得象征性的表现方法,思索可以通过它超越概念上的限界,还可以通过它把不能有定义的理念当作自己的主题,即人的思索可以因诗的艺术超越定义的限界。”[10]以上孔子关于诗与哲学的关系的看法和实践,以及今道友信由它引发出来的理论,对于我们深刻理解艺术作品哲学解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是很有启发的。
当然,也不是所有艺术作品的解读都非要用哲学的方法不可;我本人也无意提倡唯一的解读模式;更何况,艺术的解读有时出于作品的特殊性以及特定情境下读者观众的强烈的感性的娱乐狂欢的需求,就不一定要勉强地进行哲学的思考。我在看以武打为主的《黄飞鸿》、《方世玉》这些电视剧时,我就不太去深究其中的人生境界、精神境界,而把重点放在欣赏武打及拍摄技巧的形式美和追求娱乐狂欢上;在看杂技艺术和魔术表演时,我就只懂得感叹和惊奇;在听一些旋律和音色非常优美或和声繁富、节奏别致、具有强烈的冲击感官的力量的乐曲时,我就只会摇头击节甚至手舞足蹈。(无调性、旋律难听、节奏疯狂的例外——它们反而常常迫使我去从哲学的高度上问个为什么。)
不过,话说回来,绝大多数艺术作品毕竟总是这样那样地与人和人的生活世界相联系着,往往或明显或隐晦地表现着人们对人和生活世界的本体性存在和理想的存活状态的询问和追求,特别是当艺术相当突出地呈现出人的存在问题时,它那种对心灵的冲击力量,就会迫使我们不得不用哲学的眼光来看待和思考它,不得不对其精神向度进行追问和反思。例如,前不久我们从南宁电视新闻综合频道看到的一个行为艺术展览,那俯伏着的裸体男人被人盖上许多伦理、道德的印章,(照我猜想,作者可能还想让人盖上政治、法律的印章,但他不敢)我们就不能不对它表现的人的存在问题以及为什么这样表现作哲学的反思和追问:它表现的大概是人的自然性受到人的精神性和社会性的压抑吧。但这种表现,由于肉身的过分突显而无法表达人对自然性存在与精神性存在、社会性存在的内在同一的渴求,它给人的印象就只能是一种对“肉身本体论”的宣扬,是对生命哲学的一种误解。
总而言之,运用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对艺术作品进行哲学的解读,无论从艺术哲学的功能质、艺术哲学研究的趋向和艺术哲学研究的实在性和普遍有效性看,还是从艺术作品与哲学在功能性质上的对应关系看,都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不过,需要声明的是,用哲学的方式解读艺术作品并不是要把艺术哲学化,因为那样会损害到艺术的美的魅力和读者对艺术美的享受。这就涉及到对艺术作品哲学解读实质的理解了。关于这一点,拙文《艺术作品的哲学解读是一种享受》已有所论述,恕不再赘。
标签:哲学论文; 艺术论文; 艺术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人生哲学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文化论文; 美学论文; 孔子论文; 思无邪论文; 儒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