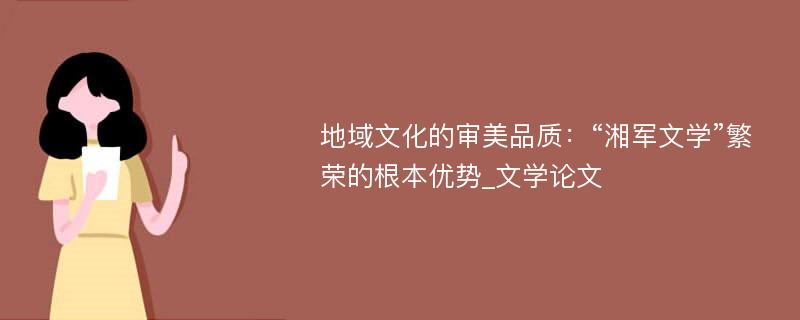
地域文化美质:“文学湘军”兴盛的根本优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湘军论文,兴盛论文,地域论文,优势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总觉得,文学湘军基本上是一个“土著”作家群,精神心理结构受地域文化的影响至大至深,湖南文学的发展态势,除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等客观原因外,从创作主体的角度看,一方面是缘于具体作家的才情、功力与学素是否出类拔萃,另一方面,则往往为湖南地域文化的不同因素所宿命般地左右和规定着。最近重读80年代文学湘军曾获广泛关注的力作,细辨它们的演变轨迹与内在状况,我更为真切清晰地发现,湖南文学的盛衰皆与地域文化息息相关,文学湘军在80年代前期的辉煌和中期的热闹,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地域文化特征与特定时代思潮的高度契合。以往的论者多半着眼于文学本身,仅从地方色彩和民间、乡土气息等艺术性内涵的角度予以分析,对此实在很有深化和拓展的必要。
一
我们不妨首先荡开笔墨,打量一下湖南这块神奇的土地,审视一番湖南的地域文化。
湖南地域文化的辉煌源头,是以楚辞为制高点和凝聚点的先秦楚文化。楚文化实质上是人的天性、心智高度自由地发挥而理性未曾明晰强健这样一种特殊精神心理机制的产物,它具有浓郁的原始宗教意识和神话色彩,在天人合一、人神共娱的愉悦型审美倾向中,充分表现出楚人情感、灵性的丰富、活跃与无拘无束。楚辞花草缤纷、神奇瑰丽的艺术境界,奇幻而华美的表现形式,则展现出楚人奇异的想象力、鲜明的浪漫主义气质和自然审美意识。在这种文化人格的深层构成骨架的,是屈原“上下求索”、耽于以理想改造现实的痴迷般的斗争精神,“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注:屈原:《离骚》,林庚、冯沅君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第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的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和强烈的主体意识;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桀骜不驯的性格,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励精图治、积极进取精神。而且,楚文化还显出一种不甘完全融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独立姿态、边缘姿态。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湖南地域文化的最初格局,表现出与中原文化迥然不同的风貌。
秦汉以降,楚文化湮没无闻,却并未消失,而是潜隐到民间世界之中,凝成弥漫于这方水土的氛围,并渗入生生死死于这块土地的人们的精神血液,冥冥中规范着他们的命运和行为。特别是在偏远封闭的苗、瑶、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地区,楚文化更是以巫术、传说、民俗、民风、方言等方式隐曲而实实在在地保存着,还通过民歌、民谣、地方戏等形式,传达和传播着其渊源久远的神韵。以至本世纪前期,沈从文满怀惊喜地发现,“屈原虽死了两千年,《九歌》的本事还依然如故。”(注:沈从文:《凤子》,《沈从文文集》第4卷第387页,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80年代中期,韩少功同样满怀惊喜地宣称,在湘西,楚辞所描绘的一切都是活生生的,“那里的人惯于‘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为裳’,披兰戴芷,佩饰纷繁,索茅以占,结茞以信,能歌善舞,唤鬼呼神。只有在那里,你才能更好地体会到楚辞中那神秘、奇丽、狂放、孤愤的境界。”(注: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4年第5期。)所以,在湘西,在湖湘大地,尽管乡土文化不具有远古传统的完整形态,文化的古意、文化的历史连贯性与纵深感较为稀薄,弥散在民间现实的生气和灵性之中,但是,“绚丽的楚文化”依然还活着,并构成了民间文化的某种底蕴,始终有力地陶冶着湘人的性情。
宋代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南移后,地处华中腹地的湘楚,成为东南西北各种思想文化潮流的汇聚之地,成为全国的一个学术、人才中心和革命风云际会之所,并形成了近现代史上的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经邦济世作为湖湘文化的基本特点,秉承并发展了楚文化的深层基因,促成了湖南人在近现代历史上的重大影响,以至“自曾国藩编练湘军,取得镇压太平天国的胜利之后,湖南士人养成了一种倨傲强悍的风气。指划天下,物议朝野,是甲午战争前湖南士人的通性。”(注:林增平、范忠程主编:《湖南近现代史》第35页,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这无疑培养了湖南人注重政治功利、讲究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桀骜莽勇而又算计精细的文化品性。
综上所述,可以说,湖南地域文化主要是一种功能主义而非历史主义的文化,它的精神内核,是以“楚骚”文学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传统,和近世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特征。它所具有的政治功利意识、社会责任感和桀骜莽勇的性格,有助于作家形成直面现实、独立思考的态度,发达的政治情结,和敢为天下先的艺术家勇气;它的浪漫主义传统,孕育着优秀作家所必需的多情善感的文人气质、丰富灵动的内心世界和自由无羁的艺术想象力。而且,湖湘这块土地并不雄阔深沉,却多姿多彩,富于变化和情调,灵山秀水洋溢着生命的气息,风俗民情弥漫着地域的氛围,生动、丰富而贴切地构成了湖南地域文化的外在形态,天然地为湖南作家提供了时代社会生活之外的,创作锦绣篇章的丰富素材。所以,历代湖南作家多灵气四溢、山歌野调式的精妙篇章,也多大胆泼辣、血气方刚的激情文章;一旦时代机缘、作家才情和地域文化优势高度契合,就能既领风气之先又标个人之异,如果诚笃执着地抒写自我丰富独特的生命体验,也能营构出诗意盎然、韵味绵长的艺术世界。
当然,对于地域文化还存在一个开掘阐释的同时从人性、人类文明的层面进行提炼、升华和超越的问题。纯粹的风情描绘也许可弥补时代生活画卷中文化气息的浅淡,却难以构成真正深厚的精神文化价值,纯粹的乡土精神也许可对时代风潮形成某种深化、校正和平衡,却难以产生真正的大气之作。只有作家能从人性、人类文明的高度进行观照和领悟,地域文化的蕴涵才能在精神文化的较高层次显示出一种普遍的意义和人性的光采。因此,仅仅对乡土熟稔、认同和写实,也许可产生清新一时的名作,却难以造就文学长久的辉煌。湖南地域文化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同样如此。
二
众所周知,新时期以来文学湘军成就卓著、国人瞩目的,主要在80年代初以获奖为标志的繁荣风光期和80年代中期以“寻根”为精神指向的探索争鸣期两个阶段。如果我们细辨一下,构成80年代初湖南文学辉煌的力作,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即以《将军吟》、《第二次握手》、《祸起萧墙》等为代表的社会政治层面的呐喊之作、义愤之作,和以《芙蓉镇》、《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醉乡》等为代表的寓政治风云于风景民俗画卷的乡土小说;80年代中期的探索、“寻根”小说,则包括《爸爸爸》、《女女女》、《死街》、《桃源梦》等颇成阵势的荒诞、寓言型小说和《大泽》、《血坳》等散兵游勇性的对地域历史文化进行写实性剖析的作品。那么,这些小说文本与湖南地域文化关系的具体情形到底如何呢?
80年代初的湖南乡土小说力图成为一曲曲“严峻的乡村牧歌”,从艺术景观到创作倾向,都明显地表现出楚文学内含痛楚而依然明丽神奇的浪漫风韵和近世湖湘文化经世致用聚焦于政治功利的特征。那些社会政治小说则大胆泼辣,犯死直书,勇敢地表达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率先甚至超前地喊出人民心底的呼声,由此而引人注目,它们所表现的作家的政治胆识和艺术勇气,从文化血脉的渊源看,实质上也是近世湖湘文化的政治情结和湖南人莽勇性格的体现。
我们其实还可以从文本的内在机制,来分析湖南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密切关系。在《芙蓉镇》、《爬满青藤的木屋》、《蓝蓝的木兰溪》、《醉乡》、《甜甜的刺莓》、《远处的伐木声》这些作者、主题、小说样式等等各不相同的作品里,我们细察即可发现,其中都存在一个光照全篇、作为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枢纽的女性形象。作者塑造胡玉音、盘青青、玉杉、竹妹、阳春这类女子形象时,远比塑造其它人物形象来得灵气焕发、挥洒自如、真情洋溢,从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她们是作家的心理兴奋点和精神敏感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女性形象并未容纳多么深厚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作家们着力展示的,是她们的性情、性灵以及这种性情、性灵在社会历史环境中的遭遇。在作家们的笔下,女子们性格的心路历程大致相似,一个个美丽善良、善解人意,甜媚得时露风骚,柔弱得稍嫌蒙昧,她们都凭自己的天性自在地生活,经历了一段止水般的生存境遇或悲剧性的命运后,往往不是凭教化、凭理性,而是凭慧心、凭悟性,直觉到了生命的本质和人生的真谛,于是心明眼亮,终于以决然的行动反抗窒息生命发展的不合理环境,走向现代文明的广阔天地。这些最为诗意化地凝聚着湖南地域文化美质和风韵的女子,显然是作者们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是作家们体察生活的深度和烛照生活的亮点,作家们正是以她们为价值临界线,通过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建构起小说的意蕴格局,传达出社会政治性的创作题旨。这些女子的性情、性灵,实质上就是文学湘军感应到的人所应有的素质和品性,对这种性情、性灵的认同与抒写,对它们的境遇的刻画,则体现出作家们从人性和文明的高度对湖南地域文化底蕴的审美化的提炼与升华,也反映出文学湘军以此为标准判断社会生活的价值眼光,在这里最为凝炼透彻地显示出文学湘军对于地域文化优势的依赖。而且,强调人性人情和文明意识的审美价值眼光,恰恰与新时期之初中国精神文化界的人道主义和现代化思潮高度合拍。于是,内在的美学、精神价值和外在的社会共鸣可能性同时具备,一批优秀的乡土小说就在文学湘军蓄积已久的创作激情的催发下喷涌而出,引领中国文坛的风骚,铸造了湖南文学在80年代初的辉煌景观。
当然不是没有局限,没有暗影。但是,由于特殊的时代机缘,80年代初的文学湘军有效地隐去了地域文化劣势造成的不足。中国文坛关注《第二次握手》、《将军吟》,最看重的是作者闯“禁区”、唱“反调”,直面真实的政治胆量和大无畏精神,不过,这些作品实际上隐含着思想的开阔新颖度和思维的哲理深度有所不逮的局限,康濯当时就因《将军吟》未能形象地揭示出形成文革动乱的历史、社会、政治、文化、心理的种种根源和依据而说过:“作品的效果看来还都借助了今天的读者在十年浩劫中亲身经历或半亲身经历的补充。”那批乡土小说中的人性蕴涵和文明意识,也非作者的文化、哲理感悟,而只是一种生命情趣和心理方面的感应,因而在体验的厚度方面存在着欠缺。这些特征性现象,实质上是湖南地域文化过分地胶着于政治功利和一味莽勇或灵慧,缺乏充实发达的理性思维与理论形态作为根基的劣势在文学中的反映。但是,80年代初的中国处于刚刚由禁锢僵化走向开放反思的特定历史时期,各种新观念、新思潮都尚未形成明晰的文化形态,思考也尚未向纵深发展,说出具象层面的真实和感应生命脉动的灵慧,恰恰可成为那种时代环境中最易见效的精神创造能量,这样,湖南作家隐藏着劣势的文化特征,反而转换为成全创作的优势。
从两类小说比较的角度来看,乡土小说从对地域文化景观的捕捉描摹,到对地域文化精神的开掘提炼,直到对蕴含其中的人类生命动力的认同与张扬,全方位地发挥了湘楚文化的优势,而文学湘军同期创作的社会政治小说,展示的是时代的政治话语,地域文化仅仅在创作主体精神的范畴内对作家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结果造成了二者价值背景和文化含量的差异,以至我们重读旧作,会觉得一类小说魅力尚存,另一类则给人以时过境迁之感。这也说明,对地域文化优势的发挥程度,在当时极为重要地影响着湖南文学作品社会反响之外内在价值的份量。
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浪潮中,湖南作家作品最突出的特征是其中的玄虚色彩、变形意味和荒诞品格。从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到莫应半的《桃源梦》、《驼背的竹乡》,孙健忠的《死街》等等,无不如此。这一时期,湖南的中青年作家们纷纷去寻找散落在民间的神秘、诡异甚至丑陋的古文化碎片,将它们融入自我梦魇般的生命体验与文革记忆之中,构筑起一座座具有荒诞变形意味和寓言色彩的艺术迷宫。从表面上看,它们似乎是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摹仿,但实际上,80年代中期创作力旺盛的湖南作家绝大部分对于西方现代派文学并没有很深厚的修养,魔幻现实主义只不过给予了他们某种艺术灵感的触发,这批作品在更本质的层次上,体现的恰恰是“庄骚”文学将充满奇诡、孤愤、迷茫、高远之感的生存体验辐射于写作客体,从而营造臆想型艺术境界的精神传统。当时中国文坛的“寻根”文学作品,大都具有深沉的历史文化意识和浓郁的生活实感,不少作品甚至隐含着某种实证色彩,湖南的“寻根”文学作品则以其浪漫风韵独具一格,不能不说,这是地域文化的丰厚馈赠。而且,玄虚色彩和变形意味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湖南作家思维深度较为欠缺、当时在思想的具体内涵上未能全面处于时代前沿的潜在局限,以致在晦涩的同时因确乎充分的艺术化而显出某种深长的意味。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即:文学湘军在80年代的兴盛,与湖南的地域文化紧密关联,具体作品的价值含量,则与作家对湖南地域文化的开掘、提炼、升华程度密不可分,正是湖南地域文化的优势,成就了80年代湖南文学的兴盛。
三
80年代湖南文学辉煌期活跃的作家们,大都是60年代或70年代即开始文学习作的,在有了初步的文学基础之后,他们由于种种原因沉入了生活的底层。长期的、与普通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的生活,使作家们真切地看到了中国社会的本来面貌,把握住了历史运行的脉搏,对时代的翻云覆雨也就能够洞若观火,生活就这样锤炼形成了他们关注现实、体察政治的精神特征。而且,他们初学写作时遵循临摹的,多半是周立波于地方风景风情画卷中显露时代政治文化气息的文学方法。沉入底层后,作家们又得以从容细致地体察和品味潇湘明丽的山水和妩媚的人情,从而在社会意识之外,又较为充分地培养了自我的自然审美意识和乡土情结。同时,作为出生乡土的农家孩子,这些作家往往把从事文学创作当成谋求出路、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因而虽然处在艰难困苦的生活环境之中,他们照样凭自己的悟性勤学苦练,并未放下手中的笔,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能够略为自在地展现自我艺术灵性的,是描绘充满诗情画意的自然山水,对社会、对时代的描述则暂时处于畸形扭曲的状态之中,而这种扭曲又恰恰显示出他们追逐时代潮疏、向往正统的深层心理。随着历史新时期的到来和拨乱反正的进行,党和人民的立场高度一致,关系高度融洽,作家的文学灵性与社会政治激情、个人功利欲求也得以高度合拍,于是,作家们有备而为,创作热情就充分地迸发出来,丰富的生活积累、深切的底层体验和不羁的艺术才情,共同凝结为一幅幅内蕴沉重而色彩秀丽的艺术画卷,一篇篇泼辣而精致的文学佳构。而且,在时代走向新历程的初始阶段,他们较为容易地与时代保持着同样的前进速度,同时又有早已练就的描摹风情风景的妙笔,这样,在反映时代新生活方面,湖南作家同样能奉献不少独具匠心之作。由于已有骁勇的作家在黑暗年AI写作就的义愤之作纷纷面世,为湖南文学引来了众多的关注目光,这些作品又接二连三地被推出,文学湘军崛起、湖南文学辉煌就成为中国文坛一时的亮丽景观。显然,这时文学湘军的精神心理充分体现出湖南地域文化的特征,他们的创作准备过程则鲜明地表现出是一种对地域文化蕴涵的观察、体验、理解的过程。
然而,文坛湘军毕竟多半是土著作家,缺乏多方面的严格的修炼,他们作为群体的后劲实际上存在欠缺,湖南文学长久地引领风骚是可能性甚少的。在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后,作家们又先后离开了生活的底层,作品的生活实感也就自然地会受到削弱。但就在文学湘军几乎捉襟见肘之际,“寻根”的口号被提了出来,这真是别开洞天。那些长期沉在生活底层的作家早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过“庄骚”文学浪漫气质和湘楚民间巫文化的浸染,虽然由于长期抑制而难以在创作中完整地再现,但文化的残留加上个人的想象,构制为数不多的诡异之作毕竟不是难事。而一些新进作家底层体验较浅,却受到了高等教育,他们在韩少功等人的倡导下,纷纷深入边远地区寻找古文化的遗留物,从而也创作一批亦真亦幻的“文化”小说。这样:文学湘军在80年代中期,又一次以自我独特的体验和才情,修筑了一道诡异而美丽的文学风景线。
80年代的中国文学往往有迹可寻,有源可溯,明显地存在着发展的内在必然性。但是,偶然性总是存在的,无论作家作品都是如此。湖南文学也不例外。如果说,80年代初期任光椿以学者姿态创作历史小说,尚与近世的湖南历史风云和湖湘文化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80年代中期残雪的现代派小说,在湖南文学中则近乎横空出世。他们虽然疏离地域文化心理建构的框架独行其是,但卓具影响的创作,却也为湖南文学的辉煌增添了亮色。
总之,山川钟灵秀,时势造英雄,80年代湖南文学的辉煌,也是我们伟大的时代和湖南这块神奇的土地共同作用于才情勃发、热情洋溢的文学湘军的结果,正是这种地域文化贮备和特定时代需求的也许永远值得庆幸的机缘巧合,使湖南当代文学在80年代达到了一个足堪自豪的、甚至可遇而不可求的高度。对于这中间的正反两方面的丰富意味,我们都必须细加体味,并长久地以之为鉴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