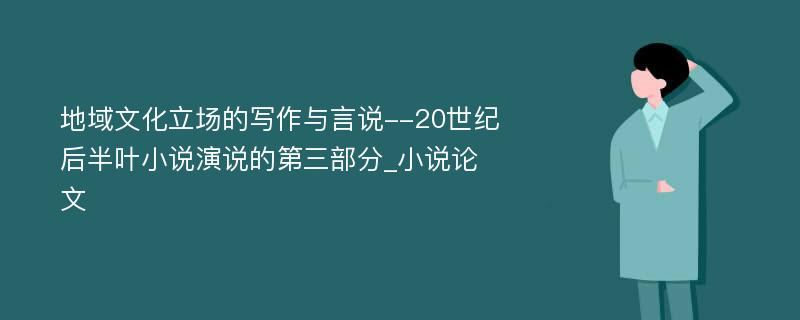
地域文化立场的书写与言说——20世纪后20年小说语言论之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三论文,地域论文,立场论文,语言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04)01-0042-05
每一个作家都是生长在一个文化场之中的。所谓文化场,就是指在特定的时空里汇聚着多种形态的文化,而且这些文化相互碰撞、交汇与融合,形成特定的文化氛围,从而引导、制约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对于作家来说,文化场中的多种形态的文化形成一股文化的合力,综合地作用,影响着他的创作。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作家所生长的那个文化场虽然可能汇聚着多种形态的文化,但是必然有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这往往决定着他创作时所持的基本立场与态度,恰恰是这种文化立场与态度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作家对具体语言形态的选择。
在作家生长的文化场中,文化形态是多种多样的,而且作家生活的时空具有很大的变动性,人生数十年,居行不定,因此,影响着作家对小说语言形态的选择的文化因素是错综复杂的。不过,作为重要文化因素的地域文化尤其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作家青少年时代所生活的文化环境,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家乡的地域文化。所谓地域文化,简单地说就是在某一区域内千百年来形成的比较稳定的有别于其他地方的文化。一个地区越是封闭落后,其地域文化的独特性越是显著;与此相比,那些较为发达地区,由于对外交往的频繁,文化间互相交流的机会很多,地域文化的特色就会变得很淡,甚至可能消失。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地域文化常常可以其独特性令文学作品大大增色。人们常常这样评论作家作品: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因为地域文化不仅深刻地影响着当地民众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准则,沉淀于人们的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从而成为小说创作反映与揭示的对象并为之提供极其丰富的创作资源,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生长于斯的作家的审美理想、美学风格、艺术技巧与语言运作。我们相信,每个人青少年时期的人生都是浸泡在较为稳定的地域文化之中的,而且从出生时的文化心理的空白到青少年时期的文化心理的初步形成,地域文化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20世纪我们这个基本上仍然是较为稳固的农业型的社会里。而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形成了众多的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正是通过语言等各种途径渗透进作家创作的地域文化使小说成为独具特色的文本,从而赢得巨大的成功。
对于绝大多数作家来说,地域文化就是他的精神母乳。几乎每一个作家,特别是那些在农村生活长大的作家,在其成长过程中,少不了要从地域文化的母乳中汲取营养。到了成为作家的时候,这些地域文化已经化为他的血肉,渗透到他的创作中。或者说,作家在创作时往往是下意识地站在某种地域文化的立场上书写与言说,那么他的小说语言也就不由自主地浸染着地域文化,从而显示出它的鲜明的个性。
20世纪后20年在文坛上具有一定影响的作家大多数出生于这个世纪的20年代到50年代,其中不少就出生在某个乡村并在那里长大。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曾在某个地域文化的怀抱中度过自己的童年与青少年时期。因此,当地风土人情、民间风俗、戏曲小调、故事传说、历史掌故、文物遗迹、生活习性、地理风貌、方言土语等都为作家们耳熟能详,深深地储藏在作家的情感记忆中,融入其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并制导着作家文化视界的形成,成为作家观察世界、认识世界与理解世界的一个起点。这就为作家的小说语言提供了一个坚强有力的支点。换言之,地域文化一直深刻地影响着小说语言的基本流向。
正如每个民族都有她的民族精神一样,每一种地域文化都有它的文化精神。从小说语言方面来看,文化精神对一个作家来说往往意味着小说叙述焦点的定位与运动、小说话语与叙事视角的选择、言语风格的确定以及语言结构的形成等等。地域文化精神在小说的叙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是关键性的,那些地域文化所深深浸染的作家总是在这种文化精神的制导下展开叙事的。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在这方面很具有代表性。这部小说浸透着陕北高原某地区的“白鹿文化”的精神(尽管“白鹿文化”包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的成分,但是从小说文本来看还应当说是地域文化)。白鹿文化精神成为小说叙事的灵魂,统帅着作家的叙述视界,使作家把叙事的重点放在白鹿村与白鹿书院,让白鹿文化精神融化在白嘉轩与朱先生等代表着这种文化精神的人的言语之中。在他们的言语当中,那些表示仁义、谦让、威严、正直、孝道、刚毅等精神的词语不时从他们的嘴里吐出,并在他们的身体力行的行为中熠熠生辉。因此,他们的语言在小说文本中可以说代表着一种当地农业社会里的不可动摇的秩序。或许是因为作家在白鹿文化中陷得太深,作家或许没有意识到这种文化的局限,作家对于朱先生的描写基本上采用具有神话意味的语言,取仰视视角,不知不觉中将白鹿文化的化身的朱先生神化了。同时,在对其他人物的叙述与描写中,小说的叙述语言也运用饱含着体现着白鹿文化的价值取向的词语予以褒扬或贬斥。从语言结构上看,《白鹿原》的语言特别讲究的是结构的完整与稳重,行文合乎语法规范,句式虽长,但层次分明,逻辑严密,叙述节奏比较舒缓而沉稳,显示出语言的厚实与从容;从整体的语言风格来看,《白鹿原》基本上是传统的宏大叙事模式,以极富传奇色彩的语言叙述白鹿原上白、鹿两大家族的历史。
由于地域文化的浸润,许多作家的小说语言往往都显示出浓烈的地方色彩。
首先是方言土语涌入小说语言,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小说语言的语言资源,而且为小说语言增色许多,增强了小说语言的艺术表现力。翻开陕西绝大多数作家的小说,人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当地的方言土语带着泥土的芳香扑面而来,直逼人们的眼睛。在贾平凹的大部分小说中,商州地区的方言土语可以说是俯拾即是。“具有商州山地特色和文化民俗积淀的独特事物的命名形式的专有名词”、“商州方言中富有表现力的动词形容词”、“商州方言中的古词语”[1](p.154-171)等成为他小说语言中的一大景观。贾平凹之所以对方言土语情有独钟,是因为“入古都西安以前,他在商州生活了20年。这20年又是人生极为重要的黄金岁月。这期间,他不仅学会了商州语音,至今乡音未改,而且掌握了大量的故土语汇。”[1](p.154)方言土语凝聚着当地人的文化精神与智慧,是当地人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独特的解读,反映了他们的人生态度和各种欲望。小说要描写一定文化区域里的人,要向这些人的精神的深层世界掘进,方言土语则为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因为小说家在方言土语中找到了这些乡党们精神存在的家园。然而,方言土语由于只在很小的地域圈子里流行,对于绝大多数的外地读者来说比较难懂,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到小说的被阅读与接受,很可能成为小说传播的一个障碍。这就给作家在小说语言的处理上带来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一方面,生活在一定的地域文化中的人们总是在方言土语中生活,方言土语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因为小说要给广大的读者阅读,就不能不考虑到读者对方言土语的理解与接受。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作家们往往要费尽心机,使出浑身解数。贾平凹在这方面的努力还是富有成效的,为人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他根据自己的艺术经验对商州地区的方言土语作了一定的筛选,对于那些可以为现代汉语中合乎规范的语汇能够替代的方言土语,他一概不用。必须用的则是那些只能由其传达思想与极富表现力的方言土语。比如贾平凹的小说常常用到这样一个词:“瓷”。“瓷”,在普通话里主要是名词“瓷器”或“搪瓷”、“陶瓷”的一个词素。在贾平凹的小说中,“瓷”(据了解,念chi,阴平)根据商州话的意思,表示人的“痴呆或笨拙”[1](p.159)的神态,词性为动词或形容词。《土门》中的“我摔掉了衬衫,老冉还瓷瓷地站在那里,……”双“瓷”连用,突现出老冉那种发呆发愣的神态,使之具有形容词的性质;在《浮躁》的“福运瓷了好久,末了还是近来”中,“瓷”显然是一个动词。在这里,无论是“瓷眼儿”,还是“瓷了好久”,都非常传神,是“痴呆”或者“笨拙”甚至这二词连用都无法替代的。而且,通过对贾平凹小说中“瓷”的用法的考察,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中的韵味比较丰富,大多用来形容或描写楞头楞脑的男子在女子面前的那种尴尬神态,表现的是一些怀有某种程度女性崇拜的男子的傻相。尽管这是商州的方言土语,但是在具体的语境中,一般的读者还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有一些方言土语的词语与当地的物产、风俗、地理、器具等关系密切,一般来说,外地的读者由于缺乏相应的知识,很可能不甚知之。针对这样的情况,贾平凹往往结合有关物产、风俗、地理、器具等的描写与叙述,让外地读者在饶有趣味的描写与叙述中,来熟悉这些词语。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看山狗”是什么,一般不知道,很可能误以为是一种狗。《浮躁》在叙述了子夜时的招魂声之后紧接着写道:
接着就是狗咬,声如巨豹的,彼起此伏,久而不息。这其实不是狗咬,是山上的一种鸟叫;州河上下千百里,这鸟叫“看山狗”,别的地方没有,单这儿有,便被视若熊猫一样珍贵又比熊猫神圣,作各种图案画在门脑上,屋脊上,“天地神君亲”牌位的左右。
在这里,贾平凹从“看山狗”的叫声写起,先给读者一个初步印象,进而指出这是一种鸟,再结合当地的民俗交代它在州河地区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同时为隐喻主要人物金狗的人格和命运埋下了伏笔。还有“烟灯”(《小月前本》)、“送夏”(《浮躁》)、“糊联”(《浮躁》)等商州地区的民俗语汇也都在相应的描写与介绍中得到了应有的解释,此外,为那些一般读者感到茫然的方言土语营造适当的语境,可以使读者根据语境来正确理解。这就为读者的接受扫清了障碍。
其二,地理风貌既表现为一个地区自然风光与景色,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是那个地区独特的文化心理与民风民俗形成的极其重要的因素,还是那里民间语言存在的重要条件之一。小说要深入探究人的精神世界的奥秘,自然少不了对人所生活的外部自然环境的描述,于是,一个地区的地理风貌便很自然地进入了作家的艺术视界,并融入到小说语言中来。随着作家对一个地区地理风貌的描写,小说语言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饶有趣味的地名(包括山名、河名、村镇名和动植物名等)。这些地名的命名过程既是当地人对各种自然环境的认知和解读,也是作家对这种认知和解读的认同。《白鹿原》在介绍白鹿村时,叙述了那里曾经发生过的“一个改换村庄名称的风潮”,使这里的村庄的名称与白鹿挂连起来。其实这股风潮正是这里的人们白鹿崇拜心理的具体表现。而白鹿崇拜心理则源于白鹿的神话传说,这个神话传说又是与原上的一定的地理形势联系在一起的。北方雄浑的山河与南方的小桥流水的自然风光进入小说的时候,必然影响着作家描写这些风光的语言风格的选择。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中的北方的几条母亲河气势磅礴,那么作家描写这些母亲河的语言也就很具有强烈的阳刚之气,铿锵有力;而苏童、叶兆言在写到江南小镇的自然景色时,其描写语言自然与那些景色一样玲珑清秀,柔和轻婉;商洛地区的河流,大多地形复杂而险要,河床变化多端,水流湍急,因而在贾平凹的小说中,河上的放排情景就给写得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商州的山区地势起伏不定,沟壑众多,常有野兽出没,于是贾平凹在写这里的人和事也就不由自主地给小说语言增添了几分神秘的氛围。古华的《浮屠岭——唱给山里人的歌》对观音溪的描写很有特色:
观音溪和麻花石路,一水一旱,时分时聚,相偎相伴,像山姑娘身上的两根裙带,逶迤飘逸。别看它的水浅,行不得船,走不得筏。在深深的山谷里,她的两岸边居然也滋润出一块块翡翠般的稻田,养育着好些座山寨人家。山寨里有些后生家还要在她的上游建个小水电,在她的身上披挂上一串串的夜明珠呢。可惜小水电至今也没有建起来。因为她的水性有点野,有些浪,喜怒无度,涨落无常。每到春、夏、秋三季,她就涨桃花水,端午水,重阳水。她的胸脯就要丰满起来,体躯就要膨胀起来,流经山口时就会势如崩雪,吼声如雷……涨过了这三秋水,她就又细瘦了,清悠了,苗条得像山寨人家的小妹儿。观音溪和麻花石路,直到出了娘娘庙山口,才分道扬镳,各奔南北去了。
这里与其说写的是观音溪,倒不如说写的是山里的姑娘,或者说作家赋予了观音溪以山里姑娘的特性:既有点野性,又清秀苗条,十分可爱。这种描写语言也显得十分活泼,从而使这个观音溪趣味横生,富有魅力。
第三,不少小说常常被誉为某一地区的“民俗史”或者“民俗百科全书”,这是因为这些小说充分描写了那里的民风民俗,而这些民风民俗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小说语言产生影响。对于外地人来说,一个地方的民俗总是带有几分神秘感或者十分有趣,为了迎合读者的好奇心理,作家在小说的相关叙述与描写中总是乐于营造相应的氛围,对其神秘性加以一定的渲染,于是小说语言就很有导游的解说词的味道,具有某种宣传性。贾平凹的《美穴地》中的踏穴、《五魁》中的背新娘等民俗描写就具有这一特点。当然,由于一些地方因袭着十分沉重的历史重负,严重的偏僻与封闭的自然环境使这些地方的历史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因而那里的民风民俗比较落后、保守、愚昧甚至冷酷与血腥。这些民风民俗在经过现代文明洗礼而具有现代思想意识的作家的笔下,受到了应有的批判与谴责,那么,此时的小说语言往往显得比较冷峻,暴露性特征比较明显。《白鹿原》中的“棒槌会”、叶蔚林的《五个女子与一根绳子》中的“沉塘”等就给人一种沉重的压抑感,有些民风民俗重在隆重的仪式,有的重在乐趣,这也常常影响到作家叙述时的语言节奏与词语的运用。写那些仪式性的民俗,作家总是在庄重的氛围叙述其过程,突出其场面的严肃。《白鹿原》对白孝文得势后回乡祭祖仪式的叙述便是在威严的锣声中开始的,虽然在这仪式上回旋着一个异质的不谐和音——因田小蛾而受罚的记忆不由在白孝文的脑海里浮现,但是白嘉轩那洪大如钟鸣的声音与“祖宗宽厚仁德”的祭辞,给这个仪式增添了肃然的气氛。在写富有乐趣的民俗时,小说的语言往往显得欢快而明亮。《白鹿原》中的清明节时的男女老幼荡秋千大概是这里的狂欢节了。小说的叙述几乎就是在笑声中展开的,给人以“轻松活泼”之感。随着对于民风民俗的描写与叙述,许多与之相关的专有词语跃进了小说语言,从而丰富了小说的语言资源。
第四,作为民间语言代表的戏曲小调、曲艺小唱、故事传说、历史掌故、顺口溜等也常常被作家们挪进小说的文本之中。诚然,这些戏曲小调、故事传说、历史掌故可能融进不少传统的官方意识形态,但是毕竟是一种民间立场的叙事,总是与现行的官方文化拉开一定的距离,并且显示出民间幽默的智慧与解构的才能。《白鹿原》写到了贺家坊的戏楼所演的折子戏《走南阳》。这出戏以比较粗俗的语言描写落魄皇帝刘秀饱了肚皮后的调情。它既解构了高高在上的皇帝的威严,同时又表达了一个朴素的观念:衣食满足之后情欲便生,尊贵的皇帝尚且如此,更何况普通的百姓呢!这出戏就是以民间特有的智慧表达了对主流文化中性禁忌的嘲谑。贾平凹的小说中多处写到这些戏曲小调、故事传说、历史掌故与顺口溜,其意就是将地域文化当作民间文化立场的立足的基石,以此来疏远、拒绝和消解来自官方的权力话语,或者他是通过这些民间文化的表现形式来强化那里人与事的传奇性,牢牢地将读者的注意力引领到他的商州这块土地上来。贾平凹的家乡商州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深厚的民间文化的积淀,民间流传的故事、传说、笑话、轶闻等等特别多,他自幼对这些民间文化耳濡目染,铭记于心,在创作时不时潮水般地涌进他的小说,化为他小说语言的一个有机部分。《浮躁》中的金狗与州河上的船工都是讲故事的能手。尤其是金狗,讲故事的时候,总是“激动不安的,且脚手辅助以表演动作”。他们所讲的这些故事传说就是他们精神饥饿中的一点点聊以填腹的食粮。然而这些故事传说或详或略地出现在小说中既可以调节小说的叙述节奏,活跃一下小说的叙事气氛,也可以给小说语言涂上民间文化的色彩。莫言的《天堂蒜薹之路》在每一章的开头都摘引了民间艺人张扣演唱的歌谣,并且还在第16章中将张扣的演唱纳入到具体的情节之中。莫言此举之意显然是从民间立场出发对天堂县发生的蒜薹事件作出评判,这与为父亲辩护的青年军官的精英话语形成互补关系。
由于地域文化给作家哺育了极其丰富的精神乳汁,成为作家的精神家园,并且给作家提供了一定的语言资源,影响着作家对小说语言的选择,因此作家们就很容易对自己最为熟悉并已积淀于自己文化心理的地域文化产生很大的依赖性。他们很可能长期地在地域文化中陶醉,并且沉湎于此,致使自己的小说语言也深深地陷于其中。这样,地域文化就很可能成为困住作家的栅栏,成为一些作家难以逾越的文化围墙。贾平凹从思想意识到文化心理还没有走进现代化的大都市,虽然早在1972年他的户口就迁进了省城西安,他试图从长篇《废都》开始描写20世纪80~90年代大都市知识分子生活,却怎么也走不出狭小的地域文化的圈子,其主要原因之一大概就在这里。他的小说语言似乎也笼罩在地域文化的阴影之中。因此,对于小说家来说,地域文化固然可以成为小说创作的圭臬,但也仅仅是圭臬之一,一个真正有作为的作家不仅善于到地域文化中去淘金,而且应该跳出其拘囿,去经受各种异地文化的洗礼,穿行于不同的文化之间,汲取各地文化的营养,再从异域文化返过来观照自己所属的地域文化。惟其如此,小说的文化内涵才能格外深厚,小说语言的立足点也才能更高,小说语言的文化底蕴也才能更加厚实。
收稿日期:2003-09-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