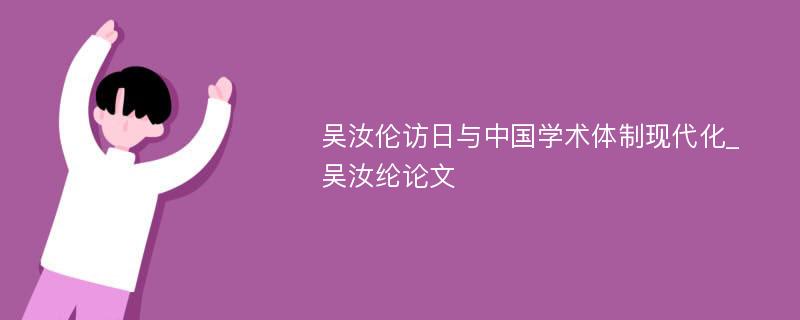
吴汝纶赴日考察与中国学制近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制论文,中国论文,赴日论文,近代化论文,吴汝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甲午战争中惊醒的中国人认识到:日本之所以获胜在于它吸收欧洲文化、政治制度、重在教育。(注:康有为:“近日者日本胜我者,亦非其将相兵士能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康有为政论集》,第307页。)此后,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出于不得已实施“新政”,其中兴办学校即是一个重要内容。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前身),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1902年,硕学吴汝纶被委任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故此,他赴日本作了为期近4个月的教育考察。在当时日本的报纸上有极为详尽的报导。吴汝纶的赴日考察在日本人看来,是中国兴办新教育的讯号。(注:日本《中央新闻》以“清国教育と吴汝纶”为题,阐释其远来日本教育考察,皆在实行教育改革的换负,扶植国民精神。日本《二六新闻》、《每日新闻》也有相应报导。)因此,无论政界抑或教育界均极为重视。
因此,笔者着意探究吴汝纶的赴日考察究竟如何影响到中国近代学制的设立以及中国教育近代化,进而分析中国既然学习了日本成功的近代学制却为什么未能真正推进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原因。
一、就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前的吴汝纶
吴汝纶(1840-1903),安徽省桐城县人。“少贫力学,尝得鸡卵一,易松脂以照读”。(注:《吴汝纶传》,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4册,中华书局,1977年8月,第13443页。)1864年25岁时乡试合格为举人,翌年会试得进士,官至内阁中书职。1868年,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拔擢他为幕僚。1870年李鸿章继为直隶总督时仍被重用。“时中外大政常决于国藩、鸿章二人,其奏疏多出于汝纶手。”(注:《吴汝纶传》,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4册,中华书局,1977年8月,第13443页。)1871年起任深州知州,其间因双亲去世而归乡里服丧。1876年再度到天津仍为李的幕僚,先后担任过天津知府、冀州知州。“其治以教育为先,不惮贵势,藉深州诸村已废学田为豪民侵夺者千四百余亩入书院,资膏火。聚一州三县高材生,亲教课之,民忘其吏,推为大师。”“及莅冀州,仍锐意兴学,深、冀两州文教斐然冠畿铺。”(注:《吴汝纶传》,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4册,中华书局,1977年8月,第13443页。)1889年辞知州职,任保定莲池书院院长。“至于西国名士、日本儒者,每过保定,必谒吴先生,进有所叩,退无不欣然推服,以为东方一人也。”(注:姚永概:《吴挚甫先生行状》,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文集》卷首,引自《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5月,第445页。)他力倡新学,认为“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吾国所独优。语其实用,则欧美新学尚焉。博物格致机械之用,必取资于彼,得其长及能共竞。旧法完且好,吾犹将革新之,况其瓜败不可复用。”(注:《吴汝纶传》,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4册,第13443页。)吴氏著有《易说》2卷、《写定尚书》1卷、《尚书故》3卷、《夏小正私笺》1卷、《文集》4卷、《诗集》1卷、《深州风土记》22卷,以及点勘诸书,皆行于世。
吴汝纶不仅熟悉国内的教育,撰有极为详尽地阐明学堂的各个段次和讲授内容及教学方法的《学堂课程》,而且对世界各国教育也颇有研究。他先后摘录了官书局报、《四国志略》等书报中有关英、美、德、法、俄各国的学校教育情况;多次接待过日本来访者,如伊藤博文来访,谈及教育之法,谓有德育、智育、体育,今中国志在智育似未善,无德育则乱,无体育则弱。吴氏曰:“吾谓智开然后知德教。”(注: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日记》(教育),莲池书社印行,1929年5月,第12页。)他还将日本学校与别国学校作比较,日本“帝国大学之学科比时於欧美最上等之位,如英国之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美国之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有优无绌。”(注: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日记》(教育),莲池书社印行,1929年5月,第14页。)
综上所述,吴汝纶确是中国清末的一个倾向西学、主张革新的幕吏,富有学术硕果的文章家,热心社会公益、循循善诱的教育家。
1902年,当清政府的变法政策转变之际,吴汝纶被管学大臣张百熙推荐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张百熙在推荐吴汝纶为总教习的上奏文中曰:关于总教习的人选,“人德、人望具备,学问、品行皆优”,必须是“学问纯粹,明察时事,深通古今,详知中外”的人物。(注:《德宗实录》卷493页。)然而,吴汝纶却提出了十条理由谢绝之。此后,张百熙先经几次直接面谈,后又拜托曾国藩之孙、吴汝纶的旧知曾祖诒劝说,还请吴氏的日本弟子、北京东文学堂长中岛裁之予以劝诱,仍均不见效。最终,同年2月13日,张百熙强行上奏,推荐吴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同日,上奏获得裁可。张百熙为表自己的诚意,“百熙具衣冠拜之,”(注:《张百熙传》,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1册,第12441页。)竟亲自向吴氏低头跪拜恳请。吴汝纶正是在既有政府命令、又顾及人际交情的情景中才承诺就任总教习职的。
二、吴汝纶在日本教育考察的经纬
“先生不得已于张公,则请往日本考察学制,以报其意,遂以壬寅五月东渡。”(注:姚永概:《吴挚甫先生行状》,《桐城吴先生文集》卷首,引自《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第445页。)吴汝纶一行,包括了大学堂提调官、浙江补用道荣勋(军机大臣荣禄的侄婿),大学堂提调官、兵部员外郎绍英等5名文武官吏和16名学生,随行者还有中岛裁之。
吴汝纶一行于1902年6月9日从塘沽出发,20日到达长崎。在长崎,考察了高等中学校、医学堂等;去神户,考察了神户小学校、女学堂、御影师范学堂;到大阪,参观高等女学校、大学堂。
吴汝纶一行在长崎、神户、大阪、京都的考察,只化了不到10天时间。此后主要集中在东京考察。首先,访问了东京大学,与该校总长、理学博士山川健次郎面谈,后由理科大学长箕作佳吉及数名教授引导参观法科讲堂、图书馆、物理实验室、动物解剖室等。再是访问大学堂、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华族女学校、徒弟学堂、盲哑学校、常磐小学校、富士见小学、东京市立师范学校、东京第一中学校、东京府女子师范学校、早稻田学堂等。据笔者统计,吴汝纶一行在东京访问过的学校多达25所以上。
他们在东京的访问考察,主要是对学校制度的视察和调查。因此,一方面,除访问参观学校以外,还历访跟学校有关的官厅,如文部省、外务省、参谋本部等。在文部省从9月10日至10月7日的将近一个月内参加了19次“特别讲演”的听讲,其内容均是有关教育行政、教育大意、学校卫生、学校管理法、教学法、学校设备、日本学校沿革等。另一方面,历访学校领导、教育行政长官、教育名家以及政军界人物。依吴汝纶日记所记有:东京帝国大学总长山川健次郎、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文部大臣菊池大麓、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华族女学校长下田歌子、东亚同文会副会长长冈护美、帝国教育会会长辻新次、外务省总务部长珍田舍己、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陆军大臣寺内正毅、参谋总长大山岩、教育家伊泽修二、宪政党总裁大隈重信、前文部大臣滨尾新、前文部大辅田中不二麿、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长井上哲次郎、枢密院顾问官副岛种臣、法务大臣清浦圭吾、政友会总裁伊藤博文等。此外,出于对近代日本国家的关注,还参观了议院、法院、警视厅、监狱以及造船和造币的工厂及各种会社、银行、电话局、邮局等等。
笔者依据其日记统计,吴汝纶在日访问期间,先后到达的单位不下50个,持有会见者名片的也在百人以上。吴汝纶赴日考察受到日方的空前重视,不仅经常被邀出席招待会,还破例受到天皇的接见,记者采访、新闻报导也连续不断,他的一言一行随时被传录于报章杂志。
吴汝纶一行在东京考察以后,经京都、神户,于10月22日(旧历9月21日)返抵上海。记录吴汝纶赴日教育考察详细经纬的,一是由在日访问期间日方各种报纸的编集成的《东游日报译编》,该书除了报道访日进程外,还有日方官员、学者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建议以及吴汝纶本人的教育改革设想;二是由吴汝纶在归国前写就并经日本三省堂书店出版(1902年10月17日)的访问报告书《东游丛录》。
该书分为四部分:一、文部听讲,记述教育行政、教育大意、学校卫生、学校管理法、教授法、学校设备、学校教育沿革,并附欧美各国小学校学科课程;二,摘抄日记,起于5月15日至9月6日(阴历);三,学校图表,如东京大学员数度支表、西京大学预算表、东京府立中学校学则课程度支成绩表、西京寻常中学校宿舍规则、东京市富士见小学校略图、私立女子职业学校概则、现行学校系统、高等学校预备科课程表等19幅;四、函札笔谈,收录了日户胜郎、望月兴三郎、胜浦鞆雄等来书,九州《日日新闻》、东京《日本新闻》等报的译文,以及与井上哲次郎、高木政胜等人的笔谈,与大学长山川健次郎、前文部大臣滨尾新、帝国教育会会长辻新次、贵族院议员伊泽修二等的谈片(由他人作的记录)等共28篇。
吴汝纶撰著该书,其意十分明确,就是要将日本考察所得集录下来,呈管掌大臣在推行教育改革时“以备采择”。
吴汝纶一行将近4个月的赴日教育考察,像他在给张百熙的信中所言:“辰承尊命,渡海东游,视察学制,居处三月有余,仍未得要领。”(注: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尺牍》卷四,第55页。)其实,吴汝纶视察日本以后的教育改革思想已基本上在这封信中表白出来了,其要点似可概括为:一,培养教员,“窃谓吾国开办学堂,苦乏教员”,“谓救急办法,惟有取我高材生教以西学,数年之闲便可得用。查日本初时,令各藩送士人入大学,谓之贡进生,意也如此。今所开师范学校适与符契,即明年开大学堂,恐仍须扼定此指”;二,普及基础教育,“欲令后起之士与外国人才竞美,则要由中小学校循序渐进,乃无欲速不达之患。而小学培养成大中学基本,乃是普及国人而尽教之,不入学者有罚。各国所以能强者,全赖有此”;三,统一语言,“此为国民团体最要之义,日本学校必有国语读本,吾若效之,则有省笔字,不可不仿办矣”;四,兴办实业学校,“若初办大学堂之专科,……政治法律之外,则矿山、铁道、税关、邮政数事为最急,海陆军法、炮工、船厂次之。此皆数年卒业即可应用者也”;五,废科举,“其尤要者,教育与政治有密切关系,非请停科举则学校难成。”(注: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尺牍》卷四,第55-59页。)
那么,吴汝纶考察日本教育后的这些意见究竟对清末教育改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就得通过考察近代学制的建立过程加以说明。
三、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
1901年1月29日西太后下达“变法上谕”,要求内外大臣及各省督抚提出教育改革方案。山东巡抚袁世凯、礼部侍郎张百熙、两江总督刘坤一及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均上奏,提出了教育改革的具体方案。一时间各省废旧有书院,设立高等学堂和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设中学堂,各州县开设小学堂,各地设蒙学堂,因义和团运动而关闭的中国第一所近代大学——京师大学堂获重新开设。是时,清政府“新政”的教育改革,确有意导入近代学校制度,建立全国规模的从小学堂到大学堂的近代学校体系。
1902年8月,由张百熙奏进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大学堂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及《各学堂系统图》予以批准颁布,总称《钦定学堂章程》。因这年为阴历壬寅年,故史称“壬寅学制”。《钦定学堂章程》的制定和颁布意味着中国实行近代教育制度的开始。可是,张百熙所制订并正式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由于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加上这个章程本身的不完备性,故除了《京师大学堂章程》外,其它的几个章程几乎都未能实施。结果在其颁布的一年半后,即1904年1月,又颁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三人共同制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其实,这个章程主要是由张之洞的手下陈毅起草的,经过张之洞的审订。该章程较前章程除内容上有修改外,还增加了师范学堂、实业学堂、洋学馆、进士馆等的章程,以及各类学堂的管理通则、任用教员、学堂奖励等章程。各种章程、通则各为1册,共20册。《奏定学堂章程》颁布的年份,为阴历癸卯年,故史称“癸卯学制”。
《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标志着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体现出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正规化、体系化。所以,它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如将“钦定”、“奏定”两个章程作一对照,我们就不难发现:“奏定”章程的分类、细目较“钦定”大幅增加,因此,体系就较前者更加完备;再从后一章程对前一章程所作的修改内容来说,张之洞等在《奏定学堂章程》的《学务纲要》中强调“此次尊旨修改各学堂章程,以忠孝为敷教之本,以礼法定训俗之方,以练习艺能为致用治生之具。”(注:《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10月,第200页。)更明确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指导思想。同时,“奏定”较之“钦定”的学堂章程,更加显明地表现出是以日本明治维新初期的教育制度为“模特儿”的。两者除了学制的阶段、年限大体相同以外,学校的类型和宗旨基本上相似,甚至是基本照抄日本的。例如,《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设初等小学堂,令凡国民七岁以上者入焉,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为宗旨;以识字之民日多为成效”。(注:《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多贺秋五郎:《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清末篇),日本学术振兴会刊,昭和47年3月,第297页。)《高等小学堂章程》规定,“设高等小学,令凡已初等小学毕业者入焉。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为宗旨,以童年皆知作人之正理,皆有谋生之计虑为成效”。(注:《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多贺秋五郎:《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清末篇),日本学术振兴会刊,昭和47年3月,第288页。)所有这些,与日本明治23年(1891年)的《小学令》所规定的“小学校以留意儿童身体之发达,授以道德教育及国民教育之基础,并其生活必须之普及知识技能”,(注:明治23年《小学校令》,黑田茂次郎等编:《明治学制沿革史》,有明书房,平成元年10月,第56页。)两者是何等的相似!另外,《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的急办师范学堂和强调军事教育的精神及措施也与日本的学制大体相同。显而易见,《奏定学堂章程》的制定和颁布,使清末建立的近代学制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日本型时代”。但是,它又区别于日本的明治学制。日本明治学制是广泛吸收了欧美的教育制度结合本国实际所形成的,也就是吸收欧美教育的先进经验,与本国传统的教育经验和民族精神相结合,故* 符合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对内对外政策的需要;而清末制定和颁布的学制,虽然照搬了日本的教育制度,然而其指导思想仍强调传统的封建道德和“中体西用”思想观念,故成为资本主义与封建制度的复合体。
四,吴汝纶赴日考察对清末学制设立的影响
1902年8月,张百熙制定和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时,吴汝纶已在日本考察。他并未参与这个章程的制订工作。但是,吴汝纶访日期间曾有6封信写给张百熙。他在信中所阐释的教育改革意见,也在章程中有所体现。例如,吴汝纶主张中西兼学、学制要缩短,故《钦定学堂章程》所规定的读经时间和内容相对的少些;在学制年限上,以初等教育来说,寻常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各为3年,这较之后来的《奏定学堂章程》所规定的初等小学5年、高等小学4年,合计为9年的要短3年。
吴汝纶与张百熙的关系比较密切而跟张之洞的关系不好,相互持对立态度,以至于他从日本考察回来,归避乡里,不到京师大学堂就任。由张之洞主持制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其基本精神是依据由他任命去日本考察的罗振玉的意见。据罗振玉在自传中所云:“至于‘保存国粹’之说,因予在教育杂志发表论文,充分阐述其道理,‘国粹保存’四字成一时众人所言,持续其效果。文襄(张之洞)在制定学堂章程时,课程中增加读经科目。”(注:罗振玉:《罗雪堂先生全集》五编,台湾大通书局,1973年,第16页。)这显然与吴汝纶要削减读经的意见是相左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奏定学堂章程》中确实反映出吴汝纶要办好师范学校、实业学校、重视普及教育等主张。如在《奏定学堂章程》的《学务纲要》中专有‘宜首先急办师范学堂”、“各省宜建设实业学堂”之款项,指出:“此时惟有急设各师范学堂、初级师范以教初等小学及高等小学之学生,优级师范以教中学堂之学生及初级师范学堂之师范生。……查开通国民知识,普施教育,以小学堂为最要,则是初级师范学堂造就教小学之师范生,尤为办学堂者第一义。”(注: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10月,第200-201页。)“农工商各项实业学堂,以学成后各得治生之计为主,最有益于邦本。其程度亦有高等、中等、初等之分,宜饬各就地方情况,审择所宜,函谋广设。……此项实业分作两班,一班习中等,以期速成,一班学高等,以期完备。”(注: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10月,第202页。)
另外,吴汝纶在日本考察报告书《东游丛录》中不仅有28幅图表,而且还有“译教育法规中建筑准则”、“早川译中学设备一则”、“早川译学校清洁法”等,对学校校址的选择、校舍规格、教室要求、学生坐椅以及灯光和黑板的亮度及角度、清洁卫生要求等都有明确详尽的叙述。《学务纲要》中专有“各学堂建造须合规制”的款项,规定“外省大小各学堂,建造屋宇均宜求合规式,方能有益。查各国学堂,其布置之格局,讲堂斋舍,员役之室,化验之所,体操之院,实验之场,诵读之几凳,容积尺寸,光线之明暗,坐次之远近,屋舍联属之次序,皆有规制。一为益于卫生,二为便于讲习,三为便于稽察约束,皆系考验阅历多年而后审定者。凡游历外国者,固已亲见其规模式样。近来日本专绘印有学堂图,尤可取资模仿。若限于地势经费者,原可酌量变动。但其有关系处,万不可失其本意。虽不师其形,要必师其法。”(注: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10月,第217-218页。)显然,吴汝纶的考察报告是被详加采纳的。
以上就是有关吴汝纶赴日考察对清末两个学制设立的影响的简要叙述。然而,笔者认为,清末两个学制的设立,正如张百熙、张之洞所言,“数月以来,臣等互相讨论,虚表商榷,并博考外国各项学堂课程名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注: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10月,第197页。)他们所说的“博考外国……”,当然不只是指吴汝纶、罗振玉的考察意见了,因为清末赴日教育考察是相当频繁的。
从1898年至1903年,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派遣乃至自费赴日考察且有考察成果出版的,约在15次以上,人数多达65人,出版的著作也近20部。另外,上述同时期内,尚有管学大臣孙家鼐所遣监察御史李盛铎、湖广总督张之洞所遣湖北道台朱滋泽、山东巡抚周馥派遣补用知府李凤年、湖北巡抚端方所遣看操委员统带忠全营、四川总督岑春煊所遣翰林院编修胡俊等人赴日考察。据笔者统计,尽管他们没有成果出版,但无论是人数抑或次数均超过了前者,即19次、108人。(注:据汪婉《清末中国对日视察者一览》的统计,《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视察の研究》(附录),第3-13页。)无疑,他们的考察也不会对学制改革没有影响。
笔者所以要稍微详尽地列举上述两类赴日教育考察的情况,意在说明清末所制订的两个学制均是在充分考察日本教育后制订的,故不必过分地拘泥于究竟是依据了谁的考察而编订成的。当然,吴汝纶考察所写的《东游丛录》被认为是“介绍日本教育制度的书籍中最为详细的。……共计410页的该书,近半数即用190页的纸幅介绍了日本教育制度的所有方面。若称它为日本各种学校的‘指南’或‘便览’也决不过分”。(注:熊达云:《近代中国官民の日本视察》,第194-195页。)固然,它会对两个学制的设定有直接影响。同样,也该承认罗振玉所说“保存国粹”的意见对张之洞制订学制的影响;此外,他所主持编辑的《教育世界》杂志,从1901年至1903年间共出版了45卷,其中介绍得非常具体的各类学校的大纲、规则、文部省法令等,也成为两个学制制订的一个重要的参考讯息来源。
迄今,对于吴汝纶赴日教育考察,有两个问题还没有引起研究者们的充分注意:一是对留学生的关心和理解问题;二是聘请日本教习问题。
吴汝纶到日本访问,也关心留日学生。他到东京后不久,“至成城学校,遍阅中国留学诸生,各以数语勉励之”。(注: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日记》(教育),莲池书社印,1929年5月,第28页。)吴汝纶访日期间,驻日公使蔡钧拒绝承诺为钮瑷等9名私费生作入成城学校的担保,激起了以吴敬恒为代表的留学生的抗议,并有27名留日学生集会于公使馆,要求与公使面谈,而公使不予会面,反而在晚上让日本警察拘留了吴敬恒、孙揆均二人。虽次日释放,但被处以强制送返国内,吴敬恒自杀未遂。吴汝纶日记所记:“吾目见此变,一筹莫展,愤慨无极。”(注: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日记》(教育),莲池书社印,1929年5月,第31页。)吴汝纶日记中竟有8天的日记中论及此事。他与10余个学生相谈,也跟蔡公使反目,并与日本外务省官员等交涉。他作为清政府派出的官员,因与蔡公使不同调而受到蔡的轻蔑。事件随着蔡的职务更迭终算解决,9名留学生获得了入成城学校的许可。此后,吴汝纶多次与日本外务省政务局山座圆次郎、外务部长珍田舍己交谈,“告以私费生有益于国,望外务部爱惜保护,以振鄙国新机。”(注: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日记》(教育),莲池书社印,1929年5月,第32页。)对珍田舍己曰:“吾请其官、私学生皆一律待遇。”(注: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日记》(教育),莲池书社印,1929年5月,第33页。)并对学生事件辩解说:“至学生与政府反对实无其事,若欲明其来历则近来学生会馆有干事,若五人保一人,决无他虑,且我学生中私费生皆有余之家、开化之土,岂有学归谋反者乎!此可请放心也。”(注: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日记》(教育),莲池书社印,1929年5月,第33页。)又言:“缘吾国财力支绌,官生不能多送,私费生不用国家资给,正当奖励招徕。若一有阻滞,实于国维新有碍,所关甚钜。”(注: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日记》(教育),莲池书社印,1929年5月,第33页。)以上寥寥数语,足见吴汝纶对留日学生的关心、同情和支持,以及对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意义的认识。
清末聘请日本教习来中国任教,虽有1896年京师同文馆聘用杉几太郎,1898年杭州创办蚕学馆也聘请了日本教习,但当时并没有明文规定和形成制度。清政府正式向日本提出招聘教习是在吴汝纶访日期间,且吴汝纶作出了不少的努力。他一方面对日本政府官员、教育家进行交谈,要求日本选派教员到中国来任职。这也正合日本之意。如日户胜郎给吴汝纶的信中曰:“养成教员者,是教育上最先最大之急务也。……文相之意,方今之际,鄙国虽乏干济之材力,然欲为清国送良教员,正在妙选未定,又不日期应阁下之质问,予有所审虑碎心,待面谈吐胸中之见。”(注:吴汝纶:《东游丛录》(函札笔谈),东京三省堂,1902年10月,第1-2页。)在与日本帝国教育会会长辻新次的交谈中,辻氏谈及聘请外国教员,如若“始基之不慎,贻害於后学者匪浅。日本明治初年,迭受此种弊害,愿贵国勿复蹈此也。”他还直接向吴汝纶提出:“窃拟募集鄙国师范生之卒业者,授以贵国历史地理,并告以风俗人情,及通行之语言。此假鄙国人士,养成贵国教员者也。”(注:吴汝纶:《东游丛录》(函札笔谈),东京三省堂,1902年10月,第86-87页。)由他所主持的帝国教育会专门设立了“清国派遣教员养成所”,负责训练来中国的教员。另一方面,吴汝纶又去信张百熙,推荐日本教员来中国任教。如推荐服部、岩谷两人来中国任教,还介绍湖南留日学生范景生为之作翻译。(注: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尺牍》卷四,第59页。)从此,清政府聘请日本教习成为定例。因此,也有人称清末教育改革为“日本教习时代”。(注:增田史郎亮:《清末の教育にぁたぇた日本の影响》,载:多贺秋五郎:《近代ァツァ教育史研究》(下卷),1975年3月,第144页。)
清末的教育近代化,从壬寅学制、癸卯学制的颁布到1905年废除科举又设立统辖全国各级各类教育管理的学部,初步形成全国统一的学校教育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实施格局。这无疑是有益于教育近代化的演进。但是,笔者认为,留日学生和日本教习又是推进这个教育近代化的两个车轮。因此,我们在评价吴汝纶赴日考察对推进清末教育改革的影响和作用时,就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吴汝纶赴日教育考察,不仅直接影响到壬寅学制、癸卯学制的制订,而且与其他赴日教育考察者相比,为吴汝纶所特有的,即对留日学生的关心和理解及为聘请日本教习所作出的努力。所以,吴汝纶赴日教育考察对清末教育近代化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是同期其他赴日教育考察者所不能相比的。
结语
清末硕学吴汝纶的赴日教育考察,受到中日双方政府及民间的重视,不仅对当时清末教育改革,而且对加深中日两国的教育关系和民间交流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从以硕学和官员双重身份赴日的吴汝纶在日受到的热情接待和频频交往中,也能体察到日本人自甲午战争以来所形成的“对古代中国的尊敬、对现代中国的轻蔑”这个中国观的缘由。
吴汝纶在日本作了将近4个月的教育考察,他所写成的考察报告书《东游丛录》,不仅在归国前已于日本出版,而后又在国内出版了《重订东游丛录》,这对清末学制设立无疑产生了直接影响。同时,从该书所记的吴汝纶关心留日学生、聘请日本教习的言论和行动,也可说明他的访日对清政府在建立近代学制的基础上推进教育近代化所产生的影响。(注:吴汝纶:《东游丛录》,东京三省堂,明治35年10月。)
吴汝纶的赴日考察,正如他自己所说:“东来三月,考览日本学制,未能得其精奥。”究其原因,关键是其头脑中的“传统观念”和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体制形成的冲突,致使像他这样一个力主进行教育改革的人也跳不出“半封建半殖民地”模式的框框。清末近代学制的起始,标志着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但要有所推进,还得摆脱只是形式上的学习日本,且不能“以猫画虎”,而要吸取日本教育改革成功经验的精神实质,拓展对欧美教育思想、制度、方法等的宣传和介绍(包括通过日本的翻译书籍),并付诸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