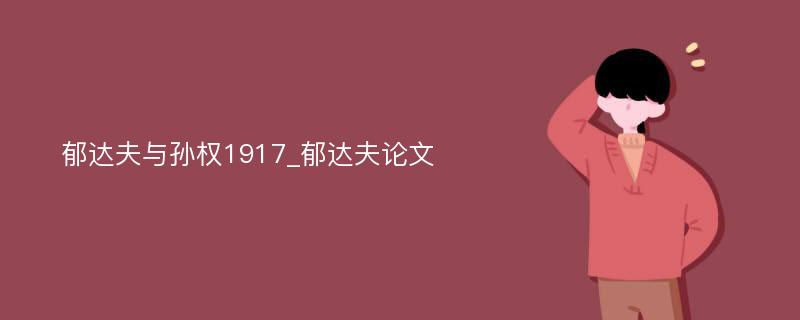
说郁达夫与孙荃的1917,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达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的感情生活,向来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谈论的焦点往往集中在他与王映霞女士的悲欢离合上——窥视隐私是普通民众最正常不过的心理,何况窥视的对象是《沉沦》的作者、“风流才子”郁达夫。众所周知,郁达夫一生有过三次婚姻,每次婚姻都有其不同的条件和背景,每次婚姻也折射出作家不同阶段的思想倾向与人生态度,甚至是文学追求。可是从1927年郁王之恋开始,到《日记九种》、《毁家诗纪》的公开发表,甚至到上世纪末王女士的《自传》出版,关于郁王的文章与专著不绝于耳,倒鲜有真正研究原配夫人孙荃与最后一位妻子何丽有的专门著述,即使在绝大部分传记中,也仅仅是一笔带过,或者干脆把郁与孙定性为包办婚姻,把郁与何的关系定性为为了掩护流亡进步文化人士的伪装。然而事实上,细致考察郁达夫与原配夫人孙荃的婚姻状态,对于正确理解作家在作品中(特别是早期小说)对社会和现实生活的种种指责、作家个体思想的变迁,以及作家生活细节和文本当中所描绘细节的整合分离,都应该大有裨益——比如说,许多郁达夫研究家都认为,当年郁达夫以种种理由推迟婚期,并且在婚礼当天提出在现在看来也属苛刻的条件——取消拜堂、花轿、鼓手和筵席,只请至亲便餐完事,是出于对母亲包办婚姻无声的反抗与不满。因为反抗包办婚姻正是“五四”时期知识青年最强烈的呼声,所以就有了推论:郁达夫无论从思想上(主要指他的作品)还是实践中,都具备了反抗封建思想的倾向和斗争精神。然而这样的定论又有多少史实的依据呢?在这种对抗表象下有没有别的深层次原因呢?比如说家庭经济的窘迫、郁达夫孤傲的文士性情等等。在不经任何探究的情况下,将郁孙联姻看作简单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仅有悖于严谨的学风,也显然是不完整的。
当然,仅就郁达夫与原配孙荃的研究而言,第一手资料的匮乏也是一个阻碍的瓶颈。近日,笔者有幸得到郁氏后裔同意,得以查阅郁达夫1917年相关日记及郁孙往来书信,并以此为基础作了调查与走访。本文仅从史料角度出发,把1917年有关郁达夫与孙荃的婚约形成、第一次会面、书信往来等,作一系统的回顾与梳理。
一、婚约
孙荃夫人为富阳宵井下台门人氏,下台门孙氏与郁家的交往可谓源远流长。查阅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的《萧邑郁氏宗谱》①,可清晰地看到两家的世交图谱。据《宗谱·卷一》辑录的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2月十四世郁大镛与孙氏祖上所订合同议信记载:郁氏十三世宸章公与孙天佑公“从少年结义一生,情同手足,胜若同胞”,以至于后辈“不忍二君墓设两处”,共同出资在富阳屠山(今属场口镇)买了一块田地作为两家的祖坟地,并将一对结义兄弟“安葬一处,始全遗命”。从此,两家间的过往关系更加密切,到郁达夫与原配孙荃联姻,已经历了数代的老亲沿袭:十四世郁大镛在原配邵氏没有生育的情况下,续配宵井下台门的孙氏;十五世郁嗣海也迎配宵井下台门孙氏。
关于郁、孙间的这门婚事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最广泛流传的是“三岁定亲说”。主要证据来自于郁达夫自己对王映霞女士的交代,“是完全由父母作主,在三岁的时候定下的”②,然而这种说法并不能令人信服。首先因为说话的背景,正是郁达夫热烈地追求王映霞之时,“一个未成年的少女,是怎样地被一个已婚的浪漫男人用诱和逼的双重手段,来达到了他的目的”③;其次,这种说法并没有别的佐证,郁达夫自1917年阳历2月16日开始记日记,在前4个月的记载中并没有出现有关婚事的片言只语,直到6月17日:“……今日接家信谓将予完婚,明日将作复绝此信一封。”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史料中最早的有关郁孙婚姻的文字记录。
笔者为此专门走访了与孙荃共同生活达三十年之久的郁达夫长媳陆费澄女士(郁天民夫人)。据她回忆,孙荃与郁达夫的婚约确实是由郁达夫的母亲陆老太太做主所定。陆老太太在郁家的地位无疑是崇高的,因为她嫁到郁家的当年除夕夜晚,“吃完年夜饭,她的婆婆就将全家的收支债务移交给她这个过门不久的新儿媳妇”④。粗略算来,到1917年止,陆老太太已做了近三十年的“当家人”,特别是在丈夫郁企曾英年早逝后,她硬是把这个两代寡妇祖孙老幼七口⑤ 啼饥相守的贫寒之家撑了下来,并且培养出了两个日本留学生、一个陆军学堂的毕业生。因此,由她给小儿子挑个媳妇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
郁企曾病逝后,一家老小的生计操持,逼得陆老太太不得不抛头露面,出入于各种场合。郁达夫在《自传》中写道:“自父亲死后,母亲要身兼父职了,入秋以后,老是不在家里;上乡间去收租谷是她,将谷托人去砻成米也是她,雇了船,连柴带米,一道运回城里来也是她。”⑥ 而且,郁家在宵井附近应该是有田产的——到目前为止,在宵井附近的下塘村,还有郁家的祖坟山地——孙荃夫人与郁天民先生就长眠于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陆氏(生于1866年)是宵井栗园里人——而栗园里与孙荃娘家下台门相去不过数里,即使是步行,半天也可以打个来回。
陆费澄女士转述了孙荃关于此事的回忆:她和郁达夫的婚约,虽然双方家长早有所谈及,但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娃娃亲,只是停留于口头上的约定而已。到了1917年,一来二人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二来双方家里也都相识相知,于是在双方家长的一致同意下,想趁郁达夫回国之际举办婚事。至于两家最终敲定联姻的时间、地点,因当事人及知情者都已离世,现已无可考证,但肯定与1917年相距不会太远。所谓的“三岁订亲”,根本是不存在的。而且,陆费澄女士还特意澄清一个事实:孙荃在正式订婚以前,从未到过郁家——有资料称郁母曾提出来要亲眼见一下未来儿媳妇的模样,她通过中介人捎信:“要她有空到城里来玩玩”,其实就是要亲自给儿子相亲,看看这位乡下姑娘够不够条件做郁家的小房媳妇。孙荃到了郁宅后,因为对了郁母的胃口,郁母还硬是把孙荃留下来住了一个晚上。⑦ 事实上,按照富阳的风俗,未出门的姑娘不能随便到未婚夫家串门,何况是宿夜不归。郁达夫1917年10月17日信中明确要求孙荃“汝若赴杭,道经富阳,不妨暂至家中一坐,使祖母一见,安伊老后之心”,而且12月30日郁达夫致孙荃明信片再一次证明:1917年12月初,孙荃才第一次来到满舟弄的郁氏老宅。陆费澄女士还谈到,因为郁母经常回娘家或者到宵井一带处理事务,加上与孙荃娘家本来就有亲戚间的走动(下文将论及——笔者注),郁母偶尔也到孙家吃个午饭歇个脚,甚至于住上一晚两晚的,因此郁母与孙荃的会面,应该是早在1917年以前很久就完成的了。
二、孙荃
孙荃,原名兰坡,小字潜媞,1897年出生于富阳宵井下台门村,比郁达夫只小了一岁。她的父亲孙孝贞,也曾苦读寒窗数十年,最终科举无望,遂弃文经商,经营着一个规模不小的纸厂和百来亩田地。他娶过两房妻子,前妻早故。因经商的缘故,孙孝贞跑过不少的码头,见过不少的世面,杭州、上海这样的地方常来常往。因此,他继娶的第二房妻子,也就是孙荃的母亲,是杭州拱宸桥人氏,据说也能识文断字,具有一定的文化。这在当时,殊为不易。
孙孝贞作为江南小县的乡绅,无疑是开明的。这种开明不仅体现在他自小就亲自教导孙荃读书,也体现在他乐于将心爱的女儿嫁入贫寒的郁家,嫁给一个前途未定的日本留学生。从他同意与郁家联姻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在今后的岁月里必须对女儿女婿倾注更多的关怀和经济上的支援,甚至种种在农村人看来不能承受的委屈。比如说,他比较平静地接受了郁家苛刻的婚礼方式,如期将女儿送入郁家大门;再比如说,正是因为郁家贫寒,所以他就省略了一个结婚礼仪中必不可少的程序——聘礼,反而为当年没给女儿一份丰厚的嫁妆而耿耿于怀——这个心结,直到1930年代郁氏三兄弟分家时才解开:他为了心爱的女儿能获得现达夫弄1号郁氏祖宅的产权,拿出了五百现大洋,理由就是当年孙荃夫人出嫁时他没给嫁妆⑧——当然,这是后话。然而孙荃正是在父亲的影响和关注下才读完了一些童蒙书籍,后来孙孝贞还特意聘请了家庭教师李宴春(富阳场口人),指导孙荃进行较长时间的学习。在孙荃十来岁的时候,已能跟父亲、长兄进行诗词唱和了。
孙荃长兄孙灏,字贻清,又字伊清,小名阿水,与孙荃同父异母。他个子矮小又有些驼背,虽其貌不扬却满腹经纶,曾中过秀才,诗文俱佳还有一手高明的医术,本地人亲切地称他为“阿水先生”。孙荃对这个同父异母的哥哥相当尊重,不仅时时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向他咨询意见,还在与郁达夫通信之初请他润色修改。郁达夫1917年9月22日致孙荃信中曾写道:“前次关绪带来书一封,虽系汝手笔,然语气不合,当是汝兄草稿。此后无论如何,不可使人代作。若辞不能达意时,只可问一句二句,不可通篇求人改削也。”⑨ 孙荃对伊清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
在富阳郁氏后裔的手中,到现在还保存着一页郁达夫致孙伊清的信,落款为:“近作四律呈伊清表叔斧正”。这封信有几个很值得关注的地方:第一,郁达夫称伊清为“表叔”,说明除孙荃这一层关系外,孙郁两家还是表亲,孙荃还长郁达夫一辈。而且这个“表”应该来自于郁达夫母亲陆氏身上,因为毕竟栗园里与下台门相去不过数里。其二,郁达夫对孙伊清比较敬重,首先当然是因为他是年长的表叔,但常有诗词往来,也说明他对孙的学识是承认的。第三,查信中四首诗的成诗时间均为1915年,最晚一首《寄曼陀养吾市师》同年10月8日发表于杭州《之江日报》副刊《浙輶新语》,对照信末“达夫又启”(按,前四首已见于之江、神州日报,或已达览,亦未可知。),以及“近作四律”,可确知该信应该成稿于1915年11月前后。以上几点,充分印证了郁氏后裔的说法:两家原本走动,郁母还曾到孙孝贞家歇脚、住宿。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自孙郁订亲后,郁达夫对孙伊清的称谓就起了变动,从“表叔”一变而为“外兄”,有1918年10月2日郁达夫致孙伊清信为证。⑩ 也可从另一侧面印证郁氏后裔对于郁孙婚约的说法:开始,仅限于双方家长的口头约定,对双方都没有约束力,直到订亲,这段婚姻才正式被认可。
在孙氏家庭里,还有一个人物应当引起注意,就是自1917年8月始多次在郁达夫日记和信件中出现的“关绪”或“树祺”。孙树祺,小名关绪,即孙伊清的长公子,即孙荃侄儿,1917年9月(也即订亲不久)即随郁达夫东渡留学。郁达夫也似乎在这个内侄身上花费了很多精力与时间,甚至曾帮助他找枪手替考,可惜这个内侄本身甚不争气,最后学无所成,在浪费了孙孝贞大量的钱财后灰溜溜回到家乡,舒舒服服地做起了“关绪老爷”(11),直到“文革”后病死于宵井家中——因关绪与本文不甚相关,暂且按下容另文再提。
总之,孙荃出生、长大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形成了她沉着、内敛、自主、刚强的性格。对于这门亲事,孙荃心里应该是有自己的主张的,虽然“在家从父”是传统道德不可突破的界线,但嫁到贫寒之家受苦受累的毕竟是自己。说到底,孙荃是向往着与东渡日本的郁达夫结合的,与其说她明知郁家是个火坑还往里跳,把自己一生的幸福全然不当回事,不如说她接受的是“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样的传统教育,在“日本留学生”这层耀眼光芒的照射下,很自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哪怕明知自己免不了要受些相思、离别之苦,但还是无怨无悔地尽力去迎合未来夫君的口味,习字、吟诗、作文,深怕自己配不上郁家三少爷的满腹经纶。
三、郁达夫
查郁达夫1917年日记,最早提到归国一事是在6月8日:“今日颇思归,苦无余钱,只能作罢论耳。来年则无论如何必欲归国一次也。”第二天,也即9日日记:“郁极思归颇苦,晚发信两封,一问经理员支费,一问家中索旅费者也。”大多数《郁达夫传》都认为,1917年夏,家中老祖母、祖母非逼着郁达夫归家完婚而郁达夫一拖再拖归来的日期,然而以上记载却表明此次归乡是郁达夫自己先向家里提出来,并索要旅费。归家的原由,是因为与长兄反目近半年(12) 而“郁极思归”,6月8日同日日记中他还写道:“午前颇不振。夜雨,同学某来予正苦寂也。嗟乎!予自与曼兄绝后予之旧友一朝弃尽,影形相吊,迄今半载。来访穷庐者二三小孩外只洗衣老妇及饭店走卒耳!而某犹不识予心,时或一来,探问若愚若敏,似醉似醒,其嘲予者耶,抑怜我者乎?”此外,在此之前的日记中也没有提到婚事,或者表现出因婚事所引起的焦虑与不安。反而在6月10日开始,“为Venus所缚”,与开设小杂货铺的后藤隆子小姐共同谱写了一支短暂却悦耳的恋曲。(13) 当然,这支恋曲并没有奏得震天响,在6月25日郁达夫伏枕吟成《别隆儿》后就寂静无声了。然而笔者注意的并不是这段恋情的开始和完结,而在于完结的原因——原来就在20日晚,郁达夫思前想后,不胜自卑:“思人事如潮,寸怀良苦。予不怨予兄,乃怨全人类也!予兄不过人类中之一人耳。予已不幸,予断不能使爱予之人,亦变而为不幸。此后予不欲往隆儿处矣……”(14) 很明显,这段感情最后没有着落,是与经济有直接关系的,与所谓的“家庭逼婚”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
但郁达夫对这桩婚事至少还是不愿意的。6月16日日记:“今日接家信谓将为予完婚,明日将作复绝此事之信一封。”17日果然“今日发家信一封”,说的应该就是此事。但此后数天的日记中非常平静,只记录了如何请假,如何与隆儿交往,甚至记录了自己腹泻,担心“不能耐长途辛苦”,而绝口不提“逼婚”大事。以6月前后的日记来看,如果家庭“逼婚”渐紧,他又对此无限抵触,日记上无论如何应该有所记载,然而没有;再从郁达夫的个性来看,他尽可以躲在日本不回来,以逃避“逼婚”,然而也没有。事实证明,郁达夫对这次回乡并非充满恐惧,因为也没有人强硬地逼迫他近期内就要完婚(这一点从郁达夫很随意地回了封信,然后还是欣欣然准备回乡即可看出)。而他不愿太早结婚是有道理的:经济还未独立,学业还未完成,哪有精力与财力养家?至于孙荃,只是听说而未谋面,也谈不上喜欢不喜欢,所以“走一步看一步”应该就是郁达夫当时的心态了。
四、谋面
1917年7月7日,郁达夫终于回到了阔别五年的故乡富阳。免不了拜见过祖母、母亲后说些家常,也免不了会提到婚事,但令人称奇的是郁达夫在随后的日记里还是绝口不提人们想象中婚姻带给他的烦恼,也没有祖母、母亲,包括二哥养吾劝他早日完婚的片言只语,只是不停地走亲访友,吟诗读书,直到7月22日才赴宵井,当日日记云:
晨起即往宵井,午前十一时顷午膳,膳毕偕树祺等至贝山寺,雨时方在贝山寺小饮也。入山里许至白纸槽,有劈竹使成细束者,有置细竹于灰水中者,有洗涤之者,有于槽中沥纸者,千工万苦始能造成一纸。创业之艰于斯可见矣!午后接陈某谈。拟明晨回富阳。夜不成睡,苦蚊子多也。
从孙家一路缓坡大约二里地,即到贝山寺,现建有贝山寺水库,从孙家门外即可望见。因富阳传统造纸离不开水,所以纸槽建在这里再合适不过。郁达夫此行到宵井更像是走亲访友,或者说是专门去考察竹制宣纸工艺,而不带有别的目的,心情好像也不错。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天虽然在宵井吃午饭,甚至晚上也宿于宵井(但是否一定食、宿都在孙家,未可断定),然而并未与孙荃相见。唯一值得推敲的是“午后接陈某谈”中的“陈某”到底是哪路神仙,是否就是媒人陈凤标?如果是,那么就应该谈及婚姻大事,而且按郁达夫记日记的习惯,至少应该有所表示,然而语焉不详,不得而知。但就在从宵井回来的当天,即7月23日,“陈凤标表公以婚事来谈”,24日,“晨起作书致陈某婉辞婚也”。(15)
至此,孙郁联姻似乎走入了一个死胡同。从郁达夫当机立断地通过媒人陈凤标“婉辞婚”的第二天(7月25日)始,他就欣欣然与姐夫某畅游杭州西湖去了,直到29日才回到富阳。在随后的近10天时间里,生活又回到了正常,天天走亲访友,不是这个招饮,就是那个聚会。对于郁达夫来说,此次婚姻大事的谈判,已经画上了一个句号,结果就是“婉辞婚”。然而,到了8月9日,正当郁达夫“……接莫干山潘氏书,系召予等往游者。明日欲赴招,不识亦来得及否也……”的当天晚上,“薄暮陈某来,交予密信一封,孙潜手书也,文字清简已压倒前清老秀才矣”。可惜的是因这封密信早已佚失,里面的文字已永远不能呈现,但笔者还是竭力想打探出其中的内容。在与陆费澄女士多次交流后,这封信的内容逐渐有了大致的轮廓。
原来,自郁达夫长子天民先生被打成“右派”发回原籍富阳工作后,陆女士一家就与孙荃夫人一直住在一起,直到孙老太太1978年离世。天民先生是个孝子,每天晚上总要抽出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陪母亲闲话,陆费澄也常常陪侍在旁。他们谈论的话题绕来绕去,常常就会绕到郁达夫与孙荃的婚姻中去,特别是有一段时期天民先生(笔名于听)正着手编辑《郁达夫诗词抄》,就更加有目的地请母亲回忆起这段往事。和每个上了年纪的人一样,孙荃夫人也愿意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候的一些往事,虽然她嫁给郁达夫后得到的苦难与幸福不成比例,但她却每每以达夫夫人而自豪。(16) 据她讲述,郁达夫“婉拒”的并不是这段双方家长期望的婚姻,而是双方家长让他们尽早完婚的提议。“婉拒”的最主要原因,就是郁达夫学业未成,无经济力量去负担家庭用度,所以请孙家是否能将婚期推迟一些。当这些信息通过媒人陈凤标传到孙家后,孙孝贞表示这事还得征求孙荃的意见,于是孙荃直接写了这封密信交陈凤标转达,信中孙荃善解人意地表示:好男儿当以学业为重,所以我尊重你的意见,但能否先订婚,也可以在父母、乡亲面前有个交待?
对于孙荃而言,这其实是个没办法的折中选择。但她在信中表现了一个大家闺秀的优良传统美德,再加上“压倒前清老秀才”的文采(笔者一点都不怀疑这封信是经过了长兄的润色),郁达夫应该是动心了。
郁达夫的动心,或者说已从思想上接受了孙荃的建议,在日记上并无表示,因为他即将开始莫干山之旅。可是从第三天(8月11日)起,他就开始了致孙荃的第一封长信《云里一鳞》的创作。在长信前的跋文中,他写道:
八月九日某以书来谒。予东行在即,欲作答苦无时,不答则又不足以报垂顾之盛意,于是每日于月落参横际,割一小时,依枕疾书,将所欲言者尽笔之于书,使闺中弱女子,亦得知二十世纪之气风若何。盲行,需求助于相,否则亦必待行杖之扶。予虽无相者之指挥术,或者亦能代行杖之支助乎。
这篇跋文还是有些用词遣句能引起注意。首先是称谓,在此信中,并未称孙荃为“未婚妻”,说明郁达夫还未与孙荃达成先订婚的协定(在郁达夫与孙荃会面后,所有往来书信及日记当中的称谓就有了变化——笔者注);其次是“垂顾之盛意”,反映出在“密信”中孙荃是言明了对郁达夫的接受(当然也包括了对暂不结婚的理解),也证明了孙荃当年与其子天民先生的谈话可信度较高;其三,“使闺中弱女子,亦得知二十世纪之气风若何”句,更可窥一斑而知全豹:郁达夫对孙荃是欣赏有加,准备慢慢培养以减小与自己“东洋留学生”的差距了。
笔者从郁达夫1917年的日记本中还发现一个易被忽略的问题,就是在8月11日日记的上方页眉处,有达公手迹的毛笔“孙荃”二字,而下方则是当日日记:“晨起作云里一鳞寄孙氏,明日当有莫干山之行……”这就提供了一个郁达夫给孙兰坡赠名的确切时间:8月11日前后,而非旧体诗《赠名》的创作时间10月16日。这一点,在后文引用的郁达夫致孙荃信中也可映证,如1917年9月5日致孙荃信中落款就为:
孙荃女史
达公初稿
郁达夫于1917年9月2日动身离开富阳赴日本,在此之前的五六天没有写日记,但在此页的眉批上却有一段细小的字详细记录了他与孙荃初见时的情景:
临行前陈某以未婚妻某所作书信来谒,翌日即乘舆至未婚妻家。时因作纸忙,伊父母皆在贝山寺。未婚妻某因出接予于中厅,晚复陪予饮。时乃旧历七月十一日(8月28日——笔者注)也。膳毕,予宿东厢。因月明,故踏月出访陈某,陈某出未归也。田中稻方割尽,一望空阔,到处只见干洁之泥田及短长之稻脚,清新畅达。大有欲终老是乡之意。翌日岳父归,与偕赴柳坞听戏,夜遇雨,归已迟……
很明显,这一段是日后补记,而且补记的时间应该是在9月3日之后(因为8月27日与9月3日之间并无空隙——笔者注)。请注意,这是郁达夫首次称孙荃为“未婚妻”,也就是说,在补记这段日记的时候,郁达夫与孙荃已经完成了订婚过程。除了称谓的变化,这段文字还显示,他们俩的见面结果,郁达夫是满意的,因为“大有欲终老是乡之意”,而且郁达夫在1918年4月27日致长兄郁华信中明言:“文来日本前一日,曾乘舆至宵井,与未婚妻某相见,荆钗布裙貌颇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处。”孙荃是满意的,因为“晚复陪予饮”;孙孝贞是满意的,因为“与偕赴柳坞听戏”。至此,这段曾经走入过死胡同的婚姻终于有了一个各方面都满意的结果,那就是:1917年8月29日到9月1日间,郁达夫与孙荃正式订婚,他们俩的命运也从此捆绑在了一起。
五、书信
如果把《云里一鳞》算作郁达夫与孙荃通信的开始,那么在1917年8月11日至12月30日,郁达夫共有信八通、明信片二通致孙荃,兹先将各信时间录之如下:
一、信件:
1.1917年8月11日《云里一鳞》;
2.1917年9月5日《奉赠》;
3.1917年9月22-23日;
4.1917年10月2日;
5.1917年10月10日;
6.1917年10月18日;
7.1917年10月25日;
8.1917年10月28日。
二、明信片:
1、1917年12月30日
2、1917年12月31日
到目前为止,上述信件中有两通已全文发表(17),分别是第一通《云里一鳞》、第五通(10月10日信);第二通《奉赠》的内容只有四首诗,亦可算作全文已发表。经过笔者与书信保存者的沟通与交流,现征得同意,将断篇已收入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郁达夫全集》(第6卷)的第三通(9月22-23日)、第六通(10月18日)以及两通明信片全文发表如下:
第三通信(1917年9月22-23日):
久欲与汝通信,然到名古屋后,未尝有一刻暇,迟延至今,亦势有所不得已也。在杭州时曾托邦钧太带上诗若干首,欲附一书,天苦热不能执笔,到上海后日日与关绪探访旧迹,又无暇作书。今日午后有客来谈家事,客去后,西风飒飒,吹人衣带。举头见新月如眉,斜挂于碧天云影中,蟋蟀一鸣,万籁俱寂,西望故园,觉怀乡情切,不能暂耐,俯首凭栏,竟泫然泪落矣。予自去国迄今,五易寒暑,其中得失悲欢事颇多:祖母病报至不泣;姪儿死耗至不泣;去年因微事与曼兄争,曼兄绝交书至亦不泣;今日之泣,尽为汝也,然则汝亦可以自慰矣!
忆来时约各寄书,何以至今,尚未见汝只字?此信到后,无论如何,必须作复。若无言可道,可将汝每日所作(做)事告知,予实颇欲识汝在家时动作也。文不论通否,必须己出,前次关绪带来书一封,虽系汝手笔,然语气不合,当是汝兄草稿。此后无论如何,不可使人代作,若辞不能达意时,只可问一句二句,不可通篇求人改削也。予每日作“起居注”,汝亦可效此。每日作日记若干行,若是则每日思想言行,俱残留于纸上,他是临风读之,兴味当不浅也。今日日记一则,即录于下,汝此后若记日记,但依此格式记录可矣:
廿一日,早起觉头昏不可耐,昨夜因齿痛不能安睡故也。七时上学,校中虚无人,庭前黄雀呀呀鸣不已,若辈殆将有事于工作矣。午后之时退学、返舍,热甚。脱衣后客来谈家事,未几关绪亦来教日文毕,客亦去。予乃赴浴室,澡毕,凭栏独坐良久。新月一弯,照人孤宿,予之悲叹,乃至无地,即起而作书与孙某,书毕而人亦疲矣。
书止此,余待他日。
达公白
阳历九月二十二日
若有兴作诗可将下列各题做来:
秋闺 落叶 山家秋色 红叶 对月 慵绣咏菊
灯下闻鸣虫 杂感 题岁寒三友图(松竹梅)
文题:
写秋收后田间之光景
月夜独坐时之思想
说松竹梅
送侄儿东游序
予寓舍为“日本名古屋市外御器所村广见ヶ池字念佛七五、山田方”,若有信来,寄至此处可矣,或寄至“日本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亦可。然汝有信时,不若寄至寓舍为妙,恐信到校内,为他人所见也。来书自称妾,固合于礼,然未免太拘,不若自称荃之雅而简也。余过临平时,曾得诗一首,兹录之于左,以供雅览。
文白
九月廿三夜再书
过临平
清溪波动菱花乱,黄叶林疏鸟梦轻。
又是一番秋气味,稻香风里过临平。
第六通信(1917年10月18日):
阳历十月十五日,接汝阴历八月二十日所发书,是日予病热,头昏目眩,不能执笔,是以不即答。夜汝姪来,谈至二更,觉病势稍减,然犹不能起坐也。翌晨起床,病体已安,头昏痛如故,勉强更衣,怀书入学,头痛更不能支。及晚归,欲作答,因胸前微痛,遂不果。今晨起,诸病尽去,予乃得偷数刻闲(今日为日本祭日学校放假),与汝作别后谈。
弟兄争攘事,本世间愚人之所为。予与胞兄某均达理之人,决不至此,请勿念。二人不通信虽及半年……(此处省略若干字,主要是写与胞兄之关系,应保存者之要求略去——笔者注)但东来后,两人已照常通信,前言尽作戏观,兄弟间已无复有少许怨限矣。
祖母欲见汝,自是老人望后辈之心。汝若赴杭,道经富阳,不妨暂至家中一坐,使祖母一见,安伊老后之心。若不赴杭,亦不必特地来富阳。不使祖母见,亦不妨事也。农人习俗,每喜谈人家琐事,予最恨之。汝若畏彼辈流言者,不去富阳见祖母可也,区区一事,想祖母亦不至含怨,去见与不去见,汝其自定之。近因身体有不安,文思大减,诗久不作矣。前信(第二信)(18) 中附有唐诗选一张,今日本拟续选一张寄上,因头脑尚昏,恐有滥选,故置之。汝姪身体颇好,用钱亦尚有节制,汝母前乞以客居安泰告知。
予以(已)决计入文科。功名富贵,将来或居人物,然予之华显,非数百年后不见也。
汝弟尚幼,将来如何,原不能预料。然积善之家,庆必有余。汝家世诚朴,想老天定能默佑之,可勿为虑也。
客居孤寂,最欲得故乡书,针线余暇,还乞时赐手札,当远胜砧声千叠也。
一号信中曾嘱汝作日记,未识亦曾作过否?若有闲日,不妨将此等日记抄出寄来,若然则予仍能得与汝同居之乐矣。
文手书 呈
荃君座右
阳十月十七日
今日犹有病意,故字迹不请,乞谅之。所谓病,毫无妨于大事者也,可勿念。
第一通明信片:
中华民国浙江富阳县西门外裕号米栈转宵井庙孙汇泰交
孙荃君 收
日本名古屋御器所村龟口八七、郁文
除夕(1917年12月31日)
除夜奉怀
又是一年将尽夜,不知青鬓几痕丝。
人来海外名方贱,梦返江南岁已迟。
多病所须唯药物,此生难了是相思。
明朝欲向空山遁,为恐东皇笑我痴。
海外流人荫生初稿
第二通明信片:
中华民国浙江富阳西门外裕号米栈转宵井下台门 孙汇泰号
孙荃君 收
日本名古屋八高郁文寄
阳十二月三十日
昨自东京归,接十二月六号书并写真一,知汝已至予家,祖母见汝,欣喜当异于寻常。老人暮景,得汝为之抚慰。文虽索居异国,亦能高枕眠矣。汝侄事,已为料理定当,告汝母汝兄,勿作依阁望可也。病已愈,唯入夜时有热症,想静养数月,当能复原也,勿念。此番上东京,途中成诗若干首,录呈如右:
晨发名古屋
茅店荒鸡野寺钟,朔风严冷逼穷冬。
骑驴独上长街去,踏破晨霜一寸浓。
朔风吹雁雪初晴,又向江湖浪里行。
一曲阳关人隔世,衔杯无语看山明。
过天龙川桥
一种秋容不可描,夕阳江岸草萧萧。
十年湖海题诗客,依旧青衫过此桥。
奉寄
赠君名号报君知,两字兰坡出楚词。
别有伤心深意在,离人芳草最相思。
文近欲迁居,有信乞寄至八高可矣!
六、结语
在引言部分已经说过,本文只不过从现有史料入手,对郁达夫与孙荃1917年的情感历程作了初步的整理,离系统性和完整性都有很大的距离。并且在写作过程中,笔者尽量不加主观性的评论,为的就是从客观公正的角度出发,重依据、重逻辑推理、重第一手资料,少猜想,让广大的郁达夫研究者与爱好者从史实出发作出自己的判断。但笔者还是不得不说,郁达夫与孙荃的1917年,其实还有很多值得“说”的地方。比如说达夫与胞兄曼陀的关系,如此隐秘的家庭私事甚至于连书信保存者都不愿意公之于众,而郁达夫什么都愿意与孙荃坦白,这说明了什么?再比如说在郁、孙订婚后,郁达夫的日记里还有不少关于未婚妻的记录,其中有不少的篇幅对于研究作家的整体特别是他早期的感情历程、爱情观等等应该大有裨益,但限于篇幅和整理时间的仓促,只能留待今后再加以充实和补足。
笔者将上述文字整理出来的时候,有两个特别突出的感受:其一,郁达夫与孙荃的婚姻到底能不能定性为传统的包办婚姻,恐怕在这批史料问世后学术界可能会产生新的争论。包括郁老太太陆氏在这桩婚姻里的态度与作用、郁达夫个人对这桩婚姻的看法与做法、孙荃个人在这桩婚姻中所起的主动性作用等等。其二,从正式订婚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郁达夫与孙荃的通信就有十封之多(还不算多达十数首的诗词唱和),而且书信中并不缺乏作家对未婚妻情深意切的关照与谆谆眷恋之语(“祖母病报至不泣,姪儿死耗至不泣;去年因微事与曼兄争,曼兄绝交书至亦不泣;今日之泣,尽为汝也,然则汝亦可以自慰矣!”),甚至有些时候让人感觉到是郁达夫手把手地教导孙荃,想的就是尽力提高未婚妻各方面的素养,以达到夫唱妇随、举案齐眉的结果。这样的婚姻,不正是任何男性所追求的目标吗?
事实上,笔者在写作时并没有一定的倾向性,只是想让这些史料尽量客观地呈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面前,希望能对郁达夫研究有所贡献。如果这些材料能引起广大郁达夫研究者重新审视这一段特殊的婚姻,予愿足矣。
注释:
① 转引自郭文友:《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9页
② 郁达夫:《致王映霞》(1927年3月4日),《郁达夫文集》第9卷,第351页。
③ 王映霞:《我与郁达夫》,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页。
④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
⑤ 指祖母、母亲自己、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及使女翠花。
⑥ 郁达夫:《悲剧的出生——自传之一》,《郁达夫全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0页。
⑦ 蒋增福:《郁达夫家族及其女性》,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149页。
⑧ 参见拙著:《郁达夫故居》,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⑨ 见郁达夫致孙荃信第三通(1917年9月23日)。
⑩ 该信现存富阳郁氏后裔处,主要内容为郁达夫向孙伊清传达树祺近况。
(11) 直到现在,宵井村上了年纪的老人还口口声声称树祺为“关绪老爷”。
(12) 郁达夫1917年日记中多次提及因转科事与长兄曼陀反目,甚至在致孙荃信中也用一定篇幅讲述,几次“几欲自杀”,可见郁曼陀在郁达夫心中地位。因与本文关系不大,故略去。
(13)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第121—124页。
(14) 郁达夫1917年6月20日日记,现存富阳郁氏后裔处。
(15) 同上,引自郁达夫1917年7月23、24日日记。
(16) 现存郁达夫后裔处的早年书信,大都由孙荃珍藏,在经历了抗日烽火、解放战争硝烟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后仍能完好无损,不能不说这批书信在孙荃心目中的分量是极重极重的。
(17) 郁达夫:《致孙荃》,《郁达夫全集》第6卷,第17—25页。
(18) 郁达夫自己也将1917年致孙荃信进行了排序,共排6封,分别标在日记本或信纸上。分别是第三、四、五、六、七、八通。
标签:郁达夫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