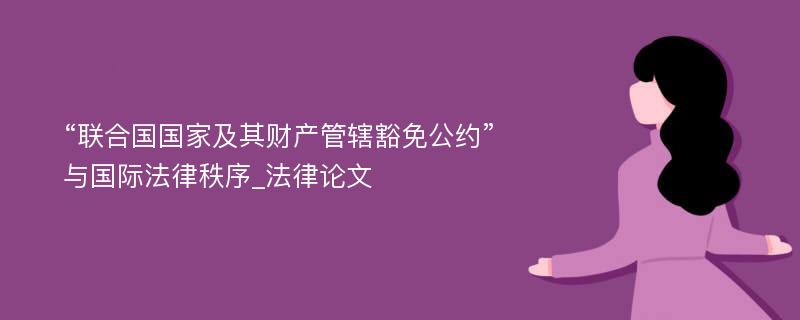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与国际法律秩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合国论文,公约论文,秩序论文,财产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69X(2006)06—0117—04
经过22年的努力,《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以下简称国家豁免公约)终于在2004年12月16日的第59届联合国大会上获得一致通过[1]。 这意味着在国内法院的民事诉讼中坚持限制外国国家豁免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种共识。
从法律社会学的观点来说,限制豁免理论的发展归因于经济领域中的国家活动的不断增加,私人企业不仅要同本国国家打交道,并且在更广泛的范围里还要同外国国家打交道,因此需要对它们提供法律保护[2]。限制豁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限制国家(外国)的公权力,维护个人的私权利,这也是民商事法律关系中平等原则以及人权保护的需要。然而,国家豁免问题更关系到国家的主权利益,国家享有司法管辖豁免权是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因此,国家豁免公约的出台将对现代国际法律秩序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从国家主权的角度审视公约
由于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持限制豁免立场,所以豁免公约总体上是对发达国家立法与司法实践的一种肯定。然而,对其他一些国家来说,国家豁免公约无疑会给他们带来一种新的概念。近年来,欧洲和拉美一些民法法系国家在有关国家豁免问题的实践方面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而一些正处于经济、政治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持绝对豁免立场[3]。对于这些国家来说, 国家豁免公约为他们提供了一项新的国际法规则。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有关国家豁免的国内立法受到了相关国家政府和民众的一致欢迎。政府发现,豁免立法有效地缓解了法院在处理涉及国家豁免问题的案件时所面临的外交方面的压力。而由于国家豁免立法在有关货物销售、服务贸易、贷款及其他金融性质的交易的诉讼中限制外国援引国家豁免,因此,也得到了国内经济界人士的拥护。跟这些国内立法一样,国家豁免公约原则上允许自然人或法人就有关合同、贷款等问题对外国国家提起诉讼,这将对现有习惯国际法规则产生一定的影响。
国家豁免公约第五条重申了“国家及其财产在另一国法院享有管辖豁免”的一般原则,这表明公约仍然确认国家在“国内法律体系中”扮演着首要角色。但是第五条同时也规定国家享有的豁免权必须“遵照公约的规定”;公约第十至十七条还规定了八种国家豁免的例外情形;公约授权国内法院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对国家“具体用于或意图用于政府非商业性用途以外目的”的财产采取强制措施。这表明公约在强调国家在“国内法律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的同时,在有关商业交易、合同等领域又把国家置于与自然人和法人同等的法律地位。特别是公约关于诉讼文书的送达、时效、缺席判决、举证等程序性规则,虽然没有对作为被告的外国国家规定强制性的举证责任,也没有规定罚款或刑罚等法律后果,但是公约并不妨碍一国的国内法院作出与外国国家拒绝提供的证据意思相反的结论。
一些缔约国必然会对公约中与“国家主权”相冲突的某些规则提出保留。然而,在一个没有统一监督机构可以强制执行公约的国际社会里,公约能否得到有效实施,取决于缔约国对公约各重要条款的接纳与贯彻。这是缔约国在对公约条款提出保留时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
二、关于公约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公约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将给公约的实施带来不利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允许法院地国通过国内法对“商业交易”任意下定义,从而可能导致主要豁免例外范围的无序扩大;二是公约在国内法院管辖权方面缺乏统一的原则,从而影响公约在国内法院的有效实施。
(一)商业交易的定义问题
商业交易是规定在公约第十条的最重要的一种不得援引国家豁免的情形。公约第二条第2款第(3)项为“商业交易”作了界定之后,第3项紧接着澄清:本公约“不妨碍其他国际文书或任何国家的国内法对这些用语的使用或给予的含义”。这一规定显然是各国之间存在着广泛不同观点的一种折衷方案。不过,第2 款所界定的“商业交易”已经囊括了货物销售、提供服务、贷款及其他金融性质之交易、担保以及商业、工业、贸易或专业性质的任何其他合同或交易等广泛领域,因此,缔约国想要另外给商业交易重新下意义,应该也难以超出公约所规定的范围。
在“商业交易”的判断依据方面,国家豁免公约采取了以性质依据为主,兼顾目的依据的折衷方案。之所以说是“兼顾”目的依据,是因为公约第二条第2款对使用目的依据作了一些限制:要求合同或交易的当事方达成一致,或法院地国在司法实践中有考虑目的依据的惯例,才可以适用目的依据。由于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理论和实践上一贯主张性质依据,排斥目的依据[4],因此,第2款的规定意味着这些国家仍然可以只适用性质依据而不必考虑目的依据。而对于那些向来主张目的依据的国家来说,则不得不改变其原有立场。
(二)有关不得援引国家豁免的案件的管辖规则问题
公约第三部分(第十条至第十七条)是关于国家豁免例外的规定。在这一部分所述的八类诉讼中,被告国在某些情况下不得援引国家豁免,即法院地国的法院对案件有管辖权。然而,公约对于法院地国法院管辖权问题的规定比较零散,缺乏一个总的原则,而且有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例如,对“商业交易”问题,公约规定法院地国法院的管辖权应该根据该国的“国际私法适用的规则”来确定;而对“雇用合同”以及“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问题,公约则设置了非常严格而详尽的管辖条件。又如公约第十一条第2款规定,如果雇用国“招聘雇员是为了履行行使政府权力方面的特定职能”,则可以援引国家豁免。至于何谓“履行行使政府权力方面的特定职能”,公约没有作明确规定,这给国内法院确定管辖权带来一定的困难。而公约对法院地国法院管辖权规定的零散性,将影响法院对案件的有效管辖。这一点也遭到许多学者特别是国际人权运动人士的批评。他们认为,在国内法院对外国国家提起诉讼是自然人或法人获得救济的最有效途径,如果法院不能行使管辖权而给予外国豁免,则意味着不保护人权[5]。
其实,管辖与豁免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正如国际法院在“逮捕证”案中所指出的“必须把国内法院的管辖规则与管辖豁免规则区别开来:管辖并不必然意味着拒绝豁免,反过来,拒绝豁免也并不必然意味着管辖。”[6] 希金斯、伯根索等法官在有关该案的个别意见中也表示:“豁免并不是国际法上一独立的概念……“豁免”与“管辖”是密不可分的。”[7] 豁免公约也体现了这个观点,即法院地国对案件的管辖权与豁免范围的确定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根据公约的规定,无论是确定法院的管辖权还是被告国的豁免权都必须要考虑管辖基础的性质、被告国行为的性质以及被告国的主权地位等因素。
当然,与国际社会在个人国际犯罪管辖权方面具有广泛一致的意见不同,在民商事管辖权方面,各国的步调还很难统一。国际法委员会特别报告员Ogiso也不得不承认,由于不同法律体系之间的民商事管辖规则各不相同,导致公约缺乏总的管辖原则是在所难免的[8]。
总体管辖原则的缺失将会增加公约在缔约国法院适用的复杂性。但是公约毕竟在统一各国在国家豁免问题上的立法与实践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只要缔约国法院在实践中遵循“在充分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维护自然人及法人的利益”这一原则,公约的各项规则和制度还是能够得到有效实施的。
三、公约对国际法律秩序的促进作用
公约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对国家豁免原则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长期以来,“国家主权豁免”被认为带有一定的任意性质,一些国家于是随意确定国家豁免的范围。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在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出台以前,美国法院一般是根据行政部门(国务院)的意见来决定给予或拒绝外国国家的豁免权[9],往往把“国家豁免”作为推行外交政策的工具。美国学者开普兰就认为:“国家豁免只不过是法院地国给予外国国家的一种优惠或特权”,他把国家豁免定义为“法院地国为了促进国家间友好关系而放弃对外国进行司法管辖。”[10] 这意味着国家在给予外国主权豁免的问题上可以任意取舍。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虽然对豁免的范围有所界定,但美国法院仍然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例如《外国主权豁免法》第1605条第1款(b)项规定,外国在美国领土以外进行商业活动,只要对美国造成了“直接影响”,美国法院就有管辖权。对于何谓“直接影响”,该法没有明确规定,留作法院自由裁量。
近年来,美国等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进一步扩大国内法院对外国的司法管辖权,缩小国家豁免范围的趋势。例如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第1605条第1款(e)项规定,外国的侵权行为在美国境内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时,美国法院对此有管辖权。即法院管辖的前提是损害结果发生在美国境内。然而,美国1996年《反恐怖活动和有效死刑法案》以反恐需要为由对《外国主权豁免法》的上述条款进行了修正,使美国法院对行为和结果都发生在美国领土以外的诸如伊朗、叙利亚等所谓“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的侵权行为也具有管辖权。这一修正案可以说把美国法院对外国政府的司法管辖权扩大到了极限。正如美国学者锡林所指出的:“……(修正案授权)美国法院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候对任何外国行使国内司法管辖权。这显然是美国凭借其‘超级霸权’地位作出的不合逻辑的规定……。”[11]
欧洲人权法院在近年来审理的一些案例中也主张应该进一步限制国家豁免的范围,认为法院地国的法院可以对外国在法院地国领土外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行使管辖权[12]。
这种不断限制外国国家豁免、扩大国内法院对外国政府的管辖范围的做法如果超过一定的限度,必然会侵犯到他国的主权,从而引起国家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作为对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修正案把伊朗列入管辖范围的报复,伊朗就针锋相对地通过了一项立法,允许伊朗国民在国内法院起诉美国的“侵略”行为[13]。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出台将结束各国在国家豁免问题上各自为政的局面。公约肯定了国家豁免是一项国际法规则,而不仅仅是法院地国出于国际礼让给予外国的特权。公约在绪言中郑重申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是一项普遍接受的习惯国际法原则”,并强调“习惯国际法规则仍然适用于公约没有规定的事项。”无论对缔约国还是非缔约国来说,公约明确和巩固了国家豁免作为国际习惯法原则的法律地位,对国内立法和司法实践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国家豁免是现阶段国际法发展过程中一项不可或缺的法律原则。国家豁免原则在维护国家主权与保护自然人和法人利益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在“豁免”与“不豁免”的关系问题上,公约肯定了“豁免”是原则,“不豁免”是例外。而且,公约对所列的八种豁免例外规定了比较严格的适用条件。例如对于有关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的案件,美、英等国的国内立法规定,只要外国侵权行为或损害结果发生在法院地国,法院地国的法院就对案件具有管辖权[14],而国家豁免公约第十二条不但要求外国的侵权行为发生在法院地国领土内,而且要求侵权行为人在侵权行为发生时也必须处于法院地国领土内。又如在有关雇用合同的诉讼方面,1972年《欧洲国家豁免公约》和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立法都没有特别强调维护雇用国在行使任命或不任命某人担任某一官方职位方面的自主权,而联合国国家豁免公约第十一条则明确规定,当“诉讼事由涉及个人的招聘、雇用期的延长或复职”时,雇用国可以保留豁免权。
联合国国家豁免公约在注重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也强调保护自然人或法人的利益。正如公约绪言中指出的:“公约将加强法治和法律的确定性,特别是在国家与自然人或法人的交易方面。”当今世界全球化日益盛行,国家与外国自然人或法人在经贸、财产、服务、金融等各领域交往越来越密切,如果作为当事一方的国家仍然一味强调其主权地位,而忽视“在民商事法律关系中各当事方地位一律平等”这一重要原则,必然会损害作为当事另一方的自然人或法人的利益,从而使民商事交往无法正常进行。联合国国家豁免公约正是适应这一要求,首次以公约的形式确立了国家与外国自然人或法人在发生商业交易、雇用合同和侵权关系等交往过程中各自的地位,以及国家在处理财产、工业和知识产权、参加集体机构、国有船舶等问题上的民事法律地位。这对于促进世界范围内的经贸发展和民商事交往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6—10—02
注释:
① 国际法委员会经过12年的起草工作,于1991年二读通过了《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条款草案》;后来联大第六委员会又花了10年时间对条款草案进行讨论修改,最终形成了公约的草案。
② See Singer,Michael:Abandoning Restrictive Sovereign Immunity:An Analysis in Terms of Jurisdiction to Prescribe,in: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Volume 26,1985,p.16.
③ See David P.Stewart:Current Development of Jurisdictional Immunities of States and Their Property,in: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January,2005,p.196.
④ See UN Doc.A/C.55/L.12,1998,p.12.
⑤ See Christopher Keith Hall:UN Convention on State Immunity:The Need for a Human Rights Protocol,in: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vol.55,April 2006 p.422.
⑥ Se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Reports,2002,para 39.
⑦ Ibid Joint separate opinion para3.
⑧ Se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1988,II,pt1,p.109.
⑨ 参见陈纯一.国家豁免问题之研究——兼论美国的立场与实践[M].台北:三民书局,2000.125—129.
⑩ Se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97,2003,pp.741—755.
(11) See 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vol.38,2003,pp.103—105.
(12) See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vol.123,2003,pp.24,para 56.
(13) Se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97,2003,p.968.
(14) 见美国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第1605条第1款第(5)项、英国1978年《国家豁免法》第5条、澳大利亚1985年《外国国家豁免法》第13条等。
标签:法律论文; 美国法院论文; 国际法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国家主权豁免论文; 民事诉讼管辖论文; 商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