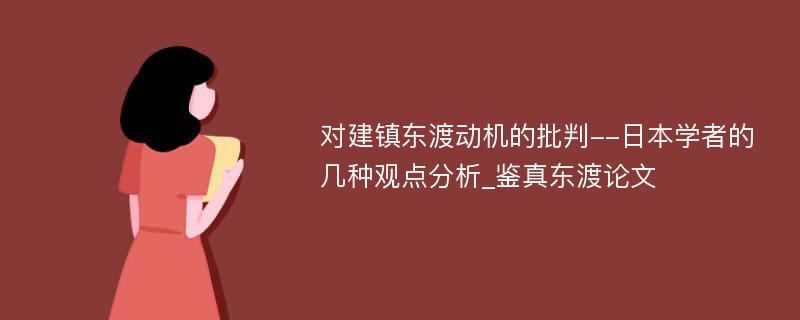
鉴真东渡动机诸说批判——剖析日本学者的几种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种论文,日本论文,动机论文,学者论文,观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 242;B 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09)04-0043-06
一、引言
8世纪中叶,扬州僧侣鉴真携徒先后六次东渡,最终于天宝十二载(753)突破“地狱之门”①到达日本。在前后约12年间,支撑他们完成这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艰苦旅行的,无疑是一种坚定的信念。但这一代价也极为惨烈,《唐大和上东征传》这样描述:
大和上从天宝二载,始为传戒,五度装束,渡海艰辛。虽被漂回,本愿不退。至第六度过日本。三十六人总无常去,退心道俗二百余人。唯有大和上、学问僧普照、天台僧思托,始终六度,经逾十二年,遂果本愿,来传圣戒。[1]
如果仔细品味上述记载,可以发现鉴真东渡非同寻常。当初(742年)荣睿等从长安南下扬州,面谒鉴真发出邀请时,众弟子竟无一回应,此已隐约显露“异常”之端倪;②一旦开始渡海,先后有36人失去宝贵生命,最终到达日本只有24人,死亡率之高,令人惊诧;更为令人惊讶的是,航海过程中有200多人打退堂鼓(思托撰《延历僧录·普照传》,记载“退心二百八十余”),意味着在鉴真的东渡活动中,高达90%以上的人中途退出。即使仅从上述几点来看,鉴真对东渡之“异常”执著,不可以常人常理来论之。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鉴真产生如此坚定的信念,不屈服于任何自然威胁和人为阻碍,最后成就东渡日本壮举的呢?关于鉴真东渡日本的动机,小野胜年是较早予以关注的日本学者,他着眼于鉴真在唐的地位,对鉴真不顾危险,选择各种冒险的方法东渡的原因,作出如下几种推测:
第一,鉴真被日本留学僧荣睿和普照充满激情的游说所感动,又因后辈道璿已先期应邀赴日而深受鼓舞。此外,荣睿背后有政界权贵舍人亲王和佛教长老元兴寺隆尊的支持,也令鉴真对赴日传教满怀期待。
第二,日本著名政治家圣德太子不遗余力地在日本兴隆佛法,并努力推动实现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这种精神历经百年而生生不息,因此深深打动了鉴真。论述圣德太子与鉴真东渡的结合点,主要依据的是《唐大和上东征传》所载荣睿与鉴真的对话(涉及圣德太子“二百年后,圣教兴于日本”的预言)。
第三,对鉴真来说,当时的日本乃律宗尚未普及之地,具有传戒授律的巨大空间。此外,在长期同甘共苦的渡航过程中,通过身边的日本僧侣加深了对日本的了解,这也是鉴真锲而不舍坚持初衷的原因之一。其中“对日本的了解”,就是遣唐使以及留学僧带来的日本各地造寺建塔安置《金光明经》、京师造卢舍那大佛等圣武天皇的政治活动和宗教政策等消息。
第四,小野先生也注意到中国国内的情势,指出当时处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将要发生巨变——即“安史之乱”的前夜,鉴真东渡可以说是与“旧世界”即祖国诀别,为开创“新世界”而远赴日本。[2]
关于小野先生提示的上述几个答案,即道璿先行赴日对鉴真产生了多大影响?鉴真是否看重舍人亲王和隆尊的存在?鉴真“对日本的了解”究竟有多深刻?鉴真是否真的与“旧世界”诀别而离弃祖国?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从客观上进行分析论考,不能仅仅停留于主观臆说之上。
二、“留学僧怂恿说”
鉴真曾经被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充满热忱的邀请所感动,这是毋容置疑的,否则他不会在弟子们沉默不语的时刻,自告奋勇答应东渡弘法;而且鉴真对荣睿的死“哀恸悲切”,也证明他们感情颇深。但上述感情与鉴真东渡动机,或许有某些关联,但不可等同视之。
实际上,鉴真随从中退却的200多人,也包括几名日本僧人在内。第一次东渡时有日本僧人玄朗、玄法、普照、荣睿4人相随,因遭高丽国(疑为渤海国)僧如海诬告,第一次东渡出海前即受阻,玄朗和玄法随即脱离团队,此后去向不明。剩下两人虽然继续跟随鉴真,但荣睿在第五次航行中不幸去世,最后一位普照打消回国念头,离开鉴真独自去了明州(今浙江宁波)。因此,在鉴真决定第六次东渡时,他身边已经没有一名日本僧人相随了。
假设10年前,鉴真为荣睿等的恳请所感动,因此决定东渡的话,那么第二次东渡时已有半数日本僧人退出,鉴真的赴日热情多少会冷却下来;第五次航行中,担任聘师使命的主要人物荣睿去世,鉴真东渡日本的热情也许会更加低落;当最后一名日本僧普照也脱离团队时,鉴真的热情应该完全消失了。因此,留学僧的热情支撑鉴真东渡的说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与此相关,部分学者认为,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南下扬州,特意到延光寺恳请鉴真东渡,是为鉴真决定第六次东渡的直接原因。这一观点看似有一定道理,但如果细心阅读《唐大和上东征传》的后续记载,便不会囫囵吞枣地予以全盘接受。
天宝十载(751),鉴真一行从漂流地海南岛,迂回曲折,历经艰辛,回到扬州。翌年(752)遣唐使一行至明州,在阿育王寺与日本僧普照会面,似乎了解到鉴真东渡之事。天宝十二载(753)完成使命的大使一行从长安南下,至扬州延光寺拜访鉴真,劝说鉴真东渡日本。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藤原清河先通报公开聘请失败的消息,然后予以邀请:
弟子等先录大和上尊名,并持律弟子五僧,已奏闻主上,向日本传戒。主上要令将道士去。日本君王先不崇道士法,便奏留春桃原等四人,令住学道士法。为此,大和上各亦奏退。愿大和上自作方便,弟子等自有载国信物船四舶,行装具足,去亦无难。[1]
虽然这种邀请模棱两可、含糊其辞,但鉴真决意第六次东渡。再次东渡的消息很快传开,当鉴真从延光寺返回到龙兴寺,发觉官府已经加强戒备。后来幸得信徒帮助,他才得以从龙兴寺脱身,赶赴苏州黄泗浦,欲搭乘在那里候风待发的遣唐使船。如果认为事遂人愿,中日合作将功德圆满,那就错了。事实上,鉴真赴日的路途并非一帆风顺。在由4艘船组成的遣唐使船队即将出航之前,大使藤原清河突然把各船的负责人召集起来,召开紧急会议,通报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
方今广陵郡觉知和上向日本国,将欲搜舟。若被搜得,为使有殃。又风被漂还著唐界,不免罪恶。[1]
这大概是遣唐大使惧怕承担连带责任,因而违背此前在扬州延光寺对鉴真许下的诺言。于是,谢绝弟子们的恳切挽留、不顾同门的屡屡反对、打破国禁偷渡出海的鉴真一行,不得不离开已经分乘的各船,他们自断后路而又失前途,其沮丧无助之状可以想象。
遣唐副使大伴古麻吕见此情状,实在于心不忍,遂私自把鉴真一行收容到自己的船上。因此,鉴真的东渡无论是对唐政府来说,还是对遣唐使来说,都属于密航偷渡。如果仅仅是日本方面的恳请诚聘支撑鉴真东渡的话,那么鉴真大概就此放弃赴日。但即使被日本遣唐使抛弃,鉴真也没有放弃东渡。因此支撑这一决心的因素,必须从遣唐使和留学僧之外来寻找。
三、“圣德太子敬慕说”
既然“留学僧怂恿说”缺乏说服力,让我们来剖析小野胜年提到的第二种可能,即以荣睿与鉴真的对话为依据,认为鉴真对圣德太子怀有的崇敬和景仰,是其不畏艰险东渡弘法的原动力。事实果真如此吗?《唐大和上东征传》中所载荣睿与鉴真的对话如下:
荣睿、普照师至大明寺,顶礼大和上足下,具述本意曰:“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法人。日本国昔有圣德太子曰:‘二百年后,圣教兴于日本。’今钟此运,愿和上东游兴化。”大和上答曰:“昔闻南岳思禅师迁化之后,托生倭国王子,兴隆佛法,济度众生。又闻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来施此国大德众僧。其袈裟缘上绣著四句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以此思量。诚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也。”[1]
荣睿、普照的恳请,包含三个主要内容:(1)日本无传法高僧;(2)圣德太子的预言;(3)恳请鉴真东渡。鉴真的回答中也包含三项内容:(1)慧思的倭国转世传说;(2)长屋王的袈裟偈句;(3)对日本的评价。
福井康顺先生把鉴真的回答视为表明对圣德太子的敬慕,亦即昭示其赴日动机的重要证据,主张鉴真赴日的动机源于把圣德太子视为南岳慧思大师的后身。③福井康顺等提倡的“圣德太子敬慕说”迎合了日本人的心理,因而广为流传。
事实上,把鉴真与圣德太子链接起来,并不是近现代史学家的创见,平安时代的日本天台宗僧侣们,早已开始宣扬倡导。最澄在其所著的《注金刚錍论序》中,明言日本天台宗的创始,与慧思(南岳)、鉴真、圣德太子具有渊源关系:
今斯法性宗,龙猛苗裔,南岳子孙也。性相圆融,理事具足。觉者明师,禅者心镜。伏愿远仰上宫太子,近凭过海和上,建立此宗,报谢彼德。我国佛弟子,谁忘二圣恩者哉?[3]
继承最澄法系的圆仁,于承和十四年(847)自唐归国,他在递呈朝廷的上表文中说,慧思托生的圣德太子派遣隋使从中国取回慧思的遗物《法华经》,并亲自制作“三经义疏”(《法华经》、《维摩经》、《胜鬘经》三种佛经的注疏)宣讲,在日本弘扬大乘佛教;迨及鉴真东渡,天台宗始传日本:
伏寻天台宗传本朝之元始,南岳思大禅师后身圣德王子,以不世之德降生此国,遣使于西邻而取经,自制章疏而讲赞。黎庶于兹,始闻佛法。其后唐鉴真等远慕圣化,将天台法门而来朝。[4]7
最澄、圆仁的上述论说,乃是日本天台宗对鉴真东渡动机作出的阐释,亦即“圣德太子敬慕说”的根源所在。事实上,“圣德太子敬慕说”的唯一依据是荣睿和鉴真二人的对话,只不过鉴真回答中的“倭国王子”,被偷梁换柱成了圣德太子。
《扶桑略记》卷3、敏达天皇六年(577)6月22日条,在记载南岳慧思入寂之后,还有如下的内容:
鉴真和尚云:闻南岳思禅师迁化之后,托生倭国王子,兴隆佛法,济度众生。倭国王子者,圣德太子也。[4]32
文中把“倭国王子”比拟为圣德太子,显然有些牵强。唯一自始至终跟随鉴真东渡的唐僧思托,所著《大唐鉴真传》④在记载荣睿述说圣德太子的预言之后,紧接着用如下一段话来说明日本方面的佛教状况:
又舍人亲王广学内典,兼博览经史,敬爱佛法,慈爱人民。每悕求传戒师僧来至此土。[5]
对鉴真来说,传说中的圣德太子,应该不如同时代的舍人亲王(676~735)更具亲近感。但是笔者以为,与荣睿相见时,鉴真意识中的“倭国王子”,既不是圣德太子也不是舍人亲王,而是赠给中国僧侣千件袈裟的长屋王子,这从鉴真的回答即可清晰明了。
由此来看,荣睿宣扬的圣德太子事迹即使让鉴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甚至加强了鉴真对日本佛教界的憧憬,但决不会是鉴真决意东渡的直接动机。
四、“鉴真间谍说”
如上所述,“圣德太子敬慕说”把鉴真和圣德太子联系在一起,起源于日本天台宗的始祖信仰,并无令人信服的史料根据。福井康顺极力推论此说的背景,多少是为了对抗流行一时的“思托捏造说”,这一点不容忽视。
例如,著名史学家辻善之助在《关于圣德太子为慧思后身说的几点疑问》(载《历史地理》第348号,1929年)一文中,把《唐大和上东征传》中荣睿所说的圣德太子预言,判定为思托的恣意捏造,认为鉴真赴日前根本不知道圣德太子其人其事。也就是说,广为学者引用的鉴真与荣睿的问答,被看作是唐僧思托的伪造。
辻善之助的“思托捏造说”,被一部分门生继承发扬,甚至有人把思托视为撒谎者,进一步成为了衍生“鉴真间谍说”的温床。倡导“鉴真间谍说”的铃木治教授在其著《白村江》中,对“思托捏造说”作了如下评价:
据《东征传》载,圣德太子是中国广东省衡山⑤慧思禅师的转世,而鉴真和尚立志渡海赴日是因为仰慕圣德太子的遗德。但是“转世说”实际上是思托编造出来的,在他以前即8世纪以前,日本并不存在这样的说法。辻善之助博士的研究表明,“转世说”自不用说,《东征传》本身也不足信凭。[6]178~179
《白村江》全书包括序言在内分为15章,虽以描述从663年白村江战败到894年遣唐使废止的231年间的历史为主,但可以说,全书的论述聚焦于把唐朝作为颠覆日本并使之发生动荡的“幕后黑手”这一点上。该书充斥危言耸听、哗众取宠的情节,徒具学术书籍的外表,其实缺乏最基本的学术常识。且以书中涉及鉴真的记述为例,来看看作者倡导的离奇古怪的“新说”。首先,铃木治把《唐大和上东征传》所载荣睿邀请鉴真东渡的事实,从以下三方面予以否定:
(1)如此重大的事情,应该托付给遣唐使才对,一介僧侣不应该有如此权限。
(2)律师道璿和婆罗门僧正已经乘坐完成使命归国的遣唐船赴日,荣睿不可能再次聘请戒师。
(3)如果荣睿被赋予招聘高僧的重任,天平八年入唐后居然十年时间无所作为,到了天宝元年才履行使命,这也不太合情理。[6]181
《东大寺要录》列举的招请戒师的发起人是舍人亲王和高僧隆尊。铃木治认为不管列举多少权贵高僧的名字,日本主动招聘鉴真之类的事情,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从而予以全盘否认。在此基础上,铃木治开始自己独特的推导:“鉴真赴日之目的,无论思托如何隐瞒,明显地出于唐朝政府的指派。”[6]181
既然鉴真是位不速之客,那么唐朝处心积虑派遣他东渡日本,究竟怀有什么居心、肩负何种使命呢?铃木治充分发挥想象力,继续演绎他的故事:
大概唐朝是为了严密监视我国情势,本打算派遣大量的间谍前来作乱。但唐朝到了玄宗治世,由于各地的节度使专横跋扈,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管制趋于松弛,结果造成“藩镇之乱”,安禄山之乱迫在眉睫,实在是没有多余的精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唐朝为了有效监视我国,欲利用佛教控制日本的寺院和僧侣,遂令距遣唐使必经的扬子江河口很近的扬州延光寺的鉴真律师,搭上归国的遣唐船而潜入日本。[6]172
按照铃木治的说法,鉴真是唐朝派出监视日本的间谍。由于此说把以前蓄积的鉴真研究从根本上予以推翻,所以为了使之得以立足,必须对鉴真有关的一切事件进行重新解释。关于唐朝派遣鉴真赴日的契机,铃木治用日本和新罗在唐争夺席次事件⑥予以说明。也就是说,这一事件不仅仅引起了新罗对日本的仇恨,也唤醒了唐朝对日本的戒心。其结果是唐朝扣留了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大使作为人质,同时派遣鉴真等人前往日本刺探情报。
但据《唐大和上东征传》的记载,前后五次渡航失败后,鉴真乘坐大伴古麻吕的第二船偷渡日本;大使藤原清河的第一船至阿儿奈波岛(今冲绳岛)后,才遇逆风漂流到驩州(今越南荣市)。因此,唐朝派遣与鉴真偷渡、藤原清河大使被扣留与第一船到达冲绳等,存在很大的矛盾。换言之,既然是唐朝派遣,鉴真就不必偷渡出海;如果大使藤原清河被唐朝扣留,怎能允许他乘船抵达冲绳岛?
铃木治把这些事实视为“《东征传》设下的圈套”,认为“鉴真赴日出于他自发的愿望与日本方面的招聘,这是思托为了掩盖唐朝的派遣使命而捏造出来的,完全不足信凭”,于是逐一进行反驳。亦即,鉴真12年间六次东渡云云,犹如“白发三千丈”,只能用来哄骗小孩;正因为有唐王朝在背后支撑,虽然第一次航行失败,但第二次就成功了;鉴真从乘坐第一船换乘到第二船,是为了把鉴真送到日本、把藤原大使扣留中国的“谋略”,唐朝甚至把第一船漂流到冲绳岛也计算在内;更有甚者,铃木治把鉴真盲目也视为不可思议的捏造,肩负间谍重任的鉴真以佛教来牵制政治,受到了众人的蔑视,于是通过其弟子思托捏造出“天涯孤独盲目圣僧”的形象,以博得世人的同情。
大略通读一下铃木治的著作,就可以发现,诸如汉文史料的误读、文献的“断章取义”等错误比比皆是,本文限于篇幅不及一一批驳,以上仅介绍了有关鉴真的“新说”而已。顺便提一下,铃木治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美术史专业,修完博士研究生课程后,就职于东京日日新闻社,撰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天理大学的教授。
五、“鉴真亡命说”
小野胜年考察鉴真东渡动机时,也把研究视野扩展到了中国方面。他指出,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将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也就是“安史之乱”的前夜,对已经放弃“旧世界”的鉴真来说,无疑是看到了新世界的光明。
按照小野胜年的推断,人们很可能会误导出以下结论:鉴真已经预见到“安史之乱”将要发生,把逐渐衰败的祖国视为“旧世界”而背弃,要到日本去寻求新生而执著东渡。类似这样的见解,在有关论述鉴真东渡动机的著作和论文中经常可以见到。举例来说,自称凝视鉴真的画像、感受其活生生的呼吸、怀抱深深敬仰之情的丹青高手东山魁夷,曾经颇感疑惑地提问:鉴真作为一名拥有高度文化素养、深受世人尊敬的唐朝高僧,为何要决意赴日?不管经历多么深重的挫折和艰难困苦,仍不改自己的初衷呢?他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给出如下答案:
当时的唐朝社会,鼎盛时期已经过去,社会也呈现出了糜烂及颓废的景况。……以长安、洛阳为首,大小都市极尽繁荣,“一城之人皆若狂”(白居易《牡丹芳》),衰败的景象被享乐和消费的表面风潮所遮掩。但从鉴真和尚的性格来看,这些应该不是唐朝的魅力。不,鉴真对此应当感到绝望。在这个关口,作为新兴佛教国家的日本出面招请鉴真东渡。对他而言,这个邀请无疑预示着开启新生而充满无穷魅力。[7]
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史思明挑起叛乱,史称“安史之乱”。以此为标志,大唐帝国由盛及衰。但是,如果说鉴真在此前13年就已经预测“安史之乱”发生而接受荣睿的邀请,笔者无论如何也不能苟同。与这种“唐朝衰弱论”相比,更离谱的是“鉴真亡命说”。一部分日本学者认为,鉴真预测到中国将要发生大乱,于是携带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字帖等稀世珍宝,逃亡日本避难。小野胜年博士认为,这些说法漏洞百出且“牵强附会”,是缺乏证据的“武断解释”,因而“不可草率相信”。⑦
在此,笔者关注的是,当时唐朝的普通中国人对于乘船到海外(尤其远赴日本)是如何考虑的。实际上,藤原清河一行去拜见玄宗皇帝时,除了鉴真,他们还曾极力邀请一位儒学家。他的名字叫萧颖士,是唐代一流的文人。关于邀请萧颖士的记载很少,而且相关记载还存在矛盾。据《全唐文》卷359,萧颖士的弟子刘太真在《送萧颖士赴东府序》中这样写到:“顷东倭之人,逾海来宾,举其国俗,愿师于夫子。非敢私请,表闻于天子。夫子辞以疾,而不之从也。”可信度当属最高。
由此可知,萧颖士受到了来自“东倭”即日本⑧的邀请,但他却以生病为由拒绝了。虽然日本要迎他为国师,但他却称病婉拒,甘做唐朝东府(洛阳)的微官。如果说萧颖士看透了唐朝的衰落,对前途产生绝望情绪的话,或许会趁着这个好机会逃亡到日本去吧。
如果细致研读鉴真的传记,就会发现鉴真非但没有丝毫“绝望”情绪,而且还处处散发出盛唐时期人们所特有的大唐气度。鉴真对于荣睿邀请的答复,《唐大和上东征传》中所载的内容如上所述,《大唐鉴真传》中有关此事的记载稍有不同——鉴真没有提到慧思转世传说,而引用了智者大师的预言:“三百年后,我所遗文墨,感传于世。”继而发出感慨:“大师无常,洎二百年。而今大唐国家道俗总大兴隆,圣人言语,未曾相违。”[5]
从“而今大唐国家道俗总大兴隆”的措辞中,可以看出鉴真对祖国满怀自豪,对大唐充满赞赏。由此推论,鉴真东渡日本并非是看透了“旧世界”的衰落,而产生“亡命”日本的绝望念头。
六、结语
综上所述,关于鉴真渡日的动机,立足于日本史而倡导的“留学僧怂恿说”和“圣德太子敬慕说”,着眼于中国的政治形势和社会背景而臆造出“鉴真间谍说”和“鉴真亡命说”等,均属偏颇之见,未能真正揭开鉴真东渡之谜。
本文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剖析批驳,同时注意到道教与佛教的势力消长、舍利信仰和转世渴求的内心世界,与鉴真东渡动机关系极为密切,唯文章篇幅已经过长,留待其他机会再呈陋见。
附记:本稿原系拙著《鉴真和上新传》([日]农山渔村文化协会,2002年)第四章“鉴真东渡动机诸说”之部分内容,葛继勇博士将其翻译成中文,笔者在此基础上作了较大幅度的增补删减,兹记之,谨表谢意兼明文责。
注释:
①日本第一批遣唐使于贞观五年(631)抵达长安,唐太宗“矜其道远,敕所司无令岁贡”,翌年派新州刺史高表仁赴日宣抚。高表仁一路艰辛,浮海数月方至,回国后谈虎色变地描述渡海经历:“路经地狱之门,亲见其上气色葱郁,有烟火之状,若炉锤号叫之声。行者闻之,莫不危惧。”(《册府元龟》卷662)。在航海经验匮乏、造船技术落后的古代,中日之间的航道事故频发,被称作“地狱之门”。
②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荣睿发出邀请后,鉴真问众弟子:“谁有应此远请,向日本国传法者乎?”然而“时众默然,一无对者”,良久大弟子祥彦说明缘由,强调航海危险、人生难得:“彼国大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人身难得,中国难生;进修未备,道果未克。”这一席话大概代表当时唐人的“常识”。
③福井康顺在论文《鉴真和上东渡动机及其传戒》(载安藤更生编《鉴真圆寂一二○○年纪念》,[日]春秋社1963年版)中,针对学界出现的“思托捏造说”,宣称“为鉴真和上、亦为唐僧思托而颇感痛愤”,因而“在鉴真和上远忌之际,彰显其渡海动机”,列举出五大理由,进行犀利的批驳。
④《宋高僧传》(《唐扬州大云寺鉴真传》)云“僧思托著《东征传》详述焉”;又据日本文献《招提千岁传记》,思托所撰《东征传》为“广传”,淡海三船所撰《东征传》称“略传”。思托的《东征传》据诸书所引逸文,全称为《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本文为行文方便略作《大唐鉴真传》。
⑤衡山当在湖南省,铃木治误作“广东省”。
⑥即所谓的“争长”事件,发生于天宝十二载(753)。《续日本纪》卷19、天平胜宝六年(754)正月三十日条,载有遣唐副使大伴古麻吕的回国报告:“大唐天宝十二载,岁在癸巳正月朔癸卯,百官诸蕃朝贺,天子于蓬莱宫含元殿受朝。是日,以我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新罗使次东畔第一、大食国上。古麻吕论曰:‘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大日本国久矣。而今列东畔上,我反在其下,义不合得。’时将军吴怀实见知古麻吕不肯色,即引新罗使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日本使次东畔第一、大食国上。”
⑦对于部分日本学者所持的这种观点,小野胜年在《鉴真传及其周边》(收入《日本绘卷大成16东征传绘卷》,[日]中央公论社,第93页)中予以批驳。
⑧刘太真《送萧颖士赴东府序》中的“东倭”,《新唐书》作“日本”,《旧唐书》作“新罗”,围绕招聘国学界尚存分歧,笔者认为刘太真系萧颖士弟子,且《送萧颖士赴东府序》记载亲历之事,故持“东倭”即日本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