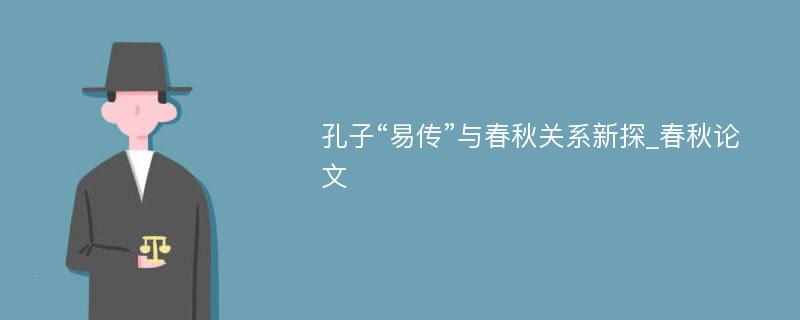
孔子传《易》与作《春秋》的关系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新论论文,春秋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82(2006)05-0036-07
近几年来,随着诸多先秦、秦汉简帛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许多疑案得到了科学的解决。其中之一就是曾受到广泛怀疑的孔子传《易》之说,终于初步得到了证实。但还有许多深层的问题尚待探讨。如:孔子为何“晚而喜《易》”并传《易》?其与孔子作《春秋》有何联系?对孔子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又有何影响?这些问题虽然早已有人论及,但由于对孔子作《春秋》的问题尚未突破前人窠臼,故多有似是而非之论,笔者试结合对孔子作《春秋》的最新研究,对此作探讨与辨正,与同好切磋商榷,并就正于方家。
一、孔子“晚而学《易》”直接出于作《春秋》的需要
帛书《要》篇记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1] 这与司马迁之所记恰相吻合。《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而喜《易》,序(《正义》:“《易·序卦》也。”)《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第1937页)[2]《论语》对此亦有记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第144页)[3]
孔子为什么“晚而喜《易》”?为什么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对此,前人曾有种种怀疑与不同的诠释。近年来论者虽也承认孔子传《易》,但对孔子这位一向“不语怪力乱神”不相信占卜的圣人,为何到了晚年,突然对占卜的《易》感起兴趣,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
笔者认为,孔子读《易》,直接出自其作《春秋》的需要。《史记》记载:“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太史公自序》,第3297页)[2] 这就是说,孔子于五十六岁鲁司寇受挫时,即萌生作《春秋》之志。《史记·孔子世家》亦记:“子曰:‘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第1943页)[2] 可见孔子立志作《春秋》,是从鲁司寇受挫发现“吾道不行矣”之时开始(而非如传统所传说的“获麟而作《春秋》”又“绝笔于获麟”——此乃以董仲舒为首的汉儒所炮制的经学神话,其荒谬不值一驳)。而作《春秋》,就不得不精通于《易》。一来古代史与巫相通,史中多有占卜之记(卜辞亦为史)。若不通《易》,则无法通史。二来,春秋时期中原各国已经普遍形成引用《周易》的习惯,不仅史官普遍用《周易》占卜,而且,一般官员、士大夫,也普遍引《易》占筮。对此,据各国史料汇编的《国语》中也有明确记载,如:“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闭而不通,爻无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晋国,以辅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晋国”,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国之务也,吉孰大焉!《震》,车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乐也。车班外内,顺以训之,泉原以资之,土厚而乐其实。不有晋国,何以当之?……’”(《国语·晋语》,第362页)[4] 公子重耳非巫而亲筮之,司空季子引《周易》而解之,可见当时《周易》的普及。据不准确统计,今之《左传》引《易》及占卦就有一百余次,其中引《易》“象”四次,引《周易》十余次,记占卦九十余次。很难想象,若非通《易》,如何读懂史料,又如何能作《春秋》?
正是为了作《春秋》,孔子才发奋学《易》。其时孔子已年过五十六岁,因后悔学《易》太晚,故说:“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意思是,如果让我多活几年(即能倒退几年),五十岁就开始学《易》,那我就能(运用自如)不会发生大的过错了。因《易》深奥,故手不释卷,以至“韦编三绝”。
但一些论者却认为“《春秋》作于孔子辞世前两年,即鲁哀公十四年。《易传》的著述时间当在返鲁之后,作《春秋》之前。”[5] 将传《易》与作《春秋》隔裂开来,于是传《易》便成了空穴来风;于是一向不信算命占卜的孔子为什么突然对这部算命的书感兴趣并将其改造成贯通天人的宏著,只能归因于圣人的天才与特异功能了。
二、孔子传《易》之“窃义”与作《春秋》之“窃义”异曲同工
“《易》本为卜筮之书”,这是早在宋代朱熹就已明确指出的。“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自是孔子《易》……文王以前只是大亨而利于正,孔子方解作四德。《易》只是尚占之书。”(卷六十七《易·纲领下》,第1475页)[6]“盖文王虽是有定象,有定辞,皆是虚说此个地头,合是如此处置,初不黏著物上。……到得夫子,方始纯以理言,虽未必是羲文本意,而事上说理,亦是如此,但不可便以夫子之说为文王之说。”(同前,第1477页)[6] 不仅明确区分了《易》之成书的三个阶段,而且指出《易》理出自孔子。
《易》本是卜筮之书,其卦爻辞乃据卜筮命中率较高者所整理,虽然《易》的作者在卦序的建立与排列上有整体的理性及一定的哲学思维(如世界事物间的对立与转化观念),但其卦爻辞的内容包罗万象,各卦辞间本无内在的必然逻辑联系。自孔子作传后,方赋予其统一的易理。这恰为今所出土的先秦典籍所证实:
帛书《要》篇记载:“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1] 孔子说出了他与巫、史的本质区别:巫赞而不达于数,史达数而不达于德,孔子则唯德义是求。这段话,不仅印证了朱熹的推断,而且与今本《易传》正相参证。
如《乾卦》卦爻辞:“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第13页)[7]《乾》之卦爻辞只讲凶吉,其“九三”爻的“终日乾乾”究是何意,并不十分明确。而《易传》作者则解其意为:“《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见龙在田’,德施普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同前,第14-15页)[7] 将讲究神道天命为主的卦象,解为以人事为主并强调君子道德修养的道德论,这不能不说是对《易》的根本改造。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易传》中有直接引孔子之语以解者:“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同前,第15-16页)[7] 证实此种思想观点,出自孔子。将占凶吉的卦爻辞,解释成君子进德修业和自省修政的教义,这可以说是孔子对《易经》的独具匠心的“窃义”。
笔者认为,孔子对《易经》的“窃义”与他作《春秋》的“窃义”,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第338页)[8]
孔子是如何作《春秋》“窃义”的?这是两千年来争论不休而至今依然烟深滓重是非不明的重大问题。由于这一根本问题长期以来没能得到解决,故直接影响到一系列学术问题的深入。在《易》学研究上同样如此。笔者深感有一辩是非的必要。
传统的说法是孔子作《春秋》,就是对《春秋经》进行“一字之褒贬”的“笔削”,以便显现其“微言大义”。对此,其实早在唐代刘知几就以“惑经”为名,对其提出“虚美者五”“未谕者十二”的责难。朱熹、郑樵也都明确表示怀疑和否定。朱熹说:“《春秋》只是直截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会褒贬,却要去求圣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里事!”(卷八十三《春秋·纲领》,第1480页)[6] 郑樵痛斥:“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以阴中时人,使人不可晓解。三传唱之于前,诸儒从之于后,尽推己意而诬以圣人之意,此之谓欺人之学。”(《通志·灾祥略》,第1905页)[9]
但至今还有论者引《史记》中的“践土之会实召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孔子世家》,第1943页)[2],以明孔子“修”《春秋经》①。其实,这段话与司马迁别处所述的孔子《春秋》矛盾,很可能出自后人插笔。《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明称孔子所作“《春秋》文成数万”(第3297页)[2](而《春秋经》文仅一万多),“《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春秋经》中弑君仅二十六,亡国仅三十四。《公羊传》中弑君亦仅三十一,亡国仅四十二——笔者)。在详述孔子作《春秋》渊源与影响的《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司马迁首提《左氏春秋》,而一字不提被认为是《春秋经》“嫡传”的《公羊传》与《谷梁传》;反之,《史记·儒林传》述《春秋经》的流传源流时,则唯提《公羊传》《谷梁传》,只字不提得到孔子《春秋》“亲传”的《左氏春秋》。这就充分说明,司马迁所称的孔子《春秋》绝然不是《春秋经》。笔者于拙著《〈春秋〉考论》[10] 中以先秦两汉以来典籍中的大量史料考论,全面批驳传统成说之谬(由于问题重大,涉及面广,此不赘),指出:孔子所作《春秋》,不是传统经学家所说的《春秋经》,而是内容和思想都与之大相径庭的另一部独立的《春秋》。孔子因其《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太史公自序》),“不可以书见”——不能把书给学生看,故“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旨”,“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即孔子《春秋》——笔者)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第509-510页)[2] 这就是说孔子《春秋》被左氏为存其“真”而改编成了《左传》(考《左传》中弑君恰为三十六,亡国恰合五十二,这说明《左传》中的弑君亡国之事,源自孔子《春秋》)。换言之,孔子作《春秋》以“窃义”,不表现在《春秋经》,而表现于《左传》。
从《左传》中,我们的确可以考见孔子作《春秋》以“窃义”之迹[11]。例如,《国语》与《左传》都记载管仲辅佐齐桓公争霸的史实,而二书之内容与思想倾向大相径庭。《国语》中之管仲大谈法家路线,“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修旧法”,推行“轨长制”(《国语·齐语》)[4],富国强兵,以实现争霸理想。而《左传》中的管仲则极力提倡招携以德、怀远以礼,宣扬德义为本的儒家思想。《左传》记载,僖公七年,管仲劝阻了齐桓公武装侵郑的企图,曰:“君以礼与信属诸侯,而以奸终之,无乃不可乎?”(《左传·僖公七年》,第318页)[12]“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同前,第317页)[12] 僖公四年管仲代表齐桓公以“尊王”为名,不用战争而迫使楚国就范(《左传·僖公四年》)。这与《论语》中孔子所赞扬的管仲恰恰契若符节:“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第311页)[3]。《左传》思想倾向同于《论语》而异于《国语》。而据其他先秦史料,如《管子》等所记,《国语》较接近史实。显见得《左传》经过作者的加工,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义则丘窃取之矣”。由此可见,孔子作《春秋》的“窃义”是通过有意识的剪裁取舍和对史实的内涵进行改造,以突出其“德义”的主题,这与《易传》的“窃义”可谓同一机杼,殊途同归。
孔子作《春秋》的主导思想,是从“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历史教训中,总结出治国安民之道,指出政权的不稳,源于统治者本身的腐败,故提出“克己复礼为仁”的纲领。所谓“克己”,是要求执政的“君子”加强自身修养,“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3]。而《易传》中恰恰也贯穿了这个思想:“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文言》,第19页)[7]。明确指出保权位的问题:“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第79页)[7]
《易传》全文具有明确的中心,主要集中于治国特别是君子“进德修业”的修身之道上,如《大象传》主要就是讲君子修德与国家治理。《文言传》也主要讲修辞立诚。
《周易·大象传》中大半标明君子修身正位治国之道,使《易》成为君子明德修身知戒惧之器。这就是孔子传《易》以“窃义”的本旨。
需要指出的是,对《易》进行“窃义”的改造,首先表现于孔子《春秋》即今以左氏命名的《左传》。如昭公十二年:“南蒯之将叛也……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下坤上坎),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而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左传·昭公十二年》,第1337页)[12]——明确指出祸福由德,而不取决于占卜之凶吉。这种以德为先,置于卦占凶吉之上的思想,是《左传》的主导思想,贯穿于全书。
有人认为这是春秋时期的时代性产物,称其“成为当时的共识”[5]。这种看法未免失之偏颇。如果这真的已成为“共识”,孔子难道还会以“德义”高自标榜而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的话吗?再说,与之同时代的《国语》中,三引《周易》,未见以德义释卦并置德义于卦占之上者,可以说基本没有这种思想。《国语》对占卜是绝无疑议的,甚至唯占是从。《左传》称民为“神之主”,置民于神之上;而《国语》总是民神并列。故《左传》这种德义至上的道德本体论,绝然不同于《国语》,不可能出自左丘明。相反,他与孔子则一脉相承。帛书《要》记孔子语曰:“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孔子所言,正与惠伯之语同出一辙。
还有一个更有力的佐证是《左传》襄公九年写穆姜解《易》之语:“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第965-966页)[12] 穆姜之语,完全同于《易传》之语——《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第15页)[7],二者如此吻合,甚值得深思。章太炎认为是“孔子以前说《易》者发为是言,而孔子采之耳。”(《经学略说》,第65页)[13] 笔者认为,如果孔子之前“说《易》者”已“发为是言”,以“德义”解卦,则孔子就不会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的话了。春秋时期还是迷信鬼神、每事必占的时代,《易》的正常功能是占卜,以“德义”解卦的思想不可能自发产生。它只能是出自博学而“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3] 不信占卜的孔子——孔子想利用这部宗教经典,宣扬他的以道德为基础以仁为核心的儒家理论,故以“德义”解《易》,借神道设教,化腐朽为神奇。这对于《易》学具有革命的意义。穆姜之语,与前面所举昭公十二年惠伯的以德为先语意相同,都是孔子“以德义”解《易》的体现。在历史上,孔子是以德义解《易》的第一人。故此语只能是出自孔子之笔(这也可看作孔子作《左传》蓝本的又一佐证)。
三、孔子传《易》对其作《春秋》的影响
对《易》的研究,使罕言“性与天道”的孔子,产生了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重大转变。
《论语》记载:“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第98页)[3] 这段话似乎可以反映孔子读《易》作《春秋》前即五十六岁之前其治学教学的特点。孔子前半生主要研究政治伦理,学术目光未及“性与天道”,故学生“不可得而闻”。而学《易》之后,他把目光扩展到了“性与天道”,从本体论上为其仁学理论找到了基础,并建立了“天道—性命—道德”三位一体的道德本体论,从而大大升华并完善了他的儒学理论体系。
帛书《要》记载:“子曰:‘《易》之道,[存乎其辞也。其用者,]此百姓之道[之谓]《易》也。夫《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图,愚者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顺于天地之心,此谓易道。故易,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要之以上下。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物尽称之,故为之以八卦。”[1] 这段话,集中反映了孔子对《易》之道的朴素唯物与辩证的诠释。用《易》占凶吉,这是百姓的实用,而真正的《易》之道,在于懂得天地人道万物内部阴阳刚柔间相对立相转化的道理。今本《易传》之《说卦》与这段话正相呼应:“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第93-94页)[7]
天道讲“阴阳”。所谓“阴阳”即《系辞上》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对天道运动规律性的高度抽象。阴阳之道,乃天地变化的必然性。《左传》(亦即孔子《春秋》)中正是从这样的原则出发对阴阳的范畴作了界定:“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鷁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对曰:……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第369页)[12] 这里特地明确将“阴阳之事”与“吉凶”之事区分开来,指明“阴阳”非关凶吉,一方面确定了天道“阴阳”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也突出强调了“吉凶由人”的人事主观性,突出了“德义”的重要。这种朴素唯物的阴阳观正是孔子作《春秋》和传《易》的哲学基础。
上面所谓的“刚柔”,指“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系辞上》)[7] 的万物之道。孔子称之为“地道”,亦即事物的“损益之道”。孔子戒其弟子曰:“二三子,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门也……损之始凶,其终也吉。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要》第九章)[1]。“君者之事”即社会政治,反映的是人类社会之规律。所谓“刚柔”,为君之道的“刚柔”“损益”,具体的说就是以“刚”(刑罚)、“柔”(道德)来治民。战国楚竹书《季康子问孔子》篇记载孔子之言曰:“德以临民,民望其道而服焉。此之谓仁之以德。且管仲有言曰:君子恭则遂,骄则侮,备言多难。”“君子强则遗,威则民不导(道),逾则失众……好刑则不详,好杀则作乱。”[14] 这就是说,以“柔”德施民,民就能顺从,而用“刚”的刑罚杀戮手段,就会招致“作乱”,就会天下大乱。所以君子要自“损”,自抑谦恭,“克己复礼”,才能顺遂成功。这就是“君者”的损益刚柔之道。
正是这种朴素唯物的宇宙观与辩证法,使孔子在他的《春秋》中客观分析统治阶级大权旁落的原因,将其归结为统治阶级本身的腐朽没落。“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叔向曰:‘然。虽我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况日不悛,其能久呼?’”(《左传》昭公三年,第1234-1235页)[12] 陈氏代齐,源于“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三家分晋,源于“庶民疲蔽,而宫室滋侈”。齐君残酷地剥削百姓,“民叁其力,二入于公”,最终众叛亲离——借用《要》中之语,君“益之始也吉,其终也凶”;而陈氏贷粮给百姓则大斗出小斗进,故“民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可谓“损之始凶,其终也吉”。这与《易传》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文言》,第18页)[7] 二者正相呼应。
《春秋》指出季氏专鲁,源于君室的世代腐朽:“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第1519-1520页)[12]。“一阴一阳之谓道”,《大壮》“雷乘乾”,即阴乘阳,阴极而向阳变化,故“利贞”,利于坚守正道。任何事物都向其反面转化,故“艰则吉”。运用解《大壮》卦象,归纳出历史之规律是“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天之道也。”《易》之《革》卦《彖》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第60页)[7] 意与此相通。
《易》之道,使孔子对历史运动规律的认识,上升到了朴素唯物的本体论与辩证法的高度。
《乾》卦《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第14页)[7] 这里的“乾道变化,务正性命”,把天道变化与“性命”之“正”统一起来。又进而与道德相联系:“昔者圣人之作《易》也,……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第93页)[7] 将“和顺于道德”与“穷理尽性”并提,这就将道德上升到天理的高度;而以“穷理尽性”为“命”之前提条件与途径,又将“命”的内涵客观化。《易传》又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说卦》,第93页)[7] 将天道与人事,客观性的“理”“性”与人伦的“道德”“义”统一起来。联系三者的桥梁是客观性的“性命”,指出《易》以顺从“性命之理”为目的,把“性命”与天理相统一起来。将宇宙万物的“天道”,与社会性的“立地之道”,及伦理性的“立人之道”统而一之,从而确立了他的以天道为基础,以“性命”为纽带,以道德为核心的“天—地—人”三位一统的仁学理论体系。
孔子在他的《春秋》中对此理论作了充分的发挥:“刘子(刘康公)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左传·成公十三年》,第860-861页)[12] 所谓“受天地之中”亦即“天地之正”。命受于天地,性是命在具体之物的体现,而礼义的目的和作用是“定命”:“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第1457-1459)[12] 这段话全面发挥了儒家的道德本体论。将礼视为天地之经义,顺从礼,就是“则天之明,因地之性”——“性”亦为物本身所秉受于天地者。“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左传·襄公十四年》,第1016页)[12]“淫则昏乱,民失其性”,只有顺从礼,方能“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将礼乐与性、命联系起来,提到本体论的高度,并把自然天地之道作为仁义礼乐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的依据,这就为儒家理论建立了最高的依据,哲学的基础。
由此可见,孔子传《易》与作《春秋》,是二而一的事,是相互促成者。作《春秋》,是孔子学《易》的原动因;而《易》的学习研究,使孔子作《春秋》及其建立道德为本的儒学理论找到了本体论的基础;作《春秋》的过程,又使孔子在传《易》时,更一步增强了他的道德本体论。
注释:
①其实,杜预即已引汲冢《竹书纪年》所书“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以明国史皆承告据实而书。”(《春秋经传集解·春秋经传后序》)据《史记·晋世家》:“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有人将句子断至“无召王”,则明显语气未完整。《史记·周本纪》亦有相关记载,明其为史官所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