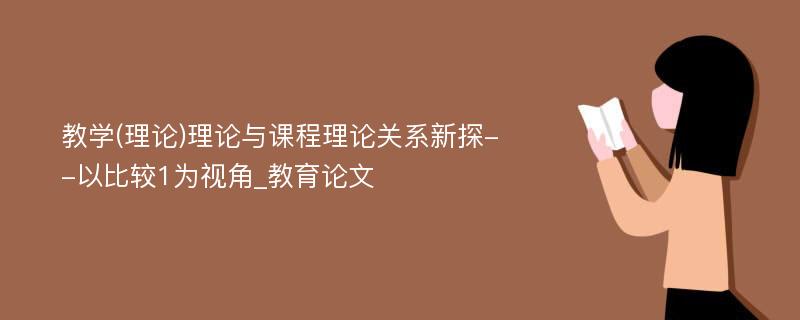
教学(理)论与课程论关系新探:基于比较的视角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课程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667(2009)12-0044-07
教学论(Didactics)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它与教学理论(Theory of Instruction)一样吗?它与课程论(Curriculum Studies)究竟是怎样的关系?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理论界一般都把教学论当成教学理论,虽然这两者只有一字之差,但却有很大区别。教学(理)论与课程论均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但教学论是一门源于欧洲教育文化传统、尤其是植根于德国教育文化传统的教育学科,而课程论(以及与之相关的教学理论)则主要兴起于美国及英国的教育文化传统。我国教学论与课程论学者长期误读了源自西方两种不同的教育文化传统,致使关于教学(理)论和课程论关系的争论陷入了误区与僵局。走出这一误区和打破这一僵局需要从这两门教育学科所赖以产生的不同教育文化传统来重新认识它们,比较它们和研究它们,并在理解它们各自特点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教育文化传统和教育实践,建构具有中国教育文化特色的教学论和课程论。
一、教学论≠教学理论
要厘清教学论与课程论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区分教学论与教学理论,因为前者源于以德国为主的欧陆国家的教育文化传统,而后者和课程论则植根于美国及英国的教育文化传统。我国许多教育学者一般都把教学论与教学理论不加以区别,结果在讨论教学论与课程论的关系时把教学理论也牵扯进去,其实美国并没有教学论而只有课程论及其下位的教学理论。
例如《教学论稿》一书中援引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里的话为依据,指出:“教学论或教学理论,英语为Didactics(又称Theory of Instruction),俄语为дидактика;均来源于希腊文δυδατυοco,即‘我教’的意思。”[1]这段引文对Didactics与Theory of Instruction未加以区分,因此,在汉语中也就把教学论与教学理论等同起来了。《20世纪西方教育学科的发展与反思》一书同样也没有把教学论与教学理论加以区分。该书在第五章“应用性教育学科的崛起”首先讨论了“教学论”(Theory of Teaching,Didaktik),认为“夸美纽斯以后的许多教育家也在教学论研究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如洛克、裴斯泰洛齐、赫尔巴特、威尔曼、杜威等”。[2]从括号里使用的英文名称看,这本书也把教学理论当成了教学论。该书列出的教育家名单中把英国的洛克和美国的杜威都说成是对“教学论”做出了贡献,可见是把教学理论与教学论混为一谈了。《教学理论:课堂教学的原理、策略与研究》一书,从书名(以及书中的内容)即可以判断作者把“教学论”纳入到美国教育文化传统的教学理论中了。但是,美国学者自己却并不认为他们也有“教学论”,甚至连Didactics这个词在英美教育学者的著述中也极少出现。
诚然,20世纪美国有了自己的教学理论。20世纪上半叶,杜威对教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泰勒也对教学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最大的课程研究组织即督导和课程编制协会(ASCD)甚至还专门成立了“教学理论委员会”,掀起了一股教学理论研究的浪潮,出版了许多有影响的论著,如盖奇的《教学研究手册》(1963),希尔加德的《学习与教学的理论》(1964),麦克唐纳德等人的《教学理论》(1965),布鲁纳的《教学理论探索》(1966),等等。[3]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教育学家舒尔曼还研究了教学专业的知识基础,提出了著名的“学科教学知识”(PCK)概念,推进了教学理论的研究。然而,所有这些在美国学者的眼里都只是教学理论而不是教学论。事实上他们在探讨教学理论时并没有沿用Didactics一词,而是使用了Theory of Teaching或Theory of Instruction。从20世纪初期以来形成的美国教育科学的学术传统来看,教学理论研究部分是在课程论的学术传统里进行的,部分与教育心理学研究紧密相关。例如,被誉为“课程评价之父”的泰勒,其代表作《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里的“教学”(原文为Instruction)是与课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课程研究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而布鲁纳在20世纪50、60年代主要研究了学科结构课程理论,与之相应的教学理论与其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息息相关。
假如教学论与教学理论果真是一回事的话,那么美国教育学者对前者按理说不应当陌生。可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一些教育学者才第一次与德国及北欧国家的教学论学者进行学术对话,才算正式遭遇了教学论。说是“第一次”或许并不准确,因为19世纪下半叶许多负笈德国的美国教育学者早已把包括教学论在内的德国教育学说引进到美国,甚至在1895年还成立了全国赫尔巴特学会(此前在1892年成立了赫尔巴特俱乐部),但美国人进入20世纪后另辟蹊径开始了课程研究和教育心理学研究,却没有再关注德国的教学论。所以美国著名的课程论学者、《课程研究期刊》(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的主编(Ian Westbury)在2000年曾坦陈:“教学论(Didaktik)是思考教与学的(另)一种传统,这在英语世界里几乎无人知晓。”[4]因此,美国课程论学者与德国及欧洲国家的教学论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才展开了一系列对话。
原来当代美国教育学者竟然不了解植根于德国的教学论!他们自己的教学理论只是课程论这一较晚形成的教育文化传统内的与教学论有别的教育科学研究而已,与源自德国的教学论并非一回事。我国学者在论证教学论与课程论关系时常常引用美国课程学者(Oliva)提出的所谓“课程(论)与教学(论)关系的4种模式”,笔者查看了英文原著后发现,其实那只是课程(Curriculum)与教学(Instruction)的4种模式,只是在课程论框架下对课程与教学关系的分析,并没有展开课程论与教学论关系的讨论。[5]那么,究竟什么是德国及北欧国家教育文化传统意义上的教学论(德文Didaktik,挪威文Didaktikk)呢?
二、教学论:德国教育文化传统中教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我国教育理论界比较熟悉的教学论,首先是夸美纽斯的教学论和赫尔巴特的教学论,其次是前苏联的教学论。而对于源自当代德国的教学论,我们与许多英语国家的教育学者一样也“几乎无人知晓”。
教育学(Pedagogy)学科史研究表明,教学论(拉丁文为Didactica)这一概念最早是由17世纪德国的拉特克(Wolfgang Ratke,1571~1635)提出的,具体时间在1612~1613年间。“教学论”一词是由希腊文Didaskein[其含义是指向(Pointing at)、演示(Demonstrating)]加上由希腊文拉丁化的词Techne,Ike(意思是技艺)撰造出来的。由于是一个撰造的新词,据说当时德国语言学家讥之为“厨房拉丁词”。[6]拉特克当时是拉米斯派罗斯托克大学的学生,他建议把“新的学习艺术叫做教学论”,这一建议在他游学途中得到拉米斯派吉森大学的教师(Junge,1587~1657)和(Helwig,158l~1617)两人的支持。[7]
教学论这一概念的内涵在17世纪与以后几个世纪有所不同。最初它是与学校教育有关的一个主导概念,在其撰造出来后最初100多年里,它与“教育学”(英文为Pedagogy,德文为Padagogik)是同义词。[8]教学论作为一门教育学科在欧洲国家传播开来当推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J.A.Comenius,1592~1670)。他在1637年出版了《大教学论》(拉丁文是Didactica Magna,英译本为The Great Didactic)一书。这部著作的内容远远超出了教学论的范围,涉及教育理论的各个方面。以往我们不理解夸美纽斯何以用《大教学论》而不用《大教育学》作为书名,可否这样考虑,夸氏用的书名在德语语境下并不是大教学论,1939年傅任敢先生翻译成《大教授学》更贴近原意,而他后来解放后改译为《大教学论》,恐怕也是受了当时引进的前苏联教学论一词的影响吧。当然,这样译也有不了解德国教育文化和教育术语意义的因素。鉴于17世纪时Didaktik与Padagogik可以“通假”,其实这本书的书名本当可以译为《大教育学》的。
学科概念史的考察还表明,18世纪时“教育学”在德国已成为一个主导术语。[9]如德国大哲学家康德在柯尼斯堡大学讲授过教育学,他的学生林克(Friedrich Theodor Rink)把他关于教育学的授课讲义进行了整理,形成了《论教育学》(1803)一书。康德使用的教育学一词是Padagogik而不是Didaktik。赫尔巴特是康德在柯尼斯堡大学哲学教席的继承人,他的两部主要的教育著作也都冠以“教育学”的书名,而不以“教学论”命名,但赫尔巴特提出了著名的“教育性教学”(Educating Instruction)的原理,他的教育学著作里面也有许多教学论的内容。后来赫氏弟子齐勒和赖因“把教学论从一般教育理论中抽取出来,把它变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专门探讨学校教育条件下的教学问题”。[10]于是德国教学论就从教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了。
当代德国的教学论是建立在“教化”(Bildung,也译为“教养”)概念基础之上的。“教化”是德语世界里特有的一个新人文主义哲学概念,它是德国“精神科学赖以存在的要素”。[11]“教化”不同于英语中的“教育”(Education)及其德语对应词“教育”(Erziehung),而“仅指教育的一部分,其中只涉及下一代应当获得的内容与技巧方面”。[12]但是,这些“内容与技巧方面”不仅仅是就其本身而言的,因为正如哲学家伽达默尔所指出的那样:“在教化(Bildung)概念里最明显地使人感到的,乃是一种极其深刻的精神转变。”[13]对“教化”理论作出了深刻阐述的洪堡曾指出:“如果我们以我们的语言来讲教化,那么我们以此意指某种更高级和更内在的东西,即一种由知识以及整个精神和道德所追求的情感而来的、并和谐地贯彻到感觉和个性之中的情操。”[14]换句话说,“教化”乃是通过教育而使人“向普遍性的提升”,让“他脱离了直接性和本能性的东西”。[15]
根据上述对“教化”概念的理解,教学论并不是如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只是研究如何(How)教与学的理论,而是要研究人之为人的根本问题,亦即为什么(Why)知识和技巧能“成人”的问题。由此可见,教学论同样关注课程问题,但关注的角度和方式不同于课程论。对此,当代德国教学论专家(Rudolf Künzli)作了精彩的分析:[16]
“根据教学论的观点,教化是一个超越了知识和技巧本身的概念,是指通过主动参与到文化遗产中来并创造性地获得它们而形成个体的过程。其最初的任务不是要问学生如何学习或如何使学生接近知识,也不是确定学生应当能做什么或知道什么。相反,教学论专家最初的任务是追求文化所赋予的知识和技巧在形成品德上的意义。这才是考虑对象时所关注的焦点,而正是这一焦点决定了各种可能的教学方法及其情境与相互联系。教学论首要的基本问题是要追问,为什么学生要学习这个课题?如果不能至少间接地对教化有所助益,任何教学目标都是不值得的。所以,首要的任务是依据教化找出将要学习的对象的意义,然后才去追问它能够和应当对学生有何意义,以及学生如何能够自己体验这种意义。”
上述观点在德国著名教学论专家克罗恩(Friedrich W.Kron)提出的对教学论的界定中也得到印证。克罗恩指出:(1)“教学论是教和学的科学”;(2)“教学论是教学的理论或科学”;(3)“教学论是教育内容的理论”;(4)“教学论是控制学习过程的理论”;(5)教学论是教和学方面心理学理论的应用”。[17]从克罗恩的观点看,教学论不只是教学的理论或科学,教学论也是教育内容的理论,亦即教育内容如何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培养理想人格的问题。这就是教学论与课程论在对待课程问题上的差别。前苏联教学论把“教养”当作教学论的一个重要范畴,正是继承了德国教学论重视“教化”的传统。
三、课程论:美国教育文化传统中的教育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与历史较为悠久的德国教学论相比,课程论则是20世纪初期美国教育文化传统的产物,后来成为在美国发展起来的教育科学(Educational Sciences)的一个分支学科。具体而言,课程论最初是在19世纪末期美国兴起的赫尔巴特运动中酝酿,在进步主义教育理论背景下课程科学化运动中形成,并主要在3所著名大学中诞生的与德国教学论不同的教育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课程论兴起于美国已为课程史学者所公认。英国著名课程论学者李德(William Reid)认为:“课程作为学术活动的一个焦点,首先是在北美国家制度化的,其目的是为学区提供懂得能够和应当改进、更新和改革课程的教育领导。这种期望至今仍是课程事业的核心。”[18]课程学史研究表明:在19世纪9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赫尔巴特运动中,美国一批曾在德国留学的教育学家受到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启发开始关注学校课程问题。例如,赫尔巴特学会会长德伽莫(Charlses De Garmo)著有《方法的要素》(Essentials of a Method,1889);另两位赫尔巴特主义者莫克默里兄弟(Charles and Frank McMurry)合著了《讲授的方法》(The Method of the Recitation,1897)及《一般方法的要素》(The Elements of General Method,1903),他们被认为是美国“课程领域的先驱”。[19]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阐述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著作在书名中都使用了“方法”而不是课程,但是,他们对“方法的概念作了广义的延伸,它几乎成为课程概念的同义词”。[20]由此可见,源于美国的课程论之根最初是受到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教育思想启发而在美国教育文化土壤里萌发的。这对于当前我国教育理论的创新不无深刻的启迪。
美国的课程论是在教育科学(Educational Science)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大体而言,课程论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形成是进步主义教育背景下课程科学化运动的结果。最初的课程研究主要集中于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俄亥俄州立大学教育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这3所著名大学的教育学院都把教育作为社会科学来研究。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先后有贾德(Charles H.Judd)、博比特(Franklin Bobbitt)和泰勒(Ralph Tyler)3位著名的课程专家;俄亥俄州立大学教育学院有博德(Boyd Bode)和查德斯(W.W.Charters)等课程专家;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则有腊瑟尔(James E.Russell)、拉戈(Harold O.Rugg)、纽伦(Jesse H.Newlon)等课程专家。芝加哥大学的课程专家是“逻辑经验主义取向的课程研究先驱;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课程学者是批判概念取向(The Critical Conceptual Approach)的课程研究的鼓吹者;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课程专家则独特地代表了社会诠释取向的课程研究(Social Hermeneutical Approach)”。[21]这3所大学的课程学者都参与了20世纪30年代的“8年研究”,他们不同的研究取向相互激荡、碰撞,为美国学校的课程改革提供了强劲的理论支撑。至1937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在院系组织结构调整时,一个独立的课程与教学系产生了,早期的课程学会也诞生了,专门的课程著作也开始出版了。[22]至此,课程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正式在美国得以形成。
美国的课程论在20世纪60年代被引进到德国,并对当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教学论和课程改革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以罗宾逊(Saul B.Robinsohn)为代表的一批西德教育学者认为,美国的课程论远比德国自己的教学论高明,“……课程研究和规划是期待已久的包治百病的良药”,以至于当时德国“大多数研究者和教育行政官员都只坚持课程论的观点而把教学论当作过去的模式予以撇开”。[23]可是,好景不长,“课程热并没有热多久……似乎课程运动只是一种初恋:热烈却很短暂”。[24]尽管如此,美国的课程论还是对德国教学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正如德国教学论学者(Hopmann)和(Riquarts)所言:“教学论从课程之恋的‘难忘岁月’中走出来并非没有改变。它在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教学论学者接受了课程运动(对教学论)所作的批评,即教学论在对待国家的规范(State Regulations)时曾经是过于天真了……今天不同学派的教学论都一致同意教学论必须有批判精神,当国家的要求不符合教学论认为是有利于学生时甚至应当予以抵制;第二,而且这也同样重要,教学论恢复了昔日的雄风,它彻底地向(学科)内容转向从而成为内容、教师和学生的一个中介。”[25]德国教学论与课程论的这段遭遇也颇有意味,它是否昭示我们在对待本民族的教育文化传统时既需要批评与反思,也需要尊重与体认呢?
四、结论
解放前,我国受到美国课程论的影响,课程论成为教育决策的选择;解放后由于政治需要的影响,前苏联教学论成为教育决策的选择;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选择课程论,也有政治上摆脱前苏联影响,更多地受到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教育理论的影响,但这种选择并没有经过缜密的学术论证。
解放以后,我国教育学者长期深受前苏联教学论的影响,在教育政策上没有接受课程论。改革开放初期,有些学者认为课程论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而只是教学论的一部份,此即所谓的“大教学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课程论在我国教育理论研究界的恢复及其影响的日益扩大,加上近年来课程改革的推动,也有一些教育学者主张“大课程论”,即认为教学论是包含在课程论里面,试图削弱教学论独立的学科地位。[26]经过多年的学术探讨和争鸣,现在多数教育学者倾向于认为教学论和课程论是两个有密切联系,但显然不同的教育学分支学科。如田慧生提出“教学论与课程论是两个关系密切、部分内容相互交叉但同时又有各自独立的研究领域和专门研究对象的平行的教育分支学科,两者都从属于教育学,是教育学的下位学科”。[27]持此观点的还有廖哲勋(2007)[28]、王鉴(1995)[29]等。此外,还有一些教育学者主张课程与教学整合论,如张华(2000)[30]就持这一观点。
上述关于课程论与教学论关系的观点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把课程论与教学论看作是同质文化中的教育理论,即所谓源自“西方”的教育理论。固然,课程论和教学论都来自西方,但西方教育文化传统有英美与欧陆之别,亦即“日尔曼式教育学”与“盎格鲁式教育科学”之别。[31]在英美教育文化传统中,前文所述的教学理论可以说是包含在课程论里面的,但源于德国教育文化传统的教学论却不能包含在课程论里。我国主张所谓“大教学论”的学者错误地以为教学论包含了课程论,其实这是因为看到美国课程论中也注重研究教学理论而产生的一种误读;同样,主张“大课程论”的学者也错误地把教学理论等同于教学论,结果导致了课程论包含教学论的错误推论,这无疑也是一种误读。
第二,主张课程论与教学论各自平行独立的学者虽然承认了它们各自的生存权利和空间,却又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更没有看到它们之间在教育文化传统上的区别。例如,教学论与课程论都涉及教学内容或课程问题,但在具体处理方式上却不同。教学论传统强调由教育系统确定教育目的和来源知识(Knowledge Sources),再由教师把来源知识转化为适合于教学的知识,此外教师还需要自主地选择教学方法和评价方法;而课程论传统则强调由教育系统确立课程机构,由课程机构规定课程内容和评价方式,教师只能自主选择教学方法进行教学。[32]由此可见,在这两种教育文化传统里,课程与教师的关系以及教师处理课程的方式是很不相同的。
第三,课程论与教学论整合的主张虽然有其可能性,并且事实上我国近年来学术建制上形成的所谓“课程与教学论”二级学科也是这一主张的结果。但这种“整合”的基础并不牢固,因为这不是在课程论与教学论两个学科之间进行充分对话的基础上构建的,而是在消解所谓的“二元对立”的基础上一种生硬的拼盘。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教学论与课程论(以及教学理论)的关系远比我们以往所认为的更为复杂。教学论不同于教学理论,正如教学论不同于课程论一样。教学论与课程论及其下位的教学理论是源自西方两种不同教育文化传统的教育分支学科。前者植根于17世纪以来德国的教育文化传统,具有深厚的德国哲学文化的根基,基本上是一种规范的、具有哲学思辨性质的教育学中的一门分支学科,其核心是新人文主义的“教化”理念;后者则是20世纪初叶以来源自美国及英国教育文化传统,是在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背景下兴起的教育科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其核心是注重经验的、实证的实用主义哲学理念。我国教学论与课程论的学科建设,需要在理解它们各自特点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教育文化传统和教育实践,建构具有中国教育文化特色的教学论和课程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