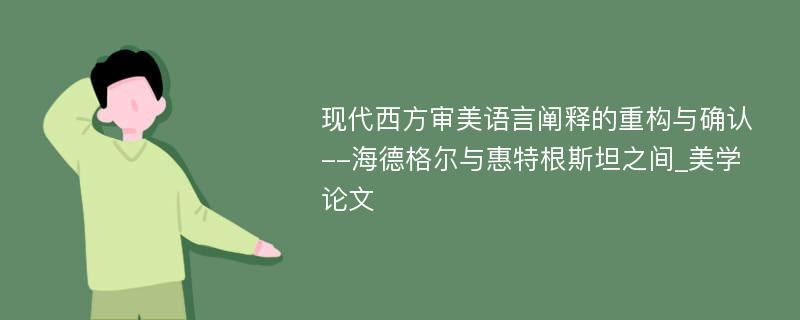
现代西方美学语言释义学的重构和确认——在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之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特根斯坦论文,海德格尔论文,释义论文,美学论文,重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西方美学革命的重心和焦点是围绕语言展开的,美学语言释义学的全面崛起和发展就是其最为显著的标志。但是,在认识论时代,在理念本质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语言问题是根本不可能成为美学的主要问题的,因为语言仅仅作为一种受理性支配的符号,仅仅是意义的记录和反映,是主体和客体交流的工具,理性是先存者、中心或主宰,而语言只是派生物、边缘或从属者,语言是理性的永恒辩证运动的必然外在表现形式。而在现在,从语言入手,以语言取代理性本质主义中心,以语言与意义的关系取代理性与感性的问题,本身就是一种革命,就是对认识论地位的动摇和摧毁,这是其一。其二,从语言入手,重视语言的本体论地位,一方面可以恢复语言在古希腊时代就具有的本体论地位:另一方面,这个本体论一俟奠定,就可以打开一个新的通道,使美学进入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天地。其三,由于近代语言学的突出成就,人们对语言的了解日渐深入和广泛,语言已经广泛地涉及到人类认识的一切方面,这个革命一旦成功,就可能使人类文化发生巨大的变革。总之,无论从哪方面说,语言问题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此,现代思想大师几乎是同时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从不同的方面开始思考语言问题的,而对此首先取得重大突破的是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
与其他思想家不同,海德格尔一开始就把语言放在本体论的地位予以思考。他的目的有二,一是要找到它的本源,恢复语言在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代所具有的本体地位;二是通过解构和批判传统语言思想,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找到它的归宿,这即是美或诗意的归宿。海德格尔明确地指出,“形而上学以西方逻辑和语法为形式,很早就开始解释语言。我们今开只能推测这个过程中隐含的意义。把语言从语法中解脱并放置更原始、更基本的框架,这是留给思想和诗歌的任务。”①他认为语言问题最终是一个美学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它和存在密不可分,或者它们本身就具有此在的存在特征。在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代,语言、存在它们本身都具有谈论、说话的意思,使事物无遮蔽地显露出来,并展现于我们面前,而且这是语言最根本的特性,所以“归根到底,哲学研究终得下决心询问一般语言具有何种存在方式。”②海德格尔认为,这即是言谈,“语言的生存论存在论基础是言谈。”③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和言谈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尽管语言和此在的活动紧密关联,但是言谈比起语言来和此在的关联更为紧密,更为源始,更具有存在的特性。“言谈,同现身、领会在存在论上是同样源始的。……言谈是此在的可理解状态的勾连,展开状态则首先由在世来规定;所以,如果言谈是展开状态的原始存在论性质,那么言谈也就一定从本质上具有一种特殊的世界式的存在方式。现身在世的可理解状态道出自身为言谈。可理解状态的含义整体达乎言辞。言辞生于含义而荫蔽含义,却并非言词物得而具备含义。”④在这里,言谈、现身、理解、解蔽、存在具有相同的意义,言辞生于含义,而这个含义又不是因为表明词物而得来的,根据什么得来呢,根据存在。语言是比言谈更直接的东西,“把言谈道说出来即成为语言,言谈就是存在论上的语言。”⑤所以语言和言谈又是相同的东西,它们都和此在的存在有关,这是无可怀疑的。有了这个缘故,任何意义上的语言都有可能由此引入生存的本体论方向。美及其艺术创作即是如此。“当人思考存在时,存在就进入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寓所。人栖居于语言这寓所中。用语词思索和创作的人们是这个寓所的守护者。”⑥在海德格尔看来,运用语言进行艺术创作就是建筑,作品就是寓所,作家和诗人就是这寓所的看护人。对于艺术家的作品,“不论就它们自身,还是它们两者的关系而言,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依赖于一个先于它们的第三者的存在。”⑦但是,真正能被称为居所和守护人的作品和作家并不多,在他看来只有少数的几位如索福克勒斯、荷尔德林、里尔克、梵高等人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守护人。
而美,在海德格尔看来,就是和语言相连的东西,美是存在在语言作品中的显现。美,成为存在之真理被显现的途径:它如一束光芒把存在从晦蔽处引入澄明地带。“这种光照将自己射入作品,这种进入作品的照射正是美。美是作为敞开发生的真理的一种方式。”⑧海德格尔在其关于艺术和美学的论述中,意味深长地经常运用光、照射、澄明、淀露、泄示、呈现、显现、解蔽等词,其矛头直接针对传统哲学和美学语言释义学的镜子说,不仅是一种本体论的置换,实际上也是一种方法论的置换,镜子与灯,是两个不同时代哲学美学和语言学的不同追求,而美学的语言释义学也就因此获得了新的意义。这就为审美解释开辟了许许多多新的前景和方向。既然是灯,而不镜子,那么那个高高在上的永不变化的理念本质就不再是唯一的前提了。审美的理解和阐释随着光芒四射的灯光,可以走进一个个被照亮的天地。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把握和理解海德格尔的语言观以及由此而来的审美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经常把语言和诗相提并论,并且把诗作为一切思想的最后归宿。他反对传统的逻辑语言,逻辑语言迫使语言委身于理性,“诗意语言”的重视正好说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意图和方法论目的。他说,“语言本身在根本上是诗,……诗在语言中产生,因为语言保存了诗意的原始本性。”⑨“投射的言说是诗”,“诗作为澄明是投射”,“诗意只是真理光明投射的一种方式”,“艺术的本性是诗,诗的本性却是真理的建立”,“建立是充溢、赋予、赠送”,“投射是敞开或者显示。”⑩诗意的把握、诗意的理解、诗意的居住等等,这是一种十分激进和冒险的主张,有着强烈的破坏性,它意味着把逻辑、规范、理性等全部从语言活动中完全排挤出去。海德格尔晚年最终走向一种诗意的追求,就最深刻地表明了这一点。
海德格尔在重构和确立语言本体论的同时,也进行了对释义学的本体论思考。他是从重新追向logos的本源倾向着手这项工作的,他从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代开始。在前苏格拉底时代,logos的基本含义是言谈,但是在苏格拉底时代以后,哲学家们对这个词进行了形形色色的随心所欲的解释,被赋予为理性、判断、概念、定义、根据、关系等含义。海德格尔认为,“logos作为言谈,毋宁说恰恰等于把言谈时话题所及的东西分开出来。”(11)他认为阐释无非是“让人从显现的东西本身那里,如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来看它。”(12)这正符合现象的观念,因此他把自己的阐释工作称之为现象学的释义学,他说:“现象学描述的方法上就是解释。此在现象学的logos具有诠释的性质。通过诠释,存在的本真意义与此在本已存在的基本结构就向居于此在本身的存在之领悟宣告出来。此在的现象学就是释义学。”(13)这是释义学的主要工作也是第一层意义;释义学的第二层意义是整理出一切存在论探索之所以可能的条件;释义学的第三层意义为它是生存的存在论状态的分析工作。哲学和释义学的区别就在于哲学是普遍的释义学存在论。显然,海德格尔的阐释思想与语言思想是一致的,它们都根源于他的存在论的本体论。
很清楚,海德格尔的释义学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释义学,它不是以客观的理性原则为前提的,它不是为了追求客观对象的本质为目的,而是以此在的存在论为基础,解释领会此在本身的存在。他不仅为此在的存在论阐释建构了本体论的基础,而且使其在更广泛的生存论状态上成为可能。这就为以后的语言释义学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海德格尔对语言释义学存在论的分析,以及由此建立的美学语言释义学本体论基础,表明了近代美学的认识论的本质主义不仅是彻底错误的,而且它所依赖的那个形而上学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西方美学由于这种新的本体论的奠定,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广义的美学语言释义学从此成为20世纪西方美学的主流,并终由伽达默尔等人的推动,获得了蓬勃的发展。
二
维特根斯坦从另外一条途径开始了他的哲学思考和美学思考。他的哲学就是一种语言分析哲学,他的全部思想就是语言释义学的思想,他的美学就是一种语言分析美学,他是把语言分析美学“推进到决定性转折点上的头一个人”。与其他思想家不同,他是直接从日常语言分析入手开始他的工作的。他在其语言游戏和家族相似的学说中,使近代以逻辑语言和理性语言为“镜子”的反映论遭到了严重打击,使近代美学占传统地位的认为事物有共同的、固定不变的本质主义观点面临着毁灭性的破坏,并以此确立了一种新的美学语言释义学。
他明确指出:“传统思想关于哲学问题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虚伪的,而是无意义的。因此我们根本不能回答这一类问题,我们只能确定它们的荒谬无稽。哲学家们的大多数问题和命题是由于我们不理解我们语言的逻辑而来的。它们是属于善或多少和美同一这一类的问题的。”“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14)维特根斯坦不仅彻底击中了近代认积论的本质主义哲学要害,而且使哲学和美学发生了根本的转向,转到语言释义上来。
他从日常语言分析开始他的哲学批判和美学批判,他说:“我们称作符号、词、句子的东西有无数种用法。我们可以用同样的语言做许多不同的游戏从而使它具有许多不同的意义,我们可以用它来下命令、服从命令,描述一个事件的外表或陈述对它的预测结果,根据一个描述构造一个对象、报告一个事件、思考一个事件、形成或试验一个假设、用图表陈述实验结果、构思和欣赏小说、做游戏、唱歌、猜谜、开玩笑、讲笑话、解数学题、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询问、感谢、诅咒、打招呼、祈祷”,等等(15)。这样,语言就等同于工具,同一个工具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用法,因而就有了不同的意义,这是维特根斯坦的一般语言理论。在语言的这种“游戏”——多种用法中,只有某种相似性,而没有共同的本质性。他举例说:“想一下工具箱中的各种工具吧,有锤子、钳子、锯子、螺丝起子、尺子、熬胶锅、胶、钉子和螺钉。词的功用就和这些东西的功用一样是各种各样的。”(16)然而,我们对词的用法的误解的根源之一,就是这种不同语言领域的表达形式之间的相似性。因为本质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的人总是想通过这种相似性寻找某种共同的本质,而忽视它们的实际状况。因此他们往往只看到共同性,以假的共性抹煞真的个性。特别是在我们从事审美活动的时候。比如有人说“这朵白菊真美”、“这朵红菊更美”时,那些持认识论的本质主义者肯定不会满意,而会说那不过是在举例,而我们追寻的是菊花的美的一般的不变的特征、共性和本质,因为它符合了这种美的共性本质它才是美的。
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的日常语言理论中对这种认识论的本质主义作了更为深刻的批判。他认为追求事物共同不变的本质而轻视其特殊、具体、变化的方面乃是对我们概念的日常用法的误解。因为我们日常对某个概念使用的不同情况中,总有某些相似性,而人们则误认为这是一种共同性。那么如何消除这种对日常语言的误解,从而克服本质主义呢?维特根斯坦要我们“去看,而不要去想”,他认为我们用这种求实而非理想的态度去看待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时,我们就会惊人地发现,在我们用某一名称称呼的各种事物中根本没有什么共同的不变的本质。相反,所存在的只是一种相互重叠、交叉的性质。例如,如果把各种游戏进行比较:网球、篮球、象棋、扑克等,我们就根本找不到同一个共同特性总是在每处游戏中都能重复出现,它可能在第一种游戏中具有,第二种游戏则不具有,而第三种游戏则又具有。这种交叉的相似在多子女的家族中则表现得特别明显:弟弟和哥哥可能完全不相像,而妹妹和弟弟则又可能很相像,但不能说它们就相等。因此,“游戏”只是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游戏”这个名称本身。这种相互重叠、交叉的类似性,维特根斯坦称之为家族相似,“因为家族成员之间的各种相似性,如体格、体形、眼色、步态、气质等等方面的相似性是以同样的方式重叠交叉的。所以我们说游戏形成了一个家族。”(17)然而,维特根斯坦着重说明的是,在一类包含着同一个概念的事物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的、不变的、本质的东西,而只存在相似性,而且只是重叠、交叉的相似性。他用纺线作为例子来说明。我们把一根根纤维绕在一起,但线的强度却不是因为有一根纤维统贯其长,相反,是由于许多纤维的重叠,重叠的类似性,绝对不是传统认识论的本质的共同性。
游戏强调语言是活动的一部分,或者生活的一种形式,并非概念的形式和理念本质的表达,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不能为任何一个词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18)如果我们要研究象愿望、思考、理解、意指等词的用法时,我们应满足于描述一些愿望、思考等实例。如果有人说,这肯定不是人们称作愿望的所有东西,我们将回答,确实不是。但是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构造更复杂的实例,而且没有一类确定的特征是所有愿望的实例共有的。另一方面,如果你想为愿望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即为它划一个明确的界限,那么你要怎么划就怎么划;但你划的这个界限永远不会与实际的用法完全重合,因为这种用法没有明确的界限。因此,词的无数用法的“多样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一旦有了就永远存在的,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新的语言,新的语言游戏,而另外一些要遭到废弃,被人遗忘。”(19)我们可以把语言看作是一座古老的城市,这里有大街小巷、新旧房屋。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新的建筑出现了,一些老的建筑则消失了。因此,虽然我们用同一个名称称呼这个城市,但它开初时的面貌与现今的面貌已经很不相同了。而从另一方面说,由于同一个语言表达或表示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城市面貌,它的用法也就表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看到,我们称之为‘句子’或‘语言’的东西并没有我们原先设想的形式上的统一,而是或多或少相互联系着的结构的家族。”(20)
由此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家族相似性和活动性打破了索绪尔的语言系统概念的封闭性,使人类语言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通过语言用法的多样性、变化性来否认事物有固定不变的、共同的本质,而强调事物的实际的具体变化的发展的方面。面对传统美学的本质主义,“在寻求自己的解决问题办法时,分析美学把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和‘家庭相似’学说作为方法论上的钥匙。”(21)语言游戏和家族相似在分析美学中不仅起着方法论的和启发的作用,它也是解决美学问题的原则的依据。分析美学的主要特点之一就表现在,它的方法和原则都是在日常语言实践具体问题的语言学研究中形成和实现的。“因此,这个或那个理论家选取问题时,无论是美学范畴(赖尔),艺术中的表现力(鲍乌斯马),还是艺术定义问题,都不是从哲学美学的角度,而是从具体语言学的角度来阐释的。”(22)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维特根斯坦得出了如下三条结论:1.整个哲学的云雾凝结为一滴语法(23);2.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3.哲学工作主要由解释构成(24)。
维特根斯坦的结论无疑是个石破天惊的结论,他把全部的哲学和美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释义学,语言释义成了哲学和美学的逻辑起点,语言释义也是哲学和美学的本体论基础,他的工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正如伊格尔顿所说,“从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到当代文学理论的二十世纪语言革命之标志,是承认意义不只是用语言‘表达’和‘反映’的东西:它实际上是被语言所创造的东西。并不好象我们有了意义或者经验,然后我们进一步替它穿上词汇的外衣,首先我们之所以有意义和经验是因为我们有一种语言使两者可以置于其中。”(25)维特根斯坦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让人们懂得,语言不是思想驯服的、可塑的工具,它能够使思想歪曲、走样,坑骗不经考虑就随意使用的人;意义不是某种以语言表达或者反映的东西,意义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语言既可以是创造的力量,也可以是破坏的渊薮;美学不是其它,就是审美活动和语言释义本身,而这些审美活动和语言解释只有相似性而没有共同性,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共同性,那就是审美形式的相似性,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本质特征,那么这种相似性就是。这是20世纪美学语言释义学的基本精神。
三
维特根斯坦的这种美学的语言释义学本体论与海德格尔哲学美学的语言释义学本体论的共同特征在于他们都坚决反对传统认识论的本质主义本体论,都以语言释义学为方法,都认为哲学和美学就是一种活动——语言释义活动,都强调意义的变化性、发展性和可能性,都把人(此在)放在突出的地位,并以此形成一种“主体——客体”、“人——自然”互相联盟的新观念,即没有纯粹的客体,也没有纯粹的主体,人和自然代表着一种互相依赖的结构,这种结构最终是一种文化的结构,美学的结构,人的目的是最终的目的,人的胜利是最终的胜利。
同时,我们应该清晰地看到,由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奠定和形成的现代西方美学语言释义学,对整个人类文化具有一种动态的历史的整体人文结构,代表着未来的进步倾向,他们的努力,打击和摧毁了近代认识论的本质主义本体论,但是他们并不否认和拒弃认识论和认识论的成果,他们只是否定和批判把认识论当作人类唯一目的和手段,把认识论的本质主义当作凌驾于人类之上的最高追求,事实上这是不可能也是无法成立的,他们是想要在认识论的基础上把人类文化引向更高、更新的境界,并开创更加无限美好的未来。他们也为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由他们二人奠定开创的美学语言释义学在后现代主义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将在作者的另一篇文章中作出专门的论述。历史已经证明,他们的思想是一种创世纪的思想,他们的工作也是一种创世纪的工作,并且将对21世纪的人类文化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⑥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信》,《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二卷第471、487页。
②③④⑤(11)(12)(1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02、196、197、197、41、43、47页。
⑦⑧⑨⑩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4、69、68-70页。
(14)(24)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4·003,4·0031,4·112。
(15)(16)(17)(18)(19)(20)(23)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92年版,§23、§11、§63、§43、§23、§108、第二部分第11节。
(21)(22)瓦·阿·古辛娜:《分析美学评析》,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63-64、60页。
(25)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75页。
标签:美学论文; 本体论论文; 认识论论文; 存在论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哲学家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现象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