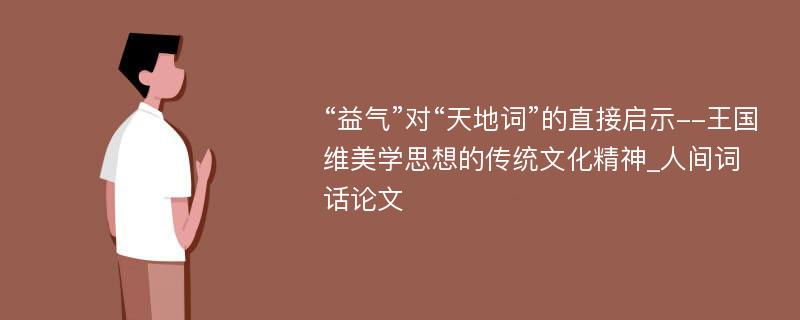
《艺概》对《人间词话》的直接启迪——王国维美学思想的传统文化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话论文,启迪论文,美学论文,传统文化论文,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国维《人间词话》的主体思想是传统文化的结晶,笔者曾著文加以论说〔1〕。 近年笔者在研究中进而发现《人间词话》对清代传统文人刘熙载《艺概》的大量认同。
这种认同首先表现在对《艺概》的引用与沿袭上。《人间词话》多引用前人观点与评词名句,笔者统计了一下,引用者有萧统(昭明太子)、王绩(无功)、晁补之、陆游、朱熹、严羽、沈义父、陈子龙、毛晋、贺裳、朱彝尊、张惠言、潘德舆、周济、刘熙载、谭献、冯煦等〔2〕。大部分提到一次两次,或引用发挥、或批评(居多); 只有朱彝尊、张惠言各提到三次,周济提到四次,而两次是批评,可见对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均有所不满。唯独刘熙载被提到四次,皆为赞许或肯定。足见对《艺概》的推重。《人间词话》还自觉不自觉地发挥过《艺概》的观点。当然,仅仅是引用与沿袭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笔者认为,王氏《人间词话》的哲学基础、美学思想与意境观的理论框架都直接受启于《艺概》,当然,王氏又有创造与发展。
一、“观物、观我”的审美观照论
王国维的境界说有一个基础,这就是他的“能观”思想,他说:
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附录·人间词乙稿序》)
王国维的“能观”即审美观照或审美静观。王氏对此十分重视,在《人间词话》中有七处提到“观”,他自号“观堂”、“永观”,文集也叫《观堂林集》,可以说,“观”即是他的人生观出发点,也是他的宇宙观出发点;既是他的哲学出发点,也是他的美学出发点。那么,这一“能观”思想到底源于那家哲学呢?无可讳言,王氏受到叔本华“直观”思想的影响。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3〕一文中, 王国维说:“叔氏哲学全体之特质,亦有可言者。其最重要者,叔氏之出发点在直观(即知觉),而不在概念是也。”这儿用的“直观”一词,英文为Intuition,指直接感觉,又可译为“直觉”。王氏也说:“吾心直觉五官之感觉,故听嗅尝触,苟于五官之作用外加以心之作用,皆谓之‘Intuition’,不独目之所观而已。”(《论新学语之输入》)〔4〕这与中国式的“静观”是有区别的。与中式“静观”相对应的英语语词为“Contemplation”,指注视、沉思。 叔本华在谈到艺术的认识方法时,就用了静观,观审这样的词语。(如说:“这种眼神既活泼同时又坚定,明明带有静观,观审的特征。”〔5〕)他叙述了艺术的审美观照,他的审美观审法,在主体排除一切欲念,凝神专注于观照对象这一点上,与中国的虚静观是相通的,这使得王国维能够以之为参照,反观中国式的静观理论。但是,叔氏理论中高踞于主客之上的理念,与中国式的观照客体毫无相同之处,中国式的观照客体是活泼的,充满生命力的大自然,是体现自然本体生命的“气”,这正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别所在。当王国维的探究目光凝注在古典诗词意境上时,他不可能用西方的理念来附会艺术中的自然本体,而只能用中国式的物我关系来表述这种审美观照。
“观照”一词古已有之。唐代李华《律师体公碑》说:“于人法得无我,于观照得甚深。”而“观”的观念产生更早。早在《易经》中就有“观卦”,《易经》以八卦象征八种自然物,就是观物而取象。《老子》一书有“涤除玄鉴”说,涤除主体的各种欲念以观照大道,“鉴”即是观照。《老子》还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观复即是观照万物的本源。到《易系辞传》就说:“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古代思想家、哲学家把仰观俯察作为认识事物的一般法则,来进行形而上的思考。到了魏晋时期,这种哲学上的“玄鉴”被引进审美领域,产生了审美静观。宗炳说:“澄怀观道”(《宋书·隐逸传》引)、“澄怀味象”(《画山水序》)。从“道”到“象”,看出从哲学领域走向审美领域的轨迹。而陆机说:“佇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情曈曈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文赋》)。已经注意到审美观照时的物我两端。唐代意境论兴起,观照理论进入意境领域。王昌龄讲诗有三境:物境、情境与意境。又讲诗有三格,其中“生思”一格为:“心偶照境,率然而生”(《诗格》)。这就强调了观照与意境的密切联系。后来张彦远论画也说:“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历代名画记》)刘禹锡说:“虚而万景入。”(《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苏轼说:“空故纳万境。”(《送参寥师》)这才是王国维观照理论的源头。正是在这些前人总结的基础上,王国维明确指出:“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强调了在审美观照阶段的物我交融,把这种观照过程等同于意境创造过程。即从这点看,王氏的能观思想也是传统的。
王国维把观照又进一步划分为“观物”与“观我”,这一观点西方绝对没有。王国维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中虽也大谈“观我、观物”,却不是叔氏的原话,只能认为是王国维的理解与发挥。“观物、观我”说来自刘熙载。刘氏说:
学书者有二观:曰观物,曰观我。观物以类情,观我以通德。《艺概·书概》〔6〕
而刘氏这一观点又来自《易系辞传》: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刘氏所说的“观物以类情”即《易系辞传》的“远取诸物”、“以类万物之情”;“观我以通德”即《易系辞传》的“近取诸身”、“以通神明之德”。从《易系辞传》到刘熙载到王国维,这一条线索标明了“能观——观物、观我”理论的具体发展轨迹,由此可见王氏能观思想的渊源所自。
下面我们分别论述一下“观物”与“观我”思想的发展过程。
“观物”一词出于《礼记·礼器》:“无节于内者,观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礼,弗之得矣。”《礼记》一书出自西汉,发挥了儒家伦理思想。《礼器篇》所说的“观物”,强调内修,从而达到察物之明,不具有冥观思索的形而上内容,其贡献在于提出了“观物”这一名词。而此前,《易经》中早已出现了“观物取象”的思想,《老子》的“观复”,战国中期宋钘、尹文的“毋先物动, 以观其则”(《管子·内业》),都发展了《易经》的观物思想,后出的《易系辞传》以“仰观俯察”作为认识世界的一般法则,是古代观物冥思的哲学认识论的成熟。此后,“观物”思想由宋人加以发挥,邵雍有《观物》内外篇,以“观物”为篇名。他以理学家的心性之学谈观物:“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尽管偏颇,却成为《易系辞传》到刘熙载、王国维的中间一环,尤其王国维发挥改造他的“以我观物”、“以物观物”观点,使观物又具有两个不同角度,在审美领域揭示出观物与境界的对应结构。
“观我”一词出现很晚,到明清有人以“观我”名堂。(明丰城李材“观我堂”、清丹徒唐培英“观我斋”。)在“观我”一词出现前,古人有观身、观心之说。《老子》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以身观身,以家观家。”这是《易系辞传》“近取诸身”的更早源头。《老子》、《易传》以后,还是邵雍对此作了发挥,他说:“以心观身,以身观物,治则治矣,然尤未离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则虽欲相伤,其可得乎?”(《伊川击壤集序》)可见,观我指观身与观心,即身心两个方面。问题是“观我”的主体为谁?有人认为是叔本华的“纯粹而无意志的主体”,这显然不合于古典诗词中的意境。王国维说:“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他的观我,是以我观我,是反观自身,是一种内观照,是我观我心。前人对“我与我”的关系早有表述。庄子说:“吾丧我。”(《齐物论》)东晋殷浩说:“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世说新语·品藻》)王国维同时的词论家况周颐也说:“我与我温存。”(《蕙风词·双调望江南》)前一个“我”都是化身事外从而反观自身的我。刘熙载的“观我”亦如此,只是偏重于心灵的道德方面,还不是纯粹审美的。王国维的“观我”是一种审美内观照,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新的境界:“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六)
由此可见,王国维的“能观——观物、观我”理论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哲学之中,其源头为《易经》、《老子》与《易传》。在哲学方面由邵雍揣摩体会,在审美方面由宗炳、陆机、王昌龄、刘禹锡等发挥创造。到清后期,刘熙载首先总结,他发挥《易系辞传》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吸收后出的“观物”与“观我”概念或名词,概括为一对审美范畴,较好地总结了古代静观理论。王国维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尤其吸取了刘熙载的研究成果,以西方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为参照,把能观思想提到审美认识论与艺术创造论的高度来理解,同时对观物与观我这对范畴作出内涵的界定,丰富和发展了古代静观理论,使之成为他的意境理论的出发点。
二、物我相应的境界类型论
王国维从他的“能观——观物、观我”理论出发,考察物我关系,建立了他的境界类型理论,这是他对古代意境说的重大贡献。可以说,王氏对意境理论的贡献不在于“拈出境界二字”,而在于从“能观”出发,对境界类型的划分。在《人间词话》中,他从不同角度把境界划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对应,“写境”与“造境”的对应。研究者大多认为出自西方美学思想,其实并没有深究其渊源。
我们先看王氏对“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表述:
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三)
显然,这是从不同的观物角度开发出的一对境界类型。而要搞清“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来历,首先要搞清“有我”与“无我”的出处。钱钟书在《谈艺录》之《白瑞蒙论诗与严沧浪诗话·附说二十二》中认为“破我之说,东西神秘宗之常言。”他大量列举东西方破我之说,恐怕是当今在破除我执方面论述最详尽者。钱氏致力于东西方文化的打通工作,其所列举注重东西方文化的共性。但是,从他列举的大量条目中,我们仍然看到,西方古代无一人用“无我”、“有我”这一对概念。只有东方佛教经典《瑜珈师地论》、《宗镜录》、《大般涅槃经》及佛法“三法印”中有此说法。可见“有我”、“无我”这一对概念出自佛教。前引唐代李华《律师体公碑》也说:“于人法得无我,于观照得甚深。”显为“三法印”语。唐诗人孟浩然以禅入诗,也有“会理知无我,观空厌有形”之语,可见唐代“有我”、“无我”这对佛家语十分流行。钱氏所举还有《关尹子》一书云:“道无人无我”。《关尹子》还说:“枯龟无我,能见大知;磁石无我,能见大力;钟鼓无我,能见大音;舟车无我,能见远行。故我一身虽有智有力有音有行,未尝有我。”《关尹子》为宋人伪书,虽为道家著作,《四库提要》谓其多佛家语,从前引诸语可以看出道教对佛教观念的移植。宋代理学也从佛教禅宗吸取思想,故程颢说:“以物待物,不以己待物,则无我也。”(《遗书》十一)邵雍说:“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观物》)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与理学已经从观照角度来谈“有我”与“无我”了,当然,他们还是在宗教、哲学领域来谈;而把“有我”、“无我”移植到审美领域的是刘熙载,他说:
太史公文,如张长史于歌舞战斗,悉取其意与法以为草书。其秘要则在于无我,而以万物为我也。(《文概》)
陶诗“吾亦爱吾庐”,我亦具物之情也;“良苗亦怀新”,物亦具我之情也。(《诗概》)
代匹夫匹妇语最难,盖饥寒劳困之苦,虽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无间者也。(《诗概》)
刘熙载已经从审美角度来谈物我关系。他所说的“物我无间”,与王国维的“意境两忘,物我一体”(《人间词乙稿序》)同意。他的“无我,而以万物为我”,“我亦具物之情”,与王氏“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无我之境”有相通之处。他的“物亦具我之情”,与王氏“物皆著我之色彩”的“有我之境”相近。刘氏的缺点在于,第一,虽然谈到“物我”、“无我”,但是没有直接与境界联系起来,更没有据此划分境界类型。第二,没有把观照与物我联系起来考虑。这使得他的观点显得支离散乱,没有系统化,没有脱离诗话体例的范囿。但是他启发了王国维,王国维在他的论述基础上,进一步把“有我”、“无我”与观物,类型相结合,天才地区分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前者是“以我观物”,后者是“以物观物”,表现了理论思考的周密与系统。
我们看王氏另一对境界范畴:写境与造境: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二)
王氏指出造境与写境是理想与写实二派所由分,似乎毫无疑问出自西方。但是,在《艺概》中仍然能找到近似的阐述:
书当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谓书肇于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复天也。(《书概》)
刘熙载所讲的“肇于自然”即王国维的“写实”,“造乎自然”即王氏的“理想”。前者是王国维所说的“客观的”、“知识的”,“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后者是王氏所说的“主观的”、“感情的”、“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见《文学小言》)〔7〕前者是物(景),后者是我(情)。或者可以说,前者是再现型艺术,后者是表现型艺术。刘熙载就书法立论,而古代绘画、雕塑、书法以及文学都开始于再现自然。中国的书法、绘画一直到唐五代仍然是再现型艺术。孙过庭在《书谱》中说:“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张怀瓘也说:“同自然之功”,“得造化之理”。王维论画,也说:“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画山水诀》)都强调表现自然物的本体与生命,表现其形神与气力。这就是汉代蔡邕讲的“肇于自然”。唐代以前,这是真理。宋元以后,绘画书法理论来了一次革命性飞跃,从重再现转入重表现,把山水景物作为抒发内心情感的手段,逸品开始出现,并居于最高品位。逸品与神品、妙品的区别在于:神、妙二品着眼于再现自然,而逸品则着力表现画家本人的生活情趣与人生感受,倪云林认为“聊以写胸中逸气”(《题自画墨竹》)。神、妙二品仍是肇于自然,立天定人;而逸品是造乎自然,由人复天。刘熙载对书法艺术的总结是准确而简约的。缺点仍然是没有明确以之分属于两种境界,使他在《艺概》中所谈的意境、境界没有与观照物我相挂靠,体系性不强。而王国维正是在刘熙载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这一挂靠。他直截了当地以“造境”与“写境”两种境界来概括“造乎自然”与“肇于自然”。“写境”是“观物”的产物,他说:“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造境”是“观我”的产物,“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他又说:“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这也就是“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王国维所举西方“写实”与“理想”二派,在这儿显然是一种参照。
综上所述,王国维的两对境界类型既有天才的独创性,又有内涵的继承性,它们无一例外地源出于古代文化哲学,而刘熙载正是连接古代文化与王国维美学思想的桥梁。
三、“忧世、忧生”的审美情感论
王国维强调“以物观物”的“无我之境”,标举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句,似乎并不重视情感的强烈表达;实际上,王氏对人间情感并不疏远,他的词集名《人间词》,充满了忧世忧生的人间情感。他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序》)〔8〕《人间词话》中也说:“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删稿·八)古代诗哲往往表现出这样的两难心态,一方面醉心于“物我两忘,离形去智”的最高精神境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正视人生的诸多苦难。所以王国维尽管以“无我之境”作为艺术的至境,却又意识到这是很难达到的,“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所以他的审美注意实际常常系结在“有我之境”上。在对“有我之境”的情感体验中,他建立了自己的“忧世、忧生”审美情感观: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二五)
以词中忧世、忧生的句子来比照类似的诗句,显然有所本,这所本就是刘熙载的话:
大雅之变,具忧世之怀;小雅之变,多忧生之意。(《诗概》)
王国维所举的“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出自《小雅·节南山》,正是刘氏所说的“多忧生之意”的“小雅之变”。可以看出,王氏“忧世、忧生”的情感观直接源于刘氏《艺概》,因此也就是源出于传统文化。
检视传统典籍,我们发现“忧世”一词出自《庄子》。《骈拇篇》说:“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尔雅翼》疏解道:“庄子称‘今之君子,蒿目而忧世之患。’今蒿细弱而阴润,最易栖尘,故以比蒿目,言世之君子,眯眼尘中而忧世也。”庄子主张出世保生,反对为仁义而牺牲生命,蒿目忧世的形象从反面描写了儒家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进取精神,具有一种殉道者的悲壮色彩,为庄子所始料不及,而“忧世”一词也就具有了儒家入世的具体内涵。汉代王充《论衡·骨相》说:“辅主忧世”。魏国曹植《王仲宣诔》说:“忧世忘家”。唐代杜甫老年时感叹:“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西阁曝日》)宋代以后,“忧世”一词十分流行,苏轼说:“仲尼忧世接舆狂,臧毂虽殊竟两亡。”借庄子寓言,再次指出忧世是儒家思想。而南宋叶适说:“立志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赠薛子长》)以忧世为儒生的最高志向。可见忧世出于儒家达则兼济的入世思想。儒家的入世怎样衍化成了忧世呢?这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古代社会乱多治少,白居易说:“理安之世少,离乱之时多。”(《序洛诗》)其次,儒家有一种居安思危、朝乾夕惕的危机意识,《易系辞传》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再次,儒家有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自觉地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前。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最后,古代知识分子可贵的使命意识,使得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样,心怀天下的儒者就进一步心忧天下,由入世衍化为忧世。
具有强烈功利色彩的儒家意识形态坚定地规范着文艺思想与文艺创作,他们的忧世意识必然延伸到他们的文艺思想中去。忧世文艺思想的确立在汉代,具体表现在对辞赋的功利要求上。由战国时期屈原代表的《楚辞》发展而来的汉赋,变成了供给封建王侯娱乐的工具,辞赋家被以俳优畜之,在独尊儒术的时代氛围中显得很不协调。为了端正儒家诗教,汉代儒生以解释屈赋为中心,展开了一场文艺大辩论。时间跨两汉,以刘安、司马迁、王逸为一方,而以班固为另一方,先后辩驳,或肯定、或批评,而出发点都在重新弘扬《诗经》所代表的诗教。有趣的是,论辩的结果,都肯定了屈赋的忧国思君。到宋代洪兴祖作《楚辞补注》,就对这场论辩作了总结,他说:“《离骚》二十五篇,多忧世之语”。可见,汉儒的屈赋讨论,实际是确定了儒家忧世的文艺思想。从此,《离骚》被奉为经书,成了忧世文学的压卷之作,而其主人公屈原也就被铸塑成儒家忧世的代表形象,对后世影响深远。
“忧生”观念出于道家保生养生思想。道家考虑的不是政治伦理,而是生命本体。老子的最高范畴是“道”,而他考虑“道”的出发点是“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老子》五十九章)。《庄子》一书更是贯串了保生养生思想,他批评道:“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骈拇》)保生养生的思想出于对生命短暂、无常、不再的忧虑,所以他发聋震聩地呼唤:“死生亦大矣!”(《德充符》)这一观念在当时没有引起世人重视;而到了社会乱离、风衰俗怨,儒家思想没落,而道家及玄学思想兴起的魏晋时代,却被社会普遍接受。王羲之再次提醒大家:“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兰亭集序》)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忧患生命、张扬个性的诗歌:“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古诗十九首》),“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哀哉人命微,飘若风尘逝”(阮籍《咏怀》),“未厌青春好,已观朱明移,戚戚感物叹,星星白发垂。”(谢灵运《游南亭》)从汉末古诗到晋宋文人诗,充满这一类忧叹,这一文学自觉在文艺思想上的规范即是对忧生主题的总结。刘宋时期的谢灵运在《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并序》中概括曹植的创作情感,说:“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忧生之嗟。”生平经历了宋齐梁三朝的江淹也在《自叙传》中提到:“宋末多阻,宗室有忧生之难。”此后,距南朝时代不远的唐初学者李善注释晋诗人阮籍《咏怀》诗,也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文选注》)他们的总结准确地描状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情感主流,并以曹植、阮籍作为这一情感主流的创作上的代表。从此,“忧生之嗟”成了古代抒情诗忧患情感的一个方面,吸引着后代诗人的注意。
中国古代抒情诗以忧患情感为主体。白居易在《序洛诗》中说:“愤忧怨伤之作,通计古今,什八九焉。”而近代王韬从作者角度总结道:“古人著述,大抵为忧患而作。”(徐继畬《瀛环志略》跋)钱钟书进而概括为“写忧而造艺”(《管锥编》)。这种忧患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忧世与忧生,前者出于儒家的入世意识,后者出于道家的保生意识;前者指向外在现实,后者指向内在生命,从而包容了古代文化的两大意识形态,成为古代抒情诗的两大情感主题。同时,由于儒道两家思想的对立与互补,忧世与忧生情感也就形成了对立互补,起伏消长的律动,展现出古代抒情诗的情感流程,并进而演化出一部忧患情感为主体的忧患诗歌史。但是古人对此并没有清醒的认识与总结。由于儒家思想的强大覆盖,古人大多忽视了忧生情感的存在及其价值,而以忧世作为忧患意识或情感的唯一内容,因此,也就没有人把忧生情感与忧世情感合并考虑。一直到清代后期刘熙载才第一次提出了忧世与忧生情感的对立格局,而他的发现也只是局限在《诗经》中变风变雅的情感表达上,还不具有普遍意义。王国维接过刘熙载的这一对范畴,首先将其范围扩大,从《诗经》发端,中经汉末古诗,下到宋词,使得忧世与忧生这一对范畴可以概括整个古代抒情诗的情感。同时,由于《人间词话》核心理论为意境,而意境又包括“景”与“情”两大原质,这种忧世与忧生的情感观就自然进入到他的意境说中,成为其中“情”之一端,使得他的意境观更充实、更完美,更具有对古代意境说的总结意义。
四、文学批评观——以宋代词家为例
《人间词话》可以讲是以词为起点、为范例来阐释自己的美学观点,因此它有大量对历代词家的评价,尤其是对两宋词家的批评。总起来看,王国维尊北宋而抑南宋,似乎于常州词派为近;但是在具体词家评价上,他说:“于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于北宋喜永叔、子瞻、少游、美成,于南宋除稼轩、白石外,所嗜盖鲜矣。尤痛诋梦窗、玉田。”(附录《人间词甲稿序》)这又与常州词派异旨。常州词派后劲周济主张“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在对吴文英词的态度上,可以看出王国维与常州词派的不同。比较起来,王氏同意刘熙载的词学观。古代诗论中有一种类比的评诗法,王国维也以宋代词人比唐代诗人,他说:
北宋人如欧、苏、秦、黄,高则高矣,至精工博大,殊不逮先生。故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南宋惟一稼轩可比昌黎。而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昔人以耆卿比少陵,犹为未当也。(附录《清真先生遗事尚论》)
这一段话可以认为是王氏宋词批评论的总纲,可以据此研究他的词学批评观。而这一段话虽有自己精到见解,亦有所本。刘熙载说:
柳耆卿词,昔人比之杜诗,为其实说无表德也。余谓此论其体则然,若论其旨,少陵恐不许之。(《词曲概》)
词品喻诸诗,东坡、稼轩,李、杜也;耆卿,香山也;梦窗,义山也;白石、玉田,大历十子也。其有似韦苏州者,张子野当之。(《词曲概》)
比较王、刘二人的批评观,可以看出,他们对唐诗的看法是一致的,比如对李、杜评价最高,这可说是历代诗家的共识。而从宋词评价看,第一,以何人比诗中李、杜,这是词论家的立足点。刘、王以苏轼比李白,可谓恰当。苏、李二人无论从处世态度、人生处境还是从作品风格看,都有惊人的相似。而对于词中老杜为谁?刘王二人都颇费踌躇。首先,他们一致认为柳永不能比杜甫:“昔人以耆卿比少陵,犹为未当也。”(王国维)“柳者耆词,昔人比之杜诗,为其实说无表德也。……若论其旨,少陵恐不许之。”(刘熙载)那么,当推举谁呢?王氏认为是周邦彦,但这是他后期的看法。刘熙载十分鄙薄周邦彦,他说:“美成词信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个‘贞’字。”“周旨荡而史意贪。”(《词曲概》)这是以人品概词品,是传统的伦理批评方式,合于刘氏经师身份。前期王国维接受刘氏观点,他不但转引了刘氏“周旨荡而史意贪”语,而且说:“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三二)后来王氏再次研究周邦彦,摆脱传统伦理,以其“精工博大‘(注意:“精工”一词亦出刘评)比杜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其实,在前期,王氏就称赞过周词“叶上初阳”句“真能得荷之神理”(三六)。这是因为王氏以纯粹审美的意境观评词,尤其以“无我之境”为最高境界,这种“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物我合一境界,在周词中常能发现,这埋下了王氏后来高评周词的种子。当然,王氏对周词的评价还是表现出前后矛盾,这反映了他在伦理与审美标准之间的两难心态。第二,对于辛弃疾,刘王二人都评价很高。刘氏评为词中老杜,这是从忧世的情感内容方面的评价。王氏对辛词亦十分推重,认为南宋一人,并且说:“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四三)这与刘氏所说:“苏、辛皆至情至性人”(《词曲概》),如出一辙。王国维比较苏辛,认为“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四四),实际亦源于刘氏。刘氏亦以豪、旷评诗,如说:“东坡、放翁两家诗,皆有豪有旷。”“退之诗豪多于旷,东坡诗旷之于豪。”(《诗概》)又说:“稼轩词龙腾虎掷”(《词曲概》),可见也是主张苏旷辛豪的。第三,对于柳永词,刘王一致认为可比诗中白居易,这是因为在“俗”之一点上,柳、白相类。刘氏这一观点并不高明,而王氏也认同。
另外,王国维喜欢冯延巳、欧阳修、秦少游词,这一点也受到刘熙载影响。首先,刘氏认为:“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词曲概》)晏、欧词乃宋初词代表,故王氏说:“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十九)其次,刘王都高评秦观词,认为胜过晏几道。刘氏说:“少游词有小晏之妍,其幽趣则过之。梅圣俞苏幕遮云:‘落尽梅花春又了,满地斜阳,翠色和烟老。’此一种似为少游开先。”(《词曲概》)而王氏引用刘氏语,并说:“小山矜贵有余,但可方驾子野、方回,未足抗衡淮海也。”(二八)也认为小晏不及少游。
凡此种种,均可看出两人词学批评观的接近或一致,也可以说,王国维受刘氏词学观点的影响。当然,两人也有不少相异的观点,如对姜夔、张炎的评价。
注释:
〔1〕参见拙文《传统文化与王国维境界说体系》, 载《文史知识》1993年第5期;《对王国维“隔”与“不隔”的美学认识》, 载《文艺研究》1993年第6期。
〔2〕王国维《人间词话》,包括樊志厚《人间词》甲乙稿序、 《清真先生遗事尚论》摘要,均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蕙风词话·人间词话》。樊序,赵万里先生认为乃王氏自作。下引只注条数。
〔3〕〔4〕〔7〕〔8〕见《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周锡山编校,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5〕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 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63页。
〔6〕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下引只注分概。
标签:人间词话论文; 王国维论文; 文化论文; 艺概论文; 美学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易经论文; 老子论文; 读书论文; 刘熙载论文; 关尹子论文; 儒家论文; 国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