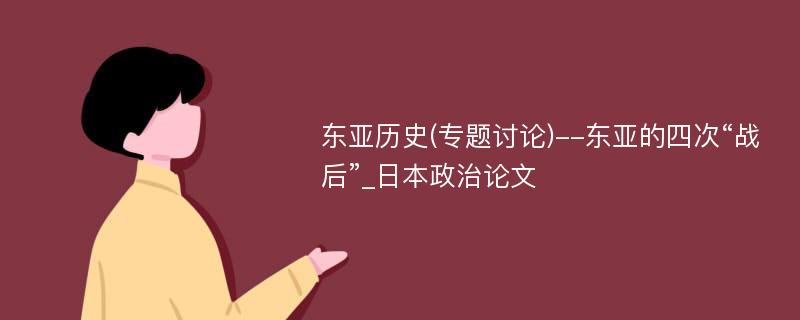
東亞歷史記憶(專題討論)——近現代東亞的四個“戰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專題討論论文,東亞歷史記憶论文,戰後论文,近現代東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近現代歷史上,東亞國家尤其是日本先後經歷了日清戰爭(即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亞洲太平洋戰爭(簡稱“二戰”)。這四個不同的“戰後”,不僅導致日本內政發生巨變,也引發東亞格局產生巨變。本文試圖通過分析這四個不同的“戰後”性質,來對這種巨變作初步的理論探討。 一、甲午戰爭的戰後 甲午戰爭的爆發,在日本一方看來,是日中之間圍繞朝鮮王朝的國際地位而引發的武力衝突事件,因此戰後簽署的《馬關條約》第一條規定:“中國認明朝鮮國確爲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國。故凡有虧損其獨立自主體制,即如該國向中國所修貢獻典禮等,嗣後全行廢絕。”以清朝爲宗主國的東亞朝貢冊封體制宣告終結,爲以獨立主權國家爲單位的近代外交制度創造條件。 但是,它並未給該地區帶來對等的國家關係。通過《馬關條約》,日本獲得了從清朝割讓出來的與該戰爭無直接關聯的臺灣及澎湖列島,開始了向帝國周邊地區的殖民統治。①而實現了“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國”的朝鮮,又受到日本的支配和干涉;日俄戰爭後,更是被日本以“合併”之名而亡國。可以說,甲午戰爭同時也是日本帝國化和殖民統治的開端。 正因如此,甲午戰爭是重新繪製近代東亞政治地圖的巨大轉捩點。在當時日本人心目中,這場戰爭的結果動搖了以中國爲中心的東亞國際秩序,確立了自身作爲“文明國家”的霸權;較爲典型者如福澤諭吉(1835-1901)認爲,甲午戰爭“是努力文明開化的一方與妨礙其進步一方之間的戰爭”②。而在戰敗國朝鮮和中國,則因甲午戰爭引發了正負兩面的複雜反應。其中一點就是,朝鮮和中國臺灣的民衆爲抵抗日本軍事統治展開了長期抗爭,令日本統治者苦不堪言。 與此同時,日本的勝利也成爲朝鮮和中國體制改革的契機。朝鮮爲向內外宣示自身獨立,於1897年10月成立大韓帝國,開始實行名爲“光武改革”的系列近代化政策。中國則因戰敗,變法的呼聲高漲,1898年的“戊戌變法”令改革熱潮達到頂峰。以全面改變舊體制爲目標,強化君權的自上而下的改革,雖遭到守舊派和日本的干涉而短時間內夭折,卻成了近代國家形成的“原點”。值得關注的是,在19世紀至20世紀初的東亞國際秩序中,出現了類似的君主立憲制的帝國鼎立狀況(大日本帝國、大韓帝國、大清帝國)。1899年9月,大韓帝國與大清帝國簽訂了平等的通商條約,並互派常駐使節,形成了近代條約關係。 在此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日本的民主化是與軍國化同時進行的。作爲勝方的日本獲取了清國三億日元的戰爭賠款,加上清國贖回遼東半島的三千萬日元,合計獲取了三億三千萬,一舉改善了日本政府的財政狀況。該數字也遠超戰爭所花費的數額,日本由此獲得了戰前國家收入(八千萬日元)近四倍的賠款。③不用說,其中的大部分(兩億八千萬)都用在擴充軍備上了。陸軍計劃將六個師團擴充到十二個,海軍也開始着手建造基於“6—6艦隊”方案(6艘鐵甲艦,6艘一等巡洋艦)的大型船舶,財源均來自清國的賠款。“戰後”的日本開始以俄國爲假想敵,迅速走向軍事大國之路。 同時,日本政府(藩閥)與政黨(民黨)的關係也因戰爭發生了很大變化。戰爭以前,政府與佔議會多數的在野黨爲軍費預算爭論不休,互相對立;經過戰爭中的政治休戰後,彼此的相互依存關係得到增強。結果就是,自由黨等在野黨的參政之路得以開拓,1900年成立了以伊藤博文(1841-1909)爲黨首的“立憲政友會”。但這並非意味着政黨政治的實現,政府和政黨的關係依然處於微妙的對立狀態。從藩閥的政黨化和政黨的藩閥化這點來說,甲午戰爭使得日本議會政治的民主化得以先行一步。④這種民主化的背後,是日本國民受勝利刺激後,對政府對外擴張政策的支持。而獲得了擴軍所需的巨額賠款後,藩閥—政黨聯合政權又開始積極地推動軍國化。 二、日俄戰爭的“戰後” 日俄戰爭是日俄爲爭奪在中國東北的霸權而起的戰爭。作爲主戰場的中國代表,雖提出要求但竟未被邀請參加朴茨茅斯和平會議。決定“戰後”秩序的,是日本、俄國以及從中斡旋的美國。尤其是戰勝國日本的自我存在感,自此戰役後飛速高漲。此後,日本政府和軍隊在民衆的帝國意識的鼓舞下,進一步鞏固了其在朝鮮和“滿蒙”的獨佔地位。 “戰後”出現的新潮流,可概括爲內政與外交的一體化。這可以說主要是輿論的抬頭和強硬化。具體而言,日俄戰爭後的日本,通過議會和媒體發佈的輿論(公論),獲得了左右政府所推出的內政、外交諸政策的新的力量,有時甚至還起到先導性作用。沒有民意支撐的政權,其運行也將變得困難。從這個意義上講,重視民意是民主化進展的體現。另外,從其確立了民意是外交的後盾這樣的體制來說,重視民意也可以說是“國民外交”的萌芽。 對日本而言,日俄戰爭無論從財政還是兵力來看,均非甲午戰爭所能比擬,是負擔沉重的角力戰和消磨戰,最後都要依賴納稅人即農村地主負擔,徵兵對象也是農民。而且,募集軍費需要不斷的增稅,使得擁有選舉權人數在日俄戰爭期間猛增了四倍。與此相應,隨着社會對普選要求的呼聲漸高,1911年衆議院通過了普通選舉法(貴族院否決)。由此可見,國民的政治話語權逐漸增大。⑤這也可以視做由戰爭推動民主化的一個案例。 而且,民主化也是與帝國對外膨脹的欲望表裏一體的。“對內立憲主義,對外帝國主義”(浮田和民)這個當時膾炙人口的大正民主綱領,是日俄戰爭後不久,民間團體發出的對外強硬論,它反映了此時期社會意識的巨大變化。的確,“戰後”開始抬頭的民衆的對外強硬論,將不被現有政黨接受的龐大城市下層民衆作爲“國民”看待,借助其政治能量,開始朝着確立舉國一致的立憲制邁進。⑥而且,“日比谷燒打事件”(1905年9月)所引起的民憤,也與上述對外強硬派所持的國民主義的政治要求聯結起來——圍繞和談問題的強硬言論,不僅停留在批評未能獲得賠款的“軟弱”政府,而且在更大的帝國擴張的目標下,與貧困和失業中掙扎的國民要求參與政治的呼聲產生更深層次的共鳴。⑦ 民衆因戰爭勝利開始追求更進一步的對外擴張,並支持發動下一次戰爭。從這層意義而言,日俄戰爭可謂是帝國日本膨脹主義的“原型”(prototype)。不僅如此,“對內立憲主義,對外帝國主義”的論調不但被輿論所認可,更廣爲當時政治高層人物所讚同。就連桂太郎(1848-1913)這樣的藩閥政治家,在“戰後”也決定成立新黨(立憲統一黨),主張實現更多的國民參政。此事說明,在日俄戰爭後,上述“對內立憲主義,對外帝國主義”的理念成爲了官民共有的、強力的國民目標。⑧此期間,雖有部分有識之士批評領土擴張和殖民統治,並主張“小日本主義”(石橋湛山和三浦鐵太郎),但大多數日本人還是積極支持帝國日本的膨脹,甚至有時發出比政府還強硬的言論。 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後” 1914年爆發的世界大戰,是以歐洲爲主戰場的。東亞方面除青島戰役外⑨,並無直接交火。儘管如此,日本和中國均加入協約國參戰,並以戰勝國身份出席和談,在許多“戰後”問題處理上成爲相關主體。 決定東亞“戰後”國際秩序的,是1921-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會上主要討論裁軍和中國問題,會後締結的《九國公約》中也提出要尊重中國主權及領土完整,並確認了中國市場的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原則。這雖然未否定日本在“滿蒙”的特殊權益,卻也牽制了日本在日俄戰爭後日漸加速的對華攻勢。將日本獲得的山東半島權益歸還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協調下支援中國發展,是“戰後”秩序的基調。此外,爲遏制海軍擴張,各國還締結了主力艦持有比例的《美英法意日五國關於限制海軍軍備條約》,從而暫時遏止了日俄戰爭後日本追求的軍擴路綫。在此會議上,日英於1902年締結的同盟關係也遭廢棄。由此,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國際秩序迎來了被稱爲“華盛頓體系”的安定時期。日本外交亦順應該體制,進入了以國際合作、重視經濟、不干涉中國爲核心的“幣原外交”時代。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體制變革,對日本、中國、朝鮮都帶來巨大影響。這不僅體現在戰時體制的繼續和延長,也包括觸動了席捲世界的新理念和意識形態。具體而言,有威爾遜(T.W.Wilson,1856-1924)的《和平條款十四條》和共產國際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綱領》,包括和平主義、人道主義、世界主義、民族自決、社會主義、民主主義等,都成爲引導改造國家和解放社會的新理念,席捲“戰後”東亞。無論是日本的大正民主,還是中國的五四運動,抑或朝鮮的三一獨立運動,以及殖民地臺灣的議會設立請願運動等,雖然運動的意義不盡相同,但都是受這樣的戰後理念驅動而產生的民衆運動。 日本“戰前”和“戰後”的最大變化,是甲午戰爭以來民主化與軍事化相互促進的關係在“一戰”中中斷,開始了“沒有軍事化的民主化”⑩。華盛頓體系給日本在中國大陸擴大權益套上了緊箍。另外,在殖民地臺灣和朝鮮不斷發生以民族自決和民族解放爲目的的大規模抗議運動,令日本殖民統治中的“武斷政治”面臨巨大挑戰。統治者在殖民地言及“自治”和“文治(文化政治)”等詞,也是“戰後”纔有的事情。行使武力和佔領殖民地,無論在道義還是法律上都不再有正當性。此種世界形勢下,殖民地臺灣、朝鮮的反日民族主義不斷高漲,帝國日本的統治體系面臨根本上的改變。 日本民主化也迎來了全盛期。此處所說的民主,是指普通選舉制、政黨政治和兩大政黨制。普通選舉制自甲午戰爭後得到提倡,相關法案曾多次在議會上提出但馬上又被否決。進入大正時期(1912-1926),隨着吉野作造(1878-1933)的民本主義一時風靡,議會也迎來了將其法制化的機運。受此影響,1925年,護憲三派內閣正式通過普通選舉法,並於1928年在衆議院議員選舉中首次實現了男子普通選舉。此外,“一戰”中的1918年,以立憲政友會總裁原敬(1856-1921)爲首相的首次政黨內閣正式成立,並在1920年中期將政黨政治作爲“憲政的常道”固定下來。 但是,日本對“戰後民主”的反動卻出人意料地提前到來。這一方面是由於軍部對華盛頓體系下的裁軍不滿,另一方面是因爲1929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大蕭條和經濟的區域化。1931年發生的“九一八事變”,預示着軍部開始獨立自行其事。1932年“滿洲國”宣佈建國,1933年日本退出國際聯盟等,則明顯違背了“一戰”後確立的華盛頓體系,是日本“脫離戰後體制”的開端。(11)由此,一直作爲“一戰”後體制基調的非軍事化方向開始被完全逆轉。更爲重要的是,1930年中期以後,多數國民開始對彷徨不定的政黨政治感到不安,對貧富差距感到不滿,開始偏向對外強硬,並對“暴支膺懲”的呼聲產生共鳴。最後選擇脫離“戰後”的,恰恰是日本國民自己。雖然也有石橋湛山(1884-1973)等自由主義者對“滿蒙領有論”提出批評,但在大多數人都支持一舉解決“滿蒙特殊權益”的背景下,前者的聲音則顯得過於弱小。 隨着1937年中日開戰和接下來的國家總動員體制,日本本土和殖民地均開始通過戰時動員推行社會兵營化。在殖民地臺灣和朝鮮,則推進皇民化運動,甚至強行要求與本土一樣地參拜神社和獎勵改名等精神層次的一體化(同化)。“滿洲國”甚至先於日本施行了經濟統制,構建以重化學工業爲核心的國防國家思想。 四、“二戰”的“戰後”與去殖民地化 1945年8月,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佈戰敗;此後六年多的美軍佔領,迅速推動了日本的非軍事化和民主化。“戰後”日本經過佔領期的多項改革,第一次實現了自明治以來軍事化和民主化的完全分離(“一戰”後的裁軍衹是局部的非軍事化),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完全放棄了殖民地和佔領地的非軍事化。可以說,民主化、非軍事化與去殖民地化的同時進行,纔是“戰後”日本的出發點。與中國、朝鮮不同,“戰後”一詞之所以作爲規定自己的認識架構並發揮強力的統合功能,其原因便在於此。 當然,戰時體制和戰後體制之間也並非沒有任何聯繫。雖然“國體”變成了象徵天皇制,但同時又重新規定天皇是“日本國民的統一象徵”,因此,戰前和戰中的權威基本秋毫無損地得到繼承。日本國民也未嚴格追究昭和天皇(1901-1989)的戰爭責任(雖說部分是美國佔領政策的考量結果)。另外,作爲戰時體制中的一些計劃管制體系,如傾斜生產方式在戰後的經濟復興政策中也得以延續。“1940年體制”論則認爲,戰時的勞資關係、金融政策和官僚體系都得以延續下來。但是,戰時體制並非整體上全部過渡到戰後體制。必須指出的是,戰前和戰後在總體上是不連續的,消除戰時體制的努力,在戰後改革的一系列過程中都可以明顯觀察到。 轉而看東亞國際關係,其最大問題在於“冷戰”這一新的戰時體制的出現,導致日本原有的“去殖民地化”問題完全被非軍事化問題沖淡了。(12)因此,經過戰敗和美軍佔領期,1952年恢復“獨立”後,除部分知識分子外,去殖民地化問題對日本國民而言已擱置起來,漸漸稀釋了。在“和平與民主主義”的新時代,戰後民主觀念在社會深深扎根,使得帝國時代民主化所內含的殖民地主義責任被忘卻。這既可以解釋爲什麼會出現“沒有敗給中國”、“甲級戰犯的責任是戰敗責任(不是戰爭責任)”等歷史認識,也可以說是戰後日本去殖民地化的局限。(13) 隨着“冷戰”結束,被封殺的去殖民地化課題又作爲徘徊在東亞的幽靈復活了。由此帶來的是,“冷戰”結束這一新的“戰後”。如果說1931年是近代日本“脫離戰後體制”的開端,那麼,1980年是不是現代日本“脫離戰後體制”的開端呢?新的“脫離戰後體制”要走向何方?爲了不再讓悲劇和鬧劇反復重演,人們需要做些什麼? “二戰”中的日本人高唱“東洋和平”,卻陷入了戰爭泥沼;2015年的今天,高唱“國際貢獻”的日本卻在內閣主導下朝着“積極的和平主義”方向修改憲法解釋。對仿佛再次置身於新的“戰前”之中的日本人來說,重新探究已經歷過的“戰前”和“戰後”關係,在“戰後”七十年之際,其意義變得愈發重大。 ①近年研究中一個有力的觀點是,批准並交換《馬關條約》文書(1895年5月8日)後,日本派去佔領臺灣的軍隊,與臺灣民主國軍、抗日義勇軍之間發生的“日臺戰爭”也算作甲午戰爭的一部分[[日]大谷正:《日清戰爭》(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4),第242—244頁]。 ②[日]福沢諭吉:“日清の戰争す文野の戰争なり”,《時事新報》1894-07-29。 ③[日]阪野潤治:《日本近代史》(東京:築摩書房,2013),第251頁。 ④[日]三谷太一郎:《近代日本の戰争と政治》(東京:岩波書店,1997),第36頁。 ⑤⑥[日]三谷太一郎:《近代日本の戰争と政治》,第43、250頁。 ⑦[日]櫻井良樹:“日露戰争後の日本——‘大國民’意識と戰後ナショナリズム”,《“岩波講座”東アジア近現代通史第2卷:日露戰争と韓國併合(19世紀末-1900年代)》(東京:岩波書店,2010),第293頁。 ⑧[日]千葉功:《桂太郎——外に帝國主義,內に立憲主義》(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2),第233頁。 ⑨1914年1月—11月,日軍、英軍對德國租借地中國膠州灣的攻略戰。 ⑩(11)[日]三谷太一郎:《近代日本の戰争と政治》,第56—59、59頁。 (12)[日]三谷太一郎:《近代日本の戰争と政治》,第76—77頁。 (13)劉傑:“終戰と日本の責任認識問題——蔣介石政府と汪兆銘政府をめぐっこ”,《1945年の歷史認識——〈終戰〉をめぐる日中财話の試み》(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9),第3—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