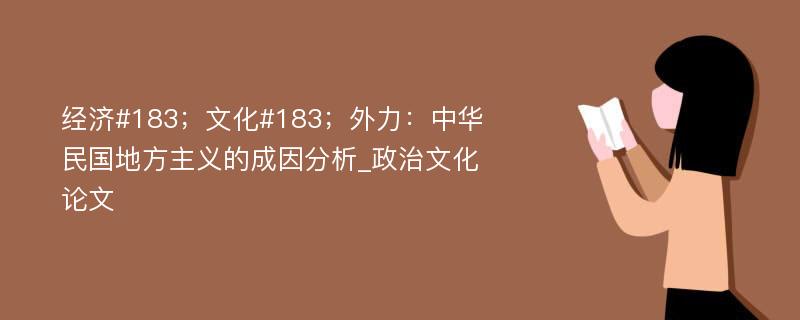
经济#183;文化#183;外力——民国地方主义成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方主义论文,探析论文,外力论文,成因论文,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地方主义极端化的发展,无疑是民国社会的一大特征。那么,民国一代何以形成如此强烈而持久的地方主义呢?对此,学术界的研究尚显薄弱,论者触及到这一问题时,大都援引毛泽东的论断作说明,即毛泽东于1928年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就“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各派新旧军阀之间的战争)所指出的,“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应当说,毛泽东的这种总括性分析是正确的,我们应对此加以深入细致的分解,此外,还应进行多方面的透析。
一、两种经济的共同作用
“一切的主义,都在物质上经济上有他的根源”,(《李大钊选集》,1版,2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和政治行为的地方主义也自不例外,不仅“地方的农业经济”仍是其主要的经济基础,而且地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包括地方官僚资本和地方民族资本两部分)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着它的物质力量。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表明,以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即地方的农业经济或小农经济),在政治上,一方面需要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大一统的中央皇权作为保护伞;另一方面,又直接为大一统下地方主义的政治局面提供经济上、物质上的可能。这种经济在民国一代仍占着绝对的优势地位,因之依然成为民国一代地方主义盛行的主要经济基础,其根本的体现就是,田赋成为省县地方政府所私有的财政上的主要源泉。同时,这种经济在民国一代的某些变化,也更有利于以省区为主体的地方主义政治局面的形成和维系。自然经济的最大特征,就是其自给自足性。马克思指出:“自然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马克思:《资本论》,中文1版,第3卷,8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在古代中国的地主制经济中,做到从生产资料到消费资料的自给自足,从空间区域上,“大体相当于过去采邑的一个乡里或邑县,包括这一地区的地主、农民、各种工匠、手艺人,还有小商人”,(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1版,21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亦即自然经济的“本经济单位”。这种情况,自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后在不断地改变着,最突出的就是农业经济的日益商品化。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将中国封建时代的自然经济强行纳入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自然经济的基础不断遭到破坏,即家庭手工业和农业日趋分离,自给自足性减弱,转而越发依赖于市场。从商品化的程度上看,1934年孙晓村撰文指出:“农产商品化已成为目前中国农村普遍的而且统治的形态,这是无疑的事实”,“中国农村中农民经济的商品性,在任何地方都不低于百分之四十,即是说,农民出卖自己的生产物不少于百分之四十,并且在市场帮助之下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也不少于百分之四十”。(孙晓村:《中国农产商品化的性质及其前途》,载《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参考资料》,(1),174~17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编印,1982。)从地域空间上看,自给自足性的减弱,即地方性的减弱;而地域扩大,即从生产到消费的“本经济单位”扩大,市场的扩大。较大的区域性市场普遍增多,尽管还难以作出准确的统计,但是,民国一代各省区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城镇的出现,应包含着这一方面。当然,农业经济的商品化所造成的亦仅仅是市场的扩大,地域的扩大,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从空间上扩
大了的市场仍“带有地方的性质”,“不但作物不同的各区域间,农产物的价格常会悬殊过甚……甚至在同作物的区域中,也有这样的情形”。(同上书,第179~180页。)一般说来,这种扩大的地方市场都难以彻底突破省区的限制。农业经济在民国一代的这种变化,无疑为地方的自立开辟了田赋之外的又一财源。民国一代地方政府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这一类。30年代许涤新发表《捐税繁重与农村经济之没落》一文,指出:“捐税之苛细,除了繁重的田赋附加税之外,最明显的要算关卡之林立,交通税之勒索了。这些捐税,有的提高肥料的价格,增加农产物的成本,有的加重农产物的运费”。(同上书,第235~236页。)另一方面,与此相联系的是,这种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下的农业经济的商品化,非但没有带来农村的繁荣和农民的富裕,相反造成广大农村的凋敝和农民的贫困破产,从而为地方的自立提供了充足的兵源,“许多没有出路的破产农民,不做土匪便投入军队,成为中国雇佣性军队的主要泉源”。(张锡昌,孙晓村:《民元以来我国之农村经济》,载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1版,358页,南京,银行学会编印,1948。)
“地方的农业经济”也是地方主义思想观念的经济根源。农业经济高度的离散性和封闭性,使人们的生产和社会生活局限于一个狭小的地域空间,形成狭隘的视野和浓厚的地方心理观念。诚如冯和法在《农村社会学大纲》一书中所说:“农村人民因受环境的支配,遂造成了特殊的心理现象。……他们生活的中心完全是他们所处的地方单位;他们对于他们地方内的邻居,彼此间是面对面的直接关系,故能互相了解。他们对于别地方的人,是以地方为单位的。”(冯和法:《农村社会学大纲》,1版,41页,北京,黎明书局,1931。)这种地方心理观念的政治化,便形成地方政治意识。民国一代,地方的农业经济虽已多有变化,但毕竟占据主要地位,因此,依然是民国地方主义思想观念的经济根源。
从理论上说,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地方主义的大敌,它所要求的统一市场是与地方主义相悖的。当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具备了强大的实力后,必然要在国家政治上改变地方分立的局面。然而,民国一代的实际情况却是,资本主义经济虽有所发展,但步履蹒跚,始终未能成为主要的经济形式。它也因之未能摆脱地域的限制,而带有明显的地方性。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没有形成一体化,而受到地域的分割。主要表现为,在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两种经济成分中,除中央官僚资本和少数跨省区的大的民族资本(相比而言,实际也具有某些地方性)外,在各省区大量存在着地方官僚资本和地方民族资本,即地方资本主义经济。它与地方主义政治形成一种矛盾复杂的关系,既对地方主义有冲击的一面,又有支持的一面。
地方官僚资本是直接为地方集团及首脑人物或其地方政权所拥有的企业,一般谓之“省营”企业。它本身就是地方主义的一种经济基础,它的存在也直接体现着地方主义。地方官僚资本的“省营”现代工商、金融企业,已日益成为地方集团增强自身经济实力、对抗中央的一种经济手段了。40年代初,为对抗中央的所谓经济统制,地方集团纷纷成立省企业公司,统一经营其地方官僚资本企业就是明证。再以个案为例,刘航琛以刘湘的“策士”和“理财家”的身份,成为四川地方官僚资本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不仅在四川的地方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投资甚多,而且尤为四川地方金融界的第一人。1942年,他“目击中央系之四行两局势力的逼迫与川帮资本之摇摇欲堕”,遂“将其控制的较为紧密又较为有力的美丰、和成、川盐及川康平民四行组织起来,叫做川省小四行,以与中央之中、中、交、农四行对立”。(《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情况资料》,1版,65页,北京,中国现代史料编辑委员会翻印,1957。)同时,从地方官僚资本在地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看,尽管不同时期不同省区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大,并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乃至具有某种地方独占性。抗战前的广西,在地方资本主义经济中,地方官僚资本占全部资本的83.06%,地方民族资本则只占16.94%。进入40年代,云南地方官僚资本的两大财团,即缪系(缪云台)和陆系(陆子安)的势力,几乎渗透了云南的金融、财政、贸易、工矿、交通、合作事业和农田水利各个部门,垄断了云南的经济命脉,独占了市场。地方官僚资本在地方资本主义经济中占统治地位,使地方资本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强化地方主义的基础作用。
地方民族资本对于地方主义政治的作用较为复杂。我们在指出它同地方主义相悖,同地方官僚资本有矛盾,对地方主义有冲击作用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它的存在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亦有利于地方主义政治的维系。一方面,客观上,不管地方民族资本是否愿意,都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它自身的弱小和先进性,必然成为地方主义的掠夺对象,而增加着地方主义的一份经济力量。另一方面,主观上,地方民族资本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尤其为对抗中央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压迫,极力寻求地方主义的政治保护,因之对地方主义政治亦给予某种程度的支持,体现在地方民族资本的某些发展符合地方主义的政治需要,当然更包括财政上的直接供给。事实上,民国一代地方民族资本同地方官僚资本和地方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地域与经济性质、形态的相同,有时难以把地方民族资本和地方官僚资本断然分清,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方民族资本家亦常常亦商亦官,有时成为地方集团中的一员,如卢作孚及其民生公司是刘湘一手扶持起来的,卢氏也由此成为刘的部属。可见,当一种先进的经济形态尚处于弱小时,它受制于现存政治形态是必然的。同时,它对现存政治形态的某种支持亦是必然的,尤其在外部环境更为不利的情况下,这种支持作用亦越发明显。民国一代地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对地方主义政治的作用,就属于这种情况。
二、两种文化的不同影响
民国一代是中西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碰撞、交融的时期,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不免或多或少打上这两种文化的印迹,本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地方主义亦自然受到它们的不同影响。
从传统文化上看,民国的地方主义与古代的地方主义有着历史的承继关系。在传统政治文化中,中央本位的大一统观为历代先贤所阐扬,是影响最大最深的政治学说。但大一统观被赋予至尊的地位,本身就说明了传统政治文化中还有着与其对立的一面,即地方本位的地方主义。虽与具有完备理论形态、光明正大的大一统观相比,地方主义实在是相形见绌,晦暗不清,但它确确实实存在于古代中国社会,并成为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另一面。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每当大一统的中央皇权式微之时,一些平素自行其是的地方诸侯,就走向公开的地方主义,成为“反叛”中央的政治力量。千百年来,国家政治这种分分合合、治乱相继的局面,由此得以延续。民国一代国家政治上的地方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承继了这种政治传统,但也有所不同,那就是大一统观的政治合法性理念——“忠君”已变成“民意”。同时,尽管大一统观的压倒之势,使古代地方主义的政治诉求无法形成理论化、见诸文字的意识形态,我们也应看到,秦代以后,分封制还不时出现,不绝于史。而且,“分封”、“郡县”孰优孰劣的争论亦不绝于书,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视为地方主义意识形态的曲折反映。马端临说:“由汉而来,有天下者,未尝不王其昆弟子姓,而名之曰封建。”他又说:“秦罢封建置郡县,自是诸儒之论封建郡县者,历千百年未有定说。”(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75、卷265。)否认地方利益合法性的传统政治文化,使地方主义成为一种无意识形态的政治意识,常常以激烈的政治行为得到体现。这一点,民国一代在相当程度上仍存在着。
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哲学更从根本上制约着民国一代的地方主义。传统文化作为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族)为背景、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其基本的价值取向就是乡土本位、家庭(族)本位和伦理本位。乡土本位实际上就是地方本位,因为一块土地,不论大小,都是空间上的一个地方。在农业社会中,家庭(族)是具有地方性的,即血缘和地缘是合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本位就是扩大了的家庭(族)本位,地方主义(乡土社会中的)也就是扩大了的家庭(族)主义,伦理教化则是地方社会的秩序规范。内圣外王的传统政治哲学也与这些价值观念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孔子在《大学》中提出的著名的“修、齐、治、平”,即“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以及在《中庸》里提出的“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就隐含着由内向外、由近及远,先家后国、先地方后中央的一面。在20年代初的地方主义声浪中,一些抱着先改造地方而后改造国家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主张所带有的某种地方主义色彩,就受到这种传统政治哲学的影响。当时《新山东》杂志的宣言中指出:“大家不要说我们只顾及到山东一域,眼光过于狭小,要知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我们一方面建设新山东,一方面联合国内的同志,建设新中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版,第3集,下册,483页,北京,三联书店,1959。)30年代中期,白崇禧阐释“三自政策”时也说到:“我们的三自政策——自卫自治自给——虽然他的含义及目的,是在求整个国家民族的自卫自治自给,但是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要想整个国家民族能够自卫自治自给,必须要一省先能自卫自治自给。”(《白崇禧先生最近言论集》,1版,118页,桂林,创进月刊社。1936。)40年代初,刘文辉构建其“建设新西康的理论体系”,使用的也是这种政治哲学。他说:“大学一书,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宝典,这是今天人人所公认的。大学上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国’。……古代以中国为天下,古之所谓天下,即今之所谓国;准此推之,则古之所谓国,即今之所谓省。我们本着这种实际的意义,则这句话实即等于‘古之欲明明德于国者,必先治其省’,再把这句话与建国来配合,则又可改为‘今之欲建国者,必先建其省’。这种推论是不会与原意有丝毫差距的。”(《刘自乾先生建设新西康十讲》,1版,82页,西康,建康书局,1943。)
传统文化的地域特征,即地域文化也是民国地方主义的文化背景中一个经常起作用的重要方面。从内容看,主要是在人文心理、民情风俗、生活方式及性格特征等方面体现出来;从地域看,主要以省区或某些跨省区的地域为其范围。它通过对各地方、各省区人们的文化塑造,使之在心理、情感、价值取向乃至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等诸多方面具有一致性,而与其他省区的人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从而使民国一代的地方主义也多少带着各自省区的文化特征,表现出差异性和多样性。对此,刘文辉看得很清楚。他说,一省之内,“大家由文化基础的协调,遂构成心志的共通合一”,“不知不觉中,心理上行为上都容易表现一个相同的类型”,而“一个运动之发生,其初自然是极少数人倡导,继而才有多数人附和拥护,多数人所以愿意附和拥护少数人者,他们所主张的理论必然能够得其心之同然,他们所欲实现的目的必然有裨于其利。在一个环境相同的区域,人与人间利害相关素切,以上两种条件,极易形成,而其他区域的人士,在感觉上便要淡漠得多,所以中国一切运动的发生,力量的结合,常有易带地方色彩者,便是这个原故”。(同上书,第604~605页。)
从西方近代文化上看,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各种政治文化随着民国的建立,得以在中国更加广泛地传播。其中,对于民国地方主义影响较大的当属联邦论、地方自治论和实用主义。
联邦论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中的一种建国理论,它主张由若干成员国如州、邦、共和国等在自愿的基础上联合组成联邦国家。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联邦论已在若干国家成为现实,美国尤为典型。这一理论契合了地方主义的政治诉求(地方本位、地方权力合法化等),在一二十年代的中国颇为盛行,对这一时期的地方主义产生了较大影响。第一,它为这一时期地方对抗中央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第二,它使这一时期的地方主义以漂亮的新概念即联省自治包装起来,公诸于世。联省自治作为联邦论中国化的概念,为章太炎所造,但却大受地方集团青睐,原因就在于它是表达他们地方主义政治主张最合适的词汇。
地方自治论作为国家对地方实行管理的一种主张,在民国一代主要表现为孙中山的理论,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体系中最具民主性的部分,它的来源在西方,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论的一部分。由于它姓“孙”,而成为蒋介石中央政府官方意识形态的一个形式,并是其打击地方主义的有力工具。但是,它的基本精神在于依法确立和行使地方自治权,这一点对地方主义又极其有利。第一,它成为三四十年代地方集团对抗中央和地方自卫的主要旗帜。他们主张的地方自治是省自治,即省是自治单位,实质是他们自治地方。蒋介石中央集团强调县自治的主要目的在于消解省的权力,加强专制独裁,两者都同地方自治论和孙中山主张中的民主精神背道而驰。第二,它为地方集团制造适乎时代的地方主义名词、概念、纲领和口号,提供了理论的支撑和来源,如新桂系集团发明的“三自”政策的概念即源于这一理论。黄旭初对地方自治的认识和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地方集团对这一理论的实际认知水平。他说:“地方自治,从前的封建制度,皇帝把一块地方封给某人,这地方便由他自己去治理,就是现在地方自治一样……不过名称不同罢了。现在要说‘教育普及’、‘土地公有’、‘地方自治’才时髦,若提起痒序、井田、封建便觉得腐败了,究其实质是相同的。就这几件事情看来,现在有许多时髦东西是自己家里有的,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宝藏翻出来;如觉得款式装潢不甚摩登,不妨参以现代的好处,补充进去。”(《黄旭初先生演讲集》,1版,127~128页,南宁,南宁民国日报社,1935。)这真可谓是一个新瓶装旧酒的把戏。
实用主义作为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验论的哲学流派,自19世纪末在美国产生后,影响迅速遍及世界各地,20世纪初传入中国。就整个民国一代的情况看,它也是除马克思主义外对当时中国影响较大的一种西方文化思潮,对民国地方主义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第一,它为民国地方主义提供了一个可资凭借的现时代的具有理论形态的世界观。威廉·詹姆士在其著名的《实用主义》一书中指出:“实用主义代表一种在哲学上人们非常熟悉的态度,即经验主义的态度”,“它趋向于具体与恰当,趋向于事实、行动与权力”。地方主义所需要的正是这种哲学的支撑。不过,在世界观上,我们不能把民国一代地方主义完全归结为这一外来哲学,但是这一形质兼备的哲学理论对地方集团认识现实外部世界的影响还是存在的。1928年,陈济棠在训导所部将领时说:“常人以为理性的目的是‘真理’。什么是‘真理’?这是哲学上打不完的官司。我们现在只能假用大哲学家杜威博士‘此时此地’的议论来解答。那就是说,适合于某一时代某一地方的便是真理”。(《陈总司令言论集》,1版,第4集,38页,广州,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司令部政训处,1933。)第二,它同时为民国一代的地方集团提供了一种理论化的行为指南。对杜威和实用主义大加推崇的阎锡山,他创造的所谓“唯中”哲学,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实用主义的翻版。其核心就是自身的存在高于一切,即“存在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存在”,并成为阎锡山统治山西、对待外部世界、推行地方主义的指针。为了自身的存在,他此一时可以对抗中央,彼一时又可以与之和解;此一时可以联共,彼一时又可以反共;此一时可以抗日,彼一时又可以与之勾结。
中西文化对于民国地方主义的作用,无论就作用的程度和作用的方面,都存在着某种差异性。概括地说,传统文化作用之大、作用的内在性是西方文化不可比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文化是民国地方主义之本源和底蕴;西方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小,并且主要是外在的,为民国地方主义提供了某些外表样态。两种文化作用所反映的问题也不一样,传统文化的作用体现了民国地方主义发展的历史承继性;西方文化的作用则体现了民国地方主义发展的时代性。
三、外力的复杂作用
这里所说的外力即外国势力,民国一代,主要是指帝国主义列强,它是民国地方主义政治演变的外部环境。帝国主义列强多种方式的侵略,对于民国一代地方主义产生着极其复杂的作用。
从经济侵略上看,主要起着增强地方主义经济、物质力量的作用。在不能灭亡中国的前提下,帝国主义的侵略,说到底是经济侵略,即从中国榨取更多的物质财富。为此,他们以种种手段施行之。首先,帝国主义列强划分势力范围,分割中国市场,强化了地方主义存在的经济环境。诚如孙晓村在30年代中期所说:“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近百年来在中国所做的工作,便是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推进更广大的侵略。依据帝国主义自身间的矛盾,这割据的形势因竞争关系而日渐扩大;所以帝国主义在中国国内市场之创立的工作上,亦有推进与各地方的结合的倾向,然而同时也在进行破坏以前联系很弱的统一的国家,划定他们各自的市场,使中国的国内市场于政治上封建性的割据外,又受到一重更顽强的阻力,而后一种工作实超过于前者,最显著的是日本之在华北,英国之在华南,法国之在云贵等省,美国之在长江流域一带,他们彼此之间的结合(如华北与日本),较诸国内市场之间的结合,还紧切得多。”(《中国近代农业史参考资料》,(1),第183页。)其次,各帝国主义在它们的势力范围内,通过对地方集团的借款、掠夺地方原材料的贸易及直接投资设厂等侵略方式,也增强了地方集团的经济力量。据统计,在四川盐务稽核分所(1914~1935)存在的20年间,列强借拨给四川军阀的盐款总数近两亿元。再次,帝国主义对各地方集团的军火输出,也直接增强了地方集团物质上军事上的实力。民国一代,各地方集团的军火,总体上说除一部分是自造外,大部分购自国外,这种军火买卖已成为帝国主义对中国掠夺的一种经常性的手段。30年代,德国在加紧同蒋介石中央政府“合作”的同时,仍同两广地方集团等进行各种军火交易。如1933年德国与两广订立的《中德交换货品合约》,内容为德国向两广提供军用制造设备,建造炮厂、炮弹及火药筒厂、毒气厂、防毒面具厂等,交易额达560余万港元。地方当局自行同外国进行军火交易,本身就是地方主义的行为,它反过来又增加了同中央集团对抗的物质力量。
从政治侵略上看,帝国主义对地方集团的政治分化,更直接造成并加重地方主义的政治局面。挑拨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地方集团进行拉拢、策动,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一项重要的侵略政策,无论是对少数民族的边疆省区,还是对内地各省,都是如此,基本上贯穿民国一代。英国、法国、日本、沙俄等是推行这一政策的主要国家,尤以日本最为突出,已成为其侵华总政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经济、军事侵略相互配合。帝国主义的这种政策对民国地方主义产生了重要作用。第一,一定时期内的某些地方主义政治局面是这种政策的直接产物。抗战前几年间,宋哲元等在华北的地方主义局面就是其中一例。1933年5月,日军参谋本部下达的“华北方面紧急处理方案”中提出:“对华北、华中、华南各方面,分别进行促使其更加分立之施策”,以此为指导展开所谓“华北工作”。“华北工作的终极目的是使华北诸省在政治、经济上从南京政权完全分离自立”,“这一工作的对象,是察哈尔的宋哲元、济南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河北的商震等华北将领”,并以宋哲元为突破口。在这一政策下,日本一方面极力打击在华北的中央势力,一方面对宋哲元等多方拉拢、胁迫。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设立,正是适应日本这一政策的结果。而宋哲元亦就在中央与日本之间均采取两面对策,既抵制又妥协,从中维系自身的存在。对此,斯诺描述说:“宋哲元藉了一连串的平衡动作存在下去,时而讨好于南京,时而讨好于日本人。当日本人要求调走蒋的特务宪兵和解散蓝衣社的时候,宋同意了,人们疑心他是暗中喜欢的。当他们要求他的委员会任用日本顾问时,他照办了,郑重地接受他们的建议,而永不加以实行。当南京方面指责他缺乏社会改革时,他在几个星期内枪决了一百多个毒犯,表示比蒋还积极。”(《斯诺文集》,中文1版,第3卷,11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第二,这一政策也加深了地方与中央业已存在的隔阂,加重了双方的政治对抗。不仅在抗战前是如此,在抗战时期也是如此。例如,日军对于阎锡山进行诱降,阎锡山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防共合作,以打倒蒋介石为基本条件”。蒋介石极力侦知阎日勾结的情况,阎则多方防范。第三,这一政策在一定的条件下,亦会使地方主义走向极端化,即分裂国家。日本在30年代对内蒙古德王等少数上层王公的策动,所造成的分裂国家的局面,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然,这种政策对地方主义的作用并不是绝对的,作用的对象不同,效果及其程度也不同,有*
并未起到上述三种作用,如抗战时期日军对新桂系的诱降,就未见功效。
从军事侵略上看,旨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对民国地方主义具有消减作用。这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中央政府未起来领导反侵略战争之前,一些地方集团公开反对中央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甚至由此造成与中央的政治对抗,而体现为地方主义,但这是积极意义的地方主义;二是在中央政府领导全国抗战后,在反对民族敌人的解放战争中,地方主义有所减弱,而被代之以民族主义。对此,有人曾作过这样的评论:“战争成为民族团结的大熔炉,抗日使国家进入了新境界”,“战前所存在的分崩离析、地方割据的局面,都因为一致抵御外侮而破除了。西北的马家,晋陕的冯阎,两广的李白,云南的龙氏,东北张学良带入关来的东北军,大家都能在中央政府的劝抚安慰下接受号令,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尤其是民国史上最令人满意的表现了”。(王平:《抗战八年》,1版,上卷,158、40页,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
从经济基础、文化背景、外部环境等方面审视民国一代的地方主义,可以认为,它既是历史的产物,更是时代的产物,是民国时期国内外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其在经济、文化、外力中的时代成分尤应加以重视,值得深思。
标签:政治文化论文; 经济论文; 官僚资本论文; 文化侵略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帝国主义时代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宋哲元论文; 农业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