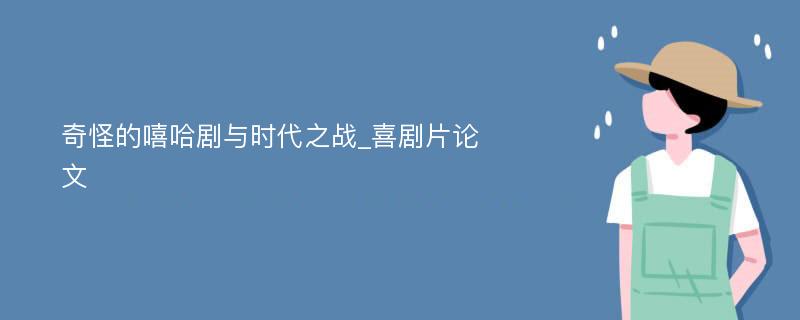
吊诡的嘻剧与时代之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1世纪以来,各种搞笑文化风生水起。从《疯狂的石头》(2006)到《泰囧》(2012),种种搞笑影视的“成功”一度挑起了学界对于喜剧的热情。人们一方面吃惊于这种新型喜剧的“逆袭”,一方面又依照喜剧的原则重新审视这些作品的价值。尽管有论者以“新美学”或者“独特性”命名《泰囧》等作品,但是,仍旧无法摆脱“喜剧”的分析框架。有趣的是,无论怎样调用已有的喜剧理论来命名和分析,21世纪以来的“搞笑”文化连同它所“指向”的时代,却毫不客气地“违背”着“喜剧”的文化逻辑和原则,以一种极其吊诡的方式“表征”当下我们这个时代的“吊诡”。
喜剧:正在发生的未来
之所以说“喜剧”这个概念无法涵盖这些产品,乃是因为这个概念的哲学内涵已经失效。马克思曾经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引用并评述恩格斯的观点时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1]在这里,“笑剧”乃是历史性地告别旧事物的讽刺性的喜剧,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理论来说,人类的历史乃是从悲剧开始,以笑剧(讽刺喜剧)的形式自我否定并进而发展,世界历史的最终形态则是喜剧——人类告别阶级、国家和压迫,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想。
所以,在马克思那里,喜剧并不仅仅是笑剧和滑稽,而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告别旧的制度、合理性的新事物胜利驱逐非合理性的旧事物的特定形式。他在评论“一个德国式的现代问题”的时候这样说:“现代的旧制不过是真正的主角已经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在埃斯库罗斯的《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里已经悲剧式地受到一次致命伤的希腊之神,还要在琉善的《对话》中喜剧式地重死一次。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这是为了人类能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我们现在为德国当局争取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愉快的历史结局。”[2]所以,只有当旧事物不再具有阻遏历史发展的力量的时候,喜剧才会痛快淋漓地发生。
显然,作为一个历史性的美学范畴,喜剧乃是一个充满了信心的时代里面社会情绪自信满满的表达。所谓“告别的年代”,并不仅仅是罗大佑所唱出来的悲伤,也是他对各种缤纷色彩的未来向往和冲动。而喜剧恰好是这种充满向往和期待的未来冲动的时刻。只有在一个“正在发生的未来”的时刻,喜剧才有力量识别什么是“丑”,什么是“美”,才有可能呈现那些无价值的东西被撕碎时刻的快乐与轻松。
就此而言,喜剧所对应的主角“丑”,并不只是现实和历史的否定性力量,更是面向未来生活的肯定性力量;只有在“未来”显露了它的璀璨的曙光的时候,“丑”才不是那样令人恐惧、厌恶和尴尬,才会在它们执着于不肯认输的作为中为我们提供胜利者才会有的快乐。
简言之,喜剧不是指一部可以搞笑的作品那么简单,而是对正在发生的未来的历史的充分肯定和把玩。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说,“喜剧”必然是一个时代的喜剧,每一出喜剧就是一个喜剧时代。
与之相应的问题乃是,“含泪的喜剧”是否也具有这种乐观的告别过去和指向正在发生的未来的能力呢?在卓别林的系列戏剧中,小人物的悲哀挣扎与工业社会的压榨凌辱同时刺激观众的泪腺和笑神经。但是,作为一种典型的喜剧形式,卓别林的含泪的喜剧效果,充满了强烈的批判现实和向往未来的冲动。卓别林对于小人物的滑稽呈现,乃是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沮丧的现实的强烈否定,而这种否定的力量则来自于有能力告别当下和否定当下的信心。从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时代的批判到韦伯对新教伦理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严峻的现实所进行的无情的揭露、剖析和批判,以及建立在其上的超越性信念。如果卓别林电影所建构的是一种充满了悲剧色彩的喜剧,那么,这种“悲剧的喜剧”正是充分调用了喜剧的浪漫和乐观的历史主义精神,调用了喜剧埋葬丑恶腐朽的现实力量的现实主义政治热情。
同样,与喜剧相关的另一个美学范畴乃是“荒诞”,即审美上的尴尬和道德上的两难。作为一种现代主义的特定概念,荒诞更多地表达了个人在高度垄断的资本体制时代的失落和不安。有趣的是,即使是这种失落和不安,也是对于更加美好和富有现实意义的未来生活的偏执的后果。
显然,喜剧乃是喻示这样一个时代:一个从总体性的角度观看历史和未来的时代,一个洋溢着理想主义情怀的时代,一个信任并敢于创造比当下更美好、更富有人的意义的未来的时代。
嘻剧:否定未来的逻辑的形式
在一首叫做《再见二十世纪》的歌中,汪峰这样唱道:
这是1999年的冬天/从来没经历过的寒冷/街边的楼群直插蓝天/人们都蜷缩在大衣里行色匆匆/我坐在深蓝色的车里/摇摇晃晃行驶在狂野的城市/太突然了一切都将消失/橘色的幻梦褪色的爱/再见,二十世纪/再见,我一样迷茫的人们/阿甘说生活是一块巧克力/我想也许他是对的/一个女人说生活是孩子和房子/我想也许她也是对的/上帝说生活是救赎和忏悔/我想也许我是个罪人/我从五岁歌唱到现在已经苍老/现在还是两手空空像粒尘土/再见,二十世纪/再见,我一样迷茫的人们
这首歌对20世纪的告别既不是悲伤的也不是乐观自信的,而是茫然和衰败的。如果生活只剩下“巧克力”、“孩子”与“房子”,乌托邦的未来冲动也就毫不犹豫地远离。在汪峰的歌唱中,我们读到了既不是灰心丧气也不是悲怆苍凉的意绪,而是纠结中的无奈与妥协。“他”或者“她”是对的,这种无奈的句式,不再是感叹,而是轻轻的承认:承认这样一种只有当下没有未来的现状,承认只有关心日常生活的油盐酱醋茶而不去思考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的意识,也就是对“搞笑”的“时代精神”的勉强而毫不客气地认可。
在这里,如果我们把新世纪以来崛起的搞笑文化看作是笑剧或者喜剧的话,那仅仅是因为看到了这种文化引发笑容的生理功能;反之,我使用“嘻剧”这个概念命名这种文化,乃是因为“嘻剧”不仅仅作为一种发笑的机制,更作为一种时代的隐喻,具有意味深长的内涵。
所谓“嘻”,本意是不严肃地嬉笑,在另外一些场合,它表示惊叹。有趣的是,如果我们将这两个词义叠加在一起就会造出一个有趣的词汇:“嘻”乃是满不在乎的吃惊、因吃惊而产生的放肆的笑。所以,“嘻剧”作为一种美学的范畴,指的就是这样一种特定的“时代精神”:人们不再是具有冲向未来、否定旧事物的信心和豪情,更加没有否定过去并创造另一种生活的兴趣,而只是在四处寻找与日常生活不同的故事传奇,并在传奇的惊讶中嬉笑、唏嘘。
所以,嘻剧不再嘲笑“丑”,而是凸现“丑”,不再通过美与丑的对立来强化美的力量,而是通过美和丑的错置,产生震撼性的嬉笑效果。所以,嘻剧在这里就变成了谈论令人惊讶的日常故事里的非日常性事件的嘻嘻哈哈,成了一种凸显每个人生活于当下时刻的捉襟见肘和无所事事的巧妙形式。
在这里,嘻剧分裂成两个层面:一个是停留在当下的传奇性力量的发现,这令嘻剧具有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功能:当下的生活已足够提供给我们好奇和期待——这令嘻剧有充分能力喂养那些被寂寞枯燥的科层制生活围困的人们,令其在窘困的生活中畅想着传奇的浪漫;另一个,嘻剧又总是虚幻地允诺一种当下生活中的未来,允诺在特定的条件下囧人或屌丝逆袭的可能性,从而把人们重新围困在科层制的牢笼之中却备感充实。
在《泰囧》中,异国旅行与富人受困,正是这样一种嘻剧表达的典型体现:“富人”鬼使神差地走了一条“穷人”的路,却又在困窘中被同行者的“穷人道德”所感化,从而彻底实现“身不得穷人列,心却比穷人列”的“公众幻想”。换句话说,电影赋予了“困窘”非常想当然的浪漫内涵:只有在困窘的人生中,人们通过重新体验伟大的困窘生活,才可以重建人的良好道德与品格。
显然,嘻剧的历史哲学乃是这样一种哲学:如果你没有机会体验困窘的处境,你就不可能具有真实的道德感和人性;与此同时,各种糗人糗事和屌丝困顿,也就自然成为当下的“真实”,喻示着生活的沉甸甸的责任和刻骨铭心的经验。
简言之,嘻剧乃是把现实处境中的困顿变成一种精神上的神圣经验,把经济上的贫富分化、政治上的等级固化和心理上的道德俗化,变成了可以在传奇的旅行中随时和随意被改变的东西。正如《泰囧》所表达的那样,嘻剧凸显出当前中国社会上空漂浮着的吊诡的生活观念:人们总是寄望于贫富的差别远远小于道德的差别,从而在道德的优势幻觉中战胜了富人们生活的优越;有趣的是,人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实现不了这种观念的时候,就在嘻剧电影中反复实现它。
所以,简单地说,嘻剧不再以“丑”这种否定着过去并预示着未来的事物为主角,而是以“糗”这种勾连着严肃和不严肃、正经和不正经、底层和上层、穷人和富人的事物为主角。糗不是陈腐的势力在摔跤,而是正经的生活在跌倒;糗不是过去的历史在告别,而是通往未来的大道在消失;糗不再是历史力量较量的场所,而是市侩主义大力叫卖的贩卖场。
吊诡的逻辑与时代之殇
显然,在今日中国,嘻剧成了这样一种形式:它不再把历史看作是进步和发展的历史,而是看作止步于“眼一闭不睁一辈子就过去了”的虚无;反过来说,嘻剧把每一个个体都看作是这个时代的胜利者,无论贫富贵贱,无论东西城乡。嘻剧不仅仅只是一部电影或糗事百科,而直接就是我们当下时代的精神状况的表征。
嘻剧只能发生在生存于丛林化的社会、匮乏抵抗的意志和改造的理想的人们臆想之中。如我此前曾经提到的,一方面,现代中国正在演绎一个极端物化的图景,另一方面,这种极端物化的世界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与之抗衡;一方面,人们对于日益物化的生活逻辑本身认同、认可,并以之为准则——在《泰囧》中,人们毫不犹豫地认可做小买卖的人不仅应该表现得更滑稽可笑,而且他也理所当然地扮演受施舍的角色;另一方面,糗事困窘的旅途中,又总是来自弱小经济族群处在驯化、教育和启蒙的位置,合法地拥有道德优越感。[3]
由此可知,嘻剧的逻辑乃是这样一种吊诡的逻辑:人们越是处在丛林的困境之中,就越是匮乏冲破这种困境的勇气和信心;反之,人们越是匮乏冲破丛林规则的信心和勇气,就越要想方设法让自己相信自己所处的世界并非是一个残酷的世界。嘻剧的诞生正是这样一种“吊诡的时代”诞生的后果:脆弱的社会想象力源于对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信念丧失,而资本机制的压制又令人无法组织起理性有效的批判,从而就不断地在想象中把经济的困顿变成道德困顿、把精神的压抑变成性欲的压抑、把现实的残酷变成人性的残酷。
简单地说,嘻剧是把“困”变成了“糗”,把“卑微”变成了“崇高”,把“富裕”变成了“卑劣”。嘻剧的时代也就自然而然地是这样一种时代:当高速发展的社会在GDP飞速提升的时候,具体的个人却在私人生活的领域中没有能力意识到自己生活日渐困顿的现实;同时,更缺少能力讲述关于历史、现在和未来故事的哲学信念,也就没有能力从总体性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生活、精神的困顿以及人格的分裂。
在这里,想象未来能力的消失,创生了嘻剧这种对未来否定的逻辑;与之相对应,中国社会严峻的“权钱私通”机制造就的资本的流氓化趋势,让人们没有能力和机会秩序化地走向未来或者看到未来,才会滋生这种关于未来的想象力消失的图景。
不妨说,当权力和资本的苟合不能被有效遏制的时候,资本就显露其流氓的本性,四处扫荡而无所不用其极。没有比权钱的私通机制更能养育资本的流氓特性;同时,资本的流氓特性又会搬走人们获得地位上升和个人发展的有序阶梯,最终破坏一个社会的发展激励机制。
正是这样吊诡的时代逻辑,才有了吊诡的嘻剧:嘻剧由此变成了当下中国社会的一种隐喻性形式。人们试图在旅游和传奇中“逃离”,试图通过嘻剧的形式“摆脱”沉重压抑的精神状况,却很少有人懂得,这种“逃离”和“摆脱”恰恰是沉重压抑的体制社会的另一种产业——正如休闲是工作的衍生品,嘻剧也是压抑的衍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