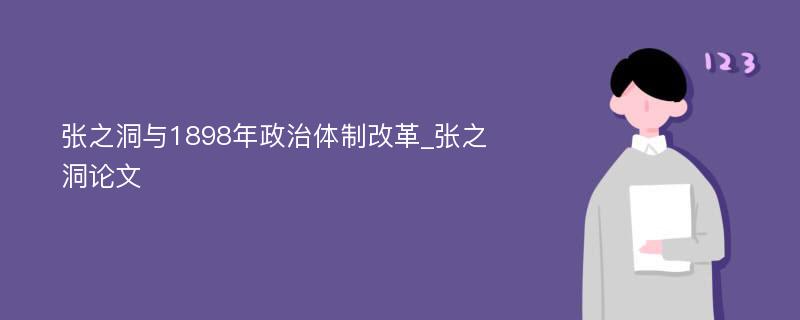
张之洞与戊戌政制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制论文,张之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史学界一般认为张之洞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以“反对议院与民权”的姿态成为维新派的对立面。对这一“定论”,笔者认为尚可商讨。
一、“西艺非要,西政为要”
19世纪后期兴起的洋务运动主要限于采纳西方的军事技术和新式工业,未能在政制近代化方面取得进展,甚至连翻译介绍西方政制的书籍也寥寥无几。时人指出:“中国通专门高等西文者寡,故译书少而劣,而译于兵戎略于政制。”〔1〕梁启超1897 年上张之洞书亦称:“中国向于西学,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2 〕在封疆大吏中,仅有两广总督张树声1884年在遗折中明确提出仿效西洋议院政制的主张。但史学界似乎尚未注意到这一事实:作为封疆大吏的张之洞同样较早地认识到了西洋政制的优越性。张在山西巡抚任上创办洋务局时,于1884年4月拟定的《延访洋务人才启》中即指明, “洋务最为当务之急”,“以商务为体,以兵战为用,以条约为章程,以周知各国物产、商情、疆域、政令、学术、兵械、公法、律例为根柢,以通晓各国语言文字为入门,世用所资,至广且急”〔3〕。 张之洞倡习西洋“政令”、“公法”、“律例”等涉及政制的“洋务”,并以此为“根柢”,足见其对“西政”重视的程度。在甲午战败之际,张之洞更是明确提出了“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 “十倍精于”军事技术的见解〔4〕。可见在戊戌维新运动兴起之前,张之洞虽然未像张树声那样明确提出效法西洋议院政制,但对西洋政制优越于中国政制之处仍有相当认知。
维新运动兴起后,张之洞在代表作《劝学篇》中又提出了政制改革的主张。他说:“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西艺非要,西政为要”〔5〕,“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 ”〔6〕可知他不仅认识到仿效“西政”、 进行政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且从较深层次上看到了政制与文化的相互依存制约关系。至于他主张的变法内容,便有兴学校、变科举、改学制、派游学、译西书、办报刊、变法制、兴实业、修铁路、练新军等等举措。同时,不难看出,在戊戌时期,张之洞主张仿效的“西政”内容,与《延访洋务人才启》提出的“洋务”内容比较,实有一脉相承之处。
张之洞的政制改革模式,可以说是“中教”为体,“西政”为用。他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7〕一句话, 就是在坚持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不变的架构下,除了“西艺”外,还采纳财经、军制、教育、法制等等“西政”。张氏视纲常名教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即“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8〕他希望以此为“体”来采纳“西政”, 即所谓的“政教相维”,但这种“嫁接”难免会出现“橘化为枳”的结果。他之所以有此认知,与其“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9〕的清流本色不无关系,也不能忽视日本明治政制及其成功经验对他的影响〔10〕。
值得指出的是,视纲常名教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在当时的士人(包括维新人士)中,也是较普遍的认识。戊戌以前,“早期改良派”大多主张在坚持中国固有的纲常名教的前提下来采纳西艺、西政。有学者已经指出,“他们在鼓吹仿行西方君主立宪制度的同时,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和维护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11〕。戊戌时期,不少士人亦持这一认识。如戊戌闰三月,因入侵山东的德国士兵滋扰即墨县孔庙,康、梁等人发起了第二次公车上书, 由梁启超、 孟麦华领衔有831名广东举人签名的上书宣称:“夫君臣之义,父子之纲, 孔子所立,若大教既亡,纲常纽绝,则教既亡而国亦从之”,强调“令天下人知君臣父子之纲,家知孝悌忠信之义”〔12〕。在张氏及当时的士人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是儒教,而儒教的核心则是纲常名教,坚持纲常名教则意味着坚持中国的传统文化。大概可以说,这是在面临“西教”对华渗透的严重情势下,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情结〔13〕。
萧公权指出,张之洞是借西学来保存中学(儒学),而康有为则予儒学以非传统的解释,但“康氏与张氏一样坚信尊孔与保教必须与富强维新齐头并进。康有为作为儒家的护卫者可说是与张之洞一样‘保守’。”此论不无见地。唯萧先生认为张氏“借自西学的不过是技器”,而康氏“除西方的科技外更建议变法”〔14〕,则不确矣。张氏借自西学的除“技器”外,更有“西政”,且“西政”尤急于“西艺”,其重心实在采纳“西政”。
百日维新之始,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其宗旨以“圣贤义理之学”为本,而“博采西学”之用,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路数是一致的。百日维新颁行的新政:经济方面保护奖励农工商业,京师设农工商总局,各省设商务局;政治方面允许臣民上书言事,裁撤冗官闲衙;军事方面编练新式陆海军,采取西洋兵制;文教方面设立学堂,提倡西学,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等等。这些举措既属于康有为所赞同的变法内容,也没有超出张之洞所说的“西艺”、“西政”范围。在变法的这一层面上,张氏与康氏实无多大分歧。
二、开议院“今非其时也”
在设议院、兴民权的问题上,张之洞是否与康、梁等“维新派”存在严重的分歧与对立呢?我们先讨论有关“议院”的问题。
论者多将赞许西洋立宪政治、主张设立议院的言论作为判断维新派的标准,但这一标准本身便存在问题〔15〕。甲午战前,以赞许的态度介绍欧美、日本等国政制的有识之士,即包括一般论著所说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林则徐、魏源、徐继畲、梁廷枬等)、“早期改良派”(王韬、薛福成、宋育仁、郑观应等)、出使官员(斌椿、张德彝、郭嵩焘、徐建寅、崔国因、曾纪泽、黄遵宪等)以及“洋务派”(张树声),其中不乏主张在中国设立“议院”者。戊戌维新时期主张开设议院者更是大有人在。如候选郎中陈时政上书主张“上下议院宜亟开设也。泰西议院为立国最良之规模,实有国不易之宏纲”。翰林院撰修骆成骧也上折建言:“窃见当今各国,其政治最善者,莫要于议院;其议院之最善者,莫要于公举执政。今议院未能骤开,则公举执政之法,不可不先务也。”〔16〕出生官宦世家的孙宝瑄在日记中也写下主张“开议院”的言论:“法非不可变,未造变法之机器耳。变法之机器奈何?曰:开民智,兴民学,扶民权。民智奚开?曰:设报馆。民学奚兴?曰:立学校。民权奚扶?曰:开议院。”〔17〕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1898年3月3日)《时务报》第53册发表赵而霖《开议院论》呼吁:“若不急开议院,则上下之情不通,即门户之见不化,又安望有富强之一日耶?”杨锐也曾说:“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18〕可见,“开议院”已经成为当时之流行语,算不上什么惊人之论,时人所争论的不过是采取何种形式、何种步骤来实施的问题。
其实,戊戌维新时期不赞成速开议院的正是康、梁。 梁启超在1896年写的《古议院考》中就曾说:“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故强国以议院为本,议院以学校为本”〔19〕。康有为则讲得更为清楚。1898年1 月他在向光绪进呈的《日本变政考》中指出,三权分立为“泰西立政之本”,三权中以“立法最要”;“民选议院之良制,泰西各国之成法,而日本维新之始基也”;同时又指出,设立议院必须以兴学校、开民智为前提,“故学校未成,智识未开,遽兴议会者,取乱之道也。学校既成,智识既开,而犹禁议会者,害治之势也”〔20〕。在康氏看来,议院应该是体现民权的“民选议院”,而当时民智未开,还不具备开议院的条件;加之守旧势力太大,速开议院必然使变法受到更大阻力。他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国闻报》上发表《答人论议院书》一文〔21〕,甚至强调说,议院“泰西尤盛行之,至国权全畀于议院而行之有效,而仆窃以为中国不可行也。盖天下国势民情地利不通,不能以西人而例中国”,“故今日之言议院、言民权者,是助守旧者以自亡其国者也”,“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他希望借助光绪帝的君权来推行变法。在故宫博物院发现的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也证明康有为那篇著名的变法纲领《应诏统筹全局折》(原名《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局折》)中并没有制定宪法、实行立宪的内容,这些内容是康氏在戊戌政变后加进去的〔22〕。故当内阁学士阔普通武“上疏请开议院,上本欲用之”时,康有为则谓“而今守旧盈朝,万不可行”。谭嗣同、林旭“又欲开议院”时,康氏仍“以旧党盈塞,力止之”〔23〕。
顺便指出,在关于维新派政治纲领与戊戌变法性质的评价问题上,不少学者的研究思路,往往是认为百日维新只有提出定宪法、开议院的政治纲领才足以表明维新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否则便是维新派在政治上的“倒退”行为或“软弱”的表现〔24〕。其实,一场改革运动的政治纲领往往有一个演变完善的过程,并具有阶段性的改革任务及出台举措,故其性质也应该放在一个稍长的历史阶段来加以分析判断。只是由于百日维新仅推行了103天即夭折, 才使研究者的分析判断缩短了视野。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日本明治维新从1868年颁布《五条誓约》,其后推行太政官制度,1885年废除太政官制度,建立内阁制度,到1889年公布《大日本帝国宪法》,正式确立天皇制君主立宪政体,其间也经历了20余年。正如康有为所言:“变法之道,必有总纲有次第,不能掇拾补缀而成,不能凌躐等级而至。经画土地之势,调剂人数之宜,学校职官之制,兵刑财赋之政,商矿农工之业,外而邻国联络箝制之策,内而士民才识性情之度,知之须极周,谋之须极审,施法有轻重,行事有缓急,全权在握,一丝不乱,故可循致而立有效。泰西变法自培根至今五百年,治艺乃成者,前无所昉也。日本步武泰西三十年而成者,有所规摹也。”〔25〕他是仿效日本明治维新,按照开民智、改官制、定宪法、开国会的改革思路“有次第”地推行,故在百日维新前致力于立学会、办报刊,从事开民智的活动;百日维新时,开始推出改官制的举措,在光绪召见和总理衙门大臣垂询时,康有为都强调“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具体举措便是设立“制度局”。至于定宪法、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那是待条件成熟后才能实现的目标,因而他一再声明开议院为时尚早。反倒是后来的研究者希望维新派在百日维新期间就提出开议院的政治纲领,仿佛不如此便难以体现维新运动的进步意义,这多少有违于康、梁的初衷。
戊戌时期,张之洞确是不赞成开议院,但并不等于反对议院政制本身,同样是认为开议院的条件尚不成熟。
张之洞对西洋议院政制也是有所认识的。辜鸿铭在1896年就上书张之洞,介绍西洋议院的演变,“分国会为上下议院,盖欲集众思广众益,达上下之情”;并指明晚近的西洋议院政制也有不少弊端,造成“西洋各国近日政治之所以外强而实弥乱”〔26〕。张之洞则说,“考西国之制,上下议院各有议事之权”〔27〕;“外国筹款等事,重在下议院;立法等事,重在上议院”〔28〕。张氏强调下议院“重在筹款等事”,并非忽视下议院在议院政制中的重要地位。梁启超同样指出,西国“每有应筹款项,皆待命于下议院,下议院则筹之于民”〔29〕。英国学者霍布豪斯(Hobhouse)论述19世纪自由主义在英国的发展时也指出:“我们更多地听见‘无代表,不纳税’的呼声而较少听见‘无代表,不立法’的呼声。因此,从17世纪开始,财政自由就包含着所谓的政治自由。”〔30〕戊戌以前,国人多认为议院是起“通上下之情”的咨询作用,而张之洞已经指明议院具有“议事之权”和“立法”权,其对议院政制的认知水准,大概并不比某些维新人士低。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还不能开议院,一是民智尚未开通:“中国士民至今安于因陋者尚多,环球之大势不知,国家之经制不晓,外国兴学立政、练兵制器之要不闻”;二是缺乏议员人选:“家有中赀者,乃得举为议员,今华商素鲜巨赀,华民又无远志”,故“此时纵欲开议院,其如无议员何?此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31〕。可知张之洞与康、梁同样关注开设议院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因此他同样认为在学堂未兴、人才未盛之前是不能开议院的。除康、梁外,其他维新人士亦持与张氏类似的看法。如谭嗣同说:“学会者开民智也。议院者民智已开之后之事也,界限不可不清也。且其权操之国家,国家即能议行。苟民智不开,议者何人?”〔32〕麦孟华说:“中国文学未昌,风气未辟,民智未开,民事未习,千百乡愚,将成哄市,议院启矣,民能建议以善事乎?不知其不能而强行之,则今尚非时,止足取乱。”〔33〕既然如此,张氏关于开议院“今非其时也”的见解,与康、梁等维新派不速开议院的主张又有多大分歧呢?
三、反对“民权”还是反对“民主”?
张之洞说:“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34〕这些言论似已成为张氏反对民权的“铁证”而被广为征引。窃以为对此言论还有必要置于一定的语境(context)中细加分析。
要了解张氏反对民权的用意,至少应该首先考察一下时人与张氏是如何理解“民权”的。
有学者考证,“民权”一词不见于中国古代典籍,系来自于日文,乃西文“民主”(democracy)的日译, “民权”与“民主”实为同义词,并据democracy源于希腊文, 释“民权”之义为“人民的权力”〔35〕。中文词汇“民权”来自日文当无疑问,但谓即西文democracy 的日译则不确。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考证,democracy 的日译仍为“民主”〔36〕。查《日本语大辞典》及《日本国语大辞典》,“民权”涵义为:一、人民参政的权利(suffrage);二、人民的基本人权,维护人身、财产等(civil rights)。“民主”涵义为:一、人民的主宰者(即《书经》中的“民主”);二、一国主权属于国民(即democracy )〔37〕。可知日语中的“民权”与“民主”仍为涵义有区别的两个词。近代日语中还有复合词“自由民权”,《日本国语大辞典》释义为:“人民的自由与权利”。故“民权”之义,简言之,即“人民的权利”。若释“民权”为“人民的权力”则不确矣,盖“权力”(power )与“权利”(right)在中文中虽仅一字之差,但涵义有别,不难明察。
与“民权”有关联的“民主”一词,在中文中则最早见于《书经·多方》:“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蔡沈《书经集传》注:“言天惟是为民求主耳,桀既不能为民之主,天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使为民主”)。“简代夏作民主”(蔡注:“简择也,民择汤而归之”)。蔡沈《书经集传》作为《五经》之一,在晚清社会具有普及性的影响〔38〕。故在时人的认知中,中国经籍中“民主”之本义虽为“民之主”,但这一“民之主”是由“天”为民求得或由“民”择而归之,这一“民主”也就隐含有“民择主”,“传贤不传子”之义。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和国人在介绍美国政制时就已经注意到了其国元首“不世及”这一特征。1838年,美国教士高理文(Elijah C.Bridgman, 一译裨治文)所刊印的《美理哥国志略》言及华盛顿当选为总统一事时,称“共推华盛顿为首,身后公举贤者更代,不世及,不久任。”魏源在《海国图志》介绍美国“公举一大酋统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39〕19世纪后期中文文献中的“民主”一词多有接近于此义者,时人将美国、瑞士等国由民“选举”(大概被理解为相当于民择而归之)的元首“伯理玺天德”(President)称之为“民主”。1879年5月31日《万国公报》541卷所刊《纪两次在位美皇来沪盛典》云:“篇中所称伯理玺天德者,译之为民主,称之国皇者。”同年5月17 日《万国公报》第539 卷所刊《华盛顿肇立美国》云:“美国虽得自主而尚无人君治理,故通国复奉顿为民主。”可知19世纪后期中文词汇中作为“伯理玺天德”之义的“民主”一词,如《万国公报》中出现的“选举民主”、“民主易人”、“新举民主”、“民主晓谕”等等,与《书经》中的“民主”实有涵义相通引申之处〔40〕。时人常谓西方之“民主”,不过是得中国经籍之要旨精义,往往以“礼失求诸野”之说,为采纳西政之文化认同。鉴于时人对“民主”之义的最初认知,这亦在情理之中。
西文democracy一词源于希腊文,其词根为demos(人民),krate-in(治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云:“我们可以以此作为准则:不容许所有公民共享的制度是寡头的,容许所有公民共享的制度是民主的。”〔41〕19世纪后期中文文献中出现“民主”一词亦有明确具有dem-ocracy本义者,如1875年6月12日出版的《万国公报》340卷所刊《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一文〔42〕,其释“何谓民主国乎?”略谓:“按泰西各国所行诸大端,其中最关紧要而为不拔之基者,其治国之权属之于民,仍必出之于民而究为民间所设也……治国之法亦当出之于民,非一人所得自主矣,然必分众民之权,汇而集之于一人,以为一国之君,此即公举国王之义所由起也。”文中还详细介绍了西方的三权分立和议院制度。该文所说的“民主”的主旨为“治国之权属之于民”,“治国之法亦当出之于民”,正是democracy之本义“人民治理”,即后来所译之“民治”。而“公举国王”不过是“治国之权属之于民”的一种体现形式(并非唯一的形式)。1895年3 月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的《原强》所言“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一语中的“民主”,亦当是西文democracy之意译〔43〕。
19世纪后期国人之使用“民权”往往与“君权”相对应,并认为两者具有互补的关系。薛福成称,“君民共主”之国,“其政权亦在议院,大约民权十之七八,君权十之二三。”〔44〕梁启超说:“君权与民权合则情易通”〔45〕。“民主”一词则常与“君主”相对应,“民主之国”亦与“君主之国”相对应,但两者则有相互排斥的关系,盖因“民主”由民公举,则意味着废除君主世袭制。故时人言“民权”多是指君权与民权互补的“君民共主”政制,言“民主(国)”则多是指废除君主世袭的共和政制〔46〕。何启、胡礼垣曾强调“民权”与“民主”的这一区别:“民权之国与民主之国略异,民权者其国之君仍世袭其位,民主者其国之君由民选立,以几年为期。吾言民权者,谓欲使中国之君世代相承,践天位于勿替,非民主之国之谓也。”〔47〕故当时的“改良派”大多赞同“民权”而不赞同“民主”。郑观应说:“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48〕薛福成说:“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然如美国则民权太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其斟酌适中者,唯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49〕王韬亦称:“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治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50〕陈炽在为郑观应《盛世危言》写的序中甚至说:“民主之制,犯上作乱之滥觞。”〔51〕有学者早已征引上述论说,注意到了“改良派大多数倡‘民权’而反‘民主’”这一现象,惜以为“民权”系西文“民主”之日译,乃同义词,而将时人对两词的不同解释且褒贬不一,视为“一个奇怪的现象”〔52〕。其实,时人对“民权”与“民主”两词作不同义的解释并不奇怪,是有其道理的。
张之洞又是如何理解“民权”的呢?《劝学篇·内篇·正权第六》对“民权”作过如此诠释:“考外洋民权之说所由来,其意不过曰国有议院,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而已,但欲民伸其情,非欲民揽其权。译者变其文曰民权,误矣。(美国人来华者自言其国议院公举之弊,下挟私,上偏徇,深以为患。华人之称羡者,皆不加深考之谈耳。)……泰西诸国无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国必有政,政必有法,官有官律,兵有兵律,工有工律,商有商律,律师习之,法官掌之,君民皆不得违其法。政府所令,议员得而驳之;议院所定,朝廷得而散之。谓之人人无自主之权则可,安得曰人人自主哉?”张之洞理解的“外洋民权”可归结为三个要素:一、实行议院政制(“国有议院”);二、民众有议政的权利(“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三、任何人都要受法律的制约(“君民皆不得违其法”)。他针对有人将“民权”解释为“民揽其权”,“人人有自主之权”,而“犯上作乱”,故对时人所倡言之“民权”持反对态度。不过他所诠释的“外洋民权”三要素,也大致不错,特别是“君民皆不得违其法”的原则,已经有了限制君权的意义。正如霍布豪斯所说:“自由统治的首要条件是:不是由统治者独断独行,而是由明文规定的法律实行统治,统治者本人也必须遵守法律。”〔53〕
上述张之洞的诠释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强调西洋各国“国必有政,政必有法,官有官律,兵有兵律,工有工律,商有商律,律师习之,法官掌之,君民皆不得违其法”,这正是为了说明所谓“民权”应是由各种法律所规定的“权利”。第二,举出美国议院“公举之弊”作为反对倡言民权的理由,又举法国为例证明民主乃迫不得已之事,“昔法国承暴君虐政之后,举国怨愤,上下相攻,始改为民主之国”〔54〕。这些看法恰好说明张氏认为将导致“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的“民权”(即所谓“人人有自主之权”),是指美、法式的“民主”,即陈炽所说的“犯上作乱之滥觞”的“民主”。郑观应所言“民主”的特征乃“权偏于下”,也与(张之洞反对的)“民揽其权”意思相近。
可知时人对“民权”与“民主”既作了不同义的解释,又有人将两者相混淆。《国闻报》曾发表《民权与民主不同说》一文〔55〕专门辨析两词的不同涵义,将“民权”释为“予民以自由而设律以定之”(与张氏所言“君民皆不得违其法”意思相近),将“民主”释为总统,(美国)“权在议院,民主仅供手画押而已”。仅就“民主”而言,时人也有不同的理解,歧义较多。“或谓西国民主之制可行于中国,此非本朝士子所忍言也。……知吾君之不可弃而已,变君主为民主,将置我君于何地乎?此一说也。”“各省会匪其所以号召党与,亦持西人民主之义。民主之说,其可倡乎?”“又有谓民主之义者,非必欲变为民主也,但以减轻君主之压力以伸民气而御外侮,于是而君主安若泰山,是倡言民主之义者,正所以保君权也,此又一说也。”〔56〕难怪梁启超在戊戌后也一再强调“民权与民主二者,其训诂绝异”,不可“混民权与民主为一途”〔57〕;并认为他倡言的“民权”之所以为当道者不容,正因对“民权”的涵义产生了误解,“吾侪之昌言民权,十年于兹矣,当道者忧之嫉之畏之,如洪水猛兽然,此无怪其然也,盖由不知民权与民主之别,而谓言民权者,必以彼所戴之君主为仇,则其忧之嫉之畏之也固宜,不知有君主之立宪,有民主之立宪,两者同为民权,而所以驯致之途,亦有由焉。凡国之变民主也,必有迫之使不得已者也”〔58〕。梁氏所言,自有道理。他之所以反复强调“民权”与“民主”的区别,正是为了表明他主张在中国建立的是君主立宪政制,而非共和立宪政制。实际上,不论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均是西洋的民主政制,皆通过各种法律规范及议院政制来实现所谓的“民权”。此即梁氏所言“两者皆为民权”。对此,曾出使欧美的崔国因早在1892年即已指明,欧美各国政体虽有不同,但都是一种体现民权的民主政制。他说:“欧墨州各国均设议院而章程不同。美之议绅均由民举,不分上下也。英之下议绅由民举,而上议绅则由世爵,然权归于下议院,则政仍民主之也。欧洲除法国、瑞典、瑞士之外,政皆君主,而仍视议绅之从违,则民权仍重。”〔59〕崔氏所言的“政仍民主之”,亦符合democracy之本义。
至于维新派所倡言的“人人有自主之权”一语,其义也不甚明确。何谓“人人有自主之权”?梁启超1896年所写的《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一文解释说:“西人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有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60〕而与张之洞关系密切的王仁俊则解释说:“西人之言曰,彼国行民主法,则人人有自主之权。自主之权者,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守其所应有之义,一国之政,悉归上下议院,民情无不上达,民主退位与齐民无异,则君权不为过重。噫此说也,是其言利也。然不敌其弊之多也。即如美之监国,由民自举,似乎公而无私矣,乃逢选举之时,贿赂公行,更一监国,则更一番人物,凡所官者,皆其党羽,欲治得乎?”〔61〕比较而言,梁氏的解释便不及王氏的明晰。梁氏仅言“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但以什么来作为确定“当为之事”与“应有之利”的法则呢?又以什么形式或程序来实行“人人有自主之权”呢?皆语焉不详。而王氏则认为“自主之权”的前提条件是“行民主法”,“当为之事”与“应有之义”(即权利与义务)相对应,并通过代议制来实现“民情无不上达。”看来,王氏的解释更符合西方民主政制的原则。而王氏强调“民主退位与齐民无异”以及美国公举“监国”之弊,也表明其理解的“人人有自主之权”即是指美国式的民主。虽然王氏因与张之洞关系密切,其文又被收入《翼教丛编》而被视为维新派的对立面,但治史者应尊重历史事实,故不应忽视王氏的这一见解。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张之洞之所以反对倡言“民权”,实是反对将“民权”释为涵义不甚明确的“人人有自主之权”、“民揽其权”,而非反对民权的本义即法律规定的“权利”〔62〕。在张氏看来,“人人有自主之权”或“民揽其权”则意味着将演变为“犯上作乱”的“民主”——这不仅是张氏也是改良派所反对的,并大体符合19世纪后期人们对“民主(国)”的认知,即其特征乃“权偏于下”(郑观应语)、“民权太重”(薛福成语)、美国乃“为民自主之国”、“有民人自主之明例”〔63〕等等。
外来词汇进入中文词汇初期,国人产生误解乃常见之事。“自由”一词在中国的命运便最为典型,常常被误解或曲解为“为所欲为”、“自由散漫”之类。故精通西学的严复在1902年发表的《主客平议》一文中即指明:“自由者,各尽其天赋之能事,而自承之功过者也。 ”〔64〕他既强调个人的权利,也指出个人对社会的责任, 并特意将约翰·穆勒《自由论》的书名翻译为《群己权界论》,正是为了避免国人产生误解。细察张氏之用意,既然其主张采纳的“西政”中已经包括“学校”、“律例”,这就意味着具有这样的潜台词:欲兴民权(法律规定的“权利”)还有待于先行兴办新式教育,采纳西洋法制。
四、“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
在戊戌政制改革中,张之洞与康有为并不是不存在分歧。熟谙晚清史事的陈寅恪曾说:“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65〕此论颇具深意,惜未引起研究者注意。笔者认为两者不同之处主要有三:
其一,是否适当改变清廷的权力结构。在康有为看来,百日维新中虽然不必开议院、言民权,但是改革官制、设立制度局,却是必要的。他主张适当改变清廷的权力结构,让康、梁等维新人士参与朝政,借助光绪帝的“君权”来进行变法。按康有为原来的设想,既要让维新人士参与朝政,又不至于增大“改官制”的阻力,则采取设立新衙门,不撤旧衙门的策略。但一提出“改官制”、设“制度局”,即“流言纷纭,咸谓我尽废内阁、六部及督抚、藩臬司道矣”,“于是京朝震动,外省悚惊,谣谤不可听闻矣”〔66〕。“彼盈廷数千醉生梦死之人,几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其实康不过言须增新衙门耳,尚未言及裁旧衙门也,而讹言已至如此”〔67〕。可见“改官制”阻力之大。
在张之洞看来,既然“外洋民权”的主旨不过是“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就可以在清廷既有的权力结构中,实现绅民的这种权利。他说:“凡遇有大政事,诏旨交廷臣会议,外吏令绅局公议,中国旧章所有也。即或咨询所不及,一省有大事,绅民得以公呈达于院司道府,甚至联名公呈于都察院。国家有大事,京朝官可陈奏,可呈请代奏”。“但建议在下,裁择在上”,“何必袭议院之名哉?”〔68〕他主张仿效的“西政”中,也并无“改官制”之类的内容,较之康有为的政制改革方案,显得保守一些。不过其间也隐含着另一层意思:政制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比康有为“有次第”的变法还稍长。
其二,张之洞反对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1895年11月,张之洞在南京会见康有为时,就表示反对所谓的“孔子改制”,提出只要康放弃此说,便可以为之提供开上海强学会的活动经费。康有为则表示,不能因张氏提供活动经费便改变自己的学说。次年1月, 康有为在上海创办强学会,刊行《强学报》,该报以孔子纪年,封面大书“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与光绪二十一年并列,又发表《孔子纪年说》。这一做法,也引起了张之洞的不快。结果,因《强学报》使用孔子纪年,“见者以为自改正朔,必有异志”〔69〕而受到非难。张之洞授意宣布上海强学会停办,《强学报》停刊,被指责为压制维新派的显例。平心而论,办报的目的本是为了扩大维新宣传,这就需要采取能为更多的人所接受的宣传方式。使用什么纪年,固然具有政治意义,但对宣传维新来说,毕竟还是一个次要的形式问题。因为使用光绪纪年,并不会妨碍维新宣传;而改用孔子纪年,便意味着“改正朔”,即改朝换代,这当然容易为他人所攻击。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一书系统阐发了“孔子改制”理论,他本希望借孔子的旗号来减少变法的阻力,即其所言:“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70〕然而,该书一刊行,便产生了梁启超所形容的“火山大喷火”的效应,引发了卫道士们的强烈不满。与康氏的初衷相违,“孔子改制”一提出来,不但“惊人”,而且未能“避祸”;不仅成为了卫道士们攻击的目标,就连陈宝箴、翁同龢这些赞同变法的官员也认为其说“荒谬”,结果被清廷强令毁版。
以“孔子改制”来宣传变法,在当时的情势下,其效果是惊世骇俗的,其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诚如萧公权所言:“康氏发展孔教的努力除有反效果外,其本身也极不成功。”〔71〕其实,作为一种变法理论,宣传面越广,影响力越大,接受者越众,才是成功的标志。“孔子改制”说除了康氏的若干弟子外,心悦诚服者并不多,而反对者、非议者、不理解者却不少。这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民智未开、守旧者众。严复译述的《天演论》也是在同样的时代和社会中传播的,其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直接抬出英人赫胥黎,并没有把进化论装入公羊学说的框子里,而宣传的实际效果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难怪梁启超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其师当年的做法,也说过一番令人深思的话:“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康有为之大同,空前创获,而必自谓出孔子。及至孔子之改制,何为必托古?诸子何为皆托古?则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72〕梁氏亲身经历体会之言,其意深焉!
其三,采取稳健还是激进的变法步骤。百日维新期间张之洞对改科举的变通便是稳健的一例。
是年3月,梁启超曾上书请废八股取士之制, 其时各省举人将及万人齐集京城参加会试,“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谣言,几被殴击”。6月,康有为先后代徐致靖、 宋伯鲁拟奏折,陈述了八股取士的危害,提出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光绪帝谕令准行。于是“举国守旧迂谬之人,失其安身立命之业,自是日夜相聚,阴谋与新政为敌之术矣”〔73〕。可见改革科举同样面临很大阻力。
张之洞历来是赞成改科举的,早年任学政时,对科举的弊端便深有洞悉,在《劝学篇》中还专门撰写《变科举第八》一章。不过他也深知改科举阻力甚大。梁启超曾记述:“张之洞且尝与余言,言废八股为变法第一事矣,而不闻其上折请废之者,盖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惧其合力发谤己而排挤己也。”〔74〕改科举的诏令下达后,张之洞与陈宝箴联名上《妥议科举新章折》〔75〕,肯定了改科举的必要性,“惟救时必自求人才始,求才必自变科举始”。因康有为代拟的上疏着重揭露八股取士的危害,反复强调改试策论以“讲求时务”,并未谈及具体的实施办法。张之洞由此认为“若一切考试节目未能详酌妥善,则恐未必能遽收实效”,遂提出了八股当废,四书五经仍作为考试内容的折中方案;主张变通科举章程,乡会试仍为三场,而“将三场先后之序互易之”,一试历史政治,二试时务,三试四书五经,并提出每场录取的具体方法,岁科两考也照此办理。尽管他宣称三场并重,因清代科考“最重首场”,把四书五经摆在政史、时务之后,其实已隐喻着虽有保留但地位降低之意。张之洞的变通方案虽然带有保守色彩,不过,考虑到科举取士“行之且千年,深入迂儒骨髓”〔76〕的实际情况,不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则较有可操作性。光绪帝当即诏准了张氏的变通方案。梁启超在记述这件事时,曾有一番较为中肯的评说:“以科举取士,必不能得人才也,故不惟八股当废,即科举亦当全废。而一切学级,悉自学校出,此乃正理也。然此次不即尔者,盖使数百万之老举人、老秀才,一旦尽失其登进之路,恐未免伤于急激,且学校生徒之成就,亦当期之于数年以后,故此数年中借策论科举为引渡,此亦不得已之办法也。”〔77〕可知当时科举改革涉及众多士人的切身利益,改变过于“急激”,反倒增大改革的阻力,张之洞采取谨慎的变通办法并非没有道理。
康有为虽然不同意在“守旧盈朝”的局势下“言议院、言民权”,却提出了同样会引起守旧势力敌视的其他激进主张。如为了扩大维新的声势,9月5日后,他以自己的名义连拟《请设新京折》、《请断发易服改元折》,提出剪发辫、换西装、改戊戌年为维新元年、迁都江苏、各地多置陪都〔78〕。这些主张固然有显示维新气象的政治意义,但是,在时人看来,断辫易服、改元迁都,便意味着改朝换代,这不仅是守旧势力所无法容忍的,即使是同情变法的人恐怕也接受不了。更何况不换西服同样可以推行新政,而穿上洋装未必就不会复旧。改元迁都这些属于朝廷大典之事,没有慈禧太后的点头岂能办到?北京城当时已经盛传光绪帝将“改衣冠,剪发辫”的谣言,形成了一种对变法明显不利的社会心理。康有为比较激进的姿态所带来的不利后果,连其弟康广仁也看到了:“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弟旦夕力言新旧水火,大权在后,决无成功,何必冒祸?伯兄亦非不深知,以为死生有命,非所能避,……伯兄思高而性执,拘文牵义,不能破绝藩篱,至于今实无他法。”〔79〕9 月中旬康有为还策划了更为激进的措施,准备拉拢袁世凯,组织力量包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80〕。为了排除变法的阻力,康有为决计对慈禧采取果断措施,这不失为有勇气和魄力,但要取得成功又必须有周密的计划和一定的军事实力。可是,连参与其事的谭嗣同、毕永年都感到不大可行时,康有为却仍坚持己见。就在谭嗣同游说袁世凯的当天(9月18日),慈禧已抢先发动了政变〔81〕。
改革之所以难,可以说正在于是一种“权衡新旧”(张之洞语)的运作过程。旧制度的存在是与旧势力的既得利益密切相关,对旧制度进行改革,势必危及旧势力的既得利益,除非以一种新的利益去换取其既得利益,否则他们就会出死力反对改革。对此,严复在百日维新前夕,就有颇为深刻的分析:“国家承平既久,则无论为中为外,举凡一局一令,皆有缘法收利之家。且法久弊丛,则其中之收利者愈益众,一朝而云国家欲变某法,则必有某与某者所收之利,与之偕亡。尔乃构造百端,出死力以与言变者为难矣。是故其法弥敝,则其变弥不可缓;而亦其变之弥不可缓,则其欲变弥难。盖法之敝否,与私利之多寡为正比例,又与变之难易为正比例。夫小人非不知变法之利国也,顾不变则通国失其公利,变则一己被其近灾。公利远而难见,近灾切而可忧,则终不以之相易矣。”〔82〕要想在短短的时间内,将旧制度一下子革新,显然是不现实的。仅仅是百日维新颁布的措施,就已经引起了守旧官僚和习惯势力的强烈反抗。改革旧的制度,需要把握时机,及时加大改革力度。但也要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减少改革的阻力。在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加快改革的步伐、扩大维新的声势,既可以动员起支持改革的力量,但同时也会将反对改革的力量动员起来;后一种动员则有可能比前一种动员的效果更加显著。当反对势力动员起来后,改革则将面临被扼杀的危机——这不能不是戊戌变法迅速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一角度审视,对张之洞在戊戌政制改革上采取的“保守”姿态似当做进一步的探讨。
注释:
〔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305页。
〔2〕《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第105页。
〔3〕《张文襄公全集》,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卷八九, 公牍四,页二四。
〔4〕此系谭嗣同转述,见蔡尚思、 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修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8页。
〔5〕张之洞:《劝学篇·序》。
〔6〕张之洞:《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7〕张之洞:《劝学篇·外篇·变法第七》。
〔8〕张之洞:《劝学篇·内篇·明纲第三》。
〔9〕《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辜鸿铭文集》上册、 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419页。
〔10〕此问题较复杂,当另文讨论。
〔11〕徐宗勉、张亦工等:《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12〕公呈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转引自孔祥吉《关于康有为的一篇重要佚文——答人论议院书》,1982年8月2日《光明日报》。
〔13〕一贯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也有相似的看法,其《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云:“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 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钱穆亦指出, 中国文化传统“讲究最透彻”的是“对人之学”,而“要讲对人之学,必从此五伦始”(钱穆:《历史与文化论丛》,东大图书公司1985年再版,第211页)。应该说,陈、 钱二氏对中国传统文化都有相当理解和研究,故对这一认知现象似不应简单否定,而应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恰当的解释。
〔14〕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版,第114页。
〔15〕熊月之已指出:用“要不要实行立宪制度”作为划分“洋务派”与“早期改良派”的标准“也很不合适”。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3页。
〔16〕《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96、197页。
〔17〕《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第125页。
〔18〕《杨参政公家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572页。
〔19〕《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96页。
〔20〕以上见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一、卷六、卷七,收入蒋贵麟主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十),台北宏业书局1976年版。
〔21〕此文收入《国闻报汇编》,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初印,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321); 该文发表时期据孔祥吉《康有为的一篇重要佚文——(答人论议院书)》。
〔22〕参见孔祥吉《戊戌奏稿的改篡及其原因》,收入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3〕《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6页。
〔24〕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可参见刘大年《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 宋德华《戊戌维新派政治纲领的再探讨》,《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 房德邻《维新派政治纲领的演变》,《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
〔25〕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九。
〔26〕《辜鸿铭文集》下册,第220页。
〔27〕张之洞:《劝学篇·内篇·明纲第三》。
〔28〕〔31〕张之洞:《劝学篇·内篇·正权第六》。
〔29〕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湘报》第27号,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六日。
〔30〕〔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11页。
〔32〕《南学会问答》,《湘报》第15号,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二日。
〔33〕《总论:民义第一》,《时务报》第28册,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日。
〔34〕张之洞:《劝学篇·内篇·正权第六》。
〔35〕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第10、13页。
〔36〕〔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38页;又见该书日本版《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增补版), 东京1970年版,第408页。
〔37〕见《日本语大辞典》,东京1989年版,第1910页;《日本国语大辞典》(18),东京昭和1976年版,第699、700页。
〔38〕据胡适的观察,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全国村学堂里的学究仍旧继续用蔡沈的《书经集传》”。《〈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第2集第1卷。
〔39〕转引自吕实强《甲午战前西方民主政制的传入与国人的反映》,《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8编上,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7、281页。
〔40〕黄彰健以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有“尧舜为民主”、“惟尧典特发民主义”、“辟四门以开议院”等语,进而论证康氏“主张民主议院”,又指出康氏所言“民主”是指“尧舜禅让,与汤武文武之传子有别”(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1970年版,第31页)。笔者认为《孔子改制考》中所使用的“民主”一词也是取《书经》的“民主”之义。
〔41〕参见〔美〕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页。
〔42〕引自台北华文书局影印本(二),第1083—1084页;卷数及出版年月日据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所收《万国公报》篇目核实确定。
〔43〕democracy还被严氏译为“庶建”, 严复译《法意》称“庶建乃真民主,以通国全体之民,操其无上主权者也”。《法意》中西译名表亦称“庶建Democracy,本书中又作民主”。 见王栻编《严复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37、1064页。
〔44〕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5页。
〔45〕《古议院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94页。
〔46〕薛福成曾指明:“而立泼勃立克(Republic),译言民主国,主政者伯理玺天德,俗称总统,民间公举,或七岁或四岁而一易。”见《出使四国日记》,第39页。
〔47〕《劝学篇书后·正权篇辩》,《新政真铨》卷五。
〔48〕《盛世危言·议院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6页。
〔49〕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第134页。
〔50〕《重民下》,《弢园文录外编》卷一。
〔51〕《郑观应集》上册,第231页。
〔52〕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第13页。
〔53〕〔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第9页。
〔54〕张之洞:《劝学篇·内篇·正权第六》。
〔55〕此文收入《国闻报汇编》。
〔56〕《南学会问答》,《湘报》第28号,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七日。
〔57〕《爱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76、77页。
〔58〕《立宪法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第4页。
〔59〕崔国因:《出使美日秘日记》,黄山书社1988年版,第435页。
〔60〕《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99页。
〔61〕《实学平义一民主驳义》,《实学报》第13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又收入《翼教丛编》卷三。
〔62〕张氏1903年主持制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称:“外国所谓民权者,与义务对待之名词也;所谓自由者,与法律对待之名词也”。与“义务”相对应的乃是“权利”,可知其理解的“民权”即是由法律规定的“权利”,这亦符合日文“民权”之本义。
〔63〕同治十二年八月十二日《申报》。
〔64〕《严复集》第1册,第118页。
〔65〕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9页。
〔66〕《康有为自编年谱》,第51页。
〔67〕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71页。
〔68〕张之洞:《劝学篇·内篇·正权第六》。
〔69〕梁启超:《与康有为书》,《翼教丛编》附卷一,第十页。
〔70〕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67页。
〔71〕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第111页。
〔72〕《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65页。
〔73〕《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70、71页。
〔74〕《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84页。
〔75〕《张文襄公全集》卷四八,奏议四八,页二——一○。
〔76〕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360页。
〔77〕《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34、35页。
〔78〕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4—370页。
〔79〕康广仁:《致易一书》,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2页。
〔80〕事见毕永年《诡谋直纪》,载《近代史资料》第63号。关于康氏在百日维新中的“激进”言行及后果,已有学者撰文详论,参见王炎《从珠岩山人戊戌诗三首看杨锐、刘光第与戊戌变法》,《杨锐、刘光第研究》,巴蜀书社1989年版。
〔81〕关于戊戌政变的具体时间有不同的说法,此处据林克光《戊戌政变史事考》,《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
〔82〕《拟上皇帝书》,《严复集》第1册,第75—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