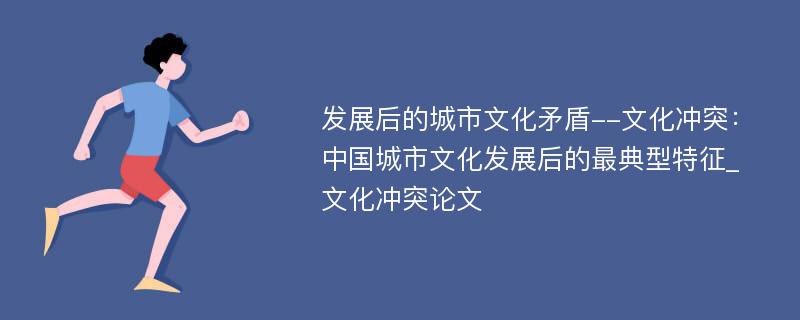
发展起来之后的城市文化矛盾——文化冲突:发展起来之后的中国城市文化最典型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城市论文,中国论文,最典型论文,冲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发展起来之后的中国城市文化矛盾”这样的命题,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甚至统计学的层面做出解答,但它同样也是一个人文学的命题。比如对社会状况的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不同量化指标指数的设置,都是相关研究的重要基础,但这些统计学分析解答不了价值层面的问题,包括城市的文化理念、发展理念、幸福理念等等。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科学是在给定的框架中展开自己的学术工作,而人文学——可以具体到“文化研究”,则具有将这些学科框架历史化和问题化的能力。比如对“城市化”乃至“发展”理念本身的反思。最近有学者指出中国近年来民主建设滞后导致矛盾丛生,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惧怕民主,而在很大程度上缘于理论准备不足。这个判断是很有道理的。用福柯的话来说,“理论并不是表达、解释或服务于应用的实践:它就是实践”。面对层出不穷的城市文化矛盾,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改革的决心和勇气,同样还需要包括反思能力在内的理论想象力。
“发展起来之后”这个看起来一目了然的概念,在文化研究的视域中就有进一步辨析的空间。即何谓“发展”,什么是“后”,或曰“发展后”。表面上看,这只是对一种现实和历史的描述方式,但使用这一概念,则意味着对一种历史观念——也就是线性历史观念的一种默认,或者说,是将现代西方的线性历史观念非历史化了,将其理解为我们讨论中国现实的基本框架和前提。在这个并非客观的历史框架中,“发展后”对应的就是“发展前”,一个可以互换的概念是“后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曾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就是线性的进步历史观。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本人认同这种历史观。他的博士论文研究伊壁鸠鲁,强调自由的“抛物线”,恰恰是反必然性的。马克思强调的自由,首先是要基于对必然性的认识,只有深刻认识到这种必然性,我们才会获得自由,否则只能处于启蒙之前的蒙昧状态。我们只有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铁的必然性”,才能够去批判,去纠正,才能够不被“异化”,才能够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这种对框架的质疑,理应成为我们讨论中国当代城市问题的重要前提。所谓“发展后”与“后发展”,对应的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同历史阶段。城市文化不过是不同时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呈现出来的各种文化表征。当代中国城市与西方成熟的发展后城市的区别不应被忽略。一方面,中国城市,尤其是上海、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在许多技术指标上早已达到了“发展后”城市的标准,有的甚至远远超标;另一方面,在很多技术指标上,中国城市却还处于“后发展”城市的阶段,尤其是在城市公共服务方面,户口、教育、医保等等。也就是说,发展起来后的中国城市,其实还是后发展城市向发展后城市的一个过渡阶段。正因为这一过渡性质,城市文化的矛盾表现出了深刻的紧张关系。文化冲突就是其最典型的特征。例如前几年广东增城四川人和本地人之间的冲突,缘起于同一个工厂里的四川籍员工和广东本地籍员工之间非常简单的工作冲突,为何却演变为一个成千上万的四川籍员工和本地员工之间的大规模地域族群文化之间的冲突呢?这当然不是什么四川文化和广东文化不同的问题,而是在这种过渡性的中国城市中不平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导致的资源配置的不平等的表现。这种矛盾,今天可能发生在广东人和四川人之间,明天可能发生在湖南人和河南人之间,如此等等。
在文化研究的视域中讨论这一问题,可能不仅仅需要聚焦当下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结构分析,而是将其放置在一个更广阔的全球化的政治文化空间中进行讨论。英国著名的批评知识分子大卫·哈维在《希望的空间》一书中将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联系在一起,将“资本累积”解读为“地理事件”。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都围绕着资本的增长与累积,资本主义就是不断发掘新的生产方式/生产线、新的生产科技、新的资本运行方式、新的盈利方式,也促使人们在地理空间上远征新的殖民地,在日常生活内容上组织新的生活方式。由于资本的累积产生了“不均衡的地理发展”,这是资本对利润敏感性本质所决定的。地理空间的划分过程,就表现为资本主义在地球表面运行的历史。并且,资本在无可避免地膨胀和扩张,成为一种推动世界不断改革的力量,也同时不断改变我们以二元对立为内核的时间意识:1.宗主国/殖民地之二分(19世纪);2.先进地区/落后地区之二分(19至20世纪);3.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之二分(20世纪);4.全球城市/非全球城市(20世纪末开始);5.在城市空间内:城市中心与边沿地区之二分。在哈维看来,这种划分的标准,虽然有很多非常细化的技术指标,但是其得以建立的基石却是“发展后”与“后发展”所界定的“进步”历史观,这种进步观成为资本主义衍生出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它以生产(科技)的进步及发展、经济的增长和扩张为正面价值取向,成为落后地区和后发展国家在国家建设、社会及文化建设各个方面的圭臬。无疑,我们如果不能摆脱这种线性的进步历史观,不能真正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铁的必然性”,我们未来就会陷入韦伯所说的“铁的牢笼”。
哈维从蜜蜂的工作角度,提出了一种“辩证乌托邦”的主张来解决资本主导的地理扩张与区域空间的碎片化问题。在他看来,蜜蜂的行为最接近其生命发展的核心规律与自然历程。很多城市的建筑师通过想象建筑出来的怀旧性建筑,不过是满足了少部分人对“世外桃源”的怀旧心理,它与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大多数市民或产业工人没有关系,根本不可能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例如城市改造拆迁导致居住在城中村的居民不得不远离城市,只能到城市的边缘生活。哈维认为,我们要寻找人类的“蜜蜂”一样的“类存在物”,这就是用“自然、社会等多元乌托邦”责任下的“生命之网”来构建人类的“辩证乌托邦”,以使人类获得“平等生存的机会”。他强调,人类要学会在“他者的世界中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自己”,同时要关注知识的统一性。只有这样,把个人与身体的力量扩展开来,并带着具有人类生态学的特征,才能彻底解决目前城市的糟糕的空间格局。在这里,哈维和马克思一样,强调理论的武器必须转化为武器的批判。这其实也是康德对启蒙的要求,一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二要敢于行动。
与哈维在人类生态学角度提出“希望的空间”类似,美国人类学家阿帕杜莱则倾向从人类学的视角观察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散裂”与“差异”。阿帕杜莱在《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中指出,当今全球互动的核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异质化之间的冲突,建基在这一基础上的全球文化经济秩序具有复杂的、相互交叠的散裂的(disjunctive)特征。当今全球经济的复杂性即与这种经济、文化和政治间的某种根本性散裂有关,而我们才刚刚开始从理论层面研究它。阿帕杜莱提出了五个维度探究全球文化流动的散裂:1.族群景观;2.媒体景观;3.技术景观;4.金融景观;5.意识形态景观。后缀“景观”一词强调了它们流动的、不规律的形状,它们并不是客观给定的关系,并非从各个角度看来都一成不变,而是根据观点构建的,深受不同类型行动者的历史、语言和政治处境所影响;这些行动者包括民族国家、跨国团体、流离者社群、亚民族团体和运动(无论有关宗教、政治还是经济),甚至村庄、邻居和家庭等关系亲密的、能面对面交流的组织。这些景观正是构建所谓想象世界的基本砖石:全球各地的个体与群体基于历史处境而想象并建构出的多元世界。
阿帕杜莱的“想象”和哈维的“希望”具有同样的解放力量,并且都指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复杂性,但阿帕杜莱比哈维更进一步,把“想象”理论化为一种分析概念,他承继从涂尔干等人类学家将集体表象视为社会事实的传统,认为集体表象超越个体意志,承载着社会道德的重量,是客观的社会现实。阿帕杜莱进一步指出,基于近百年来的科技变化之上,想象已成为一种集体性的社会事实。这一发展转而为想象世界的多元性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在后电子时代,想象拥有了崭新的重要地位,它早已突破了艺术、神话及仪式这些特定表达空间,在许多社会中已成为普通人群日常精神活动的一部分。它在当今世界具有现实的社会力量,曾被排除在日常生活的逻辑之外,现已回到这一逻辑之中。
所以,当我们讨论“发展起来之后的中国城市文化矛盾”这一问题时,首先是要认识到这一文化矛盾背后的深层生产机制,即哈维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资本积累,所导致的不均等地理发展的“时间—空间修补”关系。但在哈维这里,“文化”还基本上是一个“名词”,而阿帕杜莱则强调自己是在“形容词”意义上来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文化的名词形式暗示着文化是某种对象、物质或实体。而阿帕杜莱更强调文化的维度性,强调境遇化的差异,即相对于某种地方的、具体的、重要的事物而言的差异。文化的力量之所以具有对抗资本力量的可能性,就在于它的反抗性,它通过差异重写全球文化经济秩序的历史,日益呈现出流离与散裂的面貌,从而破除线性历史的进步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