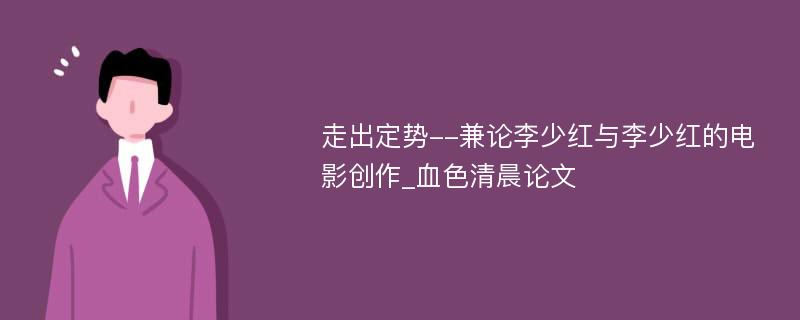
走出定势——与李少红谈李少红的电影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定势论文,电影论文,李少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电影人物
第五代导演李少红以其作品《银蛇谋杀案》引人注目,以诺《血色清晨》获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大奖,以《四十不惑》获瑞士洛迦国际影评人奖,今年,又以《红粉》从西柏林捧回银熊奖,在大学生电影节摘取最佳导演的桂冠。我们认为,李少红的电影作品,不仅在风格上相互迥异,而且每一部都有特定角度的创新和探索,尤其她最近拍摄的《红粉》,在电影形态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为此,我们与李少红做了交谈。
一、走出定势的形态
张:你今年完成的《红粉》评论界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大家的感觉是一致的:与以往的作品不同。
李:以往我们拍电影习惯先确立一个主题,然后营造一个氛围去烘托这个主题,用各种手段去塑造思想形象。我觉得压根儿就不应该这样,应该换一个方式拍电影。比如你对一个人、一个事物很有兴趣,你就把这种感觉拍下来,在这个过程中,你是拍摄一个个人的感受呢?还是为思想营造一个形象,我认为这是想法完全不同的两种创作方式。我觉得中国电影在变,它在其形态的变化过程中出现了各种新的样式,这些新样式与原来的定势不同,如果用传统的方法读解它,你会感到困难,你会问:它的主题在哪儿?用原有的理论套这些作品后发现作品与他使用的理论模式对不上了,用原来的方式看这些电影,突然觉得什么都不是了,人们太习惯于用一种定势去欣赏电影,好象突然有一种食物与以往的食物不同,大家不知道这东西能不能吃。
张:我最近想写一篇文章,题为“话语定势的尴尬”,就是想说明这个问题,既定的理论模式在新的电影形态面前手足无措。例如在分析《红粉》这部作品时,一种话语想说明妓女是封建社会压抑女性的产物,妓女是被压迫者,这是一种历史话语;另一种是女权话语:新的社会形态是解放了女性,让女性与男性有同等地位,但使女性走向了无性。《红粉》游离出这二元对立的理论话语,描写了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妓女有被压迫被侮辱的一面,也有过寄生生活自感舒适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消灭娼妓制度对妓女是一种解放,可有些妓女走出妓院后不能适应艰苦的集体劳动生活。这部电影在描述历史时没有定位于某一种固定的话语,没有按关于女性的既成话语套路走,而是真实把握历史过程的复杂性。
李:过去我们描写的女性,主要从政治和历史的作用出发,《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女篮五号》、《舞台姐妹》这些影片都是把女人作为一个群体形象推出来,都是带着反封建、反压迫的政治意向,这种意向对于当时的政治要求是对的。我觉得我们应走出定势,去反映女人的个人存在价值,反映她的复杂的个性状态,而不只是为历史和社会而存在。我们这部片子的创作过程就是遵循人物原本的状态和面貌。
张:我看《红粉》,感到其中的意义在滑动,在游移,它不象常规电影,有一个固定的结构,按照某种价值观念的取向,安排事件的发展和人物的行动必然这样或必然那样。然而客观事物也可能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又那样,它一直在发展变化着,不是非此即比,这种游移状态和多义性,使得一些既定的话语在这部作品中难以找到定位。比如,按照常规的说法,在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上,男性压抑女性,可在这部作品中,男人既有玩弄女性的一面,可又好象有对女性很疼爱的一面,如按常规的说法或按女权话语的说法,女性一般在旧社会是受压迫的,可《红粉》也同时表现了女性牵制男性的一面。林语堂在《 吾土吾民》中就论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家庭里的女性对男性有着潜在制约。《红粉》用游移的方式,复现复杂的状态,这也是艺术观念的变化,它不再有一个主题单一、脉络单一的,稳定的中心结构。
李:我感觉到我在努力摆脱原来的思维方法,寻找新的感觉。原来总是非常理性地去想,去设计。摆脱原来的思路是个很艰巨的过程,在拍《四十不惑》时我就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可以用一个人的内心视角讲一个人物内心里的故事,不一定局限在外部的事件上,现在我已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红粉》小说本身就非常个人化,作者主观随意非常强。历史已不是客观的历史,而是作者个人感受的历史。讲故事的语序也很主观化,如同一个阴雨天,街坊邻居在屋檐下的只言片语,然后是作者望着黄霉天际的一番遐想,因此,它带着强烈的个人局限、破碎感和个人化的情绪。这些正是小说本身魅力之所在。因此,你读它会感到亲切,它带有的南方特有的低语的音调,都形成了小说的风格。是苏童的小说启发了我,使我敢于大胆地去尝试,不再去考虑戏剧的三一律、起转合,而是紧紧跟着个人的情感变化走,在情感变化的流程中,她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不求全面、客观、合理性。情绪是贯穿全戏的中心。
张: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流动状态、变化状态和游移状态,流动、变化、游移就必然呈现丰富性、复杂性和多义性。
应:你拍的《血色清晨》在表达意义方面就很明确,很有目的性。
李:是的,可《血色清晨》还是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的创作方法,它的清晰感和强力度很容易被人接受,很容易满足人们的期待。
应:这部作品叙事完整。
李:对,它是一个故事性很强的东西,但这种东西还是从集体意义出发,从社会意义出发,突出了历史感,电影的表现对象在为意义服务。
张:若拿《红粉》与《血色清晨》作比较,变化就十分明显了。
二、关注个体的镜语
李:现在,咱们的电影正在向描写个体转化,比如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为什么跟《菊豆》完全不同,他注重了秋菊个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经历。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从一个戏子的眼光出发,讲他们的生活历程。他们把对集体的关注转变为对个体的关注,包括田壮壮和更年轻一代导演的电影都是如此。电影的镜头语言转向描述个体的存在,以及个体的精神状态。以个人化的视角去重新解释已被解释过的历史。过去我们的影片先写文化大革命怎么回事,再写主人公怎么回事,现在有些电影把这个次序颠倒过来了,镜语从对个体状态的描述开始。
张:由于关注了个体,以描述个体为出发点,个体反过来可能真实地折射出社会大背景,于是电影有了新的逻辑程序,这与从整体性的大意义出发,用个体人证明大意义的逻辑顺序不同。
李:“解放”这个概念对两个妓女来说有特殊的意义,她们这种人的解放,区别于其他劳动人民解放,从她们的视角看解放、土改、收房子等等历史过程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因为有局限性也就有特殊性。
我之所以选这篇小说,就是因为这篇小说从特定的角度描述个人,这些人身上没有明显的缺点也没有明显的优点。
张:我们通常所说的优点一般有着伦理的尺度和价值系统的尺度。这些人不一定完全遵循尺度而生活。
李:历史是政治家的事情,个人在历史中是被动的,而且个人在历史中所接触和看到的只可能是历史的局部,不可能是全部,并且还要夹杂着个人环境中的世俗因素、伦理因素,以及个人性格因素,所以和政治家理想放在一起显得很黑色。《红粉》中的人物和社会就存在这种不谐调。
张:这可能是一个创作观念的问题,有的创作传统和习惯是想以人物揭示大背景、大时代,可有些人与人之间的事可能超越各个社会发展阶段,在任何一个历史状态下都可能发生。
李:可过去我们忽略了个体,忽略自我,淡漠到自己对自己都很陌生。
张:夏刚拍了《无人喝彩》,这可能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性格龃龉,背后不一定有深广的社会背景,可能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那种既互相矛盾又互相依赖的你来我往的关系,描述这种关系本身就挖掘了人性,它自身就有价值,可有的评论从中整出社会时代的“大义”来了。
应:这可能是我们的意识形态批评和文化批评影响力太大了,对什么片子都要找到微言大义。许多国际优秀影片写凡人小事,很感人,很受欢迎。
张:当然,人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写人不可能不带有历史的烙印,但不要太牵强,不要从概念出发,从话语出发,硬让一个小人物、小事情去证明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个人身上的历史痕迹也许是隐晦的,折射的,以写人为根本,历史就自然带出来了。
李: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过去我们强调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那是一部公共的历史。而这个历史是由每一个人组成的,历史从每一个人眼中折射出来的可能都是不同的,而那恰恰是历史的一部分。刚解放那阵,整个社会在变化动荡,社会各阶层的地位层序大颠倒,原来的非主流社会上升为主流社会,原来的主流阶层下降为非主流阶层,这时社会上有两种人的地位变化最明显,一是象老浦这种民族资产阶级的后代(当然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本身),他们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社会地位,重新审视和安排自己的生活,重新确立自己的感情选择。还有一种人就是妓女,只有这个职业被新时代取消了,妓女突然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成为社会地位不明确的人。一个问题摆在她们面前:我属于谁?我属于原来的社会范畴和职业,还是属于劳动妇女,社会给她们的唯一选择是:成为劳动妇女。小萼在妓院里出生,认为自己天生就是妓院里的人,现在突然不是了,那我是谁呢?我又不会干别的,她突然觉着自己没有归属感了。从小萼、从老浦、从秋仪的眼中看解放,是很有意思的。老浦从两扇门的缝隙中看到仆人从乡下回来,老太太问:地契呢?仆人答:地契都烧了……这是老浦这种小人物对历史的特定感受。
应:如同我们感受“文革”,当时红卫兵来了我们还爬在树上玩,从树叶中间看到了红卫兵,他们敲着锣,进入某人家庭,那人正在训斥女儿,一见红卫兵又满脸堆笑:“小将们请坐”。小将突然他一个耳光说:你这个国民党军官老实交待,这时树上玩耍的孩子们全都静了下来……
李:这种感受好象没有历史的全貌,可艺术的视角恰恰就在这里,你当时作为一个孩子感受到了历史,老浦坐在客厅里,知道外面的世界全变了。公家的人来收房子,他们很自然地腾房子,他们心里明白:新社会到来了。从一个特定角度叙述解放比从正面叙述解放有意思。
张:不仅个体审视历史的角度有意思,个体自身的活动也有意思,这些活动、这些行为虽与大背景无涉,但是在每一个体身上,在每一家庭中都存着的,它能够勾起观众联想起自己的生活经验来,比如老浦与小萼的吵架,大家都说:“太象了”,象谁呢?象他们自己。
李:所以有些观众自己看完后,又把一家人带来看,上海人、江浙人觉得这部影片特别真实。观众会渐渐为看到自己而满足,会平静地观赏与他们亲近的生活流程。
三、位处边缘的人物
张:《红粉》这部电影因为它的描述对象引起了许多争议。
李:有人觉得我放着社会先进分子不写却要写下九流的东西。我们长期以来习惯电影和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多是主流人物,有些人不习惯于读解社会中的一些地位低下、位处边缘的小人物,他们认为这些太不值得写了,这种习惯性思维是理解的障碍。
张:这种思维的逻辑是:作品描述了低下的人物,作品就低下了;作品描述了脂粉,作品就有脂粉气,就是病态的,归根到底这是一种“题材决定”论和“人物决定”论,承袭了一种“在普通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逻辑贯性,这种贯性认为写某一种人作品就有价值,写另一种人作品就没价值,写妓女不但没价值而且粗俗下流,这是在用伦理观念判断文艺作品的价值,伦理判断与美学判断、艺术判断之间是有联系,但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区别呢?这种分析方法很象“文革”中的大批判文章,流于简单。
其实中外文学史、电影史上的许多著名大师诸如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莫泊桑、雨果、大仲马、老舍、巴金、吴永刚、袁牧之等都写过妓女,他们的作品并不因为描述了妓女而粗俗低下,而脂粉病态,莫泊桑笔下的妓女羊脂球,托尔斯泰笔下的妓女玛丝洛娃,大仲马笔下的茶花女,老舍笔下的小福子、月芽儿等等,都渗透着大师们对她们的同情,被公认为优秀的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神女》、《马路天使》也不因为表现了妓女或以妓女为主人公就丧失其深刻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谁能说这些作品没有深刻的人性开掘和深广的社会内涵呢?所以作品是否有脂粉气、是否病态关键在于怎样写,而不在于写什么。
应:我看《红粉》马上就想到了50年代,接着就认识了这些人,这些非工农兵的人,知道了他们在那个时代的特殊状况。
李:这些非主流状态的人位处社会的边缘,他们远离中心,从他们的视角看社会变化,有着特殊的价值。
四、性格相异的女性
张:《红粉》描述了性格相异的女性,剖析了她们的心理状态。例如秋仪面对老浦有一种自我的尊严感,老浦给她钱,她把钱撕了,其实她很缺钱,但她更需要感情上的爱,她很爱老浦,由于得不到平等的情感给予,又为了尊严,只好放弃了。老浦似乎也喜欢秋仪,但他又觉得秋仪太任性,只好任其而去,双方冷静之后,都意识到自己爱对方,后悔自己一时冲动而决裂的举动,影片是否试图在男人与女人之间一来一往的磨擦和龃龉中描画人们的心灵流动和情感波折?
李:当时我认为生活中的女人起码有两类,有象秋仪这种自己比较有主意的女性,从表面上看性格坚强,这种女人在感情上要求十全十美,不允许男人对她的爱有丝毫的游离,如果男人有一点不投入,她都受不了,她把生活理想化了,实际上,十全十美的男性在生活中是不存在的,这种人比较脆弱,在生活和情感交往中有一点挫折她就放弃。秋仪不允许老浦的感情有任何偏差,哪怕有一点瑕疵她都受不了,这就是为什么秋仪吵了两句嘴就甩手出门,老浦给她钱的时候她感情上受到了巨大的刺激,她觉得老浦完全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种男人,所以这时老浦说任何话她都不能接受,老浦说得越多,她的反应就越糟糕。秋仪这种女人在生活中往往是失败者,生活中有许多人们看来外表很强的女人在感情生活中不愉快,她们更容易比小萼这种人大起大落,别人不知道她们为什么为一点小事情绪冲动,其实她们为的是追求完美。
女性中还有小萼这种人,她的依赖性很强,有男人的时候,她依靠男人,没男人的时候,她依靠女人,她是被动型的人物,需要别人来安排她,她需要别人告诉她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她身上理想性的东西很少,她好象很实际,别人给予她什么,她就接受什么,如果有十个男人爱她,那么十个男人的爱她都接受,她会在这里边处理得很微妙,她的魅力仅次于象秋仪这样的人,但由于她的性格特点,使得男人跟她在一起,就可以考虑跟她结婚,而秋仪这种人只能被当作情人。小萼获得一切要比秋仪容易得多,但她由于得来的容易,失去的也容易,她不觉得这些东西很有价值,会很容易地将其放弃。她很容易就把自己搞得一片混乱,搞混乱后自己又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完全是被动性的,没有一个理想化的东西在支撑她。秋仪与小萼两人的性格比较很有意思。
张:小萼一开始依赖性很强,她在被赶出妓院那阵子离不开秋仪,后来又离不开老浦,按说依赖性极强的女性逻辑应该是百依百顺,可谁知她与老浦结婚后极端的任性,为一点小事就把丈夫整得无所措手足,用南方话讲就是“嘬”死,让人感觉到这个依赖性很强的女性反而死死控制了依赖对象。
李:我觉得这是很好玩的一件事。
五、传达女性的感受
张:各种话语对女性都有描述,都有使动意向,如女权话语指出女性正处在什么位置,女性应该怎样怎样。
李:女权主义与女性意识是两回事,女权主义是一种运动,它的意义不在于描述一种现实生活的状态,说到底它要把男权社会颠倒过来。
而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不在于描写的对象是不是女人,它应指创作者看待事物的思维方法和视角是女性的。有人看了我的电影后很纳闷:“女人怎么能把一些东西弄得血淋淋的?”他们认为女人脑子里应该没有血,没有暴力,没有残忍的概念,女人应该是柔美的,是柳条,是婆婆妈妈。实际上在这个社会中,男女经历的过程,经历的事件是一样的,不是某条路只能女性通过,某条路只能男性通过,实际上男女共同走过大街,区别仅在于两性对事情的感受不一样,并且不同的女性对同一事件的感受不一样。
张:我们不能从外部对女性意识做强行的规定。
李:对。有些人质问我,你的《银蛇谋杀案》、《血色清晨》里为什么描述了凶残和暴力?如果说影片中的凶残和暴力令人感到震惊,也许是由于一个女性眼睛中看到或者感受血腥原来是这样的造成的结果。
张:女性可能对暴力和凶残感受得更强烈。
李:也许更细致。男性对残忍和暴力的感受可能很理性。
张:我记得应雄为《血色清晨》写过一篇文章。
应:我当时用了特学术化的词:“导演用忧郁的目光掠过这片乡土”,镜头给我就是这种感觉。
李:当时拍这部片子时,我们有截然不同的意见。当那一斧头砍下去的时候,我感觉中的那种凶残放大了。我觉得表现那种细微的过程特别重要,我决定用慢镜头,但有人不同意用慢镜头表现,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是男导演的表现方式还是女导演的表现方式,我只觉得这种表现象显微镜一样把残忍放大了。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让观众感受更多的东西。
在画面上,斧头掠过了,鲜血掠过了,灵魂也掠过了,留下的是我对那一事件中最本质的感受,对人存在目的最深层的疑问。我一定要细微处进入、进入,我坚持这样细致地表现,我如果在这过程中停下来,那就会停留在事件的表层上,我还要深入下去:由于愚昧,整个村子,集体的村民都是杀人凶手!这一切都在银幕上掠过之后,留在我心灵上的最强烈、最深刻的感受,这也许就是我作为女人的特殊感受。
张:这种感受越尖锐、越强烈,对暴力对残忍的反思和控诉也就越深刻越有力。描述暴力不等于歌颂暴力。
李:不能因为女性控诉了血腥就不成其为女性。
张:这个逻辑与描述妓女就粗俗低下的逻辑一样是荒谬的。
李:不能说,女人就不能拍暴力影片,不能说女人就只能拍爱情,拍孩子,只有爱情和孩子才是女性题材,才是女导演该干的事,对题材不应有女性和男性的划分。
六、再度创作的改编
张:你对《红粉》的处理与苏童的原创作是否一样?
李:苏童的小说提供给我一个作为女性可以认可的视角,透过这两个女性的个性特点,我可以感受许多东西,可以感受到她们在那一历史过程中的微妙变化。
张:原作者给女主人公安排的这种身份是否更容易表现女性微妙的变化?
李:有人说这个故事离开改造妓女这个历史事件也可以成立,我觉得不能,这个故事建立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有特殊的意义。
应:我觉得在改编中可以让老浦和王姬更亲密一点,我理解王姬扮演的角色是老浦的红粉知己一类。
李:我们在改编时把这条线加强了,秋仪对老浦好,老浦也打动了秋仪的心,但老浦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秋仪心中的分量,一直到很晚老浦才意识到秋仪对他的感情很深。人在生活中,一般对自己的意识是模糊的,老浦到最后才意识到,秋仪是她最喜欢的女人,可是他已经来不及想了。人在生活中不可能理性地意识到自己存在什么情绪,别人在旁边倒有可能看清楚。别人觉着老浦喜欢秋仪,老浦自己可能还不是很明确,当他听说秋仪为他怀过一个孩子,一下子就了,于是他后面所做的一切都失控了,小萼不足以使他变成这样,这时候,我们才觉得秋仪在他心目中分量有多重。他一下子把什么都看淡了,找了一个最愚蠢的方法,弥补自己的过失。每个人的情感一定反映在他的行为中,而不在他的理性中。
应:你们的改编过程一定很艰苦。
李:我现在想起来了,我们改作品、编剧本的过程,为什么那么艰难?我们写了许多稿,推翻了许多稿,剧本游离小说已经很远了,写的不是我原来想象的那个样子,有时我们想到应该象原小说那样有一个清晰的故事,重点写老浦,使他的感情铺垫到一定程度再展开。有时我们又觉得这是一个独立的故事,不是原小说给我们的。秋仪是一部分。小萼是一部分,都可以单独成篇。我们还搞过一个非常清晰的故事化的东西,这个故事虽然很清楚,但我们觉得不是原小说的味道,不是那种感觉。那么原作感觉究竟是什么?我们说不出来,后来我们自己与自己打架,甚至不能用清晰的个性化的思路考虑问题,后来我反复问自己,到底当时是什么打动了你,到底为什么当初觉得它好?因为最初对原作的感觉特别重要。经过思索,我意识到作品写了女人自身的感受,这种感受是生活中的感受,不是从意念出发的,人物在当时的状态很有意思。在外景地我们又重捋了一遍剧本。
应:现在看来,你对你的剧作很满意。
李:虽然有人说不好,但我自己心里很踏实,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影片和这种手法会被更多的人接受。
七、独具匠心的导演
张:《红粉》的场面调度多在上海、苏杭那种有天井的小院和院内的两层小楼中进行,看完后让人觉得只有在这个空间里才能讲述这个故事,你设置的这个空间一定与这个故事存在着内在联系。
李:我们对原作的空间有所改动。原小说中的江南地域特点不十分明确,似乎是上海,也似乎是苏州,小说中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小楼,感觉是平面的,不是天井式的。影片根据改编的思路选了上海石门窟的那类房子,这类套院中间是一个井,旁边是石头砌起来的,这是南方典型的民国时期建筑,这是一般市民的住房,老浦进入这种院落,意味着降入平民生活。
南方的空间特别小,人口稠密度高,房屋之间的隔墙多用木板为材料,隔壁打嗝,这边的人便知那边的人吃饱了,从这一空间,你可以感受到生活的拥挤。
张:有的评论家说中国电影中常见四合院,这是鲁迅所说的铁屋式的寓言。可我看《红粉》中的院落,不但没有闭锁式的压抑,反而让人感受到墙外大时代的轰轰烈烈,如老舍《茶馆》中的空间感觉:外界大的历史变化要破墙而入了。
李:我原想用大喇叭播社论来说明历史背景,但这些东西显得无力且司空见惯。
应:我觉得《红粉》表现这方面的历史内容与《霸王别姬》以及田壮壮、张艺谋表现时代变化的电影不一样,这完全是从个人、小家庭的角度来表现。
张: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那是一种全知叙事,这是一种限制叙事,如果用全知叙事,微妙的个人感受就出不来了。
应:你是怎样处理表演的,你觉得王姬与何赛飞的表演怎样?
李:小萼这一形象的塑造地域性强,很象南方女人。秋仪身上的共性比较多,她是一个比较理想化、比较戏剧化的人物,她的地域定位不明显,王姬学说上海话不熟练,这一点限制了她的表演。王志文是上海人,他演的老浦说了许多“叽叽嘎嘎”的上海话中的碎词,所以演得很自如。王姬的优点是,她的性格呈现很准确,她往那里一站,你就不能不承认她,她在老浦和小萼中间起轴心作用,她的性格优势以及准确把握弥补了她在说上海话方面的不足。
我们原来担心有些戏处理不好,可把演员一放到那个特定情境中,戏就自然流出来了,全然不需要演员自己去使劲儿,这个感受是我在这部片子拍摄过程中最舒服的一种感受。比如对老浦看秋仪,见到秋仪已经是光头的那场戏,我一直不敢拍,怕不好处理,一直放到最后才拍,由于场景设计非常生活化,给我们带来一个难题,一个人在门内,一个人在门外,没有任何遮掩,特别白。可生活本来就是一种无设计的状态,我们如果硬拍,来回打镜头,也不过就是这两个机位,这是处理起来不得不单调的一个场景。可魅力在那两个人身上,两个人一开演,什么都有了。
张:在特定场景中,人与人的情感自然交流是最好的戏。
李:我没有觉着这场戏没有刻意的设计就不艺术了。我对演员讲了几个表演点,一开机他们的感情就流泻出来了,流泻得很自然,不存在戏过了或火候不到的问题,这种自然的流泻与导演的意图特吻合,不需要加工它。两个演员进戏了,进入角色了。
八、当代题材的期待
应:现在张艺谋、陈凯歌都不太敢碰现代题材。
李:其实我很想拍现实题材。但当代题材特别难搞,因为当代题材要涉及当代城市。我们虽然是第一代城市人,但我们成长过程中更多接触到的不是城市气息,这和我们的国家依然是农业国家有关系,中国严格说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所以中国的城市形态和西方完全不同。
张:这是变化中的城市变革中的国家。
李:东西方是两种文化形态。西方人最初是通过传教士了解东方的,所以几百年来西方对东方的认识依然停留在这个水平上,他们容易接受《红高粱》、《菊豆》,而对中国现代生活中非常认真的东西,如《背靠背,脸对脸》,样们认为拍得不错,可外国人理解不了,他们觉得很奇怪。对于《凤凰琴》这们既有过去因素又有现在内容的复杂形态,外国人看不懂。
张:是否外国投资商容易给中国过去题材的影片投资?
李:投资商是根据市场的要求来投资的,他觉得某一段时间内,某类题材看好,他就投资这类影片。如果这个题材市场慢慢疲软了,新的题材市场又出现了,他就会投向新题材。我觉得我们的电影对西方市场的供应是喂养式的,你给他哪一口,他就吃哪一口,没有选择性,他们对中国电影太不了解,不知道你们有什么。《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这类题材发行成功了,他们就发这类作品,可现在西方电影节和发行商希望看到我们的当代题材电影。《红粉》如果在前几年搞出来,一定比现在更受欢迎。在国外,看片的人一听说中国当代题材,都争着要看,选片人首先问有没有反映中国现实生活的作品。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我们现代题材的影片能否找到国际化的语言,不局限于特定的历史和社会形态。
应:我想你今后的创作会落到现实题材上去。
李:我想会的,但创作时要把握好。搞创作的人不一定那么理性,总结得头头是道,但如果感觉找到了,片子就能搞出来。我觉得我一定要搞现实题材,过去我们之所以搞历史题材,是因为在特殊的情境下没法搞别的,讲历史最安全,现在搞现实题材,创作的自由度会大一些。但搞现实题材不要一窝蜂最好,应该是你喜欢什么就搞什么。搞现实题材我们需要对自己进行一次革命。
张:如搞现实题材,你打算怎样搞?
李:第一步可能是先写一个人。
应:你对本子有无一个构想?
李:已经有了。我写的这个人表现出来可能有争议,可能有许多人反对我这么写,但我要写好“这一个”。
李少红创作年表
1982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1982年上半年任《见习律师》副导演。
1982年底任《包氏父子》副导演。
1983年任《出门挣钱的人》副导演。
1984年任《清水湾·淡水湾》副导演。
1988年导演《银蛇谋杀案》。
1990年导演《血色清晨》。
1992年导演《四十不惑》。
1994年导演《红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