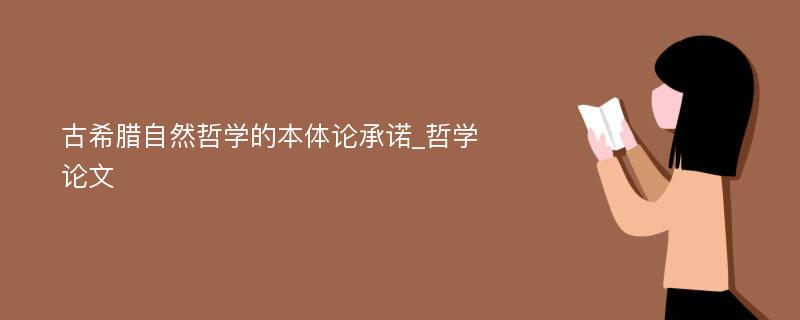
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本体论承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希腊论文,本体论论文,哲学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希腊哲学渗透着科学的求真精神、神学的求善品德和哲学的求美风格,蠕动着诗人的自主意识,弥漫着哲人的思辨风采。直观与思辨、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自然和谐是这一时期哲学的基本特征;从总体上把握世界,寻求规范世界的统一性始基、本原,是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围绕这一中心课题,哲人们思虑着一与多、心与物、质料与形式、具体与抽象、存在与非存在、实体与非实体、动力与目的、自动与他动、感性与理性、意见与真理等对偶性范畴,形成了古希腊哲学本体论从“一”出发、一分为二,对偶发展的传统模式。
古希腊哲学本体论用“一”来规范世界,是始基、本原、本体的客观要求。本原之所以是本原,就在于它不能用另一个本原对之加以规定,否则它就是被限制、被规定的东西。真正的本体是不受限制的,它是唯,是“一”,是世界统一的基础、万物之共性。它是自我存在和他物产生的原因,万物由此而生又复归于它。因而只有“一”才能成为本原,杂多则不能充当本原。因为杂多是堆缺乏必然联系的现象,是被限制、被限定、被规定的东西。“一”是世界的本体,是哲学所寻求的最高原则。
古希腊哲学二分为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自然哲学力图从自然世界本身的事物中寻求统一自然万物的共同性始基。虽然质料与形式的概念最早明确地两两出现于亚里士多德哲学,但是,构成本体的质料与规范质料的形式之关系问题,实际上是自然哲学的基本问题。
植生于海洋崇拜的文化心理和观察事实的经验材料,泰勒斯将“水”设定为万物之源,认为万物由水所构成又复归于水。水是质料,是构成万物的“一”;水具有流动性,它既存在于万物之中,又能保持自身的“纯洁性”,成为宇宙的始基。水是一与多之统一,既有单一性又有统一性,既是个体的又是普遍的。个别是统一中的个别,统一是个别基础上的统一;分是实现多的手段,合是达到一的途径,分离亲和的动力则是“灵魂”——一种外在的规范。
水还是一种没有能力自我定形的无定形者,它自身不能规定自身,也无力推动自身构成为他物。具体形态之“水”要由具体的外形来规定。这外在于水的形式是水成为他物的模型。具体之形消失了,万物又变成为水。
在泰勒斯那里,外在的形式是什么的问题存而未论,因此质料与形式是分离着的。形式独立游离于本体之外。那么世界之统一性如何实现?另外,水是具体的可感之物,它如何能成为形态各异的具体事物的要素?多样性何以可能?但泰勒斯的水毕竟是种“无定形”之物,又是一种具有流动性和稳定性的“类”,阿那克西曼德继承了这些思想,并试图将质料与形式统一起来。他提出了“阿派朗”的概念。
“阿派朗”“严格地说应该译作‘无定形的东西’,亦即一切无定形之物的总称。”〔1〕任何东西,只要它是无形的,它就是本原。 “无定形的东西”包罗万象,种类繁多的无定形者统一于“无定形”。“无定形的东西”支配一切,它无形无限,不生不灭,富有生命,善于变化,变化的冲力就是“正义”、“命运”——事物自身所拥有的必然性。因而由“无定形的东西”所构成的世界亦是无限的、多样的、变动不居的。相对于水而言,“阿派朗”是一种概括和抽象,一种共性。它不是任何具体的东西,但又是任何具体之物的原因,它是质料与形式的统一体,亦拥有自动的能力——正义与非正义的矛盾斗争、“命运”(必然性)战胜“不义”性。
然而,正因为“无定形的东西”无任何规定性,质料与形式都是不可言状之“无”,因而它是一种思维中的具体。尽管它是“客观”的,但确切地说它是一种离开具体的抽象,一种虚无。这“无”如何能构成丰富多采的世界?因此,在阿那克西曼德那里,质料与形式虽然获得了同一性,本体亦有了自我创造世界的功能,但由于质料与形式并未获得现实性,亦未真正归属于“本体”,从而使得本体流于空寂,亦使得“宇宙”只具有分析型意义。阿那克西米尼的“气”本体论,克服了“无定形的东西”的理论缺陷。
气可视为水(正题)与“无定形的东西”(反题)的一个合题。〔2〕气弥漫于苍穹,无形无影,它克服了水的具体可感性, 从而使得世间万物具有一致性和可比性,气本体由此而拥有了“一”的特性,能够将世界现实地统一起来。气作为世界统一性之基础,它既无开端亦无结尾,气是无限的;气自身拥有外形,或者说宇宙便是气的定形之体。因而气构之物是定形的,宇宙是无限的。似水一样,气是定形的。它不象“无定形的东西”那样虚无缥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可以说,气是无定形之物中最有形的,亦是有形之物中最无形的。它与“无定形的东西”相似,看不见,摸不着,但作为思维的抽象与感性之具体的统一体,气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着(人们亦知道它存在着)。气拥有现实性,有资格成为世界之始基、统一性之基础。
作为始基,气还导致自然界的千变万化,使世界万物萌生。不仅如此,气还具有自动的功能。这自己流动性变化来自于主动性的生命。在古希腊人心目中,“气”具有精神的特征。作为生命、灵魂、思想的嘘气,它是自我流动的。〔3〕气的自动不似水式的惰性运动, 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随“心”所欲式运动。这种运动克服了水的消极性,为“火”之冲动式的积极运动创造了“空间”。因此,在水那里分离着的形式与质料、在“无定形的东西”那里未获得现实统一性的形式与质料,在气这里则统一了起来,并拥有了现实性。于是,气便超越了一切具体可感之物而在“无定形”层次上占有了“形状”。
不过,严格地说,气所拥有的形式是从普遍性、统一性意义上而言的。而具体个别之“气构物”,其形式仍然是外在的。因为气如水类似,有惰性,无自我生成的冲动向上之力。它不能自我规定自身成为他物。更何况从总体上看,由于世界的无限性,气的“定形”疆界是不存在的,气终未被定形,使气成为“气之物”的同样是“无”。气作为无定形的否定性概念,它不足以使世界获得肯定性的现实基础,不足以成为一切有形之物的生成原因,亦未能将世界统一起来。气论有待于深化,赫拉克利特的火论,便是自然哲学深化的结果。火的思想是古希腊自然哲学(抑或是整个古希腊哲学)的一次意义重大的飞跃,它开启了一个更为深邃的理性思辨阶段。
火的思想在阿那克西曼德哲学中已见端倪。在其著名的“宇宙起源说”中,他认为本原是运动的,从本原中分离出一些对立物如冷和热、湿和干,对立物形成涡旋式运动,由此便使冷而湿的东西凝结于中心,热而干的东西扩散在外围成为火球。由于火的影响,在中心的冷而湿的东西一部分烤干为地,剩余的为水;水又在火的作用下蒸发为云雾(气)。气由于蒸发(火)而具有了冲力。气的膨胀使外围的火球破裂成车轮式的火环,每个火环上面有一个通气的孔道,从孔道中所显现出的火就是日月星辰。由此观之,火是矛盾性同类物之凝结物,它是一些其他元质的驱动力;同时,火又受外在他物(如气)的作用,这种影响来自于火自身的作用(如使气膨胀)。因此,火既是他物的结果又是使他物、使自身运动的原因,亦是他物形成的原因。但是,火的自动与他动之力是分离的,并未统一于火,而是通过中介(气)完成的。此外,火由他物转化而来,并不是世界的始基,构成火的质料与形式先于火,优于火,火亦未能使两者统一于自身。然而,阿那克西曼德之火,毕竟有了使他物定形的动能,是日月星辰等光明之所。这火,在赫拉克利特的“火论”中燃烧成为了统一的“大火”。
赫拉克利特之火是永恒燃烧的“活火”,是一种肯定性存在。火不像水、气那样无自身定形的力量,也不像“无定形的东西”那样虚无漂泊。火是无定形的定形体,是自我定形的无定形者,同时还是给他物定形的主动者和推动者。它既是定形的又是无定形的;既是统一的、无限的,又是可分的、有限的;既是普遍的、又是单一的。它实现了质料与形式的自身的内在统一。在这里,统一性与多样性、形式与质料达到了本质上的一致。由火来规范世界,使自然哲学获取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而使人与自然亦相通相融。在人那里,“火”便体现为理性和激情,这便是往后“逻各斯”和“奴斯”的原型。
火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它是一股内在的积极进取的正义力量,是必然性、规律性的使者,是自变与促使他物变化的动因,变化之动力来自于矛盾和斗争。火作为自由而能动的主体,它给自己定形或给他物定形都不是盲目的、不自觉的,而是有方向、有目的的自觉行为。它遵循着一定的“分寸”和“尺度”,“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4〕这分寸,这尺度,便是“逻各斯”,它是使火成为火,使万物成为万物的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形式和规律。“逻各斯”使得同一性质或性质各异的东西构成为具体之物,使世界呈现出色彩斑斓、流变不已的生动壮观图景。“逻各斯”的提出,使质料与形式、动力与规律都统一于本体自身成为可能,“火”因之而拥有了目的性、必然性和规律性,成为了统摄宇宙的“大一”,具体之物(“小一”)则与它同样光泽,成为独立自存的存在。据此可以认为,火是世界自我生成、自我运动、自我统一的基础,是世间万物形成的本原。
可是,火仍然是具体的感性之物。它在实现了将世界统一起来的“本体”任务之后,却将自己排斥在了本体之外;它在规范他物成为他物之时,却使自己为何成为自身成为了问题。构成火的质料是什么?使火自变和推动他物运动变化的“变者”是什么?火使自身分裂了,并未真正将质料与形式统一起来。另外,“逻各斯”作为尺度、规范、规律、“理性”,更多的是一种外壳,一种框架。这外在的规定性如何实现?如何充盈以实现“尺度”?阿那克萨哥拉提出了“种子”说和“奴斯”论,发展了“火”的思想,对本体作了更进一步的规定。
阿那克萨哥拉认为,“世界的东西在数量上是无限的。”“每一件东西本身都是既大又小。”因而“结合物中包含着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即万物的种子,带有各种形状、颜色和气味。”〔5〕种子是万物的“种子”。种子相互联结,彼此影响,拥有诸多因素或属性,数量无限多,体积无限小。小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大亦不表明它是具体的定形之物。种子克服了火的具体可感性和形态的有限性。它既大又小,是定形与非定形、实体与非实体、存在与非存在之统一体。“非存在”是相对于“存在”而言它失去了确定性,而非“不存在”,非存在亦是一种存在(这是“虚空”的雏型)。因而种子是构成万物的最初元素,火只是万物中的一种,火亦由火的种子所构成。种子无限可分,所以种子的混合与分离也是无限的。一切是一,一是一切,每种事物既是“一”,又是“多”。“每件事物中都包含着每件事物的一部分”〔6〕, 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联结是形成万物的必要条件。因此,一变为多,多归于一,宇宙万物既是多样的,又是统一的。由种子所繁殖生成的世界必定是有限与无限、一与多、普遍与特殊、存在与非存在的统一体,是相互影响、互为一体、普遍联系的。“种子”是在种类上无限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本体”是多元的。因为“种子”作为一个总体概念,它是“一”,是“类”。这种情形与“无定形的东西”类似。这表明,在自然哲学那里,物质本体的“抽象”亦是客观的物质性抽象,而不是“理念”式的主观性的精神。
“种子”既是构成万物的质料,又拥有自身决定自身并进而决定他物的形式和动力。大凡“种子”都有繁殖功能。它虽有形,但种子的本质是基因的无形性。唯其如此,它才能成为生命的胚胎,才能按照自身的生命原则去实现那有形的使命。这冲动的能动力量和生命原则便是“奴斯”。
在阿那克萨哥拉看来,“奴斯”是能动的心灵、灵魂,有目的,守秩序,它不仅能安排这个世界,而且能按“理性”将世界安排得和谐美好。这“理性”更多的是指尺度即“逻各斯”。似乎可以说,“奴斯”是实现“逻各斯”的内在冲力。在自然领域,“逻各斯”与“奴斯”表现为规范与内在冲力之关系,在精神王国,两者则体现为“概念”内(人的)理性与感性的矛盾。(这并不意味着阿那克萨哥拉自觉到了奴斯与逻各斯的内在关系,只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里,两者才构成对应关系。这是一次跨世纪的飞跃。)同时,奴斯是“无限的,自主的,不与任何事物混合,是单独的,独立的”〔7〕, 是万物生成的原初功能,是普遍的能动法则。据此可以认为,奴斯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是自立于“种子”之外的。这是对泰勒斯“灵魂”思想的回归,是潜存于“嘘气”、“活火”等自然哲学中的能动性、主体性原则的显现。
但是,种子虽然精致,但它仍是一种概括和猜测性抽象,就整体而言,它既是什么又不是什么。它作为存在的部分,只有与别的成分相结合时才能发挥作用,成为构成他物的有机部分,因此,即使是具体的“种子”亦不能独立自存。一种事物是多个种子的产物,由此类种子所衍生的世界应是浑沌的混合体。种子作为抽象的普遍性存在,难以完成统一世界的本体任务。奴斯虽然自主自为,能动有为,但它作为与种子并列的另一“本体”,便从种子中分离了出来,因之而丧失了其存在的根基。它虽然拟人化地存在于万物之中,但它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则只能存在于(人的)精神世界。由此,奴斯便拥有了精神性质,演变成为了情感和激情的冲动力量。它作为一种精神性力量,则不能成为宇宙万物自己运动的原因。此外,种子与奴斯作为“本体”的二元对立,使质料与动能分离为二元存在。这样,世界之物质统一性也初步分离成为了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这不仅破坏了自然哲学的统一性基础,而且还为往后哲学形态的分化播下了“种子”。(亚里士多德首分科学与哲学的研究领域则是这种分离的“意外”收获。)
由种子和奴斯发展到原子和虚空,是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必然归宿和逻辑总结。如同火、“无定形的东西”和气之辩证关系一样,由火到种子再到原子亦呈现出“正反合”式的逻辑建构态势和内在承袭关系。
原子论者(留基伯、德谟克利特)认为,物质自己是自身产生、存在和消亡的原因,“没有一样东西是从无中来的,也没有一样东西在毁灭之后归于无”,而“一切事物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8〕原子与虚空“是一切事物的质料因”,但它们仍属另一个更为根本的实体——“元素”〔9〕。原子和虚空都是组成世界的元素。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原子论者实际上是将元素视为本体,而原子与虚空则是元素在质料和形式上的二分。原子是由元素构成的充满的小球。小球有形,但此形有别于虚空之形。虚空作为一种元素,其特点是“空虚”、“疏松”。它广阔无垠,是供原子组合、聚集成“球形的东西”的场所,是“大形”。由原子所构成的球形之物,运动着,“燃烧”着,形成为大地和星辰。这类似于阿那克西曼德的宇宙生成论,同样具有火的冲动。原子论将火的热烈与种子的柔情溶为一体,使原子占有了奴斯的冲力;原子论认为灵魂(奴斯)也是由原子构成的,“一切都遵照必然性而产生”〔10〕,逻各斯的蕴意亦保持在了原子之中。
原子论用“一”(元素)将质料因(原子)、形式因(虚空)和动力因(奴斯)统一了起来。“德谟克利特说灵魂是一种火或热的东西。”〔11〕这似火般冲动的奴斯便是原子构成为他物的驱动力。原子独立自存,虚空和奴斯使原子既有自我规范性又有运动变化的动力。原子作为无定形的元素的自我定形者,它是一些圆球式微粒,是构成万事万物的定形之物。“圆球”之物滑润细腻,富有惯性,便于运动,因而具体个别事物便有了生存和发展的理由;原子又具有同一性,不可分,不可入,是最普遍的类,因此,世界万物又具有一致性和共同存在之基础。作为元素的另一种形式,虚空虽为形式因独立于原子之外,但它与原子仍具有一致性和相通性,因而可以服务于原子的集合与分离的创作活动。据此,原子与虚空可视为一个因素的两个方面,“存在者并不比不存在者更实在”,虚空作为“不存在者”,与“存在同样实在”。〔12〕因此,原子和虚空既是个别的又是普遍的,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是个别与一般之统一体。由原子和虚空所构成的世界必定是一元性的自我形成、自我发展、自我统一的物质世界。
若说种子是个抽象的普遍概念,那么原子则是一个实体性概念。它否定了种子的不确定性和抽象性,使本体重新获有了实体性和确定性。原子与火一样还是一个肯定性概念,它有超越一切具体感性之物的可操作性。若说火是个具体的可感之物,或说“火”是一个具体有限的“抽象”概念的话,那么原子则是无定形的普遍性“抽象”概念。它比火更无定形,比火更精致玄妙,尤其是它比火更普遍、更原则。它克服了火的具体性和有限性,使本体具有了普遍性和无限性。同时,原子与虚空的统一,避免了由于种子与奴斯的二元化倾向所带来的理论陷讲,将质料与形式复归于本体自身。原子论还否定了奴斯的精神属性,将质料因与动力因合为一体,坚持了世界的一元论原则,恢复了本体论“大一”统宇宙的权威。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原子论仍然陷入了自己理论所设下的“虚空”之中:其一,原子、元素,作为实体性、肯定性概念,它仍然不是最小的微粒,从而亦陷入了具体与抽象的矛盾之中;其二,原子、虚空、奴斯在异质同构的非本原意义上是各自独立、平起平坐的,那么谁更根本?其三,逻各斯与奴斯都是作为原子的不同形态而各自独立,分而存在着,两者并未统一于现实性的“一”,亦未能建构成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新质性“共同体”,因而本体缺少了目的因。这样,奴斯作为原子的一种表现形态,便消失了它在(阿那克萨哥拉哲学中)“心灵”意义上的目的性,而成为了一种盲目的躁动。原子、虚空期待“实体”,奴斯(和逻各斯)企盼“隐得莱希”。这一切都在亚里士多德的终结性哲学体系中寻找到了历史的回音。
由上可知,早期自然哲学家自觉不自觉地思考着形式与质料、目的与动力等种种问题,如:质料是什么?质料来自何方?质料构成为他物的动力来自何处?是质料自动还是外力推动?动力机制为何能够推动质料构成为他物?动力遵循什么法则?是自律还是他律?世界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若是有限的,那么本原又来自于什么?若是无限的,那么本体何以能使世界无限?构成世界的本体又从何而来?规范本体的形式是什么?本体按什么形式去建构他物?本体有形吗?若无形,那么它何以能够使万物有形?千姿百态的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又统一于什么?本体若有形,那么使本体成为本体的“形”又来自何处?”形是本体自身所有还是外在的规定?若是本体自身所有,那么本体便是具体的感性之物,这具体的感性之物何以能成为形态各异之物的原因?这具体之形若来自本体之外,那么这外在的形式又如何产生?世界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到底是什么?
质料与形式以及由此而衍生的种种矛盾,实质上是“用来表达哲学概念的语词在意谓方面的感性局限性(如具体的“水”)与它所承担的普遍使命(即成为万物的本原)不相适合的矛盾。整个希腊早期自然哲学的发展和运动,可以说都是这一内在的基本矛盾在思维中不断推动的结果。”〔13〕这一矛盾亦即是具体与抽象的矛盾。它根源于“一统二分”式的自然哲学以及“二分”的思维方式。古希腊时期,哲学与自然科学浑然一体,对象未分,自然哲学是科学与哲学的统一体。作为自然科学,它以具体的感性之物为研究对象;作为哲学,它以普遍性抽象为原则,由此便形成了自然哲学用具体可感之物作为规范宇宙的普遍性原则的两难选择和思维矛盾。
尽管存在着理论思维矛盾或具体与抽象的两难选择,但是,古希腊自然哲学毕竟为唯物论奠定了本体论基础,此“开端”亦决定了往后物质本体论发展的基本态势和理论特征。古希腊自然哲学本体化的逻辑进程告诉人们,哲学作为研究“存在”或“有”以及“有”凭本性具有的各种属性的学说,其最高原则是“有”或“存在”。〔14〕本体、本原、始基是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不研究“有”的“哲学”不成其为哲学,而只能是某种哲学形态的部分内容的延伸(如“四根说”)。“有”“在定义上、在认识程序上、在时间上全居第一位”,并“能够独立存在”。〔15〕因此,本体是“一”,是多中之“一”。它不能由其他事物来规定,它不是“二”。自然哲学是从自然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因而统一、规范世界的本体必然是产生于自然世界本身所固有的客观性存在。具体的个别事物也好,抽象的种类事物也罢,自然哲学的物质本体决不能掺杂进半点人为的“主观性”因素。渗入精神因素的本体,便不是物质本体,而是主客观交织的“人造物”。在这里,不掺杂“主观性”因素,是说在诸如水、种子、原子等等“本体”之中,物质是客观地独立存在着的;并不是说它们里面未带有哲人的主观猜测或理性推理的因素。本体是“一”、“人造物”是“二”。貌似客观的主客观渗透体,必然与二元论殊途而同归,“被劝的”物质最终要倒向“主动的”精神。(虽说亚里士多德本人不赞同“一”为本体,但他不赞成的是柏拉图式的“一”——脱离了个别的理念王国。事实上,在亚里士多德所建立的古希腊最庞大的综合性体系中,尽管到处是二——这是协调各种矛盾的需要,但是,从本质上看,他是歌颂“一”的,“二”服从并服务于“一”。这一点,仅从他的“第一哲学”、“第一实体”、“第一动因”、“第一推动者”等思想中便可见一斑。)自然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对于我们今天理论界讨论“本体论”问题亦不失为一种启示和回答。
自然哲学本体论的思维矛盾或具体与抽象的二难选择所陷入的思维困境告诉人们,哲学的“有”有别于自然科学的“有”。由于古希腊自然哲学本体论的影响和制约,往后的物质本体论从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继承了“具体性”,强调的是个体、微粒,直到近代的“原子”,愈来愈精细和精确;一是发挥了“抽象性”,强调的是种类、共性,直到斯宾诺莎的“实体”,越来越充盈和神奇。但是物质本体的种种矛盾依然如故。至此,转变思维方式的问题显得至关重要。因此,当“客观存在”出现在物质世界之时,唯物论哲学便有了坚不可摧之“物质”本体。这一一劳永逸的解决方式,为科学的世界观奠定了物质基础。
注释:
〔1〕〔2〕〔3〕〔13〕邓晓芒:《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8、18、15页。
〔4〕〔5〕〔6〕〔7〕〔8〕〔9〕〔10〕〔11〕〔12〕〔13〕〔14〕〔15〕《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1 、38、39、39、47、49、45—47、51、47、122、1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