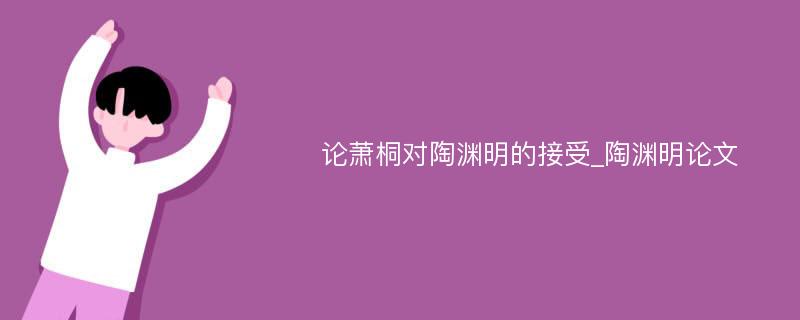
论萧统对陶渊明的接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陶渊明论文,论萧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陶渊明在中古时期最高的评价来自梁代昭明太子萧统。萧统“望陶以圣贤”,〔1〕不但在为人上给陶渊明以崇高的赞扬, 而且在为文上给他以前所未有的至高评价。他自称“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萧统《陶渊明集序》)他为陶潜编集、作序、作传,并于自己的创作中用陶潜之典,并于历代文人学子必读必究的《文选》中选录了陶潜诗文。因此,在陶潜尚被忽视的时代,萧统在陶潜的接受、传播史上写下了最有价值的一页,为陶潜的被接受开通了重要的渠道。
一
与其诗文的遭遇截然相反,陶潜的为人在中古时期就有口皆碑。为陶潜作诔的颜延之、写传的沈约对其为人都极为推崇。萧统的叔父萧秀天监六年(507)为江州刺史,“及至州, 闻前刺史取征士陶潜曾孙为里司。秀叹曰:‘陶潜之德,岂可不及后世!’即日辟为西曹”。(《梁书·萧秀传》)
萧统对陶潜为人的记述、推崇基本承袭了时人的观点,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对比萧统《陶渊明传》和沈约《宋书·陶渊明传》(以下分别简称《萧传》和《宋传》),我们会发现萧统对陶潜的刻画有一种理想化、完美化的倾向。《宋传》云“(陶)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此虽推崇陶之操守,但对其年轻时“不洁去就之迹”却略有微词。《萧传》对陶的生平记述基本上承袭了《宋传》,但对上面引文,删去前两句,只说“自以曾祖……不复肯仕”云云,对陶潜早年的仕宦生涯不置微词。这说明萧统对陶的节操比沈约更加推崇。因此,他在传记中除了承袭记载了陶潜不愿折腰向乡里小儿、自解罢职一事外,又记载了《宋传》中没有的两件事:一件是江州刺史檀道济以“粱肉”救济断炊的陶潜,被陶“麾而去之”,另一件是作诗嘲讽出山的周续之等在马队边讲《礼》。这两件事都突出了陶潜高尚自洁的操守。
萧统将陶潜理想化的倾向在他的《陶渊明集序》(以下简称《陶序》)中得到进一步鲜明的体现。沈约在《宋书·隐逸传》开头站在儒家入世者的立场上来推崇“贤人之隐”,把他们所晦之道看作以社会为指归而非以个性为指归的儒家之道。萧统在《陶序》中则主要以道家思想为准的推崇陶潜。他说:“圣人韬光,贤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逾于道,亲已之切,无重于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可见他所理解的道实为道家自然之道,主要以觉醒的自我个体为指归,而非以儒家等级社会为指归。人只要获得道之德性,“与大块而盈虚,随中和而任放”因以晦迹,与道逍遥,得享天年,便是圣贤。否则因逐物欲而亡道害身便是愚夫贪士。而陶潜“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才为病”,“与道污隆”,正是一位得道全身的近代“大贤”。
陶潜的生活情趣和爱好以其鲜明的特色也倍受中古接受者称赏。陶潜好酒是出了名的,从颜延之开始便推崇他“性乐酒德”,把他的饮酒看作隐士高洁出俗的举动。之后,陶的早期接受者江淹、鲍照、钟嵘等都提到了陶潜与酒的关系。沈约在《宋传》中把饮酒看作陶潜的独特爱好,除了引用陶潜作品中写酒的文句外,在他自己的叙述文字中接连六次写到陶潜和酒的关系。
萧统在《萧传》中承接《宋传》进一步突出了陶潜的好酒志趣,七次写到了陶与酒的关系。除了沈约写到的六次外,还补写了一次。《萧传》云:潜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尝得醉于酒足矣!’”因要“舂秫作美酒”(《和郭主簿》),所以“悉令吏种秫”。萧统补写的这一笔不但解释了为什么悉令种秫的原因,而且富于夸张性地突出了陶好酒的志趣。
在《陶序》中,萧统还第一次揭示了陶潜饮酒的内在涵义。他说至人达士晦迹山林,“或怀釐而谒帝,或披褐而负薪,鼓枻清潭,弃机汉曲,情不在众事,寄众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这里,萧统联系对隐士“寄众事以忘情”的理解来阐释陶潜的饮酒行为,说他“意不在酒”,也是“寄酒为迹”,即像众贤人达士意不在负薪、鼓枻,而是以之为生命依托,来忘掉俗情一样,陶潜饮酒也是如此。这便将陶潜饮酒的志趣同一般意义上的饮酒区别开来,点出了饮酒行为背后的深层寓意,为后人进一步挖掘出陶氏饮酒行为背后的涵义开辟了路径。
萧统还将陶潜饮酒的志趣及其诗文中写到的其他典型意象,以典故的形式写入自己的诗文。其《锦带书十二月启》云:
走野马于桃源……放旷烟霞,寻五柳之先生。琴尊雅兴,渴孤松之君子。(《夹钟二月》)
郁郁丹城,并挂陶潜之柳。(《中吕四月》)
既传苏子之书,更泛陶公之酌。(《南吕八月》)
“陶公之酌”、“五柳之先生”、“陶潜之柳”、“桃源”等,都是作为一种高雅脱俗、自由自在的隐居生活或环境的象征而被引用的。这种现象表现了萧统本人对陶潜审美情趣的心向神往,从而表明陶潜的志趣爱好,理想憧憬、生活方式已开始被象征化、模式化,开始获得越来越普遍的文化新义。这在萧统的时代并非是孤立的存在。下面是梁代诗文中几则珍贵事例:
鱼从流水,本在桃花之源。(萧绎《荆州放生亭碑》)
虽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径。接五侯,不妨门垂五柳。(萧绎《全德志论》)
篱下黄花菊,丘中白雪琴。(庚肩吾《赠周处士诗》)
况乃交垂五柳,若元亮之居。(庚肩吾《谢东官赐宅启》)
纺绩江南,躬耕谷口。庭中三径,门前五柳。(费昶《赠徐郎六章》之六)
开筵临桂水,携手望桃源。(沈君攸《赋得临水诗》)
在上面的诗人中,萧绎是萧衍七子,萧统七弟,后来的梁元帝。庚肩吾在萧纲为太子时,兼任东宫通事舍人,属上层文人。费昶,江夏人,官至新田令。沈君攸生平不详,但据其遗诗, 至少应为下层文人〔2〕。上列文人诗文中所用陶典,最多的是“桃源”之典和“五柳”之典。前者用以指超出凡俗、非人间所有的美好所在,后者用以指隐士居处的象征景物,用以抒写性爱山水、高雅脱俗的胸怀志趣,表现出当时重隐崇隐的时代之风。可见,陶潜作为高雅隐士的形象是颇受梁人推崇的。
三
中古时期,陶潜诗文虽然一直悄悄地被有识之士发现、接受和传播,但也有许多有识之士忽视了陶潜诗文潜在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颜延之、沈约接受陶潜,重其为人而轻其为文。刘勰《文心雕龙》、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对陶潜只字未提。有史家眼光的评论家当中,独钟嵘与萧统独具慧眼,看到了陶潜诗文的夺目光彩,而尤以萧统为最。
如评陶的为人一样,萧统评陶的为文也有理想化、完美化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陶序》中,萧统给予了陶潜诗文以前所未有的极高评价。
概言之,萧统把陶潜的为文和为人统一起来考察,看到了陶潜文如其人的特点。钟嵘在《诗品》中已表现了将陶潜为人与为文联系起来的倾向。他说:“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而又推崇“陶公《咏贫》之制”(《诗品序》),评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说“每观其文,想其人德。”这里钟嵘把陶潜隐居、清贫的生活、高尚的品德和他的诗文联系了起来,但尚不直接,也不具体。而萧统则克服了这一点,在《陶序》中,他先以古代贤人达士暗比陶潜,接着对其为人为文交互评赞。在指出陶诗篇篇有酒的同时,又品出“酒中有深味”(陶潜《饮酒》之十四);在高度推崇其文章取得的艺术成就的同时,又赞扬他“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云云。这便把论文与论人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向我们指出陶潜文如其人。
具言之,萧统认为陶潜诗文的特点首先表现为“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跌宕”、“抑扬”近义,是指陶潜诗文情感充沛而富于变化,而非平铺直叙,寓目辄书。“昭彰”、“爽朗”近义,是指情感表现清澈明朗,不浑浊晦涩,即《文心雕龙·风骨》所谓“风清”“文明”。合而言之,陶潜诗文超群出众,文采精妙拔俗,情感显豁起伏而动人情性,有一种超越众人,无与伦比的风力。这种评价与钟嵘评陶“协左思风力”是相通的,也符合齐梁人以诗歌吟咏情性、摇荡性灵的文学观念。
其次是“横素波而傍流,千青云而直上”。这是从总体评陶潜诗文在精神风貌上立志高远,远离尘俗喧嚣,远离声色歌舞。
再次评陶潜诗文“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渊明所处正是晋宋易代之际,正如汉末、魏末“道丧向千载”(《饮酒》之三),“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序》)。历史上频繁上演的弑君之剧这时又重演了一次。渊明好多诗中暗写了晋宋易代的时事。如其《述酒诗》、《读山海经》之十一、《拟古》之九等。沈约在《宋传》中就指出陶潜诗文年号在晋宋所标相异的现象。《萧传》上承《宋传》,推崇陶潜不仕二代,在《陶序》中又说“语时事则指而可想”,当是指陶潜诗文中那些隐射晋宋易代的作品。因此,萧统是陶潜接受史上最早将其作品与时代联系起来解读的读者之一。
萧统又进一步从陶潜诗文的情感特质上将其诗文取得的高度艺术成就概括为“旷而且真”。旷,本义指空间的辽阔远大。《老子》用之来形容道,曰:“旷兮其若谷”(15章),使道具备了抽象的哲学意义。后来,特别是品评人物兴盛的中古时代,旷又获得了价值、审美意义。《世说新语·品藻》王导评王述云:“真独简贵,不减父祖,然旷淡处故当不如尔”。又《任诞篇》云“张季鹰(翰)任诞不拘。”刘注引《文士传》云:“(张)翰任性自适,无求当世,时人谓其旷达”。旷,都是指心胸开阔,对世俗孜孜以求的东西不存芥蒂:陶潜虽箪瓢屡空,却依旧“晏如”,他“不慕荣利”,“忘怀得失”(《五柳先生传》),正表现了开朗阔达的胸怀。所以萧统用“旷”来评价陶潜。
那么“真”又指什么呢?《老子》云:“道为为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21章)。又云:“修之身,其德乃真”(54章)。真是道与德在本原意义上的属性。《老子》又云:“道法自然”(25章),真又是自然的本性。因此《庄子·渔父篇》进一步发挥说:“真者,所以受于天地,自然不可易人。”真表现在物身上就是物的天性,故《庄子·马蹄篇》云:“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真表现在人身上就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来自我:“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者无声而哀,真怒者未发而威,真亲者未笑而和”(《庄子·渔父篇》)。真既然是人内在的本来自我,所以人要“法天贵真”(同上),要“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庄子·秋水》)。如此则获得了自性,获得了自然之性,与自然融为一体,回归到宇宙万物和谐初始的化境。
陶潜“养真衡茅下”(《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要追寻的最高人生境界也正是“真”的自然境界。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之五)正是对这种境界的审美幻觉。在这种境界里“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之十四)“不喜亦不俱”(《形影神》)。在日常生活中当然不可能总达到这种伴随着审美的形而上体验,但是不论做什么,陶潜都以“真”为依归,精诚待人,不“强笑”、不“强怒”、不“强亲”,而是“真悲”、“真怒”、“真亲”。总之,陶潜诗文中流露的是精诚、真挚的感情,摆脱了世俗的旷达之情。即渊明并非心胸狭隘者,他虽发抒真情,但不执迷于真情,难以自拔,而往往以理、以玄遣情,重情而不役于情,显得心胸开阔,旷达脱俗。因此萧统评陶曰:“论怀抱旷而且真”。是明言其感情特质拔于流俗,有“大贤”之风,读其文如见其人。此唐人所谓“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皎然《诗式》),也是后人评陶“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的本源(元好问《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钟嵘《诗品》亦以“真”评陶,说陶诗“笃意真古”,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总之,萧统认为陶潜文如其人。其人为“大贤”,“少有高趣”,“颖脱不群,任真自得”(《萧传》)“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发抒旷达真情。其文与其人皆堪称楷模。
三
萧统评陶的理想化倾向还表现在他苛求陶潜《闲情赋》的看法上和重视陶潜诗文的社会作用上。
萧统在《陶序》中高度评价了陶潜文如其人之后,接着说:
白璧徽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尝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去,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亦乃爵禄可辞!不劳旁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耳。
一方面,他认为像陶渊明这样的“大贤”是不应该写无助于讽谏的《闲情赋》这样的文章的。在萧统的人生观中存在着言行一致的观念,即人的心灵与外在的一切行为(包括创作)应该在真善美上统一起来。他主张“立身行道,始终如一”(《梁书·到洽传》评到洽语),推崇“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的文章(《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而他本人也是如此做的,“持性严谨,不畜声乐”(《南史》本传),而非如其弟萧纲所云“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那么陶潜既为“大贤”,就应写“大贤”之文,而不应有失身分,写《闲情赋》这样“劝百讽一,卒无讽谏”的文章。当然。萧统本人排斥浮艳之文,但并不完全排斥写女人。这从《文选》中所选的宋玉等人的情赋及他自己创作的《三妇艳》等写女人的文字可以看出。按儒家文学观念,写艳情、写女人可以,但应好色而不淫、“既温且雅”(萧统《答〈玄圃园讲颂启〉令》)、“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闲情赋》写爱情大胆奔放,虽“终归闲正”,但爱的表白太直露、太热烈,有伤温柔敦厚,有伤中和之美。这就难怪有着浓厚正统观念的昭明太子为陶潜这样的“大贤”写这样的文章而叹息了,觉得“亡是可也”。而于《文选》中也不予选录。
与上述相联系的是,萧统高度评价了陶潜诗文的社会教育作用,认为其诗文有助于风教。这与萧统从小所受的儒家正统教育、太子身份以及与时代批评风气息息相关的文学主张密切相关。其父萧衍从小便注重对萧统进行严格的儒家经典熏陶(《梁书·昭明太子传》),萧衍晚年很注重诗文的教化作用(《梁书·徐摛传》)。作为皇储,萧统的文学思想与其父晚年的文学思想是较为一致的,都黜靡崇雅,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与曹丕、陆机等一脉相承,齐梁文论家面对讹滥的文风,大多没有忽视儒家风教观。萧统就是站在这种批评氛围中,形成他的风教观的,非但在《陶序》中,而且在《文选序》中也有鲜明的言论。他依此来评价陶潜的作品。虽看到一篇《闲情赋》不合风教观,但总体上认为陶潜诗文还是可以激贪厉俗的。因此,他高度评价了陶潜诗文“有助于风教”的社会教育作用。
四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文选》的传播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萧统紧密联在一起的。而《文选》中编选了陶渊明诗文,所以萧统《文选》成为后人接受陶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途径,这在陶渊明诗名未盛而《文选》广为人知的唐代尤其如此。(限于篇幅,本节将另文论述。)
五
总之,萧统在陶渊明接受史上写下了极有价值的一页。那么萧统为什么会接受陶渊明呢?萧统接受陶渊明的根本原因何在?
文明和异化的二律背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4〕“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 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5〕魏晋时期是中国封建文明的成长期, 这种文明的成长也是依靠恶的形式促成的,是以平静的家园和古老而神圣的道德的丧失为条件的。这便是历史前进过程中文明与异化的“二律背反”。陶渊明看到了历史发展带来的丑恶:“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序》)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陶渊明在痛苦和彷徨中拒绝了历史发展的逻辑,毅然在历史发展所否定的平静家园和神圣道德里寻找生命的依据。他固穷守节,躬耕自资,安贫乐道,用整个生命实践了整整几代人在痛苦中寻求的真善美的人生,铸就了一种拒恶守善的高洁人格。萧统对此大加赞扬说:“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原因就在于作为同一历史时期的接受者,萧统也面临着社会、历史带给他的痛苦和彷徨,因而他与陶渊明有着相似的心灵渴求。
据《梁书·昭明太子传》,昭明太子与其父梁武帝的关系并不好。“昭明对梁武帝始终是深怀畏惧,战战兢兢的”。〔6〕作为皇储, 萧统密切注视着梁武帝的思想言行,随时在自己的一言一行里作出响应以取得父皇的欢心。如武帝崇尚俭朴,萧统亦时时奉行;武帝大宏佛教,萧统亦崇信三宝,遍览众经。从梁武帝多次干预萧统的行动看,萧统的思想言行也是处在父皇的密切监视之中的。发生在普通七年的事是最典型的例证。这一年统母丁贵嫔薨,萧统哀毁骨立,不进饮食,武帝多次派人制止他的这种过分行为。名义上是劝儿节哀,实则不满儿子的做法,明确地对儿子说:“有我在,那得自毁如此!”“正为汝如此,胸中亦圯塞成疾”。可见,萧统连饮食起居也在父皇的监视干预之中,他的其他言行就可想而知。也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充分暴露他们父子间矛盾的事件。《南史·昭明太子传》称:“初,丁贵嫔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将斩草,有卖地者因阉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万,许以百万与之。三副密启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于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毕,有道士善图墓,云地不利长子,若厌伏或可申延。乃为蜡鹅及诸物埋墓侧长子位。有宫监鲍邈之、魏雅者,……密启武帝……帝密遣检掘,果得鹅等物,大惊,将穷其事。徐勉固谏得止,于是唯诛道士。由是太子迄终以此惭慨,故其嗣不立”。年仅31岁的萧统史载因溺水受惊而死,其真假也是一个谜。可见,身为太子的萧统因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并不能获得一个正常人应有的自由和轻松。陶渊明所指斥的“大伪”,天天在宫廷上演,而且他也不得不于其中扮演一个角色。因此他所奉行的儒家神圣道德和向往的平静生活受到了无情的嘲笑,他绷紧的神经和劳累的心灵需要一块休息的天地。对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的萧统来说,最好的休息天地莫过于自然的家园了。
事实上,萧统经常让他绷紧的神经和劳累的心灵在社会推崇和认可的自然山水里放松和休息。《梁书》本传称他:“性爱山水,于玄圃穿筑,更立亭馆,与朝士名素者游其中”。他这种将山水纳入紧张人生的生活情趣在他的《与何徹书》、《答晋安王书》、《七契》等多篇文章中都有鲜明的体现。从现存《全梁文》看,梁代还没有哪一个人对自然的兴趣比萧统表现得更浓厚。正是在自然家园里,通过与战战兢兢的宫廷生活相对比,萧统读懂了包括陶渊明在内的隐士之所以归隐的原因:存道全身(《陶渊明集序》)。从而对隐士倍加推崇。而隐逸诗人陶渊明在他的诗文里为在文明与异化的二律背反中挣扎的人提供了一种自然的精神家园,足以使“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消除社会历史发展带给人的异化现象和心灵矛盾,获得现实生活中寻找不到的心灵和谐。所以当爱好文学的萧统在读陶隐士的诗文时便摆脱了宫廷生活带给他的紧张与痛苦,在陶诗文构筑的自然家园里获得精神上的解脱,也难怪他对陶诗文爱不释手了。这便是萧统对陶渊明为人为文高度推崇的根本原因所在。
注释:
〔1〕郭于章《豫章诗话》。
〔2〕参见其《陆廷尉惊早蝉诗》、《羽觞飞上苑》诗, 逮钦立辑《先秦汉魏南北朝诗》(下)第2110~2112页,中华书局1995年1 月版。
〔3〕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颜氏家训全译》本第18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版。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33页、第二卷第67 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3月重印版。
〔6〕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下第59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