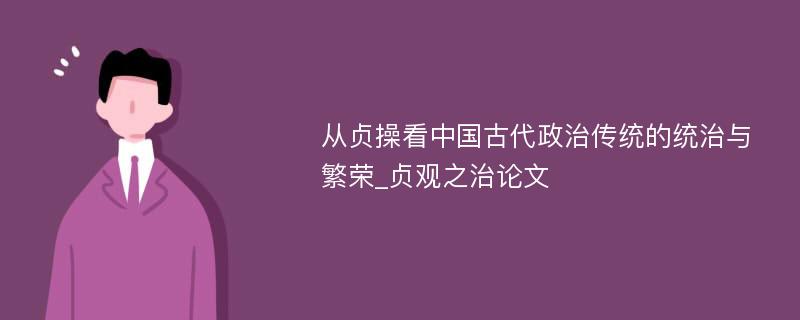
从贞观之治看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世与盛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贞观之治论文,盛世论文,古代论文,传统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917(2003)02-0064-06
在中国历史和政治传统中,贞观之治既是指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的统治局面,也是一个核心的政治概念。作为历史事实的贞观之治,是指唐太宗统治下出现的政治局面;作为政治概念的贞观之治,则是被贞观以后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不断阐发的治国理论意义上的一个理想,是被“层累地造成”的历史。唐太宗时期的统治局面之所以被称为“贞观之治”,源于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对统治形态进行划分的概念系统。在王朝更迭的历史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治理局面,对治理局面的界定,大抵可以归入治世与乱世、盛世与衰世等概念系统之中。对世局进行治乱兴衰的划分,并对此进行褒贬,是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功能,也是中国政治传统的重要内容。从历史事实和历史观念双重角度,廓清这些概念,对于进一步认识中国史学传统和政治传统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本文以贞观君臣在治国实践中所运用的政治概念为中心,探讨帝道与王道、治世与盛世等概念形成的历史传统,进而分析“贞观之治”本身如何成为一个政治概念并进入到传统的概念系统之中。
1 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世与盛世
由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由于史官和史学在中国早期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使得对王朝更迭和治道兴衰的历史现象的探讨,构成了对治国理论进行探讨的核心内容。
早期儒家政治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基础,就是对古史及其政治形态进行系统性的构造。从东周到秦汉之间,以儒家为主,根据不同的古史信息,从不同渠道汇合而成了一个以“三皇五帝”为核心的圣圣相传的圣统史观,[1](P149)加上夏商周的历史衔接,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古史体系,它既是一个历史演进的系统,也是一个政治观念的系统。政治观念依托于对历史时代的定位,这是中国政治传统中的重要特色。
在这个系统中,尧舜之道是治国的最高境界,是圣人之道,是帝道,其具体内容,用出土的由战国儒家编撰的《唐虞之道》的话说,就是“禅而不传”和“爱亲尊贤”[2];夏商周三代之治,则是礼乐文明,是王道。《礼记·曲礼上》:“大上贵德,其次务施报”。郑玄注曰:“大上,帝皇之世,其民施而不惟报。三王之世,礼始兴焉。”大上,就是太上,谓三皇五帝之世。三王之世,就是禹、汤、文武为代表的夏商周三代。《礼记·礼运》篇对此有更具体的解释: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按:唐代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二时指出:“《礼运》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即帝也。大道既隐,各亲其亲,即王也。”宋代朱熹在《答吕伯恭》的信中也谈到:“《礼运》以五帝之世为大道之行,三代以下为小康之世,亦略有些意思,此必粗有来历,而传者附益,失其正意耳。如程子论尧舜事业,非圣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贤可为也,恐亦微有此意。但记中分裂太甚,几以二帝三王为有二道,此则有病耳。”(注:朱熹:《晦安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三,四部丛刊本。)在朱熹看来,尧舜之道和三王之道其实是一个道,这是一个哲学意义的“道”。但从政治形态来说,其间大同与小康、帝道与王道的区别还是明显存在的。
帝道王道之下,在治国实践中,所达到的局面又有不同的形态,其中最判然分明的一个区分就是治世与乱世。战国秦汉之间,诸子对治世和乱世的区分以及成因进行了集中的探讨。如《荀子·大略》从义利关系上立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礼记·乐记》和《诗大序》则从乐与政的关系立论:“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吕氏春秋·观世》在解释“治世之所以短而乱世之所以长”的原因时,提出圣人(欲治之君)与士(欲治之臣)都少有,即使偶尔出现了也难以相遇的观点。董仲舒则从天道和人治关系的角度进行了阐释,提出:“天出此物(春夏秋冬)者,时则岁美,不时则岁恶。人主出此四(与春夏秋冬相对应的好恶喜怒)者,义则世治,不义则世乱。是故治世与义(按:义当作美,形似而误)岁同数,乱世与恶岁同数。以此见人理之副天道也”。又说:“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气正,则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起。世乱而民乖,志癖而气逆,则天地之化伤,气生灾害起”。(注: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三》《春秋繁露·天地阴阳》,四部丛刊本。)
治世和乱世之外,东汉时期,又出现了“盛世”的概念。《后汉书·崔骃列传》载,东汉初年的崔篆,临终作赋以自悼,名曰《慰志》。其辞有:“何天衢于盛世兮,超千载而垂绩。岂修德之极致兮,将天祚之攸适?”崔篆之孙崔骃,献书告诫外戚窦宪,提出“今宠禄初隆,百僚观行,当尧、舜之盛世,处光华之显时,岂可不庶几夙夜,以永众誉,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3]他们所说的盛世,都是对当世的赞美,并非历史的评价。唐宋以后,盛世的概念使用得越来越多,人们把“欣逢盛世”视为人生最大的幸运。但是,都没有对什么是盛世作出界定。汉魏之际的历史学家荀悦在《申鉴·政体》中,把国家政局分为治、衰、弱、乖、乱、荒、叛、危、亡九种形态,其中没有将盛世作为一个独立的形态列出。
到底有没有盛世?治世和盛世有什么区别?古人对此没有进行严格的学理上的区分。现代历史学概念中,则往往以盛世、衰世和乱世三种形态来概括国家的治理局面。有的将治世包括在盛世之中,有的则以盛世为比治世更高的一个层次,有的则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治世和盛世的概念。一般所指的盛世,其标志性特征是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吏治清明。但历史上的盛世大多维持时间不长,衰乱之局即接踵而至。[4]
无论如何,治世与盛世,和帝道王道一样,也是兼有政治观念和历史时代双重意义的概念。盛世在历史时代意义上的含义不是很清晰,如果严格按照以上五个标准来衡量,则中国历史上称得上盛世的时代,大抵只有称为“天汉雄风”的汉武帝时期,称为“盛唐气象”的唐玄宗时期,以及清朝的康雍乾盛世,有时人们还以汉唐盛世与康雍乾盛世并称。不过,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严重的流民问题,使其比开元天宝盛世和康雍乾盛世要逊色一些。而治世的时代所指则是明确的,除了尧舜之时外,周之成康,汉之文景,唐之贞观,被公认是历史上典型的治世。《汉书·景帝纪》赞曰:“周、秦之敝,网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吴兢在《贞观政要》中也发出了“此皆古昔未有也”的感慨。至于南朝刘宋时期一度出现的“元嘉之治”,明朝的所谓“仁宣之治”,都只是短暂的相对的治世局面,没有成为政治观念系统中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概念。
依托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概念体系,结合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本文拟对历史上的治世与盛世进行界定。所谓治世,指国家治理的一种理想形态,侧重于国家治理的水平,强调行帝道王道,主要特征是政治风气良好,社会秩序稳定,百姓对国家政权充满信心。所谓盛世,指社会发展的一种理想状态,侧重于国家治理的成果,主要特征是在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上达到经济发达和文化繁荣的局面。
2 贞观之治的历史面貌
“贞观之治”是唐代以后中国政治传统和历史观念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这里先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一下贞观时期的国家治理究竟处于何种局面,回答为什么“贞观之治”是治世而非盛世的问题。
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始于制定有效的治国方针,并很快迎来了社会秩序的安定和政权的巩固。唐太宗即位之初,在关于治国方针的讨论中,存在着以魏征和封德彝为代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魏征来自社会下层,参加过反隋起义,对农民的情况和全国的形势能够比较准确地加以把握,他分析当时百姓的动态是,大乱之后人心思定,建议太宗实行教化,采取轻徭薄赋、劝农务本的方针;而封德彝则站在农民战争中受到沉重打击的山东士族的立场上,怀着对农民阶级的刻骨仇恨,主张人心难治,应当实行高压政策。最后,太宗在事实面前完全接受了魏征的意见,很快确定了实行教化的治国方针。而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是由唐太宗本人提出来的,他当时对于能否迅速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还缺乏信心,所以他主动同魏征商讨自古理政之得失,并且试探性地说道:“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治!”[5](P17-18)
当时的唐太宗还不到30岁,正是年富力壮、思想上趋于成熟又不守旧的年龄。但是,由于他常年征战,而且法定没有皇位继承权,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条件去过多考虑治国理民之事。当经过几年的斗争,终于把皇位夺到手之后,对于如何治理国家,在思想上还是缺乏准备的。不过唐太宗毕竟是经历过隋末的动荡,而且在开国战争中积累了赫赫战功,加上惊心动魄的夺取皇位的斗争,把他锻炼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对于巩固皇位具有充分自信,有着虚怀若谷的政治家风度,十分注重对统治理论和文化知识的学习。他坚持君主不能一人独断的为政作风,强调发挥各级官僚机构的作用,充分运用互相配合、互相制衡的政治体制,以保证决策的正确制定和政令的贯彻执行。所以,在贞观初年频繁的关于治道政术的讨论中,唐太宗一直处于主动的地位,许多时候都是唐太宗主动向侍臣询问、求谏。
最早对贞观时期的治国状况进行总结的是唐玄宗时期的史臣吴兢,他在《贞观政要》中对贞观之治的局面有一段概述,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新皇帝得人心。尽管唐太宗即位之初“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是既有内忧又有外患,灾荒的严重程度到了一匹绢才得一斗米,但是“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等到贞观三年(629年),年成稍有好转,流亡他乡的百姓都纷纷回到家乡,竟无一人逃散。老百姓没有把天灾人祸归怨于最高政权,他们替政府着想,替政府承担着灾害带来的后果。根本原因是百姓对政府有信心,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而这种信任无疑来自唐太宗本人的人格魅力和贞观君臣共同努力营造的良好政治风气。用吴兢的话说,就是“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
其次是政治清明,上下一体,同心同德。尽管唐太宗的掌权来自一场政变,但他并不计较个人恩怨,对于当初的政敌,皆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时论以为能断决大事,得帝王之体。唐太宗注意严明吏治,对于王公贵族和势要之家严加控制,对于贪赃枉法者,必置以重罚。
再则社会风气有了根本好转,犯罪率低,社会治安状况良好。“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在接着几年丰收之后,更是呈现出太平景象,“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赉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时有馈遗。此皆古昔未有也”[5](P24)。
尽管《资治通鉴》将这种局面的出现系在贞观四年(630年)有所不确,应该注意《贞观政要》中“频致丰稔”指的是贞观三、四年以后连续几年丰收,然后才出现社会经济的根本好转,但是,其中的描述还是概括了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的:“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6](P6085)。无论是《贞观政要》还是《资治通鉴》,对贞观之治的描述都是着眼于政治风气和社会稳定状况的,而不是指经济和文化繁荣局面。贞观之治的现实背景和实际情况,我们可以从《贞观政要》《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等文献记载中窥见大概。
从社会经济上看,唐太宗即位之初,既有经济上的危机,同时又面临着突厥的威胁,社会秩序很不稳定,政局也不平稳。尽管后来通过和平的方式暂时解除了突厥的威胁,在对外关系中赢得了主动,但是,内地的形势却并不乐观。一方面,隋末动乱以来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生产尚未得到恢复,土地荒废、人口减少,全国呈现出一片经济凋敝的景象,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脆弱;另一方面,社会矛盾还很尖锐,不仅一些农民还在亡命山泽,继续进行反抗,一些地方势力引发局部动乱的危险也还存在。应该说,后来到贞观四年打突厥,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一场战争,唐朝的取胜,除了突厥自身因素,某种程度上应当归因于老百姓对新王朝的一种期望,一种信心,是老百姓的高昂斗志赢得了这场战争。与此同时,经济开始恢复和发展。贞观三、四年间局部地区的丰收,并没有完全扭转生产凋敝的局面,是经过“频致丰稔”,也就是连续多年的丰收之后,才出现了米价下跌、粮食充裕的大好形势。但是,经过大动荡大破坏之后,经济上需要有相当长一段时期才能恢复元气。贞观六年(632年)前后,社会经济形势有了重大好转,在当年令州县行乡饮酒礼的诏令中,便提到“比年丰稔,闾里无事”,是礼制的建设跟不上经济的发展,“乃有惰业之人,不顾家产,朋游无度,酣宴是耽”[7](P498)。所以才要通过行乡饮酒礼,来达到改善社会风气的目的。于是,出现了纷纷请封泰山的议论。魏征针对太宗稍稍滋长的自满情绪,坚决反对封禅,比照隋朝全盛时期的情况,指出当时经济形势并不乐观,“自今伊洛洎于海岱,灌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尤其是“自丧乱以来,近泰山州县凋残最甚”[7](P81)[6](P6094),经济形势的好转,是相对隋末以来的残破局面来说的,并不等于经济发展的水平有多高。
从政治风气和社会稳定状况看,老百姓的信心和斗志,来自贞观初年政治上的得民心。也就是说,实行教化、轻徭薄赋的政策,是天下大乱之后的正确选择。全国上下部有着为国家着想的积极意识:皇帝为民担忧,励精图治,崇尚节俭;各级官僚都致力于政权建设,灭私徇公,坚守直道;老百姓也理解政府的难处,即使四处逃荒逐食,也安分守己,不把怨愤发泄到政府和皇帝的身上。尤其是君臣之间维持着一种同心协力、励精求治的良好关系。这一时期的政权结构中,有一个各取所长、各尽所能、团结合作的宰相班子,为推动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和维护这种良好的政治局面提供了保证。这样,即使经济上还有严重的困难,社会秩序也不会乱,只要经济形势一旦好转,很快就能够恢复社会的安定。
从最高统治者的治国之道看,唐太宗在政治上有全局观念,常常因为某一件具体事情,而想着把另外一类事情办好。他心里装着老百姓,他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在对自己严格要求的同时,能够严格约束各级官吏和王公贵族,严惩贫官污吏。他有着大政治家的风度,所谓“得帝王之体”,在夺取了政权之后,没有将原先反对自己的力量完全排斥,而是对他们大胆地加以重用,把他们放到重要的岗位上。正是由于唐太宗在思想上和实践中的这些表现,才有可能出现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的很快稳定,至少当时和后来的很多史臣都是这样认为的。此外,房玄龄、杜如晦等操劳国务,魏征、王珪等坚持进谏,并且能够站在对理论、历史和现实深刻认识相结合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治国方略,保证了贞观时期国家治理的高水平。
贞观中期以后,尤其是在考虑安排皇位继承人的过程中,贞观政治局面有所转变。但是,居安思危、善始慎终,还一直成为贯穿贞观中后期的政治话题。尽管唐太宗晚年出现了复杂的权力斗争,但是,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社会关系和统治政策的调整下,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势头。
3 贞观君臣对历史传统的认识和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历史定位
贞观君臣在政治思想上的重要贡献,在于结合治国实际提出了“为君之道”和“安人之道”等治国方略。到贞观六年,太宗在又一次与侍臣讨论历代兴衰存亡的问题时,引用《尚书》中“可爱非君,可畏非民”的典故,进一步提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5](P16)。这是一种具有真实感受的畏民心理,是贞观君臣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戒惕思想的根本前提。魏征则搬出了“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语,而且,在后来的议论中反复引用,成为贞观君臣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以“为君之道”和“安人之道”为核心的治国方略的提出,是从总结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开始的。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正好说明了“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5](P1)的道理。也就是说,老百姓生活的安定,是国家安定的前提,是维持长治久安的根本,是最重要的“为君之道”。尽管中国古代不乏强调“以民为本”的思想家,但像唐太宗那样,从最高统治者的角度,将这个问题提到如此高度,并坚持贯彻到自己的施政实践中,在历史上并不多见。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只有安定了百姓,才能安定天下,但是,如何真正做到不损百姓呢?这就是安人之道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贞观君臣得出了一个规律性的结论,即国家的征发必须以百姓的承受能力为限度,而生产的正常进行和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生活条件,是这个限度的底线。贞观二年(628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5](P237)
从隋朝亡国的事实中吸取治国的教训,只是贞观君臣制定治国方略的前提之一。“为君之道”和“安人之道”,是在总结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历代统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贞观君臣对于古代的历史传统,进行了积极的探讨总结,并进而明确了自己时代的历史定位。也就是在历史事实与历史观念构成的关于治国传统的坐标上,确定了自己时代的位置。一方面是追迹尧舜,高悬圣人治国的政治理想,以期达到行帝道王道的境地;另一方面是总结秦汉以来历代王朝的经验教训,克服各个时代出现的弊政,并上升为治国理论,争取达到历史上最好的统治局面。
在治国目标和政治思想上,贞观君臣继承了西汉前期贾谊、董仲舒等人的思想,高悬着尧舜之道的治国目标。董仲舒的理论建设,是从界定《春秋》的性质和地位开始的,在他看来,《春秋》作为治国指导思想,核心的内容是“奉天而法古”,奉天是要在以皇帝为中心的权力世界之上确立天道,所谓“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而“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所以“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8]因为后代治国都是不顺于天而任刑的,所以要从理论上奉天,就必须从实践中法古。所谓古,在董仲舒看来,主要是指上古尧舜之时,即使是夏商周三代,也还不足以成为最高目标,只有古代的尧舜,才是头号圣人。董仲舒之所以要把治国的目标定得那么玄远,似乎可望而不可及,就是要强调教化的过程。太平之世,制礼作乐,是一种伟大的政治理想,永远为这个理想而奋斗,才能不断进步。
在圣圣相传的史观系统中,贞观君臣同样选择了尧舜(即唐虞)之时为最高目标。贞观时期关于治国理想和治国方针的探讨,集中在尧舜之道,其目标是魏征在贞观十四年(640年)上疏中提出的“若君为尧、舜,臣为稷、契”[5](P85)。唐太宗自己也曾表示,“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5](P195)。
唐太宗与侍臣讨论天子要怀有谦恭和畏惧之心,以“称天心及百姓意”,其历史依据是尧舜。他引用《尚书》里舜诫禹之语:“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又引用《周易》“人道恶盈而好谦”的说法,说明天子必须上畏皇天,下惧群臣百姓。魏征进一步强调这是唐虞之道,曰:“古人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愿陛下守此常谦常惧之道,日慎一日,则宗社永固,无倾覆矣。唐、虞所以太平,实用此法”[5](P191)。
唐太宗在谈论灾异祥瑞问题时,主张百姓富足、天下太平是最大的祥瑞,其理论依据仍是尧舜,他说:“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纣?……夫为人君,当须至公理天下,以得万姓之欢心。若尧、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爱之如父母,动作兴事,人皆乐之,发号施令,人皆悦之,此是大祥瑞也”[5](P287-288)。
魏征在贞观初年关于治国方针的讨论中,坚持实行教化的方针,一个重要的历史和理论依据,就是“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后来唐太宗在总结自己的成功时,也着重强调了魏征在劝行帝道王道方面的贡献,他说:“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征之力也”[5](P18)。
在关于明君暗君的讨论中,魏征同样以尧舜为参照,而历史实际中的秦二世、梁武帝和隋炀帝等人,则成为背离尧舜之道的反面教材。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征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征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昔唐、虞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5](P2)
在关于君臣关系和君民关系的讨论中,魏征的参照还是唐虞之世。他说皇帝任意威罚,是所以长奸。“此非唐、虞之心也,非禹、汤之事也”。接着引用《尚书》“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荀子“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和孔子“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等古训,说明“故唐、虞战战栗栗,日慎一日”,提醒唐太宗“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虑之乎?”[5](P83-84)所以王珪对当时人物的评价中,魏征的特点是“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5](P35)。
综而言之,贞观君臣以尧舜之世、唐虞之道为自己时代的政治理想和治国指导思想,并将抽象的帝道王道落实为具体的治国方略和施政措施,将自己的时代定位为用唐虞之道开创的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治世。[9](P355-381)正如侍御史马周在上疏中所说:“陛下当隆禹、汤、文、武之业,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得但持当年而已!”[6](P6132)
4 小结:贞观之治在中国古代治国传统中的历史地位
贞观君臣的政治理想,在很大程度实现了,贞观之治成为中国古代治国传统中一个可以效法的样板,成为唐虞之道以后一个新的典范。
还在贞观中期,人们就开始意识到贞观之初的政治局面具有落实帝道王道理想和开创治世局面的双重意义,上引马周的上疏中就提到,“陛下必欲为久长之谋,不必远求上古,但如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吴兢在唐中宗时写的《上〈贞观政要〉表》中,已经不再把五帝三王视为楷模,而是把贞观政化视为典范,其文曰:“窃惟太宗文皇帝之政化,自旷古而来,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虽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皆所不逮也”[10](P3023)。开元时期吴兢修订完成《贞观政要》,其序云:“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10](P3026-3027)唐代以后,历代想要有所作为的君主,都以唐太宗为效法的榜样。对后世治国者来说,重现贞观之治,就如同贞观君臣追求尧舜之世的重现一样,成为崇高的理想。贞观君臣和他们开创的贞观之治,逐渐确立了在历史进程中的典范地位,总结贞观之治的《贞观政要》,也因此成为了历代帝王的教科书。
“贞观之治”是以其特有的内涵进入传统政治的概念体系,进而成为新的典范的。在贞观政治实践中,已经将古代治国理念具体落实为治国方针和施政措施,是历史上少有的对帝道王道的具体落实。对后人来说,贞观治国方略比帝道王道更加真实可信,也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和现实借鉴意义。
[收稿日期]2003-07-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