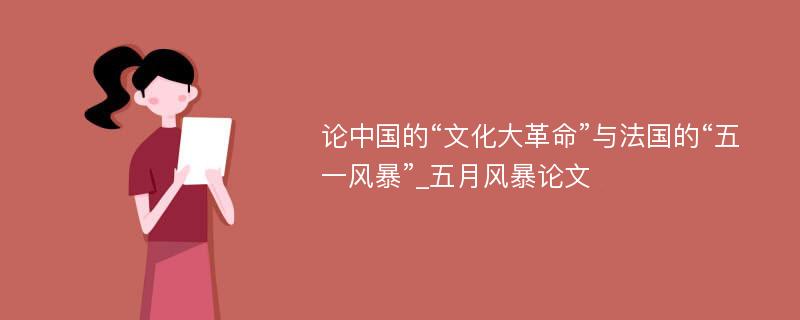
中国“文革”与法国“五月风暴”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文革论文,中国论文,风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62:D73/77(56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698(2001)05-0055-13
1968年5月,在举世震惊的“文革”爆发整整两年之后,法国也爆发了举世震惊的“五月风暴”。实际上,从1968年1月到1969年4月戴高乐下台,运动持续一年多,只是在1968年5月为高潮期,所以法国舆论界称其为“五月运动”,“五月事件”,“五月革命”、“红色五月”的都有,史称“五月风暴”。
5月28日为“五月风暴”的最高潮。这一天,总人口约为5000万的法国有1000万工人罢工,300多个工厂被工人占领,30多所大学被学生占领。这一天深夜,总统戴高乐又神秘失踪。据当时法国舆论界和学者们后来评论,这一天如果不是法共和它所控制的法国总工会坚持不搞暴力革命、不乱中夺权、坚持合法斗争,法共领导人民夺取政权不是没有可能的。运动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教育部长和总理先后辞职,最后导致总统戴高乐辞职,直接经济损失估计为几十亿法朗,整个运动中仅五人死亡。(注:Laurent Joffrin《Mai 68》,Editions du Seuil,1988.)与“文革”的灾难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运动的间接后果是导致法国左翼力量——社会党党魁米特朗上台执政达14年之久,并与法共合作进行了一些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化改革。法国的高等教育法、新选举法、最低工资法、私人电台和电视台法都是这个运动的直接产物。运动使法国这个欧洲大陆式保守型社会向美国现代化社会进一步发展。法国对这个运动十年一纪念,是好是坏,众说纷纭,好的说法似乎大于坏的说法。至少远不像中国“文革”那样:“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决议》,《中共中央文件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68页。)一场历史大悲剧。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文革”和法国“五月风暴”是二十世纪后半世纪东方和西方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个最大、最典型的群众运动。两个运动之间客观存在着相互影响和强烈的反响。这个很值得注意的课题,迄今在国内外尚无人问津。这是中法两国学术界的一个怪现象,也是国际汉学家们的一个疏忽。
中国“文革”对法国“五月风暴”的影响
时隔30年了,仍可在一向十分注重市容的巴黎建筑物上偶尔发现红油漆喷的毛泽东像以及有关口号的陈迹。法国纪念“五月风暴”,电视台总要播放当年的文献纪录片,那景象更令中国人惊讶和“倍感亲切”:游行队伍中有高举马、列、毛画像和毛泽东语录牌的,最醒目的是“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的巨大横幅。“文革”对“五月风暴”的影响,还有以下历史行迹可寻:
(一)中法建交打开了中国在法国和西欧扩大影响的合法缺口。1964年4月27日,两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使法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周恩来说:“通过同法国建交可以打开一个缺口,进一步扩大我国同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打破美国的封锁,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注:《中国外交演义——新中国时期》,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60页。)法国因此掀起“中国热”:自1966年中国“文革”爆发以来,亲华的“法中友好协会”(西方的说法)经常举办介绍毛泽东思想和“文革”的讲座,吸引了许多大学生;1966年至1968年,《毛主席语录》(法国称为“小红书”)在法国再版四次,估计有几百万册。西方舆论界评论戴高乐主动与新中国建交“具有讽刺意味——中国共产党驻巴黎大使馆将要扮演一个从事颠覆活动的角色——虽然其作用不易精确估计出来——这些活动有助于1968年5月的骚动,这个骚动几乎使戴高乐统治垮台。(注:布赖恩·克罗泽《戴高乐传》下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85页。)
(二)法国一些对新中国和毛泽东思想感兴趣和同情“文革”的重要名人,对法国“五月风暴”的影响非同小可。具代表性的有三位:一位是戴高乐的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劳(Andre Malraux),他曾在“文革”前夕的1965年访问中国,并写了一本《反回忆录》,引起了国际性重视。其中与毛泽东的谈话一段尤为世人注意,几乎各国大报均予译载。马尔劳与中国革命甚有关系,二十年代曾来中国,国际盛传他曾直接参入1925-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并写了两部以中国革命为题材的小说,(注:即以1925年省港大罢工为背景的《中国大革命序曲》(1928年出版)和以1927年上海"4·12"政变为背景的《人之命运》(1933年出版)。均绝版久矣。)均成为世界文学经典著作,他因此获龚古尔文学奖。他一直是戴高乐的高官、死党。奇怪的是他的左倾只是在观念而不在行动。“五月风暴”中他公开声明支持戴高乐,但他的作品不仅影响了一代代法国人,使他们了解中国革命和毛泽东,而且对法国青年的精神偶像——萨特和加谬也有着若干影响。第二位就是法国青年崇拜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可与卢梭相提并论的让·保尔·萨特(Jean Paul Sartre)。他五十年代初,就曾访问过中国,写了《我对新中国的观感》,影响也很大。他不仅在思想上影响“五月风暴”,而且身体力行直接参加:当法国左派的《人民事业报》受政府压制时,他不顾高龄,挺身而出,保护这家“毛主义”的刊物,并亲自上街叫卖,其照片遍登法国各大报。5月22日及后几天的“五月风暴”高潮中,他多次去巴黎大学演讲,支持左派学生。他甚至比当时的中国《人民日报》还激烈,对法共的言行万分愤慨,当时就著《法共害怕革命》控告法共背叛法国人民,又一次丧失法国大好革命时机。他的言行像旋风一般影响着“五月风暴”。法舆论认为“五月风暴”简直就是一场“萨特的革命,戴高乐的麦城”。第三位是巴黎七大东方语言系主任,中国问题权威让·巴比(Jean Babi),自1966年“文革”爆发以来,就不断著文和演讲褒扬“文革”和毛泽东思想,在大学生中影响也很大。类似上述三位的学者、教授、讲师在法国和巴黎大学中为数不少,只是在“五月风暴”中的影响或大或小而已。
(三)“北京”、“毛派”——成为法国“五月风暴”中最敏感最可怕的词。1968年1月5日,法共总书记乔治·马歇在法共机关报《人道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硬说法国“毛派”组织从北京得到几亿法朗的援助,法国特务机关也惊恐起来。二月间,法国国外情报局和反间谍局报告说,欧洲的“毛派”领导人正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和德国汉堡举行会议,目的在于煽动法国大学生闹事,据说已得到中国慷慨提供的经费。(注:布赖恩·克罗泽《戴高乐传》下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42页。)此事在法国上上下下闹得纷纷扬扬,活灵活现,影响极大。不管是真是假,却从另一个方面大大鼓舞了法国“左派”、“毛派”学生组织——法国“五月风暴”的生力军。一些“毛派”小组,如青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小组、马列主义政党等。这些组织很小,它们的重要性不在于人数,而在于通过拥有三千多党员的比利时毛派党得到中国提供的经费。(注:布赖恩·克罗泽《戴高乐传》下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39页。)
(四)毛泽东暴力革命的名言和“文革”的理论、实践活动极大地煽动了苦闷不满现实的法国青年起来反对现政权。毛泽东暴力革命的理论和活动以及关于战争的“十六字”(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著名流行歌在马尔劳的《反回忆录》中与毛泽东的谈话一段记叙得十分精彩,在法国青年中广为流传。“五月风暴”中,法国青年挖铺路石与警察进行巷战和焚烧小汽车,法国舆论界把此也“归罪”于毛泽东暴力革命理论的煽动。这似乎有些牵强。但毛泽东号召红卫兵学生帮助他摧毁自己付出那么多艰苦努力建立起来的现政权并再重建的继续革命理论和亲手发动红卫兵“破旧立新”向当权派夺权的惊世之举,对当时世界性的群众运动有很大影响,尤其极大地震动了不满现实,早就跃跃欲试反对现政权的法国青年,使他们有了理论依据和光辉榜样,他们高举“十年太长了!”“把戴高乐送进档案馆、修道院!”“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建立一个新社会!”“再创一个巴黎公社!”的旗帜奋起战斗。
(五)法国学生也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五月风暴”高潮中,巴黎大学的学生也响应毛泽东“学生与工农相结合”的号召,冲破警察重重阻拦,步行去郊外的雷诺汽车工厂与工人联合斗争。因警察阻拦,一学生掉进塞纳河里淹死。(注:Laurent Joffrin《Mai 68》,Editions du Seuil,1988.)“五月风暴”高潮前夕——1968年4月16日,毛泽东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在全世界引起强烈的反响,这恰恰给法国青年学生提供了一个团结战斗的号召。
(六)运动中,法报曾呼吁法国“最好能有一个既是戴高乐又是毛泽东的那样一个人”。其中具代表性是法国著名评论家罗伯特·纪兰(Ro-bertet Quillam)在1968年1月6日评论说:如果把中国的情况搬到法国的话,不妨假设,我们的“红卫兵”即造反的学生,也应该找到一个同盟者和首领,以便抗议和攻击现存制度。这个像毛泽东一样的操纵者,应该就是戴高乐将军本人。最好能有一个既是戴又是毛的那样一个人,出于对自己所建立起来的一切都不满的心理,决定“统统砸烂”,然后加以改造和更新。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应该由他来培养出一个科恩·本迪特COHN-BENDIT——法国学潮时的学生领袖,并且制造出一批“狂热分子”,就像中国的红卫兵那样,指挥这支突击队从事破坏和建设。(注:《巴黎龙报》,1989.1.10-16。)
(七)洋红卫兵访问中国。1967年,法国、西欧有一批洋红卫兵不远万里访问中国,被康生接见,并参观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韶山。中国当然不会为法国培养大批大批的“狂热分子”和洋红卫兵。他们的意义不在于人数,也不在于他们回去后起了什么作用,而在于他们“留学”中国“文革”“专业”的影响。
(八)“五月风暴”中,法国“左派”、“毛派”组织的报刊书籍的形式几乎就是中国“文革”时的报刊书籍的法文版。它们的报纸头版右上角也是方框框住的“毛主席语录”,刊物和书籍前扉页和每篇文章的前面也是“毛主席语录”统帅,也是黑体字,书籍封面封底一般都是红色,法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如中国的包装一样——名副其实的“小红书”。
由上可见,使毛泽东思想得以更广泛传播的“文革”对法国“五月风暴”的影响不仅存在,而且难以估量,其影响的过程则很像中国的一句古诗所说的那样——“春雨润物细无声”。其影响的具体过程和表现形式则有待系统和深入地研究。
“文革”时的中国对法国“五月风暴”的反响
法国“五月风暴”在全世界引起了反响,特别在欧洲各国以至到智利、澳大利亚、泰国、巴基斯坦等国都有工人、大学生游行、集会以示声援或进行舆论支持,但都不及“文革”时中国的反响那么深入、广泛、那么声势浩大。
1968年5月间,中国各级报刊广泛报导法国“五月风暴”,高度赞扬和大力声援法国工人、学生的斗争,几乎每天都有,有时头版头条,一连几版。仅以《人民日报》为例,对法国“五月风暴”就发了60多篇社论、评述和报导以及40多幅照片、宣传画和示意图。5月27日,法国“五月风暴”高潮之颠,《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重要社论《伟大的风暴》,赞扬法国工人、学生的斗争是“巴黎公社革命的继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伟大的人民运动”,并算帐式地严历谴责法共继承多列士的衣钵,继续扮演法国人民的“叛徒、内奸、工贼”的丑恶角色,继二次大战胜利时又一次出卖法国人民,失却法国大好革命时机。社论还谴责了“苏修”对法国“五月风暴”的诬蔑,同时高歌中国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世界意义。一些学习“毛著”的著名积极分子如尉凤英、陈昌奉、张学臣等和一些“文革”著名组织如“上海工造总司”、“北航红旗”、“鞍山8号、11号高炉”、“韶山革命委员会”等也分别著文赞扬和支持法国工人和学生的斗争。《人民日报》还发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工人“对口”支持法国雷诺汽车制造厂工人斗争的报导。
5月22日,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的红代会、工代会分别发表“人民声明”声援法国学生和工人。5月21日至23日,北京工人、学生、解放军战士连续三天经过天安门广场游行示威声援法国人民,达2000多万人次。22日,上海、天津、南京、沈阳、武汉、广州分别都有20至30万人的同样游行示威。到25日,除台湾和西藏以外,全国二十多个省、自治区省会首府和直辖市均举行了同样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集会。不几天,此类游行和集会活动便扩展到大部分中、小城市和少数乡镇。各级报刊、电台、电视台和广播台均进行了报导。可以说,在中国有多少人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就有多少人参加了声援法国人民的游行和集会活动。
显然,上述中国对法国“五月风暴”的声势浩大的反响是官方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布置行动。虽如此,却使当时的中国人民进一步实际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世界意义,更坚信毛泽东已成为“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心中的红太阳”,大大鼓舞了当时的中国人民更坚定自豪地紧跟毛泽东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当时的法国舆论对中国如此反响它们的“五月风暴”也及时作了些报导,很难精确估计这对当时正如火如荼的法国“五月风暴”又有多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风云变幻的六十年代,东方和西方的两个文明古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个大国的这两个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尤其在1968年5月间风助火势、火助风势、互相影响、彼此反响。这也是国际群众运动史上的一大奇观。
中国“文革”与法国“五月风暴”比较研究的意义
法国“五月风暴”与中国“文革”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由教育问题引发,由学生运动开始,其策源地都是各自首都的头牌大学——巴黎大学和北京大学;运动的高潮期相近;基本都经历了学生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三个阶段;学生组织的派别都是基本上分为两大派——前者的“右翼”、“左派”和后者的“保守派”、“造反派”,也都存在“极右”和“极左”派别。彼此的“右翼”和“保守”派都是带官方和半官方性质的组织或其改头换面,彼此的“左派”和“造反派”都是对官方和半官方组织的否定而自发成立的;运动都有学生发动工人、市民群众的过程,也都是在工人、市民群众参加运动后才使这运动得以广泛、深入的发展;运动中都是文斗与武斗相结合;运动的宣传舆论形式更是惊人的相似……这是群众运动的一般规律或偶然巧合,还是东、西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有值得注意和研究的相通之处?
如果说这两个运动的表面相似之处使人颇费思量,那么它们的内在不同更耐人导味:
其一是运动的本质差别——爆发原因和运动性质的差别:法国“五月风暴”爆发的政治上的原因是戴高乐只关心外交事务,忽视国内事务。由于二次大战初法国的总溃败和法国贝当政权投降德国,导致法国国际地位大幅度下降,连盟军策划在法国诺曼底登陆的计划也把法国排斥在外,更排斥在处理战后的三大国(美、英、苏)之外。这被戴高乐视为奇耻大辱,他的后半生一直对此耿耿于怀,他对恢复法国大国的地位梦寐以求,甚至不惜处处与美国作对。但对老百姓必须生活其中的法国本身则很少在意或漠不关心。他执政十年积累起来的改革太少,变化不大的压力使“五月风暴”成为不可避免。戴高乐对国内事务的最大忽视是对教育和学生问题:1968年,法国人口为五千多万(1946年为四千万),20岁以下的占总人口的34%,便出现了教育方面的新问题和看待事物方面“两代人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就成为导致“五月风暴”的主要原因。
到六十年代,十九世纪型式的旧的教育制度仍然统治着法国教育,主要是大学教育,新的思想的传播有利于不满现实的法国青年拼命寻找可以支持他们的佐证的意识形态。存在主义、无政府主义、托洛斯基主义、毛泽东的暴力革命和摧毁自己现政权并重建的“文革”理论被他们普遍宣传和接纳,反对美国越南战争也成了他们经常集会的理由。这是“五月风暴”爆发的思想上的原因。
由于戴高乐不关心国内事务,经济虽有发展,但仍显得迟缓。六十年代,法国财政常发生危机。工人普遍要求增加工资,但政府无力解决,关闭和开工不足的工厂太多。这是大学生振臂一呼,千百万工人积极响应的原因。也是“五月风暴”爆发的经济和社会原因。
可见,法国“五月风暴”是六十年代法国社会由于戴高乐对国内事务的忽视所导致的各种矛盾积累的必然,是一场真正自发的“自下而上”地反对最高统治者的人民运动。
至于“文革”爆发的原因,国内外方家学者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的研究,他们一直追溯到五十年代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此文不作赘述。总之,公正地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应该是毛泽东对六十年代初、中期中国面临的问题判断失误和他的错误发动所导致。但毛泽东为什么能发动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对官僚主义和腐败特权现象的普遍不满,就不可能解释数以亿计的红卫兵和群众那么全身心地投入毛泽东号召的造反运动,以致中国的每个角落、每个人统统卷入了这个政治漩涡。并不完全是毛泽东在运动群众。更公正地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发展的必然与群众对官僚腐败的普遍不满的社会必然因素相碰撞,毛泽东的人为发动与群众的自发互为推波的结果。根据“文革”历史事实,可概括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最高领导者号召和发动群众“自上而下”地重新组合起来打倒妨碍他的政治路线的中国第二号领导者刘少奇以及号召群众同时“自下而上”地摧毁刘少奇的社会基础,而群众却没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设计,同时趁“合法造反”之机与各自的“官僚上司”进行肆无忌惮的“总算帐”、“总报复”和试图参入政治的一场“极左”的群众运动,一场有限度的合法造反,有组织的混乱,人为的无休止的内乱。与法国“五月风暴”相比,“文革”的爆发原因和性质显得更为复杂。
总的来说,当时的法国需要戴高乐领导一场革命进行彻底的改变,但戴高乐没有做。毛泽东大可不必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摧毁自己的政权并重建,而毛泽东偏偏做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五月风暴”是戴高乐太注重外交事务(却总是不成功),忽视国内事务的结果;相反,“文革”是毛泽东太注重国内政治事务(却总是一错再错!),忽视外交事务(很少出访)和经济问题的结果。仅这个问题就够世界学者们和各国首脑、政治家们研究和吸取教训的了。
其二是运动的生力军——青年学生的理想和命运的差别。法国“五月风暴”实质上是一场学潮;“文革”很大程度上是一场红卫兵运动。红卫兵的理想只是“革命”,法国学生是向往生活更自由、幸福的新社会,似乎比红卫兵的理想高一个层次,这也符合两国的经济基础。西方说:在法国,革命吞噬了孩子;而在中国,孩子们几乎吞噬了革命。前者说法的理由是:法兰西民族最富有政治热情和参入意识,法国人我行我素,朝三暮四,喜好政治变动,“在不超过一个人生命的两倍的时间里,法国变过十三次政体”。(注:布赖恩·克罗泽《戴高乐传》下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48页。)因此,一次又一次的革命不知吞噬了多少孩子(但“五月风暴”的“孩子”们照样可以当教授和部长,有小汽车和旅游全球)。后者说法的理由是:红卫兵向往革命,但不知怎么革命,只有盲目崇拜,盲目革命,终于几乎吞噬了革命。对于前者,是法国人说法国,自然有它无可辩驳的道理。对于后者,似乎只说对了一半:应该是红卫兵既吞噬了革命,革命也吞噬了他们,是“同归于尽”。六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学生受惯了革命理想和老一辈革命事迹的教育,他们悔恨自己没有遇上像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那样的革命战争年代。恰恰在这时,他们无限崇拜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号召他们进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们认为梦寐以求的革命大好机会到来了!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若不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也不会都走向自己的反面;亿万红卫兵疯狂破“四旧”,北京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甚至一些红卫兵冲出国界,援越抗美和参加缅共游击队,不能不说是“反帝反修”教育长期普及的结果。武汉“高层次”造反的“北、决、扬”(“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和《扬子江评论》)正是对青年毛泽东的“新民学会”和《湘江评论》等革命事迹的模仿。可见,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是红卫兵运动产生的本质原因,而无数的红卫兵组织和派别则是这个矛盾的大小和层次高低在组织上的地域化、单位化的表现,红卫兵们万万没想到,革命的结果使他们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更大了:毛主席一声令下,统统下乡了事,成了“文革”最大的牺牲品。一些汉学家、学者和“文革”过来者对红卫兵运动众说纷纭:什么“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发泄残暴的感情”、“封建主义心理的集中体现”、“人性的变态”、“理性的丧失”、“极左暴徒”、“红色恶魔”……不是说这些说法完全没有道理,而是说在非本质的问题上隔靴搔痒乃至咬牙切齿是无助于历史的理解的。“五月风暴”和“文革”表明: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和教育问题都是攸关国运以及如何防患于未然的大问题。
其三是运动的结果和影响的差别。如前所述,“五月风暴”对法国社会有积极的甚至是革命的作用;而中国“文革”则是举世公认的“十年浩劫”,中华民族的一场大灾难。为什么同是一场“左倾”群众运动,其结果和影响会如此不同呢?主要是基本社会状况不同;六十年代的法国社会基本上是欧洲大陆式的保守型社会,又在戴高乐右翼势力下统治了十年之久,可以说是右上加右。因此,“五月风暴”这场“左倾”群众运动对法国当时那种社会的冲击显得十分必要。这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由于群众运动的不断发生而不得不进行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奥秘”之一。而“文革”是在五、六十年代的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社教等一系列的“左倾”运动之后的一个更大规模、更长时间、更深入、更广泛的“极左”群众运动,其破坏性当然是很大的。中国为什么不能在一系列的“左倾”运动之后进行自我调节反而再来一个更大的“极左”的“文革”呢?邓小平恰中鹄的地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它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法国人对我们把他们的国名译成“法国”—“法制的国家”十分赞赏。戴高乐举行全民投票决定他的去留,是遵法;法国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群众游行示威也是遵法,并未越轨多少;连法共坚持议会道路,不乱中夺权也是遵法。当年,假若我们的法制健全,不仅毛泽东的错误方略难以被认可并付诸实施,干部们的官僚、腐败也不会那么普遍使群众不满;假若当年公民的守法意识普遍牢固,也不会那么造反和制造那么多冤假错案;假若当年公民参入政治有合理的渠道和法律保障,公民也不会借造反之机来参入政治和发泄不满,以致猛乱暴烈到连毛泽东也无法控制的地步。早在本世纪初,鲁迅先生就提出了改造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使中国人民缺乏自主意识,奴性十足。它表现为对一己责任的逃避和对救世主的期待。“文化大革命”中对毛泽东的神化以及把“文化大革命”作为他一人的过错正是这种国民性的表现。每个经历“文革”的人,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面对“文革”历史都要审视自己的灵魂,反省自己的责任。
其四是改造我们对“文革”的研究方法。它们的比较研究除了从大的方面可能使“文革学”研究更深入和可能是一条赶超洋人的“文革学”研究水平的“捷径”之外,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既然法国“五月风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乃至革命意义,而中国“文革”对它又有一定影响,是不是说“文革”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中国“文革”不仅对法国“五月风暴”有一定的影响,对六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各国风起云涌的人民运动都有一定的影响,甚至是极大的影响。1972年,基辛格陪尼克松会见毛泽东时,曾认真而恭敬地对毛泽东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注:《中国外交演义——新中国时期》,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60页。)这话并不完全是恭维和夸张。信手翻开那个年代的《人民日报》、《纽约日报》、《泰晤士报》、《真理报》、法国《世界报》等世界各大报都不难找到有力的佐证。是的,中国“文革”在全世界的影响很坏,这多半是后来反省的结果,当时并不完全是这样。从另一方面来看,毛泽东思想正是在文化革命中在全世界得到最广泛传播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扩大了新中国在世界各国的影响。“文革”十年中与我国建交的国家占与我国建交国家中的一大半,终于在1971年使我国恢复在联大的席位,为尔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国际基础。当然,这主要是毛泽东、周恩来直接把握外交政策,迅速纠偏,不允许“四人帮”随便插手外交领域的原因。但与“文革”加速扩大了毛泽东思想在世界的传播,从而扩大了中国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再如革命和生产问题。法国学者罗伯特·纪兰(Robertat Quillain)1968年著文评论说: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法国最近时期的革命之间,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也存在着许多明显的差别。其中最大的差别是,我们这里的造反派不肯坚持生产。毛派的文化革命碰到的头号问题,是一边干革命,一边继续生产,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工人虽然参加了革命运动,却从来没有长时间地停止生产。(注:《巴黎龙报》,1989.1.10-16。)罗伯特的确很有见地,在1968年就与我党1981年的《决议》有不约而同的评说:(文化大革命使)“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决议》,《中共中央文件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68页。)“文革”中,工农业生产总值发展的平均速度(1969-1976年平均为11.575%)并不低,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经济基础。这似乎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史无前例的创造,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决议》,《中共中央文件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68页。)罗伯特由于不了解中国国情以及条件所限,偏偏只是看到了中国“文革”与法国“五月风暴”之间这一非本质差别,不可能看到这两个运动之间的本质差别。
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Maurice Meisner)说:“今天宣讲一种新的福音并谴责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主要是幸存的受害者。……事实将证明,当前对文化大革命不加选择的谴责和过去那些年里不加批判地赞颂那场运动一样,无助于历史的理解。”(注:(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44-345页。)资产阶级学者就懂得马列主义辩证法,信仰马列主义国度里的学者们有什么理由违背辩证法呢?这决不是说要不得人心地为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的“文革”翻什么案,而是说在全面否定“文革”的前提下,客观地研究非主流的某些方面的问题,例如“文革”中官僚、腐败、犯罪等现象相对较少和低消费、高积累等问题。客观,全面地研究“文革”,将有助于更全面更深刻地吸取其经验教训的营养,把今天的事办得更好些,也有助于历史的理解。
其五是我国目前的状况与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前夕有着惊人的相似乃至相过之处,从现在起往后十几年,将愈来愈接近。因此,这两个运动的比较研究将会为我们的今天提供更深刻的借鉴和更好的作法,尤值得我国人文科学工作者开拓和重视。
一般说来,我国较之发达国家落后半个世纪左右。1960年法国工薪阶层低收入者的平均工资为480法朗(约合90美元),比我国目前工薪阶层一般平均工资略高。到二十一世纪初,我国国民经济状况的这一表面象征(人均收入)将与法国六十年代中期和末期差不多。从另一方面看,法国“五月风暴”的三个阶段以及一个月高潮中的发展进程和猛烈状况,与其说与“文革”有相似之处,不如说与我国后来1989年的一次风波更相似,这在深层说明我国越向后越接近法国六十年代的状况。
1967年,法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人达2210美元,超过比利时、西德、联合王国和荷兰。法国“五月风暴”告诉我们:经济形势好的情况下不一定不会发生政治危机。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最有才干的技术顾问之一雅克·纳博纳(Jacques Narbonne)在1963年就给戴高乐写信曾预言1968年将爆发一场风暴(注:布赖恩·克罗泽《戴高乐传》下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25页。)(多么准确!)。他作这个预言的根据就是大学生人数的迅速增长和“两代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戴高乐和蓬皮杜都没预料到“五月风暴”的爆发,纳博纳是准确预料“五月风暴”的唯一人,可没有人听他的!中国“文革”也只有一个人预料到了它的一半,那就是毛泽东本人。我们有幸有一位睿智老人早在不断地警告我们:“在这个世纪不把中国的事情多干几件,下个世纪中国要有大麻烦。”(注:《新闻启示录》,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16页。)这一次,我们要努力使这位老人的预言不要实现,更不要提前实现。那么,人文科学工作者的责任是什么呢?
这两个运动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各方面得到一次彻底的大暴露,是东西方文化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一次大碰撞,深入比较研究它们,对于更深刻地吸收“文革”的教训,学习西方合理东西,融合中西文化,如何重视和解决学生问题、青年问题,如何健全民主和法制,如何在经济较发达时期预防群众运动的发生不无裨益,可以为我们的今天提供更深刻的借鉴和更好的作法,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一定的意义。这几乎是时代特赐的拓展研究的仅有机会,被忽视是十分可惜的。
标签:五月风暴论文; 中国法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法国文化论文; 文革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大革命时期论文; 戴高乐传论文; 工人运动论文; 毛泽东论文; 红卫兵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