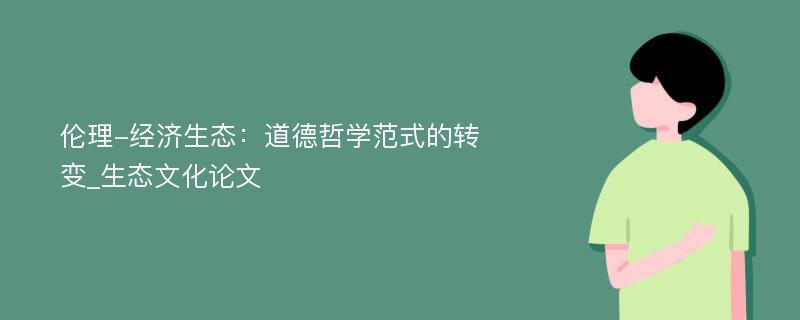
伦理—经济生态:一种道德哲学范式的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伦理论文,哲学论文,道德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第四种理念”
从哲学范式的层面考察,三种理念的共通特质是:(1)形上出发点和价值目标:“原子的观点”;(2)主体品性及其价值基础:“道德世界观”;(3)认识方式:本体思维。
“原子的观点”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的两种伦理的把握方式之一,他批评这种把握方式“没有精神”。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第一,自德谟克利特从哲学上演绎出“原子”的概念之后,“原子的观点”就成为最重要的哲学范式之一。还应当进一步承认的事实是,在德谟克利特提出哲学的“原子”的概念之前,“原子的观点”就已经是古希腊哲学的传统方法,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概念看作哲学方法论长期发展的结果,比仅当作是他个人的哲学发现更合理,也更具解释力。第二,在“现代性”被充分演绎的20世纪,“原子的观点”比其他任何时期的文明中更有充分甚至极端发展的条件,虽然在发展到巅峰的同时已经孕育了自身的否定性,就像在“现代性”中孕生了“后现代性”一样。
“道德世界观”是相对于“伦理世界观”的概念。作为伦理—经济关系的世界观基础,道德世界观的基本特点是:(1)它是个体的而非实体的或共体的世界观,因而在本质上是道德的而非伦理的;(2)它是关于道德与自然关系的理性或自我意识,属于并往往只停滞于现象学的场域,难以由现象学进入法哲学,即难以由关于理性与理智的考察,进入意识与行为的把握,因而难以成为真正的“精神”或“实践理性”。
“本体思维”是三种理念最显著的特质。“决定论”、“气质论”、“立法论”之所以在直观中很容易被认作一种哲学,根本上就是它们的本体论气质。三大命题,本质上都是本体论思维范式下,关于伦理与经济何者为第一性,何者更具本质性的问题的回答和解决。因此,与其说它们是在探讨伦理与经济的关系,不如说是对伦理与经济关系的本体论追究更恰当。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无论是对伦理与经济关系的理论解决,还是伦理进步与经济的现实发展,最重要的不是本体,而是关系,是合理地调节这些关系所形成的伦理与经济的文明实体。三大命题不仅表现出一种哲学本体论的共同偏好,而且直接就是本体思维的结果。“决定论”作为对伦理与经济何者第一性问题的回答,直接就是一个本体论命题;“气质论”作为“决定论”的反命题或补命题,其实质也是关于“第一性”的追究;而“立法论”表面上是价值论或“纯伦理”的,但当道德或道德的发现者与宣断者充当经济的立法者的时候,道德也就成为“第一性”至少被赋予“第一性”的资格。无疑,哲学本体的追究具有意义,但本体思维却可能以最一般的本体追究,代替具体问题的现实解决,从而将丰富生动的生活世界抽象化和理念化。所以,本体思维虽然自古希腊以来一直为西方哲学所倡导,并在20世纪中得到极度发展,但却缺乏足够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特别是当它作为“一般”的思维方式的时候。可以这么说,它越是成为“一般”,非合理性也就越“一般”。
“第四种理念”作为对前三大理念的辩证否定,必须既超越前三种理念,又涵摄前它们的积极成果。新的理念被置于以下诸概念对立的基础上,并作为前者扬弃后者的成果。(1)“实体的观点”与“原子的观点”;(2)“伦理世界观”与“道德世界观”;(3)“生态思维”与“本体思维”。于是,道德哲学范式转换基本课题,便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由“原子的观点”走向“实体的观点”;由“道德世界观”走向“伦理世界观”;由“本体思维”走向“生态思维”。探讨这些课题形成的新概念是:伦理—经济生态。
二、从“生态实体性”出发
“伦理—经济生态”的第一个形上基础,是“从实体出发”的观点,它是关于伦理、经济、伦理—经济关系的价值取向,及其合理性的存在状态的概念。由此进行的道德哲学方面的理论推进,就是由原子关注,到关系重心和实体取向的价值转换。
关于伦理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和讨论,存在三种可能的价值重心和现实关注:伦理;经济;伦理—经济的实体。
“伦理—经济生态”的理念以黑格尔“从实体性出发的观点”为理论资源,但绝不是对它的简单回归,其理论推进表现为:透过“生态实体性”的概念,它已经不是一般地“从实体性出发”,而是“从‘生态实体性’出发”。这一推进的认识论前提是:“伦理”、“经济”两个“单一物”有机关联所形成的“普遍物”就是,生态;伦理、经济及其相互关系的真理性的精神也是,生态。
生态的基本理性内涵,是实体或整体的观点,但生态理念的根本精神,在于它不是一种外在的或粗暴的实体主义与整体主义,而是以内在有机关联和生态因子间平等互动为基础的实体取向或整体取向。因此,生态哲学,既反对以原子观点为基础的个人主义,也反对专制式的实体主义和整体主义。萨克塞已经指出,生态学最初起源的方法论基础是“认识到一切生命的物体都是某个整体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广泛地理解生态学这个概念,要把它理解为研究关联的学说。”生态学的思维向度和价值重心是事物之间的关联,而不是单个事物的绝对价值,“生态学要求观察事物之间的关联。”伦理—经济的生态关联及其形成的生态实体,是“伦理—经济生态”理念的价值取向和形上基础。
“从‘生态实体性’出发”的理念要在理论上成立,就必须逻辑地进行一种理性追究:伦理或经济,能否“原子式地”作为文明的目的?伦理、经济在文明体系中的存在方式及其价值合理性,到底是“原子”的还是“实体”的?
可见,无论是基于经济,还是基于伦理的“原子式地进行探讨”,都既不具有理论合理性,也不具有实践合理性;只有“伦理—经济生态”,才是伦理、经济的“原子”,以及伦理—经济关系的真实而合理的存在状态。由前者向后者的转换,期待形上理念、价值观、文明观方面的一场革命。
伦理—经济的“生态实体式探讨”的价值取向和形上方法,要求将价值和思维的重心由原子和因子,转向关系与生态。它是一种肯定文明多样,以及多样性文明的具体、历史的合理性的价值观与文明观。这种取向与方法,对中国文明具有同样的解释力。
可以这样概括道德哲学方面的这种转换:理论上,将形上出发始点和价值取向由伦理或经济的“原子”,转换为伦理—经济的“生态实体”;实践上,由对伦理或经济“原子”的关注与归责,转换为对伦理—经济生态的分析与建设。
三、“实体”的“伦理世界观”
“伦理—经济生态”的第二个形上基础,是“伦理世界观”,它是关于伦理实体的伦理自我意识及其伦理责任的概念。由此作出的理论推进,就是由个体道德主体到实体伦理主体、由个体道德到实体伦理,准确地说,到特殊与普遍相统一的实体伦理的转换。
关于伦理与经济关系的理念,在终极意义上是一种世界观,“生态论”与“决定论”、“气质论”、“立法论”之于世界观的概念发展在于:它将“道德世界观”推进为“伦理世界观”。
“道德世界观”的概念以意识为对象,但冷落了意志,尤其是实体意志。历史原因很简单,黑格尔的工作只完成了一大半,即在现象学中探讨意识,在法哲学中探讨意志,未能最终如愿以偿地建立他的“精神哲学”体系,而“精神”则被规定为是意识和意志的统一。因此,推进现代伦理学研究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实现现象学与法哲学研究的链接与整合,使意识与意志的统一,而不是以其中任何一个要素,作为它的对象。而当这样做的时候,一个新概念的发展就是必须和必然的了:“伦理世界观”。
最重要的理由还在理论合理性本身。“伦理世界观”与“道德世界观”的显著区别在于:它的主体不是个体,而是实体或共体。道德世界观的基本问题主要是个体的义务意识与客观现实、自然冲动与道德命令之间的关系问题(注:在黑格尔看来,行为只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即“冲动形态的意识”);而伦理世界观的基本问题,则是伦理性实体的义务意识与它所面对的现实、实体的自然冲动与伦理要求之间的矛盾。二者之间本质的差异是两个。(1)义务同一体与“冲动的体系”。实体虽然由个体构成,但实体的意识和冲动决不只是个体的“集合并列”,个体诚然需要建立一种“冲动的合理体系”,但对实体来说,这种合理体系的形成更重要,也更困难,因为它需要达到特殊与普遍的统一,实现个体道德性与实体伦理性的统一,以及实体中诸自然冲动的合理协调,从而建立起一个真实的伦理实体和合理的“冲动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道德世界观是一种主观精神,伦理世界观就是一种客观精神。(2)实体或共体的伦理责任。由于伦理世界观是一种以实体义务和实体冲动为主体和对象的概念,因而实体的伦理性及其伦理责任就被突显。在“伦理世界观”的概念中,不仅实体内部的关系具有伦理性,而且实体与实体之间,以及实体与它所面对的自然之间也应当具有伦理性,于是,实体不仅被赋予伦理属性,而且被赋予伦理责任。“道德世界观”的概念虽然也与伦理有关,但它只有在个体意识与意志的现实合理性的意义上才被讨论,而“伦理世界观”根本关注和直接指向的就是实体的伦理属性和伦理责任,正因为如此,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着力研究的,就是家庭、市民社会、国家诸伦理实体,并且认为,“伦理”高于“道德”,是对它扬弃的结果。
诚然,“决定论”、“气质论”、“立法论”,并不是完全不关心实体的伦理性及其道德责任,根本的问题在于,它们在理论和现实中都可能导致并且已经导致这样的后果:以实体内部的伦理性,消解实体与实体之间、实体与它所面对的自然之间的道德责任,于是,在这些理念之下,就会出现这种状况:对内部关系来说,实体是“伦理的”,甚至是非常“伦理的”;但对外部关系,包括实体与实体、实体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来说,它却可能是“不道德的”甚至是非常“不道德的”。“伦理性”的内部关系与“不道德的”外部关系,就是潜在于20世纪三大理念之中的逻辑悖论与历史悖论。生态危机、文明霸权、文化帝国主义,就是这种悖论的现实后果。
基于“伦理世界观”的“伦理—经济生态”或“生态论”的理念试图实现一种转换。它努力建立实体内在关系中的伦理性与它所面对的外在关系中的道德性的统一,其转换点将道德责任的主体由个体移向实体,不仅追责个体的道德责任,而且追责实体的伦理责任,最终实现内部伦理性与外部道德性、个体责任与实体责任的辩证统一。“生态论”所以是一种以“实体”为主体的“伦理世界观”,而不是以“个体”为主体的“道德世界观”,所以能实现个体与实体、道德与伦理的统一,根本原因在于:(1)既然“生态论”将价值的重心从伦理或经济的“原子”,转向二者之间的关联以及由这种关联形成的生态实体,那么,它的取向和品质就必然是特殊与普遍统一实体,而不是原子式的个体。它强调,伦理与经济的合理性以及它们的文明责任,应当从二者建立的生态关联中得到诠释,因而其主体必然是实体的,而不是个体的,准确地说是包含了个体的实体,理由很简单,“生态”的形成,必定是诸多个体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实体“冲动体系”或“有组织的冲动”的结果,它属于整个实体以及它的文化传统。(2)在“伦理—经济生态”的理念中,无论是“伦理”,还是“经济”,都不是个体及其行为,而是共体或实体及其行为的概念。在这里,“伦理”已经回归它社会性和共体性的本性,作为一种关系的复合体,而“经济”也普遍意义上的人类共体合理地获得物质财富、以增进自身幸福的理性过程,而不是至少不只是个体获利的活动。
“生态论”在提出了一个新的道德哲学难题的同时,也作出一个新的理论推进,这就是实体的伦理性,与实体冲动的道德合理性及其道德责任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实体的伦理性、实体冲动的合理性及其道德责任,逃逸于伦理评价和道德归责之外,这种状况建立在一种极端错误而又富有欺骗性的道德哲学理念之上:实体(或集体)的利益及共同追求总是“道德的”。这种可悲的错误造成了诸多可能危及人类生存的十分可怕的伦理后果,上文指出的生态危机,文明霸权,就已经触手可及。有人曾指出,20世纪后期伦理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就是由个体伦理向集团伦理转化,这种概括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准确,也缺乏必要的形上基础。“生态论”的理念,可以提供这种基础,也更能对这种趋势作出必然性的解释。
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一个重要的文明边缘,迫切需要建立一种不仅控制个体行为,而且能够合理地指导实体行为或集体行为的世界观,“道德世界观”对现代文明的诸问题过于苍白无力,以实体为主体和对象的“伦理世界观”是这个时代的急需。
四、生态思维
“从实体性出发”的取向、“实体”的“伦理世界观”,必然衍生、也必然要求关于主体与客体关系方面的形上思维范式的转换,这就是:从“本体思维”到“生态思维”。
上文已经指出,本体思维是深植于古希腊哲学传统,在“现代性”西方哲学中被泛化为一种世界观、价值观、文明观,在中西方文化互动对中国哲学与伦理发生重大影响的思维范式。这种思维范式的特质,不仅在形而上的层面表现为对多样性存在背后的本体、本质和“原子”的追究,而且在现实性方面将多样性的存在归结为某个文明因子;不仅以“原子”解释现象世界的多样性存在,而且将对“原子”的追究作为形上指向和价值目的。简单地说,将“多”归结为“一”,以“一”为“多”的根据和目的,是本体思维的基本特质。问题在于,这里的“一”并不是多样性统一,也不是同一体,而是作为超验存在本质的“一”,和作为多样性实体中某一单一原子的“一”。说到底,本体思维与“从原子出发”的价值取向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
“本体思维”转换的前途是什么?就是“生态思维”。有学者曾提出,新的哲学范式的转换,应当是由“本体思维”到“伦理思维”。我认为,由“本体思维”到“生态思维”才是这个转换的“应然”和“必然”。因为,“伦理思维”很容易被理解为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范式,难以具有最普遍的形上意义,而“生态”则是体现时代精神的哲学文化概念。“生态思维”之所以可以作为一个具有更大合理性的思维范式,问题在于,“生态思维”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必须经过一个由“生态世界观”,到“生态价值观”,再到“生态文明观”的辩证运动和具体历史的落实。
经济与伦理的关系,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课题,可以不夸大地说,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认识和解决,在相当意义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走向及其道路。因为,不仅经济与伦理总是任何文明体系的基本因子,而且因为像业已形成的共识那样,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现代化需要思想启蒙。正如有的学者所发现的,启蒙运动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复古为解放”,另一条是“反传统以启蒙”。西方选择了第一条,因而在走向近代、现代和后现代时,提出的口号总是:“回到古希腊!”中国显然选择了第二条道路,最有代表性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中国在走向现代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反传统是如此的激烈,以至一些海外学者惊呼,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民族那样,对自己的传统如此反复涤荡,试图摧廓殆尽!激烈的反传统导致的严重后果今天已经显露,需要认真反思的是,这种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实际上也是经济与文化、尤其是经济与伦理关系中的“本体思维”的直接后果。反传统主义的思维方式的特征是,将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伦理作为中国经济落后、文明不合理的根源,其隐含的形上实质是,将文化或伦理作为经济和文明的本体,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可能和必须将文化与伦理作为整个文明的归责对象。过度的文化批判和伦理批判背后,隐藏的是“伦理本体论”和“文化决定论”的“本体思维”的范式与品质。时至今日,严重的文明后果诏告世人:这种基于本体思维的激烈文化批判已经走到尽头!
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事实上采用了另一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具有生态思维的特征,至少我们可以作样的假设和诠释。这里姑且以在中国伦理反思中为千夫所指的家族主义传统为例。家族主义伦理传统被当作发展现代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的最保守的文化因素。然而,当我们对家族伦理传统视若仇寇时,却发现这个中国传统之“枳”,在日本、新加坡等东亚“小龙”那里居然长成现代化之“橘”。如果说文化上的同根性难以让人们找到深层的原因,那么,另一个还未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事实会引发更多的思考:西方尤其是欧洲的许多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却出人意料地具有家族主义伦理的文化基础。
由“本体思维”到“生态思维”转换的最深刻也是最困难的努力,是完成一种思维方式的革命,即由基于“从原子出发”的取向而导致的本体追究,到生态合理性的建构;由对个别因子的过度归责批判,到互补互动的生态合理性的建构。由批判性转向建设性,是这种转换或革命的实践本质。
摘自《江苏社会科学》(南京),2005.4.103~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