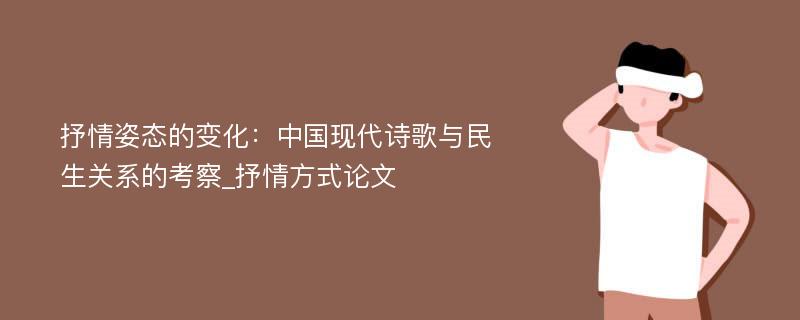
抒情姿态的变化——现代汉诗与民生关系的一种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抒情论文,民生论文,姿态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5X(2006)06-0040-03
一
由于受到时代特殊的启蒙语境的影响,现代汉诗自发生伊始,就与民生主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种紧密联系其实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共同特点,正如沈从文曾经描述的那样,“新文学运动的初期,大多数作者受一个流行观念所控制,就是‘人道主义’的观念,新诗作者自然不能例外”[1]。早期新诗中不乏高扬人道主义大旗的诗作。胡适、沈尹默的同名诗《人力车夫》,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卖萝卜人》,周作人的《画家》,罗家伦的《雪》等,都是一些颇具代表性的例子。
“五四”初期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在《人力车夫》中表达了自己对未成年车夫的恻隐之情。而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则向我们展现了隆冬季节被一张薄纸所隔开的两个世界的巨大反差:屋里的老爷享受着温暖的炉火而嫌太热,屋外的乞丐冻得咬牙切齿,真可谓冷热两重天。不难发现,这些诗作所流露的情感,尽管被包裹上一层人道主义的外衣,仍然是一种自上而下(居于社会上层的大学教授面向作为下层平民的人力车夫和乞丐)的有限怜悯。这种情感可能不失其真诚,但就实际表达效果而言,显然是十分微薄的。这是中国现代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居高临下的抒情姿态,带着一种鲜明的“知识分子腔”,自然难以真正触及民生主题的内核。
在此,笔者无意苛责胡适等人的作品,而是试图由此揭示,现代汉诗处理民生主题时体现在诗艺层面的某种先天性不足。这种不足,概而言之,表现为:眼高手低,有心无力。事实上,这种不足与缺陷在现代汉诗后来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地重现,一直延续到当下的诗歌写作中。在更多的情况下,由于某种时代性氛围的强大影响,这种不足还常常成为诸如“多作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2]、“把自己推进了新的生活洪流里去,以人群的悲苦为悲苦,以人群的欢乐为欢乐,使自己的诗的艺术,为受难的不屈的人民而服役,使自己坚决地朝向为这时代所期望的,所爱戴的,所称誉的指标而努力着创造着”[3]、“新诗也有很大缺点,最根本的缺点是还没有和劳动人民很好地结合”[4]之类的非文学性议题张扬其某种理念的口实。
而早期新诗坛聚讼纷纭的所谓“诗的平民性与贵族性之争”,也从理论的向度说明了现代汉诗与民生问题之间的某种表达困境。譬如,针对康白情所主张的“‘平民的诗’,是理想,是主义;而‘诗是贵族的’却是事实,是真理”[5]这一论调,俞平伯就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新诗”应该是一种平民的诗,即所谓“诗底进化的还原论”。具体到新诗的写作实践,俞氏认为,“新诗不但是材料须探取平民底生活,民间底传说,故事,并且风格也要是平民的方好”[6]。俞平伯的这个观点,与“五四”时期的大多数理论文本一样,显然是一种姿态性很强的宣言式的话语。事实上,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早期新诗作者,他们的“新诗”写作都未曾真正实现从内容到风格的“平民化”。因此,这些所谓“新诗”的平民性的谈论,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地架空了“新诗”和民生问题的有效联系。
现代汉诗与民生主题之间的关联,首先应该是一种美学意义上的。换言之,民生主题在诗里不应是一种社会学的存在,而是必须得到一种想象性的、艺术化的呈现。就一首诗的写作而言,民生主题不应仅仅体现为一种内容要素(“写什么”),更需要在语言、形式的支持下诉诸一种美学效果(“怎么写”),否则就可能沦为观念的传声筒,诗歌的本体性特征也将遭到放逐。现代汉诗对民生问题的介入,必须采取一种诗歌的方式,而非流于某种机械性的现实“再现”或标语口号式的叫喊。换言之,这种介入的旨归,不是社会学或政治学层面的某种意义,而是必须最终落实到诗歌文本的美学效果上。
二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民生主题的抒写,构成了现代汉诗写作越来越重要的一个方面。一位学者将之概括为一种“平民化倾向”,认为这种倾向“体现了诗人在经历了八十年代封闭的、高蹈云端式的实验后,对现实的一种回归,是诗人面对现实生存的一种新的探险”[7]。与其说这是面向现实的一次“回归”,不如说是面对这个时代出现的种种新情况,诗人的话语姿态所做出的一种主动调整。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阶层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往昔那种均质化的“同志”关系已经轰然瓦解,新兴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尤其是从乡村拥向城市的庞大的务工群体,逐渐成为支撑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坚实基座。在这个大背景之下,现代汉诗必须寻求一种新的语言策略,才可能有效地表述内涵日渐多元化的民生问题。
考察当下的诗歌写作状况,我们就不难发现,现代汉诗关于民生主题的抒写,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诸如语言形式的丰富与多样化、主题内涵的新开掘、主体言说方式的变化等。其中,抒情姿态的变化是最为突出的,即诗人的抒情姿态,由原先居高临下的“代言”变成设身处地的“立言”,这种变化为现代汉诗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艺术空间。
沈浩波的组诗《文楼村纪事》,一方面延续了其一贯的犀利、尖锐的风格,另一方面又流露出某种终极关怀的温情。这组作品运用一种冷叙述的新闻式笔法,冷静而锐利地向读者呈现了河南省一个艾滋病肆虐的村庄令人触目惊心的惨相。譬如,《程金山画圈》一诗,不动声色地讲述了一个家族正在遭受的灭顶之灾。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组诗里,作者并非一味表达某种廉价的同情,而是窥测到一些隐藏在深处的某种意味。这样的抒情,不是直线式的直抒,而是显得更为曲折和丰富。譬如《哑巴说话》,写当地的一个哑巴利用人们的同情心,趁火打劫,向外地来客勒索钱财。作者毫不留情地批判了人性中丑陋的一面。在诗人笔下,艾滋病不再仅仅是一种肉体上的绝症,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病入膏肓的文化症候的一个隐喻。这种富有反讽意味的批判话语,既体现了诗人的洞察力和良知,也表明了诗歌介入现实的可能性。不仅如此,这组诗还流露出一种深刻的自省意识,如《我不知道我是否可耻》即是如此。
与沈浩波诗歌一针见血的锋利不同,杨键是一位“像松树一样生长”的诗人,他曾经是一位下岗工人,过着一种“与蓝天和大地共享清贫的繁荣”的生活,他的诗在朴素的语言里流动着一种博大的悲悯情怀。这样的诗,从容、不做作,肆意地挥洒生命的喜怒哀乐。像《狮子桥》一诗,写的是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作者并没有立身于这一表现对象之外,而是将自己融入其中:看着码头上晚归的农民工,“他们在回家去/我痛苦得想蹲下来”。这首诗里人称代词的变化耐人寻味:前半部分用的是“他们”,后半部分则用“我们”,“他们”与“我们”合二为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表明抒情主体与表现对象之间的一种身份重合。杨键的笔下还常常出现“夜里的老乞丐”、“两颊落满煤灰的乡下妇女”、“偷铁的乡下小女孩”等,这些弱势者的形象,都被深深投下诗人主体形象的影子。有论者曾把杨键命名为“草根诗人”,认为在他的诗里,“草根性与悲悯之心是与生俱来的,深入骨髓的”[8]。这个命名在一定程度上刻意突出了杨键诗歌的某种平民特质,不过,也不可避免地遮蔽了其他一些可能更为重要的艺术特质。杨键诗歌的问题在于,他的表达有时过于急切,情感的流露有时显得太直接,这样,与表现对象之间的距离反而被拉得更远。
谢湘南从一位都市打工者到一位诗人的成长,同样也是反映现代汉诗抒写民生主题的新变化的一个样板。他的诗《一起工伤事故的调查报告》,前两节叙述一个女工的受伤过程,是不加任何主观情感的“调查报告”,第三节的几个“据说”以工友的口吻来描述女工工作条件的恶劣,似乎要引向一种谴责的情感抒发,却又被结尾的转折戛然中止:“事发当时无人/目睹现场。”如果说谢湘南早期的一些诗作在诗艺上尚嫌单薄,那么,他的《蟑螂》却初步显现出一种成熟与丰富。
在诗中,蟑螂不同于卡夫卡小说《变形记》里的甲虫,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并没有变形为虫,而是与虫同居,与虫共舞,惺惺相惜。人与虫之间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两者之间不是同质化的叠合关系(这是现代主义文学常用的手法),而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和相互指称的“亲戚”关系。
和《蟑螂》一样,卢卫平的《玻璃清洁工》和荣荣的《钟点工张喜瓶的又一个春天》,也不约而同地以小昆虫来比喻底层小人物。前者把玻璃清洁工比作苍蝇,“比一只蜘蛛小/比一只蚊子大/我只能把他们看成是苍蝇/吸附在摩天大楼上/玻璃的光亮/映衬着他们的黑暗/更准确的说法是/他们的黑暗使玻璃明亮”。在这里,“苍蝇”不再是那种肮脏的昆虫,而是被赋予了某种闪光的人格。这一意象符号的内涵因此得到更新。后者则以蚂蚁来比附钟点工低微的幸福,“她仍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比世俗的生活更低/低到不再抽绿开花/低到尘土里一只跑动的/蚂蚁追赶着她的温饱”。一个人的幸福,跟一只蚂蚁的温饱相差无几。与谢湘南笔下个性张扬的蟑螂相比,这里的苍蝇和蚂蚁显然弱小得多,它们所指代的底层形象也显得更为卑微。
对于乡村世界的想象,也是现代汉诗抒写民生主题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注意到,晚近的乡村题材诗歌,在抒情姿态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再把乡村设定为一个世外桃源或文化避难所,而是在乡村与自身的过去、乡村与城市、乡村与现代世界等多重关系中,重新塑造一个更为丰满的乡村主体。只要对比20世纪90年代初期农业题材诗歌的矫情倾向,及其对于乡村生存境遇的表面粉饰,就不难察觉晚近诗歌中乡村想象的深度和有效性。
在庞杂的当下诗歌景观中,批评家王光明敏锐地发现了诗人辰水。这一发现的意义在于,它表明现代汉诗的乡村经验表达已被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在辰水的诗里,一方面,乡村保持着一些诸如坟墓、马匹、槐棘树、春天的河流等原有的风貌,另一方面,在它那里又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对都市的向往,一条“通往北京的铁路线”,寄托了民工的希望,也延伸了乡村孩子们想象的快乐。更值得注意的,是诗人的主体观照角度的变化,尤其是关于乡村死亡的思考如《穿堂风》,显然是有意提升常常被忽略的乡村生命的意义。
同样是抒写乡村经验,如果说辰水《纸上的村庄》所采用的是一种较为沉静、平和的抒情风格,那么,王夫刚的方式就显得有些激烈。《走近大河》抒发的是一种彻骨的大爱大恨,乡村题材的局限性在这里被超越了。撒谎的诗人终将遭到乡村和大地的放逐,真正有良知的诗人应该调整自己的话语姿态,“在广阔的乡村安下我的心——/在广阔的乡村,安下我缓慢的心/死水泛起微澜的心/一览无余的心,像盲肠一样/多余的心……”(《在广阔的乡村安下我的心》)这颗心充满热爱与悲凉,裸露而又秘密,沉默并且黑暗。这样“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抒情姿态,才可能真正切入民生问题的内核。
以辰水、王夫刚等诗人为代表的新写作群体的出现,标志着乡村经验的诗歌想象得到了新的拓展,也意味着底层人物不再仅仅是一种被表现的对象,而且逐渐成长为自我表达的主体。对此,王光明在《2002-2003中国诗歌年选·前言》中从抒情主体的角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9]。
三
在论及文学与底层的关系时,批评家南帆辨析了“底层”的表述与被表述之间的悖论,指出,“文学企图表述底层经验,但是,身为知识分子的作家无法进入底层,想象和体验底层,并且运用底层所熟悉的语言形式。……如何弥合知识分子与底层的距离是一种挥之不去的焦虑”[10]。就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而言,此论基本上是准确的。不过,如果我们把谈论范围缩小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这个观点或许就需要做出一定的修正。在这一时段里,一些出身底层的作家(诗人)的出现,使得底层经验获得了一种主动表达的机会。比如,上文提及的谢湘南、杨键、辰水等诗人,莫不如此。
相形之下,另一位论者的描述,可能更切近于本文所讨论的抒情姿态的转变问题:“底层自我表述的有效性有赖于底层知识分子的叙述,以庶民记忆与经验再现的方式真实地呈现出底层意识,从而获得表述自我的话语权力。底层文学必须构建一种‘美学原则’,一种在语言、叙述立场、文化趣味上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迥然不同的底层美学。另一方面,不能否定非底层知识分子底层书写的意义,他们的底层想象有时构成了文学价值世界的一个重要维度。”[11]这里所说的“底层自我表述”和“定非底层知识分子底层书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诗人转变后的抒情姿态。
与小说、散文文类的“写实性”特征不同的是,诗歌表现民生主题,更侧重于一种“象征性”,因此需要特别警惕现代汉诗表现民生主题的非诗化倾向。这里所谓的“非诗化”,是指只注重传达某种观念,而放弃了诗歌的艺术本体要求。诗人西川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曾声称,“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我对用市井口语描写平民生活产生了深深的厌倦,因为如果中国诗歌被12亿大众庸俗无聊的日常生活所吞没,那将是件极其可怕的事”[12]。尽管此论主要是针对当时“市井口语诗”的泛滥而发的,却也从一个角度提示了现代汉诗处理民生主题的一些潜在的危险,诸如只满足于日常生活场景的罗列而完全忽略了诗艺要求。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讨论现代汉诗与民生主题的关系,并非为了彰显某方面力量以对抗另一种力量,而是试图通过这种论述表明,抒情姿态的这种变化使得抒写民生主题的诗歌写作拓展了自身的艺术空间,获得了艺术上的自足性,从而丰富了现代汉诗的语言、风格等诸方面的可能性。
收稿日期:2006-1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