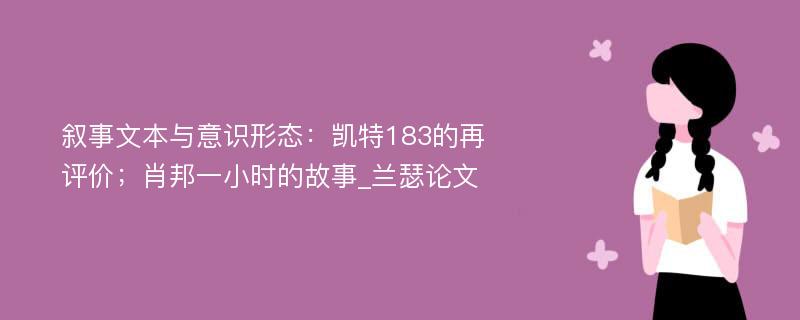
叙事文本与意识形态——对凯特#183;肖邦《一小时的故事》的重新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肖邦论文,意识形态论文,凯特论文,文本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珊·兰瑟是女性主义(也称女权主义)叙事学的开创者和领军人物,她在1981年出版 的《叙事行为》一书中率先将叙事学的方法与女性主义相结合。兰瑟写道:“我受了很 深的形式主义的教育,可我看问题的眼光也有同样深的女性主义色彩。两者之间的冲突 和交融使我超越了传统的形式主义,同时保留了对形式的兴趣。我采用了更为宽广的视 角来观察形式,将形式理解为内容,将意识形态理解为形式,看到文本内与文本外结构 之间的关系。”(注:Susan Sniader Lanser,The Narrative Act:Point of View in Prose Fic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p.7;p.246,p.252;p.25 2;p.257;p.254;pp.258-259;p.259;pp.260-261;p.261.)该书虽尚未采用“女性主义叙 事学”这一名称,但初步提出了其基本理论,并进行了具体的批评实践,堪称这一学派 的开山之作。兰瑟对文本形式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关注,有助于克服文学批评中的单纯形 式研究或单纯政治文化批评的片面性。这部开创性的著作20多年来频频出现在叙事文学 研究(尤其是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参考书目中。该书第六章以“作为意识形态和叙事技巧 的视角”为题,对美国女作家凯特·肖邦的短篇小说《一小时的故事》进行了女性主义 叙事学分析。兰瑟在叙事学和女性主义两方面都造诣很高,她在《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 》一文中对《埃特金森的匣子》的分析和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对叙述声音与性别政 治之关联的分析非常精彩。(注:Susan Sniader Lanser,“Toward a Feminist Narratology,”in Feminism:An Anthology,edited by Robyn R.Warhol and Diane Price Herndl,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1;Susan Sniader Lanser,Fictions of Authority:Women Writers and Narrative Voic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然而,在笔者看来,兰瑟在《叙事行为》一书中对 《一小时的故事》的分析却颇值得商榷。这一分析体现了部分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共同 弱点:在分析时仅仅从女性主义角度来看文本,忽视或无视文本在意识形态立场上表现 出来的矛盾性、复杂性和“非性别政治”性。
肖邦是美国19世纪重要女作家,女性主义文评兴起之后,备受学界的重视。其作品中 最受关注、再版次数最多的是《觉醒》以及《一小时的故事》。朱虹认为后者的“主题 与《觉醒》相近,表现了一个女人的自我意识的突然发现,比《觉醒》更集中,更有戏 剧性”。(注:朱虹《编者序》,见《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年版,第16页。)兰瑟则断言这一作品表现出“特别清晰的”女性主义意识,而 且在她所接触到的读者中,对于文本究竟表达了何种意识形态无人与她看法相左。(注 :Susan Sniader Lanser,The Narrative Act:Point of View in Prose Fic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p.7;p.246,p.252;p.252;p.257;p.254; pp.258-259;p.259;pp.260-261;p.261.)那么这一短篇究竟是否像五年之后出版的《觉 醒》那样构成一个典型的早期女性主义文本呢?这正是本文旨在探讨的问题。值得注意 的是,《觉醒》中的女主人公追求的是“妇女永恒的权利”(the eternal rights of women),(注:Kate Chopin,The Awakening.in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vol.2,New York:Norton,1979,p.605.)但《一小时的故事》中的意识形态 从实质上说并非性别政治,而是不涉及性别压迫的婚姻枷锁与单身自由之间的关系,且 文中隐含着对追求单身自由的多重反讽。从肖邦的个人经历来说,她五岁时父亲突然去 世,30来岁时丈夫又突然去世,她不得不单独承担起经营农场的繁重工作。后来她带着 六个孩子回到娘家,但不久母亲也去世了。她是在母亲去世后才开始从事写作的。肖邦 在写完《一小时的故事》几周之后,在日记中写下了对丈夫和母亲深深的眷念:“假如 我的丈夫和母亲能够复活,我觉得自己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他们去世后进入我的生活的所 有的东西,与他们的生存重新结合在一起。”(注:Kate Chopin,Kate Chopin's Private Papers,edited by Emily Toth and Per Seyersted,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8,p.183.)肖邦在此不仅将丈夫与母亲相提并论,而且将两者视 为一体(“他们的生存”)。她在丈夫死后,独当一面,获得了自我成长的机会。但正如 她在日记中所表达的,有时对丈夫的深切思念导致她宁可放弃自己的成长,只要能换得 夫君回。倘若她的日记反映了她在那一创作阶段的真实心境,那么她在《一小时的故事 》中对女主人公、对追求单身自由不无反讽的态度就不难理解。诚然,肖邦在日记中表 达的对丈夫的深切思念和感情,并非就一定是她创作这一虚构作品的实际出发点。但不 管怎么说,阅读肖邦的日记也很可能会为我们理解这一作品提供某种帮助。近年来,历 史语境中的真实作者在西方学界越来越受到重视。真实作者与文学作品的联系是难以割 断的,作者在“死亡”了多年之后,终于在西方学界“复活”,这恐怕也是一种历史的 必然。
一
为了更好地解读《一小时的故事》之文本结构所表达的意识形态,让我们先看看这一 短篇故事的全文:
一小时的故事
1.大家都知道马拉德夫人的心脏有毛病,所以在把她丈夫的死讯告诉她时,是小心翼 翼,极为注意方式方法的。
2.是她的姐姐朱赛芬告诉她的,话都没说成句;吞吞吐吐、遮遮掩掩地暗示着。她丈 夫的朋友理查德也在她身边。正是他在报社收到了铁路事故的消息,那上面“死亡者” 一项中,布兰特雷·马拉德的名字排在第一。他一等到来了第二封电报,把情况弄确实 了,就匆匆赶来报告噩耗,以防任何不太小心、不太体贴的朋友会先他一步。
3.要是别的妇女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会因过度震惊而无法接受现实。她可不是这样。 她立刻倒在姐姐的怀里,突然放肆地大哭起来。当哀伤的风暴势穷而静止后,她独自走 向自己的房里。她不要人跟着她。
4.正对着打开的窗户,放着一把舒适、宽大的安乐椅。她一屁股坐了下来,全身累得 就像散了架,这种体力上的劳累似乎进入了她的灵魂。
5.她能看到房前场地上洋溢着新春活力的轻轻摇曳着的树梢。空气里充满了阵雨的芳 香。下面街上有个小贩在吆喝着他的货色。远处传来了什么人的微弱歌声;屋檐下,数 不清的麻雀在嘁嘁喳喳地叫。
6.对着她窗口的正西方,相逢又相重的朵朵行云之间露出了这儿一片、那儿一片的蓝 天。
7.她坐在那里,头靠着软垫,一动也不动,偶尔有一个抽噎冲到她的嗓子眼里,使她 全身一抖,就像那哭着哭着睡着了的小孩,做梦还在抽噎。
8.她还年轻,美丽,沉着的面孔上出现的线条,说明了一种相当的抑制能力。可是, 这会儿她两眼只是呆滞地凝视着远方的一片蓝天。从她的眼光看来她不是在沉思,而是 暂时停止了理智的思考。
9.什么东西正向她走来,她等待着,心中感到恐惧。那是什么呢?她不知道,太微妙难 解了,说不清、道不明。可是她感觉得出来,那是从空中爬出来的,正穿过满天空的声 音、气味、色彩向她奔来。
10.这会儿,她的胸口激烈地起伏着。她开始认出那正在向她逼近、就要占有她的东西 ,她挣扎着,决心把它打回去——可是她的意志就像她那白皙纤弱的双手一样无能为力 。
11.当她放弃抵抗时,一个悄声说出的词语从她那微张的嘴唇间溜了出来。她一遍又一 遍地低声重复着那个词:“自由,自由,自由!”紧跟着,从她眼中流露出茫然凝视的 神情、恐惧的神情。这两种神情强烈而明亮。她的脉搏加快了,快速流动的血液使她全 身感到温暖、松快。
12.她没有停下来问问,控制自己的究竟是否为一种邪恶的欢欣。一种清楚和亢奋的感 知使她得以认为这一问题无关紧要,不再加以考虑。
13.她知道,等她见到死者那亲切体贴的双手交叉在胸前时,等她见到那张一向含情脉 脉地望着她、如今已是僵硬、灰暗、毫无生气的脸庞时,她还是会哭的。不过她透过那 痛苦的时刻看到,来日方长的岁月可就完全属于她了。她张开双臂欢迎这岁月的到来。
14.在那即将到来的岁月里,没有人会为了她而活着,她会为了自己而活着。不会有强 有力的意志使她屈从——男人和女人都盲目坚信自己有权把个人意志强加于自己的伴侣 。在她受到启示的那一刻里,她觉得无论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这种行为本身都是有罪 的。
15.然而,她是爱过他的——有时候是爱他的。但经常是不爱他的。那又有什么关系! 现在可以自作主张了——她突然意识到这是她的生存中最为强烈的冲动!在这种情况下 ,爱情这还未有答案的神秘事物,又算得了什么呢!
16.“自由了!身心自由了!”她不住地低语。
17.朱赛芬跪在她关着的门外,嘴唇对着锁口,苦苦哀求让她进去。“露易丝,开开门 !求求你啦,开开门——你这样会得病的。你干什么呢?看在上帝的份上,开开门吧!”
18.“去吧。我没把自己搞病。”没有;她正透过那扇开着的窗子畅饮那真正的长生不 老药呢。
19.她在纵情地幻想未来的岁月将会如何。春天,还有夏天以及所有各种时光都将为她 自己所有。她悄悄地做了快速的祈祷,但愿自己生命长久一些。仅仅是在昨天,当她想 到说不定自己会过好久才死去时,身上就一阵颤抖。她终于站了起来,在她姐姐的强求 下,打开了门。她眼睛里充满了胜利的狂热,她的举止不知不觉竟像胜利女神一样了。 她紧搂着她姐姐的腰,她们一齐下楼去了。理查德站在下面等着她们。
20.有人在用弹簧锁的钥匙开大门。进来的是布雷特里·马拉德,略现旅途劳顿,但泰 然自若地提着他的大旅行包和伞。他不但没有在发生事故的地方呆过,而且连出了什么 事也不知道。他站在那儿,大为吃惊地听见了朱赛芬刺耳的尖叫声;看见了理查德急忙 在他妻子面前遮挡着他的快速动作。
21.不过,理查德已经太晚了。
22.医生来后,他们说她是死于心脏病——死于致命的欢欣。(注:凯特·肖邦《一小 时的故事》,葛林译,见朱虹主编《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年,第1-4页。笔者对文字进行了改动。)
不难看出,这一短篇的题名具有反讽性,作品最初出版时定名为“一小时的梦想”,( 注:这一短篇于1894年12月6号在Vogue杂志上面世时,题名为“The Dream of an Hour ”,具有明显的反讽意味,但在1969年由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肖邦全集 》(由Per Syersted主编)中,题名变成了“The Story of an Hour”,反讽意味受到削 弱。这一作者死后的“擅自”更名与当时正在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也许不无关联。该短 篇后又出现在The Storm and Other Stories(The Feminist Press,1973);Women and Fiction(New American Library,1975);by a woman writt(Penguin,1973);Images of Women in Literature(2[nd]ed.Houghton Mifflin,1977)等集子中。这些在当代妇 女运动的背景下诞生的妇女文学的集子,均采用了“The Story of an Hour”这一题名 。朱虹先生在为《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所写的序言里,将题名译为“一小时之内发 生的事情”,进一步消除了反讽意味。)反讽意味更为明显。与此相对照,《觉醒》却 不带反讽意味,而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在解读这一短篇时,兰瑟仅看到作者对女 主人公的赞同(详见本文第三节),笔者则旨在揭示作者叙事手法上的多重反讽。本文认 为,前面七个自然段中存在两种反讽性的对立:一是大家的期待与马拉德夫人实际情况 之间的反差,二是马夫人的身体与情感之间的对照。其他人担心马夫人得知噩耗时会出 现意外,因而极为小心翼翼,而实际上这种小心是多余的。从表面上看,马夫人闻讯即 放声大哭,显得十分伤心。但若仔细阅读,则会发现作者笔下的马夫人并非真的如此伤 悲。首先,叙述者将马夫人与其他人进行了对比,别的妇女听到丈夫去世的噩耗都会因 极度震惊和悲伤而难以面对,马夫人却立刻哭了起来。为了加强与他人的对比,叙述者 在“立刻”后面又加上了“突然”一词,意在突出马夫人之反应的反常,这种反常有一 种疏离效果,加大了读者与马夫人的距离。
此外,叙述者独具匠心,通过遣词造句,刻意制造了马夫人身体与情感之间的对立。 文中强调的是马夫人体力上的消耗:“她倒在沙发里,全身累得就像散了架,这种体力 上的劳累似乎进入了她的灵魂”(Into this she sank,pressed down by a physical exhaustion that haunted her body and seemed to reach into her soul(注:兰瑟 在文中引用了《一小时的故事》的全文,本文所引原文来自兰瑟的版本。笔者将兰瑟的 版本与其他版本作了比较,没有发现文字上的变动。引文中的黑体和下划线均为笔者所 加。))。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体力上的疲乏呢?是哀伤的风暴自身(When the storm of grief had spent itself)。这种分离的效果在第7段进一步得到加强:“偶 尔有一个抽噎冲到她的嗓子眼里,使她全身一抖”。叙述者将这比喻为哭着睡着了的小 孩,做梦还在抽搭。显然叙述者是在暗示,这只不过是大哭之后身体器官反应的余波, 与情感无关。其实,“哀伤的风暴”这一夸张的词语本身就不乏反讽的意味,而“had spent itself”强调的是风暴的势穷而静止,但真正的哀伤是不会瞬间即逝的。第4段 与第5段之间有一个观察角度上的转换。在前面四段中,观察角度是全知叙述者的,但 第5段却以“她能看到”开头,强调的是马夫人的视觉。观察对象为窗外的新春活力, 包括阵雨的芳香。这显然是在平和欢快的心境中才“能看到”的事物。这里的转折非常 突然,产生了一种反讽的效果。当然,倘若第5段出现在第12或第16段之后,则会显得 较为自然,此处的反讽主要源于转折之突然。
从第8段开始,叙事焦点转为描述马夫人走向追求自由的过程。笔者认为文中的描述不 乏反讽意味。首先,叙述者突出了马夫人之追求的非理性性质。第8段第一句描写了马 夫人的自制力,第二句却以“可是”(But)开头,强调她在此时失去了这种理性的力量 :“两眼只是呆滞地凝视”,“暂时停止了理智的思考”。诚然,这发生在“它”进攻 之前,然而,呆滞凝视(a dull stare)的对象就是“它”出没的蓝天,而且当“它”侵 入马夫人后,她眼中也出现了同样茫然的神情(a vacant stare)。此外,“自由”“从 空中爬出来”,向马夫人逼近,要“占有她”。马夫人对此感到十分恐惧:“She was waiting for it,fearfully.”叙述者在“fearfully”前面添加的逗号,起到了强调恐 惧感的作用。马夫人“挣扎着,决心把它打回去”,但没有成功。值得注意的是,这里 的反讽源于作者的描写手法,而不是马夫人内心情感本身的冲突。一个女人突然丧失时 ,情感反应往往不是单一的。在她的内心深处或潜意识里,或许——甚至必然——还间 杂着其他什么情感或考虑。当内心深处的某种“杂念”浮上脑际时,自然会与她的“超 我”发生抵牾,令她恐惧不安,“突然失重”状态下的对于未来的没有把握也会加重这 种恐惧感,这往往会导致她对内心愿望的抵制。但这样的情感描述本身一般都不会产生 反讽。重要的是,在《一小时的故事》中,作者刻意将马夫人潜意识中的愿望描写成了 一种外在的入侵力量,将马夫人的潜意识与“超我”的冲突转换成了入侵者与马夫人的 冲突:“什么东西正向她走来,她等待着,心中感到恐惧。那是什么呢?她不知道,太 微妙难解了,说不清、道不明。可是她感觉得出来,那是从空中爬出来的,正穿过满天 空的声音、气味、色彩向她奔来。……她开始认出那正在向她逼近、就要占有她的东西 。”在这里,肖邦在某种意义上偏离了文学规约,将抽象的比喻“具体化”、“实写化 ”,制造出一种“自由”是真正的外来入侵者的印象。而作者选择的词语“什么东西正 向她走来……那是从空中爬出来的,正穿过满天空的声音、气味、色彩向她奔来”,又 显然是在刻意将“自由”描述为一种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怪物或幽灵。
在第11和第12段中,“自由”之幽灵入侵和占有了马夫人。文中展现出马夫人“着了 魔”的状态:“当她放弃抵抗时,一个悄声说出的词语从她那微张的嘴唇间溜了出来(
When she abandoned herself a little whispered word escaped her slightly
parted lips)。”不难看出,发出“自由”这一词语的是马夫人体内的幽灵。马夫人对 这一词语的重复是在着魔状态下的非自主行为。正因为如此,她眼中才会流露出“茫然 凝视的神情、恐惧的神情”。这两种神情“强烈而明亮”(stayed keen and bright), 构成一幅典型的着了魔的画面。马夫人在“呆滞”、“茫然”、“恐惧”的非理性状态 下被“自由”之幽灵“占有”和“控制”,其中的反讽意味相当明显。幽灵的入侵使马 夫人的血液快速流动,这种身体上的物理变化使她感到温暖、松快。在此,叙述者再度 强调了马夫人缺乏理智思考的状态:“她没有停下来问问,控制自己的究竟是否为一种 邪恶的欢欣。一种清楚和亢奋的感知使她得以认为这一问题无关紧要,不再加以考虑。 ”这种“清楚和亢奋的感知”正是幽灵的魔法所产生的短暂作用。不过,此处也存在另 一种阐释的可能性,即叙述者对“清楚和亢奋的感知”持赞赏的态度。然而,上文对马 夫人着魔状态的描写和前一句中“邪恶的欢欣”这样的叙述评论,使我们可以从反讽的 角度来理解这句话,它也很可能体现的是着魔状态下的马夫人自以为是的眼光。值得一 提的是,在女性主义的作品中,倘若出现了女主人公面对自由的恐惧和茫然,往往可以 理解为父权制社会对妇女长期压制的结果,是作为客体的妇女受传统制约、被动无能的 一种表现。但这样的描写绝不会以“自由”为反讽对象。肖邦采用了“占有”、“控制 ”等词语来描述“自由”这一幽灵般的“入侵者”,产生了强烈的反讽性张力。这一场 景中的戏剧性也与《觉醒》中女主人公自然而然的“觉醒”过程形成了鲜明对照。尽管 短篇故事往往更富有戏剧性,但“它”强行让马夫人“着魔”所体现的如此强烈的戏剧 性恐怕不是短篇故事的创作规约所能解释的。
第13段首次描写了马先生:他的双手“亲切体贴”,他“一向含情脉脉地望着她”。 这是文中对马先生性格特征的惟一描述,让读者感到亲近。相比之下,《觉醒》中的庞 先生以家长自居,将妻子视为个人财产,不时命令和责备妻子,令妻子伤心,让读者反 感。诚然,我们应注意区分父权制的社会结构与具体的家庭关系,温情脉脉的丈夫并不 能排除父权制的压迫(譬如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夫妻关系)。但正如我们在下一段中 会看到的,这一作品涉及的并非男权压迫,更何况文中隐含对追求自由的多重反讽。可 以说,在这一语境中,将马先生描述成“亲切体贴”只是加强了对马夫人的反讽。值得 注意的是,叙述者在描述马夫人想像中的面尸而泣时,采用了“bitter”(痛苦)而非“ sorrowful”(悲伤)一词,似乎再次暗示马夫人缺乏一般人突然丧偶时应有的那种悲伤 情感。
在涉及婚姻的第14段,文中描写的并非男权对女性的压迫,涉及的并非性别政治,而 是婚姻约束与单身自由之间的关系。在婚姻中,男女互相帮助、互为枷锁:“在那即将 到来的岁月里,没有人会为了她而活着。”(试比较:“她不用为了一个男人而活着。 ”)至于婚姻约束,文本对男女两性各打五十板:“男人和女人都盲目坚信自己有权把 个人意志强加于自己的伴侣。”与此相对照,《觉醒》中同样想摆脱婚姻束缚的女主人 公反抗的却是父权社会对“女人永恒的权利”的剥夺。的确,在包括《觉醒》在内的各 种女性主义作品中,婚姻束缚往往象征父权制的压迫,但这样的作品强调的是妻子所受 的压迫(是丈夫的私有财产,为丈夫和孩子而活着),而不会男女各打五十板,更不会仅 仅说“没有人会为了她而活着”。值得注意的是,第14段的前两句与第3句之间出现了 叙事方式的转换。前者有可能是叙述者的评论,也有可能是自由间接引语,后者却明确 转为了马夫人自己的看法。这种段落内部的转换暗示着叙述者不赞同后者提出的观点。 婚姻意味着单身自由的结束,意味着夫妻互为制约。但婚姻也有单身生活所没有的长处 ,正因为如此,肖邦才会在日记中表示,只要能换得夫君归,自己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一 切,与他重新结合在一起。在这种心态下写作,肖邦自然会对“着了魔”的、连善恶动 机都不再区分的马夫人加以反讽。这种反讽可进一步见于叙述者这样的遣词造句:“现 在可以自作主张了(this possession of self-assertion),”“她突然意识到这是她 的生存中最为强烈的冲动(strongest impulse)!”将独立自由形容为对“自作主张”的 “占有”,进而将这种占有描述为一种冲动,恐怕不乏反讽意味。当然,“冲动”一词 具有含混性,也很可能是对女主人公之经验的一种自然表达。在这种冲动之下,马夫人 眼中“充满了胜利的狂热,她的举止不知不觉竟像胜利女神一样了”,这多少带有一点 漫画式的讽刺意味。
对马夫人的反讽在结局上也有所体现。着了魔的马夫人认为“自由”是“真正的长生 不老药”,可她却在几分钟后猝死于“致命的欢欣”。肖邦受莫泊桑的影响很深,常常 赋予其短篇故事出人意料的结局。可以说,《一小时的故事》中的结局具有多重反讽意 义。医生和旁人都以为马夫人是因极度高兴导致了心脏病爆发,但读者却知道马夫人是 因丈夫生还而幻想破灭,大受刺激,从而猝死,由此产生了戏剧性反讽。当然,马夫人 也很可能只是为丈夫的死而复生这一简单事实“惊讶”致死。无论是什么原因,这一戏 剧性反讽凸显的是外人的判断与马夫人内心活动之间的错位。对于马先生而言,他回家 是想与妻子聚会,没想到却引发了妻子的猝死。而读者原来真以为马先生死了,他的突 然生还也对读者的“无知”形成了一种反讽。然而,笔者认为这一结局最重要的反讽对 象是“自由”本身。值得注意的是,“致命的欢欣”是全文最后的一个短语,在读者阅 读心理中占有突出位置,该短语前面的破折号也起了一种强调的作用。“致命的欢欣” (of joy that kills)与前文中的“邪恶的欢欣”(monstrous joy)直接呼应,巧妙地暗 示着作为自由之幽灵的“邪恶的欢欣”控制了马夫人,并导致了她的猝死。我们不妨比 较一下肖邦另一描写婚姻生活的作品《赛勒斯坦夫人离婚》(1894):赛夫人的丈夫酗酒 作乐,虐待妻子,离家数月而不给分文,赛夫人被迫辛勤打工养活自己和两个年幼的孩 子。在帕克斯顿律师的鼓动和支持下,她顶住各种社会压力,决意与丈夫离婚。就在帕 律师精心修饰打扮,憧憬着与离异后的赛夫人相结合的美好前景时,却得知赛夫人不离 婚了,因为她丈夫前一天夜里回来了,许诺要改头换面,重新做人。这一出人意料的结 局使一心想跟赛夫人结婚的帕律师成为反讽对象。不难看出,与《觉醒》相对照,这是 一篇在意识形态立场上相当保守的作品。女主人公希望靠丈夫生活,她告诉帕律师,丈 夫曾许诺要给她不少钱,“假如他给了我这么多钱的话,我就不用工作了”。(注:
Kate Chopin,A Pair of Silk Stockings and Other Stories,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1996,p.7.)很可能正是对丈夫的这种依赖,使她放弃了离婚的念头。值 得注意的是,这一“非女性主义”的短篇与《一小时的故事》是在同一年面世的。
二
如前所述,《一小时的故事》的文本结构具有多重反讽意义。诚然,从文中也可看出 作者对自由的赞赏。第5段具有明显的象征意味,将自由比喻为富有活力的春色,第14 段也对婚姻的约束进行了抨击。尽管反讽和赞赏在文中共存,但应该说反讽还是占据了 主导地位。此外,与《觉醒》相对照,这一短篇中的意识形态涉及的实际上并非性别政 治。那么,兰瑟又是如何从叙事形式入手,将《一小时的故事》阐释成一个典型的女性 主义文本的呢?首先,兰瑟认为文本创造了叙述者、受述者和女主人公在心理上的亲近 ,通过展示马夫人的意识,使读者对她产生了同情。由于只有叙述者和受述者可以看到 马夫人的内心活动,这种了解对于读者而言是一种带有特权的信任。(注:Susan Sniader Lanser,The Narrative Act:Point of View in Prose Fic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p.7;p.246,p.252;p.252;p.257;p.254;pp.258-259 ;p.259;pp.260-261;p.261.)的确,无论是从叙事空间、叙事时间,还是心理透视而言 ,这一作品均聚焦于马夫人。但这并不能说明作者对她仅仅持一种“单一的”(注:Susan Sniader Lanser,The Narrative Act:Point of View in Prose Fic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p.7;p.246,p.252;p.252;p.257;p.254; pp.258-259;p.259;pp.260-261;p.261.)赞同立场。实际上,正因为只有读者才能看到 马夫人独处时的内心活动,方产生了戏剧性反讽——只有读者知道众人的小心翼翼是多 此一举。独处时的马夫人于被动之中被自由之幽灵“占有”和“控制”。然而,在兰瑟 眼里,独处中的马夫人只是从客体变为了主体,这是“得到了充分承认的‘觉醒’”, “对文化文本构成了最大的潜在威胁,因为这不是一个潜意识的愿望,而是对她自己的 想法的一种自觉的认识”。(注:Susan Sniader Lanser,The Narrative Act:Point of View in Prose Fic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p.7;p.246,p .252;p.252;p.257;p.254;pp.258-259;p.259;pp.260-261;p.261.)兰瑟的看法与其他女 性主义学者的看法相呼应:埃米莉·托特认为马夫人的独处标志着她对“自我选择的觉 醒”;芭芭拉·尤厄尔则认为这一作品描述的是“追求自我的创造性的斗争”。(注:Emily Toth,“Chopin Thinks Back Through Her Mothers,”in Kate Chopin Reconsidered,edited by Lynda S.Boren and Sara deSaussure Davis,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p.23;Barbara C.Ewell,“Chopin and the Dream of Female Selfhood,”in Kate Chopin Reconsidered,p.160.)但实际上,马夫人的所谓 “觉醒”是在被“它”占有之后的一种着魔受控的行为。兰瑟还从人物话语的表达方式 入手进一步论证马夫人作为主体的觉醒。有关第11段中首次出现的直接引语,兰瑟写道 :“重要的是,马夫人直到认识和接受自己的情感时,方采用直接引语说话:‘自由, 自由,自由!’”如前所述,这里的直接引语是马夫人在着魔状态下产生的一种非自主 行为。可兰瑟看到的却是马夫人的“自我觉醒,学会用她自己的声音说话”。兰瑟还用 注释的方式进一步说明:“在妇女的话语中,这种从沉默到言说(一般都会再度沉默)是 一种普遍现象。”的确,妇女的觉醒常常表现为从被动沉默到大胆言说。可是,马夫人 在受控状态下由茫然和恐惧相伴的言说与真正的妇女觉醒之言说实际上相去甚远。
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文本描写了自由之幽灵违背马夫人意愿的进攻和马夫人于恐惧之 中被“它”占有的过程。那么,兰瑟对这一描写又是如何解释的呢?首先,兰瑟认为这 是叙述者将马夫人的觉醒描述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因而说明马夫人自 己的“天性”要求她走向觉醒。(注:Susan Sniader Lanser,The Narrative Act:
Point of View in Prose Fic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p.7 ;p.246,p.252;p.252;p.257;p.254;pp.258-259;p.259;pp.260-261;p.261.)也就是说, 兰瑟将女主人公在外力作用下的着魔受控解读成出于内在天性的不可避免性。接着,兰 瑟又从另一个角度切入,说叙述者是为了帮助读者从正面理解这一过程,看到其“健康 的”正面意义,方描述了这一过程对于马夫人的艰难。对这种推理,笔者实在难以苟同 :叙述者将“自由”描写为强行入侵、令人毛骨悚然的幽灵,将马夫人描写为恐惧茫然 、着魔受控,又怎么会帮助读者认识这一过程的积极意义呢?
总而言之,兰瑟认为这一作品只有一个“单一的”、“特别清晰的”意识形态立场: 作者对受到男权压迫的马夫人之觉醒的同情和赞赏。从这个单一的立场出发,兰瑟仅仅 看到了文字的表面意义,看不到深层的反讽性、复杂性和矛盾性,才难免对有的文字加 以牵强附会的解读。就仅看文字的表面意义而言,不妨再举三例:其一,兰瑟认为叙述 者将马夫人比喻为梦中抽噎的小孩,是为了将其描述为“令人同情的受害者”,未察觉 这一描述的反讽意义(马夫人的抽噎只不过是身体器官反应的余波)。其二,兰瑟认为叙 述者将马夫人的感知描述为“清楚和亢奋”是为了说明这种感知“十分可靠”,而笔者 认为叙述者这么描述是在暗示“魔法”的作用。其三,兰瑟没有察觉“她眼睛里充满了 胜利的狂热,她的举止不知不觉竟像胜利女神一样了”的描写中所暗含的反讽意味。在 兰瑟的眼里,“这样的语言帮助创造了一种叙述声音,表达对马夫人的赞同感,甚至是 一种钦佩感”。
至于兰瑟牵强附会的解读,也不妨再举几例:其一,兰瑟认为,当马夫人在房间中独 处(“觉醒”为“主体”)时,对她的称呼从“马拉德夫人”变成了“露易丝”,这显示 出更为亲近的叙事距离。实际上,叙述者只是在篇首第一句中用了“马拉德夫人”,在 文中其他部分则一概采用第三人称代词“她”。“露易丝”这一称呼出自马夫人的姐姐 之口。其实无论马夫人是否独处,其姐姐只会称她为“露易丝”,因此,第17段中出现 的这一称呼体现不出任何叙事距离上的变化。其二,兰瑟对第12段进行了这样的解读: 因为叙述者担心受述者依然会将“它”对马夫人的逼近和占有过程视为“邪恶的”事情 ,因此“叙述者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不是这么一回事”。在兰瑟看来,第12段实际上不 是对马夫人的描述,而是对叙述者自己和读者的描述,因为“既然马夫人没有停下来问 一问,又怎么会对这一问题不再加以考虑呢?很可能这是叙述者预料读者会提出的问题 ,而且是叙述者对这一不恰当的问题不再加以考虑”。(注:Susan Sniader Lanser,The Narrative Act:Point of View in Prose Fic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p.7;p.246,p.252;p.252;p.257;p.254;pp.258-259;p.259;pp.260-261;p.261.)其实,只要在“问一问”前面加上“好好”两字,原文的逻辑就十分 顺畅了。无论原文的逻辑是否顺畅,兰瑟将对马夫人的描述硬性阐释为叙述者与读者的 直接交流,实在难以服人。那么,兰瑟为何要硬性进行这一“行为主体的置换”呢?答 案不难找寻:如果第12段是叙述者对马夫人的评论,就完全可以理解为叙述者对马夫人 缺乏理性思考的批评和对“邪恶的欢欣”的抨击。这显然是兰瑟无法接受的,因此她将 叙述者从居高临下的位置对马夫人的反讽性描述解读成了叙述者对自己和读者的描述。 其三,兰瑟将作品对男女婚姻约束的批评硬性解读成了对男权的批评。(注:Susan Sniader Lanser,The Narrative Act:Point of View in Prose Fic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p.7;p.246,p.252;p.252;p.257;p.254;pp.258-259 ;p.259;pp.260-261;p.261.)让我们先看看第14段第2句的原文:“There would be no powerful will bending hers in that blind persistence with which men and women believe they have a right to impose a private will upon a fellow-creature.”兰瑟聚焦于这句话中的“powerful”一词,她注意到文中仅有两处 采用了“power”一词:“马拉德夫人被描述为‘无能为力’(powerless),而压迫她的 那个男人却被暗指为具有‘强有力的意志’的人。”可是,马夫人并不是在面对男性时 “无能为力”,而是在抵抗“自由”之幽灵的进攻时缺乏力量(第10段)。倘若马夫人有 足够的力量将“它”“打回去”的话,不是就没有后来的所谓“觉醒”可言了吗?兰瑟 一方面将“它”视为给马夫人带来觉醒的女性主义力量,一方面又将马夫人在抵抗“它 ”时的无能视为在男权面前的无能,这岂不是转眼之间又将“它”变为男权力量的代表 了吗?其实,不难看出在14段第2句中,“powerful will”与“private will”的所指 对象完全相同。既然“private”涉及婚姻中的夫妻双方,那么“powerful will”也显 然涉及夫妻双方,“a fellow creature”也无疑是男女共指。但在兰瑟眼里,“powerful will”仅暗指压迫女人的男人。兰瑟尽管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解读了“powerful will”一词,却无法从同一角度来解释“男人和女人”这样确切的指涉,因 此转换了一个角度切入。兰瑟一方面承认叙述者在谈人与人之间的意志压迫时没有涉及 性别政治,一方面则断言这只是“表面”现象:“然而,故事描述的是妻子对丈夫之压 迫的感觉,与叙述声音形成了一种对照,一种摹仿性的对立。”这岂不是在说叙述者自 相矛盾吗?兰瑟一再强调这一作品中叙述者的立场代表了作者的立场,强调这是一个“ 单一的”反男权压迫的立场。但倘若叙述者(作者)想表现男权对妇女的压迫,那么为何 不选择“在那即将到来的岁月里,她不用为了一个男人而活着”,而要选择“在那即将 到来的岁月里,没有人会为了她而活着”;为何不描述一个未能善待妻子的男人,而要 描述一个“亲切体贴”、“一向”充满爱意的男人(“had never looked save with love upon her”);又为何不说“男人盲目坚信自己有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妻子”, 而偏偏要说“男人和女人都盲目坚信自己有权把个人意志强加于自己的伴侣”?不难看 出,所述故事与叙述话语之间并没有产生兰瑟所断言的那种对立:话语没有涉及男权压 迫,故事也没有控诉男权压迫,两者均仅仅涉及了婚姻约束与单身自由之间的关系。值 得一提的是,在《一小时的故事》这样的第三人称全知叙述模式中,叙述评论比所述事 件更有权威性,更为直接地体现叙述者(作者)的立场。有很强叙事学背景的兰瑟对此应 十分清楚。笔者相信,若不是一味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兰瑟是不会试图用故事事件来 对抗叙述声音的。值得注意的是,第14段的前两句还提供了另一种阐释的可能性:既然 第14段第3句中的“这种行为”明确回指前两句中提到的行为,前两句就很可能是用自 由间接引语叙述出来的马夫人自己的内心想法。这种双重声音的叙述方式既可明确表达 人物的观点,又不排除叙述者的赞同。不难看出,这种阐释的可能性远远大于仅仅涉及 “叙述声音”的那一种。根据兰瑟的叙事学背景,她不可能没有看到这种可能性,而倘 若她承认了这种可能性,也就无法制造故事与话语的对立了。无论是叙述评论还是自由 间接引语,这里的文字都在暗示马夫人在丈夫“死”前的压抑感仅仅跟男女之间的婚姻 约束相关,而与男权对妇女的性别压迫无关。
那么,兰瑟又是如何解释故事之结局的呢?她写道:“虽然我认为下面这种阐释会构成 对叙事视角的一种误解,但一位反对叙述者意识形态立场的读者可能会说:[马夫人的 猝死]是诗学层面的合理要求对这位胆敢觉得丈夫的死给自己带来了自由的女人的惩罚 。”(注:Susan Sniader Lanser,The Narrative Act:Point of View in Prose Fic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p.7;p.246,p.252;p.252;p.25 7;p.254;pp.258-259;p.259;pp.260-261;p.261.)结局的反讽性是显而易见的,兰瑟不 能不面对这种阐释,但她先将这种阐释界定为“误解”,然后再将阅读主体的范围缩小 到“一位反对叙述者意识形态立场的读者”,也就排斥了这种阐释。在兰瑟眼里,正确 的理解是:马夫人“遇到了那个男人,他的归来导致了她的死亡,正如他的‘死亡’导 致了她的新生”。然而,叙述者通过“欢欣”(joy)一词的前后呼应,暗示导致马夫人 猝死的是占有和控制她的“邪恶的欢欣”,是中了“魔法”之后的一时冲动。兰瑟不仅 排除了结局的反讽意义,而且将这一结局视为面对文化环境的压力而采取的意识形态策 略:文本没有让马夫人对男权的反抗在生活中实现,因此这种意识形态不会触怒社会。 但倘若仅仅为了这一目的,肖邦为何要以马夫人的追求为靶子,精心制造“邪恶的欢欣 ”与“致命的欢欣”之间的反讽性呼应,制造“长生不老药”与“猝死”之间的反讽性 对照呢?又为何要将马夫人描写为命运的可笑牺牲品呢?兰瑟将这一结局与《觉醒》的结 局相提并论:“马拉德夫人达到了自我觉醒,又死去了;这样她就重复了很多作品,尤 其是女作家作品中女主人公的经历(包括肖邦自己的《觉醒》)。”可是,《觉醒》中艾 德娜的死是一种自觉的、独立自主的选择,她无法与现实妥协,最终投入了大海的怀抱 ,旨在通过死亡来摆脱束缚,通过死亡来获得真正的身心自由。这与马夫人不由自主、 被命运捉弄导致的猝死形成了鲜明对照。
三
笔者曾经区分了文本结构与隐含文学意义的两种不同关系,一种与文本结构的规约意 义密切相联,具有较强的客观性;(注:Dan Shen,“Stylistics,Objectivity,and Convention,”Poetics 17(1988):221-238.笔者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 :与自然界不同,在语言这一范畴,社会规约与单个主体构成“客观”与“主观”的对 立——基于社会规约的就是客观的,仅仅基于单个主体的则是主观的。)另一种则主要 依赖上下文构成的特定语境和阐释者的直觉印象,故主观性较强。本文所探讨的《一小 时的故事》中的各种反讽意义主要涉及第一种关系,应该说是较为有根有据的。那么, 兰瑟和其他学者为何对这一作品丰富的反讽意义视而不见呢?这是阐释框架所起的作用 。在此影响阐释框架的主要有三个交互作用的因素,一是对作者的定论,二是选定的理 论角度,三是文化大环境。20世纪60年代妇女运动兴起之后,有些历史上的女作家被重 新发掘出来,凯特·肖邦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评论界认为她的作品体现出比同时代 女作家更为明确的女性意识,堪称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驱。然而,出于种种原因,作者在 创作不同作品时很可能会在立场观点上发生变化。尽管肖邦比同期女作家具有更明确的 女性自我意识,但她毕竟生长于19世纪后半期保守的美国南方社会,当时的社会环境与 妇女运动取得了长足进展的今天相去甚远。肖邦有的作品表现出反男权压迫的女性主义 意识,有的作品却不涉及性别政治,有的作品甚至与女性主义背道而驰。因此,我们不 能用一成不变的眼光去看一个作者的作品,而应当关注每部作品的“隐含作者”。(注 :参见申丹《究竟是否需要“隐含作者”——叙事学界的分歧和网上的对话》,载《国 外文学》2000年第3期。)正如肖邦的日记所示,她(当时)宁可放弃一切,只要能与丈夫 的生存“重新结合在一起”。倘若她在丈夫去世之后,曾经为自己的独立自由感到过欢 欣的话,对丈夫深深眷念之时就会产生深刻的反思和自责,而这种心态也会使其反讽的 笔锋更加锐利。(注:值得一提的是,肖邦的母亲27岁时,父亲死于火车事故,(带着四 个孩子的)母亲悲痛欲绝,终生守寡,怀念丈夫(“devoted to her husband's memory ”,见Kate Chopin Reconsidered,p.22)。女性主义学者Emily Toth认为《一小时的故 事》是肖邦写的有关母亲的故事,是肖邦对母亲的“女性经历”之“最为彻底的修正” (Kate Chopin Reconsidered,p.21)。但在笔者看来,这一故事与年轻时突然丧失的肖 邦本人的经历也不无关联。而且由于文中隐含对追求自由的多重反讽,应该说该文对肖 邦母亲的“女性经历”是一种间接肯定,而非“彻底的修正”。)可以说,《一小时的 故事》的隐含作者与《觉醒》的隐含作者形成了鲜明对照,体现出大相径庭的意识形态 立场。《赛勒斯坦夫人离婚》也体现出一种相当保守的意识形态立场,与肖邦的另一短 篇《智胜神明》形成了对照。在《智胜神明》中,出身贫寒的女主人公以事业为重,拒 绝了阔少的求婚,凭藉自己的天赋和努力,成为著名钢琴家。这篇作品具有鲜明的女性 意识,体现出肖邦对女性自我成长、自我实现的追求。总而言之,面对同一作家的不同 作品,我们应摆脱对于作者之“定论”的束缚,以文本为依据,把握其中不同的“隐含 作者”,关注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在意识形态立场上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除了对作者的“定论”,所采用的批评理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左右阐释。女性主义者 往往戴着政治化的有色眼镜来审视文本,从而有意无意为原本并不那么政治化的字句涂 抹上浓浓的政治色彩。兰瑟从单一的“女性主义”的角度切入作品,难免导致牵强附会 的解读。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来阐释真正富有女性意识的作品,可以说是走对了路子 ,往往会取得丰硕的成果。采用这一理论角度来挖掘某些男作家作品中潜藏的性别政治 ,揭示性别歧视,也会很有价值。但倘若将一篇非女性主义的作品硬性解读成女性主义 的作品,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兰瑟在阐释时,面对文本中出现的不符合女性主义理论 框架的反证,总是想方设法将其往既定的轨道上拉,千方百计将反证变为“顺证”。这 种让文本顺应理论框架的做法失之偏颇,也是对作者和作品的不尊重。值得强调的是, 一篇作品的立场往往不是单一的,作品的意识形态通常具有矛盾性和复杂性。对此,我 们应有清醒的认识,要保持视野的开放和包容,避免被所采用的理论框架所束缚。此外 ,要避免被作品的表面意义所迷惑,应注意透过文中的遣词造句挖掘作品的深层意义。 而要解读作品的深层意义,就需要打破内在研究和外在研究的界线。可以说,不阅读肖 邦的日记,就难以很好地理解《一小时的故事》的深层反讽意义。
兰瑟对《一小时的故事》的女性主义解读发表于1981年。20多年来,尽管《叙事行为 》一书很受学界的关注,但兰瑟阐释中的牵强附会之处却未遇到任何挑战。这在某种程 度上可能与美国学术大环境中的“政治正确性”相关。就像中国的文革期间只要用阶级 斗争的观点来看作品就可立于不败之地一样,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只要从女性 主义角度来阐释女作家的作品在政治上就是“正确”的。从更广的范围来看,《一小时 的故事》之所以会被学界奉为女性主义文学的名篇,兰瑟之所以会对它一味进行女性主 义的解读,均很可能与文化大环境中的“政治正确性”不无关联。
当然,文学作品的意义是难以确定的。一百多年前肖邦创作的《一小时的故事》究竟 表达了何种意识形态,对此永远也难以下定论。但笔者的阐释至少构成了一种新的阅读 角度,从中得出的某些体会,或许可以给未来的批评提供一种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