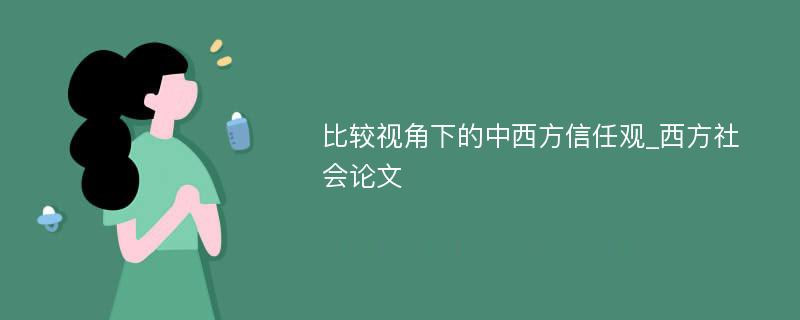
比较视域中的中西信任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中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发展,“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型”正以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
的方式呈现出来。诚信,这个曾经是中华民族立人之本的“为人之性”,在市场经济的 “解构”中正发生着变异。的确,“诚信问题”伴随中国社会的转型已经凸显出来,其 角色亦由个人品质、私人交往领域的有限制信任道德,转为公共生活的普遍要求,传统 诚信伦理能否承应这种要求?其变异的合理性何在?显然,理性的批判是发展建构的必要 前提和基础,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文明路径、不同发展阶段的中西诚信观的比较视域, 无疑为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信任伦理提供理论的参考与实践的引导。
一、中西信任观的差异性
纵观中西社会文明变迁的历史,诚信问题均为文明之意,道德之首,但对诚信为何、
何以诚信、对谁诚信等具体问题的回答是不同的。中西信任观的差异是在中西不同文化
传统与思想的观照中、在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经济的经纬交错中逐渐展现的,主要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诚信取意的轻重不同。从词义来看,在英文中,believe、trust、credit三 个词常用来表达信任的概念。“《韦氏英语辞典(1996)》,believe作为动词使用,表 示接受某件事物的真实性,确信某事的好意、功效、能力或认为是真实可靠的(第104页
)。在这个意义上,believe主要强调事物的物理特征。另一方面trust被解释为对人或 对物的特性、能力、力量和真实性的确实信赖,或者是对人的信任(第1296页),强调对 人性的期待,从trust引伸出来的关联词有trustful、trustworthy和entrust等等,这 类词常用于表示人际间的信任。再者credit用来表示对事物真实性的信任、好的名声、 荣誉或认可等意(第272页)。”[1](P67)
在中文里,与英语三个词相对应的是四个概念,即信、信任、信赖和信用。信字,本
意是“言语真实。诚实不欺”,与“诚”一字含义基本相同。东汉学者许慎(58~147)
的《说文解字》解释说“诚,信也”[2](P62)。诚、信互训,表明含义一致。信的第一
种基本含义是诚、实、专一不移、不欺等,朱熹认为“诚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谓也”[
3](P2878)。儒家学说的仁、义、理、智、信这五常之一的信,就是指这一含义。信的
第二种含义和英文中的believe相似,即当信与其他汉字连用指信任、信赖时,大体是 指相信、信行,即给予他人信任,不怀疑他人的可信性。“信”的这种本质体现在人际 交往中就是信任,如《论语·学而》所云:“与朋友交,言而有信。”[4](P3)“‘任 ’在汉语中的意思是‘使用’或‘任用’,因此,‘信任’表示相信和托付。……汉字 的‘赖’意思是‘依赖’和‘依靠’,‘信赖’意指‘信任’和‘依赖’或信任他人, ‘信任’和‘信赖’在强调人的可信性方面非常相似,两个词通常作为同一概念替换使 用,只是信任比较具体,信赖比较抽象。……‘信用’的原意是指相信和使用,与信任 相似,但是这一用法在目前已少见,在日常生活中作为名词使用,表示‘遵守诺言’、 ‘守信’和‘信誉’……和英文的credit意思比较接近。”[1](P68)
通过对“信”字的字意分析,我们概括出与信密切的三个词:诚信、信任与信用。在
三者之间,诚信是指个人的品性真实不欺;信任是指个人对他人的相信而敢于托付的程
度;信用则是诚信与信任之间的中介,一个人可以通过实践诚信而具有好的信用,从而
获得别人的信任。不过,尽管在中英文中皆有三个具相似含义的词,但从中西文明历史 变迁与实践的角度,中西信任观的取意之重或侧重向度是不同的。中国的“信”着重于 诚信,西方的“信”突出“信用”,两者以此不同的向度构建了不同的信任观。
其二,维系诚信的载体不同。在中国信任观的思想中,关注的重点是诚信,而诚信又
源于良心,是与固于内心的“忠”的德性密切相关,春秋时期的《国语·晋语》说:“ 忠自中,而信自身,其为德也深矣,其为本也固矣,故不可抈也。”[5](P464)意思是 说:忠发自内心,信是力行承诺,这样德行因为有深厚的基础,才不会动摇。宋代学者 陆九渊也指出:“忠者何?不欺之谓也;信者何?不妄之谓也。人而不欺,何往而非忠; 人而不妄,何往而非信。忠与信初非有二也。特由其不欺于中而言之,则名之以忠;由 其不妄于外而言之,则名之以信。果且有忠而不信者乎?果且有信而不忠者乎?名虽不同 ,总其实而言之,不过良心之存,诚实无伪,斯可谓之忠信矣。”[6](卷32,P374)显 然,这里的“不欺”,即不虚情假意,强调的是内心态度;“不妄”,即不妄说,不说 谎,强调的是外显言行。由此,信不过是忠的外显,两者的共同的本质是“良心之存, 诚实无伪”。即维系“信”之载体在于人的心性,因此,对个体诚信的培养就理所当然 地在心性层面进行,反求自身,通过修身养性来实现。
儒家学说一贯将道德的学习和修养称之为“为己之学”,这种学问的特点是“入乎耳
,乎心”,造就和提升自己的人格。修德首先就是要有一颗诚心,所谓诚,用古人的话
说就是“毋自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不自欺欺人。诚是一种精
神的状态和境界,同时也是一个修习的过程。《大学》把诚意作为修德之要旨,朱熹《
集注》说:“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
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
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为人也。然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 ,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7](P7)不能自诚其意,修德就无从谈起。诚意所达到 的程度,又决定了一个人修德所达到的程度。《中庸》说:“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 ;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能赞天地之 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8](P420)“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到了至诚的境界, 自我高度统一,自我的天然性就能最大限度发挥出来,最终达到赞助天地化育的境界。 可以说,只有修身养性,以诚待人,人才能形成诚信的人格,才会赢得人们的普遍信赖 。自尊者人尊之,自敬者人敬之,自信者人信之,这是人际交往的必然规律。可以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主要是被作为对人的基本评价尺度和人们应当遵循的基本生活 信条,沿着道德层面,在心性之学的纬度中发展的。
西方信任观的重点是注重信用的向度。信用体现为关系的层面,主要发生在人们的经
济活动或经济领域的交往关系之中。《新帕尔格雷夫法经济大辞典》在信任(Trust)的
词条中指出:“个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动机结构的最本质的说明是一种交易,这种交易不 能当场完成而要求在一方履行之后或者收益依赖于另一方履行的一方作出郑重承诺之后 ,另一方也同样地履行。”[9](P700)《牛津法律大辞典》对信用的定义是:“信用
(credit),指在作为回报而得到或提供货物或提供服务时,并非立即进行偿付,而是允 诺在将来进行偿付的作法。”[10](P282)可见,在西方的文化意境和话语体系中,可把 “信用”的要义理解为对借的偿还和对允诺的履行。显然,这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诚信”,后者是向内求己的德性之约,可靠心性来维系。西方的“信用”是建立在外 化与实然的关系中的,作为具体经济活动的交往关系,其“信用”必以“契约”的形式 来表达,而“契约”本身就是某种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是一种以法律为支柱的社会关 系规约。因此,西方社会的信用主要是依托法律,保证契约的签订、实施与监督。
“信用”的契约之道,在西方社会有悠久深厚的传统。从思想史的角度审视,西方思
想家大都把信用作为正当、正义之要义。主张契约就是权利的互相让渡,就是彼此承认
平等权利并表现其让渡的意志。强调遵守约定、屡行信用就是正义,否则就是不正义。 苏格拉底认为,正当是诚实和偿还自己的债务;柏拉图指出,正义的人是一个守“誓约 ”的人;格劳修斯从人性出发,认为守约是人的本性,人们订立契约就产生民法,它规 定“有约必践,有害必偿,有罪必罚”;霍布斯则以正义之名,指出守约为正义之源, 无契约即无所谓正义,有约而背约即为不义;洛克从政府的合法性的角度,犀利地道明 :如果按照契约受人民信托而存在的统治集团背信弃义,违约自是,人民则可以通过革 命来将其推翻。可以说,在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和思想发展的两个层面上,社会契 约论作为重要的思想基础,对西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意义与深远影响。
“信用”的契约之道,在西方法治社会的完善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法律与信用关
系的角度省察,西方法治社会的完善是以信用契约为基础的。一方面法律以信用契约为
前提;另一方面,法律为信用契约作注脚与诠释,即讲信用,守契约必得到法律的维护
。与中国传统把诚信主要作为人的道德品性不同,西方传统却一开始就具有法律的向度
。在《撒克逊民法典》、《法国民法典》(1804年)、《德国民法典》(1900年)、《瑞士 民法典》《美国统一商法典》等各种法律辞典中皆有相当的条文对诚实信用予以定义。
可以说,契约既是西方社会法律发展程度的反映,也是信用的法律载体。法律与信用两
者间的密合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个人信用与制度信用的统一。
“信用”的契约之道,是资本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视野切入
,信用是推动资本主义经济进步的杠杆。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亚当·斯密,从人的利
己之心出发,在其《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阐述了一个既简单而又具普遍意义 的道理:诚实守信利己利人;虚假欺诈害己害人。他清楚地看到,在市场经济中,一切 经济行为都是自由的过程,因此人们必须按照公平和信用的原则,才能与他人发生经济 交往,并从中获得自己的利益。否则,如果普遍存在着商业欺诈行为,那就既不利于商 人自己,也不利于社会利益。因为,作为价值规律的“看不见的手”——等价交换原则 ,已经内含着普遍公正和信用的基础。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 书中,直接转引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信用就是金钱”理念作为美国人的哲学和典型 的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指出:“富兰克林所有的道德观念都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诚实 有用,因为诚实能带来信誉;守时、勤奋、节俭都有用,所以都是美德。”[11](P36)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信用”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经济领域中的“黄金律”。
其三,诚信运作的社会机制不同。在中国信任观的思想中,个体诚信品性的修行与养
成是放在首位的,即诚信的运作机制是建立在对人潜在美德的相信为前提,来启动人际
交往中相互信任的循环链条的。换言之,其运作机制的逻辑程序是:首先以自己的诚信
来取得对方的信任,然后对方以诚信回报,使自己产生对对方的信任。在此,一方面我
们可以透视出,在信任的启动与实践过程中,中国文化有着强调单方主动实践诚信,不
计后果、严己宽人的道德性的要求,这是中国儒家思想所宣扬推崇的道德理想型人格的 一贯使然,可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逻辑。但另一方面,在信任的达成中 ,又隐藏着期望交往对方能够回报自身的诚信需要,满足互惠互利的动机。于是道德性 与利益性、义务性与目的性相互交织,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两方面要求的内在的矛盾性。 对于圣贤君子而言,他们可以在排除利益性与目的性之外,无条件奉行“一心利他,毫 不利己”的道德至上的准则,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人们虽摆脱不了道德规范的制约, 但生存与现实生活的处境,致使芸芸众生不会也不可能完全舍利求义,完全不计自身得 失与回报,而绝对地诚信待人。于是,每个人都有可能在理想与现实、道德与利益之间 寻求平衡:为了履行“义”与“诚”,人们以“害人之心不可有”来要求自己,愿意以 诚待人,尽己之心;为了保护自己的“利”,人们又意识到“防人之心不可无”,以免 被人利用,上当受骗。因此,在中国社会现实的层面上,诚信与不信任并存,诚信与否 的循环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判断。所幸的是,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处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 会形态中,并历经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家国同构的文明路径,这种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 定了中国平常百姓的人际交往大多局限在狭窄的范围,面对的常常是因血缘、地缘与业 缘而形成的熟人关系,因此,人们便以自我为中心,由亲及疏的关系网消解着诚信与不 信任之间的矛盾和巨大的鸿沟,弥补儒家理想主义诚信链条的缺位;以熟知度作为信任 的粘合剂,利用个人情感编织、扩展着关系网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中国社会人 际交往与社会秩序的稳定,但委以信任的大都是亲人、朋友与熟人等。信任范围的有限 性、信任达成方法的情感性,致使中国社会的信任格局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对最亲的人的 全信到对陌生人的戒备的特征。当社会由自然经济发展为市场经济、熟人交往进入普遍 交往的现代社会之时,自由市场对人之利益的诱惑,使得诚信与不信任之间的鸿沟迅速 扩张,中国社会信任层面的熟人信任、情感信任、低信任度社会等的局限性日益凸显, 暴露出与现代性的极大不适应。儒家理想主义诚信机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也是 为什么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遭遇“诚信危机”的重要原因。
与中国以个人诚信作为启动社会诚信系统的机制不同,西方社会的诚信机制主要是以 交往双方的平等性为基础,以“人性恶”(人普遍的利己性倾向)为理论前提而建立的信 用机制。在这个系统中,它是以“信用”开启“信任”,而信用又是借助契约与法律作 为保障的。所以在人际关系的层面,形成了与中国的显著差异:它不是从道德的理想性 出发,而是基于个体的现实存在,道德判断的核心成分,是以能够保证个体长期生存, 和使其获得发展并更为幸福的价值观为准,因此,诚信是指在一定程度上个体满足周围 世界对其的合法期望;它不是用道德性消解利益性,在以契约为基础的交往关系中,双 方的利益、需求、目的等都是直接表达的,契约双方的个体是自足确立的,不像中国个 体在关系项中定位,在交往中难免有差序格局造成的不对等性,而是平等身份、平等方 式、平等履行契约双方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它交往的对象不局限在熟人为主范围,而是 以陌生人群为底线的。因此,信任的达成不是依凭情感深浅而维系的关系网作保障,而 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
一方面,从社会制度层面建构维持社会信任的机制,提供信任的保障体系。即凭借诸
如法律等强制性手段的运用,确保失信行为出现时,给予受损者追究和补偿的机会,通
过影响失信行为的成本,驱使人们做出维持信任的行为选择,守信得利,失信受损,由
此保证信用互动的秩序。另一方面,从人际交往层面建立信用的文化准则。即对当事人 信任与否,主要是在理性的基础上作出判断和考量。包括对个体的诚信特质进行理性的 度量、对对方失信的可能性有多大的判断等。这样,西方的信任观形成了普遍信任、理 性信任与制度信任的主要特质,总之,西方社会的诚信机制主要是依靠制度信任的构建 与维护。
二、中西信任观的同一性
中西信任观虽然在诸多方面呈现出差异性,但由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性所使,人性
所固有的共性所趋,在人类共同面对自然、社会与人的共同处境中必有其共同回答的问
题。而且中西信任观的差异性实际上主要是历史的差异、文化的差异、不同发展阶段的
差异,因此寻找中西信任观的同一性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诚信观的建构同样是不可忽略的
其一,信任与人的向度:皆从本体论的高度诠释。在中国信任观的思想中,诚信与人
的关系是放在本体论的高度来加以阐释的,它从天之道入手,落到人之本。可以说,“
诚”在中国传统思想中,首先是一个表述宇宙本体特性的哲学范畴。《礼记·中庸》云
“诚者,天之道也”[8](P420),朱熹注曰“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7] (P18)。可见,诚就是实际有、实际存在、真实无妄的意思。自然宇宙是物质性的,实 实在在的有,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存在和运动。所以,实有 就是天道的最基本和最根本的特点。其次,“诚”是一个表述人之本的道德范畴,因为 天道的本质特性是诚,是实有,人是天地的产物,因而人在德性上也保存了天道的本质 特性。所以《礼记·中庸》云“诚之者,人之道也”[8](P420),朱熹注曰“诚之者, 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7](P18)。这样,诚就不仅是指向
宇宙自然界,而且指向人本身,成为人之本,成为判断人能否成其为人的基本标准,成 为个体德性和精神的内在实有,这样,从“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到“人而 无信,不知其可也”;从“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到“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 化为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等。诚便从天道成为人道, 成为中国人穷其一生通过后天的道德教化与培养,通过自身的修身养性之努力,不断培 育德性之追求,因而诚信也就成为个体道德的基石。
在西方信任观的思想中,虽然有多学科的多维视角与理念,但从本体论的高度阐发信
任与人的关系却是共同的。在哲学家的视野中,所谓信任,从本体论的意义而言,它就
是“存在的不孤独”。吉登斯认为,信任就是存在的不孤独,而信任危机就是存在的,
信任的对立面不是不信任,而是孤独焦虑。“当我们用‘不信任’来指称与基本信任…
…相对应的概念时,它就显得太软弱了。……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说,信任的对立状态便
是这样一种心态,它应被准确地概括为存在性焦虑或忧虑。”[12](P87)可以说,吉登
斯是以自己的方式将信任或不信任直接归结于人的存在状态,即人如何存在于生活世界
并与他人呈现出何种关系状态。萨特阐述了个体存在性的孤独与焦虑实际上是人本体论 意义上的孤独。萨特指出,人的存在和其他万物不同,因为万物是“本质先于存在”, “一切是早已被注定好的”,而人却是“存在先于本质”,“人一开始就是一种自为的 自我设计,而不是一块青苔、一朵兰花或者一棵花菜”[13](P54)。“所以人就是人。 这不仅是说他自己认为的那样——是他(从无到有)从不存在到存在之后愿意成为的那样 。人除了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不是。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14](P8) 这样,存在的个体必须独立地面对可能发生的一切,必须独自承担起所有的责任与风险 ,这就是“存在的孤独”,是“自为”的人被抛到自由中来的境况,是一种人际间的孤 独、离散状态。所以,存在的孤独是无对话、无依托、无所信赖的本体意义的孤独。信 任的作用就是消除人与人在时间与空间上的距离感,阻断种种存在性焦虑的形成,使人 感受到存在的安全性。否则的话,当一切变得不可预期、不可信赖,至深的孤独感与焦 虑感便易于窒息个体的生命,日常生活也无以为继。由此,信任危机在根本上是人的存 在危机,信任在本体意义上就是“存在的不孤独”。无论是结构主义的解释还是存在主 义的解释,都不难看出西方思想家们在这一点上是交汇的:将信任或不信任直接归结于 人的存在状态,即人如何存在于生活世界,并与他人呈现出何种关系状态。这种审视方 法,已经彰显出信任阐释的本体论视角,在一定意义上与中国信任观的诚信是人之本的 思想有着殊途同归之感。
其二,信任与社会的向度:皆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保障。人类社会从野蛮、蒙昧发展到 文明的阶段,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社会关系的日益秩序化,而促成秩序化的手段与方法 诸多,但在中西信任观的思想中,我们看到两种文明不约而同地皆将信任作为一种重要 的“稳压器”,在人际关系与社会秩序的维护方面发挥重要的保障作用。
在中国信任观的思想中,诚信是立国、交友、经商的基础。首先,诚信是立国之基。
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晋文公所说:“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
何以庇之?所亡滋多。”[15](P288)其次,诚信是交友之道。如清代学者颜元所云:“
人而信,则至诚无妄,见之于伦,朋友信也。”再次,诚信是商道之本,如《论语·里
仁》所讲“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4](P28)。可以看出“信”既被中国的智者当成是
“国之宝”,是人民福祉的保障,信又被视为人际和谐能够达成的重要因素,同时信也
是经济领域的经商之德,这些思想既是中国社会秩序维持与管理的实践总结与理性表达
,也是诚信本身内在特质外化使然。
在西方信任观的思想中,信任是建立公民社会和维持政府合法性的前提。洛克、潘恩
将信任视为政府合法性的来源;赛格里曼将信任作为公民社会的基础;普特南将信任看
作是一种社会资本;齐美尔则认为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凝聚力量之一。可以说,在西
方社会,信任同样既被界定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工具与公民社会的基础,也被当作增
加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重要方法与途径,从而成为维系社会之基石。
三、中西信任观差异的追根溯源
当我们将诚信这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置于比较的视野时,自然会去追问隐藏在其后面
的缘由,我们以为至少有三点应予以正视。
其一,中西文明路径的差异。经典作家在论及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历史进
程时,认为东西方曾经走了两条不同的路径。中华文明走的是“亚西亚的古代”之路。
这种模式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由氏族直接进入国家,即“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
族里”。它的方法是家国同构。因此,在中国社会,“国家”的概念是指天下、邦国和
家庭的统一体,可以说,“家是国的根基,国是家的扩大,由家庭中的父子关系引申出 君臣关系,由家族中的“孝悌”引申出政治上的忠君,由以血缘为基础的人伦关系延伸 为以阶级为基础的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各种等级关系”[16](P10)。因此,家与国两者 有着同根同质的不可分割的交融关系。这种文明的路径,一方面先天地决定了中国社会 政治伦理化的特质,形成了以道德作为政治的载体和基础,道德原则即为政治原则、德 政同构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历史地决定了中国社会人际关系呈现出如费孝通先生所概括 的“差序格局”、亲疏有别的特征。这些特点反映在社会信任观上,则一定程度预制了 将诚信作为立国之本、立身之基,预制了特殊信任、情感信任、人际信任和低信任度社 会。
与中华文明的开端不同,西方社会走的是“古典的古代”之路。即“从家族制、私产
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这个文明的进程使得个人财产从“公共财产”中得以分 离,个体的独立性得到确立。特别是伴随西方文明进程的是商业的发展、贸易与航海业 的兴盛与移民的频繁,人们的交往极大地超越了氏族的关系。于是,获得独立的个体与 归属个体的财产需要得到法律的保护。正是在这种文明的架构下,独立的个体之间,个 体与公共社会、与政府之间,需要建立一种依托法律的契约关系,以保证独立个体的合 法性生存与发展。社会契约的思想和理论不仅成为了西方社会学与政治哲学的重要传统 ,也成为了西方公民社会架构的思想基础,并成为现代民主制度的源泉。这些特点反映 在信任观上,则一定程度预制了西方信任观取“信用”之重的向度,并预制了普遍信任 、认知信任、制度信任和高信任度社会。
其二,中西经济结构的差异。从经济结构来看,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封建社会,长期处
于小农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中。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发展缓慢, 商品经济始终无法得到长足的发展;由于自然经济本身的特点,社会流动匮乏,因而人 际交往呈现出“有限性”、“熟人化”、“稳定性”、“安全感”的特点。这种情形正 如马克思所言,“是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个人没有独立性,直接依附于 一定的由血缘或地域等构成的社会共同体;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只限于共同体内部,只
是在孤立的地点和狭窄的范围内发生的地方性联系;在共同体内部,是按其地位、作用 和职能以及自然血缘而发生关系,不是按个人的需要和兴趣。因而人的社会关系和个性 在这时不可能得到丰富和全面发展,个体依赖于人的统治,个体服从人的自然血缘关系 。所以,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及其所决定的信任关系等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在商 品经济领域以平等为前提的契约文明的发展,使信用制度具有某种先天不足的缺憾。
西方社会的经济结构,在经历自然经济的发展阶段之后,伴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运动,伴随着西方社会航海贸易、商品经济的发展,伴随着工业革命和近代科学的迅速
发展等,在近代进入了市场经济为主体的时代。社会生产力呈现出巨大的进步,生产的
交往关系不断扩展,世界贸易不断增加,世界市场逐渐形成,于是,反映人类经济交往
的客观要求,类似法律中介形式的契约在现代经济领域不断得到拓展,从形式到内容不 断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形成了以信用为基础的现代信用文明。可以说,西方信任 观注重信用向度的发展,注重法律手段的保障,注重陌生人的普遍信任在一定程度上是 西方社会经济机构及发展所决定的。
其三,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从文化传统的角度,一方面,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后,儒学成为正统的国家之学。儒家主张伦理关系为本,提倡圣贤君子的理想
人格,推行修身养性的心性之道,宣扬重义轻利、整体主义的价值观。由于国家儒学体
制与威权主义思想的结合,使得儒家所提倡的这些理念与思想,一直给中国人提供相当
稳定的价值认同。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性善”作为道德前提的,因而只要
每个人都能将善的本性挖掘出来,社会就可太平,故它强调“求诸己”的道德逻辑,“
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儒家传统基本上是道德理想主义的传统,以此为基础的信任观 ,要求单方主动实践诚信,如人人而能为之,当然达到最理想的境界。但它缺失了“道 德风险”的预设,当中国社会走进市场经济的时候,没有防御系统的“道德风险”便成 为普遍的“道德危机”,没有制度保障的信用承诺,就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代价。
西方文化具有深厚的宗教传统,“人人皆是上帝的子民”,个体在上帝这个最高的善
面前要诚实、行善,以便死后进入天堂以及人人要尽天职、勤俭、信用的新教伦理深入
人心。一是理性主义在近代伴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一路高歌挺进,成为西
方近代精神的主流,它所倡导的理性分析方法,社会秩序与管理的法制精神以及制度管
理的方略在近现代蔚然成风。二是个人主义的传统,注重平等、自由与责任,追求个人
利益与需要的满足等成为西方社会主导的价值观。同时,西方传统文化以“人性恶”作
为其道德前提,由于每个人都有“趋利避害”的“利己之心”,因此信用的达成,必须
依靠制度、法律的支持,而不能仅仅依赖个体的诚信之心。
杜维明在《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一书中曾深刻指出:“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人际
关系的纽带以家庭的原初联系为典范。这种原初的联系,如果不经过创造的转化,它不
可能成为现代价值的助缘,还有异化为扼杀个性的外在机制的危险。”[17](P142)当中
国步入市场经济、实现社会转型之时,就意味着必须对“原初的联系”进行创造的转化
,否则,要么被“原初的联系”系着脖子而无法动弹,要么挣脱“原初的联系”而成为 无羁之马。建立现代社会的诚信观及其机制已经刻不容缓,期盼中西方诚信观的比较能 为“建构”提供一点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