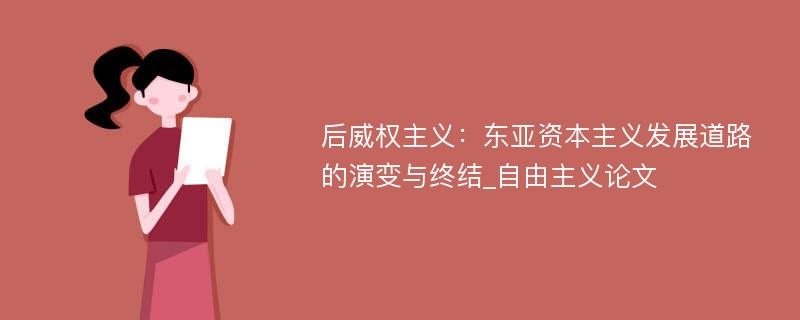
威权主义之后:东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演变和终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威权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发展道路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福山先生在1989年夏天发表《历史的终结》的论文,全面论证了西方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正在取得的胜利。“二十世纪见证了世界不断陷入意识形态狂暴的痉挛期之中……”“但是最终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取得了不可阻挡的胜利。”(注: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National Interest,16(Summer,1989),pp.3~18.)虽然有人对福山的新黑格尔主义式的推论过程不完全同意,但福山先生的结论却具有非凡的预见性。其结论不断地被十多年来的世界发展进程所证实。东欧的天鹅绒革命、苏联崩溃、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世界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全球化进程凯歌行进……这些事件无一不是对“历史终结”的说明。本文可以算作是对《历史的终结》的一个最新的东亚版注解(注:对福山先生的“自由主义最终取得了胜利”的“历史终结论”,在作为批判正统和强势群体的左翼力量占有传统优势的西方思想界,显然受到了非难,与福山论点相反的“自由主义终结论”反而大行其道。这一现象在自由主义已取得彻底胜利并占据统治地位的西方是正常和合理的。西方知识分子历来与正统和占优势的“权力”保持着一定的紧张度。作为社会的清道夫和牛虻,他们的“反”自由主义却起到了促进西方政治不断改良和进步的重要作用。但在东亚地区“自由主义”或者刚刚起步,或者还受到威权政治势力的打压而仅处于萌芽状态中。如果东亚的知识分子也邯郸学步,自以为站在理论潮头和学术前沿而引进这种西方版的“自由主义终结论”,会使具有进步价值取向的思想界同政治权力合流,最终沦为一只系在新权威主义这艘巨舰之尾的小舢板。在一些连人类基本自由都没有实现的国度或地区,谈论如何限制自由,如果不是荒谬,便是一桌架在饿死的人骨上的超级盛宴。)。文中的东亚资本主义所指范围包括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以及1949年前的中国等国家和地区。
东亚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从韦伯的中国命题开始
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和未来趋势与东亚资本主义的起源路径息息相关。如果想对东亚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和演变进行梳理,还得首先从东亚资本主义是如何发生的这一问题开始谈起。
关于东亚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论述以韦伯提出的中国命题为最早和最具有原创性。这主要集中在韦伯写于1905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1915年之后出版的《儒教与道教》之中。应该说,韦伯提出的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命题是他研究西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时的副产品。韦伯在研究西方资本主义诞生与西方新教伦理(the protestant ethic)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中国、印度等非西方国家缺乏包含有与西方新教伦理相近的精神,因而不会产生出近代资本主义。韦伯意在以之反观和证明资本主义在西方产生的独特性和惟一性,“是要寻找并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说明近代西方形态的独特性”(注:(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在《儒教与道教》一书的结论部分,韦伯认为,“较之于西方,中国尽管具有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外在条件,但就像在西方和东方的古代,或在印度和伊斯兰教盛行的地方一样,在中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然而,“可以预料,中国人同样能够(也许比日本人更加能够)在现代文化领域学会在技术与经济上均已获得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注:(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页。)。关于中国能够“学会”得到充分发展过的资本主义的原因,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曾作过论述。他把初生过程中的资本主义与取得胜利后的资本主义二者跟新教伦理的关系作了区分,认为在资本主义诞生时需要新教伦理的催生,但“胜利后的资本主义不再需要它的支撑,因为这个资本主义的基石是机械”(注:(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6页。)。二十世纪初期的韦伯已经认识到了西方宗教文化与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之间相互剥离的可能性。以上的论述构成了韦伯论证中国与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关系命题的两项主要内容:从发生学角度而言,中国没有产生西方理性资本主义的文化和其他社会结构条件;但有能力和有可能成功模仿成熟的资本主义体系。大体而言,韦伯命题的适用范围可以扩及与中国文明有亲缘关系的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历史上属于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
自从韦伯命题诞生以来,出现了许多东西方学者对韦伯命题的解释和回应。赞同者不必说,反诘者大都从两个方向否定韦伯命题。
一是认为没有外国的入侵,资本主义也会在中国和日本内部自然生成。这种观点以中国学者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成果和贝拉在《德川宗教》一书中对日本的论证为代表。罗伯特·贝拉认为,日本在德川时代的宗教信仰与韦伯表述的西欧资本主义精神一样包含有共同的“理性化”和“合理化”成分(注:(美)R.贝拉:《德川宗教》(中译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五章。)。而在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一些学者不遗余力地从中国古代社会内部找寻资本主义萌芽的证据。其中一些观点甚至认为中国在南宋时期,在商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和部门里,资本主义的萌芽已经稀疏地出现了;在明清两代的主要手工业部门中资本主义萌芽更是有所发展(注:傅筑夫等:《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2页。)。在整个封建社会后期,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虽遭重重压迫,但中国固有的资本主义还是照样前进着(注:傅衣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7页。)。“东方社会并非那么落后、停滞”,“原来认为差别很大的东西方,其实有许多是相同的、相似的”(注:马克垚等:《中国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中国历史上缺乏西方中世纪的城市自治,不过这并不能证明中国就无法产生资本主义。”(注:马克垚等:《中国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在中国大陆,所有关于中国历史的标准教科书都持这一观点。这种主张实际上是毛泽东在1938年就作出的”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论断的阐释与翻版。1949年之后,毛泽东的这种说法更是取得了特殊地位,它已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的史学假说的范畴了。
二是利用日本和二战后东亚资本主义所取得的经济奇迹这一经验现象挑战韦伯的结论,认为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也有亲和力。在美国学术界,第一个明确揭示东亚经济高速增长与儒家传统有内在联系的学者是赫尔曼·卡恩。其论点主要集中在1979年出版的《日本的挑战》(与Thomas Pepper合著)和《1979年及其后的世界经济发展》这两本著作中。卡恩认为,东亚社会中的现代儒家伦理主要包含有诸如强烈的奉献精神、对政治群体的认同、内在责任感和较高的文化素养等内容。新儒家文化与韦伯阐述的清教伦理相比更具有优势,新儒家文化圈国家所独具的这一伦理思想使现代东亚社会可以达到比其他社会更快的发展速度和更高的经济效率。这种文化优势使日本、“四小龙”和马来亚与泰国的华人比西方更善于工业化。与卡恩观点相近的是英国工党前议员麦克法库尔1980年在《经济学家》上发表的《后儒家的挑战》(注:Macfarquhar,The Post-Confucianisms Challenge,The Economist,February 9,1980.pp.66~82.)一文中提出的论点。作者指出,儒家是一种增强国家凝聚力的典型意识形态,“正是这种凝聚力才使后儒家国家变得特别可怕”。“儒家伦理在后儒家时代对大部分东亚人仍然起到精神指南的作用,就像山顶训诫在后宗教时代对西方人仍然是一种准则一样。”麦克法库尔最后得出结论:“如果说西方的个人主义适合工业化的开拓阶段,那么后儒家的集体主义更适合大规模的工业化时代。”美国社会学家皮特·伯格(Peter Berger)(注:(美)皮特·伯格:《一个东亚发展的模型:战后台湾经验中的文化因素》,《中国论坛》第222期,第19页。)则认为,而对东亚经济奇迹,在本世纪初最让韦伯关切的问题即现代资本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再度出现了重大意义。他赞同卡恩和麦克法库尔的观点,也认为儒家传统对东亚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伯格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对促进东亚经济迅速发展的“儒家传统”作了一个特别的区分,即他所指的儒家传统并非指文人、官吏等精英人物信奉的正统儒家意识形态,即政治儒学,而是指市井平民平常遵循的思想、价值和信仰,是属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俗世儒家传统。伯格认为,韦伯所指的儒家其实只是中华帝国上层的意识形态,但东亚现代化则是根源于东亚世俗的精神传统——“庸俗的儒家思想”。它与西方的新教伦理一样,不仅渗透到了普通人的灵魂,体现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和经济生活中,也培育出了普通大众遵奉的自律、节俭和奉献的精神。这种庸俗的儒家思想给东亚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力,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东亚模式。伯格更进一步推论,东亚成功地实践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非个人主义形式,这些国家可以被称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第二例”。这些学者都程度不同地把文化因素看做是推动东亚国家政治变革、经济变迁的重要动力。正如美国墨子刻所言:“韦伯在他的文化时代要说明的儒家文化的失败,而我们则必须说明它的成功。”(注:(美)墨子刻:《摆脱困境》(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5页。)当代大多数新儒家的著作同意这一观点,有人甚至还提出了“儒家资本主义”的概念(注:Herman Kahn,The Historical and World context of East Asian Development,See Asian Security in the 1980s.)。
然而,如果我们对照韦伯命题原始文本的意义来对这些理论进行分析和评判,就会发现上述两种反驳韦伯命题的观点并不足以完全否定韦伯。对于中国或日本的“资本主义自然生成论”而言,没有西方的外力介入,中国或其他东亚国家也会发展出资本主义的论点是纯属推测和臆度的非历史性结论。东亚社会在西方列强到达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诞生过类似欧美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首先来自于西方。韦伯命题比这种论点更建立在坚实的历史事实基础之上。如果按照中国在宋代就已达到近代化边缘这一说法,中国的资本主义到1840年几乎已经发展了千年之久。如从明清之际算起,也有四百年左右。正如有位学者指出的,“萌芽”一词是暗喻只有在资本主义落地生根和开花结果的前提下才有意义。而且“世界上竞有何种名花异卉,会‘萌芽’达三四百年还不曾开花结果”(注:(美)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页。)。至于用日本和战后东亚资本主义的繁荣来否定韦伯的结论,也有些文不对题。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和二战后的东亚大陆周边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繁荣,准确地说不属于韦伯资本主义发生命题之中的应有之意。明治时期的资本主义世界已进入了它的扩张阶段,二战后的资本主义更是如日中天。日本和东亚小国在发展资本主义时,不仅已有了一个供它们模仿的样板,而且这些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初始动力主要来自对西方世界压力的反应:为求生存而不得已作出的变通之策。东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对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移植、同化和吸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韦伯并没有否认这种可能。如果从这一点而言,这种观点反而与韦伯命题中的第二项内容相亲和了。
如果我们不能使韦伯的中国命题失去效用,就得承认,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社会的内部土壤中是无论如何萌发不出资本主义之芽和结不出资本主义之果的。从东亚资本主义发生学角度而言,东亚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无疑是外源性和二次性的。它不同于内源性社会变革,由于缺乏东亚传统社会内部机制的支援和配合,使近代以来的东亚外源性社会变迁呈现出巨大的动荡性和不确定性。正是由于这种外源性,使东亚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产生出了许多变量和幻化出诸多可能性来。在缺乏资本主义内部生成的条件下,如何移植、如何引进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引发了东亚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纷争。
东亚资本主义的道路之争:威权与自由
在关于如何进入资本主义的路径方面,东亚社会内部历来存在有威权与自由的道路之争。中、日两国的自由民主思想和民权运动的兴衰是整个东亚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斗争的缩影。
在东亚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急先锋日本,资产阶级自由民权的思想和运动大体经过了三个时期。第一阶段发生在明治政体的确立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摇篮期。以大井宪太郎、中江兆民和植木枝盛等为代表的自由民权思想家,吸收了洛克、密尔和卢梭等人的思想,在日本当时的思想界,不仅提出了具有人道主义含义的观点,还向天皇专制思想发起了挑战。在自由民权运动的政治实践层面,则首先由在1874年因“征韩论”下台的失意政客板垣退助等人发起,并与当时兴起的日本农民运动相结合而掀起了包括成立各种民主社团、党派并倡导成立国会的民主运动。运动的目标在于改变日本政体和明治维新初期形成的有司专政和藩阀政治,认为“政府之变革只是明治的第一次革新,而政体的变革才是第二次维新”(注:(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中译本)第3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且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曾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由于政府收买分化,使得1889年帝国宪法徒有君主立宪之名,却行天皇专制之实。这样,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有点规模但又有些暖昧和可疑的自由主义运动就此不了了之,“明治绝对主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第二阶段的自由民主运动被称为“大正民主时期”(1912~1926年)。它是继承明治十年的、并在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巩固期而兴起的第二次民主运动(注:(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中译本)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62~169页。)。其理论上的代表人物主要为吉野造作和美浓部达吉等。特别是吉野造作针对“国家中心主义的跋扈”,提出“至少有必要对个人自由及其利益、幸福之类的问题多加注意”(注:(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中译本)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84页。)。故此,同时期及其稍后的具有宪政萌芽的八年政党内阁时期(1924~1926年),日本的民主政治有所发展。但随后在军部势力兴起和法西斯政权形成之后,使日本社会在“相对稳定时期灿烂开放的‘一枝美丽的花朵’转瞬即逝(注:(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中译本)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69页。),日本的自由主义运动和初步的宪政实践就此万劫不复了。而日本自由民主运动只有在二战后的第三阶段,由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之后才得以复兴。
在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开始于严复和梁启超对西方自由主义的介绍,但直到新文化和五四运动之后,自由主义的发展才达到一定规模。前期主要以胡适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大力引进和宣传自由主义的观念和思想为主。在三十年代之后,中国的自由主义逐渐开始进入政治实践的领域。1941年民主同盟的成立是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高峰。民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当时中国流行的自由主义理念转变为政纲的全国规模的政党。作为一个没有武装的政党,在国民党的挤压下,其失败的命运是注定的。“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失败,及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则不可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注:(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8页。)1949年以后中国的自由主义转移至台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逐渐集结在《自由中国》杂志的周围,形成了台湾自由主义运动的最初阶段。
综上所述,东亚近代早期和现代的自由主义的命运已经揭示了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和宪政制度、中国的自由主义运动及其所代表的第三条道路,在中、日各自国内政治舞台的相继失败,宣告了英美自由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失败告终,以日本为模式的威权资本主义在东亚大行其道,威权资本主义在东亚最终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东亚威权资本主义:生成的背景及其特征
东亚近代以来的威权政体可以区分为左翼极权政体和右翼威权资本主义政体。后者包括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天皇制和二十世纪开始形成的法西斯政体、1949年之前在中国大陆和1949年之后在台湾的国民党一党专政、韩国二战后形成的军事独裁政权以及新加坡独立后的一党体制等。这种政体以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和军事警察统治为特征,国家力量几乎笼罩了国内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因而显然缺乏民主宪政必须具备的选举程序和法制体系。
东亚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的十九世纪下半期,正是列国纷争和强权盛行的帝国主义时代,也是欧洲霸权从广度和深度向世界的扩展时期。这一时期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在欧美甚嚣尘上。那些后起的欧洲国家诸如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和崛起本身都是通过血与火的战争来实现的,其外交政策更是奉行赤裸裸的“争夺阳光下地盘”的扩张政策。即使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和美国,在对待自由民主的态度上,也采取着双重标准:在国内基本上推行自由民主政体,但对外特别是对非欧洲国家则无视起源于欧洲的国际法标准和当地人民希望保持民族独立的意愿,用武力强行推行其殖民统治,并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作为优等的白色人种统治劣等有色人种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中充满了强权和暴力。其后的大独裁者诸如墨索里尼、希特勒就是出生于这一时代。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世界更是充满了血腥的战争和革命,也是一个各种疯狂和极端的政治势力崛起的年代。正如鄂兰(Hannah Arendt)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初版序言中描写的那样:人们“被扔进由战争和革命的暴力产生的混乱中”,“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漂流无根的心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仍然是帝国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占据上风的时代,民族独立运动和由十月革命开始的共产主义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左翼的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右翼的德意法西斯政体等威权政体盛极一时。甚至连自由主义大本营之一的美国,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也在流行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经济流派。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自由主义本身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中,东亚的自由主义更像一株没有根系的脆弱的芦苇,欧美国家在全球播撒下的暴力和仇恨,在东亚终于收获了暴政体制建立的恶果。此时,东亚国家向西方国家学习和切身体会到的并非是民主自由政体的优越性,而首先是弱肉强食的国际丛林法则。一战前后的日本、中国,其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正是处在这种极其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可供中、日两国选择和效法的政体模式,显然不利于对英美式资本主义自由政体的选择而有利于威权政体。东亚国家近代以后的第一部宪法“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也以具有浓厚军国主义色彩的德国宪法为蓝本。而二十世纪统治中国的国民党政权同样以苏联、德国和东亚现代化的成功者日本等极权国家的政体作为效法对象:国民党的组党方式参照并采用了集权式的列宁主义的建党方式;国民党的许多重要军事骨干皆从1910年代的留日学生中间产生,德国的军事教官和顾问也充斥于国民党的军队中。外部因素对国民党威权政体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二战后,东西方的冷战对峙又加固了东亚威权政体存在和暴政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基础。随着冷战的开始和中共在大陆势力的逐渐增强,美国对东亚战后安排重新作了调整,美国实用主义的考虑最终超过了理想主义的考虑,日本、韩国和台湾等东亚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迅速被美国纳入到冷战格局中的反共防波堤的战略地位之中。美国在1951年与日本、1954年与台湾、1958年与韩国分别以缔结双边条约的形式正式将它们纳入了全球范围的冷战体系中。为避免这一地区经济崩溃和内部发生革命,美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还向这些国家和地区注入了大量经援和军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美国的直接援助虽然大幅度降低,但仍然以单边大幅削减关税以及其它经济手段支撑着这些政权。美国要刻意利用东亚资本主义威权政府即右翼军事集权统治来达到遏制左翼集权国家的扩张浪潮。由于受到美国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大力庇护,东亚右翼威权政体再次获得了非常有利的国际生存空间。
从西方列强在十九世纪中叶大举入侵以来,作为现代化后发地区,东亚国家大都面临着重构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结构的任务。政府需要使用超常的国家威权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和财力以打造一个能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现代民族国家实体。在这种严酷的生存危机的压力之下,富国强兵几乎成了东亚各国上层精英和下层人民的共识。如果将近现代东亚与西方的政治体制的建立过程相比较就可知,西方近现代政治制度是随着国内民权运动的发展而逐渐完善的,国家的权力处处受到民权的制约;而东亚现代政治体制的建立则是在争取民族独立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国家的权力高高凌驾于民权之上。二战前,东亚的主要国家日本和中国先后用铁血政策把人民推向民族主义和实现工业化的轨道,明治维新、辛亥革命后的国民政府的主要目标无非就是外争国权、内部实现工业化而已。然而,自由主义在东亚的失败,并不在于自由主义者本身,而在于缺乏自由主义纲领实现的环境和机会。但是威权政体在东亚各国内部却普遍获得了强有力的生存空间。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以及其后的法西斯政体、中国国民党时代施行的军政和训政,都从来没有把民主的目标放在首位,故此,东亚国家的国权获得了比民权更为优先发展的权利,人民不得已被迫在极权制度下呻吟。二战后日本虽然在美国的占领下实行了民主化改革,在美国“指导”的民主体制下,在政治自由化改革方面比同时代的其他东亚国家取得了更多的成就,但因日本保留了战前诸多的威权成分而仍然处在向完全的自由民主政体的演进过程中。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为对付内部的革命和来自外部的威胁不断强化它们各自政权的威权性和军事统治特征,并一度形成了白色恐怖的政治局面。新加坡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作为从马来亚联邦新独立出来的前英国殖民地和城市型国家,除了生存空间狭小之外,新加坡还面临着重新塑造民族认同、锻造国家意识形态的任务,政府不仅向民众灌输并培植一整套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而且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新加坡式的家长型威权政府。然而香港在经济上一直作为繁荣的自由港而存在,但在英国殖民势力撤出之前,在政治方面并没有实行和英国一样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
与在政治上实行威权统治相对应,上述东亚国家和地区(香港除外)在经济上大都施行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取向的发展战略。在日本,政府在制定和推动经济发展战略时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明治维新开始实行的经济政策本身就是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战后经济的恢复过程中,以通产省(MITI)为主要代表的政府在技术引进、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时仍然起着决定性作用(注:Chalmers Johnsom,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p.16~17.)。战后韩国和台湾地区也同样都实行着政府指导下的经济发展战略,前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以钢铁石化等与军事相关的重工业为优先发展目标;后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又转向了以生产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产品为主的出口导向新战略。新加坡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则在政府推动下先后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61~1965年)、第二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和第一个十年计划(197l~1980年)。显著的政府导向,明确的产业政策,国家与市场相结合,国家利用市场手段达到政府目标,形成了约翰逊所称的发展型国家类型(注:Chalmers Johnson,the People Who lnvented the Mechanical Nightingale,Daedalus,Summer,1990.pp.74~75.)。这是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最主要特征。
东亚的政治文化传统即儒家思想里的重权威、喜秩序、崇尚和谐、重视教育、集团利益至上等成分也有助于近代以来东亚威权政体的建立。儒家思想的这些内容在被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整合和改造之后,去掉了传统文化中的抑工抑商成分而与工业化和市场主义相结合。这种传统的政治文化正好适应了东亚资本主义威权政体的现实需要。
东亚威权资本主义走向终结:一种价值评判和历史的最终选择
历史总是沿着一定的轨道在前行,但这种轨道既不是既定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定的物质条件、社会环境、可继承和利用的思想资源以及人类所特有的创造性活动共同推动着历史的向前发展。东亚威权资本主义政体正是上述各种条件混合产生的结果。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之后,由于国内外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二十一世纪新时代里东亚的威权政体已经、正在或将最终走向自己的终结。
威权政体只有工具性价值而无内在性价值。东亚这种威权政体之所以具有某种合法性和一定的正当性,仅仅是因为在当时的具体情境下还具有实现国家和民族独立的外在工具性价值。实现普世性的人类尊严和人类自我解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明之理,但东亚国家要实现这一目标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中还需要先成为国际平等的一员。人民忍痛暂时将民权让渡和匍匐于国权之下,为的是民权在未来正当的国权获得之后得到伸张,实现国权仅仅是民权实现的手段和保障而已。但过分的国权扩张必将损害民权的最终实现,东亚威权政体多把人民只当做实现富国强兵目标的手段,人民只具有充当劳动工具和战争炮灰的价值。“采用好战的现代化的强硬外壳来保护大量中世纪传统文化,在这其中不少东西具有原始性,孕育着爆发的深重危险。”(注:Hu Shih,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and Japan:A Comparative Study in Cultural Conflict,The Cultural Approach History,ed.by Caroline F.Ware,New York,1940,p.245.)实际上,东亚威权政体在取得令人称羡的成就的同时,也令东亚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并足以显示了威权政体这一工具性价值的毒害性。日本从1894年到1945年半个世纪中连续发动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参加了一战、二战。不仅日本国内人民被当作战争炮灰惨死异国他乡,而且仅在二战中的中国一国,在八年里就损失两千万生灵。与对外战争之残暴相比,威权政体对内所施的暴政也在伯仲间。在实行威权政策的东亚各国内部,肆意逮捕持不同政见者、悍然屠杀那些抗议和集会的学生与民众等违反和践踏人权的事例屡见不鲜,××惨案、××屠杀和××事件充斥于东亚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更为重要的是,威权政体极端的高压政治以及对人民施行反理性主义的灌输式教育,通常使国内民众的良知和正义长期处于蒙昧黑暗之中而不得自觉,民族(甚至包括所谓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整个道德思想水准和整体素质下滑堕落到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以下。反省的不仅仅是外国右翼军国主义分子,威权政体的领导人对国内政策更应该自省。政府不管以何种理由残害本国生灵,戕害和泯灭人类的灵魂和智性,这与异国侵略者屠杀同胞同样是在犯罪。由此看来,外国强权和国内暴政一起构成了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权利的严重威胁。因此,人权的标准也本来不应该内外有所区别。二十一世纪初的东亚各国早已步入了国际大家庭,而一些东亚国家的领导人也俨然以一等国际领袖的面目出现于国际舞台上,在这种国权已充分实现的前提下,如果某些东亚政府的领导人企图把只具有外在手段和工具性价值的威权政体内化为目的和永恒价值,不仅本末倒置,而且将犯下妄图奴化人民并使文明倒退的反人类的严重罪行。
东亚威权资本主义具有明显的时效性,并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特征。经过二战后三十多年来的发展,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东亚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演变的内外条件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威权政体目前正在失去其在国内外存在的效用性。
冷战后的政治格局已经使东亚资本主义地区丧失了以往拥有的“国际环境比较利益优势”的地位。首先,在国际政治关系方面,冷战的结束使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世界民主地域范围在冷战后的不断扩大,民主国家间无战事的范围也相应扩大。战争虽然还在处于现代文明边缘阶段之间的国家间以及现代文明与文明边缘国家之间时有发生,但在主流文明世界里已基本不再作为国家间解决争端的主要手段了。全球协调性组织诸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在后冷战时代解决国家间政治和经济争端中将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威权政府实行的“富国强兵”等任何强化国家主权行为的政策在当今世界不仅过时,而且成了反和平与民主的不和谐噪音。东亚威权国家如果真想在文明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并发挥重大作用,就必须自我校正原有的行为标准,以主流文明世界普遍接受和认可的准则来处理国内外事务。在这一大背景之下,东亚资本主义地区在世界中的战略地位与冷战时期相比明显下降。美国政府不仅调整了以往对这一地区的呵护政策,而且已经开始把这些国家和地区作为经济上的主要竞争对手和推广普世人权价值观的重要障碍。“美国已把昔日的样板涂改为今日的威胁”(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语)。东亚威权政体在新时代中,不仅丧失了在国际政治中的生存空间,而且也失去了最大的政治靠山和保护伞——美国的支持。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以廉价而加速发展的信息传媒技术(电视、电话、因特网)和先进的交通工具(特别在航空方面)所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使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和渗透性在不断加强,一个以全球为舞台的国际经济大分工的格局正在出现。人员、资金、原料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越来越变得迅捷而广泛,跨国公司已经基本挣脱了国家力量的控制。以政府主导为特征的传统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下的各种政策和措施,包括出口补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之下明显属于违法行为。第三,在这种开放的世界体系里,各国的内政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增大。国家不仅无力控制金融资本的快速流动,而且更无力阻挡思想、文化和图像等信息符号的大规模渗透,思想与信息获得途径的简易性和信息传播的广泛性,正在或者已经瓦解了威权政体对舆论、思想等信息资源的垄断权。这种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全球化过程将进一步促使权力从政府向市场转移,从集中向分散发展。全球化不仅正在消解着主权,而且也导致政府大权旁落,作为分享主权遗产的继承者,既有国际机构,也有非政府组织和新闻媒体。与全球化时代的信息技术最相适应的现有政府组织方式是自由民主政体,东亚政府以一种家长式的、一元化的方式来控制人民生活各个方面的传统做法已经难以维系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东亚资本主义各国内部政治和经济的最新发展已使威权政权存在的国内平台消失。经过一二百年的流血争斗,亡国灭种的危机已经成为过去,东亚国家基本上取得了独立的生存权,并已经获得了正常国家的身份。在这一比较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中,扩大政治参与度和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的条件已经具备。在经过二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东亚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内部已经培育出了一个力量强大而且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国内阶级鸿沟基本填平,阶级结构布局日益均衡化,政党格局也呈现出了多极化的趋势,国内的政治决策和执行过程越来越受到社会内部各种政治力量和利益集团的掣肘,民众希望实现人权保障和民主化的要求喷涌而出。以牺牲大众的福利和压抑民主权利为代价来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政策以及这一政策的执行主体——东亚威权政体已经成为过时之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韩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逐渐从军人政府过渡到了文人政权,并在二十一世纪初通过民主宪政选举程序已经顺利地实现了多轮政治权力的和平交接。经济上东亚国家基本上都跨过了工业化初级阶段的门槛,在工业化深化发展的同时,也已开始向后工业时代转变,工业化初期的那种靠汗水(perspiration)和大规模动员社会资源的野蛮和粗放的经营手法在以依靠灵感(inspiration)、创新为特征的后工业时代已经变得过时。而且正如克鲁格曼早在1994年就已指出的那样(注:Paul Krugman,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Foreign Affairs,11/12,1994,pp.62~78.),东亚这种依靠大投入(包括劳动力和资本)、政府推动的外延式增长方式已经或者即将走到尽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衰退,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表现出的官商勾结、裙带蔓延和缺乏透明度的黑箱操作结出的苦果,更宣告了构成威权政体与市场体制相结合的东亚奇迹神话在新的政治经济历史条件下的彻底破产。
儒家文化及其伦理是解释东亚威权政体存在合理化的主要哲学基础,但儒家传统并不是像威权政府领导人宣称的那样是自由民主的主要障碍,儒家文化具有相当强的适应各种社会环境的自我调适能力,在新的自由民主政体之下同样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儒家传统在当代并不构成建立自由民主政体的真正障碍。这主要因为,一方面,“伟大的历史文化传统,像回教或儒教都是各种思想、信念、信条、论点、作品和行为模式的十分复杂的综合体”(注:(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74页。),其中既存在有利于独裁专制的东西,也有与民主自由理念相一致的东西,还可以从中找出萌芽社会主义理论的证据,人们完全能从中挑选他们所需的内容。另一方面,文化并不孤悬于整个社会系统之外,而是会渗透到组成社会的各要素之中。文化只有通过并依托于一定的体制和结构才能作用于政治、经济过程。特别是在作为外源性变迁的东亚现代化的个案中,儒家文化从未作为东亚近现代制度变迁的“火车头”和决定性力量而发挥作用。在东亚外源性社会变迁中,器物和制度层面的变化总是先于文化观念层面的变化,近现代以来的儒家文化从未决定过制度,倒是各种制度在重构着儒家文化。
实际上,儒家文化因素的社会功能和适应的对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了巨大的弹性空间。儒家曾经作为东亚传统农业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而风光两千年,但在近代之后随着东亚各国现代化进程步伐的加快,失去传统政治经济体系支撑的传统儒家文化在新的政治、经济制度框架内却又开始呈现出积极作用。在十九世纪末期日本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特别是东亚其他国家在二战后,即传统的政治制度相继瓦解并相继赢得政治和民族独立之后,从旧制度剥离出来的儒家文化开始被现代国家机器打造成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工具。儒家文化所包含的尊重权威、勤劳节俭等价值观在经过政治、经济等社会强力要素的整合后,越来越显示出传统文化服务于现代社会系统的“工具”色彩。在当代日本以及东亚新兴工业社会中,包括儒家在内的东亚传统文化已经被完全整合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中,并成为东亚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被改造过的儒家不仅可以服务于威权资本主义政权,而且还可以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共存。这说明,在经历了工业化的初步发展和与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充分接触之后,儒家同样也可以与自由民主政体进行结合和嫁接。
儒家在经历了两千多年与传统农业社会水乳交融的生成和发展期之后,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实现了儒家与工业主义、民族主义的结合,构成了一些东西方学者所称的儒家资本主义。这是儒家的社会功能在历史中的第一次大转换,即从重农抑商向工业化和适应现代民族国家的功能性转变,这可以称得上是儒家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次革命期。不过,随着东亚经济进入稳定增长期和逐渐与国际经济接轨,这种儒家文化观同缺乏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的经济增长过程一样也潜伏着与传统市场经济规律相悖的要素:人治与裙带之风。在欧美甚至有的学者干脆将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资本主义经济称之为“老伙计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注:International Mone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Washington,1998,IMF.)。如果说儒家第一次革命造就的东亚威权资本主义政权在现代化初期有助于弥补“市场不灵”(mar ket failute),以一党专政为主要特征的强制性一元化政治秩序还能有力促进现代化的最初启动的话,那么,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在以信息技术(IT)和创新为基本特征的新经济以及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时代,新经济自身则要求社会价值体系具有崇尚变化创新和宣扬个性自由发挥的特点,而外部的全球化趋势又使各国间的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广泛流动成为必然,儒家文化中的喜同一与稳定、恶差异与变化的特征就潜在地阻碍着新经济和全球化在东亚国家的深入展开,儒家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内容在目前和未来经济发展中将显示出更多的负面作用。由此可知,东亚文化在未来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拉锯战中,将不得不综合创新以适应新时代的挑战。而全球化也会因东亚传统文化的演变发展被注入新因子和新活力。
总之,东亚威权政体所具有的价值工具性、时效性、在现实中的荒谬性和儒家文化在自由普适主义条件下的可塑性,使东亚威权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正在或即将终结。
1994年东亚国家的两位著名领导人李光耀与金大中在美国《外交季刊》3、4月号和11、12月号上分别撰文阐述各自观点,对威权资本主义和民主市场两条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战和辩护。这是一个世纪以来关于东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问题的争论在新时代的回音。李是一位亚洲价值论的坚定捍卫者,主张东亚国家应该走一条有别于西方式自由民主的具有亚洲特色的道路(注:Fareed Zakaria,Culture is Destiny.A Conversation with Lee Kuan Yew,Foreign Affairs,3/4,1994,PP.109~126.);金在文章中则呼吁在东亚国家中普遍建立自由民主政治制度,指责东亚“威权政府的领导人及其辩护者的抵制”才是推行民主制度的障碍,认为“文化并不决定命运,决定命运的是民主”(注:Kim Dae Jung,Is Culture Destiny?The Myth of Asia's Antidemocratic Values,Foreign Affairs,11/12,1994,pp.189~194.)。1997年12月19日,金大中在当选韩国总统的首次讲演中,正式把“促进民主”和“发展经济”的民主市场理论作为其施政纲领的基石。最具戏剧性变化的是,李光耀于2001年3月在一次有关经济发展的讨论会上却从其所钟爱的亚洲价值观立场退却,坦言儒家价值观不仅“导致了过分的做法”,而且在信息时代也已经过时(注:2001年3月,在初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亚洲价值观的头号鼓吹者李光耀放弃了先前的观点,提出儒家价值观在信息技术时代已经过时,并对儒家的“孝道”表示了疑义:“尊重老人在信息时代似乎管不了什么用。父亲未必最有学问,孙子也许懂得更多。”其实,如抛开伦理观念不谈,这是比较符合社会发展现实的。在农业时代,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千年一进”,社会模式相对固定不变,长辈累积下的经验教训对晚辈而言弥足珍贵;但在信息时代,技术进步“口进千里”,长辈的经验已经落伍,甚至同时代人的经验和知识也需要及时更新。由于晚辈的知识与时俱进,长辈和“我辈”反倒需要向晚辈学习了。)。李光耀作为威权资本主义道路的“护法者”,其观点的改变具有着历史性的象征意义。总之,东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或者从更广义的东亚现代化发展模式来讲,在二十一世纪新时期里已进入了路标转换期:向民主市场模式转变。
标签:自由主义论文; 韦伯论文;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经济自由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儒教与道教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