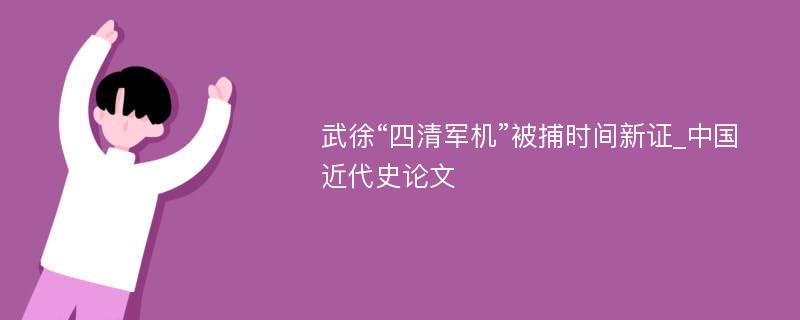
戊戌“军机四卿”被捕时间新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机论文,时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戊戌政变后“军机四卿”被捕的时间,近代以来的私家著述记载不一。学术界多以清宫档案和官文书为主要依据,认为他们与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等人一起均被捕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1898 年9月24日)(注:关于“军机四卿”被捕的时间,《康南海自编年谱》言四人均被捕于初九日;《戊戌政变记》言谭嗣同被捕于初十日,其他三人被捕于初九日;肖一山《清代通史》则言四人均于初十日被捕。对此,林克光先生在《戊戌政变史实考实》一文(见《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中指出,对于参与变法诸人被捕的时间, 似应以清宫档案和官方文书记载为准。据《清德宗实录》卷426 记:“(八月初九日)军机大臣奉上谕: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审讯”。又据戊戌年八月十一日刑部尚书崇礼等奏案情重大请钦派大臣会同审讯折(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档案材料,亦提及初九日步军统领衙门奉上谕“将张荫桓等七人悉数拿获”,并于初十日解送刑部之事。因此,林克光先生认为,慈禧是初九日下旨令步军统领衙门拿张荫桓等人的。因为此七人均未逃匿,故该衙门当天即将他们“悉数拿获”。此外,台湾学者黄彰健也持此说。)。然而,新披露出的一些材料表明,“初九日被捕说”仍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其中也涉及到分析和利用有关档案史料的问题。
一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中,收有近人魏允恭于戊戌年八月初八日(1898年9月23日)致汪康年等人的一通密札。 札中自称亲眼目睹了杨锐、刘光第、谭嗣同三人被捕的情形。现将该札内容摘录如下:
“穰、敬、仲公同鉴:前昨连发三电,收到否?……初七日前所发之信,一一均收到否?……(康)南海系奉太后密旨拿问(密旨中有‘结党营私、紊乱朝政’八字),适隔晚赴津,闻有获住之说。幼博(康广仁)已交刑部审讯。今早五更又奉密旨拿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四人,弟亲见步军统领监送登车,想已发交刑部。惟林旭尚未寻着,闻避往他处,此新政中至新者,其余外间传说纷纷不一。有谓此四人拟上条陈,请更服色殊器械者;有谓党南海者;有谓幼博在刑部诬攀百数十人,此亦在内者。总之,昨日上谕有‘门禁森严’等语,则幼博等人入内办事之说不为无因。慈宫震怒,究不知何人传递消息?且近日严拿各人,旨意甚密,竟有先拿一人,余人均未知悉者。是以新政诸人咸怀股慄,激则生变,时局正多反复,杞人之忧,正未艾耳。……敬颂台安,弟名心叩。八月初八日(八月十七日到)。”(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3115—3116页。)
此札是魏允恭写给上海《时务报》馆汪康年(字穰卿)、曾广铨(字敬贻)和汪诒年(字仲阁)三人的。魏允恭(1867—1914年),字蕃室,号让吾,湖南邵阳人。光绪十七年(1891年)举人,官内阁中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梁启超、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时,曾一度充任该报英文译事曾广铨之笔述。戊戌维新后期,被两江总督刘坤一保荐经济特科,于是年七月十二日(8月28日)到达北京。 魏氏抵京时正值新旧斗争尖锐,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之际。他受《时务报》之托,多方打探朝局变化的消息,及时电告或函告上海报馆,充当了《时务报》耳目的角色。此札即是魏氏向汪康年等人通报消息的函件之一。
该札写于八月初八日,汪康年于八月十七日方才接到。从其内容看,反映的主要是八月初六日后慈禧捕拿维新人士的情况。其中难免有一些传闻和臆测,但所言杨锐、刘光第、谭嗣同被捕于八月初八清晨则完全可信。因为他们被捕后,魏允恭曾“亲见步军统领监送登车”(注:据魏允恭致汪康年的另一通函札(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3114页)言,魏氏到京后,寄寓“南半截胡同工部李寓”,而谭嗣同寓居的浏阳会馆在北半截胡同,两条胡同南北相对,相隔不远。这恐怕正是魏氏得以现场目睹谭嗣同被捕并亲见谭与杨锐、刘光第“登车”而去的原因所在。)。
魏氏目睹的这一情况,与较为流行的“军机四卿”被捕于初九日的说法是相矛盾的。据魏氏言,初八日五更慈禧已有密旨捉拿“军机四卿”。而“初九日被捕说”则认为步军统领衙门是初九日奉谕旨逮捕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及“军机四卿”的。显然,弄清慈禧下达逮捕“军机四卿”命令的时间,是确定他们被捕准确时间的前提和关键所在。
二
许多材料及后世学者的研究表明,慈禧下令搜捕“军机四卿”等维新人士是在八月初八日,而非初九日。
在近些年对戊戌政变史实的考证和研究中,由于学者们广泛利用了清宫档案,从而澄清了一些长期以来以讹传讹的旧说法。其中对“慈禧初六日训政并非袁世凯告密直接引发”的论证尤具代表性。实际情况表明,慈禧获悉袁世凯告密消息是初八日清晨,而不是初六日训政之前;袁氏告密的直接后果并不是导致慈禧宣布“训政”,而是引发了她对“军机四卿”等维新人士的大肆逮捕。对此,台湾学者和大陆学者观点基本一致,并都对此做了严密的考证(注:可参阅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70年版);孔祥吉《关于戊戌政变二三事之管见》,《历史档案》1983年第3期; 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见《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林克光《戊戌政变史实考实》,《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 期。)。
既然初八日清晨慈禧已知康、谭等人的“围园”密谋,为何迟至初九日才下旨逮捕谭嗣同等人呢?这正是“初九日被捕说”无法解释的一个谜点。就当时事态发展的急迫性以及慈禧本人性格和心境而言,决不会推迟捕拿行动的。对此,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言:“八月初八日,皇上率百官恭贺训政。……时太后已接北洋袁世凯出首告密之事,追问皇上何意,上只得推康、谭,否则立受廷杖矣。当即饬下步军统领捕拿张荫桓、徐致靖及新进诸人,禁皇上于瀛台。”(注: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丛刊(一),第348页。)这里所谓“新进诸人”, 即指“军机四卿”。
维新官员张荫桓事后的回忆也为慈禧初八日下令捕人提供了佐证。《驿舍探幽录》记述张荫桓戊戌年八月十九日回忆自己被捕的情况时云:
“初八日辰刻,提督崇礼遣翼尉率缇骑至我宅,邀我赴提督衙门接旨。……抵提督署,各官均未至,坐数时,天已暝,仍无确耗,遂令人取行李住一宿。次日(初九)有旨拿交刑部审讯,(初十日)入监住。”(注: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丛刊(一),第488—489页。)
张荫桓在政变后被革职遣戍新疆。《驿舍探幽录》是负责押解张荫桓的官员王庆保、曹景根据与他的数次谈话内容整理成的一篇文献。张荫桓的上述回忆表明,尽管清廷是初九日才正式颁旨对其宣布“革职”“审讯”的,但初八日清晨他已被以“接旨”为名诳至步军统领衙署(提督署),实际上已遭到监视。可以肯定这是奉慈禧的旨意办理的,否则步军统领是没有资格对一位现职二品官员采取这种非礼待遇的。换言之,初八日清晨慈禧已决定逮捕张荫桓。可见,慈禧确系初八日清晨谕令搜捕“军机四卿”等维新人士的。
三
魏氏密札言初八日步军统领衙门未能捕到林旭。对于林旭被捕的情况,《郑孝胥日记》中则有较为详实的记述。
郑孝胥(1860—1938年)字苏戡,又字太夷,与林旭(字暾谷)同为福建闽县人。郑氏晚年虽然追随清废帝溥仪到东北建立伪“满洲国”,沦为臭名昭著的大汉奸,但在戊戌时期仍不失为一位思想开明的进步人士。政变发生前,郑孝胥因湖广总督张之洞保举经济特科而奉旨进京预备召见。他于七月初十日(8月26日)到达北京,寄寓福州会馆。 郑氏抵京后,林旭频频造访,特别是七月十九日(9月4日)林旭被任命为军机章京后,曾向郑孝胥吐露了许多政情内幕。从《郑孝胥日记》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林旭被捕前最后的活动痕迹,也可以看到一些涉及政变真相的珍贵史料,现将相关内容摘录如下:
“七月廿三日(9月8日),……暾谷来,余戒以慎口,勿泄枢廷事。
八月初五日(9月20日),……返馆,幼陵(严复)、暾谷皆来, 暾谷言,上势甚危,太后命新章京所签诸件,自今日悉呈太后览之。又言杨崇伊纠合数人请太后再训政,且以‘清君侧’说合肥(李鸿章),又以说荣禄。
八月初八日(9月23日),既寝,暾谷忽至,复起,谈良久, 自言不得以康党相待。
八月初九日(9月24日),晨起作字。闻街市传言, 有缇骑逮七人,即四军机章京,三人未详。……(林)怡书来,言有官员至其宅,言礼王传林旭面话,不及待车,步行而去。且云,宫中终夜扰动,发三电促荣禄来京矣。”(注: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册,第678—682页。)
据林旭对郑孝胥言,八月初五日,慈禧令将七月二十日以来“军机四卿”签拟诸件统统检出,由她重新审阅。这说明,慈禧已不能容忍新政再继续下去,并剥夺了光绪帝独立处理政务的权力。由皇帝超擢重用的“军机四卿”也开始受到冷遇。作为“围园”密谋的知情者,林旭已有惶惶自危之感。初八日深夜他与郑孝胥谈话时“自言不得以康党相待”,即是这种心情的流露。果然,初九日领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令人至林怡书宅,“传林旭面话”。林旭“不及待车,步行而去”。此去即落入魔掌。林怡书(又作贻书)即林开謩,福建长乐人,与郑孝胥、林旭关系极密,时为翰林院编修。林旭被捕前一直“寄居开謩家”(注:曾毓隽《宦海沉浮录》,见《近代史资料》总第68期,第22页。)。所以当他被带走后,林开謩立即赶至郑孝胥处通报消息。因此,“军机四卿”中林旭确系初九日被捕的。《康南海自编年谱》言“林旭入直就缚”或许即指此事。
四
魏允恭致汪康年等人的密札以及《郑孝胥日记》都是原始的第一手材料。这些新材料证实,慈禧是初八日清晨下令搜捕“军机四卿”的,其中杨锐、刘光第、谭嗣同三人于当天被捕,林旭则是初九日拿获的。
那么,为什么现存清宫档案和官文书中找不到魏允恭所言初八日捕拿“军机四卿”的那道“密旨”,能看到的只有初九日宣布对他们“革职”“审讯”的谕旨呢?为什么以这道谕旨及其它相关档案史料为依据的“初九日被捕说”与史实会有出入呢?这些问题只有从慈禧在搜捕维新人士过程中玩弄的手段说起,才能找出答案来。
慈禧捕拿康有为、康广仁与逮捕“军机四卿”的行动虽前后相继,但具体情况有所不同。八月初六日派人捉拿康氏兄弟是慈禧与奕劻、刚毅等后党官僚经过密商后决定的,是与宣布训政同时进行的。事先他们已给康有为拟定了“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注:该谕云:“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见《清德宗实录》卷426。)。因康有为已于初五日傍晚离开北京, 结果步军统领只于初六当天捕到了康广仁。至于对“军机四卿”等人的搜捕则是初八日清晨慈禧突然接到袁世凯告密的消息后才匆忙布置的,凡涉嫌“围园”密谋或与康有为关系密切者均被列入了逮捕名单。鉴于康有为逃走一事的教训,在这次搜捕中,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沉着老练的慈禧采取了先封锁消息秘密捕人,然后再追查内情的稳妥策略。现存清宫档案和《清德宗实录》、《光绪朝东华录》中均未发现初八日这天有下令捕人的谕旨。显然,这次秘密搜捕是奉了慈禧的口谕(注:慈禧不经光绪帝面谕和军机处拟旨,直接向步军统领衙门“交派事件”,乃其特权。据《张樵野戊戌日记》言,戊戌年五月初五日左翼总兵英年曾奉慈禧懿旨(口谕)查抄张荫桓宅,步军统领崇礼因与张私交甚笃,遂“与之(英年)耳语,仍令候军机处旨意”。后经立山、奕劻等人从中斡旋,张荫桓才暂免抄家之祸。是年八月初八日,慈禧又令步军统领将张荫桓传至提督署监视起来。可见,慈禧懿旨(口谕)在行政效力上与上谕相比,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更具随意性。)。这样虽有违常例,却有利于封锁消息。据魏允恭言当时“严拿各人,旨意甚密,竟有先拿一人,余人均未知悉者。”整个搜捕行动布置得很周密,采取的办法也很灵活(例如张荫桓和林旭实质是被诱捕的),搜捕活动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了一天多。正因为如此,除后党核心人物和极少数象魏允恭这样的目击者外,局外人对初八日开始逮捕“军机四卿”等人的活动毫无知晓。待到“要犯悉数拿获”后,慈禧才于初九日发布上谕,正式对外公布消息。这是后党搜捕“军机四卿”等维新人士的真实过程。
时人和后世学者将初九日谕旨习惯性的理解为清廷下达的逮捕令,这是“初九日被捕说”虽与史实不符却不易被人们察觉的症结所在。从某种程度上说,初九宣布对张荫桓等人“革职”“审讯”的谕旨与初六日宣布对康有为“革职”“治罪”的谕旨意义完全不同。初六日谕旨是按正常程序,由军机大臣拟旨,对康氏兄弟立即实行逮捕的“逮捕令”,是在搜捕开始前下达的。至于初九日谕旨,从形式上看虽与前者相类似,实际上它只是对已捕在押人犯宣布“革职”“审讯”的公告,是在逮捕行动结束之后才发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