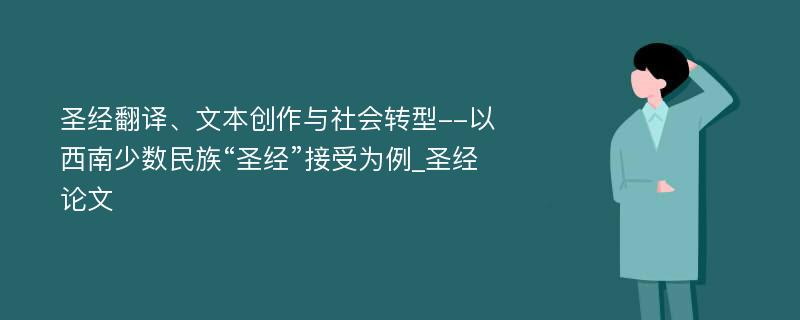
圣经翻译、文字创制与社会转型——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圣经接受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圣经论文,为例论文,少数民族论文,中国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尤其是傈僳族)的文字创制与圣经翻译为分析对象,运用社会人类学、经典研究以及田野调查的方法,通过对文字与经典的社会学意义的分析,指出文字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一种语言保存的方式,而且是一个具有丰富社会学内涵的事件,当其与《圣经》翻译共同出现时,对于这些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威权体系、身份意识都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同时,文字作为一个具有社会人类学意义的象征符号,在从一种口语向多种文字之间的过渡中,多种文字之间的竞争也显示出隐藏在其后的社会力量的博弈。
社会人类学家普遍意识到,书写(writing)不只是一种语言的技术,而且与社会结构与社会行为密不可分。它不仅对语言使用者的精神,而且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产生深刻影响。然而,对于大多数文明来讲,书写技术或文字是如何出现的,它对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只能凭借考古与文献对远古进行猜想。可是,在上世纪上半叶,中国西南地区的诸多少数民族在基督教传入的影响之下,普遍经历了一次文字创制的浪潮,为我们考察书写(或文字)之创制的社会人类学意义提供了一个并不遥远的分析案例。更为突出的是,相伴这一次文字创制浪潮的,是《圣经》的翻译。少数民族文字创制与基督教《圣经》翻译的相伴相随,对于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威权体系、身份认同、精神理念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在其中交织着汉文化、少数民族传统与西方外来力量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色彩斑斓的文化图景。
在过去的研究中,谈到少数民族的文字创制与经典翻译时,人们多将文字视作一种“进步文化”的载体、将“野蛮民族”带入到现代社会、文明生活的标志,①将文字、经典视为这些少数民族融入世界文化的入口,却很少真正地站在分析的立场上,来看待纠缠在文字创制、经典翻译这一过程中的复杂的社会人类学意义。为此,本文提出以下问题:1.在这些少数民族社会,文字出现的社会学后果是什么?2.伴随着文字的圣经翻译,与前文字(preliterate)社会的口传诗歌(Oral Epic)相比,这些少数民族社会在建构社会结构和秩序方面,有什么新的特点?3.接受《圣经》这样一部经典,对于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产生什么样的冲击?4.在文字化过程中,常表现出文字多样化的特点,即不仅只是一种文字(Literacy),而是多种文字(Literacies),那么,不同文字之间的博弈又有什么样的社会学含义呢?本文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字创制与圣经翻译为入手,尤其是以傈僳族为个案,力图对这些问题做一解答。
一、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有着显著不同于汉民族的社会—文化结构,因此,基督教在这些社群和地区中的传布也采取了相当不同的形式。一个非常突出而有趣的现象是,为了使《圣经》成为每一个少数民族信徒均可接近的经典,传教士普遍为这些只有口语的前文字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并用之翻译《圣经》。文字与经典一起,成为这些少数民族社会文化中新的文化符号。
这些创制的用来翻译《圣经》的少数民族文字,包括:苗文、景颇文、傈僳文、彝文、拉祜文、佤文、独龙文、纳西文、花腰傣文、卡多(哈尼族)文等。②总之,基督教在西南各少数民族中的传教活动,虽然程度深浅不一、成就有大有小,但都多多少少将文字创制与圣经翻译结合在一起,以此来推动基督教在这些少数民族中的传播。文字与经典这一对具有非常丰富的社会人类学内涵的文化符号,其影响并非仅仅局限于宗教方面,只有运用恰当的社会人类学方法,才能全面地揭示它们对于这些少数民族社会—文化虽然隐蔽却很深刻的影响。
二、方法论的说明
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字创制与经典翻译这一复杂的社会—文化象征,本文将采用人类学、经典研究(canonical study)、田野调查等多学科的综合方法对其进行分析。
1.文字的人类学研究
文字既是语言学研究的范畴,又是人类学的传统领域,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大家都对文字进行过精辟的分析,通常而言,就是将其与口语(oral language)对立起来,分析它的出现对于人类之精神形态与社会结构之深刻影响。
近来,人类学研究倾向于摆脱在文字与口语之间的两分法,而更多地去强调文字出现所带来的社会学以及心理学后果,即所谓“自主性模式”(autonomous model)。关注的问题包括:复杂的国家与官僚制度如何通过书面文字的形式,对社会进行远距离的统治;文字如何影响人们的记忆方式,使得人们可以准确地引用长篇文本,而不必像口语那样,只能依赖于不准确的、模式化的吟唱等。
此外,人们还意识到应该将文字本身视为社会一文化力量的一个结果,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这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模式”(ideological model)。也就是说:“不应该将文字视为一个单一的现象,而应该将其视作一个多面性的社会—文化载体,它的意义以及它可能对社会与个人所产生的任何影响,都决定性地依赖于与文字相关的社会操作(social practice)以及文字所嵌于其中的意义系统(ideological system)。”③人们因此而形成新的问题意识,如:文字如何成为一种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人们接近这一象征资本的程度有何不同?它又如何成为政治精英控制社会的一个途径?在文字社会与前文字社会之间,有什么样的张力关系?是什么样的力量将文字发明出来,在被引入的(introduced)文字与本土发明的(locally devised)文字之间,又有什么张力呢?在文字之发明或引入的过程中,往往存在着多种文字的使用,不同文字的不同运用又有什么样的社会学意义呢?
现代人类学对文字的研究方法论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问题意识,对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字创制与《圣经》翻译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在这些少数民族进行文字创制之前,存在着漫长的前文字时期,并形成了与之相应的社会结构与秩序,如与民族史诗之吟唱相应的萨满祭师群体。而在文字创制的过程中,从遥远西方来的传教士扮演着领导和中心的角色,并且,伴随着文字创制,出现了一批阅读文字、解释文字的宗教意义的新兴社会群体——教牧人员,他们与前文字时期的祭师之间冲突频仍,并在一定意义上借助文字的力量取代了后者的社会地位。总之,只有将文字看成是一个“多面性的社会—文化载体”,才能揭示出西南少数民族文字创制和圣经翻译中隐含的社会学意义。
2.对经典的社会学分析
与文字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一样,经典与社会之间亦有着强劲的互动关系。首先,无论是从口头传统到书写文本,还是从多个文本(texts)到一本圣经(Bible),它都是选择性的。也就是说,一些文本被确定为经典,就意味着另一些文本被确定为不是经典,在后面隐藏的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博弈,是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化;其次,从多个文本到一本圣经,诸多分散的传统被纳入到一个相对单一的经典之中,有助于使不同社群形成一个相对同一的身份,在此意义上,经典起着一定的社会整合的作用;再次,经典之确立,标志着社会边界(boundary)的形成,而经典的封闭与开放程度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经典群体的社会边界的清晰性与模糊性。口头传统具有流动性、模糊性,与之相应的,群体的身份边界也常常处于流动与模糊之中;而文字经典是相对固定的,尤其是就基督教的经典——《圣经》来说,它是绝对封闭的,不可添增亦不可删减,从而使得圣经群体具有一个清晰的身份边界。
故此,对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圣经》翻译,也应从社会学进路对其进行分析。我们的问题包括:在《圣经》翻译的过程中,各种社会力量在决定少数民族文字的《圣经》的成型中各起什么作用?文字的《圣经》给前文字的口头本土传统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并由此带来什么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圣经》出现之后,这些少数民族的身份意识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当然,对中国西南这些少数民族而言,文字与经典是同时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之中,其社会学进程是交织在一起的,需要我们将它们糅杂在一起进行分析。
3.田野调查的方法
最后,我们对本研究的另一基本的方法论——田野调查做一简单的说明。首先,由于基督教在西南少数民族中的文字创制与《圣经》翻译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许多原始资料已经散落遗失,因此,本研究将集中于对傈僳族的文字创制与《圣经》翻译,以田野调查和访谈作为资料的主要来源。其次,对中国西南这些少数民族而言,文字创制与经典形成都不是原生性的、逐渐发生的,而是由外在力量一次性地引入的,因此,以这一事件为转折点,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前文字、前经典的社区与文字的、经典的社区之间差异巨大。为获取它们之间的差异,本研究以中国云南傈僳族作为个案,采取田野研究的方法,2002年和2003年7月,我们分别选取了两个社区进行参与式的比较观察。一个是云南华坪县的傈僳族聚居区,是基督教尚未成为主流宗教的傈僳社区,原始宗教的操作与结构仍然保存得较为完好,其对社会的影响也较为清晰可见;另一个是怒江福贡的傈僳族基督教社区,基督教是当地的主流文化,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与精神生活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希望可以采用一种“将时间空间化”的方法,通过这两个空间社区之间的差异性比较,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上个世纪上半叶基督教的文字创制与《圣经》翻译之改变傈僳族社会—文化的动态过程。
三、圣经文字、社会威权与社会结构
表面看来,从口语到文字,所改变的只是语言的载体形式,即从以喉舌为载体到以纸笔为载体。但是,在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在深层意义上,它还体现了基督教与本土的少数民族民间宗教之关系。在这里,从口语到文字,意味着从本土的民间宗教到基督教之间的转移,从本土的口传诗歌到外来的成文经典的转移,与此相应的则是整个社会威权体系的转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简而言之,文字的经典对口传本土史诗的取代,在社会人类学上的直接后果包括三个方面:在社会阶层上,牧师取代本土萨满成为少数民族的知识精英、宗教精英与组织精英;在公共活动场所上,教堂取代家室成为公共活动的中心;在道德规训(或可称社会的伦理控制)方面,对权威文本——《圣经》的解释取代了对氏族谱系的吟唱,制度化、日常化的规训(discipline)取代了随意化、仪式化的教化(edification)。以下逐一详述。
正如在圣经的成典史上,随着文字在保存宗教权威文本中作用的凸现,掌握书写技术的文士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一样,在这些少数民族社区,知道如何书写、如何辨认、如何解释文字的传教士以及他们培养出来的教牧人员成为整个社区中的突出群体,他们对于以口传诗歌的念诵为基本操作模式的本土萨满群体构成了巨大威胁。文字取代了口传,社会威权也从传统的萨满群体转移到了基督教的教牧人员的手中,这也成为基督教取代民间本土宗教的一条途径。让我们先来看看本土萨满在前文字的傈僳社会发挥作用的方式。
祭师(傈僳人称为“毕扒”,学术界常称“萨满”)是一些具有特别记忆的人,他们能背诵很多的诗歌。它们既包括民族的历史来源、开天辟地的神话、祖先的故事,也包括某些在特定场合下需要念诵的诗歌。祭师之特殊的本领即在于他能够大段大段地背诵那些歌集,并知道在什么场合下念诵什么样的诗歌,与灵界进行沟通。至于一个祭师传授徒弟的方式,一般是老祭师先对周围的儿童明察暗访,发现谁家的孩子聪明伶俐,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就收他为徒,一个祭师一般只找一个。然后教授他背诵诗歌,这是一个需要持续很多年的训练,这个孩子必须经过非常刻苦的记忆和背诵,有时甚至会有坚持不下去的人,但坚持下来的,在老祭师去世后,一般都会成为远近闻名的新祭师。④
萨满成为社区中的宗教与社会威权,所依凭的是因其突出的记忆能力而形成的史诗诵念能力,通过这一能力,萨满掌控着人们通往“信仰—知识世界”(包括神灵世界、祖先世界、道德知识体系)的道路。因此,口传本土诗歌是萨满“权力”的知识社会学基础。基督教所发明的文字,以及这一书写文字所传递的新的“信仰—知识世界”,却颠覆了萨满所依赖的这一基础。文字使得萨满所特有的记忆能力不再重要,识字成为比记忆更为根本的能力。而在识字能力被普及、经典这一“信仰—知识”载体成为向所有人开放的文本之后,不是念诵者,而是解释者开始成为社会中的新的威权群体,这就是基督教的教牧人员。
与此同时,随着对文字经典的解释而不是口传诗歌的念诵成为宗教活动的中心内容,人们聚集的威权场所也发生了转移。本来,在以口传诗歌为中心的傈僳本土民间宗教的活动中,人们的活动场所是以家室或家室的延伸(如祖先墓地)为中心的,整个村寨并无经常性的公共活动中心。
在傈僳人的家中,人们都会供奉先祖的灵位,一般来说,左边是女位,右边是男位,每逢年节,人们都要祭拜先祖。在新房落成、准备搬家时,人们一般会先请祭师到新屋里做一番法事,念诵一些歌集,以驱除鬼魔,并保佑在新家里可以得福;在人死后,也要请祭师来念一些经,来将祖先的魂灵接引到一棵树上,那棵树就成为那个家族的神树;如果家人有病或是遇灾,人们也会请祭师来到家里,杀一只羊或鸡,请鬼魔离开。⑤
总体而言,虽然傈僳人的宗教形式多种多样,如崇拜自然之物、祖先之灵等,但它们都是围绕着家族之事来进行的,而它们在空间中的发生地也始终是在家室之内,口传诗歌的念诵是以家族为基本单元的仪式表演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文字经典的解释却采用了大众聆听的方式,它需要营建一个公共的活动空间,并且由于基督教所特有的“分别为圣”的观念,进而将这个活动空间神圣化,使之超越于单个的家族之上,成为整个社区的威权中心。有形的教堂开始在大大小小的村庄出现,成为傈僳社区的可见意义实体。以讲解文字经典为核心内容的教堂,成为将整个村寨整合在一起的活动中心。
傈僳人从口传诗歌到文字经典之间的转换不是连续性的,不是“新瓶装旧酒”,即以文字形式对口传诗歌的重新整理,而是“新瓶装新酒”,文字形式所承载的是一个新的经典传统。对傈僳人而言,从口传到文字的转换,亦是宗教生活方式从民间宗教向基督教的转换,因此,民间宗教的普泛性、零散性与基督教的制度化、系统化之间的差异,亦被带入到“口传诗歌”与“文字经典”之间的转换之中。让我们以道德规训的方式为例来说明它们之间这样的差异。在傈僳人的日常生活中,口传诗歌乃以隐晦、寓意的方式对聆听者进行道德教化。
在傈僳人的葬礼上,祭师吟诵整个民族的迁移史,他们经过一个周折又一个周折才来到今天这个地方。为使死人的灵魂能够从这里回到民族的起源地,祭师会将这个迁移史吟唱一遍,并将死人的灵魂一个周折又一个周折地送回到故土。在每一个周折的关节点上,他会将这个人生前的所作所为评价一番,表明这亡灵是一个清洁的灵魂,可被先祖们接纳。同时,祭师还会对亡灵说,“你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坏事,你的后人们都感谢你,他们会记住你,逢年过节也都会来看望你,你就放心地去吧!”⑥
在傈僳人生活史的某些重要时刻,萨满祭师以口传诗歌为素材对当事人进行道德评价。这既是评判当事人,也是对所有在场者的道德教化。这样的道德教化是非制度化的、隐晦的、间或性的、随意的,它对于氏族成员的道德规训是松散而间接的。但是,基督教的道德规训则与此相反,它不仅表现在它的文字经典——《圣经》中有着清楚的、系统的、完整的、囊括生活各个方面的伦理规范,而且表现在它的规训形式上。
傈僳人基督徒每周聚会五次,分别是周三晚上、周六晚上、周日的上午、下午及晚上。在聚会上,主要是唱赞美诗、听教师传道,一般是讲解圣经,以及告诫人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傈僳人教会有一些普遍认可的诫命,它们主要来自圣经上的“十诫”,还有一些针对民族特点的戒律。包括:1.除上帝、耶稣、圣灵之外,不再信仰别神。2.不妄称耶和华之名。3.六日劳碌工作,七日守安息。4.孝敬父母。5.不杀人。6.不偷盗。7.不奸淫。8.不做假见证陷害人。9.不贪恋他人的配偶,也不贪图他人的财物。10.不喝酒。11.不做伪善的人。12.不移动土地界桩。⑦
在傈僳族基督徒聚居区,教会既是一个无形的道德实体,亦是一个有形的组织架构。这个道德实体借助于牧师、长老、教师和教堂长,以及制度化的(institutionalized)、循环式的训诫方式,将社群中的信徒规整到基督教的意义世界之中;反过来,这个有形的组织架构又从基督教的意义世界中获得合法性,并通过神圣的仪式化场景,极大地提升它对社群成员的规训能力,使得傈僳社区紧密地整合在基督教的意义世界之中,更形象地说,就是围绕着文字化的经典——《圣经》建立一个新型的威权体系。
四、新文字、新经典与新的身份意识
在人们的社会属性中,除去阶层、性别等较外在化的属性之外,人们对自己是谁的看法,即所谓“身份意识”,实际上构成了一个虽然难以量化,却更为深刻、全面的“社会人”的基础。而在身份意识这一维度内,文化或传统的因素有着重要的影响。故此,要分析文字与经典对于傈僳人的社会影响,有必要来考察文字经典即《圣经》对于傈僳人身份意识的塑造。它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傈僳人基督徒如何形成他们的身份意识?在他们的身份构建与重建(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中,傈僳本土传统与基督教传统各自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而在这两种身份之间,存不存在所谓“核心身份”(core identity)的问题?《圣经》在他们的身份意识中有什么样的作用?
正如人们所公认:人们怎样讲述过去,就会怎样理解现在,在身份的建构中,对历史或过去的叙述是最重要的渠道之一。对于集体性的族群意识而言,正是依赖于对共同先祖的历史的叙述,才使得人们对于自己是谁形成鲜明的群体意识。当然,这里所说的“历史”,并非就是“事实”(fact),而是事件、意识形态与美学这三重要素的综合。人们有选择地、想象性地对事件进行加工,并以仪式化的方式将这样的历史讲述出来,而族群的每一个人则聆听着这样的讲述,并在仪式活动中将历史拉入到现在,或将现在的人带入到历史,使每一个听讲者都亲身亲历过去的历史。所以,在口传史诗中,“听者”与“讲者”共融于一个场景之中,“过去的”历史成为“当下的”事件。而参与的每一个听众也都认同讲述的历史事件,从而拥有共同的生存经验。因他们所认同的共同历史意识,而成为一个相对同质性的族群。对于前文字与前经典时期的傈僳人而言,由萨满祭师在婚、葬等人生重大事件上的仪式化的史诗念诵,成为傈僳人形成族群意识的重要渠道。
毕扒(即祭师)是特别有学问的人,他们最令人佩服之处是他们能够记住并背诵许多诗歌。这些诗歌有关于创世的神话,也有关于祖先的迁移传说。傈僳人是一个弱小的民族,常被其他民族欺侮,所以只能辗转迁移。在婚礼上,毕扒会讲述先祖的故事,以告诫新婚夫妇要学习先祖,共敬共让;在葬礼上,毕扒会讲述民族迁移的历史,将死者的魂灵交托给先祖,让他回归故土。傈僳人所记得的族源史就是由这些毕扒一代一代口头传下来的。⑧
因此,在前文字的口传时代,傈僳人就是在对祭师所念诵的口传史诗的聆听之中,知道自己族群的先祖的故事,知道自己族群与其他群体的关系史,以此来界定自己的族群身份。
当基督教来到傈僳人的社区之中,出于对傈僳本土宗教的敌视,传教士禁止在婚礼与葬礼上祭师的史诗诵念的表演,称之为“拜鬼”。因此,伴随着文字的《圣经》翻译对口传的历史诗歌的取代这一过程的,不仅是祭师权威的丧失,而且是傈僳人的历史记忆的丧失,以及由此而失去的族群身份的历史维度。事情还不止于此。随着圣经的翻译,以及在教堂里所进行的新的仪式化的圣经解释,取代傈僳人的族群史诗的,是圣经中的“属灵谱系”(spiritual genealogy)。圣经中的“犹太—基督教”道统,进入傈僳人的族群意识之中。
我们(傈僳人基督徒)所敬拜的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是耶稣基督的上帝。我们更熟悉的是圣经上的人物和故事。可能我们原来在未信主之前,有一些祭师会念诵一些关于我们祖宗的事,但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这些东西了。⑨
依附在傈僳人的口语念诵及其礼仪场景上的民族史诗,是本土傈僳人身份意识的重要根基。由于傈僳人从口语到文字的转变过程,亦是两个经典、两个传统的转换,因此,亦是两种身份的转换。圣经中的历史和信仰叙述成为傈僳人的新的基督徒身份的文本基础。
除去历史记忆之外,人们身份之构建的另一主要渠道是节日及与之相关的仪式。所谓节日,乃是在恒常的时间流动中将某段时间分别出来,用某种传统的特定意义为其命名。参与某个节日,常常即意味着认同某种身份。仪式亦如此,它以某种戏剧化的方式来重复某个历史事件,或者模拟某种传统所独具的宇宙观,从而使参与者经历其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对傈僳基督徒社区来说,基督教的文字《圣经》取代本土宗教的口传史诗的过程,亦是《圣经》传统的节日与仪式取代本土传统的节日与仪式的过程。
我们(傈僳人基督徒)过去有很多的节日。春天到了,我们会庆祝一下,并在节日上唱一些相应的曲调,如布谷调或百花调等;有人家盖新房了,唱新房调等。但是,我们信主耶稣后,我们唱的歌是颂赞诗歌,再也不唱那些老调老歌了。节日也就是感恩节、圣诞节,还有民族节日——阔时节。当然,每个礼拜我们都以星期天作为最重要的日子,我们在这一天是绝对不做任何事情的,因为上帝要我们在这一天专门崇拜,不能工作。在星期天,最重要的就是到教堂做礼拜。⑩
以七天为一个循环,并以第一天的星期天作为专门用于崇拜的节日,这是文字化的《圣经》所带来的新的节日传统;而在这一天所从事的新的仪式活动,其核心即在于建立作为仪式参与者的信徒与耶稣基督、上帝之间的关联。因此,这个七日一循环的新节日与新仪式,其直接后果就是一个新身份即基督徒身份的形成。
在对身份构建的探讨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在人们常常具有的多重族群或宗教身份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是紧张(tension)还是融合(syncretism)为主呢?就神学背景而言,成功劝化西南少数民族的传教士多数来自基要派或福音派的神学传统,在神学上主张神与人之间的对立,强调基督信仰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张力,以及惟信基督才得拯救等等。他们强调傈僳人的传统文化是“属世的”、“拜鬼的”,主张“基督之道”与“传统风俗”之间的不相容性。因此,如果说在身份转变的过程中,总能看到人们对旧有身份的“选择性同化”(selective assimilation)以及“选择性保留”(selective preservation)的话,(11)那么,在傈僳人对基督徒身份的重构过程中,可以说,“同化”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而“保留”只局限在有限的服饰、口头的语言等领域。基督教的传入与文字经典的翻译,颠覆了傈僳族群的传统身份,基督徒成为这个群体的压倒性身份,或曰“核心身份”。
五、文字博弈:文字领域内的威权与意义之争
如前所述,从口语到文字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现象,而是综合了诸多社会人类学因素的社会事件。从口语到文字的转换过程中,众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在文字出现之后,它又会影响到社会威权的形成,影响甚至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谁控制了文字,在很大程度上就控制了人们通往社会威权的道路。因此,各种社会力量都会提出自己的文字方案,从而产生“多种文字”(literacies)博弈的现象。
要对这些文字之间的博弈进行研究,社会人类学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第一,不同文字的使用可能会与不同的社会群体结合;第二,不同文字的使用会与不同的场景联系在一起,并运用在社群成员的不同的生活层面之中;第三,不同的文字可能会相互分离,但也可能为某一个与彼此都相关的知识与社会空间而相互竞争。总之,文字的使用是更广泛的社会与文化进程的一部分,它常与不同的社会群体、社会场景(social context)、历史传统结合在一起,是社会群体之间竞争的焦点所在之一。(12)在此,我们将分析在傈僳群体中,不同文字后面隐藏着的不同社会力量,以及它们所运用的不同场景,从而分析文字博弈的社会学意义。
上个世纪初传教士创造拉丁化的文字之前,在怒江的维西县有一个叫做哇忍波的祭师,造出一种象形式的文字,从表面上看来,它与汉字比较接近,但在笔画上却又很不同。他用这套文字记载下了他所能念诵的傈僳歌集,但它太过难学,因此没有流传开来,他死后也就没有人知道怎么用它了。
再接下来,英国来的传教士傅能仁创造了一种拼音文字,用它来翻译《圣经》。一方面由于这种文字的便于学习,另一方面由于基督教在傈僳人中的广泛传播,这种文字成为傈僳人中最为流行的文字。这种文字称为西傈僳文,亦称为圣经傈僳文。
怒江解放后,政府认为传教士所使用的文字既不科学,又与宗教联系在一起,于是在语言学家们的帮助下,以拉丁字母为傈僳人创造了一套新语言,用它来推进政府的各种政治运动,或者普及一些基本的科学知识和致富技术。甚至,还用这种文字印刷了一份报纸,报道在怒江州所发生的大小新闻。这种文字被称为新傈僳文。但是,目前来看,由于傈僳人中的基督徒比例很高,他们习惯于阅读圣经,因此在当地使用率最高、最为人们所认同的文字仍然是圣经傈僳文。基于这样的实际情况,原来用新傈僳文印刷发行的官方报纸也开始用圣经傈僳文印刷发行,受到当地傈僳人的普遍欢迎。(13)
从起源上来说,傈僳语的三种文字有着不同的群体背景,最初的本土傈僳文是由本土的傈僳人发明的,它与汉字的象形文字有着一定的相似,也许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而圣经傈僳文则以大写的拉丁字母为基础,是由西方来的传教士所发明的;再后面的新傈僳文则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创造发明。相对而言,对傈僳人生活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后面两种文字,分别占据他们生活的不同领域。圣经傈僳文是他们宗教生活的语言,是他们的宗教经典的语言,同时从中得到道德知识和训诫;而新傈僳文一度是通往政治权力,以及接近所谓较为先进的科学文化的语言。
因此,在这两种文字之间,是新政治与传统宗教之间的博弈。新政府为在傈僳人中建立权威,推广新的意识形态,发明了一套新的拉丁简化字来取代老式的圣经傈僳文。可以肯定的是,圣经傈僳文全面被拉丁简化新傈僳文取代之时,也就是基督教的权威消失、新的意识形态全面建立之时。但是,恰恰由于圣经傈僳文是傈僳人的宗教经典的语言,是傈僳人的信仰与道德的载体,所以,即使在语言学技术上,新傈僳文也许比圣经傈僳文更完善,又是所谓的科学与“新文化”的载体,但由于它在更深的生命信仰与道德教化层面上意义的缺失,它仍无法在傈僳人的社会生活中赢得权威的身份,成为通用的文字。
在对公共领域——报纸的争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文字之间博弈的结果。本土报纸不再以新傈僳文作为语言载体,而改用圣经傈僳文来印刷发行,以赢得更广泛的受众。另一方面,在对现代世俗生活的报道与解释中,圣经傈僳文也走出了单纯宗教、圣经、礼仪生活的限制,用来描述与解释政治事件、世俗生活方式等。它最终将发展成什么样态,仍需长期关注。
注释:
①这也是许多进入文字前(preliterate)社会传教的福音团体的主张,按Brian V.Street与Niko Besnier的分析,隐藏在这一价值判断后面的,是“西方的、中产阶级的、白人的”意识形态。见Tim Ingold ed.,"Aspects of Literacy",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London:Routledge,2002),p.537。
②关于基督教在西南少数民族中从事的文字创制与圣经翻译的具体历史情况,可参韩军学,《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161~174页;杨学政、邢福增主编:《云南基督教传播及现状调查研究》(香港:建道神学院,2004)。
③Brian V.Street & Niko Besnier,"Aspects of Literacy",p.533.
④据笔者于2003年7月20日,访谈笔记,云南华坪县。
⑤2003年7月22日,访谈笔记,云南华坪县。
⑥2003年7月25日,访谈笔记,云南华坪县。
⑦2002年7月与2003年7月在云南福贡县的访谈笔记。基督教在进入傈僳人社区时,对圣经的十诫做出了有针对性的改变。
⑧2002年7月25日,访谈笔记,云南华坪县。
⑨2002年7月30日,访谈笔记,云南福贡县。
⑩2002年7月30日,访谈笔记,云南福贡县。
(11)在此可参考杨凤岗对美国华人基督徒的分析,见Fenggang Yang,Chinese Christians in America:Conversion,Assimilation,and Adhesive Identities(University Park,P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9)。
(12)Brian V.Street & Niko Besnier,"Aspects of Literacy",p.541.
(13)2002年与2003年7月,访谈笔记与观察,云南福贡县。
标签:圣经论文; 基督教论文; 傈僳族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中国节日论文; 文化论文; 政治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