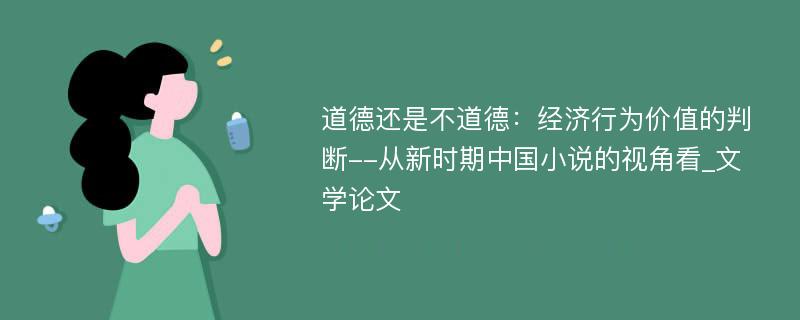
道德的或非道德的:对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从一个角度看中国新时期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论文,新时期论文,角度看论文,中国论文,或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首先声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不是纯粹的“金融文学”作品,如《商界》、《大上海沉没》、《昌晋源票号》等。我们审视的是浸淫着金融意识、描叙了经济行为的那样一些只能被称作“非金融文学”的作品,我们期冀通过对作家灌注其中的价值判断的推拿,透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某些特质。
要审视非金融文学作品的价值观,就不能不将视角伸向新时期之外。因为,价值观作为非凝固的历时的精神现象,其穿透力量,早已构成整个中国文学的脊骨,影响着作家的创作与读者的接受。
中国文学的传统价值观是非常明晰的,这就是以合不合乎“道”作为价值标准,而“道”又是以“道德”作基础的。因之,人们对文学作品总是作道德判断,而不是作审美的或历史的判断。
这显然与中国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有关。经济是基础,一定的经济关系必然与其上层建筑血脉相承。
这更与整个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儒学相关。儒学讲征圣宗经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立德立功立言,讲天地君亲师,不以道德为基垫,又如何能行?
于是,便有了义利之说,有了君子与小人之别云云。
再于是,在文学作品中,商人及其经济行为(尽管是萌芽状、未充分展开状),就是作为道德的负面出现的。除了我们能在《左传》中找到弦高犒师等少数正面例子之外,更多的,商人是以汲汲于利禄之徒、忘恩负义之辈、道德的悖反者之面目出现的,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李甲者流;我们,便也读到了白居易的“商人重利轻别离”、“老大嫁作商人妇”这样带有明显贬抑色彩的诗句——个中意味,已不言自明。
二
中国新时期文学伊始,仍然秉承着传统的道德观念,作一种社会——道德的价值判断。众所周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批判文学”,人们忙着舔弄伤口,批判着文革中各种非道德的行为。改革文学作为改革开放的“传声筒”,为其擂鼓呐喊,虽然其中也涉及到一些经济行为,如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三千万》等,然而严格地说,这些作品中的经济行为仅仅具有“题材意义”。
只有到了新写实小说中,经济因子(以及其后的经济行为)才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简言之,新写实小说经典之作中所描绘的困惑归根结蒂是经济的困惑,譬如《烦恼人生》中印家厚的烦恼(无房、奖金、送礼等)不过是金钱之累;《一地鸡毛》中小林的歉疚与欣喜不是与几毛钱的豆腐、节约几滴水少交丁点儿水费、800元微波炉等捆在一起吗?
经济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从未有过的沉重压抑着人们,燎燃起人们的生存焦灼与精神疲惫。
当代文坛不会忘记两位山东作家及其作品。前者是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它通过老少两代木匠在经济与道德的平衡木上的精神舞蹈,演绎着艰难的抉择过程。发人深省的是,作家最终投向了道德的怀抱。而后者,则是张炜的《秋天的愤怒》[①],其中讲述的是女婿李芒面对大队书记、丈人肖万昌敢不敢为分地、做工说“不”的故事。令人欣慰的是,李芒跨越了政治与道德的樊篱,依仗着经济的力量,与丈人分道扬镳……
今天的我们回过头去看一看这两个中篇,不能不惊异于作家的价值抉择。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同时更是一个必然的抉择。跨过这道经济与道德二元分离的门槛,中国新时期文学伴随着20世纪末叶(90年代)的历史车轮的轰隆声,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种往昔的以道德一统天下的价值判断局面不复出现,那种对经济行为不屑一顾嗤之以鼻的主体意识被作家所进行的重新审视所取代,文学主流,正在超越道德判断的层面。
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作为上层建筑中的一部分的文学作品,其基础便发生了重大变更。存在决定一切,更何况文学尤其是小说,本就是以反映社会现实为己任,紧扣时代的脉搏,应和社会的震荡。因之,作家们面对新的现实生活必然会作出新的价值判断。
有几句王朔式的幽默语言最能概括现实景遇:“有什么不能有病,没什么不能没钱。”又曰:“金钱不能万能,没有金钱万万不能。”举目环睹,红尘滚滚,醉生梦死之徒挥金如土,蝇营狗苟者上窜下跳,出卖色相,撕裂人格,践踏神圣,玩弄尊严等等,几乎一切行为都直接或间接地变成了经济行为。即便文学,不也因为沾染上铜臭而成了“码字”、“操作”式的“集团行为”吗?
与此相应,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印证不了人们的日常行为:道德与经济往往悖反,愿望与现实相向,随之,文学的价值抉择呈多元态势。
第一类作家如梁晓声、张承志、史铁生、张炜、北村者,他们往往以一种心灵的守望者姿态拒绝世俗的入侵,并进而要重整传统道德的律条,进行着现代的风车之斗。以梁晓声为例:梁晓声曾以《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等中短篇小说书写着人类的理想主义壮歌。面对滔天的经济大潮,作家一如既往,以《1993:一个作家的杂感》和由中篇《翟子卿》发展而来的长篇小说《泯灭》以及《浮城》等,继续着作家的道德之旅。《泯灭》把“金钱乃万恶之首”的传统道德律条发挥到了极致:“我”与翟子卿乃世交,然而在金钱的面前不仅彼此地位(作家与商人、精神的富有者与物质的占有者)发生了逆转,“我”自身的心灵与肉体也经受着一次次猛烈的洗礼。而翟子卿,这个孝子,却最终栽在金钱的膝下,断送了母亲与妻子,自己也发疯进了精神病院——这一切难道不是对金钱的有力抨击吗?作家对“我”所进行的心灵拷问,难道不是道德的自我净化?在《泯灭》的扉页,作者题写道:“某些东西已在我们内心里泯灭,并开始死亡,某些东西已从我们内心里滋长,并开始疯狂地膨胀……”是什么在泯灭?良心、道德、正义感等;是什么在膨胀?金钱欲、虚荣心等。该书封面上,漫漫黄沙湮掩着一具只剩下少许头骨的人体。这该是怎样的一种寓意?缠绕着作家的又是怎样的一种情结呢?
《秋天的愤怒》之后,张炜变得更加深沉起来。《古船》中的磨坊、古船、小红马的象征义不言自喻;《柏慧》、《九月寓言》皆寄寓着作家的哲学意蕴,演示着作家对传统与现代的深刻反思。而张承志,重写《金牧场》,用心书写《心灵史》并进而虔诚膜拜起“哲合忍耶”教。这位自称“都市的牧人,无马的骑手,公开的教徒,自由的作家”的现代斗牛士,明知难以回复到道德的原野,仍然放纵精神的缰绳,不屈不挠,“以笔为旗”寻找着“清洁的精神”。在《你选择什么》一文中,作者写道:“在如此时代,我只是倍加珍惜——使我的笔得心应手的中华文明。我没有胜利的乐观,但我打算抵抗。在一篇散文中我写过:文明的战争结束时,失败者的废墟上应当有拼死的知识分子。我讨厌投降。文明战场上知识分子把投降当专业,这使我厌恶至极。”[②]因此,作者“敢应战和更坚决地挑战,敢竖立起我的得心应手的笔,让它变作中国文学的旗。”[③],张承志在这里所痛恶的,正是知识分子向经济(金钱)的投降,他所企望并为之努力的就是要重振道德乾纲,做一面迎风猎猎的精神之旗!
第二类作家乃市场经济的弄潮儿,正如第一类作家寥寥无几一样,此类纯粹的逐新者也为数不多。他们的价值观主要体现在域外题材作品上,如《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娶个外国女人作太太》等。此类作品往往以怀旧的方式,述说着成功后的自得。他们对经济行为的炫耀超越了一切应有的和不应有的规范。事实上,他们作为经济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对经济行为的钟情甚于一切。因之,他们对自身作品所作的当然不会是道德评判,而进行着一种纯然意义上的“历史判断”。
这里有必要引用一下著名评论家赵毅衡为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所写的评论的标题:“拜金文学”。确然如此,对于一个怀揣400美元只身闯荡美利坚的女人来说,不过数年时间即成为富婆经营着上千万美元的进出口贸易的经历,足以令她自豪地写出一部“冗长的、流水帐式的通俗回忆录”。因为,在她看来,“世界是作为一个需要排除的障碍物,一个有着等级差别的贵贱之地,一个有待去占领的窗户,一个等着被攫取的对象而出现的。”[④]面对这样的社会,具有如此的心态,她还会用一种道德的价值观进行评判吗?而小说《娶个外国女人作太太》,其作者纯然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观”来述说着“伪装的个人成功的神话”,进行着“小市民的自我陶醉”[⑤],我们还期望从中获得一种深度感应、一种道德的震撼吗?
第三类作家是新时期文学(更准确地说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中最常见的作家。他们深受传统的儒学教化,周身血液中流动的是传统的质子,因之,道德价值观念根深蒂固。然而,他们作为人类灵魂的发达部分,对身边汹涌着的时代大潮较一般人来说感受得就更为深刻、强烈。他们既不愿轻易放弃传统的道德观念,又无法无视滚滚欲潮:精神的充实无法抗拒物质的贫乏。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所呈现的价值观往往是矛盾的,即:既想坚持传统的道德观念,又不能违背历史的发展规律。于是,“无奈”是这类作品的基本主题,无望的追寻是其最终的结局。
张欣是一位颇有代表性的作家。《绝非偶然》、《首席》、《仅有情爱是不够的》、《岁月无敌》、《如戏》等作品中,都是把生存的焦虑与危机放在了爱情的浪漫与甜蜜之上。虽然两者(生活与爱情)在现实中难以偏颇,然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其结果只好牺牲情爱,在生之焦灼中苟延残喘。近作《爱又如何》中,大学毕业后分到出版局工作并有着一个美满的家的可馨,这个曾在各方面超过同伴爱宛(商场经理)的骄傲女人,赌气辞职后立刻感受到了“爱情的伟大”不敌“生活的重负”;成了自由撰稿人,又被丈夫沈伟斥之“为了八十块钱的汇款单牺牲掉我们多少良宵美意”;住房问题,小孩生病,与公婆的矛盾……这位排骨美人缘于生活的重荷因了经济的困窘以至使情爱也让位了!不仅如此,可馨终于为过去的保姆现在的大腕——菊花倒卖书号前后奔走仅仅为了得取佣金……经济的力量压倒了一切!不过,作家实在不愿她“心爱的人物”“不配有好命运”,于是,在全文的结尾,让可馨发觉丈夫原来并非有了外遇而是一直在外兼做摩托车手赚钱贴补家用,“她下意识地抓住洛兵的手,但是眼里还是迸出了泪花”。而旧日的相好王洛兵在作家的笔下也全然不是乘人之危之徒,相反是位坐怀不乱的君子……但平心而论,这一份“温馨”实在无法改变现实的残酷,只不过在作家的无奈之上添上些有限的亮色而已。于事何裨?真乃爱又如何?
刘继明的小说也是颇具意味的。在被《上海文学》推为“文化关怀小说”的《海底村庄》中,欧阳雨秋教授企图通过诗歌这一形式来复活已经消失的海底村庄(即历史记忆的原型),使之最终进入现代经济异常发达的佴城人的精神生活之中。该中篇表现了一种一往无前的浪漫主义精神,然而,欧阳教授的目的并没实现,反而自身走向了大海,“我”所寻找的仅仅是“传说”(现实之中无法能找到)。另一个著名中篇《前往黄村》,叙写主人公黄毛成了百万富翁,邀请城里的大学同学来做客,客人来后黄毛却又消失了。在其墓前是他的书稿,其上有一行醒目的大字:“我在你们灵魂抵达不到的地方。”——黄毛有钱有名,为什么要去死?显然是作者谋杀了自己的主人公。在作者看来,“金钱”与“灵魂”(道德)是相悖的,黄毛不择手段地发家致富,暴发后对此梦靥解脱不了,因此只好一死了之,寻找灵魂的净土。整个小说扑朔迷离的氛围与“意义层面上的人生迷失”同样引人深思。
古清生的《文学厕所》,把文学与厕所联在一起,马上使人想起弗洛伊德的“文学如同排泻”一语。不管作者如何挖空心思地起名“雅厕”,也不管小说在叙写文人作家的诸般无奈之后终于在结尾源于作者的良好想象让张亦斌设立“雅厕文学奖”,作者对市场经济下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慨叹是一目了然的。其“良好的想象”真的能让作家自信起来吗?赵金禾的《先生耐寒不耐热》中,作家子章逐步接受对门经理楚货的经济援助之时,也就慢慢消融了自身的人格,于是妻子肖雯和情人亚丽便要消失,最终子章只落得“勾腰抱住儿子,泪水长流”;萧平的《小说二题》之《金窑主》中,市作协副主席洪涛为出书只得与暴发户赵福顺联名,总有一种“嗟来之食的感觉”;而此时的池莉在《你以为你是谁》中,让女研究生向小餐馆主陆武桥献身……这些无疑都准确地勾画出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文化人的矛盾与无奈心态,同时从这些描述中也都显示出了作家的价值判断状态——该采用传统道德的还是历史的呢?我们没有得到坚实而明确的答案,尽管在一些小说里作家人为地安上了“光明的尾巴”。
四
恩格斯在引证黑格尔的“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之后,强调:“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尊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这种“恶”,当然包括对金钱的追逐,当人们拥有金钱时,往往也就拥有了权势、自私、愚昧和傲慢;当不拥有金钱时,人们又不可避免地为之进行着疯狂的追逐、不切实际的企望和不择手段的攫取。“度”的把握是极其艰难的。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接着说:“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下来就有的,因而应当成为一切道德的基础。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受到双重的矫正:第一,受到我们的行为的自然后果的矫正:酒醉之后,必定头痛;放荡成习,必生疾病。第二,受到我们的行为的社会后果的矫正:要是我们不尊重他人追求幸福的同样的欲望,那么,他们就会反抗,妨碍我们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由此可见,我们要满足我们的这种欲望,就必须能够正确地估量我们行为的后果,同时还必须承认他人的相应的欲望的平等权利。”[⑥]
在这里,恩格斯就人类追求“幸福”的欲望作了非常精辟的评说。首先,恩格斯以辩证的、历史的眼光承认“恶”欲——当然包括金钱占有欲——是历史发展的杠杆。因之,我们的作家在描写人类的经济行为时应当以一种历史的发展的眼光而不是纯粹的道德标准去评判之,也即承认这种经济行为的合理性、必然性。然而,恩格斯对“恶”欲的限制也是颇富启迪的(却又往往为人所不引用),恩格斯强调必须正视这个“道德的基础”所导致的“自然后果”和“他人的相应的欲望的平等权利”,也即要以一种道德的衡器称量人们的经济行为。综合之,正确的价值观应是既非单纯的、固有的道德评判,亦非一味逐新的、肤浅的历史评判,而应采取一种“历史——道德”的价值标准!
我们认为,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对“恶”(含经济行为)到底采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去审视,决不只是某种姿态与风度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历史与传统、精神与物质等多种关系的哲学思考问题。沿用传统载道式的单纯的道德观作道德文章,只会是对现实主义的深入描写原则的有意违悖,有掩耳闭盗之嫌,这种做法并不可取;而一味地用所谓的“现代”的眼光去光大这种“恶”,并进而不加批判地讴歌,追新逐潮,廉价献媚,充其量不过是拜金主义的显现而已。如何既正视历史的必然进步,又审慎地面对这种进步所挟带的必然赘疣,即要把这种“恶”的后果、“恶”的本质表露出来,从而在文学作品中歌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平竞争,歌颂遵守市场竞争法则的经济行为,塑造新的道德人格,这将是一项急迫的任务!刘醒龙的《村支书》中,村长倒卖茶叶发财,反而笼络了民心;支书方建国这个“无用的好人”,却不会搞脱贫致富!刘醒龙一方面对支书的“无用”进行了毫不掩饰的叙写,但在道德层面上仍让方建国以身填塞涵洞,生发出崇高,从而也使小说获得了永恒的价值。倘若只是一味地叙写方支书的懦弱滞后和文村长的精明投机,必然不能获得如此效果;倘若无视文村长等人发财欲望的必然性,只着眼于支书的“崇高”,那么,在真实性上就会大打折扣——由此可见,只有用一种历史——道德的价值标准审视现实及其经济行为,我们才会作出既合乎历史规律又合乎社会法则的判断!
注释:
①《当代》1985年第4期。
②《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1期。
③《以笔为旗》,《十月》1993年第3期。
④《缺席的批判》,《上海文化艺术报》1992年10月2日。
⑤《移民文学的歧途》,《中国青年报》1993年6月18日。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IV卷第233、234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1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