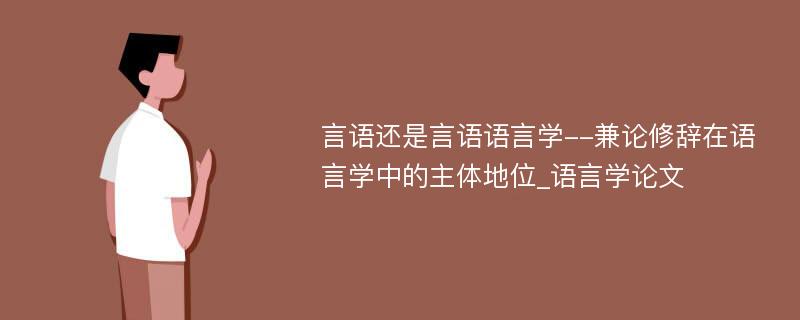
言语学还是言语的语言学——兼论修辞学在语言学中的主体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言语论文,修辞学论文,语言学论文,主体论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学术界,言语学的名称好像是越来越响了。2002年由武汉大学和国家语言研究所联合主办、三峡大学和湖北师范学院协办的“言语与言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言语是和语言相对应的,语言学是关于语言的学问;自然,言语学就应该是关于言语的学问。言语学提法在中国倒也出现得挺早,1930年王古鲁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书就叫《言语学通论》;1931年沈步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叫言语学概论。其实他们的言语学与现在我们提到的言语学并非同等的概念。现代的言语学的概念从什么时候叫起来的,我们无可查考,我们只知道对语言和言语进行最全面论述的是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但是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却没有言语学,只有言语的语言学(我国普通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的方光涛教授也坚决反对言语学的提法)。为什么索氏不直接说言语学,而说言语的语言学?我们觉得必要对言语学和言语的语言学两个概念做些分析。
一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明确区分了语言和言语。他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1](P37)。关于言语,索绪尔异乎寻常地强调了两次:1.“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其中包括:(1)以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组合;(2)实现这些组合所必需的同样是与意志有关的发音行为。”[1](P42)2.“言语是个人的行为,其中应该区别开:(1)说话者赖以运用语言规则表达他的个人思想的组合;(2)使他有可能把这些组合表露出来的心理、物理机构。”[1](P35)正因为如此,我们一贯坚持言语具有两方面,即说(写)和所说(所写),反对有人把所说(所写)从言语概念中剔除出去。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术语单一性的问题,而是涉及语言学基本矛盾的问题。也涉及言语的语言学的开拓问题。[2]
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关系,索绪尔说:“毫无疑问,这两个对象是紧密相连而且互为前提的:要言语为人所理解,并产生它的一切效果,必须有语言;但是要使语言能够建立,也必须有言语。从历史上看,言语的事实总是在前的。”[1](P41)语言系统是从言语实际中提炼出来的,每个人的言语事实又离不开语言系统,它们是互为前提的。从历史上看,言语是第一性的,语言是第二性的,先有言语,后有语言。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社会的,言语是个人的,具体的。索绪尔强调言语是纯个人的说法是应该商榷的。因为言语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言语其实也是有规律的,它必须按照语言规则去进行。
区分了语言和言语,索绪尔又提出了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他提出“两条路不能同时走,我们必须有所选择;它们应该分开走”[1](P42)。他的学生《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编纂者说,“他曾向第三度讲课的听课者许过愿。这方面的研究在以后的讲课中无疑会有一个光荣的地位”,但是“诺言也没有能够实现”[1](P14)。我们认为,语言的语言学是一种关于工具(即符号系统)及工具内部的相对静态的语言学;言语的语言学则是一种人在不同语境中运用工具的过程及结果的相对动态的关于语言的语言学。我们认为,应该好好考虑的是:言语的语言学的“言语”在索氏“言语活动”、“语言”和“言语”三个概念里,到底是指“言语活动”还是指“言语”?这一问题已经在岑运强的两篇论文《言语的语言学之由来、实质及意义》和《言语的语言学的界定、内容及研究的方法》里得到初步解决。岑运强认为可以有以下两种处理方法,即:1.言语的语言学是指“言语”,这种理解似乎比较符合逻辑,因为言语活动既然再可分为语言和言语,那么语言的语言学就应该指语言,言语的语言学就应该指言语。但我们认为,这里的“言语”应该改造为不但具有社会因素,而且具有个人因素,因为言语既然是说和所说,就不可能“在言语中没有任何东西是集体的”[1](P42)。实际上每个人在说的行为时不可能离开语言这个工具,每个人的所说也必然包含语言的要素。2.言语的语言学指“言语活动”,这种理解比较符合书中的事实,即索氏一再强调的,言语活动是异质的,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同时跨着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它还属于个人的领域和社会的领域”[1](P30)。但也应强调这种活动包括行为与结果两方面。相比之下,似乎第2种说法更符合索绪尔原意。
尽管索绪尔强调言语的个人性,但他许诺要建立的是“言语的语言学”却从没有说过建立“言语学”。他有一句非常值得重视的话:“说话者的活动应该在许多学科中研究,这些学科只有跟语言有关,才能在语言学中占一席之地。”[1](P41)如果用他的观点看,个人的言语只能是纯个人的行为和结果,它可以在许多学科中研究,但如果与语言无关则在语言学中毫无意义。所以在索绪尔的学说里,言语学是不能成立的,成立的只能是言语的语言学。
言语是说(也可以扩大到写)和所说(也可以扩大到所写),几乎所有的学科都存在言语的问题。政治学研究政治言语,文艺学研究文学言语(包括作家的言语和作品的言语),历史学研究文献中的言语,数学、物理等等都研究言语。但是,如果谁说这些都是广义的语言学,恐怕没有人会同意。因为政治学是透过言语看政治,历史学是通过言语研究历史,文艺学是通过言语的研究探求文艺创作的规律,他们都不是以语言的研究为目的。所以,言语学如果不经过严格的界定,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凡是用语言描述的学科,无例外,都是“言语学”。所以,知道了这一点,再回头看索绪尔的话:“这些学科只有跟语言有关,才能在语言学中占一席之地。”是不是觉出了他的伟大?
研究必有研究材料和目标,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是以言语为研究的材料的,而目标当然不可能一样,否则就不能说是不同的学科。根据索绪尔的观点,语言学可以分为两种: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静态的语言的语言学是以言语中不断被运用的句子以下的单位为自己研究的材料,它的研究目标是语言的系统这个工具;而动态的言语的语言学以句子以上的单位为材料,研究的目标是人运用语言工具的过程与结果的规律。在索绪尔看来,言语的语言学不但可以成立,而且在他将来讲课中无疑将占有一个光荣地位。
有人也许会说,言语学还是言语的语言学,叫什么有什么所谓呢?知道是那么回事就行了。其实,名称问题不独是名称的问题,它关涉到人们对概念的理解。古人说,名正言顺,名既不正,学科的建设也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第一,如果叫言语学,人们很容易把语言学的领地无限制的扩大,从而造成这也语言学那也语言学的问题(如上面说的政治学、文艺学、历史学、物理学都表示语言学)。索绪尔在《教程》中有这么一句话,“我们无论从哪一方面去着手解决问题,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语言学的完整对象;处处都会碰到这样一种进退两难的窘境:要么只执着于每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冒着看不见上述二重性(指语言和言语——笔者注)的危险;要么同时从几方面去研究言语活动,这样语言学的对象就像乱七八糟的一堆离奇古怪、彼此毫无联系的东西”[1](P29)。所以,“要解决这一切困难只有一个办法:一开始就站在语言的阵地上,把它当作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表现的准则”[1](P29)。后来的事实证明,索绪尔的话是正确的。结构主义,转换生成语法在语言的语言学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语言学成为能与自然科学比美的领先的学科。语言的语言学是语言学中永恒的话题。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永远只能在语言的语言学打转转,而应该大胆跨入言语的语言学无比宽广的领域。言语的语言学应该与语言的语言学同样重要。今天的语言学并不是像一些人所说,是“非索绪尔时代”,或“片面的索绪尔时代”或“部分的索绪尔时代”!而是“全面的、准确的索绪尔时代”[2]。所谓全面、准确就是既要正确处理好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又要正确处理好语言学内部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不是言语学)的关系,以及语言学内部各种语言学的关系。
第二,叫言语学不利于科学的学科分工。语言学的发展真的是很有意思。传统的语言学,是诠释经典的,重视意义,以应用为目的,但不是独立的语言学,偏激者说它是经学的附庸,处于婢女的地位。历史比较语言学用比较的方法,重视语言的历时研究,已是为语言而语言了,语言学总算是独立了。但不管是语文学还是历史比较语言学,都不区分语言和言语,只有到了索绪尔,到了以索绪尔的符号学说为基础的结构主义,才把语言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唯一对象,从而使注重形式描写的结构主义盛极一时。极端的结构主义不重视意义,而和结构主义一脉相承的转换生成语法,更是把语言学等同于数学,把形式主义推向了极端。但盛极之后,极端之后,势必走向反动。这不,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交叉语言学的出现,就一反结构主义传统,一改只重语言不重言语,只重形式不重意义的“弊病”,重语言更重言语,重形式更重意义了。语言学的历史由言语为主,到语言为主,再到言语为主,或语言言语并重。波浪式的前进、螺旋式的上升。应该看到,无论是以语言为主,还是以言语为主都是语言学,我们只能叫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而不能叫语言学和言语学。叫言语学就把自己排除在语言学科之外了,这是不利于学科的分工与联系的。
所以,明确区分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是十分重要的。如果笼统地把言语的语言学称为言语学,我们觉得给人造成的误解是巨大的。反之,如果称为言语的语言学,强调了和语言学有关,则向人们表明了这是以言语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而不是别的什么学问。现在看来索绪尔从来不说言语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方光涛坚决反对言语学提法也是完全正确的。
二
提到言语学还是言语的语言学,不能不说起语用学。语用学诞生的原因是由于传统语义学的困窘,是由于传统语义学不能解决生活中语言运用中的意义问题。所以,它是对传统语义学的一种补充。利奇 (Leech)在他的《语义学》中认为:“从最普遍的意义上来说,语用学研究语言符号及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使用这一术语一般意味着要区别对待语言本身,即抽象的语言能力跟说话人及听话人对抽象的语言能力的运用。因此,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区别大体上就是意义和用法之间的区别,或更一般地说,就是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之间的区别。”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语用学就是言语的语义学,而言语的语义学属于言语的语言学。
提到言语学还是言语的语言学,也不能不说起修辞学。在我国,修辞学一直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很多人把它排除在语言学的主流研究之外,甚至很多人并不把修辞学作为语言学的一部分看待。“从期刊方面看,……国内有影响的‘汉语研究’期刊有十多种,修辞学届向其投稿率接近零,专业修辞刊物只有《修辞学习》一种……;项目方面,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中,修辞学的申项率几乎为零;教材建设方面,在‘十五’国家级规划新编教材‘指定选题’涉及汉语的目录中没有修辞学,与其他子学科相比,修辞学教学内容改变最少,其教学体系和学科前沿的距离日益拉大;价值导向方面,同样是以一代语言大师名字命名的奖项,对陈望道修辞学奖作出反应的,仅《修辞学习》。”(谭学纯,2004)所以,刘大为说:“当命运之光没有光顾修辞学的时候,任凭修辞学者们作出了怎样的努力和探索,修辞学仍然摆脱不了它依附性的和非主流的地位。”[3]
其实很多问题并非“命运”所致,之所以形成那样的局面,我们觉得其原因大致有三:
第一,修辞学的非主流也是由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决定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在语言学史上发生了巨大的影响。索氏的初衷也许是为了明确语言学不同的研究领域,但在其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语言和言语的区分被认为是明确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索的学生总结的(注意,并非索说)“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教程几乎全部都是在讲语言的语言学问题,而索绪尔的强大影响也使得语言学顺着语言的语言学的方向大踏步地前进,语言学家无暇顾及或者就是根本不屑于言语的语言学的研究,从而把言语排除在语言学的研究之外。于是本该是两条腿走路的语言学,变成了一条腿,变成了“瘸腿”的语言学,语言学成了语言的语言学的同义语。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之下,实际上是以言语(其实很多时候是言语的一部分)为研究对象的修辞学的不被重视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甚至连修辞是否语言学研究都有怀疑,更别说有主流的地位。
第二,是因为对修辞学的学科界定。对修辞学的学科界定,长期以来有这么一种几乎公认的说法,认为它是“边缘性学科”。“修辞学是边缘性学科”,最早是陈望道在60年代提出的。陈氏指出:“修辞学是介乎语言学和文学之间的一门学科,要研究它,需要做许多准备。”又说:“修辞学介于语言、文学之间。它与许多学科关系密切,它是一门边缘学科。正如生物物理、生物化学、数学物理等边缘学科一样,研究时要先学生物,再学物理或化学、数学;研究修辞也要具备多门学科的知识。”80年代后,张志公、宗廷虎等人也操此说,并有所发展。宗廷虎在《边缘学科的特殊理论修养》中对陈说作了进一步阐发,明确指出:修辞学这门介多种学科之间的边缘性学科,必须从许多邻近学科吸取理论营养,才能壮大起来。后来,宗廷虎又在其《修辞新论》中对这个问题进行论述。张志公在《修辞学论文集》前言中明确指出:“修辞学是研究语言艺术的一门科学,是一门边缘学科;从应用的角度上说,它又同语言运用、信息传递、文艺创作、语文教学等息息相关,因而在研究中应注意它的多学科性的特点。”(参见《中国修辞学史当代卷》第109-110页)我们认为“边缘学科”的提法不如“交叉学科”的提法好。“边缘”意味两个意思:1.远离中心;2.靠近其他边界。而“交叉”则既能进入其他学科,又没有远离中心。特别是科学家公认当今是“交叉科学”的时代,作为“交叉科学”的分支——“交叉语言学”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可以说从一开始,修辞学的研究者就把自己所从事的研究边缘化了,既然是介于语言和文学之间,自然就不是正宗的语言学了,而按张志公的看法,修辞学其实并不是语言学了,不是说“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讲,它同……语言学……有着……联系”吗?强调修辞学应该从各种学科汲取营养无疑是对的,但是,在交叉科学渐渐成为主流科学的今天,我们不但要反复强调它的边缘性,我们更应该强调它的交叉性和主流性。正如伍铁平所论及过:国外现代认知语言学的兴起,将修辞学作为领先科学,用隐喻等修辞手法解释很多语言现象,包括语法。修辞学不仅在西方语言学中有跃居首位的趋势,即使在我国美学界也有此趋势。[4]异质性与动态性,这正是言语的语言学本质特征。重视言语的语言学是完全符合由静态转向动态,由结构转向过程的科学发展趋势的。言语的语言学与语言的语言学应该是互为双脚,互为双轮的关系。[5]作为主流科学——交叉科学的分支,交叉语言学正以飒爽的英姿大踏步走上舞台,其中修辞学就可充当其中的先锋。
第三,中国修辞学的“依附与非主流的地位”其实也与它一直遵循的研究范式有关系。胡范铸最近发文指出:“20世纪的中国修辞学,从辞格研究起步,直到同义结构的讨论,其中自有种种变化,但在总体上,遵循的还是同一个基本范式,这就是:语言的艺术化的技巧及选择。”“所谓‘语言的艺术化的技巧及选择’这一命题本身预设:其一:我们的语言行为是可以分为两类的:有‘修辞’的语言和没有‘修辞’的语言,亦即可以分为‘艺术化’的语言和‘非艺术化’的语言。其二,修辞是一种‘装潢’,并不是建筑本身。”所以,“根据这一范式,修辞学界在中国语言学界越来越边缘化。‘本体’是不可或缺的,‘装潢’则不一定是必需的,面对语言本体的研究,修辞学似乎也就不得不接受‘边缘化’的境遇。”正是这样的研究范式限制了中国修辞学的发展。[6]
正因为修辞学是一种“装潢”,所以,和“建筑本身”比如“建筑规则”的语法学相比,地位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修辞与语法本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语法是语言的(当然,不排除语法中的组合关系具有言语的性质),修辞是言语的(同样,不排除修辞中的某些模式也具有语言的性质),大体说来,语法学属于语言的语言学,修辞学属于言语的语言学。应当特别指出,索绪尔早就把修辞学纳入言语的语言学。1912年,索绪尔曾向日内瓦大学递交了一份关于成立修辞学教研室的报告,报告说:“语言学研究的领域是十分宽广的,其研究领域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接近语言,是消极的储备;另一部分接近言语,是积极的能量。言语是随后逐渐渗透到言语活动另一部分中去的那些现象的真正源泉。(一个系里有)两个教研室完全不是多余的。”[7]
所以,把修辞学纳入言语的语言学,符合索绪尔的精神,其实也合乎学理的逻辑。修辞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是言语的语言学,它研究的是言语活动的一方面——言语。它其实并不是什么“装潢”,它就是主体语言学的一部分。它当然和文学有关系,文学言语是修辞学研究的对象之一。
三
关于语法和修辞的关系,有过所谓的语法修辞结合论,其实,今天看来,这就叫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相结合。因为语法修辞本来就是不可分的,即结合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正如语言和言语,本不可截然分开。修辞应该是合乎语法的,而语法的表现有时正是通过语言的运用即修辞。
语法修辞是否结合还曾经引起很大的争论。其实我们觉得,讨论大多不在点上。同意者,极力证明应该结合、能够结合,其实没有看到问题并不是什么应该不应该、能够不能够的问题,结合本是事实的存在着。而反对论者是极力论证它们的不同层面,不同层面当然是不能结合,但是不同层面,其实也并不是不能结合,看出了问题,但是得出的结论不对。
语法修辞不可分割,语法学和修辞学是有联系却也不同的两种学问,或说同属于语言学,但属于不同的次范畴。有联系,当然就是结合的,不需要讨论。其实语法研究应该有修辞学的视角。语言从言语中来,语法研究如果缺乏语言和言语的观念,分析难免不到家,解释难免有疏漏。下谈一例:
比如对“吃大碗”、“吃食堂”、“洗凉水”等的语法分析。“大碗”、“食堂”、“凉水”当然是做动词的宾语,而按一般的说法,大碗、凉水是指动作、行为凭借的工具,有人用转换的方式说吃大碗就等于说“用大碗吃”,洗凉水就等于说“用凉水洗”;食堂是指处所,就等于说“在食堂吃饭”。解释当然有自己的道理,但是我们觉得未必符合语言事实。
我们知道,借代不独是一种修辞方式,它还是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小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用借代来思维了。看到小狗,小孩子会说“汪汪来了”,看见猫,会说“喵喵来了”,其实是用叫声代事物。想吃糖,小孩子往往会说,“我吃甜甜”,其实是用事物的特点“甜”来代事物“糖”。知道这个,如果我们再看上举几例,我们就应该知道,其实上几例的分析大可不必简单问题复杂化。“大碗”、“食堂”、“凉水”做宾语是真,但是和“洗衣服”、“杀鸡”一样,宾语是动词所指的动作或行为的对象。“大碗”其实就是指“大碗的饭 (或面条等)”,是工具代本体;食堂就是指“食堂的饭”,处所代本体;凉水就是指“凉水澡”,工具代本体。无他,借代而已。
上说的问题是语法的还是修辞的?应该说既是语法的,也是修辞的,是结合的,而不是分裂的。借代是修辞的,尽管随时间流逝,积极效果渐失。动词加宾语的分析是语法的。语法的是语言的,而修辞的是言语的。语法学属于语言的语言学;修辞学则属于言语的语言学。两者有时需分开,有时又需结合。
结论
在不经意间,言语的语言学已经成为语言学的“热门”,尽管很多并不是以言语的语言学的名义,不是在言语的语言学的旗号之下。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如果是合理的,那么,有了语言的语言学,就相应的,也应该有言语的语言学。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平常说的语言学是语言的语言学的简缩,这时如果有人说言语学,而不做严格的界定,术语就缺乏系统性。既然有语言的语言学,言语的语言学在哪里呢?所以,我们并不是反对言语学的术语,我们觉得如果非得称为言语学,也没有什么不可。但是,必须经过的界定,就是说,言语学就是言语的语言学,是言语的语言学的简缩。
是言语学还是言语的语言学,表面上看,是单纯的名称问题。但是,问题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名称不同,其实关涉着对同个问题的不同理解,而不同的理解,有时就是对与错的问题。索绪尔是伟大的,现代人研究语言学往往还离不开他,正如王希杰先生所说:“索绪尔和索绪尔学说是很值得认真研究的,索绪尔和他的学说,不仅在二十世纪是不可忽视的,而且在二十一世纪里,也应该高度重视。新世纪的中国语言学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学术繁荣还是绕不开索绪尔和他的学说的。”[8]但是,现在的人们对他的误读实在太深,比如任意性与理据性相似性问题,也比如语言和言语问题——我们真应该结合时代的要求,认真研读索绪尔的书。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应该言必称索绪尔,但是对于他说得对的,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地继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