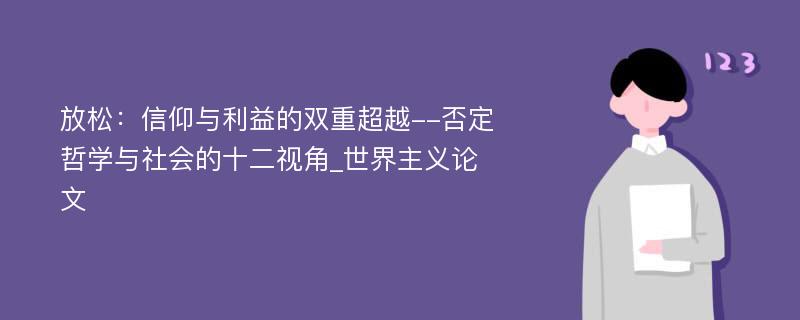
放松:对克利和逐利的双重超越——否定主义哲学社会透视之十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透视论文,主义哲学论文,克利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放松”的基本哲学内涵
在否定主义哲学中,所有“本体性否定”的“对象”,都属于“生存世界”。“生存世界”是以循环、延续、本能性和非人为性为其特点的,并渗透在人的自然性生存和文化性生存这两种类型和模式中。人类在“生存世界”的基本生活准则,便是“放松”,而不是用各种“应该”的语言,制造各种非自然性的生活。或者说,“放松”就是当代性的生存道德之体现。
在自然性生存世界中,“放松”首先具有“顺其自然”的意思,并要求着人类的自然性生活,像自然万象那样呈现出千姿百态的、丰富的天然可能性。当自然界既有风暴般的“冲突”、也有湖泊般的“宁静”,既有水往低处流的“朴拙”、也有鸟往高处飞的“激昂”,既有动物族类相残的“冷酷”、也有母子之间爱抚的“温暖”,既有“猴子称霸王”的不平等、也有私有制出现之前的原始“平等”的时候,“顺其自然”就包涵着由上述各种可能性引导的、使人类的生活显示出复杂性、有机性、不应该由任何人为性去制约的意思,并反衬出迄今为止中西方各种“自然观”的“人为性局限”。这意味着,“放松”对“顺其自然”的理解,已经既不等同于道家哲学的“简朴”,也不等同于儒家哲学的血缘性“亲和”;既不等同于卢梭意义上的“平等、无奴役”的自然观,也不等同于张炜笔下的由“小草和柔弱的动物”组成的自然世界——因为这些“自然观”,均是用一种各取所需的态度、对“自然”的“某一方面”的理解,而不是用放松的、宽容的态度去拥抱自然界的全部可能性。其结果,也就破坏了自然的丰富性,“不放松”地对待了自然。比如,人群像群落一样,既有柔弱的人,也有强健的人,而柔弱或强健的人也各自有柔弱和强健的一面,柔弱和强健也都有其可爱的资质,或在某些时候能转化为审美符号,“柔克刚”或“刚克柔”的现象也无时不在发生。顺其自然地对待、认同这一切,就是合理的、健康的。当我们既不能像道家文化那样推崇“柔弱”,贬低“强健”,也不能像西方进化论那样,推崇“强健”,贬低“柔弱”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说:人类的“霸权现象”和似乎成立的“落后现象”,其实都是人类破坏自然、以人为性的、不完整的自然性标准来衡量世界的结果。虽然这些标准都是对自然界某一方面内容的提取,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不自然”,但由于“自然”并不等于“某一种自然”,“自然”就是在许多种事物、多种形态之间自由地穿行的意思,那么我们就不好说崇尚“强健”是掌握自然的精髓,也不好说肯定“柔弱”才是掌握自然的精髓。因此,当古谚说“老虎吃鸡,鸡吃虫,虫吃棍子,棍子打老虎”时,一方面阐述的是循环论的道理,另一方面则说明:任何事物都是在“强健—柔弱”之间运行生存的。不仅推崇“优胜劣败”是肤浅的,而且推崇“以柔克刚”同样是肤浅的。“放松”地生活其间,就是说该柔则柔,该刚则刚,什么时候该什么时候不该,全凭自己的生存感受,而不是凭“应该”的意识。
以此类推,当我们说“放松”地对待自己的“欲望”的时候,就是说“欲望”在根本上说来,也像自然界万事万物那样丰富的、无序的。欲望之间并无价值的差异,也没有一个此欲望好、彼欲望不好的道德性划分。一个人喜欢这种欲望的满足,另一个人喜欢另一种欲望的满足,还有一个人喜欢多种欲望的满足,本质上都是无可厚非的。因此,说一个人或好吃、或好穿、或好玩、或好色,或什么都好,其实也都不应该是贬义词,而是“趣味无争辩”意义上的“自然而然的事情”。当我们说一个人“好吃懒做”,其实也不是指其人不应该“好吃懒做”,而是指不能成天“好吃懒做”,不能总是“好吃懒做”,总还应该有点其它欲望,或做一点超越欲望的事。但“应该做点其它什么”,并不是建立在对“好吃懒做”的“克服”和“鄙视”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生的丰富性、或人生必须还应该有另一个世界的基础上,属于与“存在”相关的问题。这样,将“克服”“好吃懒做”改变为“不满足”“好吃懒做”,便成为“本体性否定”的基本规范。这个规范,便是对“好吃懒做”的宽容。就人的生存世界和欲望世界来说,每个人在求舒服的意义上都是喜欢“懒做”的,也都是喜欢吃或吃好的的,因此这根本不应该牵涉到人格问题。甚至可以说,人类的求发展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便是“好吃懒做”驱使的。在文化的意义上,由于人类自己的创造成果(好吃生食因为火的发明而改为吃熟食,一般的熟食又因为菜谱的发现而改为美食)堆积如山,“放松”就不仅意味着要满足人吃饱的欲望,而且还应满足人进一步吃好的欲望,在吃好的前提下,还应该满足人不断变化吃的花样的欲望……如此一来,人的文化生活才能呈现自然界丰富的形态。因为各种文化“果实”摆在那里,就如自然界各种“果树”生长在那里一样,我们怎能禁止动物们去采摘呢?传统哲学将此解释为人的贪婪而赋予贬意,道家哲学要人过得“简朴”来制止欲望的生长,但在“本体性否定”中,它们因为赋予“放松”的含义而具有健康的意味。“顺其自然”的本义即在此。在这一点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物质文明的过程,便是人的欲望不断延伸的过程,本身不应该用存在主义哲学进行指责,也不应该用传统道德进行指责,更应该与利益追逐和沉湎欲望区别开来。这意思是说,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羡慕开汽车的人,这种欲望是正常的,也是健康的;但是一个人如果成天想着的就是怎么弄到汽车,弄到汽车后成天把玩汽车,这就是追逐和沉湎。这就导致为一种事物所累而没有“放松”自己。因此“放松”在价值观上,就是不排斥对任何一种事物的体验,也不受任何事物所累的意思,“放松”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动态的、欲望逐步递进的过程。它听凭身心感受的驱使,它的无目的性便成之为丰富性,它的无所驻留性便成之为健康性。至于现代人的心灵和精神空虚问题,并不直接由人不断满足自己的利益和欲望而导致,而是由于人们还停留在传统的、中心化的价值依托方式上而导致。由于欲望满足和不满足的人,都会有心灵空虚的问题(大款和下岗工人都有一个当代性心灵空虚之问题),这就使得心灵空虚问题,与欲望实现的程度相比,几乎是两回事——当心灵问题只能由心灵去解决的时候,“物质发达,精神必然衰落”,便成为无稽之谈。
这意味着:只要一个人不妨碍和伤害他人,在欲望世界中想做什么,其实都是可以的,即便他只想“好吃懒做”。但“不妨碍和伤害他人”,并不是对“欲望”的规定,而是“欲望”活动的“边界”。因此,“放松”不是随心所欲的代名词,尤其不是在随心所欲的藉口下“胡作非为”的代名词。由于欲望世界是无序的,所以欲望世界的相互冲突在所难免,这样,我们就要给人的欲望实现制造一个“边界”。我们之所以要给人的欲望设定“边界”,首先是因为大自然也有它的“边界”:如鱼类只能在水里存活,水稻难以在北方生长,所有的动植物目前只能在地球上繁衍、生息,以此类推,太阳系、银河系也会有它的边界,否则我们不会称之为“太阳系”、“银河系”……这种生物生存的“边界”,在人类生活中就体现为“法律”和“国家”。“法律”和“国家”就是人在自由地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时不可逾越的“边界”。而在“法律”保护的范围内,一个人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一个人真正的返朴归真的自然性生活,也是体现自然界之丰富性的“放松”性的生活。同样,一个人只要不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一个人即便成天都想着一些所谓低级趣味的事情,也不应该受到人们的鄙视、监督和指责。其次,法律和国家作为“边界”的诞生,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动物是相残的而又是自身无力管束的),这种区别是因为人就是“本体性否定”自然界的结果。地球既然有不同于动物的“动物”(人)产生,那就是因为人除了有和动物类似的边界,还应该有不同于动物界的边界,那就是人自觉地诞生一种“边界”——法律,便是人类为更好地、放松地、像自然界的事物那样生存,又能防止自然的无序性、相残性,而被人类设计出来的。在人类历史上,道德和法律是人类的两种创造。但道德在制约人的相残性(尽管很无力)的时候,也克制了人的基本欲望(似乎很有力),所以比较起来,不规定人应该干什么,而规定人不能冒犯、欺骗、伤害他人的“边界”,便更适合现代人的生存之道。这就是“正义论”对现代人来说优于“良知论”的地方。此外,像“公平竞争”、“买卖公平”原则等,也都是由法律这个大的边界而造成的各种小“边界”。因此,由法律所构成的人类生活很近似“野生动物园”——“野生动物园”有一个“边界”,这是为了不使之伤害人类,而各大城市现在设制的小型“野生动物园”(一种动物一个边界),除了这个目的之外,还有为了减少动物的互相伤害的功能。但在“边界”以内,动物则享有自由自在体验自然界之放松性、丰富性的功能。
二、人为性对“放松”世界的各种侵犯
首先值得说明的是:“放松”不是奥修所说的“静心”,也不是气功所说的“无杂念”——这些通过人为的努力及其练功所达到的无日常欲望的境界,皆不是“放松”,而属于人为性“忘欲”的范围。或者说,“放松”在根本上就是反人为性努力(道德性努力和身心努力)、也反对通过人为性努力离开现实欲望世界的意思。因此,当奥修批判迄今为止的人类文化是轻视欲望(如“性”),从而导致人们对欲望的迷恋和性的渴望心理时,奥修确实涉及到人对欲望、裸体和性的恐惧式的“人为性”和迷恋、追逐式的“人为性”这两种不健康的态度(所谓“反对把性教给小孩只会引起他们注意到它的存在”),但是当奥修主张在“性”之外“开创出一个新的管道”(即“静心”)时,当这个“新的管道”是指每天静默一个小时以达到安静、详和,是指通过普遍的爱意来转化人们对性的注意时,奥修就是还没有教会人们如何正面地、放松地对待性,奥修就是在承认人们压抑性进而也放纵性这种扭曲状态的合理性,奥修就是在用“回避”的方式、“转化”的方式遮没了“放松”的方式。一旦人们不能做到“静默”一小时,一旦爱的建筑倒塌、爱的教义失去听众,人们就还会沉湎于欲望或性:于是矫枉过正,人们就还是会或轻视性和欲望、或压抑性和欲望,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欲望和性的问题。
比较起来,以儒家伦理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道德,则典型地体现出人类对自己的欲望世界的轻视和钳制的态度(西方的古典主义也不例外)。虽然在先秦儒学中,孔子所说的“见利思义”并没有排斥“利”或贬低“利”的意思,但是由于“见利”就应该“思义”,由于“义”已被儒家做了“仁、义、礼、智、信”相统一的解释,由于这种统一的核心是为了维持“君臣父子”的封建等级制,而不是奠定在个人权利、个性自由、人与人的相互尊重现代平等观念上的,这就是使个人的欲望和利益,是在一种“人为性”的制约下“不放松”的来有限地实现的。与此相关,道家思想虽然不像儒学那样提倡“克己”,却禁止对欲望的追逐现象,提倡“水往低处流”式的“简朴”。它的错误在于一是将人的欲望的健康运动人为化地规定为必须往“低处”流,从而将自然界进行丰富运动的精神理解为“一种自然现象”,客观上障得了人的求快乐本能的逐步延伸。二是将欲望的正常满足与“逐利”现象混同起来了,通过禁止欲望延伸来消除“逐利”现象,这样就既损害了正常的欲望满足,又不能对“逐利”有一个明确的理论性界定,从而就既不能解决好欲望本身的问题,也不能解决好“逐利”和所谓“物欲横流”的问题。在我看来,“逐利”的界线,既在于对他人造成非法伤害,也对自己的“完整性”—生存与存在的并存的两个世界造成伤害—他变得只能追求一个世界了,因而变得残缺和不健康了,变得自身因为被利益所占满而空虚起来。因为心灵世界、存在世界是与生存世界、利益世界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逐利”损害自身,也损害他人。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我以为在根本上,来自于人类的不成熟性所产生的对自身的自然世界的恐惧心理,以及由这种恐惧心理所导致的不正确的处理欲望之无序性的解决方式——道德约束。道德约束虽然代表着古代文明对世界的一种理解,但却不能健康地解决欲望之问题。由于人的欲望是一种进行永恒运动的能量,接近孔子释《易经》哲学内涵的“损益观”(即波浪原理),而道德约束就像挡住波浪运动的大坝,其效果只能激起裂岸之“惊涛”,这“惊涛”在伦理学上便是“逐利”或“纵欲”。因此在根本上说,“逐利”就是“克利”的道德约束引导出来的。
由于“纵欲”是欲望的宣泄形态,或者是欲望实现的人为化的不健康形态,那么它就不仅会导致西方历史上罗马帝国的覆灭,而且必然会产生西方近代文学史上以于连、拉斯蒂涅乃至杜洛阿为代表的变本加厉的“唯利是图”者,导致由边沁、穆勒的“功利论”为理论支撑的、已经获得个人利益满足的当代“唯我独尊”者的内心无聊、精神空虚状态;而且,只要“克利”的道德观维持一天,这样的景观就还会继续下去。中西方虽然存在着较大的文化差异,但是由于“欲望”是人类共同的本能,这样我们就可以看见在道德制约下的“纵欲”现象是何其相似:西门庆式的惟淫欲之能事,文人介入时世溃败后的沉湎声色和把玩智力,当代官员逐利欲望受体制限制造成的受贿等腐败现象,再推衍至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任何时期所存在着的、在道貌岸然后面的“损人利己”、“男盗女娼”现象……我们就更可以判断“纵欲”的这样一种性质:欲望的满足必须在“放松”状态下实现,才能保持肌体的健康循环,但因为中国人多在传统道德捆绑下生活,从未做到“放松”,所以一旦这绳索被挣断,人的欲望喷发,还是会对“放松”构成破坏,其直接结果便同样是对肌体、身心的损伤,并加速其衰老感、麻木感和空虚感。中西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在于:西方现代人由于有肯定人的世俗欲望的近代理性主义作支撑,这就使逐利已久的西方现代人,呈现出一种普遍性的、能够在阳光下或发呆、或歇斯底里、或等待莫名的戈多;而中国的近现代文化,由于李贽、戴震等肯定人的基本欲望的声音始终处于边缘状态,“五四”以降的新文化运动,又以民族性的启蒙和救亡遮没了人的世俗欲望的正当性,这就不仅使中国人的“逐利”行为只能在私人空间进行,而且因“逐利”造成的空虚、无聊和颓败,也只能通过忙碌一天临睡前的叹息、朋友相聚时的穷开心、个人独处时的发呆等方式表现出来。这无疑使当代中国人呈现这样的人格破碎的状况:公共场合的个人缺乏放松性的生命涌动感(每个人都是“做出来的人”),私人场合的个人又缺乏不同于利益满足的价值追求。
在我看来,造成这种状况不能怪罪于人的欲望和利益冲动的无休无止性,而应该归罪于人们对欲望的历史性的不健康之态度。由于人的欲望属于自然性领域,因此它是永动的、不可改变的,而人对于欲望的看法由于属于人为性领域,因而它是暂时的、可改变的。迄今为止,人们对“纵欲”、“逐利”等的不健康性的关注,由于没有触及到对待欲望观念的改变的问题,由于都是用一种“轻利”的观念来纠正“纵欲”和“逐利”现象,也就不可能在根本上根治“纵欲”和“逐利”。“本体性否定”是在中西方共同的“轻利”观之局限处提出自己的“放松”性生存观的,这样,对“欲望”和“本能”的否定,在“本体性否定”中便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含义。
三、作为“离开欲望世界”的否定性
当叔本华将人“想做的”与人“想要的”事物区分开来之后,当这种区分启迪爱因斯坦进行他的人生实践之时,我以为世界从此以后便应该进行新的划分:“想要的”属于“欲望世界”,“想做的”属于自我价值创造的“存在世界”。但是当叔本华进一步说人“不能要他想要的”的时候,可以导致两种理解:一是对“欲望世界”应该有所克制,二是不能沉湎于“欲望世界”、将欲望之弦绷得过紧,尤其是无休无止的获取。这两种理解都包涵着对欲望的“否定性”,但前者是“克服欲望”的否定观,后者是“离开欲望”的否定观。这两种否定观在性质上存在着重要的差异。
我想说的是;“克服欲望”的否定观是导致“纵欲”和“逐利”现象的文化性依据,是一个没有正常和健康地实践自己欲望的人在一旦可以实现情况下的必然结果,而且还会呈现奥修所说的状况:一个克制自己欲望的人,必将成天想着如何满足自己的欲望;或者说,一个克制自己欲望的人,就已经在心里面纵欲了。因此,当爱因斯坦说“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时,爱因斯坦一方面是将创造性的工作作为自己的人生依托,从而“放松”地对待了享乐本身,另一方面,爱因斯坦可能是在安逸和享乐并不成为问题的情况下说这番话的,这样爱因斯坦就等于是没有受“生存欲望”所缚;但是当一个下岗工人捏着每月一百元的工资补贴时,他(她)也说爱因斯坦的这番话,将不仅显得虚假,而且显得荒谬。因此,假如爱因斯坦是在鄙视生存快乐的基础上说这番话的,爱因斯坦面对一个下岗工人,便将无话可说,或者会感到这番话是有局限性的。
在根本上说来,爱因斯坦这种可能存在着的局限,不应该视为爱因斯坦本人的局限,而应视为整个传统否定观念的局限。这个局限,虽然不影响爱因斯坦取得惊人的创造性成就,但却在影响着不能取得爱因斯坦这样成就的人追求安逸的生活。爱因斯坦本来想说的是人不能依托在安逸生活之上,结果由于这种否定观的局限,就变成人追求安逸是可耻的。在安逸作为一种本能支配着大多数人的生活、而人们又需对这种生活采取轻视态度的尴尬中,人类的基本生存状况就显得躲躲藏藏、惶惶不可终日。这里面就涉及到个关键性的问题:人们究竟为什么要否定安逸和享乐的生活?人们否定安逸和享乐的生活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又该怎样否定安逸和享乐的生活?
在《否定主义美学》一书中我说过类似的意思:由于安逸和享乐的生活里人的本能性循环性生活,所以虽然它不可抗拒,但存在着消磨人的创造性、让人产生空虚感、并且最终必然要衰老的局限。一种文化沉浸在安逸和乐融中,将必然呈现中国文化在近代衰落的格局,一个国家沉浸在安逸和享乐中,将必然导致罗马帝国灭亡的结局,一个人沉浸在安逸和享乐中,将或者成为百无聊赖的贵妇人,或者成为纵欲而死的西门庆,因此可以说追求安逸和享乐就是打开了通往死亡之门——我们用的力量越大,通往死亡的距离便越短。所以,无论是“放松”性地对待快乐欲望,还是“逐利”、“纵欲”性地对待快乐欲望,其差异只不过在于前者是自然而然地通向死亡,后者则是加速通向死亡。在这一点上,为了摆脱死亡,我们必须对安逸和享乐性的生活态度持一种否定的立场——通过创造另一个不死的世界来实现。然而,“放松”性地对待享乐与“逐利”性地对待享乐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前者是以尊重欲望世界的不可违抗性、但又不满足欲望世界的空虚性为特征的,后者是以轻视欲望世界、进而追逐快乐享受、因而也意识不到死亡的危险性为特征的。所以对欲望体验的“放松”性态度,反而有可能使人离开欲望世界,而对欲望的轻视态度,反而只能使人沉湎于欲望的追逐。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放松”地对待欲望和享乐世界,人就不会沉湎于某一事、某一物,也不会沉湎于某一种快乐的享受;当一个人对各种生存性事物既有所用心又无所用心的时候,他才可以因腻味感、循环感而产生离开这个世界的价值冲动。而“沉湎”于生存快乐,那肯定是“沉湎”于某一种事物、某一种快乐体验(如沉湎于打麻将),即便他对某一种事物或快乐体验产生腻味感,那也是对某一种事物或快乐体验的腻味,而不可能是对快乐本身的腻味。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腻味某一种事物,还会去追逐另一种事物,也就不可能在根本上摆脱快乐的诱惑。这一点,在西门庆乐此不疲地追逐、更换女人以满足性欲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也可以说,“放松”地对待欲望世界,一个人就不会沉湎性欲,而还可以有其它欲望的满足;也只有在有多种欲望满足的情况下,一个人才有可能离开欲望世界——那个时候的“否定”,就是对欲望世界本身的否定,而不是对某一种欲望的否定。
亦即在轻视欲望的否定观支配下,大多数人只能沉湎于对享乐的追求,而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摆脱这种追求的诱惑。但像爱因斯坦这样的摆脱欲望和享乐的诱惑,在“本体性否定”看来,不是因为在意识上保持对欲望和享乐的轻视态度就可以做到的。很多人冠冕堂皇地说轻视享乐,但背地里却十分重视享乐或在目的论上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享乐,也有很多人声称为理想而奋斗,但在异己性的理想破灭后只好回过头来沉湎于欲望和享乐,而爱因斯坦的“离开欲望世界”则具有这样的意味:只有真正创造性的工作,才可以使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欲望世界的诱惑,也只有在从事创造性劳作的人,才可以避免因信念和理想幻灭而导致的对享乐的热衷态度,也才可以对欲望和享乐持无所谓的态度,并因此对沉湎欲望和享乐的人予以鄙视。但这种鄙视不是对欲望和享乐本身的鄙视,而是对“沉湎”于欲望和享乐以及离不开欲望和享乐的鄙视;对“沉湎”于欲望和享乐的人的鄙视,在根本上也不是对他们没有理想追求的鄙视,而是对他们没有自己的创造性理想追求的鄙视;对没有自己的创造性工作追求的人的鄙视,也不是鄙视他们所从事从众性的、阐述性的、承接性的工作,而是鄙视他们只能沉湎于从众性的、阐释性的、承接性的工作,并且自以为这就是全部价值之所在。实际上,当多数人觉得爱因斯坦高不可攀时,他们就已经是在为自己的“沉湎”寻找理由了;当多数人觉得爱因斯坦的创造不可思议时,他们也就在为自己的非创造性生活寻找理由了:把爱因斯坦归结为天才后,他们就可以为自己是凡人、进而为自己不能“离开”欲望世界而安然处之。他们不知道,爱因斯坦之成为爱因斯坦,只在于爱因斯坦首先不满足用既定的思想和观念看问题所带来的“安逸性”,不满足阐释前人思想的所谓学术工作所带来的“享乐性”,因为这种“安逸”和“沉湎”,与满足于物质快乐和利益的享受,在性质上是等同的。因此,爱因斯坦的“鄙视”,实际上不仅在说他在鄙视物质生活的享乐,也同时在说他在鄙视只能阐释前人思想的享乐,就是在说他的创造是“何以成为可能”的。或者说,在“本体性否定”看来,除了创造性生活,其它一切生活其实都带有享乐性。站在创造性生活的角度,你就不能不对只有享乐性生活的人采取鄙视的态度了。
也因此,“离开欲望世界”的“离开”之意,一方面给人们在欲望世界的放松性的、充分的满足留下自由的空间,另一方面,也为了人的完整和健康之故,为了人的心灵有所依托。由“离开”所构成的否定内涵,由此就具有创造另一个世界之意。这样的一种“否定”(我称之为“本体性否定”),便形成了一种新的“放松”和“紧张”兼具的现代人才有的二重世界:人们在生存世界、欲望世界和享乐世界,只要不触犯他人利益,尽可以放松地对待自己的欲求,而不必人为地克制或沉湎于什么,不必紧张地追求什么,但在离开这个世界、创造自己的价值世界的否定过程中,则必须真正地紧张和认真起来——因为这是自己成之为自己的立身之本,所以可能要费毕生的努力。欲望、享乐等是大众性的,因此不可能代表一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发财只能证明一个人的生存能力,而不能证明一个人的创造能力——除非这个人在发财之道上有自己的创造。因此,不仅坑蒙拐骗与公平经商有区别,公平经商也与创造性的经商有区别。创造性工作虽然要与生存性世界、既定的现实世界打交道,但由于性质已不在获利和快感,所以就不能以是否获利和有快感为尺度。因此就有写赚钱的书和写让自己心安的书之别。当然,让自己心安的书可能赚钱也可能不会赚钱,这与心安与否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赚钱不赚钱与创造性生活才能产生的心灵依托是两回事。什么才能使人真正产生看轻享乐或真正放松地对待享乐的力量,除了创造性的生活支撑,别的力量恐怕均难以达到。爱因斯坦看轻享乐,是因为有自己的创造性生活支撑,而一个下岗女工不能看轻享乐和欲望,除了生存危机本身的原因之外,没有自己的创造性生活支撑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虽然不能要求一个女工成为爱因斯坦,但我们可以要求一个已摆脱贫困又沉湎欲望的现代人,多少具备爱因斯坦的意识。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对欲望和享乐本身持“放松”的态度,另一方面,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对欲望和享乐持“放松”的态度,则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对“欲望世界”和“享乐世界”进行“本体性否定”——在发现欲望世界本身之空虚性局限的基础上,通过离开欲望世界、创造自己的价值世界以获得心灵上的依托。可以说,一个人只有以创造性的生活为依托,他才可以真正健康地对待欲望世界——摆脱或抵抗享乐的诱惑、或沉湎于享乐的诱惑这极端性的传统的二元生活。他才可以建立新的二元性生活,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