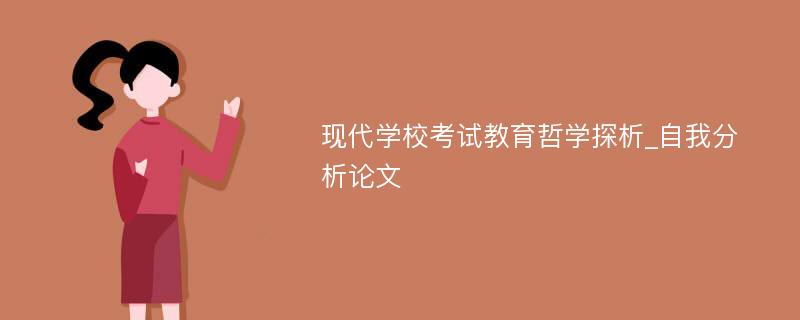
对现代学校考试的教育哲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学校论文,考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甄别、分等、选拔学生的重要机制,考试成为控制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分配的重要方式,也是教育等级化、知识特定化、教学标准化的合法化方式。考试不仅操纵着整个教育的理念与价值,而且也控制着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致使学校的选拔功能湮没了教化功能。由于考试所强调的标准化和客观性,受考试控制的教育倾向于复制行为技能标准化的教育产品,这造成教育所培养的人的精神单面化。
一、考试的标准化:规训人的方式
考试的强制以教育的“科学化”方式出现,而所谓的科学化不过是教学的程序化与模式化,以及考试的标准化与答案的惟一正确化。考试的内容是确定性的、孤立的知识条目。知识被分割成一条条孤立的、机械的条目,变成了标准化的固定的内容。标准答案预先设计了针对某一知识条目的惟一准确的答案,所测验的只是学生能够记忆识别的知识。考试的知识论预设是,知识是确定的、不变的,知识体系是由一条条人类所发现的,反映客观事物的真理所组成的,标准答案所要求的是对这一条条确定性的知识的识别。
标准答案是强制性的,因为标准答案被认为反映了惟一的知识真理。对于受教育者而言不就是接受知识真理吗?标准答案选择的惟一正确性,意味着个人必须选择、接受那个标准答案中的“真理”。这种强制性迫使教育者的想象力、创造力等就范于标准答案所设定的知识框架中。破碎的知识、妄断的结论、虚假的真理、命题者的主观偏好,都渗透在标准答案中,强迫性地要求学生接受。
为了这种形式的考试,教学过程以统一的模式与程序对知识学习过程,进行着预定的控制。为了适应考试,教师把问题和答案标准化与绝对化,以标准化的解释将固定的答案传输给学生,学生在考试中又一点不变地传输出来。应试的技巧、标准答案的选择渗透到教学的每一环节之中,教学变成了固定套路,受教育者只有圈进了这个教学结构,才能适应标准化的考试。教育的标准化意味着在考试的规导下,教育变成了强制性的结构,对人进行机械的标准化训练,对知识进行教条化的解析。考试的标准化,试图把知识的主观性判断与选择的可能性减低到最低限度,把思维、视野、知识等囿限在固定的范围中,以“别无选择”的方式把学生纳入客观化的铁板一块的模式中。考试标准化就这样在我们的学校行使着“教化”人的权力。
二、正态分布观的谬误与考试的控制权
精英主义取向的教育制度,必然使考试选拔成为控制教育、知识及人的合法权力的手段。考试的控制权的实现,是建立在对受教育者价值、资质的基本分类及与其相关的教育资源的分配上。
考试的游戏规则是筛选,它所依赖的统计学原则是正态分布率,即一个班、一个年级甚至一个较大的学生群体的才智分布是正态曲线的,处于两端的是最聪明的与最不聪明的,而大多数是才智处于中等者。考试就是要把最聪明者突出出来,而把平庸者淘汰出去。这种正态分布观不仅存于在学校考试中,而且也深深地浸透在教育的理念中。在一个教育人群中出类拔萃将成为人才者只是少数,而大部分是平平者,造就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都比较低,对社会的贡献不会很大。因而,教育对于这一部分人的要求和期望也不会很高。中国教育的学生分层与学校分类隐含着这种教育观与学生观。
但是,正态分布观对受教育者的三六九等的预设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我们无法根据任何一种测验而预测一个人发展的可能性的限度,人的发展的丰富性与不可知性,不可能仅仅通过学习成绩来体现和预定。教育如果抱着预定论的态度对受教育者的现实与未来进行划定的话,教育也就是非教育了。
儿童的生命与生活所包含的价值是不可估算和不可限制的。在发展中,儿童的生命与生活包含的可能性是不确定与不可预知的。在教育领域中考试的权力的扩展,把考试作为儿童分层的机制,严格的考试及其产生的效应减少和限制了求教育者自我发展的能力与机会,这是对求教育者最大的不尊重。这种等级化的教育体制,严重地贬低处于发展劣势的儿童的发展的价值,这种教育体制构成了对人的尊严的否定。
实际上,在考试所控制的教育体制中,不论是知识传授,还是课程设计,不论是考试体制,还是分数等级,都不是根据受教育者作为一个在教育中生活的人的需要、兴趣、目的所安排的,不是以他们为目的的。这种教育与考试所考虑的仅仅是教育如何实现选拔,考试如何达到控制。多少儿童在求得教育的生活中遭受考试无情的控制,思想和想象的自由受到压制!多少儿童在考试的控制中只能认命而失去学习的兴趣!多少儿童在这种考试制度所控制的教育的重压下心灵与精神遭受到伤害!难道这种考试制度所主导下的教育就是“社会”所要求的教育?难道对受教育者心灵的扭曲与心智的控制是公正的考试制度下必然的代价吗?不用讳言,这种教育是疏离人的,是缺乏人文关怀与生活关怀的,是对人的尊严缺乏尊重的教育。
尊重人的教育体制承认每个儿童是自由发展的自主主体,在教育中享有自由想象、思维与表达的权利。教育的尊重才能保证儿童发展的权利,保证他能利用一切可能学习的经验、事物与机会,免受非正当的强制、诱使和预定,使他的发展不受到制度性因素的限制。然而,考试体制以强迫式话语和惟一标准,对儿童加以等级化的区分,把儿童桎梏于考试所规定的发展时间与空间,以考试发难于受教育者,其对于儿童的尊严的否定正是考试霸权的体现。
三、克隆教育与教育的标准件
我国教育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一直追求着统一性和标准化。这是因为社会组织结构需要知识与行为技能规范化的劳动成员。意识形态要求思想与行为与其保持一体化的社会成员。这样,教育的规训就与意识形态的控制原则,共同结合成了教育过程统一化与标准化的力量,力求生产出职能符合社会要求的教育标准件。
考试以其所谓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在教育推行标准化的过程中起到强制作用。规范化的课程与标准化的教学成为塑造教育标准的模具,而客观化的考试检验和评价学生所达到的标准化水平,把求教育者强制性地驱赶到教育的分级分类的生产流水线的模具中,不得不接受塑造,不得不在教育结构中被规范化和标准化。
教育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把一种设计好的标准的人的形象及其社会职能当作教育的培养目标,学生的发展是按照社会要求预先设计好、计划好和预定好的。教育对学生的个性、创造、发展都进行控制,使他接受社会与教育规定好的知识,发展为他设计好的才智,获得为他计划好的思想。这样,学生在教育中被制造、被训练,最终的发展状态就是平均化与标准化。尽管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平均化与标准化,但却把复杂多样的具有独特性的个性导向发展的平均化、单面化、标准化状态。这种教育着重培养作为社会类的个体的标准化的行为与思想。因此,只是在塑造标准化的人。这其实不是在教化人,而只是根据标准形象与榜样用标准化过程“克隆”人或复制人。
从“人才”的工具性能的培养标准,到教育过程的规范化和考试评价的标准化,教育只是根据特定的标准“复制”教育产品。一个个人进入教育,被当作要复制的零件,由统一的课程、标准化知识、客观化考试进行复制,结果是个体的独特性消失了,成为了“类相似”人。教育千篇一律,而人都失去了个性的多样性。教育不过是克隆出了思维、语言、知识、行动都模式化的单面人。
克隆教育把求教者在教育中的精神变革与成长变成了单调的机械性变化。学生精神的自主创造被剥夺了,完全沦为学校与教育的被动的“塑造”物。思想与行为被标准化了,人格精神失去了深度与广度,创造热情与能力,在标准化教育的限制中消退了。教育无视个体在发展中作为主体的精神与可能生活的自我创造,而只是塑造具有标准化的知识技能的单面人。这样,个体人格精神被窒息。
教育的外在化与人的工具化意味着在“工具理性”主导的社会中,每个人在寻求着工具用途,并且通过教育而竞争高用途、高回报的社会地位。考试的客观化评价是每个人在教育竞争中所依据的标准,考试就在这一需要中固定下来成为明显的合理化的强制形式,它的测量使不同用途与职能的人获得相应的地位。客观化考试是纯技术的控制形式,它根本不考虑精神的深度与多样化,它所关心的是对某些一致性的东西的统一测量,而分配相应的回报。这样,受教育者的寻求就与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教育同一了,主观的异化的需要与教育的异化过程结合并固定下来,异化的主体被异化了的教育所吞没。
克隆教育与单面的教育产品,只是接受现实中既定的价值、观念等,而不要求对现实进行批评、反省。不论是意识形态主导的政治社会,还是工具理性主导的经济社会,由于追求同一性,都不要求社会成员具有批判理性。文革时期的政治封闭与社会生活单一,现时期的消费主义与拜金主义,从不同方面说明了教育与人单面适应社会同一性而缺乏超越性反省的后果。单一意识形态的社会拒绝反省与批评,而消费主义社会则缺失反省,只要消费欲望能够满足,一切都可接受。
由标准化考试所强化的教育所取得的齐一性、标准化,恰恰体现了一种对个体意识的强制,它使个人在教育中消弥了个性,而获得的只是假个性,因为思想与行动的齐一化被外表的差异所掩饰。“个人被融入了功能之中,存在被客观化了。”“人们是像沙粒一样被搅和在一起的。他们都是一架机器的组成部分,在这架机器中,他们时而占据这个位置,时而占据那个位置。他们不是这样一种历史实体的组成部分:在这个历史实体中,他们注入他们自己的个体自我。过着这种无根生活的人的数量正继续不断地扩大。”这正是接受过标准化教育的克隆人的形象。
四、考试控制与个性反叛
在标准化的教育中,个人的价值感、尊严、创造性、旨趣、愿望都被教育所漠视。尽管受教育者在教育的强大塑造力量中,力求迎合教育的要求,迎合那些规范、标准,迎合考试并渴望分数,但是必须在教育的生产机器中被动地接受教育的安排。他的一切是被这种教育分配并规定好的,他的自我尊严与自我价值感都取决于被教育所分配的等级。为了迎合教育的塑造,他个人的主体性不得不屈服于教育中的考试、权威、规范与条例等,而放弃自我价值实现的愿望。但是,他能意识到这种个性、主体性、价值感的断裂,意识到来自教育的模式化与考试权威的控制,也能意识到来自于教育的对“我”的否定。他体验着压抑、胁迫、屈服、不自由,于是在他内心便聚集着怨恨,这种怨恨积压在他的心底,形成敌意,在可能的时机便会表现出来。这是一种从反方向寻求确定自我价值的行动,即从反抗与破坏的方面,对抗性地表现自我,而实现对自己无所控制的外部强制力量的反叛。
每一个受教育者在成长中渴望“成为他自己”,这种自我实现要求着任何有助于他成长与发展的力量都能够尊重他人格的尊严,尊重他自我发展的权利。同时,这种自我实现的主体意志是推动他自主地实现价值的主要力量。他的自我价值感、幸福感、自我发展的愿望,都来自于他的自主的价值实现过程。然而,考试引导下的教育强制地压抑自主的价值实现,冷漠地处理受教育者的个性、权利、尊严与价值,从而培育出适合某些社会标准的一致化的思想与行动。但是,个体力图自我实现与教育力图控制形成了内在的冲突,教育的控制是强大的,而个体面对这种强制性力量是“无助的”。教育的征服意味着教育控制的成功,而对于个体则是面临着存在的不安感,形成了来自生命价值受到胁迫的焦虑感,所以力图反抗控制。
中国教育制度是竞争性的结构,竞优选能是这种制度外在的表现与内在的灵魂,考试分数实质性地表现着个人的价值比较与评价。这种教育体制通过对受教育者的价值评价系统,把他们分属于不同的价值等级序列,从而确定谁是最值得培养的,并且在受教育者之间引起一种把自身价值与他人价值进行比较的心理情态。外在的评价与内在的比较都导向受教育者个体的价值等级与秩序的体验,自己的才智、能力、个性、前途是比他人优越,还是比他人低劣?比较使在竞争结构中的受教育者在他人身上把握自己的价值。竞争中的优势者通过他人的失败,增强了存在价值感,而弱势者则形成弱化的存在价值感。在竞争性的教育体制中,价值等级与平等的机会激发了每一个个体在教育的社会化攀比中确定自我的欲求。每一个成绩中的位置都成为竞争与追逐的起点,都成为确定个体存在价值、确定未来身份的基础。在这种价值比较中,连续竞争获胜者呈现奋求心态,而失败者则滋生着怨恨心态,不仅怨恨被比较者——那些在竞争中占优势又享受着教育的积极评价与更多机会的人,而且也怨恨形成强烈竞争与客观性评价和比较的教育制度。
在大众化的现代教育中,这种价值比较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怨恨心态既产生于才智、能力等存在的个体性价值的比较上,也产生于通过竞争而分配的资源、机会、奖励、地位与身份的社会性生存价值的比较上。在比较中,弱势者的生存性价值感受到贬低与自我贬低,自尊受到打击,而又对提高与获取价值感到无助无能。比较的机制与那些享有优势价值的人对他构成一种生存性压抑,并且把这种压抑及怨恨以不同的方式否定性地表现出来。例如,表现为问题行为、社会性对抗、心理隐患乃至犯罪行为。
在竞争性的教育结构中,为了获得自我价值的提高,为了不至于在评价与比较中个人的生存价值受到否定,所有的受教育者都进行着角逐,从而证明自己的生存性价值并获得社会价值。他们都被引导和被要求着将时间、精力、能力、态度乃至情感都运用到极限,他们不得不超限度地学习,以便通过考试获得分数而实现价值的确定。每一个人都想超过他人,想得到最高的分数,证明自己是出类拔萃式的人物,同时还可以获得其它社会性奖励。学校本身的等级竞争制度重视竞争得胜的人,必然地使相当一部分人处于劣势地位。处于劣势的人的自我价值与尊严就受到打击,他们产生焦虑、失望、怨恨的情绪,产生价值贬损的心态与行为。事实上,在竞争的教育结构中,由于考试的控制与操纵,受教育者缺乏存在的安全感,不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都体验不到进步及其快乐,感受不到稳定的内在完整性与自主性。他感到自己是被控制与被操纵的,无法确定真实生活的价值,感到自己的身份与自由始终成为问题,面临价值否定与存在否定的威胁。
反抗及其怨恨的确在教育与价值的断裂中,产生心灵的自我贬抑与价值错觉。自我贬抑导向个人发展的严重受阻,并且产生内在性的自我怨恨,造成病态的自卑心理。价值错觉导向外在性的怨恨,产生错误的价值判断,在压抑性的逆反中表现否定性的价值。在教育的控制与考试的强迫性竞争中,为了对抗对自身生存价值的否定,生存价值受到威胁的学生从反方向寻求确定价值的行为,反叛性地表达自我。这正是控制性教育与考试霸权所导致的最严重的教育后果。
标签:自我分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