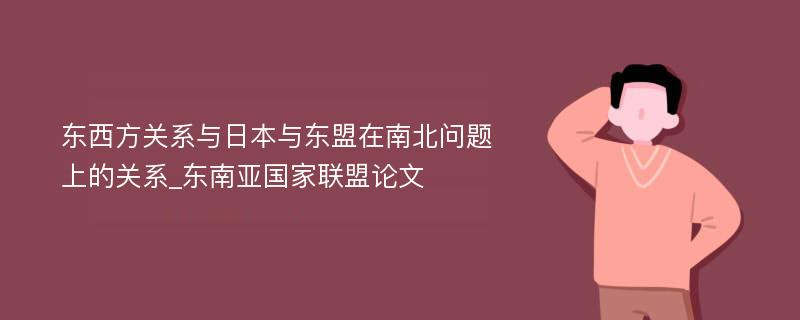
东西关系与南北问题中的日本和东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盟论文,日本论文,东西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40年日本与东盟的关系,是东西关系的一个地区缩影,也是南北问题的一个全球典型。由于经济关系是双方关系的基础与核心,故南北问题始终是日本与东盟关系中的主要问题。然而,由于东方的日本又是西方发达国家集团中的一员,所以日本与东盟关系又折射出了东西方的色彩。
一、东西关系下的日本与东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西方两极格局逐步形成。东西冷战以美苏全球争霸为主要特征,表现为在经济体系上的对立、政治上的争斗、军事上的对峙,以及对“中间地带”的争夺,严重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为美国亚太半月形包围圈上的几个环节,日本与东盟地区成为东西方冷战的前沿地带。在这种东西关系框架下,日本通过东盟政策,发展壮大了自身实力,巩固了西方阵营,对美国的东亚战略起到“补台”作用;而且,在稳定冷战局势的同时,也加剧了东西两极的对峙和分裂。
首先,日本与东盟经济关系的发展得益于冷战格局,同时提升了西方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在美国的扶植与支持下,日本加入了国际组织,也迈进东南亚及欧美市场。在东西阵营对立的情况下日本与东盟的经贸关系,实际上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进行的,(注:[英]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65页。)旨在扩充经济实力,也相应巩固了西方营垒,其本身就带有东西关系的色彩。针对日本与东盟国家经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尼克松做了一个类比:“从狭隘的贸易和利润的眼光来看,日本作为美国竞争对手的崛起,对有些人来说也许是一个不幸的事件。但在东西方斗争这一更广阔的背景下,它却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因为在自由国家的世界里,日本的实力正如强大的西欧经济一样,弥补了我们的不足”。推而广之,“日本应以长远眼光来看待同贫困国家的关系。不能使这些国家滑入苏联轨道”,日本最好能中止同共产主义的尼加拉瓜、古巴和越南的贸易,更多地同那些需要援助以抵抗共产主义“海妖之歌”的国家发展贸易关系。(注:[美]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2页。)事实上,东西冷战一定程度规定了日本对外经济的活动范围。当然,日本主要是从经济利益的必要性来考虑问题的,并没有完全受意识形态及不同阵营等政治制度上的限制。
其次,日本通过对东盟的战略援助和政治支持,配合美国的东亚战略,抵制了苏联和越南在东南亚的影响与扩张。东盟作为一个经济、社会和文化合作组织,囊括了当时东南亚地区几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不可否认,其亲西方反共的政治因素是促进内部联合的主要因素之一。所以,东盟成立后,美国评价其为“亚洲的新风”,希望盟国日本给予支持与合作。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加之越南战争失败,开始逐步从亚洲收缩势力;苏联则以咄咄逼人的攻势乘虚南下,插手东南亚事务。为了填补美国撤离后出现的“真空”,维护自由主义体制,美国也希望日本作为补充力量,加强经济援助和合作,在该地区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福田主义的出台就是一个重要标志。其中对越援助政策,就是日方把经济援助作为政治杠杆,对越施加影响。1978年,日本先后向越南提供了无偿援助和日元贷款,并邀请越南外交部副部长赴日协商。日本外相园田直表明“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是经济援助的条件”。(注:[日]《朝日新闻》,1978年7月6日。)越南入侵柬埔寨后,日本应东盟的要求,冻结了对越援助,并且增加了对泰国、菲律宾和老挝等国的战略援助。这就是如大平首相组织的综合安全保障小组的研究报告所建议的,“不仅要向重要的原材料供给国提供援助,而且还应从军事角度,向有着重要战略地位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援助。”(注:Mike Mochizuki,Japan's Search for Strategy”,International:Security,Winter 1983—84,pp.159—160.)同时,日本响应东盟的要求,坚持联合国决议和柬埔寨国际会议宣言的政治解决方针,支持东盟国家的外交努力,积极开展外交活动,维护民主柬埔寨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柬埔寨问题的解决上,日本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
再则,日本积极调整安全战略和防卫政策,介入东南亚地区的安全事务,也是其配合美国对苏遏制战略、分担东西冷战责任的表现。1969年尼克松主义的诞生,是美国霸权地位衰落的产物和表现,其核心目的在于减少对盟国的军事义务,要求盟国分担责任。70年代中期后,随着苏联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勃列日涅夫奉行霸权主义,积极推行进攻性的国际战略,加紧美苏争夺。由于苏联海军在印度洋的活动增多,自1969年起,日本政界和财界就曾展开过“马六甲海峡安全”的讨论。(注:[日]西和夫:《经济合作一面向政治大国日本之路》,中央公论社,1970年版,第182—185页。)两次石油危机,严重冲击了日本的经济基础。如何填补美国战略收缩后空缺的政治地盘,阻止苏联势力的南下,同时控制东南亚地区及其周围海域,确保海上“生命线”的畅通,成为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1979年大平首相提出了综合安全保障构想。翌年1月25日,大平首相在第91 届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强调:“我国对外政策的根本是,强化与自由阵营的合作关系,以此为基础推进与全世界的友好合作关系”,“苏联军事入侵阿富汗,无任何正当理由。……我国要求苏联尽快撤军,为此坚决支持联合国特别大会决议”,“而且,我国对印支地区事态发展深表忧虑,欲与东盟国家一道为恢复该地区的和平继续努力。”(注:[日]外务省:《我国外交近况》第25号,1981年,第332—334页。)同年,日本《防卫白皮书》提出“要从世界中的日本防卫出发,考虑如何增强防卫力量”。1981年,铃木首相访美,战后双方首次在联合公报中一致肯定在太平洋防卫上进行责任分工,并且,铃木首相还表示日本要“保卫1000海里航线”。中曾根则抛出“不沉的航空母舰”论,强调以“西方一员”的身份与美国加强合作。日本在分担责任、抑制苏联的烟幕下,谋求发挥军事安全作用,专守防卫政策随之发生质变,无形中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
东西方原本是地理概念,相应也具有文化和社会意义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苏争霸为特征的冷战兴起,形成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全面对立,赋予东西关系以意识形态的涵义。如今,冷战体制已经解体,西方发达国家与东方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主要表现为南北问题。然而东西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虽已淡化,但依然存在。有的学者认为是“一个冷战结束了,两个冷战开始了”。一个冷战即美苏争霸的结束,使两个冷战即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同第二世界的冷战突出起来。(注:卫建林:《历史没有句号——东西南北与第三世界发展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2页。)日本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既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员,又是“天然”的东亚国家;既受西方社会文化的熏陶,又属于东方文化圈。因此,从上述意义来说,包括日本的东盟政策,如何摆脱冷战思维,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立,重新看待东西关系,仍是一个现实的重要课题。至于能否还“东西”以地理文化之本意,还有待历史见证。
二、南北问题中的日本与东盟
南北问题,一般指大部分位于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与大多数位于北半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的问题。历史上的南北问题,源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既包括宗主国对附属国的经济盘剥,也包括对殖民地国家的政治压迫,由此形成了一种长期的不平等的经济政治关系。冷战体制下南北问题的政治侧面为东西矛盾所抑制或掩盖,主要表现为经济方面。冷战两极格局解体后,尽管经济发展问题仍是南北问题的主旋律,但是,南北矛盾在政治领域的表现也日益突出,有学者称之为“南北问题政治化”。日本作为后进资本主义国家,与东南亚及东盟国家的关系,可以说经历了南北关系发展的全过程,是南北问题的一个典型例证。
首先,冷战结束后,日本与东盟之间的南北政治矛盾凸显。日本等北方发达国家将人权、安全和军控的矛头,由原苏联和东欧国家转向南方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美国打出人权是其对外政策基石的旗号,为保障所谓“人权”甚至不惜动用武力。1989年欧共体在签署第四个“洛美协定”时,第一次将民主和人权列为该协定的基本条款。经济大国、援助大国日本,也把ODA与人权和军事安全等挂钩, 以求影响受援国的内外政策。1991年海部俊树首相出访东盟,在新加坡发表演讲时指出:“日本将在实施政府开发援助之际,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支出、武器进出口等动向。”(注:[日]佐佐木芳隆:《跨海出动的自卫队:PKO立法与政治权力》,岩波书店,1992年版,第104页。)1992年宫泽喜一内阁制定了《政府开发援助大纲》,提出了“ODA四原则”,其中三项原则涉及军控、民主、市场经济、人权等问题。1993年日本《ODA 白皮书》指出:“东南亚各国中那些增加军费、致力军事现代化的国家,自然引起我国的关注。在向这些国家提供ODA时,当然应注意其军费支出和武器进口动向。”(注:[日]外务省经济合作局:《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白皮书》,1993年,第51—52页。)日本在要求东盟各国“军控”的同时,却在不断加强自身军事力量、扩大军事活动范围。例如,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中期,日本与美国对同盟体制进行了“再定义”,适用范围扩大到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亚太地区,并在最近几年日本借海盗问题不断介入东南亚安全事务。2004年3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有事法”七法案, 法案中提及的“周边”,不仅包括邻近的台湾海峡,也包括稍远的马六甲海峡,从而为日本在“紧急事态”下的海外干涉提供了法律依据。
至于人权、民主和市场化原则,在表现形式上,日本主要是从正面积极支持越南、柬埔寨等国的民主化和市场化,而对缅甸军政府持批判立场。日本企图在发挥ODA经济效果、巩固经济大国地位的同时,突出对外援助的政治、军事安全影响与战略目的,从而为日本走向政治大国、军事大国铺平道路。
总之,日本等北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人权、军控为幌子,以援助、宣传甚至武力为手段,软硬兼施,诱使、逼迫南方国家加入其体系,听从其安排。如德国人所言,“东方崩溃以来,由于我们没有了敌手,不必害怕敌手竞争,所以我们能够单独做出决定,南方必须走什么样的道路。”(注:《北方对南方发动的战争开始了吗?》,[德]《法兰克福汇报》,1992年3月19日。转引自卫建林《历史没有句号》,第6页。)这不能不说是强权政治在当今时代的典型表现。
其次,经济全球化迅速推进,而南北经济关系中的矛盾也愈加尖锐,日本与东盟关系亦不例外,双方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日本与东盟关系并没有改变南北国家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问题上存在的根本性意见分歧。1974年4月, 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反映了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南方发展中国家的呼声,即要求建立公正、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然而,从1975年起,日本等北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每年召开七国首脑会议,协调立场,主张按照其制度和价值观,建立日、美、欧三极共同主宰的世界“新秩序”,拒绝在贸易、资金和货币等领域做出重大让步。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面对北方国家主导推动的全球化浪潮,东盟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境遇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2.日本与东盟关系仍反映了南北贸易权利不公、南方贸易条件相对恶化的状况。1999年,日本对东盟的出口中,仅半导体零部件一项贸易额就达107亿美元, 而东盟向日本出口的食品、原料、燃料三大类加在一起贸易额才178.7亿美元。 一块芯片换几十吨木材,这样的交换仍然在日本与东盟之间进行着。日本拥有名牌产品、雄厚资金和发达科技等垄断优势,而东盟国家生产的主要是低附加值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结果造成高科技产品与初级产品的价格剪刀差越来越大。这恰恰是南北问题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现行世界贸易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占世界人口多数的贫穷国家,只能得到世界贸易收入3%的收益;而占世界人口14%的富裕国家,得到了世界贸易收入的75%。(注:施晓慧:《坎昆谈判,富国勿打黑算盘》,载《人民日报》,2003年9月15日。)总体上南方国家的贸易条件比10 年前更加恶化。
南方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主要是由北方发达国家施行的关税壁垒、农业补贴及非关税壁垒等政策造成的。以日本与东盟为例,日本对东盟各国深加工食品征收的关税约是粗加工食品的一倍,从而削弱了东盟各国农副产品的优势,限制了东盟各国商品附加值的增加。日本还通过农业补贴、非关税壁垒等方式阻碍东盟各国农副产品的进入。经合组织的调查报告显示,2000年日本的农业补贴已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4%,而同期农业收入仅占1.1%,日本对农业的补贴显然已经超过农业收入。日本政府补贴最多的农产品当属大米。尽管日本生产1公斤大米的成本约等于泰国的9.6倍,可是在取消农产品补贴问题上日方态度强硬,拒绝开放大米市场,这就限制了泰国、菲律宾等东盟各国大米的对日出口。2003年,日本又实行了“大米身份认证制度”,并且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两道新的贸易壁垒,使日本可以继续堂而皇之地将东盟国家的农产品拒之门外。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其他南北国家之间。例如,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时要缴纳的平均关税,是发达国家向同一市场出口关税的4倍。(注: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页。) 欧盟的牛每天得到2.5美元的政府补贴,而非洲75%的人口每天生活费不到2美元,真可谓“人比牛穷”。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明确指出: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关税和其他扭曲性措施,如补贴等,严重地阻碍了穷国的发展进程,严重制约着穷国经济增长的努力。(注: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页。)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在2003年11月29日的世界粮农组织第32届大会上的基调讲演中亦呼吁:“我们要坚持的不是自由贸易,而是公平贸易”。
3.日本与东盟关系体现出北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着资本和技术,以保证从发展中国家稳定地获取高额利润的基本特征。
从资本的角度来看,日本对东盟的投资仅仅是其对外总投资的一小部分。1951年到1999年,日本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达7237.32亿美元, 其中对美投资就占投资总额的40.3%,对欧投资占21.7%,对东盟五国(泰、马、印、菲、新)的直接投资仅占9.6%。(注:[日]日本贸易振兴会:《2001年JETRO投资白书世界与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财务省印刷局第527—528页。) 世界范围内亦是如此,2000年,全球近80%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向发达国家和地区,流入发展中国家的仅为18.9%。可见,当今世界资本流动高度集中即发达国家“内部化”,造成了广大南方发展中国家总体上的“边缘化”。
即便是如此有限的投资,其主要受益者也并非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国家本身。以马来西亚吸收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投资为例,马来西亚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吸引外国投资,当时其工资水平大约相当于投资国工资水平的5%,而且还要对投资方实行多年的税收减免政策。此外,外国直接投资并不一定意味着资本的流入,马来西亚吸收的“外资”中有五分之四是从当地银行借贷的,另外五分之一则是服务等形式,实际上并没有资本进入。可见,外资赚取利润的前提是穷国的低工资、免税、提供资本等鼓励措施。如今,多数发展中国家竞相出台优惠政策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终获益的必然是外国投资者。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日本强化了知识产权保护,而且技术的交易和流动高度集中于日本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或本国公司内部,造成南北双方差距日趋扩大。日本的住友、三菱、三井、松下等跨国公司都与欧美跨国公司组成“战略联合”,通过成员之间的合同关系组织整个活动,从而构成纯粹意义上的垄断网络,这是北方国家之间的水平合作分工。日本与东盟各国多年来形成了垂直型的分工结构,即所谓的“雁行模式”。在新的发展形势下,日本技术转让保守,仍力图确保经济优势,使该模式固定化,以此为依托在东亚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至于日本跨国公司的内部技术和产品交易情况,从马来西亚日资企业生产摄像机所需要零部件的来源就可以看出,日本企业内部采购率达到91.3%。东盟各国如今面临的是一个比较严酷的经济环境,发展形势不容乐观。面对日益扩大的技术差距,发达国家仍在采取措施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并在1993年“乌拉圭回合”临近结束时强行达成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进一步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对此,长期在经合组织科技与工业领导机构从事研究的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沙奈指出:新的法律规定使大公司更有办法阻止别人接近技术。……这些规则体现的是强权政治,表现了这样一种意志:即穷国除了提供以债务利息为代表的供品之外,还要额外进贡。(注:[法]弗朗索瓦·沙奈:《资本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6页。)
4.日本与东盟关系的发展也反映了南北双方在环保问题上的矛盾。人类工业化时代的进程发展到今天,环境问题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然而,环境问题的主要责任者事实上应是发达国家。以日本与东盟为例,日本的森林覆盖率高达65%,居世界前列,但日本是亚洲最大的木材收购商,每年进口木材占总需求量的75%左右。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原始森林被大量砍伐。日本长期以“愿买愿卖”为招牌,从东盟各国低价大量进口资源和初级产品,却并没有补偿其环境成本。日本还将本国的化工、钢铁等污染工业大量转移到东盟各国,以确保本国的环境同时又赚取了利润,但东盟各国却要为此付出高额的环境成本。
据统计,拥有五分之一人口的发达国家在享用着世界四分之三的资源(包括资本资源、自然资源、环境资产),(注:胡鞍钢作序,陈百强:《谁在养活美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页。) 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资源消耗量与污染排放量分别占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三和二分之一以上。正是这种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及生活高消费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造成了严重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但北方发达国家显然并不想对环境问题负责,美国的布什政府拒绝执行《京都议定书》,温室气体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三的日本也借机“讨价还价”。更有甚者,发达国家还炒做出第三世界威胁、“中国威胁论”等论调,将环境问题归咎于南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人口增长以及贫困加剧等。
5.日本与东盟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力地证明了南北贫富差距在持续扩大。2001年,日本的GDP是东盟的7.6倍,约是东盟各国的29~2358倍,人均GDP是东盟的28.7倍,约是东盟各国的1.6~235倍。具体来看,从1985年到1999年,日本与东盟国家的GDP和人均GDP比值,除了新加坡GDP比值从75.9倍缩小到51.2倍、人均GDP比值(1.56→1.57)几乎保持不变之外,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国与日本的差距均在扩大,GDP比值的扩大分别为15.4倍→31.7倍、43倍→55.2倍、43.7倍→56.7倍、34.5倍→35.1倍,人均GDP比值也程度不同地在扩大,分别为20.9倍→52.6倍、5.6倍→9.9倍、19.8倍→33.5倍、14.7倍→17.1倍。(注: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1997年、2000年数据算出。) 同样, 在世界范围内,从1980年到1997年,发达国家(OECD成员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0450美元提高到26380美元,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划分的中低收入国家)则从810美元提高到1250美元,二者的差距从12.9∶1扩大到21.1∶1。当今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南北两极分化的时代。
总而言之,以日本与东盟关系为代表的全球南北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已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南北差距拉大、世界经济严重失衡的根源主要是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因此,北方发达国家需要基于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开展南北对话,在向南方开放市场的同时,必须赋予他们更多的发言权。(注:2000年8月,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D·沃尔芬森在《2000/2001年业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的前言中提出了旨在削减贫困的关键的五项行动:其中包括“促进全球金融稳定,为穷国的农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而开放富裕国家的市场;通过穷人组织的国际联合等方法,赋予穷国和穷人在国际论坛上的发言权。”) 当然,南方国家首先应该对内推动政治经济改革,利用或创造后发优势,缩短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自力自强是南北合作的基础:同时也要加强南南合作,提升集体的竞争力,力求改善南方国家在南北合作中的地位和形象,增强南方国家的发言权:同时,南方国家还应该积极推动南北合作,使合作的运作规则更多地反映南方国家的利益和要求,以促进区域合作的健康发展和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当然,几十年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北方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和支配地位没有改变,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
标签: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日本军事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人权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 经济学论文; 苏联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