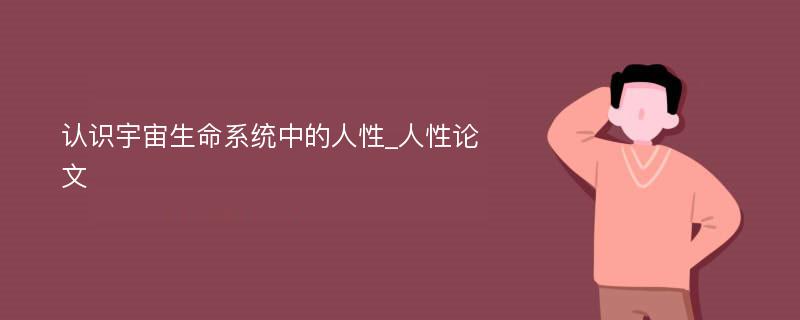
在宇宙生命系统中认知人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知论文,宇宙论文,人性论文,生命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强调人性的时代、阶级差异,这是在人群环境中研究人性;强调人性即人区别于动物的属性,这是在地球生命环境中研究人性。前者注重人的社会属性,由此凸现的是群体的特性;后者注重人的自然属性,由此凸现的是物种的特性。这是迄今为止,学术界所能认同的两种研究人性的方法,它们虽各有可取之处,但误区也是较明显的,因此,不能真正科学地认知人性的实质。
对人性问题认识的肤浅,直接影响到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伦理学、教育学、文艺学等与人的行为相关的学科,使其思想观念严重滞后,很难起到指导社会、启迪人生的作用,同时也导致了一些社会问题。如过分宣扬人性的社会性,往往造成人的自主意识缺失,一切顺从环境,甚至将自己的恶行归咎于外在的社会风气,而不从内在的自我品性上寻找原因。满足人兽对比,亦使人类失去了“取法乎上”的精神,夜郎自大,动辄以“天之骄子”自居。在“人类中心主义”这种扭曲心态驱使下,人类不断地对大自然穷兵黩武,疯狂地屠杀、掠夺,以满足无尽的贪欲。狭隘的人性理论,必然产生视一切如草芥的狭隘的人道主义。这些偏见色彩浓厚的人性观,很难使人树立境界高远的人生观,人们在麻木中将邪恶视为正常,陋习、嗜欲、变态心理等等,也仅仅被视为无伤大雅的小疵,而非一种应彻底根除的恶性。
一
所以会形成不甚科学的人性观,且研究又没有太大的突破,主要有以下一些缘由:
首先,理论界历来墨守成规,超越不了过去的一些清规戒律。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说过:“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因此,不存在抽象的人性,已成为许多学人根深蒂固的观念,甚至许多教科书皆因袭此说,认为只有具体的人性,这种具体的人性就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归结的,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换句话说,人性就是各种属性如民族性、阶级性、时代性等等的集合体,这些属汇总现象而非剖析现象,用以解释本质的理论,显而易见没有触及人性问题的根本。科学的研究理应从个别到一般,从现象到规律,从具象到抽象,纠缠于具体现象怎么能认识事物的实质?的确,抽象的人性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世界,正如抽象的“国民性”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世界。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不等于就不存在于人的思想观念,鲁迅、柏杨、林语堂等人,不都讨论过不涉及个人的、“抽象的”国民性吗?同理,抽象的人性也可以存在于人的思维之中,成为人们认知的对象。这种将人性表现视为人性本质的研究方法舍本逐末,将真相与皮相相颠倒,正如研究水汽冰霜雪雾,而不研究它的本源物H[,2]O。不真正洞察抽象的、本源的、静态的人性实质,则很难正确理解具体的、派生的、动态的人性。
人性其实是比社会性、阶级性更本质的东西。人性在不同的环境有着不同的表现,貌似变化多端,实则万变不离其宗,人性中原本就存在着不变的东西,正是这种不变的东西,导致了人的其他属性。即便是人的社会性,也是人性中的创造性、协作性、自私性等相互作用而促成的,人性中的这些具体属性,都比社会性更接近于人性的本质。
其次,对于“人性”一词的涵义缺乏科学解析。“具体的人性”中的“人”,乃是指群体、个体的人,而非“人类”,“人类”是更宽泛、更抽象的概念。毛泽东说没有超阶级的人性,许多人忽视了其前提是“在阶级社会里”,而我们要研究的正是“超阶级”甚至“超社会”的人性,是要研究一种只要人还是人,无论在自然中,还是在社会中、阶级中都会存在的属性,这种属性任何人都具有,无论贤愚、贫富、男女、老幼、古人今人、中人西人概莫能外。
对于“人性”中的“性”,也有误解之处,而古人的理解要远胜于今人。王充《论衡·初禀》云:“性,生而然者也。”《荀子·性恶》中说得更好:“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在古人看来,“性”乃“天性”之义,是先天的,不学自会的,是人的一种本能,正如婴儿吮乳。这种本能深植于人类的潜意识之中,相当稳定,很难添加,也很难去除,比“本性难移”还要难移,因为本性是指个人的禀性,而人性却是指人类的禀性,故改变人类的禀性比愚公移山还难。所谓人性会随社会发展而愈来愈完善的说法是有欠深虑的,人类可能越来越完善,但这种所谓的完善只是人性中固有的善的因子日益昭彰显露而已。
综上所述,人性的涵义应是:任何人都共同具有的、潜在的、稳定的、区别于其他不同性质生命体的一种天生的特性。
再者,人性研究之所以裹足不前,还在于有些研究者观念、思维太过“现实”、“唯物”,不敢超越时空限制去大胆构想,科学预见不足。我们可以设想更高等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为什么不可以设想更高等生命的特性?有人说,共产主义社会将要出现尽善尽美的人性,这种人性如何尽善尽美,却想象苍白。事实上,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设想比人更高等、甚至非常高等生命的特性。唯物的科学不能证明高等生命的存在,“唯心”的哲学却可以超前地推想高等生命的特性,以引导人类提升精神境界。由于惧怕“唯心”的指责,我们研究人性只好将人与地球生命相比较,这样,比上虚无,比下有余,着眼于人与动物“质”的区别,共同点抛开不议,人性的内涵当然褒义众多,又有理性,又会行善。至于人类中出现的暴行,只要将他说成“灭绝人性”、“兽性大发”,推到动物一边即可,其余则仍不失清白、高贵。
这种研究人性的方法,弊端甚多。正如评价博士的学养,如果仅将他与硕士相比较,博士当然至高无上了,但显然事实并非如此,与真正博古通今,天资勃发的智士相比较,博士的学问则微不足道。同样的,与高等生命的特性相比较,人又是一种较少正念理性、甚至野蛮的生物,正因为人有智谋,作恶往往比动物凶残百倍。生命形态越高级,无疑道德和智慧品质就越高,而人类在这两方面都十分平凡,只不过是龟缩于宇宙一隅的“乡下人”,远非“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莎士比亚语)。攀比于动物,只能助长人类的虚荣心,令人过高地评估自身,盲目乐观。
二
人作为一种生命,固然生存于地球、社会,具有自然性、社会性,但他更是生存于宇宙之中。宇宙包括了地球及其地表之上的人类社会,无论地球还是日月星辰,都包容在宇宙之中,因此可以说,地球哺育了人,社会塑造了人。人类除了自然性、社会性之外,还有宇宙性。这种特性甚至更为本源。如果仅仅研究自然性、社会性,而不去研究更内在的宇宙性,人性之谜是很难揭开的。
研究人的社会性是将人置于社会人系统之中,研究人的自然性是将人置于地球生命系统之中,研究人的宇宙性却是要将人放在更阔大的宇宙背景下,将人类置于宇宙生命系统之中加以对比研究。从理论上,我们可能懂得应在更大的生命系统之中认知人性,除了动物还应与高等生命相对照,但问题在于:科学上至今仍未发现其他宇宙生命,不说存在高等生命,即便微生物一类的低级生命也还未寻觅到。那么,在科学没有新突破之前,研究人性就不能涉及宇宙其他还未确证的生命,只能一味地同动物类比吗?回答是否定的。研究人性是从哲理思辨的角度设想宇宙生命的特性,并将人的特性与之比照,而非像科学那样去实证某种宇宙生命的存在。科学虽不能证实,但却可以建立假说、提出猜想,以促进人性的研究。事实上,当代生命学、天文学、飞碟学、哲学等学科的知识,已足以帮助我们建立宏观的宇宙生命学,由此及彼地描绘出宇宙生命所可能具有的共性。既然是生命,那么就应该具有一套与外界交流物质、交流信息的生命活动系统,并且具有某种欲求、智慧,具有或善或恶的道德观。道德、智慧、欲求,这应是宇宙生命的共同特性,而对待欲求的态度,则因生命道德、智慧的不同而显出极大的差异,这样就使宇宙生命呈现出诸多的层次。
宇宙生命系统简而言之,由神、人、兽、魔这四类不同量级的生命构成。如果在宇宙生命系统坐标示意图的纵向坐标上标出神、兽、魔三个层次,并定位其特性,则人性的本质就一目了然了。将人放在不同量级的宇宙生命之中比较,会发现人性实以兽性为基础。这里兽性不带贬义,兽性即动物性,即动物的一种天性,这种天性使动物为了生存而不断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在宇宙生命系统坐标示意图中,兽性位于纵向坐标的中间层次。人与动物相似,都有着一套维持生存的生理、情感系统,都有着物质性的肉体和感官,都要通过感官维持肉体的生存,获得情感的满足。
人在生物学中归属为: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人科、人属,撇开智慧不论,人与动物无异,都具有“食欲”和“情欲”。基本的生理欲望,在道德评判系统中应归为中性,不善也不恶。动物,包括人,无论到这个世界上目的是什么,都应生存下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物种的存在都是天经地义的,因此,生物基本的欲望也是天经地义的。适欲而不纵欲,这是一个符合天理的原则,做到这一点,这个人就不善也不恶。由于不能从中性的兽性出发考察人性,不理解“欲”,或混淆“适欲”与“纵欲”的界限,古代有些哲人曾提出过一些偏激的主张。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程颢、程颐曾提出“灭人欲、存天理”的口号,康有为则相反,在《大同书》中认为:“人生而有欲,天之性也。”认为追求享乐是人推动世界进化的原动力。他们的观点恰是两个极端,都没有很好地认识“欲望”的本质,只有领会人性之兽性为中性,方能不偏不倚。
节制欲望,使得人性在宇宙生命系统坐标示意图的纵向坐标上,由中性的兽性,趋向善性的体现——神性,反之,则趋向恶性的体现——魔性,如此,在纵向坐标上形成三个层次:神性居上,兽性居中,魔性居下。人性即是神性、兽性、魔性的共存体,此可谓人性的“三性共存理论”。
西方古谚说:人一半是魔鬼,一半是仙子;雨果认为人是二元的,人身上既有兽性,又有灵性;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认为,“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这些说法都看到了人性善恶并存,但却没有指出中性的兽性才是它们的源头。
三
事实上,用“神”和“魔”这样的词实出于无奈,因为人类的语言中很难找到相匹的用词。“神”和“魔”,姑且可以从科学假说,道德、智慧象征这个意义上去理解,而无须纠缠于神话、宗教中的含义。
在爱因斯坦看来,“神”是存在的,不过他没有作宗教式的理解,他认为宇宙明显地存在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远远超越于人类的精神,能力有限的人类在这一精神面前应感到渺小。他深信宇宙中存在着一种更高的思维力量,这就是他所理解的上帝,诸如此类的思想,在《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中可以找到许多。古代的荀子在《荀子·天论》中则说:“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爱因斯坦与荀子的意思相似,都觉得冥冥之中存在着宇宙大智慧,我们能看到他的成果,但看不到他的运作,更不要说形象了。在这里,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神”就是具有极高道德、极高智慧的高等宇宙生命,神性即是他们善的特性;“魔”就是道德沦丧、极其邪恶的低等宇宙生命,魔性即是它们恶的特性。神的概念要远高于圣贤、智者、人杰、君子之类,因为他们还都是人的境界,不可与神等量齐观。魔的概念也远甚于歹人、猛兽等。
“神”与“魔”即使在现实中也可能存在。因为判定神与魔,关键在于其本性,而不仅在于其形貌。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认为人的肉体是非本质的东西,人的本性在于人的心灵、理性和智慧。的确,一物之性理应由其本质决定而非由其外貌决定。对于生命体来说,道德是最本质的。评定生命的量级,生命体的道德水平是最重要的标准,神、人、兽、魔,即是根据这个标准划分的。智慧虽重要,却是第二位的,道德决定了智慧。苏格拉底曾提出“美德即知识”这个重要命题,认为没有道德和没有知识是同义语。《庄子·达生》中有一段文字形象地描绘了“利令智昏”的情状:“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惛。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则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庄子·大宗师》中还说:“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魔性太重必然淤塞智路,看不到真正的宇宙大道。
四
人确实具有用兽性都很难形容的魔性。野兽的屠戮是为了果腹、交配,而某些天良丧尽的人,会为了权欲、钱欲、色欲,甚至一言不合而害人,更有甚者,山珍海味吃腻之后,竟想到吃人。宋朝庄绰在《鸡肋篇》中记述了当时豪门巨族烹制小儿肉、女人肉的方法,真是触目惊心,无疑这就是一种魔行,用“兽行”远不够逼真生动。历史上大吃人肉者从原始土著到侵华日军层出不穷,不胜枚举。以形骸而论,人世间看不到魔,以行为特别是人心而论则不然。
在“阴阳、正邪、苦乐、生死”这组对立概念中,神性同于“阳、正、乐、生”,是宇宙生生不息的力量,可将人带入真正幸福的境界;而魔性同于“阴、邪、苦、死”,是宇宙毁灭消亡的力量。因此,道德对于人性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善和神性,不管人类多么聪明,建立起多么辉煌灿烂的文明,都可能在魔性的作用下,相互争斗、相互倾轧,使多年心血凝成的功业全部毁于一旦,甚至毁灭人类自身,即使不这么严重,勾心斗角,“他人为地狱”,也足以葬送人类的美好前程。
人的天性中都程度不同地潜伏着魔性,包括所谓善良的人。神性与魔性,乃是此长彼消的关系,魔性重必然抑制神性,使神性日益枯萎。人人都有魔性,这是因为人人都有肉体和感官,条件反射似地首先想到的总是自己。善行虽有,但许多是后天克制本能的结果,而且有许多善行实际上是“伪善”,利他的动机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己,“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老子语)。这种高超的计策,即便不甚智慧的俗辈都能运用自如。从善如流往往很难,正如“逆水行舟”;“以恶小而为之”却极易,稍不留神,就容易沦为欲望的奴隶。
从社会发展史也可看到魔性的步步进逼。远古时代,民风淳朴,人性处在兽性之上趋向神性的阶段,但是,自私的病毒一经扩散,就使得人类的处境每况愈下,从此,纷争迭起,民不聊生。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由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转向信息文明,由机械时代、电气时代进入电子时代,文明成果积累了一大堆,乐观之士信心百倍,纵情讴歌。可是,冷眼环顾这个世界,文明的“垃圾”也早已堆积如山,诸如生态失衡、空气污染、资源匮乏、生物灭绝,还有战争、凶杀、吸毒、走私、同性恋、爱滋病等等。
当代西方社会盛行的“文化批判”思潮,体现了人们对“文明危机”出路的积极探索,该思潮认为:现代人类与其说是苦于未能充分洞察客观世界的奥秘,还不如说是未能充分洞察人的内心生活的奥秘。这种理论启示我们应尽早对人性问题进行再认识,以便对人类的抉择作出裁判。在这里将人性视为神性、兽性、魔性的共存体,并强调魔性的破坏力,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加理智地重新反省自身。世界可以变得更美好,但前提首先须是优化人性,而优化人性,关键又在于:光大神性、节制兽性、灭绝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