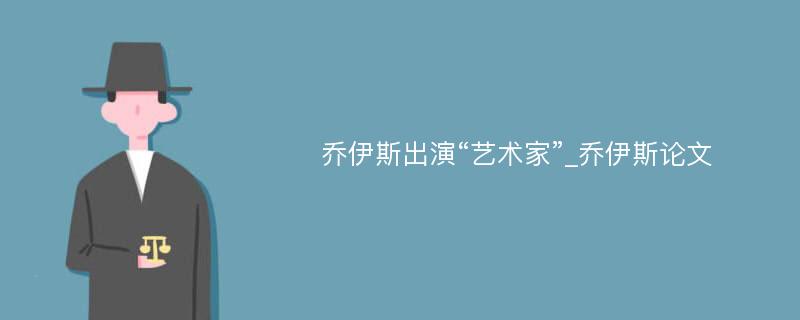
乔伊斯论“艺术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艺术家论文,乔伊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詹姆斯·乔伊斯少年时代笃信天主教,做过少年助祭,还梦想长大后能当上神父。但到青年时期,他叛了教,放弃了所学专业——三次学医、一次学法律、一次学音乐,成长为独立不羁的自由艺术家。这一人生选择所引起的精神裂变过程,在“成长小说”、也是成名作《艺术家青年时期的画像》(1916)中自传性人物斯蒂芬·代达勒斯身上,得到了最集中的表现。学术界已发现詹姆斯·乔伊斯有“恋母情结”①和“莎士比亚情结”②。本文认为,他还有驱之不散的“艺术家情结”:终其一生,他都纠结在对艺术家身份选择、艺术家本质属性、艺术家天赋修养、艺术家人格命运、艺术家职责义务等问题的痛苦思考之中。代表作《尤利西斯》(1922)运用“人物再现法”,让基本定型化了的人物斯蒂芬·代达勒斯再度出现,继续展示作家本人青年时期的成长经历及其对于艺术家与环境之间的冲突、艺术家与其笔下的人物之间关系等问题的深入思考。在最后一部小说《芬尼根的觉醒》(1939)中,主人公伊尔威克的儿子森仍是一个自传性人物,他同斯蒂芬·代达勒斯十分相似。
除上述三部主要作品之外,早期小说《斯蒂芬英雄》(1944,《艺术家青年时期的画像》初稿)集中探讨了有关艺术家的美学理论。这两部自传性小说实际上是艺术家乔伊斯的心灵成长史:青少年时代,他是一个英雄;到了成年阶段,他成为艺术家。对于“何谓艺术家?”“何谓艺术?”的思考,是这两部小说的主要写作目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1914)中“一朵小小的云”描写了青年诗人小钱德勒在呆板琐碎、毫无情趣的生活环境里的烦恼、向往、梦想、羞愧和无奈;“死者”是乔伊斯的第一首流亡之歌,他在内心已经认定飞离爱尔兰合情合理,只不过还未确定方向。乔伊斯唯一的剧本《流亡者》(1918)也是一部自传性很强的作品,它反映了艺术家所面临的来自社会的和心理的困境。诗歌“异端裁判所”(1904)讽刺了当时爱尔兰许多作家诗人,并将自己赞许为履行“净化清洗”义务的艺术家,一位有着撒旦式的高贵灵魂和巨大精神力量、在老阿奎那学派中百炼成钢、桀骜不群的今世英雄;“火炉冒出的煤气”(1912)摹仿18世纪爱尔兰著名作家斯威夫特的讽刺口吻,严厉谴责了爱尔兰的社会腐败和道德瘫痪,并把自己和巴涅尔做了直接了当的对比,悲愤地指出了艺术家必遭流放的命运;在“艺术家作为老水手的画像”(1932)中,乔伊斯把自己——“一位苍老的文抄公”喻为历经磨难的“老水手”,控诉了《尤利西斯》的遭遇,其中有许多关于金钱时代和英美出版法造成艺术家作品出版之艰难的“典故”。可见,“艺术家”是其作品永恒的主题和不朽的主人公之一。
此外,乔伊斯还写了“戏剧与生活”(1900)、“易卜生的新戏剧”(1900)、“乌合之众的时代”(1901)、“詹姆斯·卡拉伦斯·曼根”(1902)、“詹姆斯·卡拉伦斯·曼根”【2】(1907)、“奥斯卡·王尔德:《莎乐美》的诗人”(1909)、“威廉·布莱克”(1912)等评论文章来阐明了对“艺术家”问题的理论思考。他的书信也谈到了艺术家人格和职责问题。在成长为艺术家之前,乔伊斯心目中的艺术家楷模有代达勒斯、但丁、莎士比亚、易卜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在早期文论中,他还盛赞了王尔德、梅瑞狄斯、萧伯纳、曼根、布莱克等具有想象力、独创性、叛逆性的作家和诗人。诚如著名的乔伊斯传记作家理查德·艾尔曼所说:“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已经按照一个人为的模式完成了自身的孕育,因而成了他自己的母亲,他对此显然感到很满意。这种情况的复杂性,从斯蒂芬的一个想法中可见一斑,他认为自己不是他父母的亲生儿而只是他们的养子”(艾尔曼339)。这说明,艺术家只有创造了自己,才能创造艺术。本文旨在探讨乔伊斯有关“艺术家”的观点。
一
西方的“摹仿说”认为,艺术是对自然的摹仿,作家、艺术家就是“摹仿者”。赫拉克利特、德谟克里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后世许多文艺理论家、艺术家都持这种观点。回顾18世纪以前的英国文艺批评史,可以发现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在英国古典文论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18世纪以后,艺术“摹仿说”受到冲击,特别是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中叶浪漫派对“摹仿说”的批驳中,人们普遍强调艺术的想象与创造的本质,强调艺术家、诗人作为“创造者”的主体地位,艺术家就是“创造者”的观点不断为后人所重申。
乔伊斯对艺术家主体的认识经历了从“摹仿者”向“创造者”的转变。他认为艺术家的本质属性就是自由、创造。大学期间,他开始自觉地、也是理所当然地从西方哲学美学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那里接受文艺美学思想并作了大胆的修改和补充。在“巴黎日记”中,针对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的主要观点——“艺术是对自然的摹仿”,乔伊斯作了这样的解释:“亚里士多德在此并未给艺术下定义,他只是说:‘艺术摹仿自然’,即艺术的过程好像是一种自然的过程一样……”(Joyce,"Aesthetics"145)在此阶段,初学者乔伊斯并没有否定艺术的摹仿特点,但他认为艺术的过程也是一种自然的过程,这就肯定了艺术的真实、自然、创造的本质特征。在“乌合之众的时代”一文中,他虽然肯定“穆尔先生有了不起的摹仿能力”,但认为“马丁先生和穆尔先生不是具有独创精神的作家”(Joyce,"The Day of Rabblement"71)。在乔伊斯给艺术所下的定义“艺术是出于某种美学的目的对可感觉的或可理解的事物的人工处理”(Joyce,"Aesthetics"145)中,“出于某种美学的目的”、“人工处理”也强调了艺术家主体合目的性的自由创造精神。这与他借用福楼拜的说法、在“非人格化”原理中把艺术家视为创造的上帝的观点一脉相承。这个创造者不仅是男性的,也是女性的,她也是女神,在她的子宫内,创造物获得了生命。正如斯蒂芬所说,“在想象的处女子宫中,词语有了血肉之躯。天使长加布里埃尔已经来到了这个处女(指圣母玛利亚,笔者注)的闺房”(Joyce,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245)。在《尤利西斯》第九章中,斯蒂芬进一步发展了关于艺术创作的这种隐喻和神秘性理论。
在小说中,乔伊斯还通过《艺术家青年时期的画像》卷首语、主人公斯蒂芬·代达勒斯的姓氏“代达勒斯”,以神话类比象征暗示了艺术家自由、创造的本质属性。艺术家是一个天生的创造者,他创造,而不仅仅是反映现实。《艺术家青年时期的画像》的卷首语“他将致力于那晦涩的艺术”(Et ignotas animum dimittit in artes)③是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变形记》(Metamorphoses)中的诗句,乔伊斯以此暗示了小说的主题,也暗示了他将以此作为自己一生创作的座右铭。这句引语中的“他”指神话传说中的希腊建筑师、雕刻家和发明家代达罗斯(Daedalus)。“代达勒斯”这个姓氏本身就是自由反叛的艺术家家族的象征。斯蒂芬从飞鸟的形象中获得了精神顿悟:他不但拥有代达勒斯的姓氏,而且拥有这个姓氏所肩负的使命;若要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他必须像神话典故中的代达勒斯一样展翅飞出迷宫,“去生活、去犯错、去跌倒、去胜利,去从生命中再创生命!”(Joyce,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198)“他的灵魂已经从儿童时期的坟墓中重新站了起来,抛掉了身上的尸衣。是的!是的!是的!像那位跟他同姓的伟大工匠一样,凭着灵魂的自由与力量,他将自豪地创造出一个崭新的、飞翔的、美丽的、神秘莫测的、活力永驻的生命”(Joyce,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196)。他“身上的尸衣”包括民族的、宗教的、家庭的网,他的复活是艺术家的复活,而不是神的起死回生。“欢迎你啊,生活!我要一百万次地去面对生活经验的真实,在我心灵的作坊里锻造出我的家族未曾创造的良心”(Joyce,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282)。“我的家族”(my race)指代的不是爱尔兰,而是艺术家的家族,他们的成员以追求自由为第一生命。所谓自由,既包括艺术家灵魂的自由,也包括艺术表现形式的自由。围绕着自由创造这一主题,乔伊斯运用了一系列主题象征,如:鸟、牛、水、女人、绿玫瑰等,使它们在潜在的艺术家斯蒂芬的认识、思考和想象中产生变形,直到产生一系列的灵悟。这也是乔伊斯认识和发现艺术家的本质的“灵悟”。他呼唤着这位创造神,祈求力量、信心和启示:“老父亲,古老的巧匠,现在请尽量给我一切帮助吧”(Joyce,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282)。1952年,理查德·艾尔曼在开始创作传记《詹姆斯·乔伊斯》(1959)时,曾用“The Hawklike Man”(《像鹰一样的男人》)作为该书最初的题目,可见在艾尔曼心目中,乔伊斯就是新时代的代达勒斯,是现代艺术家的代表。
“斯蒂芬·代达勒斯”这个姓名借用了基督教首位殉教者斯蒂芬和异教最伟大的发明者代达勒斯的名字。乔伊斯以此暗示斯蒂芬、也就是他自己将成为殉艺术之道的“文学圣人”,实践其艺术人生和艺术救世的主张。像易卜生那样,他已经“建立起一种没有上帝的艺术神学”(莱恩78)。他说:“我的思想摒弃当前的全部社会秩序和基督教教义——家庭,公认的美德,生活的等级,宗教的教义。…现在我用自己的作品和言行对它公开作战”(Ellmann 25)。为了充当文学的神父,“把日常经验的糕饼变成永恒闪烁的圣体”(Joyce,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249),他用缪斯替代了圣母,用“实用阿奎那美学”替代了神学,用艺术创造的“启示”或“灵悟”替代了宗教的“显圣”。事实上,正如纪德所说,乔伊斯能不顾一切地把文学实验推到极端,不计成败,不计金钱,这中间确实有一种圣徒精神。这也是一种时代精神。在19、20世纪的英国,强调艺术的神圣性、视诗或小说为宗教的人,除乔伊斯之外,还有阿诺德、王尔德、T·S·艾略特、利维斯、瑞恰兹等。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代思想家和艺术家们普遍表达了对技术世界的批判和对现代人精神荒原的不满,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期待的目光转向了诗性的拯救,要求诗人肩负起对抗技术意志甚至拯救人类精神的使命。④海德格尔的诗人奉“天命”而作,荣格的诗人为“集体无意识”而歌,萨特的“文学介入论”,都强调了“艺术的拯救”,高歌了诗人作为一个类属、一个群体存在的伟大。
二
乔伊斯是“一位具有独创精神和成熟见解的天才人物”(Magalaner and Kain 55),被誉为“20世纪文学创作的奇才”。他很强调艺术天赋的重要性。尽管他认为莎士比亚属于“对话体文学”的诗剧应该归入文学的“古董店”了,但还是充分肯定“莎士比亚首先是一位文学艺术家——幽默、雄辩,有着最高天使给他的安详恬逸的音乐才能以及戏剧天性——他拥有丰富的天赋”(Joyce,"Drama and Life"39)。他非常喜欢乔治·梅瑞狄斯富有哲理性的小说,但在评论道格拉斯·杰罗尔德的《乔治·梅瑞狄斯》时,他直言不讳地说:“他的大部分小说没有史诗艺术价值,梅瑞狄斯没有史诗艺术家的天赋”(Joyce,"George Meredith"89)。
在乔伊斯笔下,斯蒂芬从小就表现出艺术上的天赋:敏锐的感觉、丰富的想象力、灵悟、创造力和内省的性格。“他(指斯蒂芬,笔者注)想象,艺术家是处于经验的世界和梦想世界之间的调解人,因此,这位调解人具有两种才能,一种是选择的才能,一种是再生产的才能。平均使用这两种才能是艺术家的成功之谜:这位艺术家,如果他能让其人物微妙的灵魂完全摆脱环境的制约,而在艺术家所选定的最严格的新环境中得到再现,他就是一位卓越的艺术家”(Joyce,Stephen Hero 73)。“经验的世界”即艺术家以敏锐的感觉感知到的现象世界;“梦想世界”却是超凡的想象力的产物;“选择的才能”即对创作材料的处理才能;“再生产的才能”即艺术创造才能。在艺术创造中,“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想象是创造性的”(黑格尔357)。乔伊斯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说,“诗人是他所处时代生活的强烈的中心,没有任何其他关系会比他与时代的关系更重要。他独自就能吸收他周围的生活并且能在星际音乐声中将之自由地挥洒”(Joyce,Stephen Hero 75)。所谓“在星际音乐声中将之自由地挥洒”指的就是艺术家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艺术家不是那种在公众面前摇摆于机械的天堂的人,牧师才那样。艺术家声称他脱离自己的全部生活之外,他创造……”(Joyce,Stephen Hero 80)。艺术家是“一个宣扬永恒的想象力的牧师,一个能够把每天普通生活上的经历变作具有永生生命的光辉形体的牧师”(Joyce,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249)。在“詹姆斯·卡拉伦斯·曼根”中,乔伊斯发展一种想象理论并试图找到爱尔兰艺术家所必须的东西,提倡把古典的力量、宁静与强烈的浪漫主义的想象融合起来。
“灵悟美学”最初出现在手稿《斯蒂芬英雄》中。对于年轻的知识分子斯蒂芬·代达勒斯而言,“思索是体验世界的一种模式”(萨义德21)。“所谓灵悟(epiphany),就是思索中突然的精神感悟。不管是通俗的言词,还是平常的手势,或是一种值得记忆的心境,都可以引发灵悟。斯蒂芬认为,作家应该极其小心地记录下这些灵悟现象,并且意识到这些现象虽然微妙,但是却稍纵即逝”(Joyce,Stephen Hero 188)。在《艺术家青年时期的画像》中,斯蒂芬将灵悟与阿奎那的审美三阶段学说关联起来(Noon 62-72),指出第三阶段——闪烁阶段(Radiance)就是灵悟,主体在此阶段从审美中介物中悟出了“事物的真谛”(the whatness of a thing)。(Joyce,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239-241)有学者认为,该理论是理解艺术家乔伊斯的中心问题,其所有成功之作似乎都可以看作是对这一理论的图解、强化和扩展。⑤灵悟即艺术家天赋的悟性和表现能力,是审美感知力、通达真理的能力和艺术升华能力的瞬间的集合体,它能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美并揭示潜在的真义。
艺术天赋固然重要,后天的努力也是艺术家成功的必要条件。天才具有自然禀赋,也具有社会属性。乔伊斯对“天才”的理解与康德“艺术家”论中的“天才”思想是一致的。潜在的艺术家斯蒂芬曾劝导自己,“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如果他希望完全地表达甚至于最简单的概念,必须不停地致力于其艺术工作;他相信在每个灵感瞬间出现之前必须先付出艰辛;他不能确信‘诗人是天生的,不是被创造的’这句格言是真理,但完全确信‘诗是被创造的,不是天生的’至少是真理”(Joyce,Stephen Hero 34)。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强调作家的个人才能应与“伟大的传统”紧密联系的英美批评家有T·S·艾略特、F·R·利维斯、W·C·威廉斯、哈罗德·布卢姆等。其实,乔伊斯在文论中也谈到了艺术家与人类文化知识和艺术传统规则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说:“最后必须问及每一个艺术家是如何与那些被人和时间遗忘、但仍发挥效用的最高的知识和永久的原则相连的。这不是为了寻找某种启示,而是为了探索创作倾向,……探索已有的艺术创作倾向是一种受尊敬的行为,许多传统手法首先必须被取消,因为可以确定,最深层的领域决不会产生渎神的艺术家”(Joyce,"James Clarence Mangan"75)。所谓“最高的知识”即哲学,真理;而“永久的原则”即艺术创作永恒不变的法则;“最深层的领域”指的是艺术自律的王国。
此外,乔伊斯还非常崇尚艺术的神圣性、神秘美、智性美,非常关注艺术家与神秘主义、艺术家与智慧之间的关系。与弥尔顿相似,他也是一个注重内省、敏感执着的学者。青年时期,他兴味盎然地购买并阅读了大量有关东方神秘主义和神智学方面的书,这个兴趣也曾激发了19世纪末的欧洲和美国。在“威廉·布莱克”一文中,乔伊斯肯定布莱克“属于艺术家的类型,我认为他在这一类型中拥有一个独特的位置,因为他把智者的敏锐和神秘主义的感觉结合了起来”(Joyce,"William Blake"221)。“乔伊斯是一部百科全书”,是“学者型作家”,引领了20世纪小说的评论化和作家的博学化倾向,其艺术成就堪与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的科学成就相媲美。
三
乔伊斯认为,“孤立是艺术家组织的第一原则”(Joyce,Stephen Hero 34)。在早年阶段,他“杀死”了生物学上的父亲(biological father)和上帝父亲(Father God)——爱尔兰文化中并行不悖的两个要素,有意选择了现在或过去一些具有艺术家英雄气概的人,如易卜生、拜伦、尼采等,作为自己精神上的“父亲”——“超我”人格追求。
挪威戏剧大师易卜生是乔伊斯最早找到的、终生崇拜的偶像。乔伊斯非常钦佩易卜生诚实到几乎否定自己的程度,赞赏易卜生客观中立的立场,崇尚易卜生独立不移、沉静高贵的人格力量,他认为易卜生“不需要辩护师和批评家”(Joyce,Stephen Hero 41)。在“易卜生的新戏剧”中,乔伊斯高度赞扬了易卜生的孤傲、沉默。他说,“如果要问谁那样坚定地统治了现代思想界,不是卢梭,不是爱默生,不是卡莱尔,不是任何超出了人类知识范围的伟大的人物,而是易卜生,易卜生以他的沉默极大地提高了他对两代人的影响力。他很少与自己的对手论战,看来论战的强烈风暴难得冲击他那美妙的平静。那些彼此矛盾的声音丝毫没有影响他的作品”(James Joyce,"Ibsen's New Drama"48)。乔伊斯特别欣赏易卜生那种“对公认的艺术经典决不理睬”(Ellmann 7)的态度以及走自己的道路的英雄气概,而他自己则认为,“在判定艺术家时,不能忽视他本人的原则,因为没有比按照诗学的最高原则来判定某个艺术家更是一个普遍的错误了”(Joyce,"James Clarence Mangan" 75),“独创的、有才华的作家颠覆不属于自己的形式”(Joyce,"Catilina"101),其孤傲绝俗、独辟蹊径的态度,和易卜生如出一辙。
受当时欧洲兴起的易卜生的反群氓思想、尼采的超人哲学以及欧洲传统文化中的精英思想影响,乔伊斯青年时期对民间文化、社会群体持鄙视态度,认为民众不过是一群愚昧冲动、没有主见的乌合之众。“乌合之众的时代”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不厌恶大众,一个人就不可能热爱真理或善;艺术家虽然可以利用民众,却与民众保持距离。这种艺术自律的激进原则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尤为重要”(Joyce,"The Day of the Rabblement"69)。这篇文章最为集中地谈到了艺术家与大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这样的艺术家就是“具有易卜生特性的人”(Ibsenite),孤独、自信、勇敢、道德意识超前、极具叛逆性。为此,他在《斯蒂芬英雄》、《艺术家青年时期的肖像》、《尤利西斯》三部作品中,连续塑造了同类自传性英雄斯蒂芬·代达勒斯。在《斯蒂芬英雄》中,他甚至把自己塑造得近乎于偶像。《艺术家青年时期的画像》淡化了斯蒂芬的“英雄”色彩,但斯蒂芬仍然是以闷屋子中唯一的清醒者形象出现的,唯有他一人在对爱尔兰传统的宗教、政治、道德乃至艺术观念进行反思。到了《尤利西斯》中,“布卢姆的‘一切主义’与斯蒂芬的‘虚无主义’的呼喊正成对比”(Brown 89)。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乔伊斯就视自己是一位反叛都柏林肮脏丑陋和市侩风气的叛逆者。在他当时的世界观里,艺术家始终是一个为社会所不容的逐客,命定地要过一种流亡生活。不过他认为,“艺术家并不需要从他的户主那里要求一张特别通行证以进入这种或那种时尚,每个时代都必须为它的诗人和哲学家寻找自己的支持”(Joyce,Stephen Hero 75)。他认为,这个时代的支持在欧洲大陆。这种自愿流亡并非意味着逃避现实、孤立和自我主义。对于流亡生活,乔伊斯甚至有自己的“流亡美学”,认为要想成为一位艺术大师,其先决条件就是过流亡生活。他固执地保持一种流亡身份,一是为了惩罚他自己和他的国家;二是一种超越和扩张的策略,人生更大的舞台可以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法国、意大利、英国等欧洲先进国家的中心城市,可以吸取最新、最丰富、最深厚的文化滋养,加入到欧洲艺术家阵营中,并与欧洲文学传统紧密地衔接起来;三是一种萨义德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形而上的流亡”(metaphysical exile),即精神流亡。(萨义德50)流亡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状态,代表着知识分子的良心。流亡的知识分子(exilic intellectual)不但不会与祖国失去联系,反而会更深切地关注民族命运,但关注的方式不是赞美,而是激进的否定与批判。萨义德认为斯蒂芬·代达勒斯是“殖民环境的产物,所以必须先发展出一种知识分子的抗拒意识(a resistant intellectual consciousness),才能成为艺术家”(萨义德21)。我们在读乔伊斯的小说时,确实是在体验一个萨义德意义上的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那不断成熟的自由意识和对任何意识形态规则的批判与疏离,而这一切又全部表现在他对爱尔兰历史的阐释、反思和批判过程中。在民族性和世界性关系问题上,乔伊斯认为,“他们(指各国的文学巨匠)都是先有民族性的。正是因为他们有强烈的民族性,他们才最终成为国际性的作家,……至于我自己呢,我是永远写都柏林的,因为只要我能抓住都柏林的心,我就抓住了世界上一切城市的心。个别之中蕴藏着普遍”(艾尔曼570)。
乔伊斯心目中的流亡艺术家榜样除了易卜生之外,还有但丁、王尔德等。乔伊斯在王尔德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因此,他对王尔德的评论大有惺惺相惜的味道。乔伊斯把王尔德看作佯狂傲世的天才,一个声名狼藉的流亡者,一个典型的被人出卖的艺术家,世人眼里的撒旦,而实则是一个替罪羊,一个受难的基督(Joyce,"Oscar Wilde:The Poet of‘Salomé’"201-204)。
乔伊斯早年最喜欢的英雄有信奉异教的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尤利西斯,他心中圣坛上还供奉着另外两位伟人,一位是天主教教义中的魔鬼撒旦,另一位是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领袖巴涅尔,这三者在许多方面都迥然不同,却在他心中合而为一,奠定了他未来叛逆的倾向。为了寻求认可和支持,他研究的不是圣方济格,而是异端创始人乔基姆·阿巴斯、布鲁诺和迈克尔·森迪沃格斯。他读过的书有两类可以借鉴:宗教的叛逆和造反的艺术家,他把二者糅合到了一起。一段时期,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美国无政府主义者本杰明·达克尔的理论对他产生了吸引力。后来,他又迷上了尼采。当乔伊斯向他的朋友解释一种新异教主义时,很有可能借用了尼采的思想。从尼采那里,乔伊斯认识了一种新的异教,懂得了礼赞自私、放纵和无情,也学会了摒弃感恩和其他“仆从的优点”。
四
在《艺术家青年时期的画像》结尾部分,斯蒂芬宣称:“我决不会为我不再信仰的事业去效力,即使它自称是我的家庭、我的祖国或是我的教堂。我将以某种生活方式或艺术形式来自由地、充分地表达我自己,并将使用我允许自己使用的唯一武器来保护自己——沉默、流亡和机智”(Joyce,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275)。“欢迎你啊,生活!我要一百万次地去面对生活经验的真实,在我心灵的作坊里锻造出我的家族未曾创造的良心”(Joyce,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282)。1912年8月22日,乔伊斯在书信中曾对妻子诺拉说:“我是这一代也许最终能从我们这个糟糕的民族的灵魂中制造良心的作家之一”(Manganiello 217-218)。1936年初在与艾尔弗雷德·克尔的谈话中,他对易卜生高度评价道:“我钦佩易卜生,正是为了这两个原因:他的道德高尚,不仅在于他能公开宣布他的伦理理想,而更在于他竭尽全力创造完美的艺术作品”(艾尔曼776)综上所述,再结合《艺术家青年时期的画像》题记和乔伊斯的创作实践,我们可知乔伊斯把艺术家的职责义务确立为表现自我、锻造良心、追求形式完美。
乔伊斯作品的自传性很强,其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是“自我”。乔伊斯认为,小说家的任务就是真实地呈现平凡人物的精神世界。早期小说《都柏林人》充分展示了乔伊斯对于爱尔兰“瘫痪”现实的感觉印象和自我疏离状态,已经出现逃避的主题。《艺术家青年时期的画像》既是一部“青春小说”,也是一部自传性很强的“发展小说”,它着力描写了艺术家青年时期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不断发现自我、逐渐走向成熟的心理成长过程以及他对自己艺术家天职和使命的不断认识过程。《尤利西斯》尽管在形式上非常新颖、独到,但本质上仍属于“自白文学”一类,具有鲜明的自传性,它是乔伊斯的自白,是一本以真诚、机智写就的自传性作品。T·S·艾略特1923年11月发表于《日晷》上的“《尤利西斯》、秩序和神话”一文也充分肯定了乔伊斯对当代生活的自我书写方式,他说:“我认为这本书将会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自我)表达;我们所有的人都受惠于它,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逃避它的影响”(Eliot 198)。其实,乔伊斯的四部小说已经构成了一部巨著,既是史诗,又是自传,对他这样一位要用艺术打造新的民族良心的艺术家来说,构造史诗的过程就是历史批判的过程,也是心路历程的真实记录,这在小说中较多地反映在斯蒂芬身上。关于这一点,乔伊斯自己也说过:“《画像》是我的精神自我的写照。《尤利西斯》把个人的印象和情感加以变形,使其获得普遍意义。《正在进行中的作品》的涵义彻底脱离具体存在,超越人物、事件和场景,进入纯抽象的领域”(Potts 132)。乔伊斯的“自我论”与现代艺术表现论相吻合。
需要指出的是,乔伊斯受福楼拜、易卜生的“非人格化美学”影响,强调文学的象征主义和戏剧化原则,反对艺术家介入作品,或使作品感情化、个性化。他认为,作家是“隐匿的上帝”,既应该表现自我,也应该摒弃自我,其书写自我的方式应该是客观、中立的。1900年,在著名的艺术宣言“戏剧与生活”中,乔伊斯说,“艺术家应该扬弃自我,在蒙着面纱的天主面前,在亘古不变的真理面前,保持中立”(Joyce,"Drama and Life" 42)。他甚至把圣奥古斯丁的一句话“无所顾虑的世界自会评判”(Securus judicat orbis terrarum)⑥用到了艺术上,认为艺术家的责任,不是去追求合乎什么宗教道德,表现美丽或理想,而是应该以真实客观地表现为基本法则。1903年在论述易卜生的剧本《凯蒂琳》时,他又强调:“戏剧家必须更加记住一条,所有完美持久的艺术原则,就是以人物自己的语言来表述他的故事”(Joyce,"Catilina"100)。在《艺术家青年时期的画像》中,他虽然把艺术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划分为抒情的、史诗的、戏剧的三种形式,但他本人更倾向于易卜生所倡导的戏剧形式,认为审美创造主体应将自我人格渗入到艺术形象中去,在形象的产生过程中让自我消失。他借斯蒂芬之口提出了自己的“非人格化”原理:“艺术家的人格起初不过是一声呐喊,一种节奏或一种情绪,接着它变成了流动的闪烁着光辉的叙述,最后使自己升华,失去了存在……使自己非人格化了。……一个艺术家,和创造万物的上帝一样,永远停留在他的艺术作品之内、之后或之外,人们看不见他,他已使自己升华而失去了存在,毫不在意,在一旁修剪着自己的指甲”(Joyce,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242)。F·杰姆逊认为,《尤利西斯》采用的是“根本的非人格化,或者说,乔伊斯完成了福楼拜的把作者排除出文本的构想”(Jameson136)。乔伊斯在小说叙事领域的“非人格化美学”与同时代的艾略特在诗歌表现领域的“非人格化美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乔伊斯终生致力于“晦涩的艺术”,竭尽全力创造完美的艺术作品。但他并非形式主义者,受唯美主义、英美新批评和俄国形式主义形式观的影响,乔伊斯认为,“形式即内容,内容即形式”(Beckett 14),内容必须通过相应的形式来表现,而形式也应该具有真实性和表意功能,只有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才是完美的艺术作品。其意识流手法的大量运用与他要表现人物的潜意识心理相对应,而小说的狂欢化是以混乱无序的形式和“狂欢式的笑”来表现维柯所说的“混乱时代”的内容,表现当代人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实现了荒诞的形式与荒诞的内容的完美统一。乔伊斯的“形式美学”与他早期的“和谐美学”和中后期的“混沌美学”思想密切相关,也与他早期的“喜剧美学”思想有关。在“巴黎日记”(1903/1904)中,他对亚里斯多德的戏剧美学思想进行了大胆的修改,提升了喜剧的地位,认为“悲剧是一种不够完美的艺术形式,而喜剧则是一种完美的艺术形式”(Joyce,"Aesthetics"144)。
乔伊斯的“艺术家”论在现代艺术家论中处于先导地位,他为20世纪的艺术家们找到了作家的学者化等新的时代标准并确立了自由不羁的主体创造精神。
注释:
①乔伊斯的“恋母情结”主要表现在他笔下两个自传性人物斯蒂芬和布卢姆身上。
②参阅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331。
③译成英语即“And he sets his mind to work upon unknown arts”,该卷首语引自奥维德的《变形记》第8卷,第188行。See James Joyce,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New York & London:Garland Publishing,Inc.1993)23.
④参阅刁克利:“诗性的拯救与诗人的弱小——一个关于现代诗人的悖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6(2003):105-111。
⑤See "Introduction to the First Edition." Stephen Hero(Grafton Books,1977)11-21.
⑥"Untroubled,the world judges." St.Augustine.Contra Epistolam Parmeniani,III.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