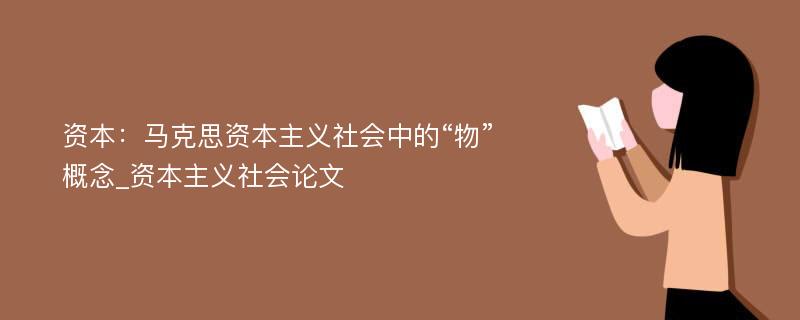
资本:马克思资本主义社会中“物”的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资本主义社会论文,资本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幽灵,一个资本的幽灵,在全世界游荡。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和灵魂,资本成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幽灵般的现实性”存在,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物”的最集中代表。“物不只是我们制造的产品,设计来帮助我们满足基本的本能需求,物也是我们籍以表现我们是谁及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的表达方式,而这也是形塑社会进展的要素。”①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完全符合“物”的这一本性。马克思强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而在政治经济学中,抓住资本是不二法门。抓住资本也就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进而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作为“资本之谜”的解答,马克思希望通过《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捉住资本这一“怪物”,变“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为“活动着的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因此,我们有理由说“资本”就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物”的概念。 一、物:“商品”与“货币” 马克思一生所关注的,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无情的解剖和批判。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和批判,既不是从抽象的“物质”出发——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物,对人来说也是无;也不是从抽象的“精神”出发——“无人身的理性”只是对物进行概念的、逻辑的和思辨的表达;而是具体地关注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里现实的“物”——商品、货币和资本。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认为“物”是由“质料”和“形式”两方面构成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强调每一种“有用物”,都可以从“实体内容”和“形式规定”两个方面来考察。马克思对“物”的分析和追问,不仅仅依赖于“物”本身,而且深入到构成“物”得以表象出来的“结构”之中去。对此,海德格尔曾指出:现今的“哲学”误解了这个时代的两重独特现实——“经济发展”与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马克思却懂得这“双重现实”。②正是在充分抓住和运用这一“双重现实”的基础上,马克思深入而透彻地把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物与物”背后所隐藏着的“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最终实现了由“物”观“人”的根本革命。 但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物的这两方面的规定性却时常是分离的。而人们在理解和把握物时,也时常只看到物的“实体内容”而看不到或忽视了其“形式规定”。虽然亚里士多德较早就发现了物(商品)的“形式规定”(价值形式),正是在这里闪耀出他“天才的光辉”(马克思语)。但由于亚里士多德所处社会的历史限制,使他不能发现这种“形式”实际上是什么。所以马克思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③因此,要想真正理解和把握事物本身,就必须从实体内容与形式规定两方面的关联和统一入手。对此,葛兰西强调:“物质不应当从它在自然科学中获得的意义上去理解……也不应当从各种唯物主义形而上学中发现的任何意义上去理解。虽然人们可以考察构成物质本身的各种物理的(化学的、机械的等等)属性,但只是在它们成为生产的‘经济要素’的范围之内。所以,不应当就物质自身来考察物质,而必须把它作为社会地、历史地组织起来的东西加以考察”。④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正是把他所关注的“物”放到一定的社会历史关系中加以考察的。我们完全可以说,“物”的关注视角在马克思这里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从一直重视的“实体性”和“主体性”转向了“社会性”。甚至应该说,马克思“物”论的贡献恰恰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着重思考了物的“社会性奥秘”,从社会性(而不仅仅是实体性或主体性)的角度阐释了物。⑤也因此,在理解和把握物时,物的社会性的“形式规定”比其自然性的“实体内容”更具关键性。而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物”的理解和把握,就是在把握到其自然性的“实体内容”的基础上,更看重其社会性的“形式规定”。 在马克思这里,对资本主义社会“物”的把握,是从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细胞”的“商品”入手,再上升到“货币”,最后归结为“资本”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开始就是以“商品”表现出来的。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⑥因此,《资本论》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而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但商品这个“物”又不是普通的物,而是具有“神秘性”的“物”:“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为此,马克思还以木头做成桌子为例进行了形象地说明:“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物。但是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转化为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⑦针对资本主义社会里作为物的商品的此种“之怪现状”,马克思追问的是:劳动产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不是来源于商品的物质内容——自然规定性,而是来源于商品的形式规定——社会关系本身。对此,马克思指出:“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虽然看上去不过是个“生产物”,也不过是个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但只要仔细去看即可得知,它居然是超越人的意志而行动,最终还直接拘束人的一种“观念形态”。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思的伟大:在最平凡、最单纯不过的“可感觉物”——商品身上却发现了“超感觉物”——“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马克思有如此眼光,其实早已不是所谓“经济学家”能够具有的。⑨任何经济学家——倒不如说恰恰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才把商品仅仅看作自明而又单纯、普通而又平凡的东西,从而随便草草打发了事。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商品,由于其“形式规定”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而具有了神秘性,就是作为商品世界的“完成的形式”——货币,也依然由于其“形式规定”而充满了谜一般的神秘性:货币“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⑩对此,马克思强调:“货币主义的幻觉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由于货币主义没有看出:金银作为货币代表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不过这种关系采取了一种具有奇特的社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11)但古典经济学家却只看到使货币成为“可感觉物”的“物质内容”,而忽视了使其成为“超感觉物”的“形式规定”。“谁都知道——即使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商品具有同它们使用价值的五光十色的自然形式成鲜明对照的、共同的价值形式,即货币形式。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做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就是说,探讨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这样,货币的谜就会随着消失。”(12)为此,马克思批评:“货币主义的一切错觉的根源,就在于看不出货币代表着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却又采取了具有一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嘲笑货币主义错觉的现代经济学家,一到处理比较高级的经济范畴如资本的时候,就陷入同样的错觉。他们刚想笨拙地断定是物的东西,突然表现为社会关系,他们刚刚确定为社会关系的东西,却又表现为物来嘲弄他们”。(13)所以马克思强调:“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14)可见,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这里,不论是商品还是货币,其真正本质都被其“物质性外观”所掩盖和迷惑。 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下,不是由于物所具有的“物质性外观”,而是其特殊的“形式规定”,使物本有的“诗意的感性光辉”消失了,物变得越来越神秘了,变得越来越抽象了,变得越来越敌视人了。而这一“神秘物”的最全面、最集中、最深刻的代表,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里占统治和支配地位的“资本”。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强调要想真正把握资本,就不能仅停留于其“物质性外观”,而是必须从分析“经济形式”入手,而“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5)这一“抽象力”,在马克思这里就是批判性与实证性相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正是充分运用这一“批判”,才理解和把握了资本这一“幽灵般现实性”的怪物。 二、资本:一个“幽灵般现实性”的怪物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虽然表现为庞大的商品、甚至货币,但商品和货币最终都走向和归结为具有“幽灵般现实性”的资本。资本是支撑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大厦的“座架”,是揭开现代社会秘密的一把“钥匙”。在历史上,资本最初也是以“可感物”的面目出现的。最早在中世纪的拉丁文中,“资本”(capital)这个词似乎指的是牛或其他家畜。家畜一直是额外财富的重要来源,圈养家畜的成本十分低廉;家畜可以活动,能够从有危险的地方转移开,并且容易计算数量;家畜还可以繁殖。但最重要的是,家畜能够通过把价值较低的物转化成一批价值较高的产品(包括牛奶、皮革、羊毛、肉和燃料),来调动其他行业,进而创造出剩余价值。这样,“资本”一词开始同时就具有两重含义:“表示资产(家畜)的物质存在和它们创造剩余价值的潜能。”(16)由此可见,“资本”从牲口棚到经济学创立者的书桌只有一步之遥。但这一步之遥,迈得却并不轻松。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资本主要还是被定义为可用来生产、制造或购买物品,然后卖出去以取得利润的那部分“物质资财”。作为“国民经济学的路德”的亚当·斯密就认为:一个人“所有的资财,如果能够维持他数月或数年的生活,他自然希望这笔资财中有一大部分可以提供收入;他将仅保留一适当部分,作为未曾取得收入以前的消费,以维持他的生活;他希望从以取得收入的部分,称为资本。”(17)由此可见,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主要是从“物质生产”而非“价值形式”的角度来把握资本的。所以,“通过将资本物质化,确立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自然性、永恒性和绝对性,完成对资本背后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遮蔽,这是所有自觉不自觉地充当资本关系和资本利益的代言人的古典经济学家们共同的理论取向。”(18)因此,即便是在最优秀的古典经济学家这里,资本也主要保持和归结为它“见物不见人”的“物质性”外观。 但资本真正成为资本——“生出货币的货币”,却不在于它的“物质性”,而在于它获得了独特的“形式规定”之后。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绝不会自发变成资本,而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制的生产关系之中,生产资料才会逐渐转化为获取利润的资本——不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了。生产资料必须被赋予一个确定的、切实可见的形式,才能够把它作为资本体现出来。在此意义上,我们方能说生产资料就其本身来说天然是资本,资本则不外是这种生产资料的纯粹“经济学名称”(马克思语)。马克思批评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等经济学家,“他们不是把资本看作处在特有形式规定性上的资本,即在自身中反映的生产关系,而只是想到资本的物质实体,原料等等。”(19)也因此,经济学家总是“把表现在物中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当作这些物本身的物质自然属性,这是我们在打开随便一本优秀的经济学指南时一眼就可以看到的一种颠倒”。(20)而正是这种颠倒,导致“单纯从资本的物质方面来理解资本,把资本看成生产工具,完全抛开使生产工具变为资本的经济形式,这就使经济学家们陷入种种困难之中。”(21)由此可见,古典经济学家虽然关注和重视资本,但仍然不能摆脱资本作为“可感觉物”的迷惑,仍然没能理解和把握资本的“形式规定”——社会关系本质。而古典经济学家自己解决不了这个困难,这个困难最终是由马克思来解决的。 在马克思看来,如果资本仅作为“可感觉物”,资本就被理解成劳动工具或劳动资料而同劳动相对立,资本恰恰只是被看作与劳动对立的对象,被看作物质,只是被动的东西,这样,资本的“形式规定”完全消失了,资本同一般物质并没有本质区别。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22)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强调: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不是资本;它们只有在同时还充当剥削和统治工人的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所以,资本不仅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这些“物质产品”,还包括“交换价值”这一形式规定。对此,马克思还专门以资本的“躯体”和“灵魂”为喻进行了具体说明:“不论我们是以棉花代替羊毛也好,是以米代替小麦也好,是以轮船代替铁路也好,只要棉花、米和轮船——资本的躯体——同原先体现资本的羊毛、小麦和铁路具有同样的交换价值即同样的价格(资本的灵魂——引者),那么资本依然还是资本。资本的躯体可以经常改变,但不会使资本有丝毫改变。”(23)而且在政治经济学家的头脑中,这个“资本的躯体”和这个“资本的灵魂”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致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当它们正好是资本的对立面的时候,也把它们称为“资本”。 由此可见,资本虽然必须体现在“物”上,“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24)正是资本的这种“社会关系”本质,才使资本获得创造剩余价值而无限增殖自身的本能:“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25)在此意义上,资本本质上就是物的“人格化”和社会关系“物化”的集中表现:“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26)也就是说,正是这个人与物颠倒的世界,“把在生产中由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充当承担者的社会关系,变成这些物本身的属性(商品),并且更直截了当地把生产关系本身变成物(货币)。一切已经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社会形式,都有这种颠倒。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和在构成其占统治地位的范畴,构成其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的资本那里,这种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就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27)因此,只有像马克思那样对现存社会秩序进行无情批判的人,才能够和敢于在古典经济学家止步的地方接踵而起,揭露商品生产形式下资本的真正社会关系本质。 在马克思这里,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化身的资本,最终成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28)在此基础上,资本就是资产阶级社会里统治一切、支配一切的权力。就连资产阶级社会里最为基本的所谓“平等和自由”,也完全依赖于资本的存在:“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在所有方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平等,那么内容,即促进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这种基础而已。”(29)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社会现存的一切都依赖和归结为资本。资本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起点”,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终点”;没有资本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取代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而摇身变成了现实社会中居统治地位的“上帝”,成了万物的尺度:任何事物都要在资本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自己存在的权利。所以说,资本决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最为强大的、总体化的、结构性的、社会新陈代谢的控制体系和控制方式:“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0)因此,马克思强调“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资本的时代。 如果说,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货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车轮”,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枢纽”,那么,资本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座架”。马克思正是抓住和利用资本这一“座架”,来解剖和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破除“普遍永恒资本”的幻象,进而揭开“历史之谜”的。 三、历史唯“物”主义:破除“普遍永恒资本”的幻象 在作为“幽灵般现实性”的资本的兴妖作怪下,资本主义社会里个人只能是受“抽象”——资本统治。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借用冯·杜能的观点表达了这一判断和质疑:“资本本身不过是人的劳动的产物……那么似乎完全不能理解的是,人怎么会落入他自己的产物——资本——的统治下,并且从属于这个产物;然而,因为实际上情况确实如此,所以不禁要问:工人作为资本的创造者,怎么会由资本的主人变为资本的奴隶呢?”(31)在这里,马克思强调杜能的功绩只是在于提出了问题,但他的回答却十分幼稚。而在马克思看来,只要是“在一种不是物质财富为工人的发展需要而存在,相反是工人为现有价值的增殖需要而存在的生产方式下,事情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正像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脑的产物的支配一样,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32)由此可见,资本所主宰的世界的必然悖论,就是它与对物的世界的利用成正比地生产着人的世界的贬值。在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制的生产关系下,只能是资本统治人而不是人支配资本,这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鲜活现实,也是马克思力求突破的魔力怪圈。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统治人的现实和怪圈之所以可能,不在于资本作为物质资料的“实体内容”,而在于资本作为社会关系的“形式规定”。“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33)也就是说,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制,使资本成为资本并神秘化而统治人。对此,马克思批评经济学家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34)也因此,马克思认为经济学家们“只是看到了资本的物质,而忽视了使资本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由此导致“资本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成了某种完全非历史的东西。”(35)他们不把资本看做是社会生产的“历史形态”,却看作是社会生产的“自然形态”。可见,在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哲学这里,资本成了“冻结的永恒”和“历史的终结”。而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这是由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把源自“资本的强制”人为地变成了一种普遍永恒有效的“自然德性”和最高规则所致。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超历史性和神秘性,并不是天生的和永恒的,而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是可以揭开和破除的:“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36)但在马克思看来,虽然古典经济学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社会历史运动”。所以,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几乎接触到事物的真实状况,但是没有自觉地把它表述出来。只要古典政治经济学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它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37)实际上,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这里,“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观念中显露出来。”(38)在马克思这里,商品、货币和资本这些“物”,不仅仅是“可感觉物”,而且还是“超感觉物”,甚至可以超越人的精神和意志,成为让人顶礼膜拜的“意识形态”。“资本”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最集中、最充分、最现实的表达。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与其说是“观念”,不如说就是“物”。而对这些“物”进行深刻历史透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也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论”——否定和批判资本的意识形态论。 实际上,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资本关系”就是在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经济土壤之上产生的。作为资本关系的基础和起点的现有的社会生产关系,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劳动力的占有者。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39)在此基础上,以资本增殖为中心和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40)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剖析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个既定的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既定基础。”(41)正是由于这一基础和性质,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42)而在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基础上,“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43)从而实现从资本的“必然王国”向现实的人的“自由王国”迈进。 由此可见,只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的剖析和研究,才既抓住了资本作为“物”的实体内容,又抓住了资本作为“社会关系”的形式规定,进而揭示出了资本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历史性。通过对资本的批判性剖析,即透过表象而分析它下面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我们才能看清资本主义本身的历史相对性和历史过程性,彻底打破了“普遍永恒资本”的幻象。对此,海德格尔曾专门强调: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基本而重要的意义上”,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个人受资本统治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而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44)在对待资本问题上,马克思并不把资本视为超历史的一种难以改变的终极存在,而是视为一种动态的运动过程,这种运动即使有其明显的不可抗拒的全球性扩张逻辑,也应该看成是历史的和暂时的。对马克思来说,败坏黑格尔哲学的不仅仅是它的“唯心主义”,而在于他持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的事实,这意味着对作为社会新陈代谢控制的资本抱一种“总的无批判的态度”。(45)可见,对资本抱一种“总的无批判的态度”,是古典经济学家和古典哲学家不谋而合的共识。破除“普遍永恒资本”的幻象,作为“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李嘉图没有做到,作为“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的黑格尔也没能做到,只有作为“批判的实证主义”的马克思做到了。正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最终又把“资本”这一“怪物”变回了“现实的个人”。 注释: ①⑤刘森林:《物与无》,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233、237页。 ②[法]费迪耶:《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 ③(24)(26)(27)(40)(41)(4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5、922、940、936、289、994、928—929页。 ④转引自俞吾金《物、价值、时间和自由》,《哲学研究》2004年第11期。 ⑥⑦⑧⑩(11)(12)(14)(15)(25)(31)(32)(36)(37)(38)(39)(42)《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88、89、93、101、62、98—99、8、269、717、716—717、97、622、429、197、874页。 ⑨[日]柄谷行人:《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13)(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7、85页。 (16)[秘鲁]赫尔南多·索托:《资本的秘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9页。 (17)[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55页。 (18)王峰明:《经济哲学规定性的哲学辨析》,《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7期。 (19)(21)(28)(29)(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268、594、48、199、213 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 (22)(23)(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723、725、612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6页。 (44)《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83页。 (45)[英]梅扎罗斯:《超越资本》(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标签: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生产资料所有制论文; 社会资本论文; 商品货币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新古典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货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