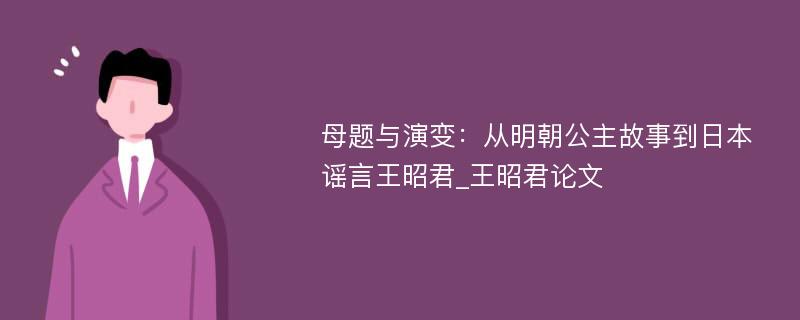
母题与嬗变:从明妃故事到日本谣曲《王昭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事到论文,王昭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悲剧冲突的嬗变
日本谣曲《王昭君》取材于中国历史上的明妃故事。明妃故事在古代日本广为流传,形成各种故事传说,很多诗人也咏唱昭君,这一切为创作《王昭君》提供了丰富素材。除此之外,中国历史上有关昭君的记录和笔记小说等成为日本文学中昭君故事的原始材料。昭君之事始见于《汉书·元帝纪》和《匈奴传》,亦载于《后汉书·南匈奴传》。其后又有《西京杂记》、《王昭君变文》等也写了昭君的故事。这些记载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素材,孕育了丰富的诗歌、小说、戏曲作品,产生了《汉宫秋》这样伟大的作品。昭君的故事也深为日本作家所喜爱,给他们以新奇的想像空间。就戏曲作品而言,无论中国或日本多为悲剧。从历史故事到悲剧作品的发展过程之中,两国作家各自以不同的想象创造出不同的悲剧形式。
《王昭君》和《杨贵妃》一样取材于中国的历史故事,但是它与《杨贵妃》有点不一样,它与中国原本有相当程度的重合,但也有很多内容是中国原本中看不到的。《王昭君》的一部亲情悲剧,也是昭君宫廷生活的悲剧。作品以昭君村作为故事发生的地点,主要写了昭君的父母白桃与王母。白桃、王母在昭君离开汉宫被遣往匈奴之后,终日以泪洗面,思念昭君。昭君在前往匈奴之前,曾在家门口栽下一株柳树,并说假如她在匈奴死去了,柳树就会枯死,柳叶飘落。白桃、王母见柳树枯死,心中甚为焦虑,便用镜子照柳树。这时镜子中出现昭君的亡魂,随后又出现了呼韩邪单于的身影。呼韩邪单于的形象奇丑无比,如鬼一般。单于自惭形貌丑陋,从镜中遁形隐去。从这一故事情节的发展来看,似乎看不出谣曲《王昭君》与史书之间的直接联系。然而白桃、王母的情节之外还有另外一条线索,写白桃、王母的邻居前来探望,并在闲聊中问起昭君为何被送到匈奴。白桃、王母便向邻居讲述了昭君被送给单于的经过。在这一条线索中回忆了昭君的身世。昭君有绝代美貌,进入宫中之后与汉元帝十分恩爱。这时匈奴呼韩邪单于强索美女,汉元帝嫔妃不少,她们个个有倾城之貌,难分伯仲。汉元帝派画师为她们画像,以像之劣下者送与匈奴。昭君因其容貌出众,汉元帝又十分宠爱,就没有贿赂画师,因此她的画像较为丑陋,她因而被送给匈奴。汉元帝虽然不愿意把昭君送给匈奴,但因“君无戏言”,只得把昭君送给匈奴。两条线索通过昭君幽灵出现于镜子中完全重合,作品的整体结构由三方面内容构成:一、父母对昭君的思念;二、昭君的悲剧身世;三、作品借助柳树和镜子把两条线索的情感发展融合起来。在这三个基本要素中,对于昭君身世的描述是依据中国史书和笔记小说而写成的。
从中国的史书所载的内容来看,王昭君的故事较少悲剧性,似乎不具备作为悲剧的品格,悲剧色彩是后世逐渐增加的。最早的《汉书》记载非常简约: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多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注:班固《汉书·元帝纪》卷9(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297页。)
这一段文字对王昭君只提到一句而已,当然也就不可能构成故事,更不能成为悲剧。但是它提供了关于昭君故事的背景。昭君故事的历史意义不是悲剧性的,汉朝与匈奴并没有什么冲突可言,两国关系和谐,呼韩邪单于是第一个来到汉朝的单于,加强这种友好关系的实际措施之一便是王昭君远嫁匈奴。同书《匈奴传》中亦有对此事的记载,所录稍详。除原来汉番和好送赠王昭君之外,还增加了王昭君在老单于死后复嫁其子、又生二女之事:
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樯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史,以休天子人民。……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呼韩邪死,雕陶莫高立,为复株累若单于。……复株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注:班固《汉书·匈奴传》卷94(第11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3803-3806页。)
《匈奴传》的这段文字也是从汉番和好的角度来记录的,仍旧无冲突可言。然而从昭君个人而言,却产生了冲突。即呼韩邪单于死后,按照匈奴习惯,昭君应嫁给呼韩邪之子,这与儒家礼法不合。昭君要求回归汉朝,但被汉元帝拒绝,这使得昭君的生活具有了悲剧性。昭君不得已复嫁呼韩邪之子,又生有二女。就儒家伦理的角度而言,昭君复嫁呼韩邪之子更具悲剧性。自汉高祖刘邦第一次远嫁公主、陪送嫁妆、实行“和亲”政策以来,汉朝多用“和亲”政策。被远嫁的公主也多有复嫁子孙之事。公元前105年汉武帝将侄孙女刘细君作为公主嫁给了乌孙国国王,乌孙国国王死后,刘细君嫁给他的孙子岑诹为妻。刘细君死后,汉武帝派楚王刘戊的女儿解忧替代刘细君。岑诹死后,岑诹的堂兄翁归靡继承王位,解忧就嫁给了翁归靡。后来汉朝与乌孙国联合打败了匈奴,“和亲”政策为汉朝和乌孙国的友好做出了贡献。被远嫁的公主身世各有不同,有的个人生活具有悲剧性,有的则没有悲剧性。然而无论如何,王昭君的复嫁生活与儒家观念之间产生的冲突,具有了创造为悲剧的可能性。
范晔的《后汉书》对昭君之事也有记载,不过与《汉书》不同,较多从昭君个人的角度来描述,也更具悲剧色彩,然而也更多传奇性,渐渐远离史书实录的特点:
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注:范晔《后汉书·南匈奴传》卷89(第9册),中华书局,1965年,第2941页。佐成谦太郎《谣曲大观》第三卷中称《王昭君》原典出于《后汉书》汉元帝条,其实误也。另,在《后汉书》之前,史书所记王昭君之字为“樯”,《后汉书》开始写作“嫱”,此后皆然。)
《汉书》主要写了王昭君远嫁匈奴之后的生活,《后汉书》则写到了昭君在汉宫中的生活。如果说《汉书》中昭君生活的悲剧性表现在复嫁之后,那么《后汉书》中昭君的悲剧性则是在入番之前。昭君入宫中多年,不能见汉元帝,寂寞孤苦,然而大多数宫女和昭君一样,过着基本人性要求无法得到满足的不幸生活,她们的生活当然是悲剧性的。昭君主动要求去和番,既出于“积怨”,也是为结束悲剧性的汉宫生活。
葛洪《西京杂记》也曾记载此事,写的也是昭君远嫁之前的生活,但是比《后汉书》更加远离历史,更多文学创作的想像与虚构。这已不是历史,而是文学创作。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阙氏。於是上按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按其事,画工皆弃市。(注:葛洪《西京杂记·王嫱》,见《五朝小说大观》卷3,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
《后汉书》写了王昭君“不得见御”,形象“丰容靓饰,光明汉宫”,《西京杂记》则进而夸张为“后宫第一”。昭君郁郁寡欢,原因是她没有给毛延寿等人钱财,故招致被赐给单于的命运,汉元帝也后悔不迭。有关毛延寿的情节是《西京杂记》新添加的内容,为后来的众多作品所接受。这一情节使得皇帝与宫人间的矛盾更加突出,也更具传奇性。《西京杂记》把昭君主动“求行”改为被迫去和番,使冲突更为尖锐,使悲剧性更强。这是从冲突的解决转到冲突的生成,是迈向悲剧的最关键的一步,以后的戏曲作品多是沿着这一方向朝悲剧嬗变的
王昭君的故事流传至日本,成为日本文学中为人熟知的故事。《今昔物语集》里就记载有如下王昭君的故事:
震旦汉元帝时,……胡国有使来朝。……朝中贤臣曰:“胡国使者此来,于国极不宜也。若遣此人,宫女甚众,择一丑者相送可也。如此使者欣然而归,此为至善。”天皇闻言以为然。……天皇以为可唤画师数人,令其观宫女绘形。天皇观像选一丑者,送于胡国。……宫女皆惧被遣于遥遥陌生之国,以重金珠宝贿画师。……其中有王照君者,姿容超群。王照君自恃貌美,不贿画师。故画师不如实绘貌,气貌劣下。天皇见此以为不美,遂定王照君。天皇略觉蹊跷,召见王照君。见她光彩四射,美如珠玉,妙不可言。其他宫女粪土无异。天皇惊叹不绝,懊恨送夷。数日之后,夷国亦闻此事,入宫相商,此事遂定,不可更改,只得送夷。王照君乘马将行,虽悲悲切切,然无济于事。天皇亦悲恋不已,思念之深,遂往照君居处。春风拂柳,莺鸣空响,秋叶飘落,厚积院中,屋檐无隙。悲怜无过于此,恋情弥深,悲伤之极。彼胡国之人得王照君喜不自胜,弹拨琵琶,吹奏诸乐,行离汉土。(注:《今昔物语集》卷10《汉前帝后王昭君行胡国语第五》,引文译自岩波古典文学大系《今昔物语集》第二册,岩波书店,昭和35年,第280-281页。《今昔物语集》误将王昭君的名字写作“王照君”。)
《今昔物语集》的内容大体与《西京杂记》相类,略有不同,故可以认为《今昔物语集》是以《西京杂记》为底本来创作的。《今昔物语集》的昭君故事比《西京杂记》更具悲剧性,这不仅是因为《今昔物语集》的描写更加细致,更重要的是,《今昔物语集》描写了汉元帝对昭君的恋情,而《西京杂记》等作品只写了汉元帝的悔恨。《今昔物语集》对恋情的描写尽管没有展开,但爱情内容的加入使冲突变得更加突出,悲剧性增强了,尽管其中爱情内容的增加似乎有些突兀。
谣曲《王昭君》并不是直接取材于中国史书和笔记小说,是《今昔物语集》和丰富的和歌、注释为谣曲作者们提供了素材。谣曲作者往往不懂汉语,不能直接读中国的书籍,他们借助内容上经过改写的物语,或者以和歌、汉诗等作品的注释作为素材进行创作,以王昭君故事为内容创作的日本小说、和歌作品是谣曲《王昭君》产生的中间形态。从《今昔物语集》到谣曲《王昭君》,内容上有同有异。《王昭君》由两条线索构成:一条线索是写照君父母思念昭君,这是基本线索;另一线索则是昭君父母谈到昭君时回忆昭君的悲剧身世,在回忆中把《今昔物语集》的内容穿插了进去。昭君父母回忆昭君不幸身世的内容与《今昔物语集》中的基本相同,没有太大的变化。最后昭君的幽灵在镜中出现,白桃、王母得以与昭君团圆,使得两条线索最后重合。白桃、王母思念昭君的线索在中国文学和《今昔物语集》中都没有,以这一线索作为基本线索来结构整个作品,使得原本没有的亲情内容占有了较大的比重,从而使作品成为亲情的悲剧。
从《汉书》到《今昔物语集》,从《今昔物语集》到谣曲《王昭君》,再比较《王昭君》和《汉宫秋》等作品,就会发现两部作品在历史事件中重新构造了冲突,而对冲突的重新构造使《汉宫秋》、《王昭君》等作品具有了悲剧冲突的形式。首先,史书所载的王昭君与汉元帝没有爱情,王昭君只是作为汉元帝的礼物赐给了单于,昭君与汉元帝没有见过面。连面都没有见过,更何谈受情的毁灭?以《汉宫秋》为同类题材作品之始的中国古典戏曲作品无不描写昭君和汉元帝的爱情。《汉宫秋》、《昭君出塞》、《吊琵琶》、《昭君梦》等都是以汉元帝与昭君的爱情作为基点构造了冲突。只有加入爱情冲突之后,昭君的故事才具有作为悲剧存在的可能性。如果没有爱情,王昭君和汉元帝的分离就只是日常生活中平平常常的分别而已,甚至不一定构成冲突,更不必谈不可解决的悲剧冲突了;而以爱情作为基点构造冲突,汉元帝和王昭君的分离毁灭了爱情,使得作品有别于历史走向了悲剧。日本的《今昔物语集》与《王昭君》对此也作了改动,《今昔物语集》,中汉元帝在决定送昭君给匈奴之前并不认识昭君,他在决定把昭君送给匈奴之后才见到昭君,并为她姣美的容貌而哀叹。但是“君无戏言”,只能把昭君送给匈奴,为此汉元帝对昭君产生了恋情。《王昭君》则不同于《今昔物语集》,汉元帝在决定把昭君送给匈奴之前就认识昭君并对她宠爱有加。这一内容的设计与《汉宫秋》完全相同,使得《王昭君》中的汉元帝与王昭君的分离具有悲剧性质的冲突。当然,《王昭君》中昭君与汉元帝的分离并不是整部作品的基本冲突,基本冲突是昭君父母想念昭君,昭君亦思念父母,以此构造了冲突。然而这一冲突与昭君、汉元帝的分离相关,如果没有昭君与汉元帝的分离,《王昭君》的基本冲突就不可能构成。这两个冲突虽分在两个层面,但是密切相关。
其次,史书所载昭君出塞并不是非她前去和番不可,真正的原因是“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于是自动要求出塞。史书的出塞较少悲剧性,即使有一点悲剧因素,也不足以成为悲剧,这与王昭君故事的中国戏曲作品大异其旨。《汉宫秋》写昭君被逼无奈,不得不远赴匈奴,昭君所面临的是无可逃避的命运,从而使得冲突具有不可解决性,也就把冲突构造成了悲剧冲突。《王昭君》的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王昭君自恃美貌和汉元帝的宠爱,不贿画师,因而落入了被遣匈奴的命运。汉元帝尽管宠幸昭君,但他有言在先,以图形丑好为准决定远嫁匈奴的人选。汉元帝不愿意更改人选,于是昭君就只能远嫁匈奴了。就因昭君的画象丑陋和“君无戏言”,就决定把昭君远送匈奴,显得不合情理,也与中国历史上的诸多史实不合。然而作为异国人的想像,如此构造冲突还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说这是异国想像的必然性,由此构成了冲突的不可解决性。当然《王昭君》具有双重冲突的结构,悲剧的主要冲突并不在于昭君远嫁匈奴的命运冲突,而在于这一冲突引起了昭君父母的思念。这一冲突是以昭君幽灵回归故里进行结构的,显然,白桃、王母的思念和昭君幽灵的回家构成了不可解决的冲突,是真正悲剧性的。
其三,昭君与老单于生有一子,老单于死后,昭君要求归里,但汉元帝不准,不得已只得按胡俗再嫁老单于的儿子,又生有二女。这一段生活对于昭君个人而言可谓是真正的悲剧,因为这完全不合儒家伦理,是乱伦行为,是儒家所贱视的淫乱。然而这一段史实并不被中国古典戏曲作品所选取,往往被删去。史实中最具悲剧性的部分反而没有成为戏曲悲剧中的内容,这是非常能说明问题的现象。《汉宫秋》的基本情节到昭君出塞投河自杀结束,昭君远嫁之后的生活完全删去,因为这一部分与昭君形象的儒家伦理意义不合。《昭君出塞》遵从《西京杂记》,止于昭君出塞,亦不写她死。《吊琵琶》亦没有写昭君嫁单于之后的生活。《昭君梦》不同于上述三部作品,写了昭君嫁单于之后的生活,但也避开了昭君嫁给两代单于生子,而主要写了昭君梦回汉宫的经历。古典戏曲选取的往往是昭君出塞之前的那段,然而这一段在历史上却并非悲剧性的。一般而言,在中国古典戏曲史上,悲剧作品的本事基本上是悲剧性事件,到了戏曲作品里就被改造为喜剧性的内容,这几乎是中国戏曲的基本模式。《汉宫秋》等作品却反其道而行,把非悲剧性的历史事件改造为悲剧,这是古典戏曲创作的特例现象,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值得深思的。《王昭君》亦没有写昭君远嫁之后的生活,《今昔物语集》本身已经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删去了昭君历史事实中真正悲剧性的部分,较之中国的戏曲作品更加远离了历史事实。
其四,为了把昭君故事写成悲剧,《汉宫秋》等作品对历史背景也做了较大的改动。汉元帝送昭君和番,是汉强番弱的时代,并非《汉宫秋》中所写的那样汉弱番强。呼韩邪单于遣子入侍作为人质,依赖汉朝的力量得以一统匈奴。统一匈奴之后,为进一步倒向汉朝,以求生存,于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自言愿为汉室女婿。王昭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为和番前往匈奴的,从当时的历史形势来看,昭君和番并不具有悲剧意义,而应当说具有积极的意义。《汉宫秋》等作品改变作品的历史背景,使得王昭君作为政治牺牲品的悲剧意义更加突出。历史上的汉强番弱并不存在多少政治冲突,戏曲作品改写为汉弱番强则构造出了原本没有的冲突,加入了政治冲突,这样就形成了悲剧,以一个弱女子去调和政治冲突正是为历史上很多诗人所耻笑的政治悲剧。《王昭君》虽然也写了汉弱番强的内容,但仅仅是作为背景来写,不能构成真正的冲突,没有使之发展,因而《王昭君》中没有政治悲剧可言。
从历史上的昭君故事到《汉宫秋》、《王昭君》等作品,都有作为悲剧存在的可能性。但中日两国作家笔下的悲剧冲突有同有异,这是两国作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创作的结果。
二、昭君形象的伦理意义与悲剧关系
中日两国作家以同样的昭君故事创作悲剧,在构造悲剧冲突时,是通过赋予意义来结构的。两国作品都不断地赋予昭君故事以伦理意义,以伦理的意义为基点构造冲突,塑造人物。伦理的意义成为创作悲剧的基本方向,那么伦理的意义同两国悲剧作品具有怎样的关系呢?
从历史上的昭君故事到马致远的《汉宫秋》等作品,从历史上的昭君其人到戏曲作品中的昭君形象,在朝着悲剧演变的过程之中,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那便是昭君在走进文学作品之后被不断理想化。这当然不是《汉宫秋》等作品中独有的现象,事实上中国古典戏曲作品在取材历史的过程中往往都有理想化的特点,好人要好到极点,好得一点缺点也没有,坏人就坏到十恶不赦,也就是将人物类型化。在进行理想化和类型化的过程之中基本原则便是诗的正义,以儒家道德伦理的善恶观念作为人物分类和理想化的基础,甚至作为创作的最高原则。这使中国古典戏曲具有伦理化的特点,成为古典戏曲创作的普遍现象。
以伦理意义作为创作的最高原则进行人物类型化和理想化的方式不适合于悲剧。亚里士多德就曾说过:“悲剧不应表现好人由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因为这既不能引发恐惧,亦不能引发怜悯,倒是会使人产生反感。”(注:亚里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7页。)尤其是好到极致的理想化人物的毁灭,更是令人反感,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好人应当是“不具十分的美德,也不是十分的公正,他们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注:亚里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7页。)亚里士多德论及了悲剧的普遍现象,理想化的好人之所以不适宜作悲剧人物,原因是诗的正义和悲剧的关系是复杂的,诗的正义与悲剧本身的逻辑并非完全和谐。道德的善恶是悲剧非常重要的内容,但它不是最终的悲剧原则。悲剧作品往往要写正义的英雄人物,这样容易引起怜悯、恐惧、焦虑等悲剧体验。但这只是悲剧的一个方面的要求,悲剧并不要求把伦理的善与恶作为悲剧的最高原则,因为这样将把悲剧自身置于自我否定的境地。悲剧不可解决的冲突不仅具有毁灭恶的力量,同时也具有毁灭善的力量。这是悲剧冲突的基本逻辑,让正义的善也不免落入毁灭的结局,这样就在否定恶的同时,也否定了正义的善,这有悖于伦理道德的最高原则。如果一定要把道德伦理的善恶置于最高原则,必然是以伸张诗的正义为其基本原则,也就要写正义必然战胜邪恶,从而彻底地解决冲突,这是与悲剧的本质背道而驰的,冲突的解决必然消解悲剧。对于悲剧而言,虽然伦理思想是本质的相关因素,但不能成为绝对的最高原则。不可解决的冲突把世上的一切事物都置于虚无的背景中去认识,由此对人的存在进行形而上的追问,追问人的存在的意义,毁灭旧的意义,同时又打开求索新的意义的大门。悲剧除了在伦理层面上认识不可解决的冲突之外,还有一个更高的形而上的层面,因此克利福德·利奇以为:“很轻松地抛弃那种‘诗的正义’的观念是可能的。这不是因为它没有抓住本质,而是因为它不符合从古希腊到现在那些重要作家的创作实际。但一种简单的描述必须补充进来。我一直怀疑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观点,一个真正的坏人不能成为悲剧英雄,并且注意到一个悲剧人物对于也卷涉着他自己的整个进程通常所起的作用。”(注:克利福德·利奇《悲剧》,昆仑出版社,1993年,第60页。)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以一个恶人作为悲剧主人公,但仍然是一部伟大的悲剧,伦理意义在这里并非绝对必须。伦理思想属于世界观的范畴,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伦理观念,如果仅仅以伦理观念作为认识悲剧冲突的根据,那么在过去认为是悲剧的东西现在就可能无法成为悲剧,因为对于不同的伦理观念来说善恶的标准是不一致的,对于悲剧冲突的认识不能仅仅建立在随着时代不断变化的伦理思想上。因此雅斯贝尔斯在认识到伦理意义对于悲剧的作用的同时,还注意到形而上学的作用:“悲剧从形而上学的视角注视着人的欲望与苦难。缺乏形而上学这一根据,我们只剩下苦难、悲哀、不幸、灾祸与失败。只有勇于去超越所有这一切,悲剧知识才展示在我们面前。”(注:雅斯贝尔斯《悲剧与超越》,见《存在与超越:雅斯贝尔斯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132-133页。)
中国古典戏曲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以教化为基本目的,以伦理道德的善恶是非为基本内容,劝善惩恶,美刺时事。中国古典戏曲虽然被以诗文为正统的古代文学观念所歧视,但是戏曲在社会功能方面也恰恰和诗文一样以教化为宗旨。戏曲本身一方面具有教化的功能,主要宣扬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另一方面戏曲作家也有以教化功能来提高戏曲地位的动机,希冀以此使戏曲跻身于与诗文同等的地位。祁彪佳谓:“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然则诗而不可兴、可观、可群、可怨者,非天下真诗也。呜呼!今天下之可兴、可观、可群、可怨者,其孰过于曲者哉!盖诗以道性情,而能道性情者莫如曲。曲之中有言忠孝节义可亲可敬之事者焉,则虽騃童愚妇见之,无不击节而忭舞;有言夫奸邪淫慝可怒可杀之事者焉,则虽騃童愚妇见之,无不耻笑而唾詈。自古感人之深,动人之切,无过于曲者也。”(注:祁彪佳《孟子塞五种曲序》,见蔡毅编《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第4册,齐鲁书社,1989年,第2745页。)这也就是要求戏曲作品具有与诗相同的社会功用,从而达到教化的目的。教化自然是以儒家伦理思想为准则,因而戏曲要以忠孝节义、三纲五常作为基本内容,以达到“美风化,厚人伦”的目的。儒家传统的教化思想体现到戏曲创作中,必然要维护儒家伦理思想体系的绝对性。宋代理学大兴以来,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被认为不仅是人道,而且是天道,如同天上日月星辰一样不可动摇,不可变更。把儒家伦理思想推到极端,必然使伦理道德成为认识人生的根本原则,其结果不但影响了戏曲文学的内容,也规定了戏曲文学的形式。在内容上塑造理想化人物,以完美无瑕的人物表现儒家伦理思想,以此教育百姓;在形式上善的力量必然战胜恶的势力,最终出现大团圆结局,以此证明儒家伦理思想的绝对性。这是中国古典戏曲的普遍模式,这种模式显然与悲剧本质相矛盾,成为消解悲剧的主要因素之一。善恶同时毁灭的悲剧结局形式无疑是对儒家伦理思想绝对性的彻底否定,悲剧的结局形式往往不适合儒家的伦理模式,这也是中国古典戏曲作品大多以幸福团圆作为结局的主要原因之一。理想人物的毁灭也与悲剧逻辑相悖,它只能引起观者的憎恶,不可能引起悲剧体验,也不可能产生悲剧快感。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悲剧创作并非没有特殊和例外现象。
诗的正义是《汉宫秋》构造悲剧冲突、塑造人物的最高原则,诗的正义又以儒家伦理思想为准则。在加入爱情、政治的冲突时,毛延寿等人物被极力丑化,甚至被小丑化,成为邪恶的代表。人物的脸谱化使观众对善恶一目了然,汉元帝和王昭君是善的代表,她们具备善的美德。善与恶界垒分明,两者的对抗水火不容,这种观念构成了善恶的不可解决的对抗。从历史事件到《汉宫秋》,从无冲突到冲突的出现及其不可解决,就是遵循了这一诗的正义原则。从历史上的王昭君到作为悲剧形象的王昭君,亦经历了逐渐理想化的过程。历史上的王昭君是普通的女性形象,她进入宫中,并没有《汉宫秋》中的昭君那样强烈的儒家思想。她在宫中因不得见元帝,心中充满了怨恨,因怨怒而主动要求前去匈奴和番,她的行为中并没有为“国家大计”的意识,完全是出于她个人的愤恨而已。这种感情不符合儒家伦理对于女性的要求,因而《汉宫秋》中的王昭君从出场开始就没有半点怨恨,即使到了不得已要离开汉元帝时,虽然恋恋难舍,也无怨怒。《汉宫秋》中的昭君是深明节义、忠于爱情的女性形象。《汉宫秋》是一出正末剧,对正旦昭君着墨不多,然而即使在很少的笔墨勾勒中,也具有较为浓厚的儒家思想。在生命与儒家伦理之道的关系上,儒家以伦理道德为准绳。孔子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注:《论语·卫灵公》,见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第238页。)孟子则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注:《孟子·告子上》,见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第475页。)舍生取义的伦理思想孕育出重气节、尚操守的殉道精神,以此抗拒邪恶,不畏强暴。在这一方面不同于西方悲剧,黑格尔认为只有英雄才具有独立意志,从而能够去同不可解决的悲剧冲突抗争,因而才有资格做悲剧主人公。然则儒家的重仁取义并非仅限于士大夫等上流社会的人物,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注:《论语·子罕》,见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第165页。)匹夫亦应善养孟子所谓“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成为顶天立地的英雄。这一精神成为中国古典悲剧精神的主要来源之一。中国历史上不仅有苏武、文天祥这样的民族英雄,也有无数小人物具“浩然之气”,在生命与道义之间选择道义,成为殉道的英雄。王昭君也是被作为儒家伦理思想的体现者塑造的,并被理想化。王昭君对汉元帝的爱是忠诚的,她亦重气节胜过重生命。当汉朝面临危机时,她的忠义胆识远胜于许多文臣武将:
(旦云:)妾既蒙陛下厚恩,当效一死,以报陛下。妾情愿和番,得息刀兵,亦可留名青史。但妾与陛下闱房之情,怎生抛舍也。
(旦云:)妾身这一去,虽为国家大计,争奈舍不的陛下!
(旦云:)妾这一去,再何时得见陛下,把我汉家衣服都留下者。(诗云:)正是:今日汉官人,明日胡地妾。忍着主衣裳,为人作春色。(注:王学琦主编《元曲选校注》第1册上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85页。文中《汉宫秋》的其他引文均据此本。)
这几段王昭君的宾白虽只有寥寥数语,却把她在爱情与道义之间的矛盾冲突中内心的焦虑与孤独表现得相当充分。汉元帝虽然在身边,却不能解救她。昭君是孤独的,这是彻底的悲剧孤独。既要保持完整的爱情,又要坚守气节,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解决的,她只有一种选择,那便是死,正是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由此可以看到昭君身上浓重的儒家伦理思想。从历史到悲剧,马致远的修改显然是为了把昭君置于不可解决的悲剧冲突之中,并按照儒家伦理思想塑造昭君形象,使她具有“至大至刚”的儒家正气,从而与不可调和的冲突对抗。《汉宫秋》删去了昭君嫁到匈奴的事实,改写为投江而死,留下千古传唱的“青冢”一堆,这就将冲突推向了极端,在死亡与毁灭中走向崇高的巅峰。在王昭君的死中透出的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作用,由此来看,儒家伦理思想不是消解悲剧,而是成为《汉宫秋》作为悲剧存在的主要根据之一。如前文所述,儒家伦理思想在一般情况下是作为消解悲剧的因素存在的,然而也不能把这一模式绝对化,儒家伦理思想也有可能成为建构悲剧的因素。儒家伦理思想把忠孝节义、三纲五常视为天道,当与此天道发生对立时就可能产生悲剧,并以死亡与毁灭的形式表现其壮烈和崇高。从马致远现存的创作来看,他的思想中更多的是全真道的思想,可以说全真道的思想是他思想的主体,然而他的思想中也仍然保存着儒家伦理思想和价值观念。马致远的杂剧多为神仙道化剧,表现出浓厚的道教思想,但在神仙道化剧中也不无儒家思想,而这部《汉宫秋》则是完全没有全真道思想的作品,由此也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
儒家伦理思想作为悲剧《汉宫秋》的诗的正义最高原则,把非悲剧性的历史改造为悲剧,道德善恶的终极力量也没有构造出大团圆结局,至善至美的王昭君的死亡和爱的毁灭并没有引起观者的厌恶,其原因是:一、善恶的伦理观念虽然作为作品的最高原则,但是并没有把作品完全框架于伦理观念之内。其实《汉宫秋》不单单是表现儒家伦理思想的善恶,伦理的善恶观念与民族精神情感结合起来,使得思想力量非常深厚丰富。悲剧冲突也不单纯是善恶斗争,这也是民族的矛盾与抗争。《汉宫秋》没有解决悲剧不可解决的冲突,昭君之死也不等于民族精神的毁灭。二、昭君之死虽然表现了爱情的破灭和善的毁灭,但是作为政治线索的汉番之间的冲突却得到了解决,从这一条线索来看是冲突的解决转换成了大团圆的结局。个体生命的死亡换来了民族的融合,使人觉得个体生命的死亡或理想的毁灭并不证明儒家伦理天道秩序和民族精神的毁灭,反而证明它们的恒存不变。最后的汉番重新修好正是昭君悲剧的胜利,是善的力量的胜利。这与善恶同时毁灭的悲剧作品并不完全相同,道德作为作品中的最高原则并没有消解悲剧,而是构成不可解决的悲剧冲突形式和冲突得以解决的双重形式。以不可解决的冲突形式毁灭了善,但又没有否定善的最高原则。
谣曲《王昭君》在其双重冲突的结构之中,同样以伦理意义的冲突建构了基本冲突,但是并没有像《汉宫秋》那样把伦理的善恶作为最高原则。《王昭君》的主要冲突线索是由昭君父母思念昭君而不得相见构成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发展过程是以父母与儿女的亲情来结构的,从而显现出冲突的伦理意义。然而这种亲情决不是《汉宫秋》中那样的善恶分明的伦理观念,《王昭君》中的伦理内容没有善恶力量的对立,也几乎没有善恶的区别。最后昭君的幽灵和呼韩邪单于的幽灵同时出现于镜中,呼韩邪单于形貌丑陋无比,昭君却姿容靓丽,两者构成了鲜明对比,但这只是美丑的对比,并没有构成善恶的对立。因此,可以认为《王昭君》在伦理层面上没有多少儒家思想可言,其表现的伦理内容也只是一般日常生活的意识而已。因此《王昭君》中伦理只是一个层面,而不是整部作品的灵魂,尽管作品中有很多关于亲情的描写,但只是贯穿作品的表面线索而已。
《王昭君》在以亲情为中心的表层之外还有一个层面,那便是形而上的层面,即以生与死的对立和断裂来构造整部作品的基本冲突,叙述昭君经历的那一条线索也是作为这一线索的前提而存在的。《王昭君》中虽然没有直接出现昭君死亡的悲剧性场面,却以间接的方式写了死亡,而且主要是以此为核心编织内容的。整部作品以两件东西为中心安排结构,一是柳树,一是镜子。昭君父母的思念围绕柳树飞扬,或在柳树前哀叹,或去扫那柳树落叶:
王母:日沉西山晚钟响,
白桃:闻钟已晓夜风凉。
王母:风吹袖宽应觉寒,
白桃:苦思我儿
王母:不知寒。
白桃、王母:树下叶落积,随风飘零作尘土。
伴唱(白桃、王母):树下叶落积,树下叶落积,随风飘零作尘土。
伴唱(白桃、王母):尘世忧深深,尘世忧深深,尘芥满心世无常。
泪珠数行袖上滴,欲拂泪露乏无力。风中花零落,水上红叶浮,袖口此泪姑且留。
伴唱(白桃、王母):月影宿泪滴,月影宿泪滴,看似吾儿却不是。霰敲细竹,听若吾儿却声无。(注:《王昭君》,见佐成谦太郎《谣曲大观》第3卷,明治书院,昭和5-6年,第1582-1583页。)
这是白桃、王母在扫柳树枯叶时的曲文。柳枯叶败,水浮乱叶,泪湿衣袖,泪映月影……其中无限的焦虑,不尽的孤独,绵长的哀怜……这里的悲剧体验实际上就是由生与死的冲突构成的,并表现了对生死意义的思考。白桃、王母从柳树的枯死中看到了昭君之死,从柳叶的飘零中体验出人生的无常。人生无常如同尘芥,人之死亦如尘芥,生与死的冲突不可解决,人生的一切都在不断改变。现世中常住的只有一个,那便是死亡,而死本身恰恰是无常。这里表面上写的是对昭君的思念,而实质是对生死不可解决这一冲突的体验。对于生死冲突的意义构造,《王昭君》和《汉宫秋》不同,它不是从伦理善恶的意义上来看生和死,而主要是从佛教形而上的层面上去建构。这一意义的生成与《王昭君》的形式相关,作品的形式使得悲剧的冲突建立在生死不可解决的冲突之上。
有人认为谣曲《王昭君》是一部梦幻能。梦幻能通常有幽灵的出现,作品的结构分为前后场两部分,而《王昭君》中确有幽灵出现,也分为前后两场,但是它和梦幻能的形式还是有所不同:前后两场的主角并非同一人,幽灵也不是出现于配角的梦幻,而是出现于镜子。从《王昭君》与梦幻能形式的同异来看,梦幻能对《王昭君》产生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些不是最重要的,《王昭君》创作为悲剧时,真正提供不可解决的冲突形式的是梦幻能的生死冲突的形式。梦幻能都要表现生死的冲突,而且主要是从死的角度来审视生。增田正造认为:“如果观阿弥展示了死亡世界的横断面,那么世阿弥则立足于死亡的时间展望生,即明确地带着回忆的时间意识进行创作。从死的世界展望生的时候,有可能使生的时间被压缩、停滞、逆行。”(注:增田正造《能的表现》,中央公论社,1996年第31版,第61-62页。)梦幻能在以生死冲突结构作品的时候,厌弃现世秽土,向往来世净土。现世和来世的冲突靠死亡来联结,但是死亡的联结并没有解决生的现世和死的来世之间的冲突,两个世界之间仍然是断裂的。里井陆郎曾就这一问题指出:“能这种新的戏剧艺术就受制于民俗传统方面而言,背负着比‘平家’更加难以回避的古代制约。但是以佛教发现和创造人性方面而言,它比‘平家”更深地触及到了中世的人类史。现实体验越是残酷,越是充满矛盾,佛教观念和彼岸净土的乌托邦世界看起来就越不可替代,这种人类的悲剧成为文学艺术的最大主题是理所当然的。”(注:里井陆郎《谣曲文学》,河原书店,昭和41年,第163页。)正因为佛教的乌托邦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沟壑无法填平,才构成了悲剧。《王昭君》同样也运用了梦幻能的悲剧结构形式,但是它没有采用死者亡灵回忆自己生前故事的方式从死的角度来审视生,而是由生者回忆死者的故事,因而是从生的角度来审视死。这一角度显然又异于梦幻能,但是二者之中生死的冲突是一样的,《王昭君》具有梦幻能悲剧的冲突形式。
《汉宫秋》、《王昭君》在从历史向悲剧作品的演变之中,都不断地赋予历史素材以伦理意义,并以此为基础构造了悲剧冲突。但是伦理意义在两部作品中的体现是不同的,前者以伦理作为最高原则,后者以形而上的佛教思想审视伦理的人间尘世。思想意义的不同,使得两部作品具有了各自不同的悲剧形式。
标签:王昭君论文; 汉宫秋论文; 汉朝论文; 日本生活论文; 历史论文; 后汉书论文; 西京杂记论文; 儒家论文; 东汉论文; 汉书论文; 历史学论文; 史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