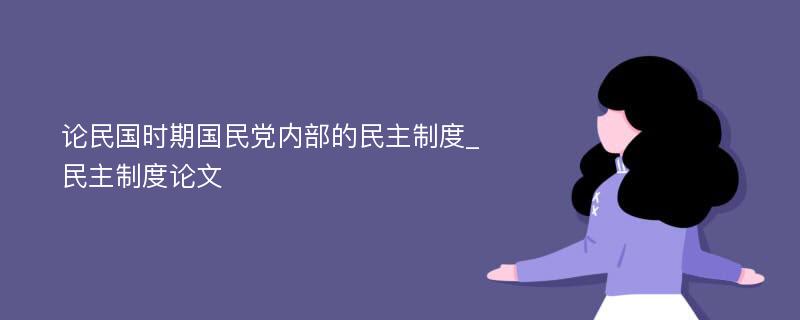
民国时期国民党党内民主制度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党内论文,国民党论文,民主制度论文,民国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民国时期,国民党曾经一度设计并试行过党内民主制度,但由于国民党的阶级本性与这一制度的内存缺陷,党内民主制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衍变为独裁制。本文即拟以此为主要内容,从一个侧面探讨—下民国时期国民党的结构变化。
一、国民党党内民主的制度设计
国民党先后经历了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等几个发展阶段,相应的,其组织结构和党内的民主制度也经历了一个演进的过程。最初的兴中会即规定了会内所议之事依照舍少从多之例而行的民主原则,但从兴中会到同盟会以至多党合并的国民党基本上均属于松散型的组织,组织制度和民主程序实际上无从执行,因此意见的分歧常常导致组织的分裂,宋教仁等由于不满华南革命战略而另起炉灶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即是其例。此后的中华革命党,试图建立强固的垂直领导,却又矫枉过正,窒息了组织的生命力。
大体而言,1924年改组前的国民党没有严密的组织,孙中山将改组前国民党的弱点归纳为:(1)革命精神的丧失;(2)群众基础的缺乏:(3)党组织的散漫;(4)党的纪律不够严密;(5)缺乏良好的宣传技术。当时的许多国民党员由于受极端平等思想的影响,以为党员应当绝对自由,反对任何束缚。廖仲恺曾提到:“本党自同盟会以来,即无精密组织,如民国成立改为国民党后,仅以议员为党员多少标准。其后经过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均属无甚组织。”[1]此语当为较客观的描述。
1924年国民党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进行改组,主要目的是要把国民党组织为一个有力量、有具体(政纲)的政党。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实行民主集中制。自此,国民党全党自下而上分为五级,即区分部、区党部、县党部、省党部、最高党部。分别以区分部党员大会、全区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全县代表大会、全省代表大会、全国代表大会为其权力机关;闭会期间则为区分部执行委员会,全区执行委员会,全县执行委员会,全省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各下级执行委员会受上级党部执行委员会之管辖,递级而直辖于中央执行委员会。
根据《国民党总章》,国民党党员有发言权、表决权、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国民党各级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均由党员大会和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应执行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国民党组织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在国民党内部应该说存在一定的民主制度。但是,《国民党总章》同时规定孙中山为总理,党员须服从总理之指导,总理为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主席,不要经过选举,总理对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有交复议之权”,对中央委员会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这种设计无疑对民主制度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据说,此举的根本用意是为了防止国民党内共产党势力壮大,但是在实际上却不免严重损害党内民主的真实性。尽管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从此不设总理,并且一度取消了所有中央机关中的首脑职务,而代以完全的集体负责制,然而国民党最初的组织制度设计中所表现出来的个人决断的倾向,却表明民主理念并未贯彻全党和全体党员之中,这就为党内民主的实施困难埋下了伏笔,也直接为1938年蒋介石就任国民党总裁,总揽一切党、政、军大权种下了前因。
二、国民党党内民主的实际运行
按照党内民主的制度设计,要想保障民主体制的有效运行,关键是两个方面,一是民主选举,一是民主决策,但是在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按照被经常引用的刘健群的那份导致了著名的法西斯组织“蓝衣社”的成立的《对改革国民党的一点意见》中的说法,取得了政权的国民党因受到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侵蚀已失去活力,党仅仅是军阀和官僚政客争权夺利和争夺贿赂成果的一个竞技场[2]。国民党无论是选举还是决策上都开始背离民主原则。
选举方面,在地方,国民党中央规定各级党部代表或委员候选人之资格年龄均应分别加以限制,在选举前必须由上级党部加以检定与考察;各级党部执行委员工作之分配除常务委员外,上级党部得分别指定。[3]地方党部的执行委员本应当由当地党员选出,结果县党部的执行委员却常由省党部的圈定或限定,而省党部的执行委员与主任委员一般由中央圈定或指派。为了加强对地方党部的控制,国民党中央还规定各省市党部书记长及铁路特别党部的秘书均由中央指派,或由地方保荐3人而由中央选定。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1928年10月,蒋介石等召集的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大纲),规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各省市党部只能选举全额之半,后又做出更为苛刻的补充规定,实际上绝大多数代表都由国民党中央圈定和指派产生(1929年召开的三大代表406人,其中指定211人,圈定122人,指派和圈定的占总数的81.2%)。这就引起了反蒋派别特别是改组派的严重不满,反蒋派组织的北平扩大会议称:本党组织为民主集中制,蒋则变为个人独裁。同时在国民党的各级组织中都出现了集体决策向个人负责,委员会制向首领制的变化过程,在中央是执行委员会内设置常务委员会以至重新恢复领袖制,在地方,省党部有主任委员,县党部有书记长,区党部有书记,党内民主渐成虚设。
反映国民党党内民主状况的一个典型的事例则是胡汉民事件。胡是国民党的元老,1931年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院长,由于反对蒋介石制定约法(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因胡汉民等人的反对,未能就制定约法一事作出决定),竟然被蒋软禁。当晚,蒋介石邀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到蒋宅赴宴,宣布他所杜撰的胡汉民的罪状,并提议次日召开中常会“同意”胡辞职推举林森继任立法院长。次日会上,据孙科回忆,会议情况是:“半分钟之久,无一发言,后蒋作默认,糊涂通过。”(注:《胡展堂先生被扣事件发生之经过》,载《为什么讨伐蒋中正》第100页,国民党广东省部执行任务委员会宣传科1931年编印。)胡汉民事件后,国民党元老们记取教训,“咸袖手结舌,莫敢一言”,民主空气丧失殆尽。
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是法律上训政期间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按《国民党总章》全国代表大会应两年举行一次,但是训政20年间国民党只召开了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以及1938年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共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家最高权力实际上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而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内,则又有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时行使其职权。事实上,中央常务委员会又常能变更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定。从中央执行委员会到常务委员会,权力便从数十至上百人的中央执行委员集中到常务委员会的数人至十数人。而这一权力集中的过程还远未结束,1935年国民党五届一中会议后,中央常务委员会设立了主席、副主席,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更恢复了一大通过的《国民党总章》规定的领袖制,设立党总裁,总裁对于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有交复议之权,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则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样就最终完成了蒋介石逐渐取得独裁地位的过程。
三、党内民主与代议民主
孙中山先生认为只有经过军政、训政两个阶段,中国才可以最终实现宪政。根据国民党的训政理论,在训政期间人民群众尚不具备独立行使民主权利的知识和能力,应由国民党代表人民行使治理国家的权力,同时逐步使民众在基层民主实践中得到训练,以最后达到能够自主行使选举、创制、复决、罢免等民权的程度,至此,国民党方可以还政于民。因此在训政期间国民党除了宣称在地方层次上实行自治以外(事实上直到制定宪法,宪政所要求的县自治也没有实现),在整个国家体系中没有设置民意机关,而仅仅以党内民主模拟代议制度。
以党内民主代替代议民主的理论基础是党员素质高于普通民众,具有更强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能力,这正是训政理论的基点。而以党内民主代替代议民主的客观可行性则要求党能体现人民大众的利益,这就要求党员的成分能够涵盖社会各领域及各阶层,同时党员人数在人口总数中达到一个相当的比例。以国民党的情况观之,截止到1945年国民党六大召开时,据吴铁诚在六大上的《党务检讨报告》,国民党党员人数达到6,926,400余人,从当时国民党控制区的人口看,党员人数已占到不小的比例,但是党员成份则相当不均衡,国民党正规军几乎全部被发展成党员,人数达400万人,而“占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工农民众,在党员数量中竟达不到半数。”[4]因此党员的代表性明显不足。
除了代表性方面的缺陷外,民主性也是—个问题。《国民党总章》规定,“各权力机关应接受上级机关之命令,并执行其决议”,“各下级党部执行委员会,须受上级党部执行委员会管辖”。由于上级对下级的决定权力和下级对上级的服从义务的存在,当上级的指令与同级权力机关的决议相冲突时,应服从上级指示,这种情况下,集中原则对民主原则的优先,就使党内民主的民主性大打折扣。以党内民主代替代议民主,使政治中心由议会斗争转为党内的派系斗争,但是由于政治派系往往与地方实力派相结合,最后政治斗争就演变成武力争夺,蒋介石与地方军阀曾发生多次这样的战争。这种武力争夺不仅损害政党团结,更严重破坏了党内民主的基础。
用党内民主模拟代议民主,出自训政理论的良苦用心,基于对民主进程的艰难性和复杂性的认识,希望通过一个过渡阶段来培养民主意识,训练人民的自主能力,最后再来建立全面的民主制度。但是党内民主和代议民主存在质的不同,首先在逻辑起点即有差异。在训政理论影响下的国民党党内民主的主张是一种精英主义的观点,即人与人之间觉悟的不同、能力的不同决定他们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而代议民主以平等主义为基础,认为人的理性具有平等地位,因此每个人都有权平等地参与政治生活。其次,党内民主与代议民主的不同还在于权力来源不同,国民党党内民主虽然也设计有自下而上的权力产生过程,但是为党员的义务本位所决定,在实际运行中起决定作用的则是自上而下的垂直指挥。1928年7月18日,蒋介石在北京大学演讲:“……简单一句话,党员只有义务,没有权利。”[5]《中国国民党党员守则)第七条规定:“服从为负责之本”[6],党员要无条件服从组织。而代议民主则以权力归属于全体人民,议员的产生是选举的结果,议员只是接受人民委托行使权力,议员要对人民负责,议员之间没有高下等级,没有行政隶属,议员只服从人民。最后,党内民主和代议民主的另一个不同,则是目的的不同,党内民主的目的是为了集中意见,得到最优决策,代议民主虽然也有决策上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作为民意的表达机制,并形成对执行机关的监督。在集权优先的情况下,党内民主往往仅具有一种工具性的价值,而代议民主是人民主权的实现方式,它本身就是目的。
国民党党内民主和代议民主的本质不同使得其以党内民主模拟代议民主,并进而谋求最终实现人民民主必须满足一些重要的条件,如应以吸纳成员的开放性保障其代表性,以权力机关选举产生保证其民主性,以保护反对意见的公开表达促进其决策的合理性等等,但由于国民党受到其阶级本性所决定,这几点根本不可能付诸实施,也就使其党内民主的设计最终归于失败。
四、余论
民国年间,国民党领袖亦曾一再表示要将党内民主付诸实践。1931年前,蒋介石就曾经在日记中写道:今后,“各省党部选举绝对自由,不再圈定,而—切议案亦绝对公开”(注:《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25日,毛思诚分类摘抄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党内的改革派孙科也曾经指出,只要党能民主化,国家就能民主化,但是一直到国民党退出大陆,此举也只是画饼充饥。究其原因,除了这是由国民党的阶级本性所导致的—个必然结果外,其制度方面的一些先天缺陷亦不可小视。米歇尔斯认为政党为实现其政治目的就必须要进行有效的组织,而组织就意味着领导,这些领导者将乐于把自己的角色看作是永久性的,要把自己锁定在权力上,而最后将导致少数人统治。他称之为“寡头统治铁律”,即无论开始如何民主,人类组织都将向寡头制转变。[7]民国时期的国民党是一个与结构松散的核心小组型政党和地方分部型政党有所不同的政治组织,对于国民党的一些领袖而言,该党首先是一个进行动员和组织的工具,而不是以争取选票、联系议员及建立议员与选民之间的接触为目标的机构,选举活动和议会斗争退居次要地位。这种结构实际上在一开始即暗含有集权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