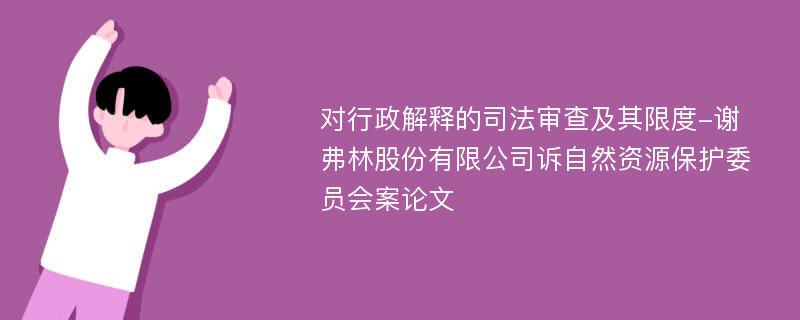
●经典判例
对行政解释的司法审查及其限度
——谢弗林股份有限公司诉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案*
吴 敏**译
内容摘要: 1977年《清洁空气法》修正案要求任何新建或修建的污染源都要经过许可审查。环保署最初将“污染源”界定为工厂中的任一排污设备。但在环保署1981年发布的规则里,却对“污染源”采取了以整个工厂为范围的定义。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向法院申请司法审查,法院认为《清洁空气法》及其立法史都没有涉及是以工厂还是以单个排污设备为范围来定义“污染源”。联邦最高法院最终认为应对“污染源”采取工厂范围的定义,因为环保署的解释在经济增长与改善环境的利益冲突间达成了平衡,所以是合理的。本案确立了审查行政解释的“两步法”:第一步是审查国会是否对争议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如果国会的意图十分清楚,则法院、行政机关都应服从于国会明确表示的意图;第二步是若国会未作出规定或规定是模糊的,法院也不能简单地适用自己的解释,而应判断行政机关的解释是否为法律所允许,只要行政解释是合理的,法院就应当予以尊重。
关键词: 气泡概念;行政解释;司法审查;谢弗林尊重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
案号:82-1005号
1984年2月29日庭审,1984年6月25日判决[注] 第82-1247号“美国钢铁协会诉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案”与第82-1591号“环保署行政官员威廉·洛克肖斯诉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案”也在本院复审。
判决摘要
1977年《清洁空气法》修正案规定,在未达到环保署制定的国家空气质量标准的州,对“新建或修建的固定污染源”实行许可制度。通常来说,污染源不会获得许可,除非它达到了严格的条件。在环保署1981年发布实施许可制度的规则中,州可以对“固定污染源”(stationary sources)采取以工厂为范围的定义,即若工厂有多个污染排放设备,那么在不增加工厂总污染排放量的情况下,工厂可以新建或者修建某一排污设备,也就是说,州可以将所有的污染设备都放在工厂这个分组之下,就好像它们都被包含在一个气泡内。被告向上诉法院提出司法审查,认为“气泡概念”(bubble concept)的规定违反了《清洁空气法》,应予以撤销。尽管上诉法院认为,在修订后的《清洁空气法》中,国会没有对许可制度中的“固定污染源”作出明确的定义,且立法史没有明确涉及这个问题,但上诉法院的结论是:由于许可制度的目的是改善而不是维持空气质量,工厂范围的定义与这一目标不一致,在维持空气质量的许可制度中强制适用这个定义是“不合适”的。
退役复学高职生在部队里经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和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与普通学生相比,他们有良好的生活作风、严格的纪律观念、良好的作息习惯和丰富的管理经验。他们发挥自身优势,能带动同学形成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好习惯。他们有过硬的内务整理能力,能指导同学做好宿舍卫生、宿舍美化、宿舍管理等工作。他们有一切行动听指挥的部队作风,能在高职院校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成为同学的榜样和标杆,并引领同学形成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2]。
本院判决:环保署以工厂为范围的定义是对“固定污染源”这一法定术语的合理解释。
从评估的几个维度中看,“体育舞蹈圈”在向盈利转型之前,用户价值需要利用更加立体化和更加实用的体育舞蹈服务内容来加以增长;客户价值的增长力度取决于行业内的资源整合;在拥有大量的粉丝群体后,行业内相关产业群体自然会主动加入进来,需求积极的合作。在微信公众号的也由“纯粹服务性质发展到“互惠互利盈利性质”的第一阶段是以普及项目文化为主的“内容为王”的前提来实现粉丝的快速增长;中期是以满足不同粉丝群体需求的“内容变现”以建立平台和粉丝之间长期和稳固的关系;后期是以“内容创新”引领粉丝群体的体育文化消费理念,更高层次的创造经济与社会价值。
1.对行政机关所执行法律的解释进行司法审查时,若国会对争议问题未作出明确规定,法院要判断行政解释是否为法律所允许。
2.对法案及立法史的审查证明了上诉法院的结论,即国会没有明确的意图在这些案件中适用“气泡概念”。
3.1977年修正案立法史中关于未达标区的部分清楚地表明,在许可制度中,国会试图协调资本发展下的经济利益与改善空气质量中的环境利益二者之间的冲突。
1982年10月14日,环保署发布了有关以工厂为范围定义“固定污染源”的规则。被告[注] Nation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Inc., Citizens for a Better Environment, Inc., and North Western Ohio Lung Association, Inc. 根据美国法典第42编第7606条(b)款第(1)项的规定,及时向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申请司法审查。[注] 原告Chevron U.S.A. Inc., American Iron and Steel Institute,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Chemica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Inc., General Motors Corp.以及Rubber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被允许参与到支持规则的辩论中。 上诉法院驳回了该规则。[注]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Inc.v.Gorsuch,222U.S.App.D.C.268(1982).
5.总体分析《清洁空气法》修正案,尤其是302条(j)款与111条(a)款第(3)项中关于“污染源”部分的规定,其并未揭示出国会在这些案件争议中的任何真实意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若任何国会“意图”都可以从法律用语中识别出来,那么法律解释的范围就会扩大,而不应限制环保署解释《清洁空气法》的权限范围。环保署在实施1977年修正案的政策上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立法史与这一观点是一致的。工厂范围的定义完全符合实现合理经济增长的政策,且环保署对它的结论作出了合理的解释:这些规则同样符合环保目标。不能基于环保署时不时地改变其对“污染源”的解释这一事实,从而得出不用尊重环保署法律解释的结论。从事制定各种规则的行政机关,必须一直考虑各种解释和政策的合理性。关于“气泡概念”的政策争议应当向立法者或者行政官员提出,而非向法官提出。环保署此处对法律的解释,体现了在明显冲突的利益之间合理的调节,并且有权获得尊重。
判决撤销原判决。[注] 222 U.S.App.D.C. 268, 685(1982).
法院判决
史蒂文斯(Stevens)大法官发表了法院的判决意见,其他法官也都参与其中,但马歇尔(Marshall)大法官和伦奎斯特(Rehnquist)大法官没有参与案件审理和判决,奥康娜(O’Connor)大法官也没有参与到案件的判决中。
第111条(a)款第(3)项中的“固定污染源”是指排放空气污染的“任何建筑、建筑物、设备或装置”。这个定义仅适用于法律明确规定的《新污染源执行标准》;法律文本本身并未要求在许可制度中适用该定义。原告因此坚持认为,除第302条(j)款定义了“主要固定污染源”(major stationary sources)外,没有与许可制度中的固定污染源定义有关的法律术语。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赞同原告。
法院在审查行政机关对其实施的法律作出解释时,会面临两个问题:第一,国会对争议事项是否有直接规定。如果国会的意图是明确的,那么问题就此了结;无论是法院还是行政机关,都必须遵循国会明确的意图。[注] 司法机关是法律解释的最终机关,应拒绝适用行政机关与国会意图相抵触的解释。参见FEC v.Democratic Senatorial Campaign Committee, 454 U.S. 27, 32(1981); SEC v.Sloan, 436 U.S.103, 117-118, (1978); FMC v.Seatrain Lines, Inc.,411 U.S.726, 745-746(1973); Volkswagenwerk v.FMC,390 U.S.261, 272, (1968); NLRB v.Brown, 380 U.S.278, 291(1965); FTC v.Colgate-Palmolive Co., 380 U.S.374, 385(1965); Social Security Board v.Nierotko, 327 U.S.358, 369(1946); Burnet v.Chicago Portrait Co., 285 U.S.1, 16(1932); Webster v.Luther, 163 U.S.331, 342(1896).如果法院采用传统方式解释法律,并查明国会在争议问题上的表意是明确的,那么这个表意就是应当遵守的法律。 但是,若法院认为国会未对争议事项作出直接明确的规定,法院也不能简单地适用自己对法律规定的解释,[注] 主要参见R.Pound,The Spirit of the Common Law 174-175(1921)。 虽然这一做法在不存在行政解释时是必然的。第二,如果国会对争议事项未作出规定或者规定是模糊的,那么对法院而言问题则是行政机关的解释是否为法律所允许。[注] 法院无需断定行政机关的解释是唯一允许采纳的解释,甚至如果这个问题最初在司法程序中提出也是如此。FEC v.Democratic Senatorial Campaign Committee, 454 U.S., at 39; Zenith Radio Corp.v.United States,437 U.S.443,450(1978); Train v.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Inc., 421 U.S.60, 75(1975); Udall v.Tallman,380 U.S. 1, 16(1965);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Comm’n v.Aragon,329 U.S.143, 153(1946);McLaren v.Fleischer, 256 U.S.477, 480-481(1921).
史蒂文斯大法官代表最高院发表意见。
1977年《清洁空气法》修正案规定,对于未达到环保署制定的国家空气质量标准的州(nonattainment States),对排放空气污染的“新建或修建的固定空气污染源”实行许可制度。通常来说,新建或修建的污染源不会获得许可,除非它达到严格的条件。[注] 第172条(b)款第(6)项规定:“(a)款计划的规定应……(6)根据173条的规定(关于许可要求),对建造及运作新建或修建的主要固定污染源实行许可制度。” 环保署在实施许可制度的规则中,允许对“固定污染源”采取以工厂为范围的定义。[注] “1.‘固定污染源’是指根据《清洁空气法》所规定的,产生或者可能产生任何空气污染的任何建筑(building)、建筑物(structure)、设备(facility)或者装置(installation)。 2.‘建筑、建筑物、设备或者装置’是指除船只活动外,所有属于同一工业组别、位于一项或多项相邻产业下,且由同一人(或多数人)管理的同一工厂内的所有污染物排放活动。” 即如果工厂有多个污染排放设备,那么在不增加工厂总的污染排放量的情况下,工厂可以新建或者修建某一排污设备。本案的争议是,州可以将所有的污染设备都放在工厂这个分组之下,就好像它们都被包含在一个气泡内,环保署的这种做法是否是对法定术语“固定污染源”的合理解释。
一
4.在1977年修正案之前,环保署曾对“污染源”使用过以工厂为范围的定义,但在1980年最后通过的规则中,环保署则大体上适用了上诉法院的基本论证思路,即在改善空气质量的未达标州中排除使用气泡概念。然而,当新的政府在1981年上台后,环保署在颁布此处争议的规则时,重新评估了关于“污染源”定义的各种争议,最后决定要在未达标区采取工厂范围的定义。
上诉法院认为修正后的《清洁空气法》中,“国会没有对许可制度中适用的‘固定污染源’作出明确的定义”,且这一争议“在国会立法史上没有直接发生过”。“未达标制度的目的应引导我们作出判决”,因此立法史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充其量是矛盾的。[注] 本院对此表示:“国会没有明确地在各种《清洁空气法》的制度中采用气泡概念,我们当然对此感到十分遗憾,我们认为进一步阐明立法意图,将有助于行政机关和法院为立法意图服务。” 上诉法院曾作出过两个适用《清洁空气法》中“气泡概念”的先例,在此基础上,[注] Alabama Power Co.v.Costle,204 U.S.App.D.C.51(1979)(以下简称阿拉巴马电力公司案); ASARCO Inc.v.EPA,188U.S.App.D.C. 77(1978)(以下简称美国冶炼公司案). 上诉法院表明,气泡概念仅仅在维持空气质量的许可制度中是“强制性的”(mandatory),而对于改善空气质量的许可制度则是“不合适的”(inappropriate)。在上诉法院看来,既然许可制度的目的是改善空气质量,那么在先例的基础上,气泡概念就不适用于本案。因此,上诉法院驳回与法律相违背的“气泡概念”规则。我们颁发调卷令来复审这个判决,现推翻原判。
1.门槛值估计结果。由表3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当东道国各项制度指标分别作为门槛变量带入式(3)时,各制度指标均存在单一、显著的“临界值”,无双门槛或更高阶的门槛值。这说明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东道国各项制度指标在影响改善东道国基础设施的中国OFDI的东道国经济增长效应上均有U型拐点。只有东道国的制度质量越过门槛值,中国用于改善东道国基础设施的OFDI才能带给东道国一定的经济增长,否则中国的这部分直接投资将带给东道国经济增长负面的影响。可见,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东道国制度对中国直接投资的东道国经济增长效应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上诉法院最基本的法律错误是,在国会未作出解释时,对“固定污染源”采取了静态的司法解释。被告没有对上诉法院的法律论证作出答辩。[注] 被告认为,环保署对“固定污染源”作出的以工厂为范围的定义与修订后的《清洁空气法》的条款、立法史和目的是相悖的。本院基于本法法律术语和立法史而反对被告的观点。本院确实赞同被告提出的规则与法案目的不一致的观点,但并未采纳被告此处对法条的解释。被告所依据的是上诉法院的观点,也可能是依据记录中任何支持判决的观点。参见Ryerson v.United States, 312 U.S.405,408, 61 S.Ct.656, 658, 85 L.Ed.917 (1941); LeTulle v.Scofield, 308 U.S.415, 421, 60 S.Ct.313, 316, 84 L.Ed. 355(1940);Langnes v.Green, 282 U.S.531, 533-539, 51S.Ct.243, 244-246, 75 L.Ed.520(1931). 然而,既然本院审查的是判决而不是当事人的主张,[注] 如Black v.Cutter Laboratories, 351 U.S.292, 297(1956);J.E.Riley Investment Co.v.Commissioner, 311 U.S. 55,59(1940); Williams v.Norris, 12 Wheat.117, 120 (1827); McClung v.Silliman, 6 Wheat.598, 603, (1821). 我们必须判断,在规则合理性这一问题上,上诉法院的法律错误是否会导致判决错误。
二
被告代理人是大卫·多尼格(David D. Doniger)。[注] 法庭之友的意见是撤销原判决,该意见来自于美国天然气协会(American Gas Association)的约翰·迈勒(John A.Myler)、美国中部法律基金会(Mid-America Legal Foundation)的约翰·卡农(John M.Cannon)、苏珊·瓦纳特(Susan W.Wanat)和安·谢尔顿(Ann P.Sheldon),以及太平洋法律基金会的罗纳尔·赞布伦(Ronald A.Zumbrun)和罗宾·里维特(Robin L.Rivett)。 法庭之友要求确认其诉状已经由宾夕法尼亚州司法部长罗伊·齐默尔曼(LeRoy S.Zimmerman)、托马斯·奥(Thomas Y.Au)、科罗拉多州司法部长杜安·伍达德(Duane Woodard)、助理司法部长理查德·格里菲斯(Richard L.Griffith)、康涅狄格州司法部长约瑟夫·利伯曼(Joseph I.Lieberman)、助理司法部长小罗伯特·怀特海德(Robert A.Whitehead,Jr.)、缅因州司法部长詹姆斯·蒂尔尼(James S.Tierney)、纽约州司法部长罗伯特·艾布拉姆斯(Robert Abrams)、助理司法部长马西娅·克利夫兰(Marcia J.Cleveland)和玛丽·林登(Mary L.Lyndon)、新泽西州司法部长欧文·金梅尔曼(Irwin I.Kimmelman)、佛蒙特州司法部长小约翰·伊斯顿(John J.Easton, Jr.)、助理司法部长梅雷德·莱特(Merideth Wright)、威斯康辛州司法部长布朗森·拉福莱特(Bronson C.La Follette)和助理司法部长玛丽安·苏米(Maryann Sumi)提交至宾夕法尼亚州等机构。 詹姆斯·英格利希(James D. English)、玛丽-温·奥布莱恩(Mary-Win O’Brien)和伯纳德·克莱曼(Bernard Kleiman)作为法庭之友,向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提交了诉状。
“行政机关执行国会法律的权力,需要通过制定政策和规则来行使,从而填补国会立法中明确或隐含的漏洞。”[注] Morton v. Ruiz,415 U.S.199, 231(1974). 如果国会明确地留下一个漏洞由行政机关来填补,这就构成对行政机关确定法律特定条款含义的权力的明确授权。这些行政解释具有很大的分量,除非它们是专断的、任意的或者明显与法律抵触的。[注] See United States v.Morton, 467 U.S.822, 834(1984)Schweiker v.Gray Panthers,453 U.S.34, 44(1981); Batterton v.Francis, 432 U.S.416, 424-426(1977); American Telephone & Telegraph Co.v.United States, 299 U.S.232,235-237(1936). 有时国会对行政机关在特定问题上的立法授权是不明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不得以自己对法律条款的解释来代替行政机关作出的合理解释。[注] 例如INS v.Jong Ha Wang, 450 U.S.139, 144(1981); Train v.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Inc., 421 U.S., at 87.
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应当重视行政机关对法律的解释,[注] Aluminum Co.of America v. Central Lincoln Peoples’ Util.Dist., 467 U.S.380, 389(1984); Blum v.Bacon, 457 U.S.132, 141(1982); Union Electric Co.v.EPA, 427 U.S.246, 256(1976); Investment Company Institute v.Camp, 401U.S.617, 626-627(1971);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Comm’n v.Aragon, 329U.S., at 153-154; NLRB v.Hearst Publications, Inc., 322 U.S.111, 131(1944); McLaren v. Fleischer, 256 U.S., at 480-481; Webster v. Luther, 163 U.S., at 342; Brown v.United States, 113 U.S.568, 570-571(1885); United States v. Moore, 95 U.S. 760, 763(1878); Edwards’ Lessee v. Darby, 12 Wheat. 206, 210,(1827). 尊重行政解释原则,一直为本院所遵循,只要有关法律的含义或适用范围涉及政策冲突的协调,以及在特定情况下全面理解法定政策的效力,那么作出决定就更多地需要依靠与行政机关所规制事项相关的知识。[注] See National Broadcasting Co.v. United States, 319 U.S.190; Labor Board v.Hearst Publications, Inc., 322U.S.111;Republic Aviation Corp.v.Labor Board, 324U.S. 793; Securities & Exchange Comm’n v.Chenery Corp.,322 U.S.194; Labor Board v. Seven-Up Bottling Co., 344 U.S.344. ……若这一选择代表了行政机关依法对政策冲突的合理协调,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对行政解释作出干涉,除非法律或其立法史表明这种协调是国会所反对的。[注] United States v.Shimer, 367 U.S.374, 382,383(1961). [注] Accord Capital Cities Cable, Inc.v.Crisp, 467 U.S.691,699-700(1984).
这清楚地表明,上诉法院误解了其在案件中审查规则时应扮演的角色。上诉法院在对法律进行审查后认为,国会实际上在许可制度中没有适用气泡概念的意图,问题不是气泡概念对于提高空气质量的许可制度总体上是否合适,而是行政机关在许可制度中的观点是否合理。在对法律及下述立法史进行审查后,我们赞同上诉法院的这一观点,即国会没有在这些案件中适用“气泡概念”的明确意图,但我们的结论是:环保署此处适用气泡概念是合理的政策选择。
三
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期间,国会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来鼓励和帮助国家减少空气污染。[注] 主要参见Train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Inc., 421 U.S.60, 63-64 (1975). 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修正案,“急剧增强了联邦在治理空气污染中的权威和责任”,但该修正案还是继续将“确保空气质量的主要责任”分配给了几个州。修正案第109条要求环保署制定《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National Ambient Air Quality Standard,简称NAAQS),[注] 首要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是指对保护公众健康十分必要的标准,次要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是旨在确定保护公众福利等级的标准。 第110条要求州在一定期限内制定执行该标准的计划(States Implement Plans,简称SIP)。此外,第111条规定主要的新污染源需符合技术执行标准;环保署应发布污染源分类的清单,并根据分类设定《新污染源执行标准》(New Source Performance Standard,简称NSPS)。第111条(e)款禁止任何违反执行标准的污染源运行。
第111条(a)款定义了在设定和执行新建固定污染源标准中使用的术语:“就本条而言:……(3)‘固定污染源’是指产生或者可能产生任何空气污染的建筑、建筑物、设备或者装置。”1970年的修正案中的这个定义不仅适用于第111条规定的《新污染源执行标准》,而且适用于第110条的规定,即各州的执行计划中应设定一个程序来审查拟建新污染源的位置,并在拟建新污染源妨碍达成或维持国家空气质量标准时阻止其建造。[注] 参见110条(a)款第(2)项(D)部分和110条(a)款第(4)项。
环保署在规定时间内制定了《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通过了《州执行计划》,且根据设备的不同分类,对《新污染源执行标准》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在其中一个制度中,环保署对“固定污染源”采用了工厂范围的定义。1974年,环保署对有色冶炼行业发布了《新污染源执行标准》,如果同一工厂内增加的排放量与其他部分减少的排放量相抵消,则该标准不会适用于主要冶炼区的改造。[注] 上诉法院最后判决以工厂为范围的定义是1970年《清洁空气法》所禁止的,参见ASARCO Inc., 188 U.S.App.D.C., at 83-84.这一判决在1977年修正案颁布后做出,因此当国会通过1977年修正案时,该标准开始生效。
关于“未达标区”,1970年法案规定,基本的《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在达标区适用到1975年为止。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州,立法目的并未实现。[注] See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Air Quality, To Breathe Clean Air, 3.3-20 through 3.3-33 (1981). 1976年,第94届国会就面临这一根本性问题以及许多其他污染控制问题。在这些地区,执行严格的计划来迅速减少污染从而消除社会成本,与经济发展总是存在法律上的利益冲突,因为执行严格的计划会阻碍工业发展,这同样伴随着社会成本。面对这些利益冲突,第94届国会无法在实现这些公共利益之间达成一致意见:针对未达标州的立法未能达成必要的共识。[注] 国会两院都通过了综合法案;但会议报告在参议院遭到了否决。
在这种情况下,1976年12月,环保署发布了一个《抵消排放解释规则》(Emission Offset Interpretative Ruling),从而在国会立法前“填补漏洞”。《抵消排放解释规则》旨在说明“根据《清洁空气法》制定的国家空气质量标准,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会限制或禁止新建或修建固定空气污染源的增长。”《抵消排放解释规则》规定,“只有满足严格的条件,新污染源才能在未达标区建立。”其重点在于尽快实现法律的环保目标。[注] 例如,《抵消排放解释规则》规定:“特别是对于基本的《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国会和法院都明确表明,经济考虑必须服从于《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达成和维持。但这个规则允许在未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地区有一定的经济增长,如果净效果能够确保在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且法案不允许以牺牲公众健康为代价来适应经济增长。” 与之一致的是,未达标州建立的每一个新污染源,必须达到这种设备在当前技术下的“最低排放量”(Lowest Achievable Emission Rate,简称LAER)。但是,1976年的《抵消排放解释规则》没有明确采纳或者反对气泡概念。[注] 1979年1月,环保署表明,1976年的《抵消排放解释规则》在这一问题上是模糊的:“许多评论家表示有必要对‘污染源’作出明确的定义。一些读者发现,根据1976年的《抵消排放解释规则》,有多个不同污染排放程序和设备的工厂是否可以被当作是单一污染源是不明确的。后来发生的变化是将污染源定义为‘位于一项或多项分类或相邻产业下,且由同一人(或多数人)所有或运营的任何建筑、建筑物、设备、设置、装置或运作(或其组合)’。为了确定抵消规则的适用性,这个定义不允许将大型工厂分割成单独的生产线。”
四
针对主要社会问题,1977年《清洁空气法》修正案作出了长篇的细节性、技术性、综合性的回应。这部法案中的一小部分,专门涉及了未达标区。这次争议的焦点就是修正案中的一个术语。[注] 具体来说,这些案件的主要争点是《清洁空气法》第172条(b)款第(6)项中的“主要固定污染源”的定义。第173条第(2)项中的“拟建污染源”的定义不是争议焦点。
法案要求每个未达标州在1979年7月1日前,准备并通过一个新的“州执行计划”。这期间,这些州要遵守环保署1976年12月21日发布的《抵消排放解释规则》。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期限被延长到1982年12月31日,一些案例中被延长到了1987年12月31日,但是所有“州执行计划”都要包含一系列尽快达成环保目标的条款。[注] 因此,除其他要求外,第172条(b)款规定,“州执行计划”还应: “(3)在此期间采取合理的进一步进展措施(参照第171条第(1)项的规定),包括通过合理技术管控来实现最低限度的现有污染源的减排; (4)包括每个区域内所有此类污染源(根据行政机关的规定)的实际排放量的全面而准确的清单,并尽可能多地提交和修订这个清单,对确保在第(1)项要求的日期前达到第(3)项的要求和评估达标所需额外减排量都是必要的; (5)明确识别和量化各地主要新建或修建污染源的建造或运行所允许产生的污染物(如果有的话); …… (8)包含排放限度、达标计划和符合本条规定所需的其他措施。” 第171条第(1)项规定:“合理的进一步进展”(reasonable further progress)是指空气污染每年逐步减少的排放量(包括早期为实施这一部分和110条(a)款第(2)项第(I)段规定的实质减排量和之后的固定减排量)足以使行政机关作出判断,可以在第172条(a)款规定的日期前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对环保目标来说最重要的是,法案规定每个“州执行计划”都应“要求新建或修建的固定污染源根据第173条的规定获得许可……”。第173条规定,在授予许可前:(1)州行政机关应确定本区域内有足够的减排量来抵消新污染源的排放量,且行政机关也要采取合理的进一步举措来达标,或者说增加的排放量不会超过第172条(b)款第(5)项规定的可允许的新建污染源的排放量;(2)申请人要证明他在该州的其他污染源符合“州执行计划”的要求;(3)行政机关要确保执行合适的州执行计划;(4)拟建污染源要达到“最低排放量”的要求。[注] 第171条第(3)项规定:“对任何污染源来说,‘最低排放量’是指体现如下特点的排放量: (A)任何州执行计划中对该类污染源所规定的最严格的排放限制,除非拟建污染源的所有者或运行商证明无法达到这样的限制;或者 (B)该类污染源在实践中达到的最严格的排放限制,以最严格的为准。”“在任何情况下,本条款的适用都不允许新建或修建污染源排放超过新污染源标准的排放量。” 与修订后的《清洁空气法》第111条规定的新污染源标准相比,最低排放量的要求更加严格。
1977年的修正案没有明确采用“气泡概念”,也没有明确定义“固定污染源”。尽管没有定义第111条(a)款第(3)项、《清洁空气法》以及《新污染源执行标准》中的“固定污染源”,但修正案定义了“主要固定污染源”(major stationary sources):“(j)除另有明确规定,‘主要固定污染源’和‘主要排放设备’(major emitting facility)指任何每年至少直接或可能排放一百吨空气污染的固定设备或污染源(包括行政机关规定的排放任何易变空气污染的主要排放设施或污染源)。”
五
1977年修正案中关于未达标区这一部分的立法史中,没有任何明确的评论是关于气泡概念的,以及对“固定污染源”以工厂为范围的定义是否为许可制度所允许。但立法史明确表明,国会在许可制度中试图协调资本发展下的经济利益与改善空气质量中的环境利益二者之间的冲突。众议院委员会报告将经济利益确定为法案第127条的“两个主要目标”中的一个。报告称:“法案第117条衍生了第127条这一全新的条款。第127条有两个主要目标:(1)在一定期限内采用合理的进一步举措来确保达标的同时,允许地区合理的经济增长;(2)对于前一目标,允许州拥有比环保署现有解释规则更大的灵活度。第127条的新规定允许未达标州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首先,州可以遵循环保署现有的‘折衷’(tradeoff)或‘抵消’(offset)规则,而且在与本条规定的目标相符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有权更改或者修改这个规则;州的第二个选择是根据新规定修订其执行计划。”[注] 在辩论中,国会议员韦克斯曼(Waxman)说该法案“在美国污染地区的环境管理和经济增长之间达到了平衡……没有其他争议能像污染控制和新的就业这样产生冲突。我们认为两者都不需要妥协……这是一个公正、平衡的方法,既不会破坏经济活力,也不会阻碍我们最终达成环保目标。” 与环保署的《抵消排放解释规则》和依照本条目的修改该规则的权力相比,第127条规定的第二个“主要目标”中允许州拥有更大的灵活度,是完全与国会无意将现有规定中“污染源”进行死板地定义的观点是一致的。
参议院委员会报告中关于未达标区的部分认为,应取代环保署的行政手段,且如果州能够“证明这些设备可以被达标计划所容纳”,那么这种扩大解释就应被允许。参议院报告注意到了“在未达标区逐个审查新建或修建主要污染源”的价值,并解释道,这种审查“需要将现有污染源的减排量与新污染源的预期排放量相匹配,以确保新污染源的引进不会在法定截止日期前妨碍达标。”对工厂设备进行逐个审查的方法,强调了新建或修建污染源产生的净后果(net consequences),也强调了对全面达成国家空气质量标准的影响,但参议院报告并没有提及本案产生的具体争议。
参议员马斯基(Muskie)发表了如下评论:“我认为,判断一个新建或修建的污染源是否适用环保署的解释规则——抵消规则,以及是否满足修订的执行计划的要求,其实是要判断污染源是否会向某地排放超过国家空气质量标准或者先例中所允许的排放量。因此,新污染源仍然满足‘最低排放量’要求,即使其是为替换旧设备以减少总排放量而建造的。”“包括转换煤设备在内的污染源,如果要对其进行增加空气污染排放量的物理改造,那么这种污染源就要作为修建污染源来适用未达标要求,因为该地区没有达到国家空气质量标准。”
数学全息定义的教学一般应强化.这里的强化主要指“三多”和“三化”,“三多”即多花时间、多思考(理解)、多应用,“三化”即正反例强化、逐步内化、螺旋深化.教师可通过设计一些典型的问题情境,让学生经历概念形成、概念理解、概念应用、概念分析的过程,并应组织好生生交流、师生互动等教学活动.非全息定义的教学一般不宜强化,只宜淡化,即不能要求过高,更不能深挖.
六
如前所述,在1977年修正案之前,环保署就已经坚持对《新污染源执行标准》中的“污染源”采用工厂范围的定义。在1977年修正案通过后,环保署至少在三个正式程序中都提议采用工厂范围的定义。
1979年1月,环保署考虑到一个问题:1976年12月的《抵消排放解释规则》中对未达标区新建污染源的限制,是否应同样规定在预计1979年7月生效的“州执行计划”之中。“存在多个不同排放点的工厂是否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污染源”,环保署注意到《抵消排放解释规则》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是模糊的,并对此作出两部分回答。在修订的“州执行计划”直到1979年7月仍未生效的地区,环保署拒绝使用工厂范围的定义;另一方面,环保署明确表明工厂范围的定义在得到“州执行计划”授权这种特定情况下是被允许的。环保署声称:“如果州执行计划被修订实施来满足法案D部分(未达标州的许可要求)的要求,包括采取合理的进一步举措的要求,那么许可制度可以免除存在内部抵消的现有污染源改建要求,这样在排放量上就不会有净增长。行政机关认可了这种豁免,这可以给污染源在最小的成本下,以更大的灵活性来有效控制空气污染排放。”[注] 同样是在《抵消排放解释规则》中,环保署补充说明:“上述豁免是‘州执行计划’所允许的,因为为了达到D部分的要求,1979年1月前修订的计划必须确保实现合理的进一步进展。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1979年1月采取的措施必须确保在法案规定的日期前达标,且在任何情况下,1982年采取的措施都能够达标。第173条所体现的国会的意图是,当州执行计划已根据D部分的要求被修订且正在被实施,那么州在一定限度内可以偏离《抵消排放解释规则》的严格要求。因此根据D部分下的州执行计划,如果改造伴随着足够的内部抵消以至于不会有排放量的净增长,那么就不需要改造现有设备来达到最低排放量和其他严格的要求。”
一人多高的钢铁棘球,在高速的旋转下,中心化作一团漆黑的月,外圈则是一环白色的晕。它携着一股金风,所过之处,砂石崩飞,在它身下的地面,留下了一道半尺多深的沟。
1979年4月和9月,环保署发表评论称,在特定情况下,未达标州修订“州执行计划”可以采用工厂范围的定义。之后,环保署作出了正式的提案,对工厂内的新建以及修建污染源允许采用气泡概念。环保署解释道:“‘气泡’豁免(‘Bubble’ Exemption):同一个污染源内的抵消可以称作是‘气泡’。”环保署建议在以下方面使用‘污染源’(source)这一概念,从而限制未达标州使用气泡概念:1.如果D部分的“州执行计划”包含了所有规定的合理的进一步举措,并能够确保在第172条规定的截止日期前达标,且“州执行计划”正在实施的,则无需限制使用气泡概念,‘防止严重恶化’的提案(prevent significant deterioration,简称PSD)也是同样如此。2.没有满足特定要求的D部分的“州执行计划”,必须通过将‘装置’(installation)定义为生产设备中可识别的一部分,从而限制使用气泡概念。[注] 环保署后来在《抵消排放解释规则》中进行了补充:“然而,环保署认为,整个D部分的州执行计划,如果包含了已通过且正在实施的确保达标的要求,则可以采用上述为‘防止严重恶化’地区提出的以工厂为范围的审查方法,而不审查单个设备。对污染源只采用以工厂为范围的定义允许工厂内的抵消,从而避免审查未达标州新建或修建的单个污染源。但是,这只有在‘州执行计划’能够实现确保达减少标所必要的现有污染排放量时才适用。如果‘州执行计划’允许的排放等级足够低,从而确保实现合理的进一步进展和达标,那么足够抵消可以防止排放量的增加,新建或修建污染源就不会危及达标。”
终孔后,在所需井管准备到位的情况下,开始冲孔换浆工作。本次采用捞渣筒从孔底捞取泥浆,水泵进行孔口补水的方式进行换浆,清孔结束后,孔内的泥浆密度小于1.05 g/cm3。
环保署相当明确地表明,在一些情况下可以对“污染源”采用工厂范围的定义,在其他情况下则要采用更狭义的定义。提案写到:“污染源是指任何排放或可能排放规定污染物的建筑物、设备或装置。在‘防止严重恶化’地区以及未达标区,除禁止空气污染增长和没有适当的‘州执行计划’存在或实施的地方外,‘建筑、建筑物、设备或装置’是指工厂。”[注] 在解释为什么在防止严重恶化的空气清洁的地方使用“气泡概念”特别适合时,环保署说:“此外,在工厂范围内使用气泡概念,可以鼓励自愿升级设备和提高生产能力。” 环保署对其提议的《抵消排放解释规则》的总结表明,其对各种政策和计划中的“污染源”这个术语采用了灵活而非严格的定义:“总的来说,环保署提议了两种方式来定义不同许可制度中的污染源概念:(1)对‘防止严重恶化’区以及整个D部分的‘州执行计划’来说,对工厂的审查仅按照不受限制的气泡概念。(2)对抵消规则、限制污染源建造以及部分D部分的‘州执行计划’来说,则要同时审查工厂和单个设备,这导致工厂范围的定义不适用于主要新建或修建的设备。此外,为限制建造污染源,环保署提议定义‘主要修建’(major modification)这个术语,从而彻底禁止气泡概念。最后,一个被讨论但未被通过的提案是,仅部分设备需要通过许可审查会导致工厂范围概念的舍弃,并会使得主要的设备规避未达标州污染源的许可审查,而不管这些设备是否在工厂范围内。”
1.1.1 常年在外,新房建而不住。大量流入城镇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往往会将赚到的钱用于老家建新房。由于他们常年在外打拼,实际上能够居住在新房的时间短暂。在家中无老人和小孩留守的情况下,新房一年会空置10个月以上,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
1981年,新的政府上台后,开始“在政府范围内对监管负担和复杂事项进行重新审查”。在此背景下,环保署重新评估了与如何正确定义“污染源”有关的各种评论,并得出结论:应在未达标区和防止严重恶化地区赋予这一术语相同的定义。
在解释这个结论时,环保署首先提出,“污染源”的定义问题在法律及其立法史中都没有明确提及,因此这一问题涉及“行政机关如何最好地执行法律”。环保署给出了几个理由,从而得出结论:工厂范围的定义是更合适的。环保署指出双重解释“可能会阻碍现有设备的修建,从而阻碍新的投资和现代化”,还“可能阻止用新的、更清洁的设备来代替旧的、高污染的设备,这实际上会阻碍空气污染控制取得进展”。而且,“如果在防止严重恶化地区及未达标区新污染源的审查和停止建造中,对‘污染源’采用相同的定义,那么新定义会简化环保署的规则。工厂范围的定义则可以减少混乱和不一致。”最后,行政机关解释道,剩下的其他替代性要求可以尽快实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根本目标。[注] 其他要求规定: “5.各州将继续遵守以下要求:所有未达标区应尽快满足《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要求,并在实现这一目标上有合理的进一步进展。因此,未达标区新污染源强制审查范围的修改不得妨碍法案D部分的基本目标。 6.《新污染源执行标准》会继续适用于大量新建或修建的设备,并确保使用最先进的污染管控技术,不论未达标区新污染源审查的适用性如何。 7.为避免未达标区新污染源的审查,进行改造的工厂须表明不会对排放造成严重的净增长。如果总排放量显著增长,将继续要求审查。” 这些结论在1981年8月的提案中得到体现,该规则在1981年10月正式公布。
七
在各项测量中,未经过相容性试验的橡胶试样的硬度测量结果为75.3 IRHD,平均体积为1 250 cm3,断裂拉伸强度为22.57 MPa,拉断伸长率为392.7%。相容性试验后的橡胶试样的各项参数变化如表1所示。
1.4疗效判定标准[2]患者PANSS减分率≥70%为痊愈;PANSS减分率在50%~69%为显著进步;PANSS减分率在30%~49%为好转;不满足上述标准者均视为无效,总有效率=(痊愈+显著进步+好转)/总例数×100%。
(一)法律术语
副检察长巴托(Bator)为所有案件的原告发表了代理意见。在“环保署行政官员威廉·洛克肖斯诉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案”中,副检察长李(Lee)、助理司法部长的代理哈比希特(Habicht)、助理司法部长沃克(Walker)、马克·利维(Mark I.Levy)、安妮·阿米尔(Anne S.Almy)、威廉·彼得森(William F.Pedersen)和查尔斯·卡特(Charles S.Carter)为原告提交了诉状。在“谢弗林股份有限公司诉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案”中,迈克尔·萨林斯基(Michael H.Salinsky)和凯文·方(Kevin M.Fong)为原告提交了诉状。在“美国钢铁协会诉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案”中,罗伯特·艾美特(Robert A.Emmett)、大卫·费伯(David Ferber)、史塔克·里奇(Stark Ritchie)、西奥多·加勒特(Theodore L.Garrett)、帕特里夏·巴拉德(Patricia A.Barald)、路易斯·托西(Louis E.Tosi)、威廉·帕特伯格(William L.Patberg)、查尔斯·莱托(Charles F.Lettow)和巴顿·格林(Barton C.Green)为原告提交了诉状。
然而1980年8月,环保署通过的规则实质上采纳了上诉法院在这些案件中的基本说理。环保署尤其关注上诉法院最近两个判决,这两个判决创造了一项鲜明的规则:“气泡概念”适用于维持而非改善空气质量的制度中。环保署十分重视这些判例,[注] “双重定义与阿拉巴马电力公司案和美国冶炼公司案是一致的。阿拉巴马电力公司案判决,环保署在解释‘污染源’这个法定术语上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从而最好地实现立法目的。因此,‘污染源’不同的定义可用于法律的不同条款中。 且阿拉巴马电力公司案和美国冶炼公司案都表明,《清洁空气法》中改善空气质量和维持空气质量的制度是不一样的…… 实行双重定义是顺应了阿拉巴马电力公司案判决,虽然环保署不能将‘污染源’定义为污染源的集合,但环保署对定义‘建筑’‘建筑物’‘设备’和‘装置’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从而最好地实现法律目的。” 并在未达标区对“污染源”采取了双重定义,即无论是对整个工厂还是其中一个设备的改变,如果会对污染排放造成显著增长,则都要获得许可,即使这个增长完全可以与工厂其他地方的减排相抵消。环保署认为这种解释比工厂范围的定义“更符合国会的意图”,因为这会“使更多的新建或修建污染源进入审查”,但环保署主要的法律分析还是着眼于上诉法院的两个判决。
第302条(j)款告诉我们“主要”(major)的含义——一个污染源必须排放至少100吨限排污染物,但该款规定并不涉及“固定污染源”(stationary sources)的概念。污染源的确等同于设备(facility)——第302条(j)款中“主要排放设备”(major emitting facility)与“主要固定污染源”是同义词。“设备”通常是指被设计或建造来达成一些目的的集成元素的集合。而且,将主要设备或主要污染源与工厂整体而不是其组成部分相关联,当然不是对常见英语用法的冒犯。但基本上,第302条(j)款的表述不会简单地强制用于“污染源”概念的理解上。
老K把教研室的暖水瓶们逐个灌满水,照例由大丫、舒曼和我,朝着每个灌满了开水的暖水瓶吐一口唾沫,再用小木棍搅一搅,盖上瓶塞儿。一人两只,提着去那幢灰色的小楼,分送到各个教研室去。
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明确反对上诉法院判决的基本说理。上诉法院非常灵活地定义了“污染源”这一法定概念:可以是广义上工厂范围的定义,也可以是狭义上覆盖工厂内每个区间的定义,还可以是适用于整个工厂和每个区间的双重定义。然而上诉法院将法定政策理解为,对维持空气清洁的许可制度授权采用工厂范围的定义,对改善空气质量的计划制度则禁止使用这一概念。被告则采取了本质上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们认为《清洁空气法》要求环保署使用双重定义——如果工厂整体或其中的部分,排放超过100吨污染物,则它就是一个主要固定污染源。因此,他们认为,环保署在1980年发布的适用于维持空气质量范围内的规则,以及1981年发布的适用于未达标州的规则,都违反了法律。[注] 被告认为:“但环保署可能不会将四个术语都仅指向工厂。1980年‘防止严重恶化’区的规则即是如此。环保署加重了此处所审查的1981年规则中放弃双重定义的错误。”
被告认可上述观点,并强调了第111条(a)款第(3)项的规定。尽管该条规定在字面上不适用于许可制度,但与法案一样,该条解释了“污染源”的含义。[注] 我们认为环保署实际上在许可制度的规则中适用了这种定义。 正如被告所述,将“建筑、建筑物、设备或装置”这些单词用来解释污染源,可以看作是将许可条件适用于工厂中的单个建筑物。[注] 由于规则允许各州选择将单个设备定义为污染源,原告就不会对按照被告的观点来解读这些术语作出争辩。 “一个单词可以有其自己的定义,而不必放置于它的语境之中。”[注] Russell Motor Car Co.v.United States, 261 U.S.514, 519(1923). 另一方面,单词的含义必须在特定背景中来确认,与之相关的单词也许表明,这一系列单词的正确含义存在共同点。合理地解释污染源这一术语,可以对分散但完整的污染设备施加要求。也就是说单个建筑、建筑物、设备或装置,而非其中的一部分,如果它排放的污染物超过100吨,那就都在污染源的定义范围之内。事实上,这个术语本身似乎暗含了气泡概念:所列举的每一项都像是包含在一个气泡内。然而被告坚持主张对这些术语都应分别赋予含义,他们还认为第111条(a)款第(3)项中“污染源”与第302条(j)款中污染源的定义相同。但第302条将污染源与设备(facility)等同,而第111条将“污染源”定义为设备,此处的设备只是其他四个术语中的一个。
我们并不认为整体分析法律文本中的术语就可以揭示出国会的真实意图。[注] 第173条规定了未达标区的许可要求,关于这一条的争议是典型的循环论证的例子。其中一个许可要求是“拟建的污染源要达到最低排放量”。尽管州可能会提交修订的“州执行计划”,其中规定了豁免“抵消条件”,但“州执行计划”不得规定对任何拟建污染源豁免最低排放量要求。被告认为以工厂为范围定义“污染源”,会造成工厂内新建的排污设备不需要达到最低排放量的要求,如果这些排放量与淘汰的旧设备产生的减排量相抵消。因此,根据被告的观点,工厂范围的定义会允许法律明确禁止的事项——对新建设备豁免最低排放量的要求。但被告的论点并没有依据,因为法律不禁止豁免,除非拟建的新设备确实受许可制度约束。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法律根本就没有强制执行最低排放量的要求,也没有必要涉及任何豁免问题。换句话说,第173条仅涉及定义“污染源”的后果,并没有对该术语作出定义。 我们非常清楚这些用语不是决定性的,术语之间有重叠,不能准确地确定给定术语在更大的语境下的适用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若任何国会“意图”都可以从法律术语中识别出来,那么国会对法律解释的范围就会扩大,而不应限制环保署实施《清洁空气法》的解释权范围。
(二)立法史
此外,被告声称立法史和《清洁空气法》的政策舍弃了工厂范围的定义,环保署的解释无权获得尊重,因为其解释是对先前解释的严重背离。
基于对立法史的审查,我们赞同上诉法院认为立法史对争点而言是不明确的观点。被告指出立法史中的评论显然不会仅针对这里争议的问题,也不能表明国会的意图……”[注] Jewell Ridge Coal Corp.v.Mine Workers, 325 U.S.161, 168-169(1945). 被告关于立法史的论点主要参照了参议员马斯基的观点,即新建污染源应符合“最低排放量”要求。[注] 我们认为,参议员马斯基没有批判环保署在1977年修正案生效前在《新污染源执行标准》中使用气泡概念。 但这个参议员整体的陈述就像第173条一样是模糊的,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新建污染源,更不用说作出明确的定义。我们发现立法史在整体上没有涉及争议问题。但环保署应在执行1977年修正案上拥有广泛裁量权,立法史的观点与之一致。
更重要的是,立法史解释了推动法律实施的政策问题;工厂范围的定义完全与其中一个政策一致——允许合理的经济增长,无论我们是否相信这个政策能够最有效地实现其他政策,我们必须承认环保署对它的结论作出了合理的解释:这些规则同样符合环保目标。事实上,环保署的说理得到了政府机构的支持,且这种支持在规则制定过程中进一步发展,[注] 例如,纽约州环保部门的声明指出,否定污染源所有者的灵活选择权,会使得“运行旧的、污染更多的污染源比更新这些污染源更加简单、低廉”。 一些特定私人研究也是如此。[注] “经济学家提议用经济激励措施来代替繁琐的行政立法。目的是使市场上的利润和成本激励措施在污染控制上发挥作用……‘气泡’或‘净排放’概念是在这一方面的首次尝试。通过让工厂管理者灵活地寻找工厂内最方便控制污染排放的位置和流程,可以更快速、更低廉地实现污染管控的目的。”L.Lave & G.Omenn, Cleaning Air:Reforming the Clean Air Act 28(1981).
审查环保署对“污染源”的各种解释(包括1977年修正案前后的解释)使我们确信,主要负责执行这部重要法案的行政机关,一直灵活地解释着这个概念——不是停留在枯燥的文本上,而是结合了执行政策这个充满技术性的、复杂的环境。行政机关时不时地改变它对“污染源”的解释,被告所说的这个事实,不能使我们得出不尊重行政机关法律解释的结论。行政机关最初的解释并不是立竿见影的。相反,从事制定各种规则的行政机关,必须不断考虑到各种解释和政策的合理性。而且,行政机关在不同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的定义这个事实,更加有力地证明了定义本身是灵活的,特别是国会从未表示过不赞成灵活地解释法律。
值得注意的是,在1980年,不是行政机关而是上诉法院,对法律的解释缺乏灵活性:对维持清洁空气的许可制度中采取工厂范围的定义,而改善空气质量的许可制度中则禁止这种定义。上诉法院所描述的区别是合理的,但我们对这个问题费力的审查无疑表明,在法院开始审查法案前,国会未曾清晰表述过这个区别,环保署也没有从法规中发现这一区别。我们认为是上诉法院而不是国会或任何国会授权执行法律的决策者,要对1980年的立场负首要责任。
经济增长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家讨论的热点话题。关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多将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等因素视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往往忽略了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在西方兴起。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快慢与其制度安排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三)政策
当事人诉状中提出的政策争议产生了这样的效果:被告正在发动一个关于政策争议的司法论坛,最终在行政机关和32个选择适用气泡概念的司法管辖区中失败了,但被告从未在国会中发动过政策争议的讨论。这样的政策争议更适合向立法者和行政官员提出,而不是向法官提出。[注] 被告指出,如果一个排放超过100吨污染物的新工厂要建在未达标区,这个工厂必须根据第172条(b)款第(6)项的规定获得许可,且工厂必须满足第173条的条件,包括最低排放量。被告认为如果一个内含多个大型排污设备的旧工厂,要通过用排污更少的新设备(但仍超过100吨)来代替排污超过100吨的旧设备,从而实现现代化,那么结果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因为“这不是建在一个新地方,而是建在一个已有的工厂内”。
在这些案件中,行政解释代表了对明显冲突的利益的合理调节,并且有权得到尊重:行政管理事项充满技术性和复杂性,[注] See Aluminum Co. of America v. Central Lincoln Peoples’ Util. Dist., 467 U.S., at 390(1984). 行政机关用一种精细、合理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注] See SEC v. Sloan, 436 U.S., at 117; Adamo Wrecking Co. v. United States, 434 U.S. 275, 287, n.5(1978); Skidmore v. Swift & Co., 323 U.S. 134, 140(1944). 且行政决定要协调政策冲突。[注] See Capital Cities Cable, Inc. v. Crisp, 467 U.S. at 699-700; United States v. Shimer, 367 U.S.374. 国会曾试图协调两种利益冲突,但在这些案件的具体层面上,国会并没有这么做。或许国会有意让行政机关在个案中寻求平衡,因为考虑到行政机关拥有大量的专业知识且负有执行法律的职责,因而更适合协调利益冲突;又或许国会根本没有在个案中考虑过这个问题;再或许国会无法在这个问题的任一边达成一致,从而决定利用行政解释来解决问题。对司法目的来说,哪个假设成真并不重要。
[例5]James reverses the usual mask of the young writer.(1972:283)
法官不是解决政策争议的专家,也不是政府的任何一个政治分支。在一些案件中,法院必须协调政治利益冲突,但不能依据法官个人的政策偏好。相反,负责政策制定的行政机关在国会授权范围内,可以适当依据现任政府合理的政策来形成自己的判断。行政机关不直接对人民负责,但行政首长向人民负责,且由政府的分支机构来作出政策选择是完全合适的——解决国会无意解决或者有意交由负责根据实际情况执法的行政机关来解决的利益冲突。
后来人类发现了金属,用铜和铁制造工具,制造铜鼎和铁容器烧煮食物,分别被人类学家称之为“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烤煮食物的用具被称之为“锅”,人类熟食方式逐渐成熟起来。
当行政机关概念化的法律解释遭到挑战时,如果实际的争议焦点是行政机关的政策是否明智,而不是对国会法律漏洞的处理是否合理,那么挑战就会失败。在这些案例中,联邦法官并非由选民选出,其有义务尊重行政机关作出的合法的政策选择。司法的职责不在于评价这些政策选择是否明智,也不在于解决公共利益冲突:“我们的宪法将这样的职责授予行政机关。”[注] TVA v. Hill, 437 U.S.153, 195(1978).
我们判决环保署对“污染源”的定义是法律允许的解释,因为这个解释试图协调减少空气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冲突。“行政机关所适用的规则可被认为……对这双重目标作了有效协调……”[注] United States v. Shimer, 367 U.S., at 383.
撤销上诉法院的判决。
特此判决。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Interpretation and Its Limits :Chevron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Wu Min (Translator )
Abstract : The Clean Air Act amendments of 1977 establish a permit program regulating “new or modified major stationary sources” of air pollution. The EPA initially defined the term “stationary source” as any discharge equipment in the factory, but the regulations promulgated by the EPA in 1981adopt a plantwide definition of the term. The Natural Resources Protection Committee applied to the court for a judicial review of the regulations. The Federal Supreme Court held that neither the Clean Air Act nor its legislative history mentioned the definition of “stationary source” in the context of factories or individual equipment, and ultimately determined that the plantwide definition is reasonable because the EPA’s interpretation struck a balance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improving the environment. This case established a “two-step approach” to the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interpretation: the first step is to examine whether Congress makes clear provisions on contentious issues, and if the intentions of Congress are clear, the courts and administrative organs should be subject to the intention of Congress. The second step is that if Congress did not provide or the provisions were vague, the court could not simply apply its own interpretation, and the court should judge whethe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 was permissible by law, and as long as the administrative interpretation was reasonable, it should be entitled to deference.
Keywords : Bubble Concept; Administrative Interpretation; Judicial Review; Chevron Deference
中图分类号: D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7076( 2019) 02- 0149- 12
DOI: 10.19563/ j.cnki.sdfx.2019.02.015
* *Chevron, U.S.A., Inc.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Inc., 467 U.S. 837(1984).
判例的主标题、内容摘要、关键词系译者所加。为了符合中文的行文规则,原判例正文中引注的案例和法条,一律改为当页脚注,且每页重新编号。——译者注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施立栋)
标签:气泡概念论文; 行政解释论文; 司法审查论文; 谢弗林尊重论文;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