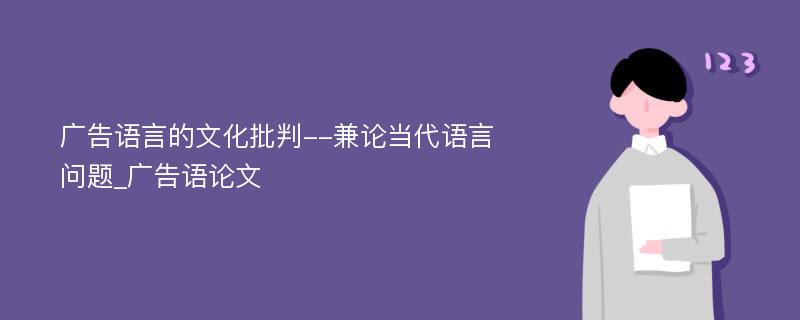
广告语言的文化批判——兼论当今时代的语言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论文,当今时代论文,广告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言和人及其文化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同时也是当今最热门的哲学思考问题之一。每个民族的文化和历史都蕴含在她的语言中,而不同的时代又会有不同的语言景观。当今时代,最热闹最引人注目的语言现象,也许莫过于广告语言了。当这种形式的语言向我们扑天盖地涌来时,所引发的问题和思索是非常复杂的。
广告:语言范式的塑造者
历史地看,语言在任何一个民族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都是一个“集体的生活”。在这种“生活的形式”中,由于人们的约定,作为游戏的语言的各种规则便被制定出来,从而构成了一定时代的语言规范。在前大众传播时代,由于交通和通讯的不发达,由于文化上的各种界限和封闭性,使得语言带有相当程度的差异性(如地区的、群体的以及家族的等),带有相当程度的恒常性。那么,到了大众传播的时代,各种电子的或印刷的媒介的爆炸性发展,使得语言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特征。占绝对的“霸权”地位的广告语言超越了其他各种语言形式独占螯头,以一种凌越其他各种语言的态式,以它自身的规则、逻辑和技术,无情地改造着当前的文化现实,改变了过去人们所熟悉和怀念的传统文化景观。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的广告语言,在当代“集体生活”中具有无与伦比的语言塑造功能。它凌越于任何其他语言活动形式之上,成为影响社会生活和人们意识形态最重要的话语,它是作为一种非个人化的体制性因素来实现着语言的塑造功能,重新塑造着我们的意识形态和语言习惯,改变着人与物的关系。在这同时,它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造了我们的语言甚至借助语言而进行的思维。它进而制定了新的语言“游戏规则”,通过它不可取代的至高地位,事实上在实行一种看不见的“排斥游戏”,即把那些与之相对立的表达方式排斥在外,剥夺它们的生存权。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对传统语言的肆意篡改和拼接,取消了传统语言及其表达方式的特定历史文化意义和特定用法,造成了“语法的混乱”。
广告语言在当代文化中具有其他语言所难以具备的强有力的塑造功能,主要表现在:首先,在当代文化生活中,广告是借助大众传播媒介而运作的一种信息形式,这使得广告的语言效应远远超过了任何其他语言形式。特别是经由电子媒介的大范围传播,广告所特有的语言表达方式是深刻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语言力量。象电视和广播这样的电子传媒在传播范围和重复频率上,是任何其他媒介所无法比拟的,因此,电视广告的语言,特别是广告口号或标题语,对人们的语言习惯乃至思维,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力量。试想一下,一位知名作家的具有“轰动效应”的文学作品,充其量不过几十万册,而电视的传播范围从来就是按百万甚至亿来计数的。其次,广告语言在其传播形态上,更是“盛气凌人”,与文学和其他艺术传播的方式相比,电视这样的传媒显然是一种单向的传递过程,是从信息发送者经有媒介再到达接收者的单向的不可逆的过程,反馈在其中如果有,那也只是一种“延迟性的”。它有一种和阅读诗歌小说或街头闲聊全然不同的传播特征,以一种强迫的方式直接诉诸受众,不管你我他的个人需求、欲望和个性,甚至把我们并不需要的商品信息一鼓脑地强加给我们。最后,广告的语言无论在形式上有如何翻新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所有广告的语言信息都是同质的,都服务于一个无法改变的目标,那就是以各种方式来诉求任何一个可能的消费者,刺激他的消费欲望,并最终达到使之购买特定产品。美国广告大师奥格威说得最白不过了:“我认为广告佳作是不引起公众注意就把产品推销掉的作品。它应该把广告诉求对象的注意力引向产品。诉求对象不是‘多美妙的广告啊!’而是,‘我从来没有听过这种产品。我一定要买它来试试。’”[(1)]这样的信息在语言形式和表达技巧上的变化是在增强了语言的诉求力量的同时,也在把一种同质的信息甚至同质的形式强加给普通受众,因而广告语式有着非同一般的强大的语言范式塑造功能。
这么来看,对广告语言的思考,就既不是广告学的思考,也不是纯粹语言学的思考,而应该是一种批判性的文化思考。
“语法的强暴”
我们知道,语言的发展形成过程是十分缓慢的,一种语言的演变是经过长期的约定和妥协而得到发展的。一旦形成具体的游戏规则,特别是语法,也就构成了一种语言的有效性的前提,构成了群体内成员可以互相交流沟通的法则。在这个意义上说,语法是不可随意改变的语言逻辑。在文化史上,对日常语言的语法改造最具挑战性的莫过于诗人作家了,他们在语言的“陌生化”探索中,改变了日常语言的使用规则,并赋予诗的语言以全新的丰富涵义。但需要指出,诗人对日常语言,特别是其语法的改造,是在“诗的语言”范围内展开的,它并不对日常语言构成直接的现实的威胁。广告则不同,它是日常语言,所以,广告语言对语法的改造就不是一个只限于文学想象性生活的问题了,它对日常语言乃至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造成深刻的影响。
抽象地看,语言的变化实际上是一种范式的变化,所谓范式是指构成一种语言的基本规则和用法的那些“游戏规则”。按照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定义,就是某个知识共同体成员对特定知识的系统的原理公式和逻辑的一致认可。科学理论的变革,正是这种共同体成员对旧范式的摈弃和对新范式的认可。[(2)]其实,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是具有普遍性的文化现象,即是说,人类文化的许多领域实际上都存在着这样的范式的演变,语言领域也是一样。我们有理由假定,语言的演变说到底也是一种范式的变化,而由一种范式到另一种范式的演变,也是一个受制于语言共同体——即所有正在使用某种语言的人——的发展变迁过程。在前大众传播时代,日常语言的发展变化是通过语言共同体内的相互约定而形成的,这就构成了一种复杂的相互认可和妥协的互动过程。一种新的哪怕是稍有变化的表达式或词汇的出现,无论它是来自个人和某个小集团,都要经过这种复杂的互动过程。
如果我们把当代文化语境中广告的作用和历史上的这种状况作些比较,就会发现借助大众传媒传播的广告语言在改变语言范式时的新特点。它不再是一部分人使用的特异语言(文化方言),它显然具有超越各种文化差异之上的普遍语言或共同语言的性质;它也不是对日常生活语言的模仿,毋宁说,是日常生活语言在模仿广告语言;更重要的是,在语言发展的历史上,它作为非个人的体制性力量而获得了某种特殊的强制力,它可以超越语言共同体的制约和约定,自行制定语言的表达方式和词汇组合,它不经共同体的“批准”,也不必和共同体成员妥协,更不把共同体中的专家“内集团”放在眼里,我行我素地发布着自己确认的语言“游戏规则”,并通过大范围的深度传播,迫使受众接受它自己的语法。唯其如此,可以说,广告语言获得了一种历史上任何一种语言形式都不曾具有的“话语特权”,一种可以违背语言日常用法和词典意义的“特权”。借助大众传媒,没有一种传统的语言形式可以和他相抗衡。这就涉及到当代广告语言的一个典型症状——“语法的强暴”。所谓“语法的强暴”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主要是指广告语言是一个相对的自律系统,它并不受制于日常语言的种种规则和使用该语言的共同体,反过来,它所设定了自己的规则,却对日常语言造成了混乱。这就构成了广告语言肆意强暴日常语言和诗意语言的普遍现象。这种语法的强暴体现在许多方面,其显著者主要有:
首先,我们注意到广告语言有一种忽略人们约定的日常语言规则的倾向,肆意扭曲和改变约定的语言用法和意义。如今广告语言中最为流行的,莫过于对汉语中最具生命力的成语的任意篡改。诸如“步步为赢(营)”——李宁牌运动鞋,“咳(刻)不容缓”——桂龙牌咳喘宁,……表面上看,这种广告语言只是一字之改,但问题在于,这样武断的篡改不但消解了成语几千年来的约定意义和用法,更重要的是,这种人为的篡改,把蕴含在成语中的丰富历史语义和内涵挤榨殆尽,剩下的只是与特定商品相关的某种片面、狭窄且武断的语义。这就排斥成语的原初意义和历史蕴涵,粗暴地攫历史语言遗产于一个特定口牌的商品,进而导致了成语的传统意义的丧失。此外,广告语言还武断地改变比喻的原初意义,或人为地强制地组合词语,或在追求创意的同时,对语言自身表达方式和规则而不顾,更是导致了一些完全越轨的表达式,有的是逻辑上的混乱,有的是意义上的强制性撮合,有的是语序的混乱……等等。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一个有规律性的现象,在广告语言的所谓“创意组合”中,汉语的基本语法规则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可以人为地任意破坏和篡改,并强制地诉诸每一个受众。于是,广告人作为当代文化中的一种特殊角色,具有不经共同体商量即可发布新的语式和表达式的特权。
更进一步,广告语言“语法的强暴”,还表现在它对日常语言和诗的语言的自由改变,导致了一种广告的“陌生化效应”,使得各种新奇古怪的表达式接踵而来,并反过来又强化和刺激了追求新奇古怪语言表达的倾向。如果说在文学中,语言的陌生化是一个基本的艺术规律的话,那么,广告语言中的陌生化是既不遵循诗的语言的那些用法规则,又同时违背了日常语言的基本要求。广告语言在自身创意的过程中,由于特定的表达式的形成,便开始对语言本身各种地域的文化的和历史的差异进行疯狂消解和同化,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同一性语言。这种对语言固有的差异的消解,主要是通过抽去各种表达式和语句的原有语境,进而构成一种脱离原有语境的意义生成,最终导致语言的差异的溶解。最典型的语言表达有如下几种:将英语或其他西文直接溶入汉语的表达式之中,如“海信电视,IIisense”、“酒的王朝,Dynasty”,这里,汉语的语音和英语的语音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语言杂烩的特有景观,对于不懂洋文的受众来说,这样的表达制造了一种不伦不类的联想效果;对于懂得洋文的受众来说,汉语的表达则被引向英文意义的思索,从而使得汉语变成了一种陪衬性的语言,而英语在这里反倒成了本体性的语言;再比如,把各种不同语言词汇的使用语境抽去,造成一种对消费者迷惑的效应,这特别明显地反映在有些商品为了提高其“高技术含量”,有意引进或生造科学的术语,从而形成了当前广告语言的又一特点。像“维他命原B5”、“保湿因子”、“贝质素”一类的广告语言随处可见。当这类科学的术语失去了其固有的语境时,在日常语言的范围内任意使用,只能是对日常语言的强暴。像借用古代典故传说来重塑语言的例子,更是屡见不鲜,三国、水浒、红楼梦、西游记……,古典的语言变成为现代的煽动术,历史的意蕴在几十秒时间里,被塞入一个品牌的拙劣吹嘘,如桃园三结义成了酒的主题……当语言的原有语境被抽去,并塞进某一产品的狭窄意义域时,语言被扭曲了,意义被扭曲了,历史被削平了,语言的深度由此而丧失了。
广告语言的“语法的强暴”还有更深一层的涵义,这就是它的虚拟同一主语语态——“我们”。广告语言的主体假定了一种和听众同一的身份角色,以集体的主语称谓“我们”的认同来拉近与受众的距离。在这种完全缺乏对话性的广告独白中,所谓的“我们”本质上不过是一种对受众的语法的强暴,即以一种包容的虚拟语态把每一个接收这条信息的人囊括其内,实际上,正是在这种广告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的虚假认同过程中,发送者把自己的意志和选择强加给了接收者。“听自己的,喝贝克啤酒!”这则广告的语言充分说明了在广告语言的把戏中虚假认同的真正目的。这自己是谁?当然不是受众自己,而是那个要自己喝贝克啤酒的非个人化的主体。至于像“挡不住的感觉”这类无人称的表述,也同属虚拟的集体主语之列。在某种意义上说,广告语言中的这种虚假的“我们”,是通过一种公众假定的普遍认同来达到消除受众中的“你”和“他”,消解个性的乃至群体的文化差异,进而使人们的消费行为甚至意识形态达到一致性。这里,我们真正瞥见了广告语言的“语法的强暴”所透露出来的语言的政治学特征,即广告语言单向的、不可逆的具有凌越地位和权力的压抑和排斥本性。
诗意模仿的反诗意本质
广告是我们时代的文化仪式,它成了人们每天都必须“参与”的“布道”,因为广告这种符号活动与一种潜在的“宗教”——拜物教——密切相关。但是,有一点看来值得深究,即作为一种纯粹的商业性诉求活动,广告的心理学功能在于最终说服和打动受众对某种商品的认可,进而驱使他们产生购买和消费行为。这种赤裸裸的商业心理学功能,却往往是在其语言极具迷惑性的诗意运用中实现的。换言之,广告语言的诗意模仿具有反诗意的本性。
国内的广告目前已经告别了最初直白式的诉求,进入一个追求雅致和风格的语言表达阶段。于是,直接的商业性内容被包裹在更加富有文学色彩的语言表达方式中,而一些学者所谓“广告美学”的鼓嗓,不过是为他们自己知识运用的合法性寻找一种虚假的根据而已。在“美学”和“诗意”包裹之下的铜臭,堂而皇之地成为一种文化主角,获得了一张合法的许可证,进而可以自由地进入传统高雅文化形式才有资格徜徉的文化殿堂。这里,我们特别要指出一个本来显而易见的现在却被“美学”混淆了的事实:广告语言的诗意表达具有一种反诗意特征,即它以诗意为手段,目的并不在于诗意本身,毋宁说,它是采取了更加隐蔽和更加有效的语言表达来实现不可变更的诉求目的。“南方黑芝麻糊”的语言表述采用了诗意的怀旧方式,“奥妮皂角洗发膏”则运用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表达式,“伊犁特曲”采用美国西部牛仔的粗犷风格,等等。
语言是我们赖以生存在的家园。通过对事物的命名,语言召唤了存在,并使之呈现于无蔽的状态之中。语言的这种功能最明显地反映在诗意的语言中。所以,海德格尔说,诗人是我们家园的守护人。那么,广告语言如何呢?显然,它与其说是呈现一个世界,不如说是蒙蔽了世界;与其说是凝定了存在,不如说是放逐了存在;与其说是为存在命名,不如说是为欲望命名。
我们知道,语言是一种符号,具有基本的命名功能。伽达默尔指出:“这里有一种对当下的距离,一种对于将临之事的瞻望。人并非仅仅被给予或提供眼前之物来对我们造成作用。正如我们在语言的本质中所发现的,语言是一种距离。”[(3)]我以为,语言的距离是诗意语言本质。在诗的语言中,诗人对事物的命名,使之从遮蔽状态中走到无蔽的呈现之中。但是,在诗的语言中,语言在呈现存在时,并不在于使人对所呈现的事物有一种直接的占有欲,相反,它使人们可以在一定距离之外(审美距离)静观事物,发现其存在样态和变化,观照其作为物的物性自然显现。在这个特定的比较意义上说,诗的语言是一种有距离的语言,它在对事物的命名中,在对存在的揭示中,形成了超越性。它通过命名唤起了人们的想象力,在体认事物存在的同时,进入了更加广大的想象空间自由翱翔。但广告语言在多方面则完全不同,比较而言,它是一种要消灭距离的语言。在广告的语言表述中,核心问题是如何使语言这种抽象的符号紧密地和某种特定的商品联系在一起,甚至作为它的符号表征。这样一来,广告语言的基本功能就不是距离,而是同一。它所导致的看似丰富的各种意义,实际上万变不离其宗地回归到商品的品牌及其有用性上。它所导致的“诗意的唤起”,最终却以消灭“诗意”为目的,即对商品的欲望是压倒一切的考虑。这表明,在广告语言中,诗意的真正用途正在于反诗意的本性。因此,它就显然只是一种限制性的语言,而不是超越性的语言,因为,在它的直接诉求中,受众的想象力被遏制了,无一例外地被引向某商品及其占有的欲望上。正是如此,它对事物(商品)的命名,实际上不是对事物的事物性的揭示,不是对物的存在的敞亮,相反,其命名是对物所以为物的存在的遮蔽。
另一方面,诗的语言是一种事物的语言,诗人在其中作为守护者,是把事物自身显现出来,让事物自己说话。诚如伽达默尔指出的:“事物是有自己存在的东西,像海德格尔所说:是‘不能强迫它什么都做’的东西。事物自身的存在由于人所想操纵事物的专横意志而被忽视了,它就像一种我们不能不听的语言。”[(4)]即是说,诗人是最善于倾听事物语言的人,他们把听到的东西告诉我们,他们是让事物自己说话。唯其如此,我们在诗里听到大自然的呼唤、倾诉和哀怨,我们听到了万事万物用它们自己的声音在说话,我们聆听着一切有生命的甚至无生命的造物的脉搏。这就构成了诗人和自然以及我们和诗人之间的真正的对话,“变成了语言的诗的结构保证了灵魂和世界作为有限东西相互诉说的过程”[(5)]。如果我们反过来审视一下广告语言,就会发现,诗意语言的这种品格不复存在了。在广告里,事物则完全变成了一种工具,不是事物自己在说话,而是商品的推销者在说话,这种话语旨在让人去消费物的有用性,于是,即使具有诗意的表达方式,说穿了不过是这些人的“叫卖声”而已。诗意的语言又一次被用来反对诗意的本质,潜藏在诗意语言之下的原本是一些强烈的拜物意识形态。
广告语言的诗意运用的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它典型的“得意忘言”的特征。诗的语言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它不但昭示了世界,同时还显现着自身。即是说,在诗意的语言中,人们不但把握了它所表现的世界,同时还体味着这种独特的语言自身的魅力,叹服于诗人驾驭语言的本领和鬼斧神功的创造。然而,在广告中,尽管诗意的手法司空见惯,可诗的语言的这种特征却荡然无存。广告语言的诗意模仿,主要目的是在传达一种商品信息的同时激发出受众的购买欲望。情感的诉求变成了一种功利性的物欲,而语言不再像诗的经验中那样处于前景,而是退到背景,处于前景的唯一角色只能是而且必须是商品。更有趣的是,在广告中,语言不仅自身处于后退的境地,而且,在电视、印刷等广告形式中,语言已经从主导的表达方式,蜕变为一种辅助性的提示语。即是说,在形象或影像的强大视觉冲击力面前,广告语言通常扮演着某种程度的“配角”,这和诗意语言的本质是绝对不相容的。我们在影像的诱惑面前,恰恰忘却了语言。
语言的“通货膨胀”
语言在我们这个时代迅速贬值了,这是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现象。而最典型的贬值语言也许就是广告语言。语言不幸也面临着“通货膨胀”。
在广告语言的急剧泛滥,特别是在语义的极限用法中,我们似乎可以清晰地辨别出一个相反相成的趋势:一方面,广告在语言的魅惑力发掘上可谓登峰造极,各种新的语言花样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广告语言的实际召唤力和作用力则在明显下降。我们时代的广告语言看来面临着一种修辞学的困境,越是注重修辞效果的广告,往往越是失去其效果。这就是语言的“通货膨胀”。语言的“贬值”,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只是广告语言的独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是我们时代较为普遍的语言病症,它广泛地体现在文学、艺术、社会日常生活语言以及其他方面。
广告语言的“贬值”有着许多内在的原因。原因之一是能指和所指的分离所导致的歧义。由于几乎所有的广告业主和客户都深信好的口号和语式有着强有力的作用,于是,在广告主题口号上刻意求新的倾向十分普遍。但一些令人莫名其妙的广告口号实际上却削弱了语言固有的作用力。能指和所指之间张力的断裂,使得广告语言的陌生化超出了受众的期待和接受水平,这种表述也就自然丧失了语言应有的意义和力量。原因之二是语言的“极限用法”,即不顾语言固有规则和使用条件,片面地强调大词句和最高级。正像文革时期“最、最、最……”的表达式异常流行一样,如今的“最新”、“最佳”、“最低价”一类的表述俯拾即是;而“画王”、“冷霸”、“帝豪”、“环球”、“国际”这样的大词更是屡见不鲜。其实,当所有的商品都冠之以“皇”、“帝”、“王”一类大而无当的词语时,所有的品牌就都有可能是“三等公民”。有了上述大词语的出现,就必须会有更大的词语尝试。“帝王”已是“寡人”了,于是只有“超霸”或“超……”才能高人一等。这种攀比和极限用法的递增,显然导致了语义的递减,进而使得语言本来所具有的某种意义判断在广告语式中不复存在,受众在疯狂的广告语言轰炸面前,已经出现了“神经魇足”。原因之三是广告语言中存在的互相抄袭和模仿,这构成了当前广告语言的一种特有的互文性语境。许多标题语或口号似曾相识,每当一种别出心裁的新的表达式出现,必然会有更多的同类表达接踵而至。类同的或大同小异的广告语言导致了受众见惯不惊,就像一种“抗药性”反应一样。第四个可能的原因是广告语言与其商品之间的差异,一方面是广告语言的过多承诺,另一方面是产品本身的各种问题与承诺不符。这就导致了广告语中人们深恶痛绝的“虚假语”现象。
广告语言“贬值”之能指和所指的断裂关系,还进一步表现为符号和对象以及广告和社会的紧张关系。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符号,广告语言正在演变成一种固定程式化的表达式。这里,新奇和俗套殊途同归,两者不过是同一符号的两个不同方面而已,正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对受众心理的研究,在不断地寻找有效的广告语言范式,大众传媒的威力,把各式各样地语式反复地强加给受众,社会的文化的群体的和个体的差异,在千篇一律的广告语式面前,正在丧失固有的区别。广告语言和社会的紧张关系还进一步反映为这种语言对其他语言的排斥功能,以及这种语言对受众的意识形态影响。语言的“贬值”是我们时代语言生态学的问题,它对社会以及自身的影响是深远的。每一个生活在大众传播时代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学会了用广告语言来思考,也不可避免地学会说广告语式。
注释:
(1) 奥格威:《一个广告人的自白》,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第79页。
(2) 参见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必要的张力》,中译本。
(3) 伽达默尔:《赞美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7页。
(4)(5)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72、80页。
标签:广告语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