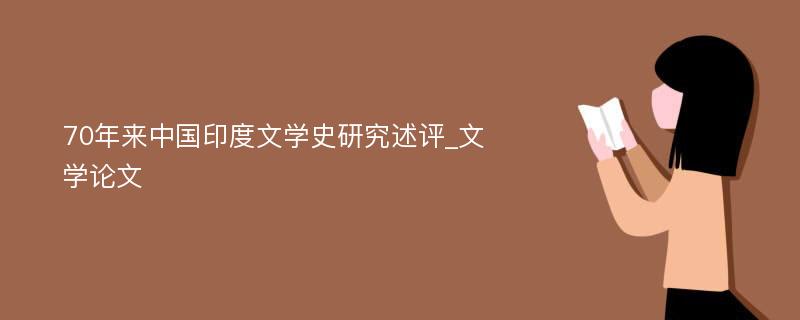
七十年来我国的印度文学史研究论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史研究论文,七十年论文,我国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印度文学史的困难性与重要性
研究印度文史,比起研究其它国家或民族的文学史,有着两个特殊的困难。困难之一是印度古来无“史”。由于宗教文化的高度发达,神话传说取代了历史学的功能,印度人对所崇拜的神及神化了的帝王将相的生平事迹,极尽想像和渲染,敷演出汗牛充栋的神话传说,并且信以为真,而视世俗层面的现实生活为虚幻不可靠,极为超越、解脱,因而根本不曾考虑记事为实,条缕为史。因此,作为世界四大古代文明的印度,却没有一部严格可信的历史学著作。这一点同中国文化、希腊文化形成了鲜明对照。直到近代,才有欧洲学者在考古、考证的基础上,参考古代中国及欧洲有关印度的记载,最先为印度人整理出“历史”来。而研究和撰写文学史著作也是18世纪以来西方人学术研究、文学研究的一种常用方式,据说印度最早的文学史也是西方学者写出来的。
现代中国人研究印度文学史的困难之二在于语言。公元10世纪以后,由于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印度社会自身的变化,作为宗教祭祀和学术语言而在几千年中被广泛运用的梵语,在印度逐渐式微,各地方语言随之逐渐兴起。如北部地区的乌尔都语、旁遮普语、信德语、克什米尔语,中北部地区的印地语、孟加拉语、奥里萨语、阿萨姆语、马拉提语、古吉拉特语,南部地区的泰米尔语、卡纳达语、泰鲁固语、马拉雅拉姆语等。这些形形色色的语言并不是人们所想像的一般意义上的方言,它们之间有相互的影响,但差异颇大,有些甚至属于不同语系。印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以后,英语又在文化水平较高的人群中间流行。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独立后的宪法不得不兼顾各方要求,将上述16种语言(包括英语)都确定为法定语言。一个统一的国家竟有这么多不同的法定语言,这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情况也给外国人学习印度的语言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近代以来,中国有不少有识之士都关注印度,有的希望借鉴印度沦为殖民地的“亡国”教训,有的寄希望于“佛教救国”,有的试图复兴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东方文化。他们都希望更多、更深入地了解印度,但都碰上了语言的屏障。近代著名文化人中,除章太炎、苏曼殊、许地山等极少数学者懂一些梵文之外,懂印度语言的人很少。当年鲁迅与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曾打算跟章太炎学习梵语,但上了几次课,便知难而退。康有为曾西游印度,并著有《印度游记》,但他并不懂印度语言。梁启超对佛教和印度文化很感兴趣,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但他也不懂印度语言。对此状况,梁启超在1920年曾感慨地说道:“隋唐以降,寺刹遍地,梵僧来仪,先后接踵,国中名宿,通梵者亦正不乏,何故不以梵语,泐为僧课?而乃始终乞灵于译本,致使今日国中,无一梵籍,欲治此业,乃藉欧师,耻莫甚焉。”直到30年代后,还是有少数学者,如陈寅格、季羡林等,“藉欧师”学习梵语,并成为现代中国研究印度文化与文学的中坚力量。建国后,北京大学设立了印度语言文学专业,培养了梵语、印地语、乌尔都语的专门人才,但一般每人只通晓其中一种语言。
尽管了解印度文学有着这些特殊的困难,但我国学者深知印度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与我国文学的密切关系。在过去上千年中惟一对中国文学产生很大影响的外国文学只有印度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博大精深,并且泽被周边诸国,但自东汉以降的上千年间却持续不断地接受印度文化与文学的影响,这足以表明印度古典文化与文学的巨大魅力,并足以激起现代中国人了解印度文学的冲动。而治中国文学史的学者,假如没有印度文学史的知识,就会对中国文学中的许多问题——如印度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问题、中国古代的翻译文学问题、印度声韵学与中国诗歌韵律的问题、梵剧与中国戏剧的起源问题、中国志怪、神魔小说与佛经故事问题,乃至于中国现代史上东西方文化优劣问题的论战与印度诗圣泰戈尔访华、泰戈尔与中国现代“小诗”的形成等等问题——不可能有深入的理解和把握。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学习西方文学(还有东方的日本文学)固然是时代大潮流,但不少学者和文学家们并没有忘记和忽视印度文学。
二、两种《印度文学》
要系统地阐述印度文学,广泛、全面地发表对于印度文学的看法,就必然要使用“印度文学史”这种著作形式。
于是,到了1930年,这样的著作出现了,那就是许地山的《印度文学》。此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0年初次出版,它的问世填补了学术空白,在当时学术界影响较大,因而它先后在1931年和1945年两次再版。它虽然未取名为“印度文学史”,而只叫作“印度文学”,但实际上是一部系统叙述从古代到近代印度文学发展进程的文学史著作。之所以不称“史”,也许是因为它在资料和篇幅上还没有达到足够的规模(全书仅六万五千字),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印度文学史的概论。此书在我国印度文学史研究领域的地位,是由它的开拓性所决定的。首先,在印度文学史的分期上,它作了这样的划分:
第一期 吠陀文学或尊圣文学
1.颂 2.净行书或奥义书 3.经书
第二期:非圣文学
1.佛教文学 2.耆那教文学
第三期 雅语文学
1.科学 2.赋体诗与往世书 3.寓言与戏剧 4.兴体诗 5.佛教文学
第四期 近代文学
1.雅语 2.俗语与外国语
这是一个简明扼要而又切实可行的划分方法。鉴于印度历史从朝代更替到作家生平等都是一笔糊涂帐,而文学作品大都不是作家个人的创作,而是逐渐累积、长期形成的,因此很难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坐标来将作品定位。像中国文学史著作那样按朝代更替作为划分文学史的根据是不可行的,只能将时间相对模糊化,大体按作品先后顺序及作品的类型来分期。许地山《印度文学》的这种文学史划分法,对后来的同类著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45年出版的柳无忌的《印度文学》,以至金克木的《梵语文学史》,都大体沿用了这样的方式。
许地山的《印度文学》作为第一部印度文学史著作,其中必然涉及到印度文学史的许多专门名词和术语的汉译问题。此前,我国历代翻译家翻译了大量佛教典籍,有些名词的翻译已经固定化,《印度文学》采用了不少这样的译词。但对于佛教文学之外的印度文学术语、名词,在没有借鉴的情况下,许地山不得不自行译出。这些名词术语的翻译,有不少为后来的学者沿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将四部《吠陀》本集分别意译为“赞颂明论本集”、“歌咏名论本集”、“祭祀明论本集”、“禳灾明论本集”。这里的“明”字取汉译佛典的含义,即许地山所解释的“知识”。这种意译使人望名会义,堪称巧妙。后来的一些学者(如柳无忌)仍然袭用许地山的这些译名。此外,“往世书”、“五卷书”等作品译名,以及后两者作品中的人名,如罗摩、悉多、难敌、坚阵(战)、广博等,也是首次译出并被后人沿用或部分沿用。还有一些名词,许地山使用了汉语文学中的相关名词来移译。例如,他把《吠陀》中颂神的抒情诗统称为“颂”,把“雅语文学”时期的抒情诗称为“兴体诗”,把叙事诗比做“赋体诗”,虽不尽恰切,但对于帮助我国读者理解印度文学还是不无裨益的。
不过,在对印度文学中某些重要体裁样式的表述方面,许地山的《印度文学》也有一些不够到位之处。例如,把吠陀文学称为“尊圣文学”,而把佛教文学和耆那教文学称为“非圣文学”。为什么这么界定?作者没有交待。他似乎是想说明:吠陀文学属于吠陀教——婆罗门教,它们在印度是正统教派,而佛教文学和耆那教文学都是反正统的,也就是“非圣”的。但这样区分显然有问题:吠陀教有吠陀教的“圣”,佛教和耆那教也有佛教、耆那教的“圣”,何况佛教、耆那教的兴起晚于吠陀上千年,所谓“尊圣”和“非圣”也就没有同一时间段上的对应性。另外,在对《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体裁性质的表述上也有些问题。从体裁上看,这两部作品是“史诗”。虽然“史诗”(epic)这个词来自西文,在印度和中国的传统文学中没有这一概念,但《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与希腊的荷马史诗完全同类,这在现在来说已是常识。但由于当时研究状况的局限,许地山对于两部作品并没有“史诗”的明确意识,在《印度文学》中甚至没有使用“史诗”这个词,而是分别使用“如是所说往世书”和“钦定诗”这两个概念来表达《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体裁性质。书中是这样表述的:“我们可以把印度的赋体诗分为两类,一类是《如是所说往世书》(Itihasa-puranas),一类是钦定诗(Kavyas),如是所说与我国古赋底体裁很相同,但在印度文学里,这个名词兼指历史、小说、寓言等作品而言。”他把《摩诃婆罗多》划归为“如是所说往世书”这一类,又说之所以把《罗摩衍那》称为“钦定诗”,是“因为这类诗的作者多半是与朝廷有关系的人,所以也名为‘钦定诗’或‘大诗’”。这里使用的似乎是印度固有的概念,但现在看来,“钦定诗”的说法并不确切,一是因为《罗摩衍那》原本是在民间神话传说的基础上经无数文人加工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渐成形的,很难断言为“钦定”;二是如果说“钦定”,印度的宫廷文学都可以说是“钦定”,并非只有《罗摩衍那》如此。由此可见,不从“史诗”的角度来认识《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这两部作品,就难以把握它们的根本性质。当然,作为中国印度文学史的开山著作,这些局限也是难免的,不好苛求作者。
许地山《印度文学》之后的第二部印度文学史著作是柳无忌的《印度文学》,1945年2月由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同年5月重印,1982年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再版。全书约14万字,篇幅超过《印度文学》一倍以上。柳无忌学西洋文学出身,印度文学并非他的专攻。据作者在联经版的后记中说,他之所以写这部书,是因为1920年在清华大学随父亲研究苏曼殊,是苏曼殊翻译的有关印度的诗歌激发他“神往印度文学”。其次是对泰戈尔的敬慕,由“对于这位近代印度诗人的敬慕,扩展到对应古代印度文物的憧憬”,由此下决心探寻印度文学中的珍贵宝藏。在资料来源方面,作者大量吸收了印度文学研究领域的英文材料,这从书后所列的18种英文书目就可以看出来。同时,柳无忌也受到了许地山的《印度文学》的多方面启发和影响。书中多次征引许著中的观点和材料,许多译名也采自许著,同时在许著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完善。例如,对于《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两部作品,柳著虽然沿用了许地山的“钦定诗”、“如是所说往世书”之类的提法,但他明确地把《摩诃婆罗达》和《罗摩衍那》作为“史诗”来看待,并论述了他们作为“史诗”的文学特征。再如近代文学部分,柳著大大拓展了论述的范围。对于泰戈尔,许著只有二三百字的篇幅,而柳著则作为全书的重点,着墨最多。柳著对于孟加拉短命女诗人陀露哆(1856-1874)高度重视,以单章的篇幅专门讲述,这似乎是受了苏曼殊的影响。陀露哆是苏曼殊所译介的为数不多的近代印度诗人之一,也是柳无忌通过苏曼殊的译文最早接触的印度诗人之一。但是现在看来,陀露哆在印度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像在柳著《印度文学》中那么高,后来出版的印度文学史著作中甚至连陀露哆的名字都找不到了。在最后一章《印度独立前后的文坛》中,柳无忌认为印度独立前后出现了三位杰出的作家,那就是乌尔都语诗人伊克巴(今译伊克巴尔)、英语诗人奈都夫人、以乌尔都语和印地语双语写作的小说家普雷姜德(今译普列姆昌德)。这是颇有见地的。
在研究与写作方法上,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本书的写作,侧重古印度文学的每一门的一二部代表作品。及近代印度文学的两位代表作家以为论述的中心,详细评介,而并非史的、综合的、概括的平行的叙述。”话是这么说,但全书还是以历史为经、以重点作家作品为纬的。它删繁就简,将头绪纷繁、内容庞杂的印度文学加以筛选和简化,用史的线索将重点作家作品的评述串连起来。它虽然还算不上是详实的印度文学史,但起码算得上是一部印度文学史简编。全书简明扼要,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印度文学的热爱之情,富有感染力,从框架结构到行文叙述都极为清晰明白,对于初学印度文学的读者尤其有益。在印度文学史各时期的划分上,柳著在许著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印度文学史的划分加以简化。许地山将印度文学史划分为四个时期,而柳无忌则把三千年来的印度文学分为三大时期,即吠陀文学时期、雅语文学时期、近代的白话地方文学时期。作者解释说:“第一为吠陀文学,约自西元前十世纪至西元后一世纪,这一千多年的文学完全是宗教文学。第二期始于西元一世纪,以迄西元十二世纪回教徒入侵之时,可称为雅语文学”;而12世纪以后,“在印度文学史上是一个较为黑暗的时代,一直到西元16世纪后,近代的白话地方文学渐渐兴起……”。这样的三分法固然将印度文学史简明化了,但也造成了许多不该有的遗漏。如在印度文学史上占重要地位的佛教文学就被排除在外了。虽然作者在讲述《五卷书》时简单交待了印度的民间文学,但民间文学并不等同于佛教文学。他一方面承认佛教文学非常丰富,但又认为佛教文学中“极少抒情的纯文学作品,说教示范的性质重而想像的成分少,不如吠陀颂那样可视为印度文学主流。”实际上,印度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渗透着宗教意识,只是程度不同、表现方式有别罢了,不能单以宗教性质作为印度文学史上作家作品轻重取舍的主要依据。
三、梵语与印地语文学专史
上述两种《印度文学》虽然都是文学史性质的著作,但作者不称其为“史”,除了作者的谨慎和谦虚之外,还在于它们在篇幅规模和研究深度上基本还是为了适合普及的需要。建国后的60年代初,严格意义上的印度文学史著作出现了。首先问世的是金克木的《梵语文学史》。
《梵语文学史》是金克木6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印度语言文学专业使用的教材,196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978年再版。全书近30万字,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的梵语文学史,也是第一部由通晓梵语的人以第一手材料写成的梵语文学史,第一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印度文学史。它的资料丰富详实,内容全面系统,论述严谨,分析透彻,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梵语文学史体系,确立了梵语文学史的基本内容,从阅读原作入手,对作家作品特别是重点作家作品作了透彻的阐释和独立的评价,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当然它也带有它写作与出版的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记。
金克木将梵语文学史的时期划分为“《吠陀本集》时代”、“史诗时代”、“古典文学时代”三个阶段,并根据这三个阶段将全书分为三编。这种划分法与上述许地山、柳无忌的划分法有明显的继承关系。所不同的是,《梵语文学史》将这三个时期分别与列宁、斯大林的社会阶段划分理论联系起来,将《吠陀本集》时代称为“原始社会和阶级社会形成时期的文学”,将“史诗时代”称为“奴隶社会的文学”,将“古典文学时代”称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文学”。作者在书的前言中很清楚地意识到,关于印度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例如“究竟印度的奴隶社会起于何时,又在何时发展到封建社会,这个过渡时期有多久,有什么样的特点和过程,各地先后差别如何,这类问题,几乎人言人殊”。但尽管存在这样的困难和问题,作者还是在梵语文学史的划分中努力体现马列主义的观念和方法。但与此同时,也明显地暴露出将这两者生硬结合的痕迹。实际上,在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马克思从未主张将东西方各国纳入一个简化的统一概念模式中。马克思将以古代印度为典型的亚洲社会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且认为:“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的政治变化多么大,可是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注: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5页。)既然几千年中印度社会状况“没有改变”,那么对印度历史划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有多大意义?《梵语文学史》努力以马列主义分析问题的另一个表现就是阶级分析。这从全书的标题目录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第二编和第三编的第一章都交待了文学的时代背景,也都强调了印度文学与阶级斗争的密切关系,甚至将两大史诗及吠陀文献、佛教、耆那教文学概括为“反映阶级斗争的庞大文献”,这显然反映了6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气候的影响。此外,作者还努力以马列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理论作为评价作家作品的主要依据,在论述和评价两大史诗、《五卷书》、迦梨陀娑的戏剧等主要作家作品的时候,作品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是作者的主要视角,而实际上,印度文学(当然包括上述作品)的主导倾向是超越现实生活的、形而上的、冥想性的、神话式的、非现实主义的。从书中的许多具体论述中可以看出,作者非常清楚印度文学的这种特点,但他没有将这种特点充分地展开来论述,而往往将它们归结为“唯心主义”并加以贬抑。
因此,《梵语文学史》既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也有着鲜明的中国现代学术的特色。金克木在书的前言中明确地表述了中国学者的这种自觉追求:“印度人写自己的古代文学史,虽有西方的影响,毕竟离不开传统背景及用语及民族观点。西方人写的也脱不了他们心目中的自己的传统及观点。写本书时,我也时常想到我国的古代文学,希望写成一本看出来是我国人自己写的书。”作者完全实现了这一目标。从这一点来看,《梵语文学史》的“时代性”又是与它的中国学术特色密切相连的,因而我们似乎还不能简单地视之为“缺点”,而应更恰当地视其为“特点”。另外,这种“中国特点”还表现为作者自觉的中印文学比较意识。由于作者对中国古代文学也同样熟知,在书中的许多地方都可以发现作者有意将印度文学与中国文学作比较,虽然通常是三言两语,却富有启发性。
梵语文学实际上在公元12世纪以后就已经结束了它的历史。金克木的《梵语文学史》也大体写到12世纪为止。12世纪以后取代梵语文学的是各地方语言的文学。在各种方言文学中,较为重要的是印地语文学。1987年,刘安武的《印度印地语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成为继金克木的《梵语文学史》之后又一部以某一语种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印度文学史。据作者自述,所谓“印地语文学”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界定。狭义的印地语文学是指以梵语的天城体字母书写的流行于德里地区的克利方言文学,到18世纪才出现书面文献;而广义的印地语文学是指印地语语系文学,即克利方言及很接近克利方言的另外十几种方言的文学。《印地语文学史》取的是广义的印地语文学的概念,它从10世纪后开始写起,写到1947年印度独立为止。全书28万余字,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全面的印地语文学史。在文学史时期的划分上,《印地语文学史》综合吸收了印度同类著作的长处,设计了一个对中国读者来说清晰简要的分期法,将印地语文学分为初期(1350年以前)、前中期(1350-1600)、后中期(1600-1857)、近代(1857-1900)和现代(1900-1947),并分六章分别讲述。每章的第一节均为“概述”,交待该时期印地语文学的背景和概况,以下各节则分别讲述重点作家作品。本书作为作者在北京大学东语系的讲义,在体例上采用的是典型的教科书写法,但由于它是我国第一部印地语文学史,书中所述大都为前人所未发,因而有着较高的学术品位。《印度印地语文学史》所提到的作家作品,除了普列姆昌德的多篇小说和杜勒西达斯的长诗《罗摩功行之湖》等少数作家作品在《印度印地语文学史》问世前后有译介之外,大都至今还没有译本。因此,这部印地语文学史既填补了学术上的空白,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又是一本启蒙书。
1988年,北京的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黄宝生撰写的《印度古代文学》。这实际上也是一部梵语文学史,但其中论及与梵语并不完全相同的中古时期的俗语文学。所以按作者的准确表述,这本书所研究的是“古代和中古印度雅利安语文学”。全书约十万字,大体按历史顺序和文学样式分别设12个专题,即:一、绪论,二、吠陀文学,三、两大史诗,四、往世书,五、佛教文学,六、耆那教文学,七、俗语文学,八、古典梵语诗歌,九、古典梵语戏剧,十、故事文学,十一、古典梵语小说,十二、梵语文学理论。由此可见其论述的范围已包括了印度雅利安语文学的方方面面。这本书的特点是简明扼要,深入浅出,不失为一本高水平的印度古代文学的入门书。只可惜印刷装帧粗陋,印数也只有一千册,影响了它在一般读者中的传播和影响。
四、综合性多语种印度文学史
我国80年代以前的印度文学史研究著作,或是个人的专著,或是单一语种的文学史。但是,古代印度文学是多语种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系统。因此,完整的印度文学史应该是多语种文学的综合史。但是,要撰写这样的一部文学史,必须具备几个基本的条件。第一,由多语种的印度文学专家学者形成一个研究群体;第二,对印度古代文学研究的成果积累应达到一定程度。进入80年代后期,这样的条件基本形成了。季羡林教授带领他的学生,组成了一个印度文学史的写作班子。1991年,他主编的《古代印度文学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共有五编,43万余字,从公元前15世纪一直写到19世纪中叶。第一编“吠陀时期”,第二编“史诗时期”,第三编“古典梵语文学时期”,第四编“各地方语言文学兴起的时期”,第五编“虔诚文学时期”。五编共计32章,每编第一章均为“概论”,交待时代背景和文学概况,以下各章以各时期的文学类型和主要作家作品为论述中心。此书集中地展示了我国学者在印度古代文学研究上的成绩和实力。季羡林在前言中说:“本书是集体协作的产物,主要是北京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间的协作。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研究印度文学的基础,较之解放前或五六十年代,当然要好多了。但是总起来看,仍然是比较薄弱的。我们写作时,尽量阅读原作,至少是原作的翻译,这是写一部有创见的文学史必不可少的步骤。但是,有许多印度语种目前在中国还是空白,我们不得不利用其他语言的材料。这对本书的质量当然会有影响。然而话又说回来,能直接阅读这样多的原文而写出的印度文学史,在我国还是第一部,我们也可以稍感自慰了。”
作为主编,季羡林的这段话是对《印度古代文学史》的恰当的自我评价。虽然这本书在文学的年代划分、写作体例等方面,与此前的文学史大同小异,并无多大创意,但是,在“多语种”——多语种的印度古代文学和多语种的研究专家——这一点上是空前的。而且,每位作者所执笔的部分,一般都是有专门研究和前期成果的。如作为《罗摩衍那》的翻译者,季羡林撰写了《罗摩衍那》的部分;作为《摩诃婆罗多》的翻译主持者和古典梵语文学研究专家,黄宝生负责撰写了《摩诃婆罗多》和古典梵语文学的大部分章节;佛教文学专家郭良撰写了佛教文学部分;泰米尔文学专家张锡麟执笔泰米尔文学部分;印地语文学专家刘安武执笔撰写有关印地语文学的部分;乌尔都语文学专家李宗华执笔撰写了有关乌尔都语文学部分。其中,季羡林本人撰写的《罗摩衍那》一章,吸收、精编了他自己的专著《〈罗摩衍那〉初探》(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年)中的材料和观点;黄宝生撰写的梵语文学部分,将他的《印度古代文学》一书的大部分相关内容做了移植和修订;刘安武撰写的印地语文学部分,大部分内容也来自他的《印度印地语文学史》。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印度古代文学史》基本上是一部“编著”。而且虽然并不称为教材,但其写法明显具有教材的性质。尽管如此,以几个主要语种的印度古代文学为内容,编写成一本完整的《印度古代文学史》,这本身就具有重要的价值。虽然上述语种的文学并不是印度古代文学的全部(例如10世纪以后出现的、在印度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孟加拉语文学就很少被提到),但它基本还是一本比较完整的印度古代文学史。有了这本书,读者就可以进入古代印度文学的天地中揽胜探奥,把握印度古代文学的大体面貌了。
《印度古代文学史》的下限到19世纪中叶。据季羡林在前言中透露,他们本来是要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印度文学史》的,但由于近代和现代部分“缺的稿子还多”,所以临时决定先出一部《印度古代文学史》,时间的下限是19世纪中叶。一直到1998年底石海峻的《20世纪印度文学史》问世之前,印度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在我国一直是空白。
《20世纪印度文学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持的“20世纪外国国别文学史丛书”的一种,由青岛出版社出版。
由于受外来的英语语言文学的冲击,由于印巴、印孟的分治等政治事件的影响,20世纪印度文学呈现出更加纷纭复杂的局面,再加上20世纪还没有完全结束,许多文学现象还有待于时间的沉淀和过滤,因而一个中国学者在世纪末为印度写一部本世纪文学史,难度可想而知。但石海峻知难而进,他主要凭借英语和印地语的材料,写出了以孟加拉语文学、印地语文学两种语言文学为重点并兼及其它各语种的、内容比较全面的20世纪印度文学史,从而在事实上衔接于季羡林主编的《印度古代文学史》,使我国的印度文学史研究涵盖古今,大体完备。
研究和撰写《20世纪印度文学史》,除了语言、材料上的困难之外,最大的困难大概就是为百年来的印度文学理出一个清晰的线索。作为一部体例上统一的印度文学史著作而不是多语种的印度文学史简编,就必须在充分了解各语种文学的基础上,抽绎出贯穿各语种文学的理论线索,从而构筑起文学史的框架体系。石海峻以20世纪印度文学思潮在各地区、各语种文学中的生成、演变为基本线索,以对代表某一时期、某一语种文学成就的大作家的创作活动的评述为中心,构建自己的文学史框架。全书23万字,分为18章,每章相对独立,但18章内部又有一条贯穿到底的、时间推移与理论逻辑相统一的线索。从19世纪中期的启蒙、复兴
运动写起,接着依次写到20世纪初期的民族主义和神秘主义诗人奥罗宾多等作家,大文豪泰戈尔,20年代兴盛的浪漫主义文学,穆斯林哲理诗人伊克巴尔,孟加拉语作家萨拉特,在甘地主义影响下的普列姆昌德等现实主义文学,30年代孟加拉文学中的现代派,萨拉特之后的三位孟加拉语小说家,三四十年代影响全印度的进步主义文学(左翼文学),印度独立前后的其他小说家,40年代出现的实验主义诗歌,五六十年代的新诗派与新小说派,50年出现并延续到80年代的边区文学,以克里山·钱德尔为代表的社会现实小说,70年代以后的“非诗派”和“非小说派”,80年代后的女性主义文学,印度的英语小说,等等。作者站在文化的多元性与统一性辩证结合的学术立场上,既强调不同语种、不同时期印度文学的差异,更在这种差异性中寻求统一。对不同的作家作品、不同文学现象的分析,也采取了不同的文学批评视角,并不用单一僵硬的文学价值观作笼统的评判。这显示了当代青年学者在学术上所具有的广阔的视野和开放的观念。同时,这样的观念和立场确保了全书作为文学史著作有着比较清晰的逻辑和历史线索。不过,由于印度语文学史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要将所有的重要材料都纳入一个严谨的理论框架内是困难的。如本书最后两章,即第17章“女性文学与贱民文学”和第18章“印度英语小说”,是分别以作者类型和语种来分立成章的,而全书其它各章都是以思潮流派及重点作家为中心构架起来的。这两章就容易给人以游离于全书框架之外的感觉。总体看来,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为20世纪的印度撰写的这部文学中,在学术上的勇气和开创意义是值得称道的。
纵观我国的印度文学史研究,从1930年许地山的《印度文学》问世,到1998年石海峻的《20世纪印度文学史》出版,其间走过了近70年的历程。这70年的研究成果,将为下一世纪我国的印度文学及文学史研究的开拓、深化和繁荣提供可贵的经验。
标签:文学论文; 许地山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读书论文; 艺术论文; 印地语论文; 佛教论文; 罗摩衍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