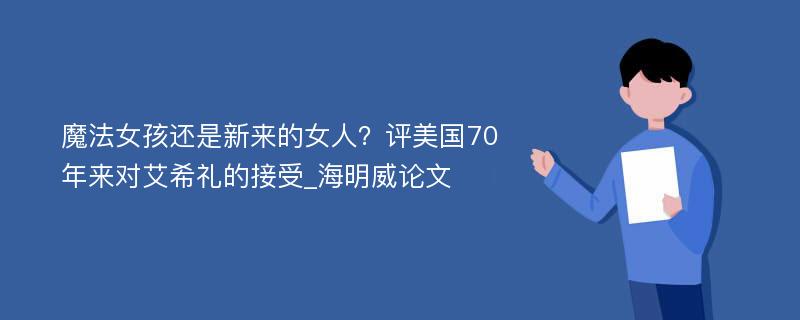
魔女还是新女性?——评70年来勃莱特#183;阿施利在美国的接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魔女论文,莱特论文,年来论文,在美国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作为文学形象的勃莱特·阿施利于1926年10月22日诞生于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注:Ernest Hemingway,The Sun Also Rises,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Scribner Library Books Edition,1954.赵静男译《太阳照常升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 本文的引文均出自这两个版本。)(以下简称《太阳》),至今已有73年。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七十多年来勃莱特·阿施利在美国的接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太阳》既是海明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又是他的成名作,但在中国却未受到评论界应有的重视。邱平壤早在1990年就指出,《太阳》不但中译本出得晚,而且“专题研究的文章至今尚无”。(注:邱平壤《海明威研究在中国》,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77页。)最近,董衡巽再次指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美国评论界对《太阳》的重视超过其他三部作品”;但“它在中国不及其他三部小说有影响。”(注:董衡巽《国外海明威研究的新成就》,《外国文学动态》,1998年第6期,第15页。)笔者认为,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 美国学者安德鲁·胡克(Mandrew Hook)说:
(《太阳》)是所有海明威小说的原型,是最纯正、最地道的海明威作品。……我并不想说自《太阳》出版之后,海明威的创作就一直走下坡路。但确实可以这么说,在经过漫长的探索之后,《太阳》和他早期的短篇小说终于建立起典型的海明威世界和典型的海明威创作手法。自那以后,海明威只不过是在那限定的世界里漫游,而不是超越。(注:Andrew Hook,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Vol.61,Detroit:Gale Research Inc.,1990,p.215.)
可以这么说,不读懂《太阳》,就不可能真正读懂海明威。因此,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70年来勃莱特·阿施利在美国的接受作一简要回顾,以利于我们更好地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并希望能引起中国学者对《太阳》的更多关注。
二
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34岁的勃莱特漂亮而有气质,虽结过两次婚,对男人仍很有吸引力,围着她团团转的共有六位男性:杰克·巴恩斯、罗伯特·科恩、米比波普勒斯伯爵、比尔·戈顿、迈克·坎贝尔和罗梅罗。米比波普勒斯伯爵和比尔·戈顿是她的崇拜者,其余四人与她有直接的感情纠葛,而其中的三人与她有过性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太阳》是关于一个女人和六个男人的情爱故事。
在《太阳》出版后的20年间,即30到40年代,在海明威研究领域里没有出现鸿篇巨制,到了50年代,卡洛斯·贝克打破了这一局面,1952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海明威:作为艺术家的作家》成为这一领域里的权威性声音,该书第四章第三节的小标题是“魔女和她的伙伴”,意指勃莱特和书中的几位男性,尤其是与她有过爱情或性关系的四位男性。在这一节中,卡洛斯·贝克将勃莱特和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魔女作了比较。俄底修斯在远征特洛亚后乘船返回故乡,途经太阳神的女儿、美丽的魔女喀耳刻(Circe)(注:Circe本是太阳神的女儿的名字,后意指善于引诱男人的女人,通常译为魔女、女巫、妖精或迷人精等。目前国内在翻译时,作为专有名词时多数根据其发音译为“喀耳刻”,作为代词时则有多种译法。本文采用“魔女”这一译法。)居住的埃埃厄岛。魔女在酒里掺下毒药,把俄底修斯的手下变成了一群猪。俄底修斯在天神赫耳墨斯的指点和帮助下,以智慧和利剑战胜了魔女,救出了自己的部下。(注:荷马《奥德赛的故事》,黄建辛、荣开珏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第25—32页。)
在《太阳》中,勃莱特自始至终都处于支配地位,颇似魔女喀耳刻。杰克虽丧失了性能力,但并没有丧失男子气概,在这一意义上,他是这群男子中的俄底修斯。小说中,勃莱特、迈克和杰克三人有这么一段对话:
“嗨,勃莱特。告诉杰克,罗伯特称呼你什么来着。你知道,妙极了。”
“啊,不行。我不能说。”
“说吧。都是自己朋友。我们都是好朋友吧,杰克?”
“我不能告诉他。太荒唐了。”
“我来说。”
“别说,迈克尔。别傻啦。”
“他叫她迷人精(Circe),”迈克说。 “他硬说她会把男人变成猪。妙哉。可惜我不是个文人。”(Hemingway,p,144,赵静男译本,第158页)。
据此,卡洛斯·贝克提出诘问:
难道勃莱特·阿施利在她那塞纳河畔低洼的岛屿上不也正是这样一位美丽动人的危险人物,就像埃埃厄岛上的魔女那样?她不也是打开自己的大门,迎接所有的现代希腊男子?当他们喝了她特制的法国苹果酒或西班牙葡萄酒等迷魂酒之后,他们不也是变成猪,或者用现代的习语来说,变成色鬼吗?杰克·巴恩斯,那狡猾的俄底修斯,不也是抵挡住了这可耻的厄运?而这一厄运不也是落到了他的一些不那么谨慎的朋友头上,使他们变成了嗷嗷叫的野兽吗?(注:Carlos Baker,Hemingway:The Writer as Artist,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Fourth Ediion,1972,p.87,p.90.)
他又进一步抨击道:
追求精神刺激驱使勃莱特从一个酒吧到另一个酒吧,从一个男人投向另一个男人,她的滥交……只会越来越多,正如喝一次酒就会喝第二次一样,周而复始,不能停止。勃莱特对于她所认识的男人来说是个不“好”的人。(注:Ibid.,p.112.又见董衡巽编选《海明威研究》(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4页。 笔者对原译文有修改,以下凡引自同一书名的均出自这一版本。)
贝克的结论是:“总而言之,她是该进地狱的致命的30岁的女人。”(注:Carlos Baker,Hemingway:The Writer as Artist,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Fourth Ediion,1972,p.87,p.90.)魔女一说从此确立,贝克也因此而成为“魔女说”的代表人物,Circe 一词成为勃莱特的代名词。 与Circe 一词交替使用的还有另外一个词:bitch,意为坏女人或者淫妇,是勃莱特在离开罗梅罗之后, 向杰克解释原委时连用三次的一个词。常与勃莱特联系在一起的词还有一大串,诸如坏女人、坏女神、女巫、迷人精、女妖、破坏性的、摧毁性的、非常有害的、致命的等等。最后,她还获得了这样一个称谓:“20年代致命的女人”。(注:Harold Bloom,ed.,Brett Ashley,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91,p.2,inside front cover.)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埃德蒙·威尔逊、菲利普·扬、约瑟夫·沃伦·比奇、莱斯利·菲德勒、约翰·奥尔德里奇、 马克·斯毕尔卡等。(注:RogerWhitlow:"Bitches and Other Simplistic Assumptions",in BrettAshley,p.149.)
由于Circe和bitch这两个词均源于海明威原著,而海明威塑造的多是硬汉人物,他给人的印象也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因而人们便推测他试图通过塑造一个坏女人的形象来表达自己对女人的偏见。加之持“魔女说”的几乎都是久负盛名的海明威专家,他们的观点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并引用,勃莱特便成为文学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女人之一。她的恶名之大,使后来的一些评论者即使没有认真阅读过海明威的原著,也可以很方便地把勃莱特端出来,作为坏女人的典型而加以批判。
三
到了6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发展,海明威一时成了众矢之的,成为许多评论家的“头号敌人”,他的作品在课堂里也不像以前那么热了,(注:Rena Sanderson,"Hemingway and Gender History,"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rnest Hemingway,ed.,Scott Donalds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71.)他的声誉滑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对于这种现象, 在海明威评论界颇有影响的学术期刊《海明威评论》(The Hemingway Review)的女主编苏珊·比杰尔(Susan F.Beegel)作了以下分析:
当潜在的读者把海明威当作对少数民族漠不关心、对妇女采取敌视态度的作家而加以排斥的时候,这往往不是对海明威小说的一种反应,而是对早期一些海明威评论者的这种漠不关心和敌视态度的一种反应,是对早期那些有影响的海明威崇拜者无意之中制造出来的具有负面影响的作者形象的一种反应。正像菲利普·扬的“准则英雄”(code hero )理论使后来的评论者难以用其他方法来解释海明威一样,早期的一些海明威读者无意识的固执和偏见,使后来的一些读者根本不可能再接近海明威。(注:Susan F.Beegel,"Conclusion:The Critical Reputationof Ernest Hemingway,"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rnest Hemingway,p.277;p.282,pp.290-291,p.293;pp.286-287.)
这段相当中肯的评论指出了海明威研究中的一个误区:即早期一些经典评论家的评论影响太大,以致成为一种固定的批评模式,后人很难摆脱其影响,他们未经消化、未经自己的独立思考就接受了这些现成的结论,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导致海明威研究的停滞不前。
然而,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对海明威的批评和质疑导致了对他作品的重读和重新评价,它关系到海明威能否赢回女权主义批评家的支持,恢复自己原来的中心地位。(注:Rena Sanderson, "Hemingway and Gender History,"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rnest Hemingway,ed.,Scott Donalds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71.)
但真正从根本上动摇了“魔女说”统治地位的新成果到了80年代中后期才陆续问世。初期的作者多是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女性,与持“魔女说”的德高望重的男性学者相比,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不是对手。然而,由于她们立论新颖,说理充分,材料丰富,很快就赢得许多人的支持,其中包括耶鲁大学著名教授、资深学者哈罗德·布鲁姆。新观点认为,勃莱特不是什么“魔女”,而是西方20年代的一位新女性。其主要论点可以归纳如下:
首先,勃莱特是一个历史人物,对她的评价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本世纪20年代,工业革命已经相当深入,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庭,和男子一样参加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批男子上了前线,留下的工作空缺由妇女顶替,加强了妇女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经济地位的改善促进了政治地位的提高,20至30年代,西方出现了本世纪以来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高潮。当时仅巴黎一地,就拥有八十多个女权组织,有成员六万多人。(注:Wendy Martin,"Brett Ashley as New Woman in The Sun Also Rises,"in New Essays on The Sun Also Rises,ed.,Linda Wagner-Mart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68.)英国议会于1918年、美国国会于1920年分别通过法案,使英美妇女在经过漫长斗争之后,终于赢得了选举权。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变化,使妇女的道德观和价值观随之也发生变化。当时一方面是强调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妇女积极参政,另一方面由于受到战后人们对政治的厌倦、1920年在美国实行禁酒令后人们对政府的反感、战后美国经济的空前繁荣、“分期付款”消费方式的首次推广等因素的影响,在许多人当中滋长了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自我放纵的思想,有人把这一时期称作“爵士乐时代”。正是在这样一个广阔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西方迎来了第一代抽烟喝酒、以离婚来结束不幸婚姻、独立意识较强的妇女。勃莱特就是其中一个,她的身上充满着时代矛盾,既有追求个人幸福、独立意识较强的一面,也有自我放纵、及时行乐的一面。只有把勃莱特置于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她的一些举止行为才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
其次,勃莱特虽然有缺陷,甚至是严重的缺陷,但从总体上来说,仍不失为一位新女性。她具有一切新女性所具有的基本品质:思想独立,不受传统观念约束,不愿受男人支配,敢于标新立异,敢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大胆追求个人的自由与幸福。
女学者西比·奥苏莉文(Sibbie O'Sullivan)批评了卡洛斯·贝克等人的双重标准, 指出当他们指责勃莱特和科恩、罗梅罗睡觉时,并没有同时也批评科恩和罗梅罗。她还批评了马克·斯毕尔卡的“严肃的爱情”已经死亡的结论,指出他的所谓“严肃的爱情”只不过是要维护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性角色罢了。(注:Sibbie O'Sullivan,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Vol.61,Detroit:Gale Research Inc.,1990,pp.230—232.)
然而,由于学术信息交流不畅,许多新的研究成果没能及时介绍进来,以卡洛斯·贝克和马克·斯毕尔卡为代表的观点一直在我国学术界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例如,李加伦认为勃莱特属于“短发型的独立破坏型女人”(注:李加伦《海明威的“头发情结”——试论海明威的妇女观》,见《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第23—31页。), 于冬云则认为勃莱特是“魔女”,属于“不道德、诱惑男人、对男人的主体位置起破坏作用的女人。她们的存在对男人的主体意识是一种直接的威胁,甚至使男人的境况变得更糟。”(注:于冬云《对海明威的女性解读》,见《外国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第74—80页。 另请参看刘荣强《90年代国内海明威研究述评》,见《国外文学》,1999年第3期,第28—33页。)很明显,这些看法带有卡洛斯· 贝克和马克·斯毕尔卡的影子。
其实,不管海明威在其他作品中有无轻视妇女的倾向,至少在《太阳》中他对妇女是尊重的,勃莱特并不像他的大多数作品中的女人那样只是男人们的陪衬,而是海明威精心塑造并寄予同情的一个极富个性的女性形象。《太阳》原稿开头中有15页的文字,后来根据菲兹杰拉德的建议删去了。原稿中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一部关于一位女士的小说。她的名字叫阿施利夫人……”(注: ErnestHemingway,
"The Unpublished Opening of The Sun Also Rises,"in Brett Ashley,p.5.)这说明塑造勃莱特是海明威的本意, 勃莱特才是这部小说的第一主人公。另外,有研究表明,《太阳》的素材源于海明威1925年在西班牙潘普洛纳的旅行经历,当时同行的有他的第一任妻子哈德莱(Hadley)和几位好友。 在旅行中经朋友介绍, 他认识了达夫·托斯顿夫人(Lady Duff Twysden),一位英国籍的交际花, 被她的美貌和放荡不羁的气质所吸引。后来事情虽然没有进一步发展,但海明威和达夫·托斯顿夫人之间确实有过这么一段短暂的情缘。可以说,杰克·巴恩斯身上有着海明威本人的影子,而勃莱特的原型则是达夫·托斯顿夫人。杰克对勃莱特的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寄托了海明威对达夫·托斯顿夫人的感情。(注:Bernice Kert,The Hemingway Women,New York:W.W.Norton& Company,Inc.,1986,pp.161—164.)
最后,勃莱特绝非美国文学史上在性生活和思想方面都非常激进的第一位女性。在她前面完全可以开列出长长的一系列名字:霍桑《红字》中的海斯特·白兰(Hester Prynne)、 福雷斯特《雷维尼尔小姐从退却到忠诚的转变》中的拉雷夫人(Mrs Larue)、 哈罗德·弗雷德里克《西伦·沃尔的诅咒》中的西莉亚·玛顿(Celia Madden)、凯特·肖班《觉醒》中的埃德娜·庞特利尔(Edna Pontellier)、 斯蒂芬·克莱恩《街头女郎梅秀》中的内莉(Nellie)、哈姆林·加兰《达切尔谷的罗斯》中的罗斯·达切尔(Rose Dutcher)、德莱塞《嘉莉妹妹》中的嘉莉·米巴(Carrie Meeber)等。 只要我们将勃莱特置于美国文学史的背景下作纵向比较,立刻就可以发现,勃莱特并不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全新人物,也不是这些新女性群像中最激进的一个。与她们比较起来,勃莱特在某些方面显得太保守了。
通过对背景、人物形象、作者的创作意图以及与美国文学史上同类人物的对比等方面的分析,一个虽然迷惘有缺陷但深得海明威本人同情、仍不失为新女性的勃莱特,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四
《剑桥海明威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rnest Hemingway,1996)和《勃莱特·阿施利》(Brett Ashley,1991)的出版,使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案暂告一个段落。这两本书中的多篇论文都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即由卡洛斯·贝克提出来的“魔女说”正日益显出其局限性,逐步成为一个历史概念,对勃莱特更准确的描述恐怕应当是:西方20年代一位迷惘的、追求时髦的新潮女性。
这两本书均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前者是很有影响的“剑桥文学指南”丛书中的一本,由美国著名的海明威专家斯科特·唐纳德森( ScottDonaldson)选编,主要介绍90年代海明威研究各个方面的最新成果, 涉及勃莱特的地方不少。后者是由哈罗德·布鲁姆选编的“世界主要文学形象”(Major Literary Characters)丛书中的一本, 布鲁姆认为,文学形象是文学中最重要的要素,研究文学首先要研究文学形象。在这套丛书中,一般是每一位作家只选一个被认为最成功、最能代表其思想和艺术成就的文学形象,例如哈姆雷特、堂·吉诃德、安娜·卡列尼娜、哈克·费恩、赫索格等。而在海明威塑造的人物形象中,惟独选中了勃莱特,可见在布鲁姆眼中,勃莱特最能代表海明威的创作成就,是可以与哈姆雷特、堂·吉诃德等相媲美的不朽的文学形象。该书主要围绕勃莱特这一文学形象,追溯在这一研究领域里的历史发展概况,将各个时期的代表性文章汇编成书,并由布鲁姆本人亲自作序,对70年来的论争作一小结。最简明扼要、能一针见血地总结争论焦点的是印在该书封二中的一段文字:
勃莱特·阿施利夫人,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中的非正统派女主角,到底是一个酒鬼、荡妇、仇视男人的“魔女”,还是一个因一战后心灵受伤、胸积郁闷而浪迹于20年代的巴黎,与一些放纵自我的人们为伍,追求时髦,寻找安慰的移居国外者?
……卡洛斯·贝克将勃莱特比作“魔女”,这种解释受到了哈罗德·布鲁姆和其他一些评论者的质疑。 (注:Harold Bloom,ed.,Brett Ashley,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91,p.2,inside front cover.)
五
一个文学形象不仅是它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缩影,同时也是后来时代发展的一面镜子。70年代来在美国围绕着对勃莱特·阿施利所进行的论争绝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的背后隐匿着深刻的社会变化。
从魔女到新女性,从经典结论到最新研究成果,反映了观念、研究方法和研究者队伍的变化。在观念上,男权意识受到批判,“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双重标准遭到摒弃;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年轻人,尤其是对过去的年轻人的道德评判采取一种更为宽容的态度,不再像以前那样严厉和苛求。在研究方法上,逐步从单一走向多元,卡洛斯·贝克在《海明威:作为艺术家的作家》中所运用的较为单一的象征主义批评逐渐让位于后来的女权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社会文化批评以及其他批评方法。
研究者队伍的变化恐怕是最引人注目的,也是导致整个评论界对勃莱特的态度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最重要的因素。自60年代以来,海明威研究者队伍中的女性比例逐年提高。据统计,60年代,海明威女学者只占研究者队伍的7%,70年代上升到13%,短短十年间几乎翻了一番。 到了90年代初,29%的海明威评论由女性撰写。到2000年,也许这一数字要攀升到50%。(注:Susan F.Beegel,"Conclusion:The CriticalReputation of Ernest Hemingway,"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Ernest Hemingway,p.277;p.282,pp.290—291,p.293;pp.286—287.)一批很有发展前途的女学者脱颖而出,成为学科带头人。例如,密执安州立大学的女学者琳达·瓦格纳(Linda W.Wagner)自70年代以来先后编辑和撰写了《50年来的海明威批评》、《海明威研究参考书目索引》、《60年来的海明威批评》和《〈太阳照常升起〉新论文集》等多部较有影响的论文集和专著。 (注: Linda W. Wagner,ed.,Ernest Hemingway:Five Decades of Criticism,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4; Ernest Hemingway:A Reference Guide,Boston:G.K.Hall,1977;Ernest Hemingway:Six Decades of Criticism,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 New Essays on The Sun Also Ris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90 年代中期她被选为美国海明威研究会主席,成为这一世界性组织的第一位女主席。另一位女学者伯尼斯·克尔特 (Bernice Kert)撰写的专著《海明威的女人》( The HemingwayWomen,1986)在评论界亦有一定影响。女学者苏珊·比杰尔在列举九位“当今海明威研究界家喻户晓的学者”时,就把琳达·瓦格纳和伯尼斯·克尔特包括在内。(注:Susan F.Beegel,"Conclusion:The
Critical
Reputation of Ernest Hemingway,"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rnest Hemingway,p.277;p.282,pp.290—291,p.293;pp.286—287.)
女学者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使海明威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得到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纠正了早期一些评论家对海明威的误读以及他们自己对女性的偏见。相当一部分女学者的研究揭示了事物的另一面:在以张扬男子汉气概为己任的大男子主义者的形象后面,海明威也不时表现出对妇女的同情,也有塑造得比较成功的女性形象,譬如勃莱特。他既不是一个只会写“没有女人的男人”的作家,也不是一个只会写两种女人(具有破坏性的女人和温顺的女人)的作家。他所创造的文学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任何过于简单、片面的结论都不免有失公允。
女权主义运动竟然更多地是给海明威带来正面的影响,这恐怕是许多人始料不及的。
标签:海明威论文; 文学论文; hemingway论文;
